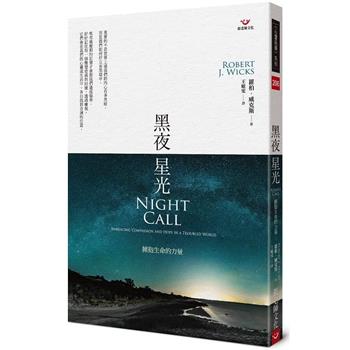妥善照顧自己很簡單
如果生命是一架班機,而你錯過了,怎麼辦?──沃克‧柏西(Walker Percy)
我想任何人連看三場足球賽,都應該宣告死亡。──爾瑪‧邦貝克(Erma Bombeck)
如果我們願意在每日的邂逅或相處中領受智慧與重要的人生教誨,這樣的智慧很可能來自於其他人,有時在我們最料想不到的時候出現。我在思考如何用簡單務實的方法執行自我照顧時,便遇到這種情形,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照顧別人的人往往最不善於照顧自己。本章前面引述了爾瑪‧邦貝克一句奇怪卻很真實的話,這位作家還提到,許多照護者似乎都缺少一份照顧自己的活動」選單﹂,按部就班照顧自己。因此,我們只靠著容易取得的心理或精神食糧生存下去。結果就是像冥想、與朋友互動、獨處時間這一類更新的因素,變成了奢侈,而不是必要、妥善安排的心靈補品。
我三十來歲時遇到了轉折點,開始實現自我更新。那時我住在賓州的西徹斯特(West Chester),在布林莫爾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研究」研究所教書,也在位於利頓豪斯廣場的診所執業,每週日必須去賓州蘭卡斯特市的某間醫院巡視病房,而面對這麼多事務,我很快就體力不支了!
然後我接到一通電話,是住在紐約的老友打來的。我是他婚禮上的伴郎,但之後我因工作去了別的城市,他也搬家了,慢慢不再聯絡。我們已經超過十年沒有好好聊天了,我聽到他的聲音極為高興,立刻認出是他,感覺得到他也很高興重新聯繫上我。他先找話聊,問我過得如何,工作上正在忙什麼。我熱切地跟他分享自己正在做的每一件事──除了當大學教授、寫書之外,還為專業助人者和醫療人員提供諮詢,到處演講,幫助大家了解何謂韌性。我告訴他,這是我真心喜愛的工作,因為它讓我接觸到心理學、精神病學、社會工作、諮商、神職、教育、醫學與護理等領域的一流人才與新手。
我喜愛協助本身壓力很大的助人者,但工作極其繁重,包括時間長、常去其他國家出
差,尤其是我擔心自己受到的影響,在在使我身心俱疲。
我講了一陣子自己的近況,最後問他:「欸,弗列德,你最近怎麼樣?」他用幾乎不帶感情的口吻回答:「嗯,鮑伯,其實我快死了。」因為我們才三十幾歲,他又那麼有活力──即使在講電話的當下也一樣—我聽了嚇一大跳,用難以置信的口吻問他:「你快死了?你說『你快死了』是什麼意思?」
「唔,鮑伯,我有個叫『星細胞瘤』(astrocytoma)的東西,是一種罕見的腦癌。我母親覺得我會遇到奇蹟,但人很清楚自己快死了。我快死了,鮑伯。」
我花了好些時間才消化這個消息,於是我們倆沉默了一會兒,最後我才問道:「弗列德,你在哪裡打電話?」
他回答:「賓州的慈愛醫院。」
我很訝異,他居然不在紐約市。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他其實離我很近。我說:「慈愛醫院?你離我住的地方只有四十分鐘欸,要不要我去看你?」
「會不會很麻煩?」他問。
「不,一點也不麻煩。」我對他說。
「嗯,你什麼時候要來?」
「就是現在。」我一字一字地說。
我走下樓,很快跟太太說明情況,告訴她要離開幾個小時,便跳上車朝賓州駛去。
我在弗列德的房間待了一會兒就知道,就算他相信自己快死了,他還是當初那個驚世駭俗的傢伙,就住在紐約市皇后區、我家對面的街上。因此,我知道他不希望我因為他現在這樣,而有所不同。我必定從頭到尾都沒忘記這一點,因為當我問他有何症狀,他說有兩個很惱人的症狀──他憋不住尿,所以得包尿布,而且也喪失了短期記憶,所以完全不記得自己住進醫院這兩個星期以來的事。對此,我回他說:「嗯,失去記憶真的太悲慘了。」他露出不解的表情問道:「我忘記在這裡發生的事有什麼悲慘可言?」
而我立刻回他:「因為你不記得我過去兩個星期,每天都坐在床邊陪你六小時呀。」
他怔住了,但不消片刻就回了我一句粗鄙不堪的話,至今回想還會笑出來。他那時正需要我跟他說笑。他一直以來都在面對深知事態嚴重、非常緊張的家人和朋友,反而幫不上他的忙。從他的神情和在床上稍見輕鬆的舉止,我看得出他知道自己可以跟老友自在聊天,無須讓老友感到放心,正如許多人面對身旁的人承受巨大苦痛時(像弗列德這樣),反而需要病人的安撫。等我們平靜下來,開始彙報近況。講完他目前的情況,以及上次見面後彼此的生活,他問了我一個問題,我原本以為只是隨口問問:」嗯,你這幾年在做的事,哪一件算是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在電話裡以及見面的第一個小時,已經仔細聊過這幾年發生的事,我以為他是指我最自豪的成就,便開始細數。
他不快地朝我揮了下手,立刻表示他感興趣的不是這個,同時告訴我:「不不,不是那個。是重要的事。」
「弗列德,那我就不知道你指的是什麼了。」
「鮑伯,重要的事情。」他慢慢說出這幾個字,彷彿是在對英語不是母語的人講話,需要花時間在心中翻譯剛才聽到的話才能夠回答。然後他開始拋出一連串問題:
告訴我你每天安靜散步的情景。
你最喜歡哪幾間博物館?
你最近看過什麼書?電影呢?
你去哪裡釣魚?
跟我說說你最親近的一群朋友,他們發自內心給你什麼樣的勸告,以免你行差踏錯?
你知道,就是重要的事。
我必須承認,我坐在那裡目瞪口呆。眼前是一個快要死去的人,照他的預感很快就沒辦法像我這樣享受人生了,而他在教導我怎麼生活,進行自我照顧,更別忘記在生命尚未消失時,活得淋漓盡致。後來我讀到醫生作家沃克‧柏西的小說,其中問了這麼一句話:「如果生命是一架班機,而你錯過了,怎麼辦?」便想起這次會面的情景。
我也會反覆想起他問到我的那群好友,裡面有誰?他們給我什麼樣不同的聲音,好幫助我達成生活的平衡?我會從他們那裡聽到符合當下情況的質疑言詞,或充滿鼓勵、啟發或幽默的論點嗎?日後,我會在文章和演說中分別形容這些朋友是:問你「生命中有哪些引導你的聲音,或許你不曾察覺」的預言家;不管我做過什麼,都會給予我同情與支持的啦啦隊;當我出發去尋找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物,幫助我認清自己繞遠路,反而把自己看得太嚴重的騷擾者或取笑者;以及最後那個給我啟發的朋友,要我只做自己、盡其在我,卻從不讓我難堪,指出我那時還不夠成熟的心理狀態。
但最使我心頭一震的是他要問的最後一個問題。待我講完正在進行的「自我更新」和有趣的事,以及用各種不同方式使我的生命更豐富的人們後,他說:「我其實還想再問你一件事。」
「弗列德,什麼事?」
「如果你不想回答,就不要回答。」
「是什麼事,弗列德?」我又問一次。
「要不是我快死了,我也不會問。」
最後,我往椅背上一靠,問道:「是什麼事?」
「嗯,就像我說的,我快死了卻不害怕。」
「你不怕?」我問。
「不會,但我覺得自己很快就要進入廣大的寂靜,而我記得你每天早上固定撥時間出來安靜獨處,專注於感恩。如果你能告訴我在你靜默的時刻發生了什麼事,我想可以幫助我面對死亡。」
如他所說,在這之後幾個月他便死了,而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次的交談。它是最有力的提醒,要我記得為自己擬定自我照顧方案,必須切實可行,涵蓋所有生活層面,思考周全,並且可以透過某種方式立刻執行。我開始意識到,就算所謂的運動只是每天靜靜散步,我也會獲益。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下班後覺得是灰色的,往往並非因為那天突然發生不愉快的事,而是某些辦公大樓內的空氣不流通所致,每天散個步可以紓解這種情況。我還可以刻意思考目前常吃的食物,確保自己不是有什麼就吃什麼。
我需要想清楚哪些人算是好朋友,又發出什麼不同的」聲音」,幫助我保持昂揚、清醒、能屈能伸,而且充滿希望。最後,替自己規劃涵蓋全面的自我照顧方案時,我需要確保我有安靜的時間進行更新、反省、調整,隨時了解自己,只要呼吸,對於空氣或人生都不要貪多務得。
我老是陷入生活匆忙的模式,以期做完每一件」重要的事」,覺得這樣才叫務實、自然,而且是有必要的。但一如往常,人生會給我們一記警鐘,我記起了一位年邁的拉比被問到他多年來在猶太會堂擔任神職,學到了什麼。他想了一會兒,便說他很少看到不負責任的人,反而常碰到忙個不停的人,而且若不是有安息日,根本就不會享受他們獲賜的人生,並為此感謝。
聽到他這麼說,當我有病人取消預約,我便將這段時間送給同樣重要的人:我。我拿出一張紙,動手列出我認為應該納入自我照顧方案的各種要素,盡可能既切實、有創意,而且範圍廣泛。我這麼做,並不是寫完以後就放進抽屜,覺得自己完成了某件事。我這麼做,是讓自己察覺到一個事實:如果我不照顧自己,沒人會來照顧我。如果我等日後再來好好活,永遠不會有那一天。使我訝異的是,這份清單並不算極端,但仍然夠廣泛,我忍不住自問為什麼不多多享受這些活動。在我死前,我打算什麼時候享受自己的空間,好好滋養自己?當我拿出這張清單檢視,雖然已經看過許多次,其中一些條目仍觸動我心:
‧ 靜靜散步。
‧ 找到零碎的獨處時間,好讓自己稍微放鬆,獨自安靜思索。
‧ 讀十分鐘左右的小說,或傳主的生平能夠激勵我的傳記。
‧ 好好和朋友聊個天,不管是面對面、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
‧ 聽幾首過去喜歡但這陣子沒聽的老歌。
‧ 逛逛附近的公園或博物館。
‧ 路過書店時進去瀏覽一番,喝杯拿鐵。
‧ 大聲朗讀詩句。
‧ 背靠著坐墊,坐在床上看晨間新聞。
‧ 種一個小花園,裡頭有多年生以及一年生植物,這樣我既可以看著種下去的植物凋零後再次開花,也可以想些別的點子裝飾花園。
‧ 午餐時間在城裡走走。
‧ 每天臨睡前寫日記,記下當天發生的事(客觀),以及我有何感受(主觀),以便多了解自己一些。
我即將再次領悟到,照這張清單去做並非只為了自己:
我能夠和他人分享的最重要天賦之一,是我自身的平靜、正面健康的觀點、盡量避免僵化的生活方式︙︙但要是我自己沒有,就沒辦法分享了。
探視完弗列德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益發明白自我照顧為心理帶來的好處,包括靜默的時刻與正面的友誼,是透過人生的不同情況與發展階段,更充分理解我正在變成什麼樣的人,這一點我在日後也時有領悟。但如此大的覺悟需要付出更多注意,不管是醫療或助人領域的專業人士,或只是想用更好的方式默默支持家人或朋友的給予者,我們每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得仔細觀察、評估自己才行。
無論我是獨處,或在進行心理治療、給予指引,抑或督導臨床心理師或其他專職助人者的時候,我發現將這幾個人生階段視為三趟」內在旅程」,對我和其他人都有幫助。我自己和其他人如何航行度過,尤其是第三趟旅程,真的相當發人深省──不光是他們如何幫助案主,也在於他們如何享受人生經驗,並從中獲益。此外,在自我反省或指引他人時,有一項令人意外的要素,是極少人重視並充分表達敬意的長處與美德,那就是平凡。
如果生命是一架班機,而你錯過了,怎麼辦?──沃克‧柏西(Walker Percy)
我想任何人連看三場足球賽,都應該宣告死亡。──爾瑪‧邦貝克(Erma Bombeck)
如果我們願意在每日的邂逅或相處中領受智慧與重要的人生教誨,這樣的智慧很可能來自於其他人,有時在我們最料想不到的時候出現。我在思考如何用簡單務實的方法執行自我照顧時,便遇到這種情形,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照顧別人的人往往最不善於照顧自己。本章前面引述了爾瑪‧邦貝克一句奇怪卻很真實的話,這位作家還提到,許多照護者似乎都缺少一份照顧自己的活動」選單﹂,按部就班照顧自己。因此,我們只靠著容易取得的心理或精神食糧生存下去。結果就是像冥想、與朋友互動、獨處時間這一類更新的因素,變成了奢侈,而不是必要、妥善安排的心靈補品。
我三十來歲時遇到了轉折點,開始實現自我更新。那時我住在賓州的西徹斯特(West Chester),在布林莫爾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研究」研究所教書,也在位於利頓豪斯廣場的診所執業,每週日必須去賓州蘭卡斯特市的某間醫院巡視病房,而面對這麼多事務,我很快就體力不支了!
然後我接到一通電話,是住在紐約的老友打來的。我是他婚禮上的伴郎,但之後我因工作去了別的城市,他也搬家了,慢慢不再聯絡。我們已經超過十年沒有好好聊天了,我聽到他的聲音極為高興,立刻認出是他,感覺得到他也很高興重新聯繫上我。他先找話聊,問我過得如何,工作上正在忙什麼。我熱切地跟他分享自己正在做的每一件事──除了當大學教授、寫書之外,還為專業助人者和醫療人員提供諮詢,到處演講,幫助大家了解何謂韌性。我告訴他,這是我真心喜愛的工作,因為它讓我接觸到心理學、精神病學、社會工作、諮商、神職、教育、醫學與護理等領域的一流人才與新手。
我喜愛協助本身壓力很大的助人者,但工作極其繁重,包括時間長、常去其他國家出
差,尤其是我擔心自己受到的影響,在在使我身心俱疲。
我講了一陣子自己的近況,最後問他:「欸,弗列德,你最近怎麼樣?」他用幾乎不帶感情的口吻回答:「嗯,鮑伯,其實我快死了。」因為我們才三十幾歲,他又那麼有活力──即使在講電話的當下也一樣—我聽了嚇一大跳,用難以置信的口吻問他:「你快死了?你說『你快死了』是什麼意思?」
「唔,鮑伯,我有個叫『星細胞瘤』(astrocytoma)的東西,是一種罕見的腦癌。我母親覺得我會遇到奇蹟,但人很清楚自己快死了。我快死了,鮑伯。」
我花了好些時間才消化這個消息,於是我們倆沉默了一會兒,最後我才問道:「弗列德,你在哪裡打電話?」
他回答:「賓州的慈愛醫院。」
我很訝異,他居然不在紐約市。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他其實離我很近。我說:「慈愛醫院?你離我住的地方只有四十分鐘欸,要不要我去看你?」
「會不會很麻煩?」他問。
「不,一點也不麻煩。」我對他說。
「嗯,你什麼時候要來?」
「就是現在。」我一字一字地說。
我走下樓,很快跟太太說明情況,告訴她要離開幾個小時,便跳上車朝賓州駛去。
我在弗列德的房間待了一會兒就知道,就算他相信自己快死了,他還是當初那個驚世駭俗的傢伙,就住在紐約市皇后區、我家對面的街上。因此,我知道他不希望我因為他現在這樣,而有所不同。我必定從頭到尾都沒忘記這一點,因為當我問他有何症狀,他說有兩個很惱人的症狀──他憋不住尿,所以得包尿布,而且也喪失了短期記憶,所以完全不記得自己住進醫院這兩個星期以來的事。對此,我回他說:「嗯,失去記憶真的太悲慘了。」他露出不解的表情問道:「我忘記在這裡發生的事有什麼悲慘可言?」
而我立刻回他:「因為你不記得我過去兩個星期,每天都坐在床邊陪你六小時呀。」
他怔住了,但不消片刻就回了我一句粗鄙不堪的話,至今回想還會笑出來。他那時正需要我跟他說笑。他一直以來都在面對深知事態嚴重、非常緊張的家人和朋友,反而幫不上他的忙。從他的神情和在床上稍見輕鬆的舉止,我看得出他知道自己可以跟老友自在聊天,無須讓老友感到放心,正如許多人面對身旁的人承受巨大苦痛時(像弗列德這樣),反而需要病人的安撫。等我們平靜下來,開始彙報近況。講完他目前的情況,以及上次見面後彼此的生活,他問了我一個問題,我原本以為只是隨口問問:」嗯,你這幾年在做的事,哪一件算是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在電話裡以及見面的第一個小時,已經仔細聊過這幾年發生的事,我以為他是指我最自豪的成就,便開始細數。
他不快地朝我揮了下手,立刻表示他感興趣的不是這個,同時告訴我:「不不,不是那個。是重要的事。」
「弗列德,那我就不知道你指的是什麼了。」
「鮑伯,重要的事情。」他慢慢說出這幾個字,彷彿是在對英語不是母語的人講話,需要花時間在心中翻譯剛才聽到的話才能夠回答。然後他開始拋出一連串問題:
告訴我你每天安靜散步的情景。
你最喜歡哪幾間博物館?
你最近看過什麼書?電影呢?
你去哪裡釣魚?
跟我說說你最親近的一群朋友,他們發自內心給你什麼樣的勸告,以免你行差踏錯?
你知道,就是重要的事。
我必須承認,我坐在那裡目瞪口呆。眼前是一個快要死去的人,照他的預感很快就沒辦法像我這樣享受人生了,而他在教導我怎麼生活,進行自我照顧,更別忘記在生命尚未消失時,活得淋漓盡致。後來我讀到醫生作家沃克‧柏西的小說,其中問了這麼一句話:「如果生命是一架班機,而你錯過了,怎麼辦?」便想起這次會面的情景。
我也會反覆想起他問到我的那群好友,裡面有誰?他們給我什麼樣不同的聲音,好幫助我達成生活的平衡?我會從他們那裡聽到符合當下情況的質疑言詞,或充滿鼓勵、啟發或幽默的論點嗎?日後,我會在文章和演說中分別形容這些朋友是:問你「生命中有哪些引導你的聲音,或許你不曾察覺」的預言家;不管我做過什麼,都會給予我同情與支持的啦啦隊;當我出發去尋找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物,幫助我認清自己繞遠路,反而把自己看得太嚴重的騷擾者或取笑者;以及最後那個給我啟發的朋友,要我只做自己、盡其在我,卻從不讓我難堪,指出我那時還不夠成熟的心理狀態。
但最使我心頭一震的是他要問的最後一個問題。待我講完正在進行的「自我更新」和有趣的事,以及用各種不同方式使我的生命更豐富的人們後,他說:「我其實還想再問你一件事。」
「弗列德,什麼事?」
「如果你不想回答,就不要回答。」
「是什麼事,弗列德?」我又問一次。
「要不是我快死了,我也不會問。」
最後,我往椅背上一靠,問道:「是什麼事?」
「嗯,就像我說的,我快死了卻不害怕。」
「你不怕?」我問。
「不會,但我覺得自己很快就要進入廣大的寂靜,而我記得你每天早上固定撥時間出來安靜獨處,專注於感恩。如果你能告訴我在你靜默的時刻發生了什麼事,我想可以幫助我面對死亡。」
如他所說,在這之後幾個月他便死了,而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次的交談。它是最有力的提醒,要我記得為自己擬定自我照顧方案,必須切實可行,涵蓋所有生活層面,思考周全,並且可以透過某種方式立刻執行。我開始意識到,就算所謂的運動只是每天靜靜散步,我也會獲益。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下班後覺得是灰色的,往往並非因為那天突然發生不愉快的事,而是某些辦公大樓內的空氣不流通所致,每天散個步可以紓解這種情況。我還可以刻意思考目前常吃的食物,確保自己不是有什麼就吃什麼。
我需要想清楚哪些人算是好朋友,又發出什麼不同的」聲音」,幫助我保持昂揚、清醒、能屈能伸,而且充滿希望。最後,替自己規劃涵蓋全面的自我照顧方案時,我需要確保我有安靜的時間進行更新、反省、調整,隨時了解自己,只要呼吸,對於空氣或人生都不要貪多務得。
我老是陷入生活匆忙的模式,以期做完每一件」重要的事」,覺得這樣才叫務實、自然,而且是有必要的。但一如往常,人生會給我們一記警鐘,我記起了一位年邁的拉比被問到他多年來在猶太會堂擔任神職,學到了什麼。他想了一會兒,便說他很少看到不負責任的人,反而常碰到忙個不停的人,而且若不是有安息日,根本就不會享受他們獲賜的人生,並為此感謝。
聽到他這麼說,當我有病人取消預約,我便將這段時間送給同樣重要的人:我。我拿出一張紙,動手列出我認為應該納入自我照顧方案的各種要素,盡可能既切實、有創意,而且範圍廣泛。我這麼做,並不是寫完以後就放進抽屜,覺得自己完成了某件事。我這麼做,是讓自己察覺到一個事實:如果我不照顧自己,沒人會來照顧我。如果我等日後再來好好活,永遠不會有那一天。使我訝異的是,這份清單並不算極端,但仍然夠廣泛,我忍不住自問為什麼不多多享受這些活動。在我死前,我打算什麼時候享受自己的空間,好好滋養自己?當我拿出這張清單檢視,雖然已經看過許多次,其中一些條目仍觸動我心:
‧ 靜靜散步。
‧ 找到零碎的獨處時間,好讓自己稍微放鬆,獨自安靜思索。
‧ 讀十分鐘左右的小說,或傳主的生平能夠激勵我的傳記。
‧ 好好和朋友聊個天,不管是面對面、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
‧ 聽幾首過去喜歡但這陣子沒聽的老歌。
‧ 逛逛附近的公園或博物館。
‧ 路過書店時進去瀏覽一番,喝杯拿鐵。
‧ 大聲朗讀詩句。
‧ 背靠著坐墊,坐在床上看晨間新聞。
‧ 種一個小花園,裡頭有多年生以及一年生植物,這樣我既可以看著種下去的植物凋零後再次開花,也可以想些別的點子裝飾花園。
‧ 午餐時間在城裡走走。
‧ 每天臨睡前寫日記,記下當天發生的事(客觀),以及我有何感受(主觀),以便多了解自己一些。
我即將再次領悟到,照這張清單去做並非只為了自己:
我能夠和他人分享的最重要天賦之一,是我自身的平靜、正面健康的觀點、盡量避免僵化的生活方式︙︙但要是我自己沒有,就沒辦法分享了。
探視完弗列德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益發明白自我照顧為心理帶來的好處,包括靜默的時刻與正面的友誼,是透過人生的不同情況與發展階段,更充分理解我正在變成什麼樣的人,這一點我在日後也時有領悟。但如此大的覺悟需要付出更多注意,不管是醫療或助人領域的專業人士,或只是想用更好的方式默默支持家人或朋友的給予者,我們每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得仔細觀察、評估自己才行。
無論我是獨處,或在進行心理治療、給予指引,抑或督導臨床心理師或其他專職助人者的時候,我發現將這幾個人生階段視為三趟」內在旅程」,對我和其他人都有幫助。我自己和其他人如何航行度過,尤其是第三趟旅程,真的相當發人深省──不光是他們如何幫助案主,也在於他們如何享受人生經驗,並從中獲益。此外,在自我反省或指引他人時,有一項令人意外的要素,是極少人重視並充分表達敬意的長處與美德,那就是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