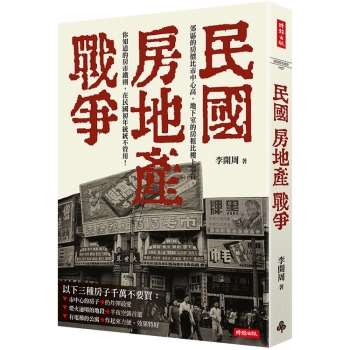緣起:為什麼寫這本書?
佛家講因緣,認為諸法皆由因緣和合而生。換句話說,無論一個東西的形成,還是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因為某些因素很偶然地湊到一起來了。
我原本是學理工的,畢業後做測量和預算,還參與過一些地方的土地規劃,是一個沒有編制的技術人員,平日最大的樂趣,是寫各種各樣的小程式。比方說工作時需要把測量誤差合理分配到圖紙上去,而利用現有的軟體做不了這個工作,我就寫一個「平差計算器」,完了把所有座標導入,一敲回車,問題解決了,於是關機,於是傲然四顧,瞧著同事們還在加班,幸福感油然而生。在那時候,我的理想是考一個資格證,做專業的程式師,從來也沒想過有一天會寫文章,更沒想到去寫書,即使想寫,也不會寫《民國房地產戰爭》這樣的書,因為興趣和特長都不在此,不具備寫這類書的機緣。
大約是2005年,專業程式師的理想還沒實現,上班前,有個師兄拿份報紙向我顯擺:「瞧,我太太編的報紙!」那是某家報紙的副刊,上面刊登的全是小品文,那個師兄的夫人正是那個副刊的責編。我看了以後說:「這樣的文章我也會寫啊!」他不信,我就寫了一篇,讓他轉給了他太太,結果發表了。我很興奮,感覺寫文章不比寫程式難,還有稿費拿,就繼續寫下去。寫了大半年,在網上看見北京一家報紙找人寫專欄,我準備了四篇稿子發過去,編輯認可了,從此開始給這家報紙寫專欄,每週寫兩期,每期一千字,每月稿費三、四千塊錢。
2006年5月,我連續拿了大半年的稿費以後,把工作辭了,開始專職寫作,做職業撰稿人,同時給四五家報紙寫專欄。專欄需要固定的選題,我花了很長時間琢磨國內報紙的版面,發現所有的選題都有人在寫,除了「房地產歷史」這一塊。房地產屬於經濟領域,我念大學時就對經濟感興趣;歷史則是我的閱讀偏好,打小就喜歡。所以我就選了「房產史」作為以後寫專欄的主攻方向,從此每天跑圖書館,翻讀正史,翻讀野史,翻讀墓誌,翻讀方志,翻讀別人輯錄的契約文書,翻讀古代名人的信劄、日記、行狀、年譜和詩集,從中尋找跟房地產有關的部分,抄錄下來,回去慢慢研究。
中國古人重視歷史,但是不重視數字,關於地價和房價的文獻,關於不動產交易的記載,鴉片戰爭以前似乎從來就沒有專書問世,要想從浩瀚古籍裡把握以往樓市的輪廓和細節,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但惟其不輕鬆,做起來才更有「技術含量」,作為一沒錢財二沒地位只有通過炫耀技術來滿足虛榮心的老派青年,我願意花力氣閱讀海量文獻,並從中發現一些別人不願意關注或者不屑於關注的東西。我一邊發現,一邊把那些發現寫成專欄,就這樣給新京報寫了兩年半的「千年宅事」,給深圳商報寫了兩年的「千年房事」,給南方都市報寫了一年半的「民國房事」。
在民國時代生活了大半生的齊如山先生說過治學的方法(雖然他不是學者):「大家總是靠著幾本圖書,皓首窮經,一輩子不管別的事情,其實真正研究經學,永遠不會離開社會。如顧亭林為研究經學,各處去訪問,郝蘭皋著《爾雅義述》,也多靠實地調查。若要研究一國的政治,更是需要察看社會中的情形及政治的實際,才能洞知其真相,若研究其法律及公文等,那是不能真知道,且是絕對靠不住的。」我非常佩服齊如山先生的見地,所以就借鑒他的話,相信研究「房產史」同樣離不開社會。所以從2007年開始,我試著通過不同途徑跟開發商接觸,譬如說給他們做樓書,或者給他們的雜誌寫專欄,或者借風水話題跟策劃部的人深聊一陣子,目的就是盡可能弄清楚現代樓市是怎麼回事兒,以便對古代樓市有更深的理解。因為我相信我們都是古人詐屍,都是今之古人,時代雖然變了,我們自私、奸詐、愚昧和鼠目寸光的人性沒有變。
在跟開發商接觸的過程中,聊起我所知道的古代樓市,並把以前寫過的《千年樓市:穿越時空去古代置業》(這是2009年寫的一本書)給他們看,他們很感興趣,有位說:「民國離我們最近,你怎麼不寫寫民國的房價啊?」我怦然心動。那時是2010年,出版界正猛刮民國風,我感覺寫這樣一本書既結合時代熱點(房地產),又符合出版潮流(民國熱),值得一寫。
於是重點搜集與民國樓市相關的文獻,邊搜集邊整理,兩年以後,有了《民國房地產戰爭》這本書。
我想,假如不是單位裡那個師兄炫耀他媳婦做的版面,我想不到去投稿;假如當初不投稿,我不會知道寫專欄也可以作為謀生手段;假如寫專欄不能謀生,我不會有時間泡圖書館;假如不泡圖書館,我沒辦法從各種文獻裡整理出「房產史」的輪廓;假如不整理出「房產史」的輪廓,我不可能去寫《千年樓市:穿越時空去古代置業》那本書;假如不寫那本書,開發商不可能建議我寫民國房價;假如沒有人建議我寫民國房價,我絕對沒有動力來寫這本《民國房地產戰爭》。這就是佛家說的因緣。
書名:為什麼叫「戰爭」?
這本書是寫民國房地產市場的,直白一點兒的書名,應該叫《民國房地產》,為什麼又在後面加上「戰爭」兩個字呢?原因有三:
一、民國是個經常打仗的時代,那時候過日子離不開戰爭,房地產市場也離不開戰爭。
比方說,很多地方樓市正火,一炮打過來,土著出逃,移民返鄉,有房的低價拋售,沒房的不再認購,房價和地價像燒餅上的芝麻一樣簌簌往下掉,新建商鋪空關,在建住宅停工,開發商債臺高築,房地產市場崩盤;還有很多地方本來沒多少購房需求,就因為其他地方都在打仗,這裡成了和平孤島,難民像潮水一樣湧過來,有錢的四處買房,沒錢的四處租房,把這裡的房價和房租抬高了,把這裡的樓市捧紅了。
甭說房價、地價和房租經常受戰爭影響,就是民國人的居住習慣也深受戰爭影響。很多民國人為什麼寧可租房也不買房?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怕辛辛苦苦大半生買下的一所房子被一個炸彈炸成平地,那時候保險公司又不包賠,豈不虧大了?所以無論有錢人還是沒錢人,每到一個城市定居,都是租房的多,買房的少。
民國人的這種居住習慣進而又影響了房產商的開發模式。在民國,建成房屋對外出售的房產公司極為少見,無論是不遠萬里來中國淘金的猶太開發商,還是本小利薄租地建房的本土開發商,也無論是開發商業地產,還是開發住宅專案,大家都偏好於出租而不是出售,因為這樣才迎合消費者需求。而消費者為什麼會偏愛租房而不是買房呢?因為老是有戰爭。
您說,戰爭對民國房地產市場影響如此之大,幹嘛不給這本書取名叫《民國房地產戰爭》呢二、「戰爭」這個詞能迎合多數讀者的閱讀偏好。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天生喜歡看熱鬧,尤其喜歡看打架,只要流的不是自己的血,只要交戰雙方的血不濺到自己身上,打架都能給人一種極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滿足。如果您喜歡交戰雙方的某一方的話,還能把自己代入進去,在觀看的同時設想是自己在打架,把另一方打得頭破血流跪地求饒,於是自豪感鋪天蓋地。因為這些緣故,武俠小說曾經很火(便於把自己代入),戰爭大片一直很火(打架的場面很大,很熱鬧)。所以我想,《民國房地產》一定沒有《民國房地產戰爭》吸引眼球。
靠書名來吸引眼球,是「標題黨」的一貫做法,我對標題黨沒好感,可是書市上每年湧現那麼多新書,要是連書名都不能吸引眼球,大夥連翻開看一眼的興趣都不會有,是吧?
三、在這本書之前,已經有好多書以「戰爭」為名了。
您上網搜一下,《貨幣戰爭》、《糧食戰爭》、《歐洲貿易戰爭》、《中國房地產戰爭》……琳琅滿目,俯拾皆是。這些書,內容跟戰爭幾乎無關,但都綴了「戰爭」的尾巴,我非始作俑者,不用怕有人罵。再說了,我這本書談的核心內容就是戰爭對民國樓市的影響,標題很切實,更不用怕有人罵。
從天地會說起
金庸武俠小說裡有個天地會,總舵主叫陳近南,麾下幫眾十幾萬人,勢力遍佈大江南北,藏龍臥虎,高手如雲,殺官劫獄,反清複明,做下了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歷史上確實有個天地會,但陳近南只是這個幫會的遙遠傳說,而且他還是個和尚(並不是武俠小說裡那個英俊瀟灑的中年書生)。金庸說陳近南原來的名字叫陳永華,陳永華是有的,他是鄭成功的手下,以文治見長,不會武功,更沒有創辦過天地會 。
從清政府公佈的奏章和邸報來看,天地會成立於乾隆年間(金庸小說裡的天地會在康熙年間就已經很活躍了),先是在廣東和福建一帶活動,後來轉戰臺灣,在臺灣發動抗清起義,「所過之處香案疊疊」(天地會「順天大盟主」林爽文的告示),受到了臺灣人民的大力支持。臺灣人拿起鐮刀加入天地會,佔領城市,驅趕貪官,剪掉髮辮,改換服式,臺灣一時變色,大半個島嶼納入天地會控制之下。為撲滅這場起義,乾隆動用了廣東、廣西、福建、貴州、浙江、湖南、四川七個省的軍隊,消耗的軍費占了全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這場起義失敗之後不到五年,臺灣南路和臺灣北路又先後爆發了兩次起義,也都由天地會發起。到了嘉慶七年,廣東惠州天地會首領蔡步雲起義。嘉慶十一年,廣東潮州天地會首領張四田起義。嘉慶後期,從天地會衍生出「平頭會」和「紅花會」(這是金庸《書劍恩仇錄》和《飛狐外傳》裡反復提到的一個大幫會),分別在廣東、福建、新疆、湖北從事抗清活動。此時天地會的勢力已經發展到東南亞,蘇門答臘島上的部分華僑也是天地會的會員。直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陶成章創建「龍華會」,其組織形式還是模仿天地會的架構。還有我們的「鑒湖女俠」秋瑾,其實也屬於天地會——她加入的「三合會」是天地會在晚清時期的一個化名。
如果追本溯源的話,民國上海的青幫,現在香港的「新義安」,都跟歷史上的天地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都是天地會的變種或者衍生品。只是時代變了,宗旨也變了,這些幫會不再提「反清複明」,也沒有別的政治追求,它們賄賂官員、滲透政府、劃分勢力範圍,要的無非是一個「錢」字,丟了天地會老祖宗的臉。
義軍製造難民
也有不給天地會丟臉的。鴉片戰爭前後,天地會又衍生出一個分支:小刀會。這個幫會在上海很活躍,秘密結黨,謀劃反清。西元1853年,小刀會首領劉麗川公然打出「反清複明」旗號,率領幫會成員和附近貧民攻佔嘉定縣城,繼而攻佔上海縣城,宣告「大明國」成立,劉麗川自封「大明國招討大元帥」。滿清政府調派軍隊圍剿,被劉麗川打得稀裡嘩啦。清軍敗退,小刀會又攻佔寶山、南匯、川沙、青浦,然後清軍再次圍剿,雙方在今天的上海市區和近郊區縣打了幾十場硬仗。
不管什麼時候打仗,吃虧的總是老百姓。西元1854年10月7號,後來出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第一把手、把持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的英國人赫德從香港坐船去寧波,途徑上海,登陸住宿。當時上海正在小刀會的控制之下,赫德親眼目睹了戰爭給上海市民帶來的災難:城裡到處是燒毀的民房,路邊還有丟棄的屍體,起義者良莠不齊,一邊跟政府軍交戰,一邊肆無忌憚地搶錢搶女人,「他們急急忙忙把任何可以拿到的東西都拿出城去換取食物。」剛才我還誇小刀會不給天地會丟臉來著,寫到這兒又覺得,這個小刀會也不是什麼好玩意兒,至少它的某些成員不是好玩意兒。
過去有句老話:「小亂居鄉,大亂居城。」意思是小股土匪騷擾地方的時候,最好搬到城裡住,因為城裡有軍隊,有員警,土匪不敢搗蛋;打大仗的時候最好搬到鄉下住,因為城裡有錢人多,漂亮女人多,機關也多,是財富和政權的象徵,是「兵家必爭之地」,而農村窮得叮噹響,「兵家」們不屑於去爭,住在農村最多被拉壯丁,比城裡安全。所以在和平年月,城市是優於農村的,有錢的農村人為了換一個相對良好的治安環境,紛紛在城裡買房定居;一旦爆發戰爭,城裡反不如農村安全,城裡人為了保住妻女、錢財和自己的小命,不得不向農村逃難。像這種反反復複如同拉鋸的城鄉之間大遷徙,曾經在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一再上演。
小刀會跟清軍打仗,戰火燒到了家門口,上海人自然要往鄉下搬遷,可是這時候連鄉下也不安全了——太平天國的起義軍,也就是被江南百姓稱為「長毛」的傢伙,正在勢如破竹地攻城掠地,一路上殺富戶、燒廟宇、拉壯丁、征軍糧,在弄清他們的進軍路線之前,貿然搬到農村去等於送死。城裡沒法待,鄉下又不敢去,外有政府軍攻殺,內有小刀會搶劫,上海市民何去何從?
第一個房產牛市
逃命的地方還是有的。自封「大明國招討大元帥」的小刀會首領劉麗川是個「洋務派」,講難聽點兒叫做「二鬼子」,他早年在新加坡打過工,後來又在英國洋行做買辦,深知中西武力相差甚遠,得罪洋人後患無窮。為了使「大明國」這個新政權獲得洋人的支持,劉麗川攻佔上海當天就去了租界,他向各國領事承諾:小刀會只針對清政府,不針對洋人,外面殺聲震天,租界安如泰山,決不讓一兵一卒進租界搗蛋。這個承諾使洋人暫時保持了中立,也讓租界成了戰爭中僅存的和平孤島。哪裡才是上海人逃難的最佳選擇?租界。
按照清政府和英、法、美等國簽訂的條約,華洋應該分居,租界裡只能住外國人,不能住中國人。可是這時候戰火燒身,凡跟洋人有點兒關係的中國人都往租界裡逃,跟洋人沒有關係的中國人也在想法設法買通關係往租界裡逃,哪還顧什麼條約不條約?小刀會跟政府軍交火的第一天,英租界裡就湧進了兩萬名中國人,小小的租界擁擠不堪。
洋人剛開始還抗議華人破壞「華洋分居」的條約來著,很快發現這些扶老攜幼前來逃難的華人都攜帶著金銀細軟,腰包裡都有點兒積蓄(窮人逃不進租界,只能在外面等死)。難民不像蝸牛背著房子走路,這時候已是深秋,也不能露宿街頭,所以得向洋房東租房住。房子供不應求,難民不惜千金,一時人如潮湧,房租陡漲,家有大屋的洋人都發了。頭腦精明的洋人趁機搭建簡易房,再高價租給華人,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很快地,在英租界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涇浜兩岸,一排一排的小木屋拔地而起,妓院、賭館和鴉片館也在附近遍地開花,上海租界迎來了有史以來第一個房產牛市。
也就是說,小刀會燃起了戰火,戰火逼著華人逃進租界,華人為租界房市帶來了需求,暴漲的需求讓歐美開發商賺到了第一桶金。過去我們一說「發戰爭財」,都是指賣軍火,現在看來還有一條發戰爭財的管道,那就是做房產。
戰爭財利潤雖大,只能在戰爭時候發,和平一降臨,生意就歇菜。小刀會佔領上海不到兩年,滿清政府遊說洋人一同「剿匪」,在洋槍洋炮的支持下,清軍打跑了小刀會,「大明國」就此覆滅,上海恢復了和平,在租界避難的人們返回家園,洋涇浜兩岸的小木屋開始空置。小刀會起義之前,租界裡有幾家洋行(例如老沙遜)販賣鴉片為業,戰爭時期都改行幹起了房地產,現在和平了,難民走了,房產牛市變成熊市了,它們又都販賣鴉片去了。
佛家講因緣,認為諸法皆由因緣和合而生。換句話說,無論一個東西的形成,還是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因為某些因素很偶然地湊到一起來了。
我原本是學理工的,畢業後做測量和預算,還參與過一些地方的土地規劃,是一個沒有編制的技術人員,平日最大的樂趣,是寫各種各樣的小程式。比方說工作時需要把測量誤差合理分配到圖紙上去,而利用現有的軟體做不了這個工作,我就寫一個「平差計算器」,完了把所有座標導入,一敲回車,問題解決了,於是關機,於是傲然四顧,瞧著同事們還在加班,幸福感油然而生。在那時候,我的理想是考一個資格證,做專業的程式師,從來也沒想過有一天會寫文章,更沒想到去寫書,即使想寫,也不會寫《民國房地產戰爭》這樣的書,因為興趣和特長都不在此,不具備寫這類書的機緣。
大約是2005年,專業程式師的理想還沒實現,上班前,有個師兄拿份報紙向我顯擺:「瞧,我太太編的報紙!」那是某家報紙的副刊,上面刊登的全是小品文,那個師兄的夫人正是那個副刊的責編。我看了以後說:「這樣的文章我也會寫啊!」他不信,我就寫了一篇,讓他轉給了他太太,結果發表了。我很興奮,感覺寫文章不比寫程式難,還有稿費拿,就繼續寫下去。寫了大半年,在網上看見北京一家報紙找人寫專欄,我準備了四篇稿子發過去,編輯認可了,從此開始給這家報紙寫專欄,每週寫兩期,每期一千字,每月稿費三、四千塊錢。
2006年5月,我連續拿了大半年的稿費以後,把工作辭了,開始專職寫作,做職業撰稿人,同時給四五家報紙寫專欄。專欄需要固定的選題,我花了很長時間琢磨國內報紙的版面,發現所有的選題都有人在寫,除了「房地產歷史」這一塊。房地產屬於經濟領域,我念大學時就對經濟感興趣;歷史則是我的閱讀偏好,打小就喜歡。所以我就選了「房產史」作為以後寫專欄的主攻方向,從此每天跑圖書館,翻讀正史,翻讀野史,翻讀墓誌,翻讀方志,翻讀別人輯錄的契約文書,翻讀古代名人的信劄、日記、行狀、年譜和詩集,從中尋找跟房地產有關的部分,抄錄下來,回去慢慢研究。
中國古人重視歷史,但是不重視數字,關於地價和房價的文獻,關於不動產交易的記載,鴉片戰爭以前似乎從來就沒有專書問世,要想從浩瀚古籍裡把握以往樓市的輪廓和細節,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但惟其不輕鬆,做起來才更有「技術含量」,作為一沒錢財二沒地位只有通過炫耀技術來滿足虛榮心的老派青年,我願意花力氣閱讀海量文獻,並從中發現一些別人不願意關注或者不屑於關注的東西。我一邊發現,一邊把那些發現寫成專欄,就這樣給新京報寫了兩年半的「千年宅事」,給深圳商報寫了兩年的「千年房事」,給南方都市報寫了一年半的「民國房事」。
在民國時代生活了大半生的齊如山先生說過治學的方法(雖然他不是學者):「大家總是靠著幾本圖書,皓首窮經,一輩子不管別的事情,其實真正研究經學,永遠不會離開社會。如顧亭林為研究經學,各處去訪問,郝蘭皋著《爾雅義述》,也多靠實地調查。若要研究一國的政治,更是需要察看社會中的情形及政治的實際,才能洞知其真相,若研究其法律及公文等,那是不能真知道,且是絕對靠不住的。」我非常佩服齊如山先生的見地,所以就借鑒他的話,相信研究「房產史」同樣離不開社會。所以從2007年開始,我試著通過不同途徑跟開發商接觸,譬如說給他們做樓書,或者給他們的雜誌寫專欄,或者借風水話題跟策劃部的人深聊一陣子,目的就是盡可能弄清楚現代樓市是怎麼回事兒,以便對古代樓市有更深的理解。因為我相信我們都是古人詐屍,都是今之古人,時代雖然變了,我們自私、奸詐、愚昧和鼠目寸光的人性沒有變。
在跟開發商接觸的過程中,聊起我所知道的古代樓市,並把以前寫過的《千年樓市:穿越時空去古代置業》(這是2009年寫的一本書)給他們看,他們很感興趣,有位說:「民國離我們最近,你怎麼不寫寫民國的房價啊?」我怦然心動。那時是2010年,出版界正猛刮民國風,我感覺寫這樣一本書既結合時代熱點(房地產),又符合出版潮流(民國熱),值得一寫。
於是重點搜集與民國樓市相關的文獻,邊搜集邊整理,兩年以後,有了《民國房地產戰爭》這本書。
我想,假如不是單位裡那個師兄炫耀他媳婦做的版面,我想不到去投稿;假如當初不投稿,我不會知道寫專欄也可以作為謀生手段;假如寫專欄不能謀生,我不會有時間泡圖書館;假如不泡圖書館,我沒辦法從各種文獻裡整理出「房產史」的輪廓;假如不整理出「房產史」的輪廓,我不可能去寫《千年樓市:穿越時空去古代置業》那本書;假如不寫那本書,開發商不可能建議我寫民國房價;假如沒有人建議我寫民國房價,我絕對沒有動力來寫這本《民國房地產戰爭》。這就是佛家說的因緣。
書名:為什麼叫「戰爭」?
這本書是寫民國房地產市場的,直白一點兒的書名,應該叫《民國房地產》,為什麼又在後面加上「戰爭」兩個字呢?原因有三:
一、民國是個經常打仗的時代,那時候過日子離不開戰爭,房地產市場也離不開戰爭。
比方說,很多地方樓市正火,一炮打過來,土著出逃,移民返鄉,有房的低價拋售,沒房的不再認購,房價和地價像燒餅上的芝麻一樣簌簌往下掉,新建商鋪空關,在建住宅停工,開發商債臺高築,房地產市場崩盤;還有很多地方本來沒多少購房需求,就因為其他地方都在打仗,這裡成了和平孤島,難民像潮水一樣湧過來,有錢的四處買房,沒錢的四處租房,把這裡的房價和房租抬高了,把這裡的樓市捧紅了。
甭說房價、地價和房租經常受戰爭影響,就是民國人的居住習慣也深受戰爭影響。很多民國人為什麼寧可租房也不買房?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怕辛辛苦苦大半生買下的一所房子被一個炸彈炸成平地,那時候保險公司又不包賠,豈不虧大了?所以無論有錢人還是沒錢人,每到一個城市定居,都是租房的多,買房的少。
民國人的這種居住習慣進而又影響了房產商的開發模式。在民國,建成房屋對外出售的房產公司極為少見,無論是不遠萬里來中國淘金的猶太開發商,還是本小利薄租地建房的本土開發商,也無論是開發商業地產,還是開發住宅專案,大家都偏好於出租而不是出售,因為這樣才迎合消費者需求。而消費者為什麼會偏愛租房而不是買房呢?因為老是有戰爭。
您說,戰爭對民國房地產市場影響如此之大,幹嘛不給這本書取名叫《民國房地產戰爭》呢二、「戰爭」這個詞能迎合多數讀者的閱讀偏好。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天生喜歡看熱鬧,尤其喜歡看打架,只要流的不是自己的血,只要交戰雙方的血不濺到自己身上,打架都能給人一種極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滿足。如果您喜歡交戰雙方的某一方的話,還能把自己代入進去,在觀看的同時設想是自己在打架,把另一方打得頭破血流跪地求饒,於是自豪感鋪天蓋地。因為這些緣故,武俠小說曾經很火(便於把自己代入),戰爭大片一直很火(打架的場面很大,很熱鬧)。所以我想,《民國房地產》一定沒有《民國房地產戰爭》吸引眼球。
靠書名來吸引眼球,是「標題黨」的一貫做法,我對標題黨沒好感,可是書市上每年湧現那麼多新書,要是連書名都不能吸引眼球,大夥連翻開看一眼的興趣都不會有,是吧?
三、在這本書之前,已經有好多書以「戰爭」為名了。
您上網搜一下,《貨幣戰爭》、《糧食戰爭》、《歐洲貿易戰爭》、《中國房地產戰爭》……琳琅滿目,俯拾皆是。這些書,內容跟戰爭幾乎無關,但都綴了「戰爭」的尾巴,我非始作俑者,不用怕有人罵。再說了,我這本書談的核心內容就是戰爭對民國樓市的影響,標題很切實,更不用怕有人罵。
從天地會說起
金庸武俠小說裡有個天地會,總舵主叫陳近南,麾下幫眾十幾萬人,勢力遍佈大江南北,藏龍臥虎,高手如雲,殺官劫獄,反清複明,做下了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歷史上確實有個天地會,但陳近南只是這個幫會的遙遠傳說,而且他還是個和尚(並不是武俠小說裡那個英俊瀟灑的中年書生)。金庸說陳近南原來的名字叫陳永華,陳永華是有的,他是鄭成功的手下,以文治見長,不會武功,更沒有創辦過天地會 。
從清政府公佈的奏章和邸報來看,天地會成立於乾隆年間(金庸小說裡的天地會在康熙年間就已經很活躍了),先是在廣東和福建一帶活動,後來轉戰臺灣,在臺灣發動抗清起義,「所過之處香案疊疊」(天地會「順天大盟主」林爽文的告示),受到了臺灣人民的大力支持。臺灣人拿起鐮刀加入天地會,佔領城市,驅趕貪官,剪掉髮辮,改換服式,臺灣一時變色,大半個島嶼納入天地會控制之下。為撲滅這場起義,乾隆動用了廣東、廣西、福建、貴州、浙江、湖南、四川七個省的軍隊,消耗的軍費占了全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這場起義失敗之後不到五年,臺灣南路和臺灣北路又先後爆發了兩次起義,也都由天地會發起。到了嘉慶七年,廣東惠州天地會首領蔡步雲起義。嘉慶十一年,廣東潮州天地會首領張四田起義。嘉慶後期,從天地會衍生出「平頭會」和「紅花會」(這是金庸《書劍恩仇錄》和《飛狐外傳》裡反復提到的一個大幫會),分別在廣東、福建、新疆、湖北從事抗清活動。此時天地會的勢力已經發展到東南亞,蘇門答臘島上的部分華僑也是天地會的會員。直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陶成章創建「龍華會」,其組織形式還是模仿天地會的架構。還有我們的「鑒湖女俠」秋瑾,其實也屬於天地會——她加入的「三合會」是天地會在晚清時期的一個化名。
如果追本溯源的話,民國上海的青幫,現在香港的「新義安」,都跟歷史上的天地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都是天地會的變種或者衍生品。只是時代變了,宗旨也變了,這些幫會不再提「反清複明」,也沒有別的政治追求,它們賄賂官員、滲透政府、劃分勢力範圍,要的無非是一個「錢」字,丟了天地會老祖宗的臉。
義軍製造難民
也有不給天地會丟臉的。鴉片戰爭前後,天地會又衍生出一個分支:小刀會。這個幫會在上海很活躍,秘密結黨,謀劃反清。西元1853年,小刀會首領劉麗川公然打出「反清複明」旗號,率領幫會成員和附近貧民攻佔嘉定縣城,繼而攻佔上海縣城,宣告「大明國」成立,劉麗川自封「大明國招討大元帥」。滿清政府調派軍隊圍剿,被劉麗川打得稀裡嘩啦。清軍敗退,小刀會又攻佔寶山、南匯、川沙、青浦,然後清軍再次圍剿,雙方在今天的上海市區和近郊區縣打了幾十場硬仗。
不管什麼時候打仗,吃虧的總是老百姓。西元1854年10月7號,後來出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第一把手、把持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的英國人赫德從香港坐船去寧波,途徑上海,登陸住宿。當時上海正在小刀會的控制之下,赫德親眼目睹了戰爭給上海市民帶來的災難:城裡到處是燒毀的民房,路邊還有丟棄的屍體,起義者良莠不齊,一邊跟政府軍交戰,一邊肆無忌憚地搶錢搶女人,「他們急急忙忙把任何可以拿到的東西都拿出城去換取食物。」剛才我還誇小刀會不給天地會丟臉來著,寫到這兒又覺得,這個小刀會也不是什麼好玩意兒,至少它的某些成員不是好玩意兒。
過去有句老話:「小亂居鄉,大亂居城。」意思是小股土匪騷擾地方的時候,最好搬到城裡住,因為城裡有軍隊,有員警,土匪不敢搗蛋;打大仗的時候最好搬到鄉下住,因為城裡有錢人多,漂亮女人多,機關也多,是財富和政權的象徵,是「兵家必爭之地」,而農村窮得叮噹響,「兵家」們不屑於去爭,住在農村最多被拉壯丁,比城裡安全。所以在和平年月,城市是優於農村的,有錢的農村人為了換一個相對良好的治安環境,紛紛在城裡買房定居;一旦爆發戰爭,城裡反不如農村安全,城裡人為了保住妻女、錢財和自己的小命,不得不向農村逃難。像這種反反復複如同拉鋸的城鄉之間大遷徙,曾經在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一再上演。
小刀會跟清軍打仗,戰火燒到了家門口,上海人自然要往鄉下搬遷,可是這時候連鄉下也不安全了——太平天國的起義軍,也就是被江南百姓稱為「長毛」的傢伙,正在勢如破竹地攻城掠地,一路上殺富戶、燒廟宇、拉壯丁、征軍糧,在弄清他們的進軍路線之前,貿然搬到農村去等於送死。城裡沒法待,鄉下又不敢去,外有政府軍攻殺,內有小刀會搶劫,上海市民何去何從?
第一個房產牛市
逃命的地方還是有的。自封「大明國招討大元帥」的小刀會首領劉麗川是個「洋務派」,講難聽點兒叫做「二鬼子」,他早年在新加坡打過工,後來又在英國洋行做買辦,深知中西武力相差甚遠,得罪洋人後患無窮。為了使「大明國」這個新政權獲得洋人的支持,劉麗川攻佔上海當天就去了租界,他向各國領事承諾:小刀會只針對清政府,不針對洋人,外面殺聲震天,租界安如泰山,決不讓一兵一卒進租界搗蛋。這個承諾使洋人暫時保持了中立,也讓租界成了戰爭中僅存的和平孤島。哪裡才是上海人逃難的最佳選擇?租界。
按照清政府和英、法、美等國簽訂的條約,華洋應該分居,租界裡只能住外國人,不能住中國人。可是這時候戰火燒身,凡跟洋人有點兒關係的中國人都往租界裡逃,跟洋人沒有關係的中國人也在想法設法買通關係往租界裡逃,哪還顧什麼條約不條約?小刀會跟政府軍交火的第一天,英租界裡就湧進了兩萬名中國人,小小的租界擁擠不堪。
洋人剛開始還抗議華人破壞「華洋分居」的條約來著,很快發現這些扶老攜幼前來逃難的華人都攜帶著金銀細軟,腰包裡都有點兒積蓄(窮人逃不進租界,只能在外面等死)。難民不像蝸牛背著房子走路,這時候已是深秋,也不能露宿街頭,所以得向洋房東租房住。房子供不應求,難民不惜千金,一時人如潮湧,房租陡漲,家有大屋的洋人都發了。頭腦精明的洋人趁機搭建簡易房,再高價租給華人,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很快地,在英租界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涇浜兩岸,一排一排的小木屋拔地而起,妓院、賭館和鴉片館也在附近遍地開花,上海租界迎來了有史以來第一個房產牛市。
也就是說,小刀會燃起了戰火,戰火逼著華人逃進租界,華人為租界房市帶來了需求,暴漲的需求讓歐美開發商賺到了第一桶金。過去我們一說「發戰爭財」,都是指賣軍火,現在看來還有一條發戰爭財的管道,那就是做房產。
戰爭財利潤雖大,只能在戰爭時候發,和平一降臨,生意就歇菜。小刀會佔領上海不到兩年,滿清政府遊說洋人一同「剿匪」,在洋槍洋炮的支持下,清軍打跑了小刀會,「大明國」就此覆滅,上海恢復了和平,在租界避難的人們返回家園,洋涇浜兩岸的小木屋開始空置。小刀會起義之前,租界裡有幾家洋行(例如老沙遜)販賣鴉片為業,戰爭時期都改行幹起了房地產,現在和平了,難民走了,房產牛市變成熊市了,它們又都販賣鴉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