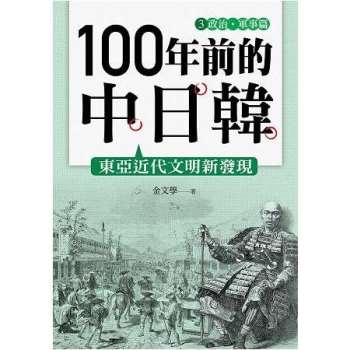1. 反觀東亞地圖
讓我們先展開世界地圖中的東亞地圖,然後將其倒過來加以觀察。
中國和韓國(朝鮮半島)、日本的方位的排列次序與原來恰好相反。
我們可以發現渤海、黃海、中國東海、日本海是大陸和列島的內海。尤其是日本海,雖然位於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之間,但其作為過去曾與大陸連結的痕跡,看上去似乎很像一個湖泊。
還有一點也不容忽視。日本的地形絕不是一個以大海為界的、不同於大陸的「孤立無援的島嶼」。
我們會發現,所謂日本這個島國,事實上是將亞洲大陸廣闊的北方與南方連接起來的橋樑。不僅如此,日本還位於亞洲(東洋)的最西端(正視地圖時則位於最東端--也稱為極東),看上去像是介於西方北美大陸和亞洲大陸之間的巨大橋樑。
而問題也正是從這裡發生的。率先實現西方近代化的日本,並沒能起到很好的「文明橋樑」作用。這是近代最大的「惡之花」。
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變身為西方式的近代國家,卻沒能形成「大海即是人類交流的舞台」這一理念,而是將「大海即為國境」這一錯誤理念植入國民意識深處,並由此做出了可怕的錯誤選擇:要想守住孤立無援的島國,就應該覬覦海外,佔領殖民地。
在世界中世紀史和近代史中,15-16世紀歷史的主人公,從大陸帝國轉變為海洋帝國。「統治海洋的國家,才能統治世界。」這正是經過大航海時代而走近我們的近代世界觀。以西方文明和技術掌握海洋控制權的近代世界殖民地統治原則,正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海洋帝國最大的話題。
以英國為中心,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俄羅斯、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橫跨海洋掠奪與強佔殖民地,便是當時世界「弱肉強食」的絕對原則。
1840年,在鴉片戰爭中受到強烈刺激的國家,事實上並非是大清國,而是島國日本。
他們很快認識到,要想避免西方帝國的殖民地統治,最好的方法只有自己首先實施「強兵富國」、「文明開化」的政策。他們認為只有成為亞洲的「西方」,才會有活路。
只要比較東亞三國的開國樣態,我們就會得知日本這個國家對所謂「西方式的」是多麼敏感,並率先模仿西方的,以至於經常被西方嘲笑為「猿猴」。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以皇帝為中心的「天下觀」所俘獲,鼓吹孔孟的悠久文化傳統,反而受累於其自身文明的重壓,最終遭到近代化進程的唾棄,成為近代化進程的「落第生」。日本在鴉片戰爭中,比大清帝國感受到更加強烈的憂慮。日本於1853年,自從美國的佩里提督(Matthew Calbraith Perry,美國海軍將領,因率領黑船打開日本國門而聞名於世。)的「黑船事件」以後,靈活應對,僅僅用了15年時間,便於1868年成功地實現了西方式的改革、明治維新,確立了近代化國家地位。
朝鮮當時是什麼情況呢?1866年「丙寅洋擾」1以後,日本於1875年9月入侵韓國江華島,釀成了「雲揚號事件」2。最近發掘出來的史料表明,「雲揚號事件」純粹是日本受到佩里提督的啟發,而引發的一場入侵朝鮮領土的挑釁。1876年2月,日韓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條規規定韓國必須開放釜山港以及另外兩個港口,是一個利於保護日本人的「通商往來」的不平等條約。從此,日本自居為「小西洋」,並站在類似西方帝國的立場上,君臨朝鮮。朝鮮在西洋和日本的雙重壓迫下,開始了「非自主」的國家命運。
「歷史是以時間和空間為軸,在超越了個人體驗的尺度上把握、解釋、說明、敍述人類生活。」考慮到這樣一種觀點,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饒恕日本以中日韓三國的歷史性時間(發展速度),和歷史性空間(地理風土)的異質感為理由,標榜「脫亞入歐」,或在「大亞洲主義」理念下對亞洲採取的侵略。日本採取的殖民化,無論如何也不能被其殖民或侵略過的國家所接受,而只能成為他們被壓迫的源頭。儘管難以用道德標準評價歷史事件,但從人類常識上說,這一點在當事一方的被害者立場上看來,是絕對不可能稱為一種美德,或是值得稱讚的價值的。
日本對亞洲的侵略戰爭與統治一直持續到1940年代中期,並在演化為亞洲、太平洋戰爭時達到極致。日本所構築的跨越海洋、無視海洋的「大共榮圈」美夢,最後以它的慘敗而告終。
現在,不妨讓我們重新凝視這張地圖。地理就是心理,而心理便是人,而人亦即文化。另外,歷史正是由人類創造的文化所確定的。即使是哪一個國家力量擁有貿然行動的意志,但只要無視文化,無視地理,就終將以失敗告終。這是歷史的殘酷一面。
2. 近代中日韓之間的第一次文明衝突
令人遺憾的是,近代東亞三國的直接、近距離交鋒是以戰爭開始的。文明或者是文化之間的衝突,總是由戰爭來發揮其作用的。
從文明史角度看,戰爭是先於正義或不義的道德準則,並作為相異的文化交鋒、交流的代理人身分,成為歷史一大主題的。從嚴格的意義上講,近代中國(當時的大清帝國)和日本之間大規模的近距離交鋒,正是1894年發生的甲午戰爭。
戰爭的原因是什麼呢?不幸的是,其實質正是日本和大清帝國之間圍繞朝鮮半島的爭奪之戰。處於大陸和海洋縫隙中的民族,必須接受從大陸和海洋勢力兩個方向襲來的紛爭和文明之風。這或許是無法回避的命運。此外,在日本和大清帝國的後面,還有俄羅斯在虎視眈眈。
英國、德國、俄羅斯、法國正準備瓜分中國這塊大蛋糕。而日本也站在旁邊,伺機出手。我們從中能夠看出,由帝國主義的心性所充滿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世界秩序。
世界地緣政治學者喜歡將其統稱為「地緣政治學的宿命」,並以此來規定類似朝鮮的國家命運。最近以來,「地緣政治學」因其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而廣受詬病,但英國的地理學家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英國地理學家與地緣政治家。)於1904年始創的這一學說,卻是無法用觀念論或宿命論一概而論的政策科學之一。所謂地緣政治學,是將地球整體視為一個單位,即時捕捉其動向,並從中得出現行政策所需的方案。但無論如何,對紛紛嚷嚷的朝鮮而言,在「地緣政治學」背後,總會有「悲慘命運」這一貶義詞相隨。
19世紀末期,明治政府對朝鮮的基本政策,是希望朝鮮以一個完整的獨立國家身分,與其實現外交關係。這一點,被引申為公然否認一直以來作為朝鮮半島宗主國的大清王朝許可權之舉。
於是,日本在明治9年,即自1876年江華島條約(《日朝兩國修好條約》)以來,圍繞著朝鮮半島問題與大清帝國產生對立。在1890年第11次帝國會議中,當時的日本首相山縣有朋決定確保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利益。緊隨其後,在6月,朝鮮半島發起了東學黨起義(19世紀下半葉在朝鮮發生的一次反對兩班貴族和日本等外國勢力的平民武裝起義運動,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索。)朝鮮政府向大清帝國發出協助壓制農民運動的邀請。在壓制了伊藤博文等漸進派的「慎重論」主張以後,日本政府激進勢力將大批陸軍派駐到朝鮮,以期在大清帝國和朝鮮之間達成某種平衡。
由於大清和日本兩國派兵進駐,東學黨起義被鎮壓。但兩國軍隊並沒有撤軍,而是繼續堅持在朝鮮駐軍。於是日本制定了擊退大清帝國軍隊的計畫,並於7月25日清晨,在忠島襲擊了北洋艦隊的一支軍隊。4天以後,日軍與在漢城南部布陣的清軍交戰。
從結果上看,大清帝國軍隊在海戰和陸戰中雙雙敗北,而日本獲得了第一場近代戰爭的勝利。中國方面對於這場戰爭的記述,我們通過教科書等資料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對這一部分內容,在此予以略述。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日本方面的戰爭樣貌。
在檢索日本方面相關文獻資料過程中,令我感到驚奇的是,大清帝國有為數眾多的國民還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在跟日本交戰,也就是說,人們並不大關心這場戰爭。但日本舉國上下,卻一致贊成這場戰爭,聲援之波勢如破竹。不僅是日本當時的著名知識份子德富蘇峰1,或三宅雪嶺2,就連素以世界主義者聞名的內村鑑三(日本基督教思想家,無教會主義的宣導者。)等知識份子,也都通過《代表性的日本人》等著述讚揚中日甲午戰爭為「正義之戰」。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明治時期啟蒙家、頭像被印製在一萬日圓紙幣上的福澤諭吉3立刻為此捐贈了一萬日圓。如果按市價計算,當時的一萬日圓,是相當於現在一億日圓的巨額資金。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在當時調動了報紙、雜誌、廣播等所有大眾傳媒資源,並把從軍記者、作家、畫家派到前線,每天以各種方式報導戰爭進展情況。根據當時日本的記錄,日本當時非常懼怕亞洲最大國家大清帝國,也在時時戒備北洋軍閥李鴻章,以及實力遠在其上的南方勢力張之洞。然而,張之洞好像隔岸觀火,只是一味袖手旁觀。很明顯,大清帝國的國家觀念非常薄弱,與此同時,民眾也缺乏愛國意識。
與此相對照的是,日本在這場戰爭中,人人以當事者心態介入其中。所有國民全都因戰爭而狂熱,變成直接或間接的戰爭參與者。無數民眾爭先恐後捐獻資金,而那些赤貧的年輕人則紛紛志願參軍。日本的報紙,在連篇累牘地報導戰爭英雄事蹟的同時,也充斥著國民捐錢捐物以戰爭為契機為國奉獻的相關報導。「日清戰爭」這一標題,使所有日本讀者為之發狂,而日本政府也以這種手段,實現了讓全日本社會通過新聞雜誌等傳媒認識世界的目的。新聞媒體的力量如此之大,同時也具有將民眾驅往同一價值觀的風險。而在這種背景之下,形成了大眾社會。
我們可以通過100年前大清帝國和日本之間,為了各自在朝鮮的利益而展開的這場戰爭,發現此類現象和問題。作為史無前例的近代戰爭,這場戰爭揭露出當時大清帝國國民的「非參與性」和國民國家的不完美性,以及國家意識的缺乏。而對於日本而言,則帶來了全社會範圍內的巨變。同時隨著「國民」這一前所未有的意識,催生了國民群體,並在真正意義上變身為一個近代國家。
此外,這場戰爭也前所未有地動搖了東亞的國際秩序,同時也讓曾經君臨東亞之上的大清帝國的領導體系毀於一旦。我們可以用如下一句話歸納其原因:大清帝國沒能形成與日本相同的「國民性國家」的一體性。我們可以稱之為「近代」的近代史,實際上是由中日甲午戰爭為界形成的。這是前近代與近代的分水嶺。
1895年,由伊藤博文和李鴻章簽署的《馬關條約》規定,大清帝國出讓朝鮮宗主國地位,並向日本割讓臺灣,從此沒落為「半殖民地」。這對大清帝國而言,也是一個莫大的恥辱。於是,日本替代大清帝國,成為東亞的所謂「領導者」,並將從大清帝國手中掠奪的朝鮮玩弄於鼓掌,從此踏上肆意殖民、蹂躪朝鮮半島的道路。
大清帝國的有識之士,開始學習日本催生國民國家共同體意識的做法,並通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運動,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中國在孫中山先生的帶領下,建立起國民國家性質的共和國。
3. 「獨立門」是從何而來的獨立?
在韓國的首爾西大門區,地鐵三號線設有「獨立門」一站。由此站步行不遠,便可看到著名的獨立門超然地站在那裡。
可是,這頗有來歷的「獨立門」所謂的獨立,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在韓國,有90%以上的國民認為,是擺脫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獨立。事實上,筆者在韓國遇到的知識份子、公務員、公司職員、學生等人當中,持有這種錯覺的人十有八九。我曾向在日本留學的韓國留學生和居住在中國的朝鮮族同胞提出過這一問題,其中絕大多數也持有相同看法。
仔細一想,這也是事出有因的。為什麼?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長達35年的漫長殖民統治之下,我們所能體驗到的情感,在遇到「獨立」這個概念時,多半會將其理解為是擺脫了日本萬惡的殖民統治的「獨立」。此外,在後殖民主義時代(Postcolonialism),對於作為殖民地後裔生活於此的我們同胞而言,1945年8月15日,韓國從日本統治之下的獨立解放,似乎也是比任何事都具有深遠意義的一件大事。這仍然可以稱之為是一種「殖民地後遺症」。
那麼,這座象徵著獨立的「獨立門」,究竟意味著從何而來的獨立呢?正確回答應該是:「從大清帝國統治之下獲得的獨立」。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清日雙方簽署的《馬關條約》第一條即是關於「朝鮮獨立」的內容。內容如下:「中國確認朝鮮國為獨立自主國家,朝鮮對中國的朝貢、奉獻、典禮永遠廢止。」這是日本與大清帝國開戰的理由,通過這一條約,明文規定永遠廢止朝鮮與大清帝國的從屬關係,宣告朝鮮自此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當然,日本在其中自有自己的算盤。在這裡有一點值得我們加以關注:雖然在我們的記憶中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但直到進入19世紀,東亞國際秩序的基本構圖,仍然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朝貢與冊封關係。
大清帝國以中和思想為基礎,在誇示自己豐富文化和先進文明的同時,持續向各民族和地區施加帝國的影響力。其中,在大唐盛世沒落期的西元894年,菅原道真向大唐帝國提出終止向其繼續派遣遣唐使的要求,以此為向大唐派遣遣唐使一事畫上了休止符。此後,過了13年,大唐帝國於西元907年滅亡,又過了53年,大宋朝於西元960年建立了統一王朝。可以說,日本是在恰當的時機,成功地擺脫了大陸中國的權力範圍,並開始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日本利用海洋這天然屏障,成功地吸收了中華文明中的精華,並在吸收外來文明方面發揮出類似於「過濾器」的作用。正因為日本很早就已經實現了作為一種文明的獨立,因此日本在日後吸收西方文明的過程也變得更加容易。在這一點上,日本和朝鮮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從地理上講,朝鮮處於與大陸鄰接的地理位置,因此也沒有任何屏障可言。朝鮮只能吸納中華文化,甚至吸納被大清帝國推翻的明王朝中和思想,並以「小中華」的身分,為自己能在東亞替代明王朝的中和而沾沾自喜。換句話說,朝鮮深深沉浸在中國影響力之中。最好的一個例子是,朝鮮甚至原封不動地吸納了中國的宦官、宮女、纏足、科舉等制度,並將其制度化。而日本卻過濾掉了這些糟粕。不管怎麼說,無論朝野,朝鮮對大清帝國表現出排斥反應的同時,又對此予以順應。這種屬國的歷史持續了數百年之久。
毛澤東於1939年在其所著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道:「用戰爭打敗了中國以後,帝國主義列強不但佔領了中國周圍的許多原由中國保護的國家,而且搶去了或『租界』去了中國的部分領土。例如日本佔領了臺灣和澎湖列島,『租界』了旅順,英國佔領了香港,法國『租界』了廣州等。」毛澤東在文中言及了前近代東亞的慘敗,以及西方和日本搶奪了中華帝國的保護國這一事實。魯迅先生也在翻譯一本日本著作的譯者序言中,就被日本合併朝鮮一事,強調其為「原來是我們的所屬國。」
韓國就是這樣為了紀念迎來「永遠擺脫了大清帝國所屬國地位」的日子,而豎起獨立門的。獨立門高15公尺、寬12公尺,由花崗岩石塊構建而成,其設計借鑑了巴黎的凱旋門(高50公尺)。雖然高度不及凱旋門,但仍不失為是一座宣示威嚴的雄偉建築。獨立門的設計者是獨立運動家徐載弼(韓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開化派政治家、思想家、獨立運動家,基督新教信徒。)這位當代韓國最著名的知識份子,同時也是獨立運動的創始人之一。1880年,在17歲的時候,徐載弼東渡日本留學,曾受教於福澤諭吉。回國後,他曾協助金玉均(1851-1894)領導「甲申政變」1,政變失敗以後,徐載弼逃往日本,後亡命美國。在美滯留期間,徐載弼用10年時間攻讀醫學,並獲得博士學位。在與美國女子結婚以後,徐載弼獲得了美國國籍。明成皇后被暗殺以後,隨著中日甲午戰爭,金弘集2總理同時也在促進朝鮮革新運動,並於1896年1月將徐載弼召回朝鮮。雖然被委以外務大臣一職,但徐載弼並不貪戀高官厚祿,予以婉言謝絕。4月7日,徐載弼創刊韓文報紙《獨立新聞》,開始展開獨立運動。現在4月7日成為韓國的「新聞日」,就是起因於此的。7月2日,徐載弼與李承晚等人一起創立獨立協會,並活躍在獨立事業運動之中。
隨後,於1896年11月著手建立的便是在上面提到的獨立門。當時,用於迎接中國使節的「迎恩門」和用於表示崇慕中華的「慕華館」被建在漢城的主幹路上。但是,將這些建築拆毀,並在原址上建立獨立門的意義是深遠的。
可是反觀近代史,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獨立」,不過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主導下的獨立而已。雖然獨立協會建立了「大韓帝國」,但由於韓國保守派的誣陷,獨立協會於1898年11月,被大韓帝國皇帝高宗(1852-1919年,李氏朝鮮的第26代君主,1897年朝鮮正式宣布脫離中國,建國號為大韓帝國。)下令取締,其骨幹人員也遭到逮捕。結果朝鮮從帝國內部放棄了自主的最後時機。於是在大清帝國勢力退出以後,給日本提供了巨大的機會。朝鮮的獨立自主,在排斥大清帝國的統治的同時,向日本傾斜了。
註
P014
1 指西元1866年法蘭西帝國武裝侵入朝鮮王朝的歷史事件。這次戰爭的原因是朝鮮發生「丙寅邪獄」,殺死了9名法國籍天主教神父,引發了法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於是決定出兵「膺懲」朝鮮。戰爭主要在當年10月進行,法軍雖然成功登陸朝鮮江華島,但遭遇了朝鮮的頑強反抗後撤退。法國在撤退時掠奪了無數金銀、書籍而去,這些戰利品的歸還問題長期是韓法外交的一個爭論點。
2 又稱江華島事件,是指1875年日本「雲揚號」等3艘軍艦先後騷擾朝鮮釜山、江華島一帶的歷史事件。1875年5月,「雲揚號」等日本軍艦奉命入侵朝鮮釜山,進行炮擊騷擾;9月入侵江華島一帶並與當地朝鮮守軍發生衝突,以日本大獲全勝告終。「雲揚號事件」是朝日《江華條約》簽訂的導火索,最終迫使朝鮮打開了國門。
p017
1 本名德富豬一郎,日本著名的作家、記者、歷史學家和評論家,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當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維與其思想一脈相承。
2 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時期評論家。1888年參加創建政教社,創辦《日本人》雜誌,宣揚國粹主義、批評歐化政策,指責政界、宗教界的腐敗。
P018
3 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
P022
1 指1884年12月4日,農曆甲申年10月17日,朝鮮發生的一次流血政變。這次政變由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主導,並有日本協助。政變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脫離中國獨立,二是改革朝鮮內政。
2 1841-1896,朝鮮王朝後期政治家,屬於朝鮮開化派,行事穩健,思想開明,行政能力優秀,被譽為「救時之才」。從政早期親近中國,屬於「事大黨」;甲午中日戰爭後轉為親日派,在日本的扶植下組建內閣,主導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1896年「俄館播遷」後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