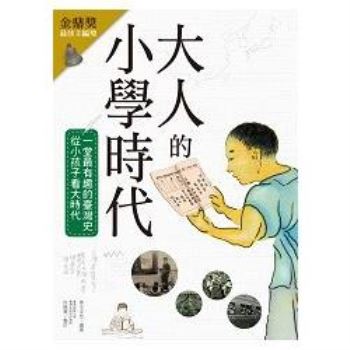芝山岩精神──震驚日臺的「教師謀殺案」
「竹藪中首先突出長槍,最後六名枕藉於稻田中。宛如實踐自我宣說的精神而倒地,這是多麼令人慨嘆至極的事。我在東京接到電報後,一夜哭到天亮。」 ──伊澤修二〈六氏周年祭弔唁演說〉
日本領臺的第一年,首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藤修二,選定臺北八芝蘭(今士林)的芝山岩,創辦了臺灣第一所新式初等教育機構──芝山岩學堂,從此芝山岩便被視為臺灣小學教育的起源地。然而,它的重要性卻不僅於此,在老一輩的人心中,它還是日治時代的師範教育聖地,因為這裡曾發生過一件震驚日臺的「謀殺案」──六氏事件(亦稱「芝山岩事件」)。
六氏事件中的「六氏」,指的是六位跟隨伊澤修二來臺建學的日籍教師,其姓名分別為: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中島長吉、井原順之助、桂金太郎與平井數馬。這六位教師多受過日本的師範教育,被伊澤修二招募來臺從事教育工作,是芝山岩學堂的第一批教師。一八九六年的元旦,六人原本準備一早下山,搭船到臺灣總督府參加慶祝新年大會,但是在半路上聽說有臺灣抗日軍襲擊臺北城,因此決定立即返回芝山岩避難,不料就在回校途中遭到當地人伏擊殺害,並將屍首棄置於芝山岩的山林中。
日本當局得知此事後大為震驚總督府乃向士林居民採取武力鎮壓行動,並造成當地一些百姓無辜犧牲。這件事不僅使芝山岩學堂的教學活動被迫暫時中斷,同時也讓招募日人教師來臺教書的計畫無法順利推展。為了撫平六氏事件的衝擊,並避免日籍教師對來臺工作望而卻步,總督府想出了一個方法,他們將這次事件予以美化昇華,把不幸殉難的六位教師塑造為捨己為人、犧牲奉獻的崇高教育典範,並以此激發其他教師們的熱血精神,讓老師們打從心裡認同:為教育犧牲性命是神聖而偉大的,一位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須手拿粉筆教學不輟,直到鞠躬盡瘁、生命止息。這就是從六氏事件衍生出的臺灣師範教育的神聖圖騰―芝山岩精神。
為了宣揚六氏先生的芝山岩精神,總督府於同年七月一日在案發地點設立「學務官僚遭難紀念碑」,並規定每年的二月一日為「六氏事件紀念日」,必須在芝山岩上舉行盛大的祭典。一九三○年時,更興建芝山岩神社,供奉六氏先生與在臺灣過世的日籍教育工作者。六氏的故事還被納入小學課本中,每到六氏殉難日,臺北城內的學校便會安排小學生上芝山岩參拜,遠在外地的也會在學校舉辦紀念儀式,甚至連小學生的修學旅行,也會將參拜芝山岩神社列入行程。總督府相信,在如此的言教、身教下,臺灣的孩子們將永遠記得這偉大的故事。
只是,歷史總是戲謔多變,二次大戰後,臺灣政權興替,中華民國政府的師範教育強調中國儒家傳統的「有教無類」、「傳道授業解惑」思想,不再灌輸這種為教育奉獻在所不辭的日式犧牲精神。五十年後,同樣是芝山岩六位老師的遭難故事,殺害者卻成為抗日的民族英雄,如今,誰還會記得荒煙蔓草間的「六氏先生之墓」與「學務官僚遭難紀念碑」,在百年前曾是臺灣師範精神的新起點。
公學校與小學校──小學教育的一國兩制
「公學校以對本島人子弟施予德教、授予實學,以養成國民之性格,並使其精通國語為主旨。」──西元1898年 〈公學校規則〉第一條
在日治時代,彰化二水地區有兩所小學毗鄰而建:二八水公學校與二八水小學校,這兩所學校僅以一道綠籬相隔,但是綠籬的兩邊,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在公學校裡上課的是臺灣人子弟,學生大多光著腳丫,身上的粗布短衣上散佈著東一塊、西一塊的補丁,書包則是一塊大布巾,將書本裹成一個包袱背著上下學。另一邊的小學校則是在臺日人子弟就讀的學校,這裡的學生穿著乾淨筆挺的漂亮制服和擦得發亮的皮鞋,手中提著整潔的大書袋,抬頭挺胸的走進教室。除了物質環境的兩極差異,這兩所學校在師資、學生待遇、學校設施,乃至於教學內容上,都有截然不同的差別。這就是日治時代小學之間,特殊的一國兩制狀況。
日本的治臺政策,一直都是採取臺日不同的差別待遇,就連教育體制也不例外。從領臺之初,臺灣的教育制度就被規劃為臺日雙軌制,日人有其專屬的教育系統,臺人也有特別設計的教育體制。後來,隨著日本人到臺灣任職的人數日漸增多,日人子女的就學問題就成為一項急待解決的工作。因此,總督府便於一八九八年間,先在臺北、基隆、新竹、臺南四個較大的城市設置小學校,作為日人子弟的教育機構,之後並陸續於全臺各地增建小學校。
臺灣小學校的課程與日本內地的學校並無二致,而專為臺人子弟設立的公學校,則以教授國語及國民道德為主。
雖然一次大戰後,在「大正民主」風潮的吹拂下,日本與臺灣都揚起「以平等無差別之待遇對待臺灣」的輿論,日本當局也在西元一九二二年發布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強調「內臺共學」的政策,不分日人臺人,都可就讀同樣的學校,但實際上,日人所讀的小學校仍以日語程度的差別為由,不太願意收不常用日語的臺籍兒童,因此日治時代的小學教育,仍大致維持臺灣人讀公學校,日本人讀小學校的情況,只有少數臺灣子弟能擠入小學校的窄門。
日語臺語說不通──北京話最紅
我是臺灣人,你是臺灣人,他是臺灣人,我們都是臺灣人。 〈第一課 臺灣人〉
我們的祖宗是福建人,是廣東人。福建人、廣東人、臺灣人都是中國人。 〈第二課 中國人〉──《臺灣暫用小學國語課本甲篇》
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各級學校自然不能再以日語教學,一切課程都改用新文字──中文來書寫,主流語言則是距離臺灣千里遠的「北京話」。
這下子,問題就來了,臺籍教師皆出身於日本師範體系,學校說的是日語,筆下寫的是日文,生活中則以福佬、客家或原住民語溝通,對於北京話相當陌生,只有曾經到中國留學或久居中國大陸的極少數臺灣人,才可能懂得北京官話──也就是說,學校的國文師資有了十分嚴重的短缺。為了避免學校課程中斷,當時許多小學老師都會利用晚上的時間,聘請會說北京話的人教他們讀寫中文,而老師晚上惡補,白天現學現賣,便成為接收初期常見的教學現象。
經歷過那段中文師資青黃不接時代的人,或許都還有相同的記憶:學校突然就不再使用日語教學,而是改用福佬語或客語等方言來輔助教授,接著再過沒多久,老師們就開始教起「ㄅ、ㄆ、ㄇ」的注音符號來。
除此之外,由於老師們自己對北京話也十分陌生,所以往往課上到一半,就會忘了怎麼發音才正確,此時師生們也只能在課堂上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是好;再不然就是發音怪異,引得笑果連連,雖然場面尷尬,卻也十分的有趣。
總之,戰後初期的國語教育,就是在一邊嘗試錯誤,一邊汲取經驗的混亂情形中,師生一起共學成長。
除了師資問題外,學校的中文教材也沒有正式的版本,為了應付沒有課本的窘境,於是出現了暫用課本。這些暫用課本有的是臺灣接收單位臨時草編印製,有些是學校教師自行編寫,有時則是借用日治時代漢學書房的教材,也有來自中國大陸所印行的漢文讀本,各式各樣琳瑯滿目。
直到接收半年之後,教材混亂的局面才逐漸消失,政府頒布統一的課本,各地機關學校也開始舉辦教師們的北京話教學,努力增進教師的國語程度。
當時的小學課本,內容大都以重塑國家意識為主,加強臺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並灌輸日本是全中國人的敵人等排日思想,期待能在小學生牙牙學國語的過程中,去除日治時代的教育思想。對於才剛剛結束皇民化運動的師生而言,臺灣這班教育列車的轉彎角度,似乎是太大了些。
牛奶與麵粉袋──美援時代的小學風景
「臺灣社會處處可見『中美合作』的字樣,包括小孩穿的褲子、衣服等,都可看見用『美援』麵粉袋做的。國小的孩子甚少有人穿內褲(我個人就是這樣子長大的),因為那不是衛生與否的問題,而是貧窮與不足的現實。」 ──臺灣長老教會牧師 盧俊義〈這也是一個契機〉
生在一九五○年代,吃過「中美合作」麵粉或是喝過「美援」牛奶的臺灣人,可能還會想起「中國中國童子軍,美國美國橡皮筋,英國英國大老鷹,共匪共匪沒良心」這段順口溜吧!
二次大戰結束後,蘇聯靠著占領區的優勢,在東歐各國扶植共產政權,並且暗中支持西歐、南歐地區的共黨活動,造成世界各國恐慌。有鑑於此,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援助計畫,藉由提供大量物資金錢援助西歐國家,重建戰後歐洲盟國經濟,以防堵共產主義的擴張。由於「馬歇爾計畫」在西歐的成效卓著,加以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東亞區域開始陷入共產危機,美國於是開始將實施金援的對象擴及亞洲幾個急待振興經濟的國家,臺灣便是其中之一。
西元一九四九年六月,臺灣政府成立了「美援運用聯合委員會」,隔年美國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五千萬美元的援華案,第一批美援物資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正式進入臺灣,開啟了臺灣的美援時代。
美援與民生最直接相關的地方,就是提供牛奶和麵粉等民生物資的援助。歷經戰火摧殘的臺灣社會極度貧困,能夠領到外國運來的生活物資,人人都感到很稀奇也很興奮。
最高興的莫過於孩子們,那時所有的孩子最期待的事就是到衛生所喝牛奶,禮拜天和媽媽一塊上教堂說「阿們」,然後領麵粉。領來的麵粉吃完後,裝麵粉的袋子還會被勤儉持家的媽媽裁成內衣褲,於是當時小學生最流行的另類衣服,就是印有星條旗圖樣的麵粉衣褲,掀開制服還會赫然發現內衣上有兩手緊握的「中美合作」圖案。
除了牛奶和麵粉,早期臺灣的若干基本建設,如電力、自來水、交通、港口和鐵路等,也是依賴美援才得以興建完成,桃園的石門水庫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一些鄉村學校由於資金不足,雖然校舍年久失修且嚴重不足,卻無法整建,於是美援又成為重要的資金來源。直到現在南部還有幾所小學校園內,保留有那段時期所建的美援校舍,這些建築的外觀上有著不同於臺灣的美式宿舍風格,為鄉村的天空增添了異國的溫馨。
從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五這十五年間,臺灣每年平均獲得一億美元的援助,當美援中止時,許多人擔心臺灣的經濟會再度陷入另一個谷底。但是事實證明,打拼的臺灣人善用美援奠下的基礎,成就了日後的經濟起飛。雖然美援時代已經成為歷史,但香濃的牛奶和土土的麵粉袋內衣,依然深植在美援世代的小學生記憶中,久久不散。
從頭看到腳──小學生百年造型
「公學校沒有學生制服,同學們各穿各的。我穿的是臺灣式的衫與褲,衫叫做「對襟仔衫」,用鈕仔扣,褲是寬而軟的,穿上後要疊合並用布帶子束緊腰部。我日常一下床就赤足踏地,大部分是赤著腳上學。」──楊基銓《清水國小創校百百週年專輯》
◎從辮子到長髮
如果將臺灣百年來的小學生照片一字排開,你會發現這百年間的小學生造型上,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頭髮!從日治初期的辮子頭,中期之後的光頭,戰後一九六○年代的平頭,到現在各式各樣的活潑髮型,這一路的造型演變,真的是趣味無窮。
日治初期,臺灣剛脫離清朝的統治不久,在生活習慣上大都延續著前朝的遺風,甚至連吸食鴉片、纏足、蓄髮留辮等惡習都沒有改變,這是由於日本政府害怕驟然變革會引起臺人的反抗,因此採取較為寬鬆放任的管理。於是,學校裡的男學生仍然是頂著光亮的額頭,後腦勺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上學,與梳著簡潔西式髮型的日本老師,形成強烈的對比。
當日人治臺的局勢漸漸穩定之後,認為臺人的舊慣惡習影響社會甚鉅,甚至會造成施政阻礙,因此決定推動生活革新,頒佈法令針對辮髮等惡習採行漸禁政策。學校基本上是政府當局最容易推行剪辮的場所,因此男學生率先被要求剪去長辮,理成清爽的短髮,但當時一般社會大眾大多未響應。直到一九一一年由黃玉階、謝汝詮等人共同發起「斷髮不改裝會」,提出剪辮的呼籲,才在各地吹起剪辮的風氣,臺灣男人不分老少終於願意擺脫辮髮的綑綁。
進入日治中期,一來是因為頭髮清潔衛生的問題,二來也可能是小學教育開始強調軍武精神,男孩子的髮型便清一色改成光頭。至於女孩子的髮型變化,則是從早期常見的清末「鉸剪眉」式髮型,變為日治中期規定的齊耳短髮(亦稱河童頭),不僅符合乾淨整齊的精神,校方也便於管理。
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初期,臺灣社會百廢待興,由於衛生環境不佳,為防範頭癬、寄生蟲等衛生問題,男女小學生的髮型大致延續日治時代的規定,但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便逐漸放寬頭髮的限制,小男生的頭髮從光頭、小平頭到大平頭,小女孩則是從清湯掛麵式的「西瓜皮」,逐漸自然留長。到了一九七○年代後,小學生原本呆板制式的髮型開始有了較大的變化,男孩子不再以平頭為主,女孩子也不是只有直髮的單一髮式,學校不再硬性規定學生們的頭上風景,但仍會要求男生的頭髮不得過長,而女生雖可燙髮,但髮型不要太怪異。
時至今日,小學生的髮型已愈來愈多樣化,也愈來愈能展現青春的活力,偶爾還會看到小男孩留著酷炫短髮卻在腦勺處留下一撮長長的髮絲,隨風飄逸,於是你終於明白,原來百年前的清末辮髮,已是現今髮式的流行話語。
◎從赤腳到便服
「臺灣錢淹腳目」是流傳臺灣民間數百年的諺語,隱喻臺灣自古以來就是賺錢淘金之地,但諷刺的是,對早期農業臺灣的兒童而言,「窮到沒鞋穿」才是真正的生活寫照。
翻開日治初期的小畢業照,不難發現新式學校設置之初,並沒有特別要求小學生要穿統一的制服,因此老師的穿著筆挺整齊,學生卻是百花齊放。一般家境小康的子弟通常上著臺灣衫,下穿大檔褲,腳上套著軟布鞋,就是當時服裝的主流。而最特別的是,女孩子還有裹小腳的習慣,直到一九○○年,黃玉階首先倡組「臺北天然足會」,其後各地紛紛成立「解纏會」,臺灣小女孩的腳才終於獲得解放。
相對於富裕人家的小孩,一般務農子女的雙腳早就解放了。俗諺說:「現吃都不夠了,哪有多餘的曬成乾。」當時的清貧家庭連三餐都難有溫飽,哪有餘錢幫小孩添購衣鞋?因此孩子們大多是赤腳薄衣上下學,日夜操勞下練就一雙「鐵腳功」與「金鐘罩」,穿上新衣新鞋反而彆扭不舒服。
隨著學制步上軌道,學校開始希望學生的衣著統一,一九一九年,殖民政府頒布〈臺灣教育令〉,對學生的衣著服飾開始有明確的規範。制服以「日式西化」為風格,材質以棉質為主,男生制服上衣為襯衫領、對襟五顆扣,長褲要過膝並著黑皮鞋或白布鞋,帽子為軟式且其上須有校徽。女生制服則白襯衫配藍背心裙為主,但「水手領」打領巾形式的上衣也很常見。此外,為求展現特色,也允許各校在制服上做一些設計變化。
二次大戰時,學生的制服又有了變化。為求減少空襲時的傷亡,衣服顏色改以草綠色為主,並須繡上名條以利辨識,女生制服則出現連身裙與工作褲的式樣,大體而言,戰時由於政經不穩,因此學校執行校服的規定就比較鬆散,學生穿著也比較隨便了。
制服的規定對經濟條件較佳的子女並不成問題,因為專門的商店或裁縫店都可訂製,但環境較差的人家就得向學校索取服裝的樣式圖,自己DIY動手做。做好的制服往往得穿上好些年,而且是兄姊穿完留給弟妹穿,代代相傳直到破爛不堪。衣服還可以自己做,鞋子就困難多了,許多家庭買不起皮鞋,只能讓孩子不分寒暑的赤腳上學,直到畢業典禮當天,他們依然只能隱身在穿鞋同學的身後,遮掩那亦裸而尷尬的雙腳。
臺灣戰後初期,學生制服樣式又有些變動,男生夏裝大多是清一色的白色上衣、藍褲子,冬天則全身卡其服。女生夏裝大多為白上衣配上藍色吊帶百折裙,冬天則換成卡其上衣搭配深色長褲。這樣的制服樣式初時是全國中小學通用,不久之後,部分小學開始自行設計各校特有的服裝樣式,就連體育課時所穿的運動服也都由學校自行設計,小學的整體樣式,不再如從前那樣呆板,逐漸變得活潑多樣化,而且富有美感。
令人驚訝的是,在小學制服的歷史演變中,臺北的太平國小獨樹一幟的維持日治時代的制服型式,百年來沒有太大變化,算是相當少見的特例,這或許代表著太平國小身為「大稻埕第一」的驕傲與堅持吧!
一九八○年代開始,臺灣經濟起飛,社會逐漸民主開放,教育部不再統一規範學校制服的樣式,改由學校自行決定,逐漸解除學生的衣著綑綁。從此,臺灣的孩們開始穿著五顏六色的便服上學,將小學校園妝點的更加生動可愛。
然而,當赤腳上學已成為校園絕響,清寒子弟不必再為皮鞋煩惱,卻開始為明天的便服而苦惱時,倒也不讓人想起從前的日子,懷念那母親親手縫補制服的古早時代。
「竹藪中首先突出長槍,最後六名枕藉於稻田中。宛如實踐自我宣說的精神而倒地,這是多麼令人慨嘆至極的事。我在東京接到電報後,一夜哭到天亮。」 ──伊澤修二〈六氏周年祭弔唁演說〉
日本領臺的第一年,首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藤修二,選定臺北八芝蘭(今士林)的芝山岩,創辦了臺灣第一所新式初等教育機構──芝山岩學堂,從此芝山岩便被視為臺灣小學教育的起源地。然而,它的重要性卻不僅於此,在老一輩的人心中,它還是日治時代的師範教育聖地,因為這裡曾發生過一件震驚日臺的「謀殺案」──六氏事件(亦稱「芝山岩事件」)。
六氏事件中的「六氏」,指的是六位跟隨伊澤修二來臺建學的日籍教師,其姓名分別為: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中島長吉、井原順之助、桂金太郎與平井數馬。這六位教師多受過日本的師範教育,被伊澤修二招募來臺從事教育工作,是芝山岩學堂的第一批教師。一八九六年的元旦,六人原本準備一早下山,搭船到臺灣總督府參加慶祝新年大會,但是在半路上聽說有臺灣抗日軍襲擊臺北城,因此決定立即返回芝山岩避難,不料就在回校途中遭到當地人伏擊殺害,並將屍首棄置於芝山岩的山林中。
日本當局得知此事後大為震驚總督府乃向士林居民採取武力鎮壓行動,並造成當地一些百姓無辜犧牲。這件事不僅使芝山岩學堂的教學活動被迫暫時中斷,同時也讓招募日人教師來臺教書的計畫無法順利推展。為了撫平六氏事件的衝擊,並避免日籍教師對來臺工作望而卻步,總督府想出了一個方法,他們將這次事件予以美化昇華,把不幸殉難的六位教師塑造為捨己為人、犧牲奉獻的崇高教育典範,並以此激發其他教師們的熱血精神,讓老師們打從心裡認同:為教育犧牲性命是神聖而偉大的,一位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須手拿粉筆教學不輟,直到鞠躬盡瘁、生命止息。這就是從六氏事件衍生出的臺灣師範教育的神聖圖騰―芝山岩精神。
為了宣揚六氏先生的芝山岩精神,總督府於同年七月一日在案發地點設立「學務官僚遭難紀念碑」,並規定每年的二月一日為「六氏事件紀念日」,必須在芝山岩上舉行盛大的祭典。一九三○年時,更興建芝山岩神社,供奉六氏先生與在臺灣過世的日籍教育工作者。六氏的故事還被納入小學課本中,每到六氏殉難日,臺北城內的學校便會安排小學生上芝山岩參拜,遠在外地的也會在學校舉辦紀念儀式,甚至連小學生的修學旅行,也會將參拜芝山岩神社列入行程。總督府相信,在如此的言教、身教下,臺灣的孩子們將永遠記得這偉大的故事。
只是,歷史總是戲謔多變,二次大戰後,臺灣政權興替,中華民國政府的師範教育強調中國儒家傳統的「有教無類」、「傳道授業解惑」思想,不再灌輸這種為教育奉獻在所不辭的日式犧牲精神。五十年後,同樣是芝山岩六位老師的遭難故事,殺害者卻成為抗日的民族英雄,如今,誰還會記得荒煙蔓草間的「六氏先生之墓」與「學務官僚遭難紀念碑」,在百年前曾是臺灣師範精神的新起點。
公學校與小學校──小學教育的一國兩制
「公學校以對本島人子弟施予德教、授予實學,以養成國民之性格,並使其精通國語為主旨。」──西元1898年 〈公學校規則〉第一條
在日治時代,彰化二水地區有兩所小學毗鄰而建:二八水公學校與二八水小學校,這兩所學校僅以一道綠籬相隔,但是綠籬的兩邊,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在公學校裡上課的是臺灣人子弟,學生大多光著腳丫,身上的粗布短衣上散佈著東一塊、西一塊的補丁,書包則是一塊大布巾,將書本裹成一個包袱背著上下學。另一邊的小學校則是在臺日人子弟就讀的學校,這裡的學生穿著乾淨筆挺的漂亮制服和擦得發亮的皮鞋,手中提著整潔的大書袋,抬頭挺胸的走進教室。除了物質環境的兩極差異,這兩所學校在師資、學生待遇、學校設施,乃至於教學內容上,都有截然不同的差別。這就是日治時代小學之間,特殊的一國兩制狀況。
日本的治臺政策,一直都是採取臺日不同的差別待遇,就連教育體制也不例外。從領臺之初,臺灣的教育制度就被規劃為臺日雙軌制,日人有其專屬的教育系統,臺人也有特別設計的教育體制。後來,隨著日本人到臺灣任職的人數日漸增多,日人子女的就學問題就成為一項急待解決的工作。因此,總督府便於一八九八年間,先在臺北、基隆、新竹、臺南四個較大的城市設置小學校,作為日人子弟的教育機構,之後並陸續於全臺各地增建小學校。
臺灣小學校的課程與日本內地的學校並無二致,而專為臺人子弟設立的公學校,則以教授國語及國民道德為主。
雖然一次大戰後,在「大正民主」風潮的吹拂下,日本與臺灣都揚起「以平等無差別之待遇對待臺灣」的輿論,日本當局也在西元一九二二年發布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強調「內臺共學」的政策,不分日人臺人,都可就讀同樣的學校,但實際上,日人所讀的小學校仍以日語程度的差別為由,不太願意收不常用日語的臺籍兒童,因此日治時代的小學教育,仍大致維持臺灣人讀公學校,日本人讀小學校的情況,只有少數臺灣子弟能擠入小學校的窄門。
日語臺語說不通──北京話最紅
我是臺灣人,你是臺灣人,他是臺灣人,我們都是臺灣人。 〈第一課 臺灣人〉
我們的祖宗是福建人,是廣東人。福建人、廣東人、臺灣人都是中國人。 〈第二課 中國人〉──《臺灣暫用小學國語課本甲篇》
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各級學校自然不能再以日語教學,一切課程都改用新文字──中文來書寫,主流語言則是距離臺灣千里遠的「北京話」。
這下子,問題就來了,臺籍教師皆出身於日本師範體系,學校說的是日語,筆下寫的是日文,生活中則以福佬、客家或原住民語溝通,對於北京話相當陌生,只有曾經到中國留學或久居中國大陸的極少數臺灣人,才可能懂得北京官話──也就是說,學校的國文師資有了十分嚴重的短缺。為了避免學校課程中斷,當時許多小學老師都會利用晚上的時間,聘請會說北京話的人教他們讀寫中文,而老師晚上惡補,白天現學現賣,便成為接收初期常見的教學現象。
經歷過那段中文師資青黃不接時代的人,或許都還有相同的記憶:學校突然就不再使用日語教學,而是改用福佬語或客語等方言來輔助教授,接著再過沒多久,老師們就開始教起「ㄅ、ㄆ、ㄇ」的注音符號來。
除此之外,由於老師們自己對北京話也十分陌生,所以往往課上到一半,就會忘了怎麼發音才正確,此時師生們也只能在課堂上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是好;再不然就是發音怪異,引得笑果連連,雖然場面尷尬,卻也十分的有趣。
總之,戰後初期的國語教育,就是在一邊嘗試錯誤,一邊汲取經驗的混亂情形中,師生一起共學成長。
除了師資問題外,學校的中文教材也沒有正式的版本,為了應付沒有課本的窘境,於是出現了暫用課本。這些暫用課本有的是臺灣接收單位臨時草編印製,有些是學校教師自行編寫,有時則是借用日治時代漢學書房的教材,也有來自中國大陸所印行的漢文讀本,各式各樣琳瑯滿目。
直到接收半年之後,教材混亂的局面才逐漸消失,政府頒布統一的課本,各地機關學校也開始舉辦教師們的北京話教學,努力增進教師的國語程度。
當時的小學課本,內容大都以重塑國家意識為主,加強臺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並灌輸日本是全中國人的敵人等排日思想,期待能在小學生牙牙學國語的過程中,去除日治時代的教育思想。對於才剛剛結束皇民化運動的師生而言,臺灣這班教育列車的轉彎角度,似乎是太大了些。
牛奶與麵粉袋──美援時代的小學風景
「臺灣社會處處可見『中美合作』的字樣,包括小孩穿的褲子、衣服等,都可看見用『美援』麵粉袋做的。國小的孩子甚少有人穿內褲(我個人就是這樣子長大的),因為那不是衛生與否的問題,而是貧窮與不足的現實。」 ──臺灣長老教會牧師 盧俊義〈這也是一個契機〉
生在一九五○年代,吃過「中美合作」麵粉或是喝過「美援」牛奶的臺灣人,可能還會想起「中國中國童子軍,美國美國橡皮筋,英國英國大老鷹,共匪共匪沒良心」這段順口溜吧!
二次大戰結束後,蘇聯靠著占領區的優勢,在東歐各國扶植共產政權,並且暗中支持西歐、南歐地區的共黨活動,造成世界各國恐慌。有鑑於此,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援助計畫,藉由提供大量物資金錢援助西歐國家,重建戰後歐洲盟國經濟,以防堵共產主義的擴張。由於「馬歇爾計畫」在西歐的成效卓著,加以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東亞區域開始陷入共產危機,美國於是開始將實施金援的對象擴及亞洲幾個急待振興經濟的國家,臺灣便是其中之一。
西元一九四九年六月,臺灣政府成立了「美援運用聯合委員會」,隔年美國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五千萬美元的援華案,第一批美援物資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正式進入臺灣,開啟了臺灣的美援時代。
美援與民生最直接相關的地方,就是提供牛奶和麵粉等民生物資的援助。歷經戰火摧殘的臺灣社會極度貧困,能夠領到外國運來的生活物資,人人都感到很稀奇也很興奮。
最高興的莫過於孩子們,那時所有的孩子最期待的事就是到衛生所喝牛奶,禮拜天和媽媽一塊上教堂說「阿們」,然後領麵粉。領來的麵粉吃完後,裝麵粉的袋子還會被勤儉持家的媽媽裁成內衣褲,於是當時小學生最流行的另類衣服,就是印有星條旗圖樣的麵粉衣褲,掀開制服還會赫然發現內衣上有兩手緊握的「中美合作」圖案。
除了牛奶和麵粉,早期臺灣的若干基本建設,如電力、自來水、交通、港口和鐵路等,也是依賴美援才得以興建完成,桃園的石門水庫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一些鄉村學校由於資金不足,雖然校舍年久失修且嚴重不足,卻無法整建,於是美援又成為重要的資金來源。直到現在南部還有幾所小學校園內,保留有那段時期所建的美援校舍,這些建築的外觀上有著不同於臺灣的美式宿舍風格,為鄉村的天空增添了異國的溫馨。
從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五這十五年間,臺灣每年平均獲得一億美元的援助,當美援中止時,許多人擔心臺灣的經濟會再度陷入另一個谷底。但是事實證明,打拼的臺灣人善用美援奠下的基礎,成就了日後的經濟起飛。雖然美援時代已經成為歷史,但香濃的牛奶和土土的麵粉袋內衣,依然深植在美援世代的小學生記憶中,久久不散。
從頭看到腳──小學生百年造型
「公學校沒有學生制服,同學們各穿各的。我穿的是臺灣式的衫與褲,衫叫做「對襟仔衫」,用鈕仔扣,褲是寬而軟的,穿上後要疊合並用布帶子束緊腰部。我日常一下床就赤足踏地,大部分是赤著腳上學。」──楊基銓《清水國小創校百百週年專輯》
◎從辮子到長髮
如果將臺灣百年來的小學生照片一字排開,你會發現這百年間的小學生造型上,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頭髮!從日治初期的辮子頭,中期之後的光頭,戰後一九六○年代的平頭,到現在各式各樣的活潑髮型,這一路的造型演變,真的是趣味無窮。
日治初期,臺灣剛脫離清朝的統治不久,在生活習慣上大都延續著前朝的遺風,甚至連吸食鴉片、纏足、蓄髮留辮等惡習都沒有改變,這是由於日本政府害怕驟然變革會引起臺人的反抗,因此採取較為寬鬆放任的管理。於是,學校裡的男學生仍然是頂著光亮的額頭,後腦勺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上學,與梳著簡潔西式髮型的日本老師,形成強烈的對比。
當日人治臺的局勢漸漸穩定之後,認為臺人的舊慣惡習影響社會甚鉅,甚至會造成施政阻礙,因此決定推動生活革新,頒佈法令針對辮髮等惡習採行漸禁政策。學校基本上是政府當局最容易推行剪辮的場所,因此男學生率先被要求剪去長辮,理成清爽的短髮,但當時一般社會大眾大多未響應。直到一九一一年由黃玉階、謝汝詮等人共同發起「斷髮不改裝會」,提出剪辮的呼籲,才在各地吹起剪辮的風氣,臺灣男人不分老少終於願意擺脫辮髮的綑綁。
進入日治中期,一來是因為頭髮清潔衛生的問題,二來也可能是小學教育開始強調軍武精神,男孩子的髮型便清一色改成光頭。至於女孩子的髮型變化,則是從早期常見的清末「鉸剪眉」式髮型,變為日治中期規定的齊耳短髮(亦稱河童頭),不僅符合乾淨整齊的精神,校方也便於管理。
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初期,臺灣社會百廢待興,由於衛生環境不佳,為防範頭癬、寄生蟲等衛生問題,男女小學生的髮型大致延續日治時代的規定,但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便逐漸放寬頭髮的限制,小男生的頭髮從光頭、小平頭到大平頭,小女孩則是從清湯掛麵式的「西瓜皮」,逐漸自然留長。到了一九七○年代後,小學生原本呆板制式的髮型開始有了較大的變化,男孩子不再以平頭為主,女孩子也不是只有直髮的單一髮式,學校不再硬性規定學生們的頭上風景,但仍會要求男生的頭髮不得過長,而女生雖可燙髮,但髮型不要太怪異。
時至今日,小學生的髮型已愈來愈多樣化,也愈來愈能展現青春的活力,偶爾還會看到小男孩留著酷炫短髮卻在腦勺處留下一撮長長的髮絲,隨風飄逸,於是你終於明白,原來百年前的清末辮髮,已是現今髮式的流行話語。
◎從赤腳到便服
「臺灣錢淹腳目」是流傳臺灣民間數百年的諺語,隱喻臺灣自古以來就是賺錢淘金之地,但諷刺的是,對早期農業臺灣的兒童而言,「窮到沒鞋穿」才是真正的生活寫照。
翻開日治初期的小畢業照,不難發現新式學校設置之初,並沒有特別要求小學生要穿統一的制服,因此老師的穿著筆挺整齊,學生卻是百花齊放。一般家境小康的子弟通常上著臺灣衫,下穿大檔褲,腳上套著軟布鞋,就是當時服裝的主流。而最特別的是,女孩子還有裹小腳的習慣,直到一九○○年,黃玉階首先倡組「臺北天然足會」,其後各地紛紛成立「解纏會」,臺灣小女孩的腳才終於獲得解放。
相對於富裕人家的小孩,一般務農子女的雙腳早就解放了。俗諺說:「現吃都不夠了,哪有多餘的曬成乾。」當時的清貧家庭連三餐都難有溫飽,哪有餘錢幫小孩添購衣鞋?因此孩子們大多是赤腳薄衣上下學,日夜操勞下練就一雙「鐵腳功」與「金鐘罩」,穿上新衣新鞋反而彆扭不舒服。
隨著學制步上軌道,學校開始希望學生的衣著統一,一九一九年,殖民政府頒布〈臺灣教育令〉,對學生的衣著服飾開始有明確的規範。制服以「日式西化」為風格,材質以棉質為主,男生制服上衣為襯衫領、對襟五顆扣,長褲要過膝並著黑皮鞋或白布鞋,帽子為軟式且其上須有校徽。女生制服則白襯衫配藍背心裙為主,但「水手領」打領巾形式的上衣也很常見。此外,為求展現特色,也允許各校在制服上做一些設計變化。
二次大戰時,學生的制服又有了變化。為求減少空襲時的傷亡,衣服顏色改以草綠色為主,並須繡上名條以利辨識,女生制服則出現連身裙與工作褲的式樣,大體而言,戰時由於政經不穩,因此學校執行校服的規定就比較鬆散,學生穿著也比較隨便了。
制服的規定對經濟條件較佳的子女並不成問題,因為專門的商店或裁縫店都可訂製,但環境較差的人家就得向學校索取服裝的樣式圖,自己DIY動手做。做好的制服往往得穿上好些年,而且是兄姊穿完留給弟妹穿,代代相傳直到破爛不堪。衣服還可以自己做,鞋子就困難多了,許多家庭買不起皮鞋,只能讓孩子不分寒暑的赤腳上學,直到畢業典禮當天,他們依然只能隱身在穿鞋同學的身後,遮掩那亦裸而尷尬的雙腳。
臺灣戰後初期,學生制服樣式又有些變動,男生夏裝大多是清一色的白色上衣、藍褲子,冬天則全身卡其服。女生夏裝大多為白上衣配上藍色吊帶百折裙,冬天則換成卡其上衣搭配深色長褲。這樣的制服樣式初時是全國中小學通用,不久之後,部分小學開始自行設計各校特有的服裝樣式,就連體育課時所穿的運動服也都由學校自行設計,小學的整體樣式,不再如從前那樣呆板,逐漸變得活潑多樣化,而且富有美感。
令人驚訝的是,在小學制服的歷史演變中,臺北的太平國小獨樹一幟的維持日治時代的制服型式,百年來沒有太大變化,算是相當少見的特例,這或許代表著太平國小身為「大稻埕第一」的驕傲與堅持吧!
一九八○年代開始,臺灣經濟起飛,社會逐漸民主開放,教育部不再統一規範學校制服的樣式,改由學校自行決定,逐漸解除學生的衣著綑綁。從此,臺灣的孩們開始穿著五顏六色的便服上學,將小學校園妝點的更加生動可愛。
然而,當赤腳上學已成為校園絕響,清寒子弟不必再為皮鞋煩惱,卻開始為明天的便服而苦惱時,倒也不讓人想起從前的日子,懷念那母親親手縫補制服的古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