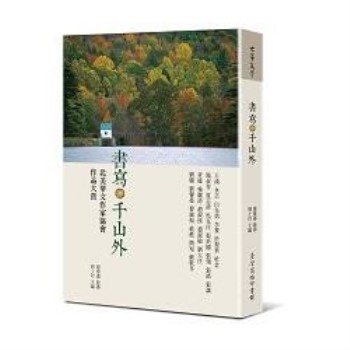父親歸真 文◎白先勇 名家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台灣,那正是大陸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台,認為台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
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他毅然到台灣。
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代。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因心臟病突發逝世,醫生研判,是冠狀動脈梗塞。二日一早,父親原擬南下參加高雄加工區落成典禮,參謀吳祖堂來催請,才發覺父親已經倒臥不起。前一天晚上,父親還到馬繼援將軍家中赴宴,回家後,大概淩晨時分突然病發。
當時我在美國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誠從紐約打電話來通知的。當晚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廳中坐到天明。父親驟然歸真,我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悲傷,而是肅然起敬。父親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們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親的辭世,我最深的感觸,不僅是他個人的亡故,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跟著父親一齊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載著的沉重而又沉痛之歷史記憶: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國共內戰。我感到一陣墜入深淵的失落,像父親那樣鋼鐵堅實的生命,以及他那個大起大落、轟轟烈烈的時代,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成為過去。
父親在台灣歸真,是他死得其所。台灣是中華的版圖,是國民黨的所在地,他一生奮鬥,出生入死,身後葬於台北六張犁的回教公墓,那是他最終的歸宿。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台灣,那正是大陸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台,認為台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他毅然到台灣。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代。當時韓戰未起,共軍隨時可以渡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正處於險境環生的形勢,父親入台,就是打算要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父親參加過武漢辛亥革命,締造民國;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抗戰抵抗外敵,護衛國土;國共內戰,父親由武漢戰退到南寧,與共軍打到不剩一兵一卒,雖然最後無力迴天,但牽制共軍數月,讓國軍有時間遷台。中共曾數度提出「局部和平」,都被父親嚴拒了。入台與共患難,是父親當時唯一的選擇;流亡海外老死異國,對他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他當然了解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後可能遭遇到的風險,但他心中坦蕩,回台灣,是向中華民國政府報到歸隊。
他在台灣的晚年過得並不平靖,沒有受到一個曾經對國家有過重大貢獻的軍人應該獲得的尊重。父親並未因此懷憂喪誌。在台灣,他於逆境中,始終保持著一份凜然的尊嚴,因為他深信自己功在黨國,他的歷史地位,絕不是一些猥瑣的特務跟監動作所能撼搖。最後他死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壇重修落成,他替鄭成功書下「仰不愧天」的匾額。綜觀父親一生,這四個字他自己也足以當之。
父親的喪禮是最高標準的國葬儀式。出殯那天,在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總統蔣中正以下,國府黨政軍高級官員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達到千人。軍事團體有國防部,陸、海、空、勤、警備各總部」,由部長及總司令率團獻花致祭。公祭儀式結束後,隨即行蓋棺禮,父親官階一級上將,按軍禮規定由四位現役陸軍一級上將顧祝同、周至柔、黃鎮球、余漢謀執旗,覆蓋棺木上,典禮儀式莊嚴隆重。出殯行列,由摩托車隊開路,隨後為軍樂隊及儀隊,靈車經過時,路上很多軍人均向靈車舉手敬禮。父親靈櫬於十二時二十分運抵六張犁回教公墓,按回教儀式下葬。回教教長領導數百位回教教友共同在墓前為父親祈禱。
這次公祭,軍人特別多,上至將官,下至士兵,在祭拜中對父親都表達了一份由衷的崇敬,這也是因為數十年來父親在軍中建立的威望所致,父親被尊為「當代最傑出戰略家」,諸葛盛名,並非虛得。
前來祭悼的,還有不少本省人士、台籍父老,很多與父親並不相識,攜幼扶老,到父親靈堂獻花祭拜。由他們大量的挽聯、挽詩中得知,他們前來吊唁,是因為感懷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措施中,對台灣民眾所行的一些德政。公祭各方送來的挽聯、挽詩、挽額、誄詞,有數百幀,多是父親的軍中同僚、部屬撰寫的,下論都很公允,有的真情畢露,十分感人。父親歸真,深深觸動了他們的家國哀思,反攻復國大業未竟,八方風雨一代名將遽然長逝。但我在這裡特別挑選出嚴慶齡先生的挽聯,做為代表。嚴慶齡先生是從上海到台灣的企業家,裕隆汽車集團的創辦人,他並非軍政界人士,跟父親並無私交,平日也無往來,但嚴先生那一輩的人經過北伐、抗戰,對父親的人格及事跡是有所認識的。
嚴慶齡先生的挽聯,很能代表他那一代的中國人對父親的評價:
「治兵則寒敵膽,為政則得民心,秉筆記宏猷不讓汾陽功業;
於黨國矢忠誠,於順逆能明辨,蓋棺昭大節無慚諸葛聲名」
─嚴慶齡敬挽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父親喪禮公祭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舉行。上午七時五十分,蔣中正抵達殯儀館靈堂,第一個向父親靈前獻花致祭。蔣面露戚容,神情悲肅,當天在所有前來公祭父親的人當中,恐怕沒有人比他對父親之死有更深刻、更復雜的感觸了。蔣、白之間,長達四十年的恩怨分合,其糾結曲折,微妙多變,絕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
父親與蔣中正四十年漫長的關系,分合之間,要分階段。
民國十五年北伐,廣州誓師,蔣中正總司令三顧茅廬,力邀父親出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並兼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一路北上打到山海關,最後完成北伐。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蔣、白兩人共同打天下的階段。
民國十七年北伐甫結束,突然爆發「蔣桂戰爭」,廣西與中央對峙七年,蔣、白分離。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開始,蔣委員長派專機至廣西將父親接到南京,任命父親為副參謀總長,並肩八年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抗戰時期,蔣對父親頗為倚重,重要戰爭如「台兒莊之役」、「三次長沙會戰」、「崑崙關之役」等,莫不賦以重任。
抗戰勝利後,蔣中正主席任命父親為第一屆國防部長。可是,國共內戰後期因父親助李宗仁選副總統,蔣、白之間又出現了嫌隙。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及其後遺症,更因兩封籲請國際調停的電報,蔣、白關系瀕臨決裂。在台灣十七年,蔣中正與父親的關系,始終沒有完全修復。
持平而論,蔣中正對父親的軍事才能是深有所知的。在國家安危的關鍵時刻,蔣往往會派遣父親前往解決困難:如指揮「台兒莊之役」,督戰「四平街之役」,「二二八事件」赴台宣慰等,在在都顯示蔣對父親的器重。但蔣中正用人,對領袖忠貞是首要條件,可是父親個性剛毅正直,不齒唯唯諾諾,而且有關國家大事,經常直言不諱,加上父親的「桂系」背景,蔣對父親的忠貞是有所疑慮的,並不完全信任。
事實上,父親一直是蔣中正的最高軍事幕僚長,扮演著襄贊元戎的角色,絕對無「取而代之」的僭越之想。李宗仁選副總統,父親最初是強烈反對的。民國三十八年「徐蚌會戰」,國軍潰敗,蔣中正下野,李宗仁代總統,那也是大勢所逼。事實上,當時黨政軍的資源還是由蔣掌握,他自己不引退,沒有人能夠強迫他。「逼宮」之說,並非事實。父親一生把國家利益放在最前面,當時國民黨政權危在旦夕,父親才「不避斧鉞」上書蔣中正,提議敦促美、英、蘇三國出面調節和平。依父親估計,如果美國願意派空軍一大隊進駐南京,青島美軍不撤退,或可阻共軍渡江,這也是當時唯可使國府轉危為安的計策了。
現在台灣及大陸一些人論及父親與蔣中正的關系,往往喜歡誇大兩人之間的矛盾,而且把矛盾變得瑣碎。其實蔣、白兩人之間的一些衝突,首先在二人的個性,二雄難以並立,兩個強人相處,衝撞勢必難免。而且古有明訓:「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其次,是兩人在國家政策方面意見分歧時起的衝突。比如「徐蚌會戰」,蔣中正與父親在這關係中華民國命運的戰役上,出現激烈爭執,前後因果,使兩人關系產生難以彌合的裂痕。但論者往往忽略了,蔣中正與父親也曾有過長期緊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結果的關係,父親在「北伐」、「抗戰」所立的戰功,亦是蔣充分授權下得以完成的。蔣中正與父親分合之間的關係,往往影響國家的安危,他們兩人在國共內戰期間,軍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協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遺憾。父親曾感嘆過:「總統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話他沒有聽。」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對「四平街之役」、「徐蚌會戰」的一些獻策吧。楚漢相爭,大將韓信替漢高祖劉邦打下天下,功高震主,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為呂后、蕭何設計殘害於長樂宮。《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高祖「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這是太史公司馬遷對人性了解最深刻的一筆。君臣一體,自古所難。
(原載於《父親與民國》下冊,〈台灣歲月〉)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台灣,那正是大陸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台,認為台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
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他毅然到台灣。
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代。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因心臟病突發逝世,醫生研判,是冠狀動脈梗塞。二日一早,父親原擬南下參加高雄加工區落成典禮,參謀吳祖堂來催請,才發覺父親已經倒臥不起。前一天晚上,父親還到馬繼援將軍家中赴宴,回家後,大概淩晨時分突然病發。
當時我在美國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誠從紐約打電話來通知的。當晚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廳中坐到天明。父親驟然歸真,我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悲傷,而是肅然起敬。父親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們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親的辭世,我最深的感觸,不僅是他個人的亡故,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跟著父親一齊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載著的沉重而又沉痛之歷史記憶: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國共內戰。我感到一陣墜入深淵的失落,像父親那樣鋼鐵堅實的生命,以及他那個大起大落、轟轟烈烈的時代,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成為過去。
父親在台灣歸真,是他死得其所。台灣是中華的版圖,是國民黨的所在地,他一生奮鬥,出生入死,身後葬於台北六張犁的回教公墓,那是他最終的歸宿。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台灣,那正是大陸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台,認為台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他毅然到台灣。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代。當時韓戰未起,共軍隨時可以渡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正處於險境環生的形勢,父親入台,就是打算要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父親參加過武漢辛亥革命,締造民國;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抗戰抵抗外敵,護衛國土;國共內戰,父親由武漢戰退到南寧,與共軍打到不剩一兵一卒,雖然最後無力迴天,但牽制共軍數月,讓國軍有時間遷台。中共曾數度提出「局部和平」,都被父親嚴拒了。入台與共患難,是父親當時唯一的選擇;流亡海外老死異國,對他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他當然了解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後可能遭遇到的風險,但他心中坦蕩,回台灣,是向中華民國政府報到歸隊。
他在台灣的晚年過得並不平靖,沒有受到一個曾經對國家有過重大貢獻的軍人應該獲得的尊重。父親並未因此懷憂喪誌。在台灣,他於逆境中,始終保持著一份凜然的尊嚴,因為他深信自己功在黨國,他的歷史地位,絕不是一些猥瑣的特務跟監動作所能撼搖。最後他死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壇重修落成,他替鄭成功書下「仰不愧天」的匾額。綜觀父親一生,這四個字他自己也足以當之。
父親的喪禮是最高標準的國葬儀式。出殯那天,在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總統蔣中正以下,國府黨政軍高級官員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達到千人。軍事團體有國防部,陸、海、空、勤、警備各總部」,由部長及總司令率團獻花致祭。公祭儀式結束後,隨即行蓋棺禮,父親官階一級上將,按軍禮規定由四位現役陸軍一級上將顧祝同、周至柔、黃鎮球、余漢謀執旗,覆蓋棺木上,典禮儀式莊嚴隆重。出殯行列,由摩托車隊開路,隨後為軍樂隊及儀隊,靈車經過時,路上很多軍人均向靈車舉手敬禮。父親靈櫬於十二時二十分運抵六張犁回教公墓,按回教儀式下葬。回教教長領導數百位回教教友共同在墓前為父親祈禱。
這次公祭,軍人特別多,上至將官,下至士兵,在祭拜中對父親都表達了一份由衷的崇敬,這也是因為數十年來父親在軍中建立的威望所致,父親被尊為「當代最傑出戰略家」,諸葛盛名,並非虛得。
前來祭悼的,還有不少本省人士、台籍父老,很多與父親並不相識,攜幼扶老,到父親靈堂獻花祭拜。由他們大量的挽聯、挽詩中得知,他們前來吊唁,是因為感懷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措施中,對台灣民眾所行的一些德政。公祭各方送來的挽聯、挽詩、挽額、誄詞,有數百幀,多是父親的軍中同僚、部屬撰寫的,下論都很公允,有的真情畢露,十分感人。父親歸真,深深觸動了他們的家國哀思,反攻復國大業未竟,八方風雨一代名將遽然長逝。但我在這裡特別挑選出嚴慶齡先生的挽聯,做為代表。嚴慶齡先生是從上海到台灣的企業家,裕隆汽車集團的創辦人,他並非軍政界人士,跟父親並無私交,平日也無往來,但嚴先生那一輩的人經過北伐、抗戰,對父親的人格及事跡是有所認識的。
嚴慶齡先生的挽聯,很能代表他那一代的中國人對父親的評價:
「治兵則寒敵膽,為政則得民心,秉筆記宏猷不讓汾陽功業;
於黨國矢忠誠,於順逆能明辨,蓋棺昭大節無慚諸葛聲名」
─嚴慶齡敬挽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父親喪禮公祭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舉行。上午七時五十分,蔣中正抵達殯儀館靈堂,第一個向父親靈前獻花致祭。蔣面露戚容,神情悲肅,當天在所有前來公祭父親的人當中,恐怕沒有人比他對父親之死有更深刻、更復雜的感觸了。蔣、白之間,長達四十年的恩怨分合,其糾結曲折,微妙多變,絕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
父親與蔣中正四十年漫長的關系,分合之間,要分階段。
民國十五年北伐,廣州誓師,蔣中正總司令三顧茅廬,力邀父親出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並兼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一路北上打到山海關,最後完成北伐。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蔣、白兩人共同打天下的階段。
民國十七年北伐甫結束,突然爆發「蔣桂戰爭」,廣西與中央對峙七年,蔣、白分離。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開始,蔣委員長派專機至廣西將父親接到南京,任命父親為副參謀總長,並肩八年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抗戰時期,蔣對父親頗為倚重,重要戰爭如「台兒莊之役」、「三次長沙會戰」、「崑崙關之役」等,莫不賦以重任。
抗戰勝利後,蔣中正主席任命父親為第一屆國防部長。可是,國共內戰後期因父親助李宗仁選副總統,蔣、白之間又出現了嫌隙。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及其後遺症,更因兩封籲請國際調停的電報,蔣、白關系瀕臨決裂。在台灣十七年,蔣中正與父親的關系,始終沒有完全修復。
持平而論,蔣中正對父親的軍事才能是深有所知的。在國家安危的關鍵時刻,蔣往往會派遣父親前往解決困難:如指揮「台兒莊之役」,督戰「四平街之役」,「二二八事件」赴台宣慰等,在在都顯示蔣對父親的器重。但蔣中正用人,對領袖忠貞是首要條件,可是父親個性剛毅正直,不齒唯唯諾諾,而且有關國家大事,經常直言不諱,加上父親的「桂系」背景,蔣對父親的忠貞是有所疑慮的,並不完全信任。
事實上,父親一直是蔣中正的最高軍事幕僚長,扮演著襄贊元戎的角色,絕對無「取而代之」的僭越之想。李宗仁選副總統,父親最初是強烈反對的。民國三十八年「徐蚌會戰」,國軍潰敗,蔣中正下野,李宗仁代總統,那也是大勢所逼。事實上,當時黨政軍的資源還是由蔣掌握,他自己不引退,沒有人能夠強迫他。「逼宮」之說,並非事實。父親一生把國家利益放在最前面,當時國民黨政權危在旦夕,父親才「不避斧鉞」上書蔣中正,提議敦促美、英、蘇三國出面調節和平。依父親估計,如果美國願意派空軍一大隊進駐南京,青島美軍不撤退,或可阻共軍渡江,這也是當時唯可使國府轉危為安的計策了。
現在台灣及大陸一些人論及父親與蔣中正的關系,往往喜歡誇大兩人之間的矛盾,而且把矛盾變得瑣碎。其實蔣、白兩人之間的一些衝突,首先在二人的個性,二雄難以並立,兩個強人相處,衝撞勢必難免。而且古有明訓:「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其次,是兩人在國家政策方面意見分歧時起的衝突。比如「徐蚌會戰」,蔣中正與父親在這關係中華民國命運的戰役上,出現激烈爭執,前後因果,使兩人關系產生難以彌合的裂痕。但論者往往忽略了,蔣中正與父親也曾有過長期緊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結果的關係,父親在「北伐」、「抗戰」所立的戰功,亦是蔣充分授權下得以完成的。蔣中正與父親分合之間的關係,往往影響國家的安危,他們兩人在國共內戰期間,軍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協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遺憾。父親曾感嘆過:「總統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話他沒有聽。」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對「四平街之役」、「徐蚌會戰」的一些獻策吧。楚漢相爭,大將韓信替漢高祖劉邦打下天下,功高震主,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為呂后、蕭何設計殘害於長樂宮。《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高祖「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這是太史公司馬遷對人性了解最深刻的一筆。君臣一體,自古所難。
(原載於《父親與民國》下冊,〈台灣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