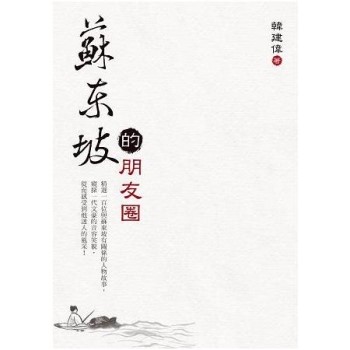程氏
蘇東坡的母親,四川眉山人。
十六歲嫁給蘇洵,共育有三男三女。不幸的是,二女一男早夭,剩下蘇軾、蘇轍兄弟和一個女孩八娘。那個叫八娘的女孩是蘇東坡的姐姐,不是傳說中「三難新郎」的那個妹妹──「蘇小妹」。八娘長大後嫁給了舅舅的兒子程正輔,但是程家人待她很不好,八娘終日鬱鬱寡歡,婚後不到兩年就死了。
蘇洵年輕的時候喜歡遊山玩水,「少年喜奇跡,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返。」丈夫不在家,教育孩子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程氏的身上。她最關注的不是孩子們讀了幾本書,而是他們性格和品德的養成。
有一天,程氏教兒子讀《漢書‧范滂傳》。范滂是東漢名士,因反對宦官專權被殺。臨刑前,范滂勸母親保重身體,不要過分悲傷。范母深明大義,反過來安慰兒子說:「既要美名,又求長壽富貴,怎麼可以兩全呢?」當時,還不到十歲的蘇東坡突然插話問:「娘,我如果成為范滂,您贊成嗎?」程氏回答說:「你能做范滂,我怎麼不能做范滂的母親呢?」
程氏吃齋念佛,心地善良,從不殺生。蘇家所居的庭院裡滿是竹柏花草,各種鳥兒都在上面築巢安家,程氏囑咐家中的婢僕、兒童要好生照料,不許傷害牠們。
程氏從不貪圖意外之財。一天,有個婢女在院子中幹活,她的腳忽然陷到了一個幾尺深的坑中。坑中有一個甕。有人猜說裡面肯定是金銀財寶,想取出來。程氏不許,說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動。
轉眼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丈夫要帶著兒子們進京趕考。病中的程氏一手拉著蘇東坡一手拉著蘇轍,依依不捨地把他們送出家門。她沒有等到兩個爭氣的兒子雙雙金榜題名的消息,不久就病故了。
王弗
第一任妻子,四川青神人。
十六歲嫁給大她三歲的蘇東坡,是長子蘇邁的母親。
王弗生長在一個讀書人的家庭,知書達理。初嫁時,蘇東坡並不知道她讀過書。每當蘇東坡讀書,王弗就陪在一旁做針線。有一次,蘇東坡背書忘了一段,怎麼也想不起來,王弗就在旁邊輕輕地提示了一句,把蘇東坡嚇了一跳──「原來你也背過書!」蘇東坡好奇地又拿出幾本書問,王弗都能答出個所以然來,讓蘇東坡喜出望外。從此,小夫妻又成了共同讀書的好伴侶。
蘇東坡首任地方官生涯始自鳳翔府的簽判。每天從官署回來,蘇東坡總要跟王弗聊聊這一天處理的公事,聽聽她的意見。王弗經常告誡他現在遠離父母,凡事要格外謹慎。王弗深知蘇東坡天性淳樸,自然率真,見誰都是好人,這樣的人在險惡的官場容易吃虧上當。她常躲在屏風的後面聽蘇東坡與客人談話,客人離開後,她會跟蘇東坡分析哪些人心術不正、笑裡藏奸;哪些人言過其實、不可深交。後來證明,王弗所說的絕大部分都對。久而久之,蘇東坡對王弗有了很深的依賴。
王弗二十七歲就去世了,留下蘇東坡和一個不滿七歲的兒子。蘇東坡哀歎自己「永無所依怙」。
十年後的一個月夜,王弗又一次走進他的夢中。蘇東坡淚如雨下,情不自禁地揮筆寫下了那首傳誦千古、公認為是最好的悼亡詩──《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
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
夜,短松岡。
張方平
字安道,號樂全居士,河南商丘人,官至副宰相。
「一門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詩賦傳千古,峨眉共比高。」這是當年共產黨全國人大的委員長朱德在四川眉州三蘇祠的題詩。四川眉州,在蘇東坡生活的那個年代,只是北宋王朝偏遠的一個小縣城。因為得到了一個重要人物的鼓勵,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從這個小縣城出發,走向京城、走向全國,日後都成為了名垂青史的大文豪。這個重要人物,就是當時主政四川的張方平。
張方平自幼聰穎過人,讀書過目不忘,被譽為「天下奇才」。早在他還是平民時就有宰相般的氣度,以「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自勉。對上不逢迎君主,對下不驕橫跋扈,一生不改率真自然的本色。蘇東坡說,如果將全天下的偉人排隊,一定要把張方平排在第一位。
張方平在成都讀到了蘇洵的政論文章,很欣賞,稱讚他深得左丘明、司馬遷、賈誼的精髓。在接見蘇洵時,聽說他還有兩個會寫文章的兒子,非常高興,讓他們一起來見他。蘇洵領著蘇軾、蘇轍來見張方平,張方平現場出了兩道題給他們兄弟倆做,自己躲到隔壁房間悄悄地觀察。得題後,兩兄弟各自專心思考。蘇轍好像對一個題目有疑問,他把有疑問的地方指給蘇東坡看。蘇東坡沒說話,把筆倒過來輕輕地敲了幾下書案,意思是「管子注」,即題目出自《管子》一書的注文。蘇轍又指了指第二個題目,蘇東坡做了個「勾掉」的手勢。二人答完卷出來交給張方平,張方平滿意地點頭微笑。
蘇東坡劃掉的第二個題目,確實無出處,是張方平故意考察蘇軾兄弟的判斷力的。張方平對蘇洵說,你的兩個兒子都是天才,大的聰明敏捷,小的謹慎持重,前途不可限量。他當即給京城的歐陽修寫了一封信,鄭重推薦蘇氏父子。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日後他對蘇東坡的成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張方平一直關注著蘇氏父子的發展。順利時為他們高興,挫折時給他們鼓勵。他萬沒想到弄出了個「烏台詩案」,蘇東坡鋃鐺下獄。聽到消息,年過七旬、已經回鄉養老的張方平憤然上書,為蘇東坡喊冤,求朝廷開恩。他堅稱蘇東坡是好人,是國家的棟樑。他原想把奏疏放到官遞公文袋中呈送皇上,但主事的官員不敢接;他只好派自己的兒子攜奏疏進京,到登聞鼓院去投遞。兒子的性格跟爹正相反,怯怯懦懦的。他雖然到了京城,但在登聞鼓院徘徊了好幾天,最終也沒敢投出去。
很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蘇東坡看到了這個奏疏的副本,他嚇得直吐舌頭。奏疏劈頭就說「軾實乃天下之奇才」,殊不知,人家整的就是這個「可與朝廷爭勝」的「天下之奇才」!這麼說只會更加激怒朝廷。還是另一位同樣賦閒在家的老人家會說話。王安石,這位在變法問題上與蘇東坡針鋒相對的前宰相,此時站出來說話了。他上書神宗皇帝,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從維護皇帝統治的角度來替蘇東坡求情,最終使蘇東坡逃過一劫。
不管奏疏寫得如何以及投出去與否,都無損蘇東坡對張方平的尊敬和感激。老人家對他的恩情,蘇東坡終身銘記。
陳慥
字季常,號方山子,別號龍丘子,四川眉山人。
陳慥是蘇東坡的朋友。「朋友」這個詞用在這裡形容他們之間的關係,顯得軟趴趴的,不如「哥們」這兩個字貼切。
我們今天還能知道陳慥──陳季常這個名字,主要是因為蘇東坡為他寫過一個傳,即《方山子傳》。此篇文字在蘇東坡所有的文章中屬上乘之作,經常拿來做散文的範本,看來確實花費了很大的心血。
陳慥是官宦子弟(其父曾任鳳翔府的太守,是蘇東坡的頂頭上司),年輕時「使酒好劍,用錢如糞土」,是遠近聞名的俠義公子哥。後來不知什麼機緣,開始參禪念佛,捨棄了萬貫家財,在湖北的岐亭隱居。蘇東坡被貶黃州路過歧亭,陳慥出城二十五里迎接並留他在家裡調養多日。此後幾年,兩人十數次往來歧亭、黃州之間互相看望,相處的時間加起來能有上百天。蘇東坡有詩《歧亭五首並敘》記錄下了那些溫馨的日子。
雖然隱居多年,但陳慥年輕時的名聲太大了,他每次來黃州都能引起轟動,百姓沿街觀瞧,豪門大戶則爭著遞名片、邀請他登門作客,以此炫耀鄉里。陳慥那裡都不去,就只住在蘇東坡家那間低矮潮濕的小屋裡,哥倆「談笑竟日,抵足而眠」。
在黃州,殺雞宰鵝款待貴客是很平常的事。但蘇東坡和陳慥都是學佛之人,幾次見面後就相約「戒殺」,不吃葷腥,彼此以粗茶淡飯招待就好。在他們的影響下,黃州不殺生、不食肉的人也漸漸地多了起來。
陳慥被譽為一代豪傑,雖然歲數大了,「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誰人能料,他卻是個地地道道的「妻管嚴」。
陳慥的妻子柳氏,非常厲害又愛嫉妒。有時候陳慥和客人正在聊天,不知因為什麼柳氏就摔鍋打碗地鬧將起來,把陳慥弄得很難堪,可又不敢把老婆怎麼樣。蘇東坡專門寫了一首詩「誇」他: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古人有「河東人氏多姓柳」的說法。蘇東坡詩中借「河東」代指陳慥的妻子柳氏。從此,「河東獅吼」就成了兇悍老婆的代名詞,「季常癖」也成了怕老婆的典故。因為一篇傳記、一首詩,使夫妻倆雙雙傳名於世,不知陳慥對蘇東坡作何感想,是該感激他呢還是該埋怨他。
蘇東坡貶謫期滿將要離開黃州了,鄉親們都來送行。平日最親近的幾個人把他送到驛站。唯陳慥萬般不捨,一路把蘇東坡送到了九江,看著他登船遠去,直到「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蘇東坡的母親,四川眉山人。
十六歲嫁給蘇洵,共育有三男三女。不幸的是,二女一男早夭,剩下蘇軾、蘇轍兄弟和一個女孩八娘。那個叫八娘的女孩是蘇東坡的姐姐,不是傳說中「三難新郎」的那個妹妹──「蘇小妹」。八娘長大後嫁給了舅舅的兒子程正輔,但是程家人待她很不好,八娘終日鬱鬱寡歡,婚後不到兩年就死了。
蘇洵年輕的時候喜歡遊山玩水,「少年喜奇跡,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返。」丈夫不在家,教育孩子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程氏的身上。她最關注的不是孩子們讀了幾本書,而是他們性格和品德的養成。
有一天,程氏教兒子讀《漢書‧范滂傳》。范滂是東漢名士,因反對宦官專權被殺。臨刑前,范滂勸母親保重身體,不要過分悲傷。范母深明大義,反過來安慰兒子說:「既要美名,又求長壽富貴,怎麼可以兩全呢?」當時,還不到十歲的蘇東坡突然插話問:「娘,我如果成為范滂,您贊成嗎?」程氏回答說:「你能做范滂,我怎麼不能做范滂的母親呢?」
程氏吃齋念佛,心地善良,從不殺生。蘇家所居的庭院裡滿是竹柏花草,各種鳥兒都在上面築巢安家,程氏囑咐家中的婢僕、兒童要好生照料,不許傷害牠們。
程氏從不貪圖意外之財。一天,有個婢女在院子中幹活,她的腳忽然陷到了一個幾尺深的坑中。坑中有一個甕。有人猜說裡面肯定是金銀財寶,想取出來。程氏不許,說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動。
轉眼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丈夫要帶著兒子們進京趕考。病中的程氏一手拉著蘇東坡一手拉著蘇轍,依依不捨地把他們送出家門。她沒有等到兩個爭氣的兒子雙雙金榜題名的消息,不久就病故了。
王弗
第一任妻子,四川青神人。
十六歲嫁給大她三歲的蘇東坡,是長子蘇邁的母親。
王弗生長在一個讀書人的家庭,知書達理。初嫁時,蘇東坡並不知道她讀過書。每當蘇東坡讀書,王弗就陪在一旁做針線。有一次,蘇東坡背書忘了一段,怎麼也想不起來,王弗就在旁邊輕輕地提示了一句,把蘇東坡嚇了一跳──「原來你也背過書!」蘇東坡好奇地又拿出幾本書問,王弗都能答出個所以然來,讓蘇東坡喜出望外。從此,小夫妻又成了共同讀書的好伴侶。
蘇東坡首任地方官生涯始自鳳翔府的簽判。每天從官署回來,蘇東坡總要跟王弗聊聊這一天處理的公事,聽聽她的意見。王弗經常告誡他現在遠離父母,凡事要格外謹慎。王弗深知蘇東坡天性淳樸,自然率真,見誰都是好人,這樣的人在險惡的官場容易吃虧上當。她常躲在屏風的後面聽蘇東坡與客人談話,客人離開後,她會跟蘇東坡分析哪些人心術不正、笑裡藏奸;哪些人言過其實、不可深交。後來證明,王弗所說的絕大部分都對。久而久之,蘇東坡對王弗有了很深的依賴。
王弗二十七歲就去世了,留下蘇東坡和一個不滿七歲的兒子。蘇東坡哀歎自己「永無所依怙」。
十年後的一個月夜,王弗又一次走進他的夢中。蘇東坡淚如雨下,情不自禁地揮筆寫下了那首傳誦千古、公認為是最好的悼亡詩──《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
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
夜,短松岡。
張方平
字安道,號樂全居士,河南商丘人,官至副宰相。
「一門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詩賦傳千古,峨眉共比高。」這是當年共產黨全國人大的委員長朱德在四川眉州三蘇祠的題詩。四川眉州,在蘇東坡生活的那個年代,只是北宋王朝偏遠的一個小縣城。因為得到了一個重要人物的鼓勵,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從這個小縣城出發,走向京城、走向全國,日後都成為了名垂青史的大文豪。這個重要人物,就是當時主政四川的張方平。
張方平自幼聰穎過人,讀書過目不忘,被譽為「天下奇才」。早在他還是平民時就有宰相般的氣度,以「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自勉。對上不逢迎君主,對下不驕橫跋扈,一生不改率真自然的本色。蘇東坡說,如果將全天下的偉人排隊,一定要把張方平排在第一位。
張方平在成都讀到了蘇洵的政論文章,很欣賞,稱讚他深得左丘明、司馬遷、賈誼的精髓。在接見蘇洵時,聽說他還有兩個會寫文章的兒子,非常高興,讓他們一起來見他。蘇洵領著蘇軾、蘇轍來見張方平,張方平現場出了兩道題給他們兄弟倆做,自己躲到隔壁房間悄悄地觀察。得題後,兩兄弟各自專心思考。蘇轍好像對一個題目有疑問,他把有疑問的地方指給蘇東坡看。蘇東坡沒說話,把筆倒過來輕輕地敲了幾下書案,意思是「管子注」,即題目出自《管子》一書的注文。蘇轍又指了指第二個題目,蘇東坡做了個「勾掉」的手勢。二人答完卷出來交給張方平,張方平滿意地點頭微笑。
蘇東坡劃掉的第二個題目,確實無出處,是張方平故意考察蘇軾兄弟的判斷力的。張方平對蘇洵說,你的兩個兒子都是天才,大的聰明敏捷,小的謹慎持重,前途不可限量。他當即給京城的歐陽修寫了一封信,鄭重推薦蘇氏父子。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日後他對蘇東坡的成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張方平一直關注著蘇氏父子的發展。順利時為他們高興,挫折時給他們鼓勵。他萬沒想到弄出了個「烏台詩案」,蘇東坡鋃鐺下獄。聽到消息,年過七旬、已經回鄉養老的張方平憤然上書,為蘇東坡喊冤,求朝廷開恩。他堅稱蘇東坡是好人,是國家的棟樑。他原想把奏疏放到官遞公文袋中呈送皇上,但主事的官員不敢接;他只好派自己的兒子攜奏疏進京,到登聞鼓院去投遞。兒子的性格跟爹正相反,怯怯懦懦的。他雖然到了京城,但在登聞鼓院徘徊了好幾天,最終也沒敢投出去。
很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蘇東坡看到了這個奏疏的副本,他嚇得直吐舌頭。奏疏劈頭就說「軾實乃天下之奇才」,殊不知,人家整的就是這個「可與朝廷爭勝」的「天下之奇才」!這麼說只會更加激怒朝廷。還是另一位同樣賦閒在家的老人家會說話。王安石,這位在變法問題上與蘇東坡針鋒相對的前宰相,此時站出來說話了。他上書神宗皇帝,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從維護皇帝統治的角度來替蘇東坡求情,最終使蘇東坡逃過一劫。
不管奏疏寫得如何以及投出去與否,都無損蘇東坡對張方平的尊敬和感激。老人家對他的恩情,蘇東坡終身銘記。
陳慥
字季常,號方山子,別號龍丘子,四川眉山人。
陳慥是蘇東坡的朋友。「朋友」這個詞用在這裡形容他們之間的關係,顯得軟趴趴的,不如「哥們」這兩個字貼切。
我們今天還能知道陳慥──陳季常這個名字,主要是因為蘇東坡為他寫過一個傳,即《方山子傳》。此篇文字在蘇東坡所有的文章中屬上乘之作,經常拿來做散文的範本,看來確實花費了很大的心血。
陳慥是官宦子弟(其父曾任鳳翔府的太守,是蘇東坡的頂頭上司),年輕時「使酒好劍,用錢如糞土」,是遠近聞名的俠義公子哥。後來不知什麼機緣,開始參禪念佛,捨棄了萬貫家財,在湖北的岐亭隱居。蘇東坡被貶黃州路過歧亭,陳慥出城二十五里迎接並留他在家裡調養多日。此後幾年,兩人十數次往來歧亭、黃州之間互相看望,相處的時間加起來能有上百天。蘇東坡有詩《歧亭五首並敘》記錄下了那些溫馨的日子。
雖然隱居多年,但陳慥年輕時的名聲太大了,他每次來黃州都能引起轟動,百姓沿街觀瞧,豪門大戶則爭著遞名片、邀請他登門作客,以此炫耀鄉里。陳慥那裡都不去,就只住在蘇東坡家那間低矮潮濕的小屋裡,哥倆「談笑竟日,抵足而眠」。
在黃州,殺雞宰鵝款待貴客是很平常的事。但蘇東坡和陳慥都是學佛之人,幾次見面後就相約「戒殺」,不吃葷腥,彼此以粗茶淡飯招待就好。在他們的影響下,黃州不殺生、不食肉的人也漸漸地多了起來。
陳慥被譽為一代豪傑,雖然歲數大了,「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誰人能料,他卻是個地地道道的「妻管嚴」。
陳慥的妻子柳氏,非常厲害又愛嫉妒。有時候陳慥和客人正在聊天,不知因為什麼柳氏就摔鍋打碗地鬧將起來,把陳慥弄得很難堪,可又不敢把老婆怎麼樣。蘇東坡專門寫了一首詩「誇」他: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古人有「河東人氏多姓柳」的說法。蘇東坡詩中借「河東」代指陳慥的妻子柳氏。從此,「河東獅吼」就成了兇悍老婆的代名詞,「季常癖」也成了怕老婆的典故。因為一篇傳記、一首詩,使夫妻倆雙雙傳名於世,不知陳慥對蘇東坡作何感想,是該感激他呢還是該埋怨他。
蘇東坡貶謫期滿將要離開黃州了,鄉親們都來送行。平日最親近的幾個人把他送到驛站。唯陳慥萬般不捨,一路把蘇東坡送到了九江,看著他登船遠去,直到「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