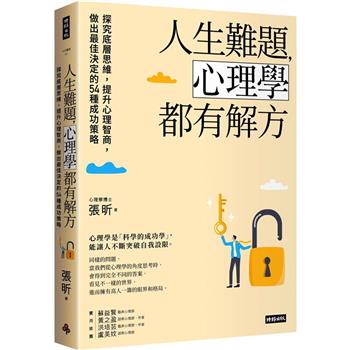為何臉部表情會出賣內心的真正想法?
【心理學效應】觀察微表情
人類在試圖隱藏某種情感時無意識做出短暫的臉部表情,稱為微表情。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著名的美劇,叫《別對我說謊》(Lie to Me)? 這部影集主角的原型是一位著名的情緒心理學家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他把自己在微表情識別的相關研究改編成電視劇,塑造了一個叫作萊特曼的形象。萊特曼主要的工作就是透過辨識別人的微表情進行測謊,進而幫助警察破案。
其中有一集很有趣,萊特曼發現有個人在撒謊之前會下意識地摸一摸鼻子,他就利用這個動作判斷這個人是不是在撒謊,而他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男人的鼻子有海綿體,當他們想要掩飾什麼的時候,鼻子就會癢。
人類的六種基本情緒
在心理學的領域,表情是情緒或情感的一種外在表現。研究發現,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的表情,都是高度一致的。達爾文認為,臉部表情是天生的、固有的,並且會被所有人類理解,也就是說,世界上的人都有相同的臉部表情。
達爾文的觀點也被心理學家艾克曼驗證了。艾克曼最著名的一項研究是在太平洋的一個島國巴布亞紐幾內亞上做的,他在小島上和當地的原住民一起生活了一年多,觀察當地的人如何表達情緒。
你可能會好奇,觀察原住民的情緒有什麼用處?美國有那麼多大城市,那麼多人口,為什麼不觀察城市中的人,而要去觀察一個島國上的原住民?其實,這牽涉到一個很有趣的心理學問題:人一共有多少種基本情緒?
所謂基本情緒,就是達爾文研究天生的、與生俱來的情緒,和基本情緒相對應的稱為後天習得的情緒。因為後天習得的情緒是高度社會化的,大部分只有在社會情境下才可能出現,不屬於基本情緒。
比如,嫉妒這種情緒只有在有其他人在的情境,尤其是牽涉到社會比較的情況才會表現出來。艾克曼的目的是研究人到底有多少種基本情緒,城市中的人受到太多社會化的影響,觀察結果可能不準確。而他在太平洋小島上進行觀察,能更準確地達到目的,因為那些原住民的社會化程度相對來說比較低。
經過一年多的觀察,艾克曼發現,人類的基本情緒大概有六種。
第一種:愉快。對應的臉部表情是嘴角會向上翹,臉頰會上揚並且皺起,眼瞼收縮。
第二種:恐懼。臉色會蒼白,眉毛上揚,嘴巴和眼睛張開,鼻孔張大。
第三種:生氣。臉部表情通常是前額緊皺,眉毛下垂併攏,嘴唇緊鎖,臉部漲紅。
第四種:悲傷。臉部表情通常是眼眉拱起,嘴角往下垂,會流淚。
第五種:驚訝。嘴唇和嘴巴張開,眼睛張大,眼瞼和眉毛上抬。
第六種:厭惡。臉部表情是額眉往內皺,嘴巴微張,牙齒緊閉,嘴角上揚。
在發現這六種基本情緒後,艾克曼便找來居住在城市裡的人,讓他們表達這六種基本情緒。之後他在全世界的各個國家和地區,讓受試者辨識這些情緒,結果所有的受試者都能準確分辨出這六種基本情緒,顯示這些情緒有高度的一致性。
微表情心理學
艾克曼的貢獻遠不止研究這六種基本情緒,他另一個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微表情。
艾克曼和他的同事弗里森(Wallace Friesen)曾受一位精神病學家的委託,對一位憂鬱症患者進行測謊。那位精神病學家說,這位憂鬱症患者一直聲稱自己絕不會自殺,所以精神病學家想請艾克曼和弗里森來判斷一下患者話語的真偽。
他們兩人觀察錄影的時候,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因為這個患者表現得非常樂觀,笑著跟他們說,我不會自殺,我沒有問題。從表面上看,他沒有顯現出任何企圖自殺的跡象,但很不幸的是,他後來還是自殺了。
艾克曼和弗里森很自責。接著他們又對患者生前的那段影像進行分析,這一次他們並沒有以正常的速度播放,而是以非常慢的速度將影像逐個觀察與分析。結果發現患者在回答一個關於未來計畫的問題時,產生了非常強烈的痛苦表情,而這個表情持續的時間大概只有十二分之一秒,也就是不到一百毫秒的時間。
這兩位學者把這樣一個持續非常短時間的表情稱為微表情,也就是一種還沒有完全表達出來的情緒,維持的時間大概在五百毫秒以內,可能表情並沒有做完就被掩蓋過去了。後來他們又把微表情理論發揚光大,做出了非常多的貢獻。
在這裡,我要提醒一下,其實微表情是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它和我們在《別對我說謊》等戲劇影片裡所看到的微表情還是有些許差異。
在測謊過程中,它只能作為一種線索,而不能做為真正的證據。即使員警在對犯人進行審訊時,可以透過微表情來判斷他是否說謊,但也無法保證這種判斷的準確度能達到 百分之百。另外,觀察微表情,要真正做到科學而專業地讀心,光靠肉眼是不夠的,還需要借助更高級、精密、尖端的儀器設備。當然,觀察者也需要經過相關的訓練。
艾克曼曾研發的一套在微表情領域中非常重要的訓練系統,叫作臉部動作編碼系統(FACS)。在這套系統中,他規定每個微表情的持續時間在五百毫秒以內,同時,這些微表情是基於生理學家對人的臉部肌肉的解剖來完成。系統把臉部肌肉劃分成大約四十六個動作單元,然後透過大量的實證性工作,以及觀察大量的影像資料,歸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動作編碼系統。
其實,微表情不是只有以動作基礎為依據,還有一些生理基礎。正如前文所說,男人在說謊時會摸鼻子。如本文一開始所說,鼻子裡有一個海綿體,人在說謊時,血液會流向鼻尖,鼻尖就會發熱,進而導致人會試圖利用摸鼻子來降溫;或是說因為發熱,所以人會覺得癢癢的,就去摸鼻子。發現這個現象的心理學家把這個效應稱為「皮諾丘效應」,也就是說這與小木偶皮諾丘說謊後鼻子就會變長的狀況類似。
如何分辨「應酬式笑容」?
辨識微表情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麼幫助?有個最簡單的應用,就是可以分辨一個人是在真笑還是假笑。
真笑和假笑的區別主要在於眼睛。想想當你不太開心,但又要強顏歡笑時會怎麼做?人們通常會把嘴角往上揚,但臉部其他的肌肉則不會動。但人在真心高興露出笑容時,除了嘴角會向上揚之外,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就是眼睛周圍的肌肉也會牽動,甚至會出現明顯的魚尾紋。
所以我經常被我太太嘲笑,她說我現在已經有魚尾紋了。我當然知道這是為什麼,其實就是我笑的頻率比較高,而且我的笑都是發自內心的真笑,所以才會有魚尾紋。如果你發現一個人笑的時候,總是簡單地嘴角上揚,而沒有任何眼部的動作,就可以知道他可能只是出於禮貌地對你微笑,而不是真的很高興見到你。
在此留給大家一個小練習。你可以觀察一下演員在笑的時候,到底是在真笑還是在假笑。雖然都是在演戲,但是那些演技好的演員在用臉部動作表達情緒時會更加精確。
為何人多反而容易誤事?
【心理學效應】責任分散
如果除了自己,還有許多人在現場,責任感會被分散,人們在面對事件發生就會變得退縮,認為會有其他人承擔更多的責任。
曾有媒體報導過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一個震驚美國社會的事件,標題很聳人聽聞——「三十八人目擊謀殺發生卻無人報警!」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淩晨三點左右,紐約一位年輕女子基蒂‧吉諾維斯在上完夜班即將到家前,遭到持刀歹徒的侵犯,她驚恐地尖叫並懇求幫助:「天啊!我被刺傷了!請幫幫我!」悽慘的聲音在寧靜的深夜中迴盪著,顯得分外刺耳,吵醒了鄰居。很多人走到窗戶邊觀望了片刻,目睹歹徒離去又重返多達三次。直到有人打電話報警,歹徒才離開,當時吉諾維斯早已倒在血泊中。之後調查發現,一共有三十八個人目睹了這場暴行,卻都無動於衷,沒人採取拯救行動。
這場慘案引發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熱潮。是什麼原因讓這 三十八個人都如此冷漠,不願伸出援手,也沒有報警呢?是因為他們都是一群冷酷無情、見死不救的壞人嗎?
「此事與我無關」
造成這場悲劇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責任分散效應」,它是指旁觀者越多,就越無人願意插手的現象。當不只有一人能夠在緊急事件中幫忙時,人們經常會假設其他人願意或也應該幫忙,於是他們自己就會退縮或選擇不插手。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那些聽到呼救聲的鄰居並非沒有同情心,他們當時可能想:「離受害者住得更近的人可能已經報警了,或者其他人可能已經報警了,我就不需要再多此一舉了」。
在這樁集體冷漠所造成慘劇發生四年後,兩位社會心理學家畢博‧拉塔內(Bibb Latane)和約翰‧達利(John Darley)研究分析了各種緊急情況,從決策的角度發現了旁觀者在面對緊急事件時的思考與行動過程。
旁觀者是否注意到了這個緊急事件呢?如果都沒注意到,那麼當然根本沒有救助的可能性。這也是二〇一一年「小悅悅事件(編註: 二○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兩歲女童小悅悅在廣東佛山,被一輛貨車輾壓兩次,之後又被另一小貨車輾過。過程中共有十八位路人或駕駛人士目擊,卻無一人出手相救。最後有一位拾荒婦人把小悅悅抱到路邊並通知她的母親,可惜小悅悅送院時已不治。)」發生時,一部分人從她身邊經過但沒有停下腳步的原因,因為兩歲的小女孩身型太小了,忙著趕路的行人中有些人很可能就沒有注意到她。
但如果人們注意到她了呢?就像這個事件一樣,受害者深夜裡驚恐的尖叫和求助聲一定驚醒了很多人。旁觀者在注意到之後會進一步對情況做出分析:這是不是一個緊急事件,情況有沒有非常危險?如果旁觀者判斷,這件事不緊急,求助者早一點或晚一些獲得幫助的影響並不大,那麼旁觀者就很可能不提供幫助。
如果把這個事件解釋為緊急事件,旁觀者會怎麼做呢?他們會進一步判斷,我在這件事情裡有責任嗎?如果他們判斷自己沒有責任,或者即使有也非常小,小到不會影響整個情勢,那麼他們也會選擇不挺身而出。旁觀者只有認定自己在這個事情上責無旁貸時才會伸出援手。
該伸出援手,還是明哲保身?
想讓旁觀者走到採取行動的道路上,過程中會有很多條叉路使他們袖手旁觀,這些叉路分別是覺察、解釋和責任,也是引發責任分散的關鍵因素。
一、覺察:旁觀者越多,反而更不會注意到發生的事,也可能不認為自己必須幫忙。
在同一個場景中,如果旁觀者越多,會注意到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反而越小,這將導致受害者更少有機會獲得幫助。
比如,有位研究人員和一百四十五位合作者一共測試了一千四百七十九次,當他們在搭乘電梯時假裝不小心掉落了硬幣和鉛筆。當旁邊只有一位乘客時,他們得到幫助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四十;當旁邊有六位乘客時,他們得到幫助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十。因此研究人員推測,當旁觀者的人數增加時,所有旁觀者都更不會注意到事件的發生,也更不容易視其為重大問題或緊急情況,因此就更不認為自己有採取行動的責任。
二、解釋:求助者是否提出確切的理由,說明自己為何需要別人的幫助。
一九七六年,研究人員設計了一項實驗,他們讓一位男性和一名女性假裝在打架。結果發現,當女子大叫「走開,我不認識你」時,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機率會得到別人的幫助;但如果她說「滾開!我不知道我怎麼會嫁給你!」時,只有百分之十九的機率會獲得幫助。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真實生活中。曾經有受害女生被歹徒當街騷擾,當歹徒向周圍的路人說「吵架啦,這是我老婆」的時候,原本準備瞭解情況、提供幫助的路人就都走開了,最後導致受害女生在公共場所陷入無人協助的困境。
這個研究的基本結論是,求助者應該給出足夠有力的解釋,為什麼需要別人的幫助,好讓旁觀者判斷自己是否應該伸出援手。「我不認識你」就是一個有力的解釋,這讓旁觀者知道男子在「欺負」或「侵犯」女性;而「我不知道我怎麼會嫁給你」,這個解釋會讓旁觀者覺得,這是別人的家務事,就不要插手了吧。
三、責任:對方提出的請求是否能引發你的責任感。
在一個實驗中,有個人(實際上是實驗者故意安排的)會對旁邊的陌生人提出不同的請求,他有時會問:「你有空嗎?」有時則是問:「你能在我離開的時候幫我看一下行李嗎?」前一種情況並未讓旁觀者產生責任感,因此當小偷拿走受害者的東西時,那些人只是袖手旁觀;但那些答應替對方看著行李的人,在小偷偷東西時幾乎都介入了,有些人甚至窮追不捨地抓住小偷。
一個小小的請求——「你能在我離開的時候幫我看一下東西嗎?」這句話所具有的社會心理學力量,幾乎使得每一個旁觀者都能熱心地提供幫助。當然,注意因素中提到的人數也是一個誘因,在人越多的情況下,每個人覺察到自己應該有責任的可能性就越少。
除了這三個因素之外,前文提到過的內團體和外團體也是引發責任分散的因素之一。我們每個人都會自動定義與自己來自同一群體的人,以及與自己不屬於同一群體的人,也就是in group member(組內成員)和out group member(組外成員)。
之所以會產生責任分散效應,很可能是因為我們把需要幫助的人當成外團體的成員,認為他和自己不屬於一個群體,自己對他沒有責任,當然不會提供援助。比如,有一個家境清寒的同學生了重病,急需醫藥費,如果他是你的同班同學,那你很可能會二話不說地馬上捐款,給予協助;如果他是你校友,你可能也會捐款,但金額就不會太多;但如果他只是其他學校的學生,他的學校你連聽都沒聽過,只是在社群網路上看到有人發起募款的連結,那可能你看完之後就忽略了,因為你不覺得自己和他有什麼關係,也就感覺不到自己有責任了。
由此看來,把需要幫助的人從組外成員變成組內成員可能就是克服責任分散的一個關鍵。因此,就像之前提到的,增加接觸的方法對這種情形下的責任分散是比較有效的,比如,一起旅遊、聊天等方法。
如何降低責任分散效應?
以下就列舉一些方法,可以降低責任分散效應出現的機率。
一、向特定的人求助。
如果我們在外面遇到了緊急情況需要幫忙,應該盡可能讓旁人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進而克服責任分散的阻力。
如果附近的人不多,首先要大聲呼救,讓周圍的人注意到自己正處於危急時刻。只要達到一定的人數,就馬上指定其中某個人,比如,眼睛注視著一個人,說:「穿紅色衣服的那位女士,我需要你的幫助。」直接向特定的人求救,而不是被動地期望能有人主動幫助自己,這樣做能夠大大提升自己獲得幫助的可能性。
二、把責任具體落實到特定的人身上。
如果你是主管或公司負責人,當你把某個任務交給一個團隊完成時,一定要指定負責人。任務的細節具體到哪個環節該找誰,出了問題該找誰,最後直接跟這些負責人溝通即可。當團隊無法完成任務時,如果你想讓自己的批評變得有力,就要讓批評具有針對性,一定要將責任具體到人,也落實到事上,不要讓大家有一種「這是所有人的責任,我一個人不努力也沒關係」的感覺。
記住,將責任具體落實到特定的人身上,可以降低責任分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