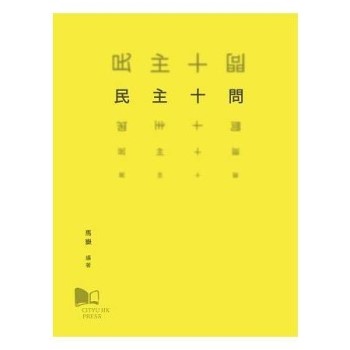為甚麼要民主?民主會帶來政治不穩嗎?是否有助經濟發展?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搞清楚「民主」到底是甚麼。本章將釐清「民主」這個概念,並打破一些常見的誤解。此外,我們亦會將民主與自由、人權、理性、容忍,以至社會公義這些概念比較,以分析各概念之間的關係。
民主是建基於政治平等的集體決策模式
社會總要作出一些重要決定。舉例說,政府應該多抽稅來作再分配 ,還是要減稅「還富於民」?我們應否立法訂定標準工時?為增加住屋供應,是否要填海或取消郊野公園?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化?……這些都是社會層面的抉擇,即一般所謂「公共政策」。和個人層面的抉擇比較,公共政策有兩大特點:首先,其影響範圍較廣,牽涉的利益團體也較多;再者,正因為公共政策牽連甚廣,不同人士也就往往看法迥異。
如何處理這些分歧呢?當然,最理想的方法是透過和平理性的討論,收窄分歧,尋求共識。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一致共識」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首先,有關公共事務的爭論往往源於價值觀的分歧;在多元化的現代社會,我們不能亦不必事事強求「一致共識」。但另一方面,很多公共或社會問題都要及時處理,根本不容許無休止的討論。因此,我們必須訂立一套集體決策模式(a mode of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好讓大家在討論過後而又不能達致共識時,仍然可以根據某種合理的程序(reasonable procedure)來作出決定。顯然易見,集體決策模式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集體決策模式,也就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政治體制(political regimes)。在傳統社會,決策權力往往集中於少數世襲貴族甚至是君主一人之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在其《理想國》(Republic)一書中,則主張由有智慧的人來當政(也就是所謂 philosopher-king)。
民主正是一種集體決策模式。跟其他決策模式相比,民主有兩大特色。第一,社會上所有成員(或至少是所有成年成員)都可以參與決策過程。第二,作決定時,每個成員的「話事權」均等,不會出現某些人的意見較受重視的情況。為甚麼每個人的「話事權」都要均等呢?這是基於「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的價值或原則,即是說在參與集體決策的時候,每一位公民的權力和地位都應該是相等的。因此,簡單來說,民主就是一種建基於政治平等的集體決策模式。以上主要是普遍性及概念性的討論。實際運作過程當中,哪種政治制度會比較合乎政治平等的理念呢?民主社會是否事事都行多數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本章稍後將加以討論。但以上定義帶出非常重要兩點。第一,民主是一種程序(procedure),換言之,市民大眾的參與過程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我們在這裏對民主採取一個狹義(narrow)的理解, 即除了政治平等外,民主本身並不包含其他概念和價值,如一般的自由、人權、經濟平等或容忍(tolerance)等等。在以下幾節,我們會再詳細解釋這兩點, 並藉此澄清幾個有關民主的常見誤解。
民主不等同「民本政治」或「諮詢政治」
「民本」或「以民為本」的理念中國古已有之。孟子便強調執政者必須以民為本。一些人更以「民本」的理念說明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已經蘊含「民主」的土壤。不過,根據我們的定義,「民本」並不等同民主。
所謂「民本」,簡單來說,就是指執政者作決定時要以人民的利益作為最後依歸。但甚麼才是「人民的利益」呢?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會認為,統治國家的聖人賢君,當然會知道甚麼是人民的利益。但問題是,統治者眼中的公眾利益可能跟人民眼中的公眾利益不盡相同。換句話說,再「民本」的統治者,其決定也往往跟民意有極大差距。這是因為,「民本政治」只要求統治者以民為本,卻沒有賦予人民參政的權利。另一方面,民主國家的政客,雖然未必會事事「以民為本」,但由於選票的壓力,其決定最終也不致偏離民意太遠。由此可見,民主和民本是不同的。民本政治不等同民主。兩者之間的關鍵分別,在於「民眾參與」。
那麼「諮詢政治」又是否等於民主?從「民眾參與」的角度來看,「諮詢」無可否認比「民本」有進步。當然,只做門面功夫、甚至扭曲民意的「假諮詢」,肯定不是民主。可是,如果當政者的諮詢是認真的,那又如何?不少學者都指香港(尤其是殖民地時期的香港)的政治是「諮詢政治」,政府就所有重大事情都會先諮詢民意。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香港算不算有民主?再進一步說,假設世襲的君主每次作決定時都以人民的偏好為最終依歸(比方說,透過民意調查來定奪),那麼民主和獨裁之間還有分別嗎?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誠然,民主的特徵之一,就是其決定最終會以民意主流為依歸。可是我們不能單憑此點來判別制度是否民主。民主的核心理念是每位公民都有平等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利。在此,「參與權」是不可或缺的。欠缺公民參與的公共決策,即使其結果合乎民意,也不算是民主的。同樣地,即使當政者真的「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只要他不肯開放權力,讓人民真正參與,那麼他依然是獨裁的。下面我們會提到,在實際情況中,人民未必可以事事直接參與決定,因此也就產生了代議政制(representation system)。然而,代議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中的代表(主要指立法機關的議員,但也可包括行政首長)仍然必須由人民選出。換言之,選舉投票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主不等同人權、自由、理性或容忍
在很多人心目中,民主、自由和人權這三個概念,即使並非同義,也至少是高度相關。這種想法不難理解。歷史上,這三個概念都源自西方。到了今天,民主傳統最強的國家,差不多全部是宣揚人權最力、自由主義主導的西方國家。然而,民主、自由和人權三者其實是迥然不同的概念,而且它們之間並非毫無衝突。民主本身的確預設了某些基本人權和自由,但並非所有人權和自由都可以從民主的理念中推導出來。最自由的國度也不一定是最民主的國度。
在分析民主、自由和人權的關係之前,我們先要把這些概念分辨清楚。如上所述,民主是一種建基於政治平等的集體決策模式。至於自由,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個人行為不受限制。當然,在群體社會中,「絕對個人自由」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基本的個人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已是大部分社會公認的價值,並通常以「人權」的形式來立法保障。所謂人權,就是指每個人生而為人都擁有的權利(或稱「天賦權利)」,而這些權利都不可以因「公眾利益」等理由而隨意剝奪。對自由主義者(liberals)來說,個人自由和人權是非常重要的價值,也就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恰當理由。由此可見,民主、自由和人權是不同的概念。那麼,它們之間又有甚麼關係?由於民主的要義就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參與制訂政策,因此這個理念本身就預設了某些個人權利和自由,否則「民主」只不過是空談。舉例說,為了讓人民有充分的政治參與,言論、通訊及結社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民主本身就蘊含了言論自由、通訊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個人權利,因為那是民主的先決條件。
然而,並非所有人權和自由都可以從民主推導出來的。民主所關心的,只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也就是指公民可以參與政治決策過程。除此之外,諸如宗教自由、職業自由、婚姻自由等人權,即使重要,也跟民主沒有概念上的關係。如果一個社會透過民主制度來訂立限制宗教自由的法例(如訂立國教),或者限制市場運作的政策(如國有化),那麼這個社會可能不算自由,但它依然是民主的。換句話說,民主的社會不一定是自由的社會,儘管民主本身預設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權利。
那麼,自由的社會又是否一定是民主的?不一定,只要個人權利和自由大致得到保障,不民主的社會也可以是非常自由的。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殖民地時代,可以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的香港人少之又少。直到今天,大部分香港人還不能投票選出行政長官。然而,國際輿論大都認為香港仍是世界上相對自由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來說明民主、自由和人權之間的分別。上面提及,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是自由主義當道的社會,但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所指涉的是完全不同的價值。自由主義的要義,在於個人自由及人權是重要政治價值,保障個人自由和人權正是限制政府權力的合理依據。自由主義的相反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國家直接干預人民所有事項,包括私人層面的活動(如家庭生活、擇偶等)。我們可以把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視作光譜的兩端,如下所示:
自由主義 極權主義
民主政體講求的,則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平等的身份來參與政治決策。民主政治的相反是獨裁政體(dictatorship),也就是說由國家最高領導人獨攬大權,其他人基本上沒有參與的份兒。東西方古代的皇帝或絕對君主(absolute monarchs)就是例子。因此,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也是兩個極端,中間還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如寡頭政治(oligarchy)、有限度民主政治2 等等。民主政體 獨裁政體
結合以上兩條「光譜」,我們可以得出至少四種不同的政治模式,即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極權民主政體、極權獨裁政體及自由獨裁政體。3 所以,「民主」不一定是自由民主體制;民主也可以是極權或不自由的(即所謂illiberal democracy)。另一方面,獨裁政治不一定是極權的;歷史上也有不少相對自由但獨裁(或不民主)的政權。
從現實情況觀察,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確有着某種共生關係。獨裁政體往往是極權的,而自由的社會似乎比較有利民主。一方面,民主制度給予人民更換政府的權力,減少執政者濫權的機會,也就保障了各種基本人權和自由。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較自由的社會,比較尊重不同意見,並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礎也就較穩固。但概念上民主政體和自由主義完全不同,必須分辨清楚。自由主義背後的價值是個人自由;它關心的,是政府權力界限(scope of power)的問題。民主政體背後的價值是政治平等,而非自由本身。民主所關心的,是政府權力來源(sources of power)的問題。
明白了民主不等同人權和自由,那民主跟「理性」及「容忍」的分別也不難理解。民主只是一種程序,本身並不包括「理性」、「容忍」等價值及概念,儘管「理性」和「容忍」的態度對民主政治的運作通常都是有利的。不少香港人都把民主等同為理性討論、包容異己,這其實是錯誤的。沒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如一人一票的選舉),再理性和包容的社會都不算是民主的。相反,民主的社會也不一定是非常包容的。上面提及「以民主制度來限制宗教自由」即是一例。
這把我們帶到非常重要的一點:民主(或政治平等)只是眾多價值之一,並可能和其他社會價值衝突。理論上民主確有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因此大部分自由民主政體的國家都透過一些憲制或法律上的制衡(如人權法、獨立的司法覆核等),來限制民選政府的權力,防止執政者濫權或出現多數人的暴政,從而保障重要的人權及自由。有些人會說,由非民選的法官及司法機構來限制民選政府的權力,根本就是「反民主」的。這種說法本身沒有錯,但我們必須記住,民主並非至高無上的價值:為了其他重要價值(如人權、自由、社會公義等等),民主不一定是絕對的。從直接民主到代議政制:如何落實政治平等?
以上是抽象層面的討論。到底我們應該用甚麼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來實行民主,以落實政治平等的理念?
先引入兩個概念: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及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所謂直接民主,就是由全體人民直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包括以投票作出決定,即所謂全民公決或公民投票(referendum)。這可算是最古老的民主方式,古希臘城邦(city-states)的民主體制就包含了不少直接民主的成分。到了今天,全民公決在部分國家及地區(如瑞士、法國及美國一些州份)依然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環。
無可否認,直接民主講求「人民事事參與」,的確較接近民主的本來理想。可是,現代社會日益複雜,基於時間及其他限制,要求所有人民直接參與每項公共決策有點不切實際,代議民主(或代議政制)也就應運而生。顧名思義,代議民主就是指人民透過自己選出的代表來制定公共政策,並由他們監察以至領導行政機關施政。事實上,今天的自由民主政體,基本上都是以代議政制主導。即使設有全民公決的國家,也只有在關鍵問題上(如修改憲法、罷免行政首長、重大國家政策)才會實行直接民主。
那麼,怎樣的代議政制才算符合民主的理念?在此,我們或可借用民主理論大師 Robert Dahl 的分析。4 Dahl 指出,下面六項都是代議民主必需的:
1.民選代表(elected representatives):這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是代議民主制中人民參與政治、控制議程(agenda control)的最重要途徑,實踐掌權者向選民問責(accountable)的理念,也就是「代議民主之所以民主」的依據。
2.自由、公平及定期的選舉(free, fair and periodic elections):只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才可體現政治平等的原則。為了讓人民可以有效控制議程,並撤換不稱職的代表,選舉必須定期進行。
3.表達意見的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
4.結社自由(associational autonomy):包括組織政黨的自由。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民主本身就蘊含的基本權利。缺乏了這兩種自由,人民根本不能有效參與政治。
5.多樣化的資訊渠道(alternative sources to information):人民要擁有充分資訊,才可以作出真正的決定(包括選擇代表),因此資訊或新聞渠道絕不可讓官方壟斷。6.廣納性的公民身份(inclusive citizenship):這是說社會上所有人(或至少是所有成年人)都應該擁有政治權利,包括投票權(franchise)。如果社會上一些群體(如少數族裔、女性、窮人)被排斥於政治過程之外,那麼再頻密的選舉也不算是民主的,因為這違反了「全體人民參與」的要求。
套用 Dahl 另一本名著的說法,以上六項可以再簡化為兩點:參與(participation)及競爭(contestation)。5 代議民主政體必須賦予人民充分、平等的政治參與(包括投票權),而這意味選舉不但要過程公平,還要有足夠的競爭性。何謂「足夠」的競爭性呢?學界對此有不同見解,但底線是不可對候選人資格作出不合理限制。舉例說,要求參選者先有一定數目的選民提名才能成為候選人,這個限制可以是合理的,不少民主國家也有類似的安排。但如果要參選者先經過一個委員會審核、提名、投票才能成為候選人,而這個委員會本身又不是普選產生的,那麼這樣的「選舉」便極可能由掌權者操控,缺乏有意義的競爭,不能賦予人民充分的政治參與,因此是不民主的。6
讀者可能會問:除了直接民主及代議民主之外,民主還可能有其他模式嗎?近年來,一些政治學者提出了第三種可能性,這就是所謂「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簡單來說,審議式民主借用了普通法系(如香港)中陪審團(jury)的模式:先從全國人口中隨機抽出若干成年公民為「審議員」,再安排他們集中一起(如數天),審議某特定公共議題(如「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化?」)。主辦機構角色中立,只負責向參與的審議員提供所需的資料及其他後勤支援。審議的過程中,理性討論是最重要的,最後的投票結果反而是其次,只作社會大眾參考之用。故此,審議式民主的特色是,在考慮到直接民主的實際困難之餘,盡量增加一般人民參與政治的機會及深度。
相對於直接民主和代議民主,審議式民主是比較新鮮的概念,有關討論仍多留在理論的層面,在實踐上則處於試驗階段。「佔領中環」運動醞釀期間的「商討日」(D-day)可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但其實香港電台近年舉辦的「慎思民調」及「眾言堂」更加貼近審議式民主的本來設計。7 無可否認,審議式民主強調理性思考討論,相比單單投票有其獨特吸引之處。然而,審議式民主並不可能完全取代直接民主或代議民主:審議式民主的參與者只是隨機抽樣出來的代表,並沒有人民投票授權,因此不能代表全體人民作出公共決策,否則便違反了「人人平等參與」的民主精神。這也是審議員和法庭上的陪審團之間最重要的分別。
總結
民主可定義為一種建基於政治平等的集體決策模式,在這模式下,每一位公民都有平等參與制訂公共政策的權利。
由於「民眾參與」是民主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民本政治」或「諮詢政治」不能算是民主。
民主是一種程序,其本身只預設了某些政治權利(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除此之外,民主並不包含其他價值,如經濟平等、理性、容忍,或一般的人權與自由,儘管這些價值在實際上可能對民主有利。
「政治平等」並非人類唯一追求的價值。由於民主本身並不包含其他價值,它也就有機會跟其他價值衝突,故民主有可能要跟其他社會目標妥協。
代議民主制是當今實踐民主的主要方式。其重點是普遍而平等的投票權,以及公平、有充分競爭的選舉。
本章對民主的理解是狹義的,僅視民主為一種程序。並非所有人都會同意這種看法,但程序式的民主觀(procedural view of democracy)至少有兩個優點。首先,將人權、自由、公義等概念排除出「民主」之外,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民主制度本身的各種優點和缺點。其次,概念定義得越窄,其傳遞的資訊也就越準確。試想想,如果我們把所有價值,如人權、自由、公義、團結等,都加諸民主身上的話,「民主」本身其實已經成為一個無所不包、但內容空洞的名詞了。
民主是建基於政治平等的集體決策模式
社會總要作出一些重要決定。舉例說,政府應該多抽稅來作再分配 ,還是要減稅「還富於民」?我們應否立法訂定標準工時?為增加住屋供應,是否要填海或取消郊野公園?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化?……這些都是社會層面的抉擇,即一般所謂「公共政策」。和個人層面的抉擇比較,公共政策有兩大特點:首先,其影響範圍較廣,牽涉的利益團體也較多;再者,正因為公共政策牽連甚廣,不同人士也就往往看法迥異。
如何處理這些分歧呢?當然,最理想的方法是透過和平理性的討論,收窄分歧,尋求共識。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一致共識」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首先,有關公共事務的爭論往往源於價值觀的分歧;在多元化的現代社會,我們不能亦不必事事強求「一致共識」。但另一方面,很多公共或社會問題都要及時處理,根本不容許無休止的討論。因此,我們必須訂立一套集體決策模式(a mode of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好讓大家在討論過後而又不能達致共識時,仍然可以根據某種合理的程序(reasonable procedure)來作出決定。顯然易見,集體決策模式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集體決策模式,也就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政治體制(political regimes)。在傳統社會,決策權力往往集中於少數世襲貴族甚至是君主一人之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在其《理想國》(Republic)一書中,則主張由有智慧的人來當政(也就是所謂 philosopher-king)。
民主正是一種集體決策模式。跟其他決策模式相比,民主有兩大特色。第一,社會上所有成員(或至少是所有成年成員)都可以參與決策過程。第二,作決定時,每個成員的「話事權」均等,不會出現某些人的意見較受重視的情況。為甚麼每個人的「話事權」都要均等呢?這是基於「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的價值或原則,即是說在參與集體決策的時候,每一位公民的權力和地位都應該是相等的。因此,簡單來說,民主就是一種建基於政治平等的集體決策模式。以上主要是普遍性及概念性的討論。實際運作過程當中,哪種政治制度會比較合乎政治平等的理念呢?民主社會是否事事都行多數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本章稍後將加以討論。但以上定義帶出非常重要兩點。第一,民主是一種程序(procedure),換言之,市民大眾的參與過程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我們在這裏對民主採取一個狹義(narrow)的理解, 即除了政治平等外,民主本身並不包含其他概念和價值,如一般的自由、人權、經濟平等或容忍(tolerance)等等。在以下幾節,我們會再詳細解釋這兩點, 並藉此澄清幾個有關民主的常見誤解。
民主不等同「民本政治」或「諮詢政治」
「民本」或「以民為本」的理念中國古已有之。孟子便強調執政者必須以民為本。一些人更以「民本」的理念說明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已經蘊含「民主」的土壤。不過,根據我們的定義,「民本」並不等同民主。
所謂「民本」,簡單來說,就是指執政者作決定時要以人民的利益作為最後依歸。但甚麼才是「人民的利益」呢?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會認為,統治國家的聖人賢君,當然會知道甚麼是人民的利益。但問題是,統治者眼中的公眾利益可能跟人民眼中的公眾利益不盡相同。換句話說,再「民本」的統治者,其決定也往往跟民意有極大差距。這是因為,「民本政治」只要求統治者以民為本,卻沒有賦予人民參政的權利。另一方面,民主國家的政客,雖然未必會事事「以民為本」,但由於選票的壓力,其決定最終也不致偏離民意太遠。由此可見,民主和民本是不同的。民本政治不等同民主。兩者之間的關鍵分別,在於「民眾參與」。
那麼「諮詢政治」又是否等於民主?從「民眾參與」的角度來看,「諮詢」無可否認比「民本」有進步。當然,只做門面功夫、甚至扭曲民意的「假諮詢」,肯定不是民主。可是,如果當政者的諮詢是認真的,那又如何?不少學者都指香港(尤其是殖民地時期的香港)的政治是「諮詢政治」,政府就所有重大事情都會先諮詢民意。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香港算不算有民主?再進一步說,假設世襲的君主每次作決定時都以人民的偏好為最終依歸(比方說,透過民意調查來定奪),那麼民主和獨裁之間還有分別嗎?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誠然,民主的特徵之一,就是其決定最終會以民意主流為依歸。可是我們不能單憑此點來判別制度是否民主。民主的核心理念是每位公民都有平等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利。在此,「參與權」是不可或缺的。欠缺公民參與的公共決策,即使其結果合乎民意,也不算是民主的。同樣地,即使當政者真的「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只要他不肯開放權力,讓人民真正參與,那麼他依然是獨裁的。下面我們會提到,在實際情況中,人民未必可以事事直接參與決定,因此也就產生了代議政制(representation system)。然而,代議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中的代表(主要指立法機關的議員,但也可包括行政首長)仍然必須由人民選出。換言之,選舉投票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主不等同人權、自由、理性或容忍
在很多人心目中,民主、自由和人權這三個概念,即使並非同義,也至少是高度相關。這種想法不難理解。歷史上,這三個概念都源自西方。到了今天,民主傳統最強的國家,差不多全部是宣揚人權最力、自由主義主導的西方國家。然而,民主、自由和人權三者其實是迥然不同的概念,而且它們之間並非毫無衝突。民主本身的確預設了某些基本人權和自由,但並非所有人權和自由都可以從民主的理念中推導出來。最自由的國度也不一定是最民主的國度。
在分析民主、自由和人權的關係之前,我們先要把這些概念分辨清楚。如上所述,民主是一種建基於政治平等的集體決策模式。至於自由,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個人行為不受限制。當然,在群體社會中,「絕對個人自由」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基本的個人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已是大部分社會公認的價值,並通常以「人權」的形式來立法保障。所謂人權,就是指每個人生而為人都擁有的權利(或稱「天賦權利)」,而這些權利都不可以因「公眾利益」等理由而隨意剝奪。對自由主義者(liberals)來說,個人自由和人權是非常重要的價值,也就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恰當理由。由此可見,民主、自由和人權是不同的概念。那麼,它們之間又有甚麼關係?由於民主的要義就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參與制訂政策,因此這個理念本身就預設了某些個人權利和自由,否則「民主」只不過是空談。舉例說,為了讓人民有充分的政治參與,言論、通訊及結社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民主本身就蘊含了言論自由、通訊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個人權利,因為那是民主的先決條件。
然而,並非所有人權和自由都可以從民主推導出來的。民主所關心的,只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也就是指公民可以參與政治決策過程。除此之外,諸如宗教自由、職業自由、婚姻自由等人權,即使重要,也跟民主沒有概念上的關係。如果一個社會透過民主制度來訂立限制宗教自由的法例(如訂立國教),或者限制市場運作的政策(如國有化),那麼這個社會可能不算自由,但它依然是民主的。換句話說,民主的社會不一定是自由的社會,儘管民主本身預設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權利。
那麼,自由的社會又是否一定是民主的?不一定,只要個人權利和自由大致得到保障,不民主的社會也可以是非常自由的。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殖民地時代,可以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的香港人少之又少。直到今天,大部分香港人還不能投票選出行政長官。然而,國際輿論大都認為香港仍是世界上相對自由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來說明民主、自由和人權之間的分別。上面提及,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是自由主義當道的社會,但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所指涉的是完全不同的價值。自由主義的要義,在於個人自由及人權是重要政治價值,保障個人自由和人權正是限制政府權力的合理依據。自由主義的相反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國家直接干預人民所有事項,包括私人層面的活動(如家庭生活、擇偶等)。我們可以把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視作光譜的兩端,如下所示:
自由主義 極權主義
民主政體講求的,則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平等的身份來參與政治決策。民主政治的相反是獨裁政體(dictatorship),也就是說由國家最高領導人獨攬大權,其他人基本上沒有參與的份兒。東西方古代的皇帝或絕對君主(absolute monarchs)就是例子。因此,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也是兩個極端,中間還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如寡頭政治(oligarchy)、有限度民主政治2 等等。民主政體 獨裁政體
結合以上兩條「光譜」,我們可以得出至少四種不同的政治模式,即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極權民主政體、極權獨裁政體及自由獨裁政體。3 所以,「民主」不一定是自由民主體制;民主也可以是極權或不自由的(即所謂illiberal democracy)。另一方面,獨裁政治不一定是極權的;歷史上也有不少相對自由但獨裁(或不民主)的政權。
從現實情況觀察,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確有着某種共生關係。獨裁政體往往是極權的,而自由的社會似乎比較有利民主。一方面,民主制度給予人民更換政府的權力,減少執政者濫權的機會,也就保障了各種基本人權和自由。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較自由的社會,比較尊重不同意見,並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礎也就較穩固。但概念上民主政體和自由主義完全不同,必須分辨清楚。自由主義背後的價值是個人自由;它關心的,是政府權力界限(scope of power)的問題。民主政體背後的價值是政治平等,而非自由本身。民主所關心的,是政府權力來源(sources of power)的問題。
明白了民主不等同人權和自由,那民主跟「理性」及「容忍」的分別也不難理解。民主只是一種程序,本身並不包括「理性」、「容忍」等價值及概念,儘管「理性」和「容忍」的態度對民主政治的運作通常都是有利的。不少香港人都把民主等同為理性討論、包容異己,這其實是錯誤的。沒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如一人一票的選舉),再理性和包容的社會都不算是民主的。相反,民主的社會也不一定是非常包容的。上面提及「以民主制度來限制宗教自由」即是一例。
這把我們帶到非常重要的一點:民主(或政治平等)只是眾多價值之一,並可能和其他社會價值衝突。理論上民主確有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因此大部分自由民主政體的國家都透過一些憲制或法律上的制衡(如人權法、獨立的司法覆核等),來限制民選政府的權力,防止執政者濫權或出現多數人的暴政,從而保障重要的人權及自由。有些人會說,由非民選的法官及司法機構來限制民選政府的權力,根本就是「反民主」的。這種說法本身沒有錯,但我們必須記住,民主並非至高無上的價值:為了其他重要價值(如人權、自由、社會公義等等),民主不一定是絕對的。從直接民主到代議政制:如何落實政治平等?
以上是抽象層面的討論。到底我們應該用甚麼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來實行民主,以落實政治平等的理念?
先引入兩個概念: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及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所謂直接民主,就是由全體人民直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包括以投票作出決定,即所謂全民公決或公民投票(referendum)。這可算是最古老的民主方式,古希臘城邦(city-states)的民主體制就包含了不少直接民主的成分。到了今天,全民公決在部分國家及地區(如瑞士、法國及美國一些州份)依然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環。
無可否認,直接民主講求「人民事事參與」,的確較接近民主的本來理想。可是,現代社會日益複雜,基於時間及其他限制,要求所有人民直接參與每項公共決策有點不切實際,代議民主(或代議政制)也就應運而生。顧名思義,代議民主就是指人民透過自己選出的代表來制定公共政策,並由他們監察以至領導行政機關施政。事實上,今天的自由民主政體,基本上都是以代議政制主導。即使設有全民公決的國家,也只有在關鍵問題上(如修改憲法、罷免行政首長、重大國家政策)才會實行直接民主。
那麼,怎樣的代議政制才算符合民主的理念?在此,我們或可借用民主理論大師 Robert Dahl 的分析。4 Dahl 指出,下面六項都是代議民主必需的:
1.民選代表(elected representatives):這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是代議民主制中人民參與政治、控制議程(agenda control)的最重要途徑,實踐掌權者向選民問責(accountable)的理念,也就是「代議民主之所以民主」的依據。
2.自由、公平及定期的選舉(free, fair and periodic elections):只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才可體現政治平等的原則。為了讓人民可以有效控制議程,並撤換不稱職的代表,選舉必須定期進行。
3.表達意見的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
4.結社自由(associational autonomy):包括組織政黨的自由。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民主本身就蘊含的基本權利。缺乏了這兩種自由,人民根本不能有效參與政治。
5.多樣化的資訊渠道(alternative sources to information):人民要擁有充分資訊,才可以作出真正的決定(包括選擇代表),因此資訊或新聞渠道絕不可讓官方壟斷。6.廣納性的公民身份(inclusive citizenship):這是說社會上所有人(或至少是所有成年人)都應該擁有政治權利,包括投票權(franchise)。如果社會上一些群體(如少數族裔、女性、窮人)被排斥於政治過程之外,那麼再頻密的選舉也不算是民主的,因為這違反了「全體人民參與」的要求。
套用 Dahl 另一本名著的說法,以上六項可以再簡化為兩點:參與(participation)及競爭(contestation)。5 代議民主政體必須賦予人民充分、平等的政治參與(包括投票權),而這意味選舉不但要過程公平,還要有足夠的競爭性。何謂「足夠」的競爭性呢?學界對此有不同見解,但底線是不可對候選人資格作出不合理限制。舉例說,要求參選者先有一定數目的選民提名才能成為候選人,這個限制可以是合理的,不少民主國家也有類似的安排。但如果要參選者先經過一個委員會審核、提名、投票才能成為候選人,而這個委員會本身又不是普選產生的,那麼這樣的「選舉」便極可能由掌權者操控,缺乏有意義的競爭,不能賦予人民充分的政治參與,因此是不民主的。6
讀者可能會問:除了直接民主及代議民主之外,民主還可能有其他模式嗎?近年來,一些政治學者提出了第三種可能性,這就是所謂「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簡單來說,審議式民主借用了普通法系(如香港)中陪審團(jury)的模式:先從全國人口中隨機抽出若干成年公民為「審議員」,再安排他們集中一起(如數天),審議某特定公共議題(如「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化?」)。主辦機構角色中立,只負責向參與的審議員提供所需的資料及其他後勤支援。審議的過程中,理性討論是最重要的,最後的投票結果反而是其次,只作社會大眾參考之用。故此,審議式民主的特色是,在考慮到直接民主的實際困難之餘,盡量增加一般人民參與政治的機會及深度。
相對於直接民主和代議民主,審議式民主是比較新鮮的概念,有關討論仍多留在理論的層面,在實踐上則處於試驗階段。「佔領中環」運動醞釀期間的「商討日」(D-day)可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但其實香港電台近年舉辦的「慎思民調」及「眾言堂」更加貼近審議式民主的本來設計。7 無可否認,審議式民主強調理性思考討論,相比單單投票有其獨特吸引之處。然而,審議式民主並不可能完全取代直接民主或代議民主:審議式民主的參與者只是隨機抽樣出來的代表,並沒有人民投票授權,因此不能代表全體人民作出公共決策,否則便違反了「人人平等參與」的民主精神。這也是審議員和法庭上的陪審團之間最重要的分別。
總結
民主可定義為一種建基於政治平等的集體決策模式,在這模式下,每一位公民都有平等參與制訂公共政策的權利。
由於「民眾參與」是民主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民本政治」或「諮詢政治」不能算是民主。
民主是一種程序,其本身只預設了某些政治權利(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除此之外,民主並不包含其他價值,如經濟平等、理性、容忍,或一般的人權與自由,儘管這些價值在實際上可能對民主有利。
「政治平等」並非人類唯一追求的價值。由於民主本身並不包含其他價值,它也就有機會跟其他價值衝突,故民主有可能要跟其他社會目標妥協。
代議民主制是當今實踐民主的主要方式。其重點是普遍而平等的投票權,以及公平、有充分競爭的選舉。
本章對民主的理解是狹義的,僅視民主為一種程序。並非所有人都會同意這種看法,但程序式的民主觀(procedural view of democracy)至少有兩個優點。首先,將人權、自由、公義等概念排除出「民主」之外,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民主制度本身的各種優點和缺點。其次,概念定義得越窄,其傳遞的資訊也就越準確。試想想,如果我們把所有價值,如人權、自由、公義、團結等,都加諸民主身上的話,「民主」本身其實已經成為一個無所不包、但內容空洞的名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