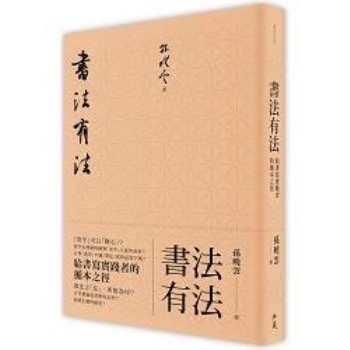一一、人是萬物的尺度
我小時候,曾經玩過一種中國古老的玩具──九連環,規則甚是嚴密,要把九個環套進再套出,程式多而且不能錯,錯了一道就卡住。
困惑的解決就像是九連環,一環通了,接下去再連一環,哪一環不通都不行。
繼而,我面臨的困惑卻是:古人為何要使用轉動筆桿的方法寫字呢?究竟有什麼優越性呢?它與中國漢字的發展又有何關係呢?
史書關於此類記載,真是無從查起。半坡遺址,距今六七千年;仰紹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彩陶器皿上手繪的圖案,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筆的存在,那時漢字還處於胚胎之中,哪來的史書?我有心查閱有關文房四寶的史料,也是不著此邊際。問人,更無對象。當時確實有些絕望。到處皆是「未知數」。
但是,有一個「已知數」是毋庸置疑的。
半坡遺址以來的六七千年的人類,衣食住行與興趣愛好,整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唯一沒有變的,只有人的生理現象和生理功能。具體說,我們與六七千年前人一樣有臂(大臂、小臂),一樣有手(掌、五指),其功能、動作依舊。我自己的軀體,自己的臂,自己的手,自己的生理自然與感受,便是超越時空最直接的證明,最可信的依據。
我記得一位古希臘哲學家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我開始查閱大量實物資料,從自身的實驗和體會中一點一點得出結論。
一二、筆法產生的動機之一:裹鋒與連續書寫
元代陶宗儀《輟耕錄》記載,上古人類用獸毛做筆之前,曾「以竹梃點漆而書」,即指嫩竹尖上的絨絲為毫。古代筆毫有裹在筆桿外沿的,亦有將筆頭剖成數開,將筆毛夾於其中的。
當時古人不外乎用的是碳、墨、漆,即一些礦物質顏料。為了能聚多些墨或顏料在筆端,一次可多畫幾筆,筆畫又可粗可細,古人便自然選擇用獸毛或質地相似的植物材料做毫。
人類使用工具的習慣和方法,必然是從實踐中總結,優勝劣汰。我用不轉筆與轉筆兩種方式試了一下,果然效果各異:
前者寫不了兩筆,筆毛不是扁就是開叉,需要不停地把筆毫舔尖。後者筆鋒始終是裹著的,可以連續寫多字而不用舔筆。即使筆鋒開叉時,依舊可以寫出清晰的字。這正是古人筆法萌芽的最初動機之一。我們可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周青銅器的銘文上看到明顯的轉筆痕跡(圖18)。或能追溯到更早,比如在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罐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徒手繪製的不規則的幾何圖形(圖19),這就是後來發展成商周青銅器上具有代表性的饕餮紋(圖20)、雲雷紋(圖21)、夔紋(圖22)等的雛形,均呈螺旋式、圓轉的對稱紋路。
只有將筆桿左右轉動,才可能將筆毫隨時裹住,既快速又勻稱地畫出這樣的線條。正是由於筆法的起源,才造就了這些具有中華民族傳統特色的圖形。不信,我們動手試試?
人類是聰明的,文字起源一開始就走上了「便捷」之路。
當然,還有動機之二。
一三、筆法產生的動機之二:沒有依託的書寫
「席地而坐」、「窗明几淨」這些詞語產生時,中國人還沒有使用桌椅。確切地說,有毛筆以來的七千年,起碼五千五百年是坐在地上,後來也只是坐在床上、榻上的。
中國古人的坐,是兩膝著地,腳掌朝上,屁股落在腳踝上。如今的日本人、朝鮮人仍這樣坐。當時在床榻上亦如是坐。到南北朝胡床、胡椅引進,才有了垂足坐。我們現在去日本、韓國,坐不慣,其實我們的老祖宗也是這樣坐的。
相傳在遠古有俎,是作為祭祀時切牲、陳牲的禮器。據說商周就有几,最初是馬襠形的憑几,是後來椅子扶手的雛形。晉代出現了圈几(圖23),是圈椅的雛形。俎很快發展成案,分長條案和方案,很低,均是席地而坐的產物。長條案到後來演變成高案,專門用來祭祀與擺設;方案則發展成高的方桌。
最早的椅子可以在敦煌壁畫中看到。當時,只是在少數貴族、僧侶中使用,尚未普及。唐到五代,出現了各式的椅子、凳子,是古老的「席地而坐」向垂足坐的過渡時期,但還是局限於上層。直到宋代,桌、椅、凳才真正普及到廣大老百姓。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依據。
先設想一下,古人當年「席地而坐」,左手持陶器或竹簡,右手執筆,沒有任何依託與支撐。如果要令用筆平穩,控制得當,必須使大臂夾緊在腰間,小臂作支撐,手掌虛空執筆。所書竹簡等物與眼睛的距離大約一尺,應該呈閱讀時的姿勢。我曾偶然看過一幀文物圖片,遂引起極大的興趣:
這是西晉永寧二年的青釉雙坐書寫瓷俑(圖24),一九五八年在湖南長沙出土。兩俑對坐,中間為一長方形几,上面放置著硯臺、筆與筆架。一俑似手捧幾塊板,這樣的板明顯是「牘」。古時的牘為薄木板所做,一尺左右,故為「尺牘」。另一俑則左手持一尺牘,右手執筆做書寫狀,正是閱讀時的姿勢。
這說明,當時的几並不作書寫時肘、腕的支撐和依託,僅用來置放器物與文具。兩瓷俑證明了西晉人的書寫姿勢,也證明了長達幾千年中國人都是在手臂、手腕無依託的情況下用此種姿勢書寫。
在北方,除了用桌子,炕上還沿用了几──炕桌,卻是盤腿而坐。古人的「坐」,自有榻、椅以來,已經失傳了一千年。
我第一次在博物館見竹簡上的蠅頭小字時,大為驚訝,駐足細觀良久。竹簡寬不過一公分,有的只有七、八公釐。奇怪的是,如此小字,筆筆流暢、順滑,無一筆顫抖、遲滯。鑒歷史年代,書寫姿勢無疑與西晉瓷俑同。
我們不妨席地而坐,以無依託的方式,做西晉瓷俑姿勢,用不轉筆與轉筆各一試,結果自然分明:
不轉筆即靠提按用筆,筆尖承受的力太大,因此把握吃力,不穩,易抖,且滯慢。正因為是左手持簡牘或紙,輔墊不能絕對穩定,筆尖的用力會使筆毫散開,影響速度與美觀。
轉筆則集力於手指捻轉,使筆尖的力分散,易控制筆畫粗細,令其圓轉光滑,且行筆快速。
由此可見,除了上一章所說的原因之外,為右臂、右手無依託的狀態設想一種最方便、最科學的用筆辦法,也正是古人「筆法」萌芽的動機之二。
我小時候,曾經玩過一種中國古老的玩具──九連環,規則甚是嚴密,要把九個環套進再套出,程式多而且不能錯,錯了一道就卡住。
困惑的解決就像是九連環,一環通了,接下去再連一環,哪一環不通都不行。
繼而,我面臨的困惑卻是:古人為何要使用轉動筆桿的方法寫字呢?究竟有什麼優越性呢?它與中國漢字的發展又有何關係呢?
史書關於此類記載,真是無從查起。半坡遺址,距今六七千年;仰紹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彩陶器皿上手繪的圖案,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筆的存在,那時漢字還處於胚胎之中,哪來的史書?我有心查閱有關文房四寶的史料,也是不著此邊際。問人,更無對象。當時確實有些絕望。到處皆是「未知數」。
但是,有一個「已知數」是毋庸置疑的。
半坡遺址以來的六七千年的人類,衣食住行與興趣愛好,整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唯一沒有變的,只有人的生理現象和生理功能。具體說,我們與六七千年前人一樣有臂(大臂、小臂),一樣有手(掌、五指),其功能、動作依舊。我自己的軀體,自己的臂,自己的手,自己的生理自然與感受,便是超越時空最直接的證明,最可信的依據。
我記得一位古希臘哲學家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我開始查閱大量實物資料,從自身的實驗和體會中一點一點得出結論。
一二、筆法產生的動機之一:裹鋒與連續書寫
元代陶宗儀《輟耕錄》記載,上古人類用獸毛做筆之前,曾「以竹梃點漆而書」,即指嫩竹尖上的絨絲為毫。古代筆毫有裹在筆桿外沿的,亦有將筆頭剖成數開,將筆毛夾於其中的。
當時古人不外乎用的是碳、墨、漆,即一些礦物質顏料。為了能聚多些墨或顏料在筆端,一次可多畫幾筆,筆畫又可粗可細,古人便自然選擇用獸毛或質地相似的植物材料做毫。
人類使用工具的習慣和方法,必然是從實踐中總結,優勝劣汰。我用不轉筆與轉筆兩種方式試了一下,果然效果各異:
前者寫不了兩筆,筆毛不是扁就是開叉,需要不停地把筆毫舔尖。後者筆鋒始終是裹著的,可以連續寫多字而不用舔筆。即使筆鋒開叉時,依舊可以寫出清晰的字。這正是古人筆法萌芽的最初動機之一。我們可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周青銅器的銘文上看到明顯的轉筆痕跡(圖18)。或能追溯到更早,比如在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罐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徒手繪製的不規則的幾何圖形(圖19),這就是後來發展成商周青銅器上具有代表性的饕餮紋(圖20)、雲雷紋(圖21)、夔紋(圖22)等的雛形,均呈螺旋式、圓轉的對稱紋路。
只有將筆桿左右轉動,才可能將筆毫隨時裹住,既快速又勻稱地畫出這樣的線條。正是由於筆法的起源,才造就了這些具有中華民族傳統特色的圖形。不信,我們動手試試?
人類是聰明的,文字起源一開始就走上了「便捷」之路。
當然,還有動機之二。
一三、筆法產生的動機之二:沒有依託的書寫
「席地而坐」、「窗明几淨」這些詞語產生時,中國人還沒有使用桌椅。確切地說,有毛筆以來的七千年,起碼五千五百年是坐在地上,後來也只是坐在床上、榻上的。
中國古人的坐,是兩膝著地,腳掌朝上,屁股落在腳踝上。如今的日本人、朝鮮人仍這樣坐。當時在床榻上亦如是坐。到南北朝胡床、胡椅引進,才有了垂足坐。我們現在去日本、韓國,坐不慣,其實我們的老祖宗也是這樣坐的。
相傳在遠古有俎,是作為祭祀時切牲、陳牲的禮器。據說商周就有几,最初是馬襠形的憑几,是後來椅子扶手的雛形。晉代出現了圈几(圖23),是圈椅的雛形。俎很快發展成案,分長條案和方案,很低,均是席地而坐的產物。長條案到後來演變成高案,專門用來祭祀與擺設;方案則發展成高的方桌。
最早的椅子可以在敦煌壁畫中看到。當時,只是在少數貴族、僧侶中使用,尚未普及。唐到五代,出現了各式的椅子、凳子,是古老的「席地而坐」向垂足坐的過渡時期,但還是局限於上層。直到宋代,桌、椅、凳才真正普及到廣大老百姓。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依據。
先設想一下,古人當年「席地而坐」,左手持陶器或竹簡,右手執筆,沒有任何依託與支撐。如果要令用筆平穩,控制得當,必須使大臂夾緊在腰間,小臂作支撐,手掌虛空執筆。所書竹簡等物與眼睛的距離大約一尺,應該呈閱讀時的姿勢。我曾偶然看過一幀文物圖片,遂引起極大的興趣:
這是西晉永寧二年的青釉雙坐書寫瓷俑(圖24),一九五八年在湖南長沙出土。兩俑對坐,中間為一長方形几,上面放置著硯臺、筆與筆架。一俑似手捧幾塊板,這樣的板明顯是「牘」。古時的牘為薄木板所做,一尺左右,故為「尺牘」。另一俑則左手持一尺牘,右手執筆做書寫狀,正是閱讀時的姿勢。
這說明,當時的几並不作書寫時肘、腕的支撐和依託,僅用來置放器物與文具。兩瓷俑證明了西晉人的書寫姿勢,也證明了長達幾千年中國人都是在手臂、手腕無依託的情況下用此種姿勢書寫。
在北方,除了用桌子,炕上還沿用了几──炕桌,卻是盤腿而坐。古人的「坐」,自有榻、椅以來,已經失傳了一千年。
我第一次在博物館見竹簡上的蠅頭小字時,大為驚訝,駐足細觀良久。竹簡寬不過一公分,有的只有七、八公釐。奇怪的是,如此小字,筆筆流暢、順滑,無一筆顫抖、遲滯。鑒歷史年代,書寫姿勢無疑與西晉瓷俑同。
我們不妨席地而坐,以無依託的方式,做西晉瓷俑姿勢,用不轉筆與轉筆各一試,結果自然分明:
不轉筆即靠提按用筆,筆尖承受的力太大,因此把握吃力,不穩,易抖,且滯慢。正因為是左手持簡牘或紙,輔墊不能絕對穩定,筆尖的用力會使筆毫散開,影響速度與美觀。
轉筆則集力於手指捻轉,使筆尖的力分散,易控制筆畫粗細,令其圓轉光滑,且行筆快速。
由此可見,除了上一章所說的原因之外,為右臂、右手無依託的狀態設想一種最方便、最科學的用筆辦法,也正是古人「筆法」萌芽的動機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