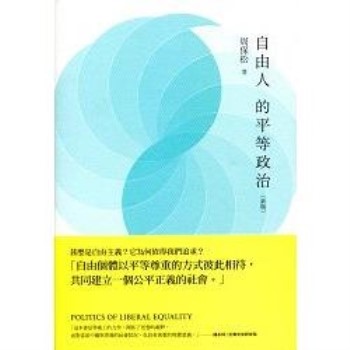第一章 契約、公平與社會正義
美國當代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於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是二十世紀劃時代的政治哲學著作。它復活了規範政治哲學的傳統,打破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哲學已死」的困局,並主導了過去四十多年道德及社會政治哲學的討論。1羅爾斯的同事、放任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諾齊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早在1974年便曾預言,《正義論》後的政治哲學家,要麼在羅爾斯的理論框架內工作,要麼必須解釋為何不這樣做。 2事實的確如此。1971年後政治哲學發展蓬勃,從強調私有產權至上的放任自由主義到左翼的自由平等主義,從效益主義到社群主義,從文化多元主義、女性主義到環保主義和國際正義理論,林林總總,無論所持立場為何,均須回應羅爾斯的觀點。即使到了今天,情況依然未變。3《 正義論》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
學術性的哲學書籍,一般只能賣一千本左右。但此書出版至今,單在美國已售出逾三十萬本,並被譯成二十七種語言,成為哲學、政治及法律本科生的基本讀物。迄今為止,已有超過五千篇文章專門討論羅爾斯的理論。以一本厚達六百頁、充滿術語和哲學論證的著作來說,殊不尋常。羅爾斯在2002年11月24日逝世後,英美各大報章紛紛發表悼念文章,高度評價他的貢獻。例如巴利(Brian Barry)在《金融時報》稱他改變了整個學科的發展,《泰晤士報》則譽他為繼十九世紀的密爾(J. S. Mill,或譯穆勒)之後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要瞭解當代政治哲學,《正義論》是最好的出發點。
《正義論》英文修訂版在1999年出版,羅爾斯修正了初版的一些基本論證,並聲稱修訂版較初版有重大改善。我在此章將對《正義論》作一俯瞰式的介紹,讓讀者對此書有個基本認識,從而為其後各章的討論鋪路。我將先介紹羅爾斯的生平及該書的寫作背景,然後逐步分析《正義論》的論證。
羅爾斯1921年生於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一個富裕家庭,五兄弟中排行第二。4父親是成功的稅務律師及憲法專家,母親生於一個德國家庭,是個活躍的女性主義者。羅爾斯自小體弱多病,兩個弟弟更先後受他傳染而病逝,這段經歷對他一生有難以磨滅的影響。羅爾斯雖然家境富裕,但年少時已感受到社會種族及階級的不平等,例如他觀察到黑人孩子不能和白人就讀同一學校並被禁止互相交友、黑人的生活環境惡劣等。
羅爾斯1939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他的啟蒙老師是當時著名的哲學教授馬科姆(Norman Malcolm)。馬科姆是維特根斯坦的學生兼朋友,並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在美國發揚光大。羅爾斯1943年以最優等成績
取得哲學學位。畢業後,旋即加入軍隊,參加對日戰爭。1945年美國投擲原子彈於廣島時,羅爾斯仍然留在太平洋。對於他的戰爭經歷,羅爾斯從來沒有公開談論過。但在1995年美國《異議者》(Dissent)雜誌的「紀念廣島五十年」專題上,羅爾斯卻毫不猶豫地批評美國當年投擲原子彈、殺害大量無辜日本平民生命的決定犯了道德上的大錯,並批評杜魯門總統不配稱為一個政治家。5戰爭結束後,羅爾斯於1946年重回普林斯頓攻讀道德哲學博士,師從效益主義哲學家史地斯(W. T. Stace)。1950年遞交論文,題目為《一個倫理學知識基礎的探究:對於品格的道德價值的判斷的有關考察》。6羅爾斯在論文中嘗試提出一種反基礎論(anti-foundationalist)的倫理學程序,他後來發展的「反思均衡法」(reflective equilibrium)亦源於此論文的構思。1952年,羅爾斯獲獎學金往牛津大學修學一年。在那裏,他認識了伯林(Isaiah Berlin)、哈特(H. L. A. Hart)等當代著名哲學家,而運用假然契約(hypothetical contract)論證道德原則的構想亦於當時成形。從牛津返美後,羅爾斯先後在康奈爾(1953–1959)、麻省理工(1960–1962)等大學任教,1962年轉到哈佛大學哲學系,1979年接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阿羅(Kenneth Arrow)擔任「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職位。此職級是哈佛的最高榮譽,當時全校只有八人享此待遇。羅爾斯在哈佛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博士生,很多在今天的哲學界已自成一家。7
羅爾斯雖然廣受各方尊崇,為人卻極為低調,既不接受傳媒訪問,亦不喜交際,生活簡樸而有規律。他治學極為嚴謹,每篇文章均經過反複修改、千錘百煉後才願意出版。例如《正義論》中很多基本概念,羅爾斯早在五十年代已經形成,並先後出版了多篇重要論文。而到六十年代,他已開始用《正義論》第一稿作為上課講義,前後三易其稿,直至1971年才正式出版。《正義論》出版後,羅爾斯謙虛聽取各方批評,繼續修正及發展他的理論,直到1993年才出版他第二本著作《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並對原來的觀點作出相當大的修正。8此書一出,瞬即成為學術界焦點,並為政治哲學設定新的議題及研究方向,可謂羅爾斯學術生涯的第二高峰。1999年,《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面世,專門討論國際正義問題。9羅爾斯在哈佛教學用的《道德哲學史講義》和《政治哲學史講義》也先後出版,10而他晚年嘗試整合前後期理論的《公平式的正義:再論》(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則於2001年出版。11哲學思考離不開
哲學家所處的時代及學術傳統。《正義論》的成功,相當程度上在於它對這兩方面均能作出積極回應,並提出極具原創的見解。《正義論》醞釀的六十年代,是自由主義受到重大挑戰的時代。尤其在美國,民權及黑人解放運動、新左派及嬉皮運動、反越戰運動等,對當時的政府及其制度提出了嚴重質疑。社會正義、基本人權、公民抗命以至貧富懸殊問題,成為各種運動最關心的議題。當時很多人認為,自由主義只是一種落伍而膚淺的意識形態,根本不足以應付時代挑戰。12《正義論》通過嚴謹生動而富原創性的論證,對這些問題作出了直接回應,並顯示出自由主義傳統仍有豐厚的理論資源,建構一個更為公正合理的社會。《正義論》的重要性,也和當時英美的學術氛圍有莫大關係。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顯學是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這種理論認為,任何規範性命題,都只是表達我們的感覺或情緒而已,不能增加任何實質性的知識。有意義的命題,要麼是分析性(analytic)的恆真命題,例如數學或邏輯;要麼是可以被證實的經驗性命題。既然哲學並非經驗性學科(那是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工作),唯一可做的便剩下邏輯和概念分析。
在這種環境下,規範政治哲學被推到極為邊緣的位置,漸漸從現實世界中退隱,對各種具體的道德及政治問題保持沉默,只從事道德語言分析的「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工作。所謂「政治哲學已死」,描述的正是這種境況。羅爾斯認為,僅靠邏輯及語言界說,根本無法建立任何實質性的正義理論(TJ, 51/44 rev.)。政治哲學最主要的工作,是要發展出一套有效的方法論,運用我們的道德直覺及各種經驗性知識,建構出一套最能符合我們深思熟慮的判斷(considered judgment)的正義體系,並以此回應民主社會出現的各種根本的政治問題。《正義論》被視為復活政治哲學的扛鼎之作,正因為它一方面能繼承傳統政治哲學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充份利用當代社會科學的新概念,系統地論證出一套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在最近的實踐哲學史上,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他將長期受到壓制的道德問題,重新恢復到嚴肅的哲學研究的對象的地位。」13
二
《正義論》的主要目的,是要建構一套在道德上值得追求,同時在實踐上可行的道德原則,以此規範社會的基本結構,決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這樣一套原則,被稱為社會正義原則(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在政治光譜上,羅爾斯的理論常被視為自由主義左翼(liberalism)或自由平等主義(liberal egalitarianism)。14它最大的特點,是一方面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另一方面重視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具體點說,一個公正社會必須充份保障每個公民有平等的權利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同時保證每個人有公平的平等機會去競逐社會職位和位置;而在經濟分配上,則主張共享發展,並強調任何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才可接受。
在這一節,我先闡明《正義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羅爾斯對社會合作的理解、良序社會的理念、正義原則應用的對象以及如何界定被分配之物品等。第三節則比較羅爾斯的正義觀和其他理論,以彰顯其獨特之處。第四節集中討論他的道德方法學和正義原則的證成理據。第五節分析他的原則如何應用到制度層面,第六節探討該書中第三部份的穩定性(stability)問題。最後,我會作一扼要總結。
美國當代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於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是二十世紀劃時代的政治哲學著作。它復活了規範政治哲學的傳統,打破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哲學已死」的困局,並主導了過去四十多年道德及社會政治哲學的討論。1羅爾斯的同事、放任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諾齊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早在1974年便曾預言,《正義論》後的政治哲學家,要麼在羅爾斯的理論框架內工作,要麼必須解釋為何不這樣做。 2事實的確如此。1971年後政治哲學發展蓬勃,從強調私有產權至上的放任自由主義到左翼的自由平等主義,從效益主義到社群主義,從文化多元主義、女性主義到環保主義和國際正義理論,林林總總,無論所持立場為何,均須回應羅爾斯的觀點。即使到了今天,情況依然未變。3《 正義論》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
學術性的哲學書籍,一般只能賣一千本左右。但此書出版至今,單在美國已售出逾三十萬本,並被譯成二十七種語言,成為哲學、政治及法律本科生的基本讀物。迄今為止,已有超過五千篇文章專門討論羅爾斯的理論。以一本厚達六百頁、充滿術語和哲學論證的著作來說,殊不尋常。羅爾斯在2002年11月24日逝世後,英美各大報章紛紛發表悼念文章,高度評價他的貢獻。例如巴利(Brian Barry)在《金融時報》稱他改變了整個學科的發展,《泰晤士報》則譽他為繼十九世紀的密爾(J. S. Mill,或譯穆勒)之後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要瞭解當代政治哲學,《正義論》是最好的出發點。
《正義論》英文修訂版在1999年出版,羅爾斯修正了初版的一些基本論證,並聲稱修訂版較初版有重大改善。我在此章將對《正義論》作一俯瞰式的介紹,讓讀者對此書有個基本認識,從而為其後各章的討論鋪路。我將先介紹羅爾斯的生平及該書的寫作背景,然後逐步分析《正義論》的論證。
羅爾斯1921年生於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一個富裕家庭,五兄弟中排行第二。4父親是成功的稅務律師及憲法專家,母親生於一個德國家庭,是個活躍的女性主義者。羅爾斯自小體弱多病,兩個弟弟更先後受他傳染而病逝,這段經歷對他一生有難以磨滅的影響。羅爾斯雖然家境富裕,但年少時已感受到社會種族及階級的不平等,例如他觀察到黑人孩子不能和白人就讀同一學校並被禁止互相交友、黑人的生活環境惡劣等。
羅爾斯1939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他的啟蒙老師是當時著名的哲學教授馬科姆(Norman Malcolm)。馬科姆是維特根斯坦的學生兼朋友,並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在美國發揚光大。羅爾斯1943年以最優等成績
取得哲學學位。畢業後,旋即加入軍隊,參加對日戰爭。1945年美國投擲原子彈於廣島時,羅爾斯仍然留在太平洋。對於他的戰爭經歷,羅爾斯從來沒有公開談論過。但在1995年美國《異議者》(Dissent)雜誌的「紀念廣島五十年」專題上,羅爾斯卻毫不猶豫地批評美國當年投擲原子彈、殺害大量無辜日本平民生命的決定犯了道德上的大錯,並批評杜魯門總統不配稱為一個政治家。5戰爭結束後,羅爾斯於1946年重回普林斯頓攻讀道德哲學博士,師從效益主義哲學家史地斯(W. T. Stace)。1950年遞交論文,題目為《一個倫理學知識基礎的探究:對於品格的道德價值的判斷的有關考察》。6羅爾斯在論文中嘗試提出一種反基礎論(anti-foundationalist)的倫理學程序,他後來發展的「反思均衡法」(reflective equilibrium)亦源於此論文的構思。1952年,羅爾斯獲獎學金往牛津大學修學一年。在那裏,他認識了伯林(Isaiah Berlin)、哈特(H. L. A. Hart)等當代著名哲學家,而運用假然契約(hypothetical contract)論證道德原則的構想亦於當時成形。從牛津返美後,羅爾斯先後在康奈爾(1953–1959)、麻省理工(1960–1962)等大學任教,1962年轉到哈佛大學哲學系,1979年接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阿羅(Kenneth Arrow)擔任「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職位。此職級是哈佛的最高榮譽,當時全校只有八人享此待遇。羅爾斯在哈佛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博士生,很多在今天的哲學界已自成一家。7
羅爾斯雖然廣受各方尊崇,為人卻極為低調,既不接受傳媒訪問,亦不喜交際,生活簡樸而有規律。他治學極為嚴謹,每篇文章均經過反複修改、千錘百煉後才願意出版。例如《正義論》中很多基本概念,羅爾斯早在五十年代已經形成,並先後出版了多篇重要論文。而到六十年代,他已開始用《正義論》第一稿作為上課講義,前後三易其稿,直至1971年才正式出版。《正義論》出版後,羅爾斯謙虛聽取各方批評,繼續修正及發展他的理論,直到1993年才出版他第二本著作《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並對原來的觀點作出相當大的修正。8此書一出,瞬即成為學術界焦點,並為政治哲學設定新的議題及研究方向,可謂羅爾斯學術生涯的第二高峰。1999年,《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面世,專門討論國際正義問題。9羅爾斯在哈佛教學用的《道德哲學史講義》和《政治哲學史講義》也先後出版,10而他晚年嘗試整合前後期理論的《公平式的正義:再論》(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則於2001年出版。11哲學思考離不開
哲學家所處的時代及學術傳統。《正義論》的成功,相當程度上在於它對這兩方面均能作出積極回應,並提出極具原創的見解。《正義論》醞釀的六十年代,是自由主義受到重大挑戰的時代。尤其在美國,民權及黑人解放運動、新左派及嬉皮運動、反越戰運動等,對當時的政府及其制度提出了嚴重質疑。社會正義、基本人權、公民抗命以至貧富懸殊問題,成為各種運動最關心的議題。當時很多人認為,自由主義只是一種落伍而膚淺的意識形態,根本不足以應付時代挑戰。12《正義論》通過嚴謹生動而富原創性的論證,對這些問題作出了直接回應,並顯示出自由主義傳統仍有豐厚的理論資源,建構一個更為公正合理的社會。《正義論》的重要性,也和當時英美的學術氛圍有莫大關係。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顯學是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這種理論認為,任何規範性命題,都只是表達我們的感覺或情緒而已,不能增加任何實質性的知識。有意義的命題,要麼是分析性(analytic)的恆真命題,例如數學或邏輯;要麼是可以被證實的經驗性命題。既然哲學並非經驗性學科(那是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工作),唯一可做的便剩下邏輯和概念分析。
在這種環境下,規範政治哲學被推到極為邊緣的位置,漸漸從現實世界中退隱,對各種具體的道德及政治問題保持沉默,只從事道德語言分析的「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工作。所謂「政治哲學已死」,描述的正是這種境況。羅爾斯認為,僅靠邏輯及語言界說,根本無法建立任何實質性的正義理論(TJ, 51/44 rev.)。政治哲學最主要的工作,是要發展出一套有效的方法論,運用我們的道德直覺及各種經驗性知識,建構出一套最能符合我們深思熟慮的判斷(considered judgment)的正義體系,並以此回應民主社會出現的各種根本的政治問題。《正義論》被視為復活政治哲學的扛鼎之作,正因為它一方面能繼承傳統政治哲學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充份利用當代社會科學的新概念,系統地論證出一套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在最近的實踐哲學史上,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他將長期受到壓制的道德問題,重新恢復到嚴肅的哲學研究的對象的地位。」13
二
《正義論》的主要目的,是要建構一套在道德上值得追求,同時在實踐上可行的道德原則,以此規範社會的基本結構,決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這樣一套原則,被稱為社會正義原則(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在政治光譜上,羅爾斯的理論常被視為自由主義左翼(liberalism)或自由平等主義(liberal egalitarianism)。14它最大的特點,是一方面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另一方面重視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具體點說,一個公正社會必須充份保障每個公民有平等的權利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同時保證每個人有公平的平等機會去競逐社會職位和位置;而在經濟分配上,則主張共享發展,並強調任何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才可接受。
在這一節,我先闡明《正義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羅爾斯對社會合作的理解、良序社會的理念、正義原則應用的對象以及如何界定被分配之物品等。第三節則比較羅爾斯的正義觀和其他理論,以彰顯其獨特之處。第四節集中討論他的道德方法學和正義原則的證成理據。第五節分析他的原則如何應用到制度層面,第六節探討該書中第三部份的穩定性(stability)問題。最後,我會作一扼要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