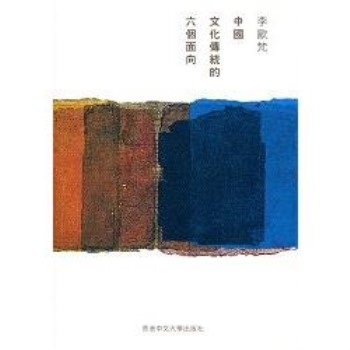第二講.續論二
從老電影的譯名學習古文
在第二講的討論環節,不少同學問我如何學古文。我完全沒有想到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且離題太遠,怎麼會從韓愈道統扯到如何學古文?不知何故,我突然想到自己幼時怎樣學古文的經驗來,說來瑣碎,在課堂上不便多講。但是本書編輯卻覺得饒有趣味,是她這一代的年輕人所沒有的經驗。於是在她鼓勵之下,寫下這點個人回憶。
其實我和大多數的華人一樣,古文都是在中學時期「被逼」學的。我的父母親學的是西方音樂,教育子女的方式也相當西化,放任自由,隨便我看什麼書,並且主動帶我和妹妹看好萊塢(荷里活)的電影。因此促成我對外文和外國文學的興趣。然而古文還是要讀的,在課堂上聽老師講,往往是照抄課本中的古文選篇,包括韓愈的〈師說〉,我聽來毫無興趣。然而卻想不到從電影片名學到了一點「古意」。
民國時期,西方的商業電影進入中國市場,好萊塢的八家大公司,在上海都設有辦事處,負責宣傳業務。那麼影片的名字找誰來譯?影片故事的說明書找誰來寫?據學者陳建華的研究,不少是來自「鴛鴦蝴蝶派」的文人(如周瘦鵑),他們也是最早介紹西片的專家。這些人皆有深厚的古文修養,讀過也寫過無數的舊小說,所以翻譯出來的外國電影片名都甚有古詩詞的意味,以便吸引觀眾和讀者。電影本來是一個通俗性的藝術,理應和俗文學相通。
這類的片名,四個字的居大多數,偶爾有五言和七言,特別是所謂「文藝片」。記得母親經常看兩部她摯愛的好萊塢名片:《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和《翠堤春曉》(The Great Waltz),後來在臺灣的一個小城新竹的一家影院裏我終於看到了。愛屋及烏,除了感到影片故事迴腸蕩氣之外,也覺得片名有點「文乎文乎」的。我一知半解,只覺得意境很美,用「翠」字來形容多瑙河堤,還加上「春曉」,這個典故是否來自我曾讀過的一句舊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然而「藍橋」的典故又出自何處?我不甚了了,但不自覺地對詩詞開始有點好奇了,讀的還是很少,不像其他人家子弟早已背誦了不少唐詩宋詞。回想這段個人經驗,令我深感懊悔,為什麼當年父母不逼我背誦古文?
幼年的經驗也使我變成一個大影迷,興趣至今不衰。妙的是:以前看過的無數部電影都忘了,唯獨有古文意味的片名至今記憶彌新。懷舊的意識流閘門一打開,這些片名一個接一個,緩緩流出。隨便舉幾個例子。
當年最轟動的影片無疑是《亂世佳人》,原名「Gone with the Wind」,傅東華的小說譯名只有一個字:「飄」。白話文,十分生動,比直譯「隨風而去」好多了;不知何人把影片片名譯作《亂世佳人》,出自古文,但切題之至,把故事的歷史背景(美國南北戰爭的「亂世」)和主角「郝思嘉」(Scarlett O’Hara)的身分點出來了,「佳人」處於兵荒馬亂的「亂世」恰是全片的主要情節。還有一部音樂片,譯名是《劍膽琴心》(原名The Magic Bow),看來像是武俠小說,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為故事說的是十九世紀小提琴怪傑 Paganini,他技巧神奇,運弓如劍。還有一部描寫小提琴家的音樂片,名叫「Intermezzo」,間奏曲,直譯毫無意義,但譯成《寒夜琴挑》,浪漫的意境就出來了。最近偶然在影碟中看到一個怪譯名《藍色情挑》,令我倒盡胃口,原來是波蘭導演奇里斯羅斯基的名片Blue,直譯成「藍色」又強加一個不倫不類的「情挑」字眼,白話配不上文言,如同強姦語言。
音樂老電影用「曲」為名的很多:《一曲情深》(With a Song in My Heart)、《一曲難忘》(A Song to Remember)、《曲終夢回》(Tales of Hoffman)是三個有名的例子,尤其是《曲終夢回》一名,是公開競爭的得獎之作,得主據聞是當年臺大歷史系的名教授沈剛伯先生。此片就是歌劇《赫夫曼故事》,主人翁和三個女人(其中一個竟然是木偶)熱戀,最後「曲終夢回」,無限感嘆。譯名既合題又典雅,我只有拍案叫絕。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歌舞片,我也看過無數。有時父母帶我和妹妹去看兩部Esther Williams主演的遊水歌舞片,一是《出水芙蓉》,一是《洛水神仙》,內容平平,片名也略帶俗氣,記得我曾問過母親:「這芙蓉是什麼意思?神仙為什麼是『洛水』而不是『落水』」?(現代觀眾更會問:何不幹脆叫「裸水」?)我當時還沒有讀過曹植的〈洛神賦〉。母親特別喜歡看文藝片,我至今只記得幾個片名:《璇宮艷史》、《獨留青冢向黃沙》,還有四十年代的國產片《一江春水向東流》,不但用李後主的一句詞作片名,而且在片頭以合唱把這首詞唱了出來。
幼時我最喜歡看的類型片是宮闈古裝片和武打片。不少片名也用古文,如轟動一時的《霸王妖姬》,片名顯然來自京劇《霸王別姬》,原來指的是楚霸王項羽和他的虞姬。這部西片指的卻是《聖經》中的人物Samson和Delilah(參孫和大利拉),但也甚適合。另外兩部我最喜歡的歷史片是:《劫後英雄傳》(Ivanhoe)和《美人如玉劍如虹》(Scaramouche),兩片的原名皆是人的名字,幼年的我當然搞不清楚,多年之後才知道前者出自林琴南的譯名:《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指的是英國的「原住民」撒克遜族(Anglo-Saxons),被來自歐陸的諾曼(Norman)貴族征服後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從電影中學到英國歷史。後者的背景是法國大革命,我看完數次之後(內中鬥劍場面特別精彩),片名七個字讀來鏗然有聲,「美人如玉」對仗「劍如虹」,比原名(一個小醜的名字)好聽多了,也令我難忘,但典故出自何處?可能又是武俠小說。
如果把這些片名和當今的此類影片的譯名對照的話,高下立見。最近偶然重看改編自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電影,西名當然一樣,但中文譯名一個是《愛比戀更冷》,一個是《貴族孽緣》,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前者故意把「戀愛」兩字拆開,片名既不哀怨又和托翁小說的原意相差太遠;後者更不知貴族式的典雅是何物,白白糟蹋了一部頗有新意的影片(2013年出品,劇本出自名家Tom Stoppard,導演是Joe Wright),難道托翁描寫的安娜的婚外情只不過是一段「孽緣」?然而本片最早的版本(1935年,嘉寶主演)的譯名倒甚為典雅,「春殘夢斷」,因為它是文言,後來的粵語片也沿用了這個片名。
這些片名所指涉的古文文類,當然是較為通俗的,多出自武俠小說或香艷小說,有時也引用詩詞歌賦,我幼年無知,無意中背了不少片名,多年後反思,才發現原來都有出處。最近因為授課,才發懷古之幽思,開始認真地看起古文詩詞來了,但為時已晚。我父親母親那一代人生於憂患,但古文底蘊猶存,時而不自覺地在說話和文字(即便是用白話寫的書信)中流露出來;這一代香港和大陸的年輕人生於安樂,沒有時間花功夫讀古文,也沒有古文感受了,一般用語白話加了不少俚語和英語,聽來似乎很流暢,但寫出來讀就不是味道。只有極少數的人還想學,因此向我求救,但我的古文涵養也很有限。我算是夾在兩代人中間,寫出來的中文文字每感力不從心,只求讀來順暢。近年來發現自己最難忍受的就是不中不西、似通非通的中文文體。還不如讀英文算了。我在堂上說過,也許現在讀古文的意義就在於此:讓我們回到自己母語的基本聲韻和節奏,再勤奮一點,或可追溯古文的美感和意境。看來太史公、韓愈和蘇東坡(這門課的三位古文大師)早已遙不可及。
從老電影的譯名學習古文
在第二講的討論環節,不少同學問我如何學古文。我完全沒有想到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且離題太遠,怎麼會從韓愈道統扯到如何學古文?不知何故,我突然想到自己幼時怎樣學古文的經驗來,說來瑣碎,在課堂上不便多講。但是本書編輯卻覺得饒有趣味,是她這一代的年輕人所沒有的經驗。於是在她鼓勵之下,寫下這點個人回憶。
其實我和大多數的華人一樣,古文都是在中學時期「被逼」學的。我的父母親學的是西方音樂,教育子女的方式也相當西化,放任自由,隨便我看什麼書,並且主動帶我和妹妹看好萊塢(荷里活)的電影。因此促成我對外文和外國文學的興趣。然而古文還是要讀的,在課堂上聽老師講,往往是照抄課本中的古文選篇,包括韓愈的〈師說〉,我聽來毫無興趣。然而卻想不到從電影片名學到了一點「古意」。
民國時期,西方的商業電影進入中國市場,好萊塢的八家大公司,在上海都設有辦事處,負責宣傳業務。那麼影片的名字找誰來譯?影片故事的說明書找誰來寫?據學者陳建華的研究,不少是來自「鴛鴦蝴蝶派」的文人(如周瘦鵑),他們也是最早介紹西片的專家。這些人皆有深厚的古文修養,讀過也寫過無數的舊小說,所以翻譯出來的外國電影片名都甚有古詩詞的意味,以便吸引觀眾和讀者。電影本來是一個通俗性的藝術,理應和俗文學相通。
這類的片名,四個字的居大多數,偶爾有五言和七言,特別是所謂「文藝片」。記得母親經常看兩部她摯愛的好萊塢名片:《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和《翠堤春曉》(The Great Waltz),後來在臺灣的一個小城新竹的一家影院裏我終於看到了。愛屋及烏,除了感到影片故事迴腸蕩氣之外,也覺得片名有點「文乎文乎」的。我一知半解,只覺得意境很美,用「翠」字來形容多瑙河堤,還加上「春曉」,這個典故是否來自我曾讀過的一句舊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然而「藍橋」的典故又出自何處?我不甚了了,但不自覺地對詩詞開始有點好奇了,讀的還是很少,不像其他人家子弟早已背誦了不少唐詩宋詞。回想這段個人經驗,令我深感懊悔,為什麼當年父母不逼我背誦古文?
幼年的經驗也使我變成一個大影迷,興趣至今不衰。妙的是:以前看過的無數部電影都忘了,唯獨有古文意味的片名至今記憶彌新。懷舊的意識流閘門一打開,這些片名一個接一個,緩緩流出。隨便舉幾個例子。
當年最轟動的影片無疑是《亂世佳人》,原名「Gone with the Wind」,傅東華的小說譯名只有一個字:「飄」。白話文,十分生動,比直譯「隨風而去」好多了;不知何人把影片片名譯作《亂世佳人》,出自古文,但切題之至,把故事的歷史背景(美國南北戰爭的「亂世」)和主角「郝思嘉」(Scarlett O’Hara)的身分點出來了,「佳人」處於兵荒馬亂的「亂世」恰是全片的主要情節。還有一部音樂片,譯名是《劍膽琴心》(原名The Magic Bow),看來像是武俠小說,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為故事說的是十九世紀小提琴怪傑 Paganini,他技巧神奇,運弓如劍。還有一部描寫小提琴家的音樂片,名叫「Intermezzo」,間奏曲,直譯毫無意義,但譯成《寒夜琴挑》,浪漫的意境就出來了。最近偶然在影碟中看到一個怪譯名《藍色情挑》,令我倒盡胃口,原來是波蘭導演奇里斯羅斯基的名片Blue,直譯成「藍色」又強加一個不倫不類的「情挑」字眼,白話配不上文言,如同強姦語言。
音樂老電影用「曲」為名的很多:《一曲情深》(With a Song in My Heart)、《一曲難忘》(A Song to Remember)、《曲終夢回》(Tales of Hoffman)是三個有名的例子,尤其是《曲終夢回》一名,是公開競爭的得獎之作,得主據聞是當年臺大歷史系的名教授沈剛伯先生。此片就是歌劇《赫夫曼故事》,主人翁和三個女人(其中一個竟然是木偶)熱戀,最後「曲終夢回」,無限感嘆。譯名既合題又典雅,我只有拍案叫絕。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歌舞片,我也看過無數。有時父母帶我和妹妹去看兩部Esther Williams主演的遊水歌舞片,一是《出水芙蓉》,一是《洛水神仙》,內容平平,片名也略帶俗氣,記得我曾問過母親:「這芙蓉是什麼意思?神仙為什麼是『洛水』而不是『落水』」?(現代觀眾更會問:何不幹脆叫「裸水」?)我當時還沒有讀過曹植的〈洛神賦〉。母親特別喜歡看文藝片,我至今只記得幾個片名:《璇宮艷史》、《獨留青冢向黃沙》,還有四十年代的國產片《一江春水向東流》,不但用李後主的一句詞作片名,而且在片頭以合唱把這首詞唱了出來。
幼時我最喜歡看的類型片是宮闈古裝片和武打片。不少片名也用古文,如轟動一時的《霸王妖姬》,片名顯然來自京劇《霸王別姬》,原來指的是楚霸王項羽和他的虞姬。這部西片指的卻是《聖經》中的人物Samson和Delilah(參孫和大利拉),但也甚適合。另外兩部我最喜歡的歷史片是:《劫後英雄傳》(Ivanhoe)和《美人如玉劍如虹》(Scaramouche),兩片的原名皆是人的名字,幼年的我當然搞不清楚,多年之後才知道前者出自林琴南的譯名:《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指的是英國的「原住民」撒克遜族(Anglo-Saxons),被來自歐陸的諾曼(Norman)貴族征服後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從電影中學到英國歷史。後者的背景是法國大革命,我看完數次之後(內中鬥劍場面特別精彩),片名七個字讀來鏗然有聲,「美人如玉」對仗「劍如虹」,比原名(一個小醜的名字)好聽多了,也令我難忘,但典故出自何處?可能又是武俠小說。
如果把這些片名和當今的此類影片的譯名對照的話,高下立見。最近偶然重看改編自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電影,西名當然一樣,但中文譯名一個是《愛比戀更冷》,一個是《貴族孽緣》,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前者故意把「戀愛」兩字拆開,片名既不哀怨又和托翁小說的原意相差太遠;後者更不知貴族式的典雅是何物,白白糟蹋了一部頗有新意的影片(2013年出品,劇本出自名家Tom Stoppard,導演是Joe Wright),難道托翁描寫的安娜的婚外情只不過是一段「孽緣」?然而本片最早的版本(1935年,嘉寶主演)的譯名倒甚為典雅,「春殘夢斷」,因為它是文言,後來的粵語片也沿用了這個片名。
這些片名所指涉的古文文類,當然是較為通俗的,多出自武俠小說或香艷小說,有時也引用詩詞歌賦,我幼年無知,無意中背了不少片名,多年後反思,才發現原來都有出處。最近因為授課,才發懷古之幽思,開始認真地看起古文詩詞來了,但為時已晚。我父親母親那一代人生於憂患,但古文底蘊猶存,時而不自覺地在說話和文字(即便是用白話寫的書信)中流露出來;這一代香港和大陸的年輕人生於安樂,沒有時間花功夫讀古文,也沒有古文感受了,一般用語白話加了不少俚語和英語,聽來似乎很流暢,但寫出來讀就不是味道。只有極少數的人還想學,因此向我求救,但我的古文涵養也很有限。我算是夾在兩代人中間,寫出來的中文文字每感力不從心,只求讀來順暢。近年來發現自己最難忍受的就是不中不西、似通非通的中文文體。還不如讀英文算了。我在堂上說過,也許現在讀古文的意義就在於此:讓我們回到自己母語的基本聲韻和節奏,再勤奮一點,或可追溯古文的美感和意境。看來太史公、韓愈和蘇東坡(這門課的三位古文大師)早已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