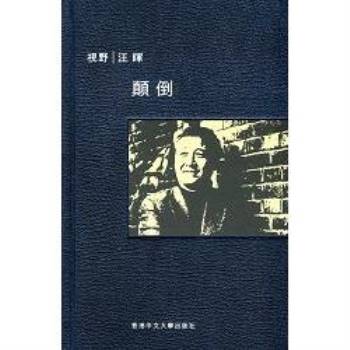金沙江之子
4月3日,清明前兩天,我轉道昆明、麗江,在朋友的安排下,乘了兩個多小時的汽車,直抵金沙江邊的車軸村──蕭亮中的家鄉,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的研究對象。村子在金沙江靠中甸的一側,在夜色之中,亮中的表哥李潤堂將小貨車開上了渡船,艄公靜靜地掉轉船頭,我們在月色、山影之中,渡過了金沙江。在一旁的小彭說:鄉親們為亮中立的碑就在江邊的山坡上。我舉目望去,夜氣繚繞之中,只有巨大的山影從上面壓下來。繞過這一截路,前面終於有了一些燈火,是車軸了。次日清晨,我沿着小路爬上亮中家屋後的小山坡去探望亮中──他的墳頭沒有任何標記,不遠處的金沙江邊立着的那塊刻着「金沙江之子」的碑上也沒有他的名字,但在江邊,你能夠感覺到他的無處不在。亮中在那裏繼續守望他的金沙江,他的確並沒有離開,幾個月來壓在我心頭的石頭漸漸地挪開,我可以回憶了。
認識亮中,是因為《讀書》,現在回憶,時間應該是在2001年底或2002年初。從《讀書》的來稿中,我讀到一篇題為〈隱喻的漫水灣〉的文章,是對四川冕寧縣南部的漫水灣的彝族村莊生活的樸實而生動的記述。一望而知,作者是一個人類學者,平靜的敍述與作者的追問相互交織;滲透字裏行間的,是對漫水灣的人、風俗、土地的真正的親切感,尤其是對彝族文化轉換及其與漢族社會之間的關係的認真思考。在文章的結尾部分,他分明地說,這個地區的彝族認同並不是植根於某種「共同的文化」,因為這裏的群體生活特徵與其他群體(漢族或其他族群)沒有多大的區別。構成這種認同的毋寧是某種隱喻性的文化特徵,然而也恰恰是這種隱喻性的文化特徵在具體的環境中會被放大或縮小,成為這一族群與其他民族不一樣、相區別的關鍵所在。我很喜歡也認同這種將少數民族認同置於多族群共存的語境中的研究方法。這篇文章隨即被編入2002年第三期的「田野札記」欄目之中,按《讀書》的發稿速度,這算是最快的了。那之後沒有幾天,雜誌發稿工作完成之後,我從編輯部來到二樓書店的咖啡館,在入口處,見《讀書》的同事李學軍正在和一個年輕人說話,她介紹說,這就是蕭亮中,〈隱喻的漫水灣〉的作者。我隨即向亮中表示感謝,並告訴他文章已經發稿。亮中中等身材,方形的臉龐,顯得很忠厚,說話也謙和。聽說文章已經發稿,他顯然略感驚訝,也很高興。我們要了咖啡,坐在那裏隨意地聊了起來,討論的問題多半與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及其歷史命運有關。他說起了雲南少數民族,也說起藏族的歷史。我那時也在讀一些有關的歷史資料,交談之中,我們好像有不少共同的想法。在那之後,我們見面的次數不算多,每次都是在三聯書店二樓的咖啡館裏,多半是他給《讀書》寫了新的文章或參加《讀書》的活動。有一次,在交給我新作〈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誌〉的同時,他還附了一篇題為《突古》的小說。文章發表於去年《讀書》的第三期,而小說卻留在電腦裏了,我粗粗地瀏覽了一下,覺得文筆很細膩,但因為手頭太多的事情需要處理未及細讀就放下了。亮中為人憨厚,但極為敏感,因為沒有得到我關於他的小說的意見,再見到我時,他帶着失落的神情問:您還沒有讀我的小說吧?我搪塞了一下,他沒有追問,但重新打印一份,專門給我送來──從此我知道,亮中的心裏永遠記着曾經發生的事情,他不會遺忘,也不會放過,雖然他的臉上總是帶着謙和的笑意。我也因此知道:為什麼亮中的笑意中總是帶着審視!
2002年秋天,我在國外做訪問研究,忽然接到亮中的一封信。這次並不是投稿,而是朋友式的關心。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和亮中的交往中超出編輯和作者關係的開始。他在一個場合聽到有人用極深的惡意攻擊我,攻擊者並不認識我,而且所說也毫無根據。亮中先是不解,而後是憤怒。他在提醒我多留心之後,又問:為什麼不反擊?亮中太年輕了,他對知識界的爭論不是很清楚,對有些所謂「知識分子」之作為還缺乏真切的體驗。我感謝亮中的慰問,但沒有多說什麼。回到北京後,有一次見到他,他又重提此事,我仍然沒有多說。在這個世界裏,人心的黑暗是永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的,為什麼要讓一個如此坦然、天真的人平添對於這個世界的悲觀呢?對我而言,有像亮中這樣的朋友的誠摯的關心已經足夠了。亮中從此不再提及這些事情,但我知道他曾經為此與他熟悉的人辯論。從認識亮中起,我就知道他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放不下,不大安於商務印書館的工作。幾經周折,據說可以進社科院社會學所了,卻在最後一刻出局。亮中為此來找過我,心裏有許多不平和不解;我為此四處打電話瞭解情況,最終也無能為力。去年春天的時候,他告訴我有兩個可能:一是進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一是進藏學研究中心;前一個手續比較複雜,後一個相對比較確定。鑒於前一次教訓,我建議他先進藏學中心。他是猶豫的。去年夏天之後,亮中在工作調動過程中捲入反對虎跳峽水壩的運動,他自己有些擔心這些事情會影響他的工作,見面或打電話都說起此事;我知道他為調動做了多少努力,心裏又有多少渴望,也擔心他捲入的運動影響調動的事情。但亮中有一次態度堅定地告訴我說,他不會因為調動的事情而放下金沙江的命運而不管,那一次,他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心裏是很興奮的。
亮中捲入反對虎跳峽水壩的事情始於去年春天。受藏族學者馬建忠之請,亮中參與籌備在中甸召開的「藏族傳統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學術討論會;他記起了我們初次見面時的討論,於是問我能否參加那個會議。我對藏族文化和生態多樣性問題感興趣,卻沒有任何研究,不敢貿然答應,但亮中說:會議的議題涉及發展主義等問題,還是希望我參加。他是在為自己的家鄉爭取更多的關心,我拗不過他。5月間,亮中說要來送會議邀請信,我說不用跑了,寄來就可以,但他不從。當天,我們約好了一起吃午飯,但大約兩點鐘他才滿頭大汗地趕到我的住處,那時我已經饑腸轆轆。他一邊擦汗,一邊解釋說商務印書館開編輯會議,無法提前離開。北京的交通情況我當然知道,何況亮中是乘公共汽車來的呢!我們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裏喝了點酒,隨意地聊起了中甸,那時在我對雲南的神往中還從未有過虎跳峽問題的影子。
6月9日,我收拾行裝,奔赴中甸。在昆明機場的候機大廳,瞥見了亮中的身影,隨他一同前來的還有年輕的體恒(印照)法師。體恒(印照)法師一襲袈裟,而亮中卻是短袖輕裝,他們剛剛拜訪了昆明的一座寺院,隨身還攜帶着寺院住持贈送的禮品。在候機廳裏聊天時,我買了雲南地圖,不斷地向亮中打問雲南的情形,計劃着未來的行程。飛抵中甸後,我們都穿上了夾克,而亮中卻依舊短衣裝,回到家鄉的興奮一直掛在臉上。臨行之前,一個朋友特別來電話關照我注意高原反應,下飛機後一切正常,我有點慶幸,亮中卻在一旁笑我:怎麼會有高原反應呢!在旅館住下後,亮中帶我到一個很小的飯店,我們要了一點飯菜,坐在小板凳上喝起了青稞酒。亮中是在中甸念的中學,這個地方藏族人最多,但也聚居着納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回族、普米族和漢族等不同民族的居民。他自己是白族人,而會議的組織者、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的馬建忠卻是藏族人,他們在不同的中學讀書,畢業後同年考到北京來讀大學。亮中考取的是中央民族大學,而建忠先入北京林業大學而後去泰國留學,各奔前途,現在卻為他們共同的家鄉重新走到一起了。談話之間,亮中提出邀請,要我在會議結束後去他的家中小住。酒酣耳熱之際,我答應了──我原以為這是亮中一時興起的建議,後來才明白他早就在為此做計劃了,但在來中甸之前,他從沒有對我提起過。
我參加過許多學術討論會,但那次會議卻很特別。頭一天的會議在旅館召開,發言者除了從北京和昆明等地來的專家之外,大多是當地的學者,其中許多是藏族的學人。降邊嘉措先生是我在社會科學院的同事,他在少數民族文學所,我在文學所,僅僅一層之隔,卻從未謀面。這次在雲南見到了。澤仁鄧珠先生是著名的藏學家,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百萬字的《藏族通史》,在藏人中享有很高威信。從青海來的活佛一臉慈祥,很少說話,但我們後來一路去德欽,他的博學讓我深為佩服。雲南社會科學院的幾位學者對當地風俗、宗教、自然狀況進行了長期的觀察,他們的論文對於中甸、德欽、麗江等地的生態狀況做了詳細研究。不止一位學者談到了藏傳佛教對自然聖境的崇拜,認為這一崇拜對於生態的保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天上午,我們驅車參加當地藏學中心的成立典禮,而後前往其茨頂村進行小組討論,亮中從一個小組換到另一個小組,終於到我所在的小組來了。他坐在我身邊。討論過程中,亮中忽然發難:現在NGO(非政府組織)紛紛來到這裏,但投資和活動都集中在藏區,難道其他民族文化就不包含保護自然的傳統嗎?我們從小在這裏長大,不同族群相處融洽,不但是同學、同事,而且也是親人,因為不同族群之間通婚和日常的交流是很普遍的。但隨着外來的投資都流向藏區,所有的宣傳也都集中在藏族文化,多少個世紀和諧相處的不同族群之間產生了相互間的芥蒂和「分」的趨勢。這不是個問題嗎?
亮中在此之前已經與我談過這個問題,我因為不瞭解情況不敢貿然發表意見;但在與馬建忠的聊天中,我特別就此問了他的意見。建忠是藏族人,又在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工作,他坦承這個問題的確存在,但感到一時很難改變。他稱讚亮中的文章寫得好,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我沒有想到他寫了這麼好的文章!建忠和亮中像兄弟一樣,偶爾爭吵,但情感深厚,8月間建忠從美國給我寫信催問答應他的文章,還特別提到亮中和大夥兒對虎跳峽水壩問題的鬥爭「有聲有色」。亮中提及的問題是尖銳的,我認為他有一種真正的人類學的視野,而不是單純地從環保出發;他並不是不支持NGO的工作,而是關注NGO能否真正將文化多樣性與生態多樣性的視野貫徹到各種項目之中。很顯然,在亮中的心目中,生物的多樣性是和文化的多樣性密切相關的,任何將一個社區簡單地按照族群、宗教來進行區分的做法,都可能瓦解社區自身的文化多樣性及其有機的聯繫,產生新的不平等。在這個意義上,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又與平等問題有着內在的聯繫。亮中對他的家鄉的關注不是從一個族群或一種文化出發的,而是從一個歷史地聯繫在一起的社群網絡及其多樣性出發的。在雲南期間和從那裏回來之後,我們曾經反復地討論過雲南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及其意義。後來在起草有關反對長江第一灣──虎跳峽流域水電工程的倡議書時,這也成為他的最重要的出發點之一。
在中甸的那幾天,亮中忙前忙後,除了招待我們品嘗當地菜餚之外,還特別帶幾個當地的朋友到我的房間來聊天。亮中是一個較真的人,他想到的事情,往往不顧及場合就要說出來。那天在其茨頂村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討論,在交鋒之後,亮中仍不罷休。他對當地將其茨頂村設計成為一個藏族文化樣板村也很有意見,在這些問題上,我完全贊成他的看法,雖然囿於客人的身份,沒有多說,但在最後的發言中還是呼應了亮中,對於過度的旅遊開發和市場擴張表示擔憂。在與亮中及他的朋友的聊天之中,我們最為關心的是:究竟是靠了怎樣的歷史傳統、文化條件和社會政策,雲南能夠保持如此燦爛多姿的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各民族為什麼能夠和諧共存而又各自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當代世界的變化──市場化、全球化、現代化──是否可能促成這樣的局面的轉化?亮中對於自己的家鄉和族群有強烈的認同感,但同時擁有同樣強烈的「中國」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也表達為對任何等級關係和習焉不察的偏見的批判態度。在他的身上,多重的認同本身構成了一種思想的和性格的特徵,有時你似乎感到他正處於某種矛盾的情感和態度之中,但最終這些所謂的矛盾在他的身上是完全統一的。有一天,在我的房間裏說到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及其危機的問題,他帶來的一位藏族朋友說:我們說藏語或納西語,但也說普通話,它們都是我們的語言。為什麼現在不叫普通話而叫漢語呢?我有時想:真該讓那些學了一大堆正確理論的人來聽聽一個少數民族的朋友是怎樣看待普通話的。亮中對於NGO興起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的追問也值得所有參與這個運動的人關注,他們的意義也許會在未來的發展中成為影響深遠的問題。
4月3日,清明前兩天,我轉道昆明、麗江,在朋友的安排下,乘了兩個多小時的汽車,直抵金沙江邊的車軸村──蕭亮中的家鄉,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的研究對象。村子在金沙江靠中甸的一側,在夜色之中,亮中的表哥李潤堂將小貨車開上了渡船,艄公靜靜地掉轉船頭,我們在月色、山影之中,渡過了金沙江。在一旁的小彭說:鄉親們為亮中立的碑就在江邊的山坡上。我舉目望去,夜氣繚繞之中,只有巨大的山影從上面壓下來。繞過這一截路,前面終於有了一些燈火,是車軸了。次日清晨,我沿着小路爬上亮中家屋後的小山坡去探望亮中──他的墳頭沒有任何標記,不遠處的金沙江邊立着的那塊刻着「金沙江之子」的碑上也沒有他的名字,但在江邊,你能夠感覺到他的無處不在。亮中在那裏繼續守望他的金沙江,他的確並沒有離開,幾個月來壓在我心頭的石頭漸漸地挪開,我可以回憶了。
認識亮中,是因為《讀書》,現在回憶,時間應該是在2001年底或2002年初。從《讀書》的來稿中,我讀到一篇題為〈隱喻的漫水灣〉的文章,是對四川冕寧縣南部的漫水灣的彝族村莊生活的樸實而生動的記述。一望而知,作者是一個人類學者,平靜的敍述與作者的追問相互交織;滲透字裏行間的,是對漫水灣的人、風俗、土地的真正的親切感,尤其是對彝族文化轉換及其與漢族社會之間的關係的認真思考。在文章的結尾部分,他分明地說,這個地區的彝族認同並不是植根於某種「共同的文化」,因為這裏的群體生活特徵與其他群體(漢族或其他族群)沒有多大的區別。構成這種認同的毋寧是某種隱喻性的文化特徵,然而也恰恰是這種隱喻性的文化特徵在具體的環境中會被放大或縮小,成為這一族群與其他民族不一樣、相區別的關鍵所在。我很喜歡也認同這種將少數民族認同置於多族群共存的語境中的研究方法。這篇文章隨即被編入2002年第三期的「田野札記」欄目之中,按《讀書》的發稿速度,這算是最快的了。那之後沒有幾天,雜誌發稿工作完成之後,我從編輯部來到二樓書店的咖啡館,在入口處,見《讀書》的同事李學軍正在和一個年輕人說話,她介紹說,這就是蕭亮中,〈隱喻的漫水灣〉的作者。我隨即向亮中表示感謝,並告訴他文章已經發稿。亮中中等身材,方形的臉龐,顯得很忠厚,說話也謙和。聽說文章已經發稿,他顯然略感驚訝,也很高興。我們要了咖啡,坐在那裏隨意地聊了起來,討論的問題多半與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及其歷史命運有關。他說起了雲南少數民族,也說起藏族的歷史。我那時也在讀一些有關的歷史資料,交談之中,我們好像有不少共同的想法。在那之後,我們見面的次數不算多,每次都是在三聯書店二樓的咖啡館裏,多半是他給《讀書》寫了新的文章或參加《讀書》的活動。有一次,在交給我新作〈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誌〉的同時,他還附了一篇題為《突古》的小說。文章發表於去年《讀書》的第三期,而小說卻留在電腦裏了,我粗粗地瀏覽了一下,覺得文筆很細膩,但因為手頭太多的事情需要處理未及細讀就放下了。亮中為人憨厚,但極為敏感,因為沒有得到我關於他的小說的意見,再見到我時,他帶着失落的神情問:您還沒有讀我的小說吧?我搪塞了一下,他沒有追問,但重新打印一份,專門給我送來──從此我知道,亮中的心裏永遠記着曾經發生的事情,他不會遺忘,也不會放過,雖然他的臉上總是帶着謙和的笑意。我也因此知道:為什麼亮中的笑意中總是帶着審視!
2002年秋天,我在國外做訪問研究,忽然接到亮中的一封信。這次並不是投稿,而是朋友式的關心。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和亮中的交往中超出編輯和作者關係的開始。他在一個場合聽到有人用極深的惡意攻擊我,攻擊者並不認識我,而且所說也毫無根據。亮中先是不解,而後是憤怒。他在提醒我多留心之後,又問:為什麼不反擊?亮中太年輕了,他對知識界的爭論不是很清楚,對有些所謂「知識分子」之作為還缺乏真切的體驗。我感謝亮中的慰問,但沒有多說什麼。回到北京後,有一次見到他,他又重提此事,我仍然沒有多說。在這個世界裏,人心的黑暗是永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的,為什麼要讓一個如此坦然、天真的人平添對於這個世界的悲觀呢?對我而言,有像亮中這樣的朋友的誠摯的關心已經足夠了。亮中從此不再提及這些事情,但我知道他曾經為此與他熟悉的人辯論。從認識亮中起,我就知道他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放不下,不大安於商務印書館的工作。幾經周折,據說可以進社科院社會學所了,卻在最後一刻出局。亮中為此來找過我,心裏有許多不平和不解;我為此四處打電話瞭解情況,最終也無能為力。去年春天的時候,他告訴我有兩個可能:一是進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一是進藏學研究中心;前一個手續比較複雜,後一個相對比較確定。鑒於前一次教訓,我建議他先進藏學中心。他是猶豫的。去年夏天之後,亮中在工作調動過程中捲入反對虎跳峽水壩的運動,他自己有些擔心這些事情會影響他的工作,見面或打電話都說起此事;我知道他為調動做了多少努力,心裏又有多少渴望,也擔心他捲入的運動影響調動的事情。但亮中有一次態度堅定地告訴我說,他不會因為調動的事情而放下金沙江的命運而不管,那一次,他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心裏是很興奮的。
亮中捲入反對虎跳峽水壩的事情始於去年春天。受藏族學者馬建忠之請,亮中參與籌備在中甸召開的「藏族傳統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學術討論會;他記起了我們初次見面時的討論,於是問我能否參加那個會議。我對藏族文化和生態多樣性問題感興趣,卻沒有任何研究,不敢貿然答應,但亮中說:會議的議題涉及發展主義等問題,還是希望我參加。他是在為自己的家鄉爭取更多的關心,我拗不過他。5月間,亮中說要來送會議邀請信,我說不用跑了,寄來就可以,但他不從。當天,我們約好了一起吃午飯,但大約兩點鐘他才滿頭大汗地趕到我的住處,那時我已經饑腸轆轆。他一邊擦汗,一邊解釋說商務印書館開編輯會議,無法提前離開。北京的交通情況我當然知道,何況亮中是乘公共汽車來的呢!我們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裏喝了點酒,隨意地聊起了中甸,那時在我對雲南的神往中還從未有過虎跳峽問題的影子。
6月9日,我收拾行裝,奔赴中甸。在昆明機場的候機大廳,瞥見了亮中的身影,隨他一同前來的還有年輕的體恒(印照)法師。體恒(印照)法師一襲袈裟,而亮中卻是短袖輕裝,他們剛剛拜訪了昆明的一座寺院,隨身還攜帶着寺院住持贈送的禮品。在候機廳裏聊天時,我買了雲南地圖,不斷地向亮中打問雲南的情形,計劃着未來的行程。飛抵中甸後,我們都穿上了夾克,而亮中卻依舊短衣裝,回到家鄉的興奮一直掛在臉上。臨行之前,一個朋友特別來電話關照我注意高原反應,下飛機後一切正常,我有點慶幸,亮中卻在一旁笑我:怎麼會有高原反應呢!在旅館住下後,亮中帶我到一個很小的飯店,我們要了一點飯菜,坐在小板凳上喝起了青稞酒。亮中是在中甸念的中學,這個地方藏族人最多,但也聚居着納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回族、普米族和漢族等不同民族的居民。他自己是白族人,而會議的組織者、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的馬建忠卻是藏族人,他們在不同的中學讀書,畢業後同年考到北京來讀大學。亮中考取的是中央民族大學,而建忠先入北京林業大學而後去泰國留學,各奔前途,現在卻為他們共同的家鄉重新走到一起了。談話之間,亮中提出邀請,要我在會議結束後去他的家中小住。酒酣耳熱之際,我答應了──我原以為這是亮中一時興起的建議,後來才明白他早就在為此做計劃了,但在來中甸之前,他從沒有對我提起過。
我參加過許多學術討論會,但那次會議卻很特別。頭一天的會議在旅館召開,發言者除了從北京和昆明等地來的專家之外,大多是當地的學者,其中許多是藏族的學人。降邊嘉措先生是我在社會科學院的同事,他在少數民族文學所,我在文學所,僅僅一層之隔,卻從未謀面。這次在雲南見到了。澤仁鄧珠先生是著名的藏學家,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百萬字的《藏族通史》,在藏人中享有很高威信。從青海來的活佛一臉慈祥,很少說話,但我們後來一路去德欽,他的博學讓我深為佩服。雲南社會科學院的幾位學者對當地風俗、宗教、自然狀況進行了長期的觀察,他們的論文對於中甸、德欽、麗江等地的生態狀況做了詳細研究。不止一位學者談到了藏傳佛教對自然聖境的崇拜,認為這一崇拜對於生態的保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天上午,我們驅車參加當地藏學中心的成立典禮,而後前往其茨頂村進行小組討論,亮中從一個小組換到另一個小組,終於到我所在的小組來了。他坐在我身邊。討論過程中,亮中忽然發難:現在NGO(非政府組織)紛紛來到這裏,但投資和活動都集中在藏區,難道其他民族文化就不包含保護自然的傳統嗎?我們從小在這裏長大,不同族群相處融洽,不但是同學、同事,而且也是親人,因為不同族群之間通婚和日常的交流是很普遍的。但隨着外來的投資都流向藏區,所有的宣傳也都集中在藏族文化,多少個世紀和諧相處的不同族群之間產生了相互間的芥蒂和「分」的趨勢。這不是個問題嗎?
亮中在此之前已經與我談過這個問題,我因為不瞭解情況不敢貿然發表意見;但在與馬建忠的聊天中,我特別就此問了他的意見。建忠是藏族人,又在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工作,他坦承這個問題的確存在,但感到一時很難改變。他稱讚亮中的文章寫得好,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我沒有想到他寫了這麼好的文章!建忠和亮中像兄弟一樣,偶爾爭吵,但情感深厚,8月間建忠從美國給我寫信催問答應他的文章,還特別提到亮中和大夥兒對虎跳峽水壩問題的鬥爭「有聲有色」。亮中提及的問題是尖銳的,我認為他有一種真正的人類學的視野,而不是單純地從環保出發;他並不是不支持NGO的工作,而是關注NGO能否真正將文化多樣性與生態多樣性的視野貫徹到各種項目之中。很顯然,在亮中的心目中,生物的多樣性是和文化的多樣性密切相關的,任何將一個社區簡單地按照族群、宗教來進行區分的做法,都可能瓦解社區自身的文化多樣性及其有機的聯繫,產生新的不平等。在這個意義上,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又與平等問題有着內在的聯繫。亮中對他的家鄉的關注不是從一個族群或一種文化出發的,而是從一個歷史地聯繫在一起的社群網絡及其多樣性出發的。在雲南期間和從那裏回來之後,我們曾經反復地討論過雲南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及其意義。後來在起草有關反對長江第一灣──虎跳峽流域水電工程的倡議書時,這也成為他的最重要的出發點之一。
在中甸的那幾天,亮中忙前忙後,除了招待我們品嘗當地菜餚之外,還特別帶幾個當地的朋友到我的房間來聊天。亮中是一個較真的人,他想到的事情,往往不顧及場合就要說出來。那天在其茨頂村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討論,在交鋒之後,亮中仍不罷休。他對當地將其茨頂村設計成為一個藏族文化樣板村也很有意見,在這些問題上,我完全贊成他的看法,雖然囿於客人的身份,沒有多說,但在最後的發言中還是呼應了亮中,對於過度的旅遊開發和市場擴張表示擔憂。在與亮中及他的朋友的聊天之中,我們最為關心的是:究竟是靠了怎樣的歷史傳統、文化條件和社會政策,雲南能夠保持如此燦爛多姿的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各民族為什麼能夠和諧共存而又各自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當代世界的變化──市場化、全球化、現代化──是否可能促成這樣的局面的轉化?亮中對於自己的家鄉和族群有強烈的認同感,但同時擁有同樣強烈的「中國」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也表達為對任何等級關係和習焉不察的偏見的批判態度。在他的身上,多重的認同本身構成了一種思想的和性格的特徵,有時你似乎感到他正處於某種矛盾的情感和態度之中,但最終這些所謂的矛盾在他的身上是完全統一的。有一天,在我的房間裏說到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及其危機的問題,他帶來的一位藏族朋友說:我們說藏語或納西語,但也說普通話,它們都是我們的語言。為什麼現在不叫普通話而叫漢語呢?我有時想:真該讓那些學了一大堆正確理論的人來聽聽一個少數民族的朋友是怎樣看待普通話的。亮中對於NGO興起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的追問也值得所有參與這個運動的人關注,他們的意義也許會在未來的發展中成為影響深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