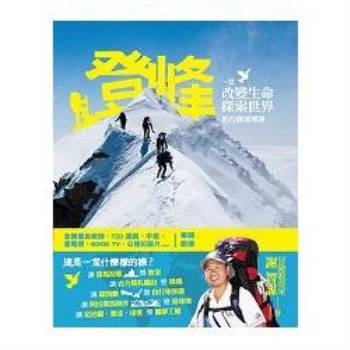金魚缸裡養不出鯨魚
師大畢業到國中實習的那一年,我被派去帶領放牛班。可以想像在師大學的「愛的教育」那一套,在這裡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屢勸不聽的學生,我只好用拳頭收服,面對從街頭出身,「實戰」經驗豐富的我,沒有學生能打得過。在暴力威脅之下,他們變得聽話,即便我非常不願意用暴力對待學生,卻也找不到其他辦法。時常學生做完掃除工作跑來問我:「老師,我們可不可以抽根菸?」「別讓我看到就可以。」我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時,覺得自己被困在一個地方,沒有出路,心情極度鬱悶,所以寫了一句話:「屬於大海的動物,需要大一點的空間。」來勉勵自己走出陰霾。沒想到,這句話,竟成為我後半生教學生涯的寫照。
老師的世界有多大,學生的夢想就會有多大
一直以來,我深信如果父母把孩子關在室內教育,他的世界就只有房間那麼大,就算再有錢,頂多也是幾百坪;一個老師的世界倘若只有教室或研究室那麼大,他教出來的學生也不過那樣大的視野。
有些時候,教室如同圍牆一樣,把我們上課內容與時間關起來,學生的創意被上了鎖,夢想的翅膀也被綁住,考試只是像機械化的勞動,把學生的精力消磨掉。圍牆外面,有許多有意義的學習,雖然考試不考,卻是人生樂趣所在。但牆外的東西往往讓我們感到陌生,因為我們被關在牆內長達十二年,甚至更久。常有學生在離開學校後,從此不想學習,因為學習帶給他們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經驗。
我一直努力突破教室的圍牆,把學生帶到戶外,帶入生活,帶向世界。二0一一年的暑假,兩位男同學去攀登布羅德峰,海拔八0五一公尺;五位畢業生帶著十二個藥物濫用的孩子,進行二十一天荒野治療課程;四位畢業生,帶領台大為期十天的冒險領導課程;一位男同學,為急難家庭募款而環島義走;兩位女同學,前往新疆旅行並蒐集夢想與希望;一位女同學在美國流浪四個月;一位聽障男同學去獨攀南湖大山;一位老師帶著十多個學生騎車環島;一位老師帶著八個學生去尼泊爾爬山,並為當地募款蓋社區儲水槽、舉辦夏令營。
這些――都是我的學生,他們見證了學習是寬廣無限的,只要激發他們學習的樂趣,認同學習的意義,他們會願意花三倍的時間來投入學習。
金魚缸裡養不出鯨魚。如果把孩子放在金魚缸裡,層層保護,仔細照料他們,可以養出有禮貌、很漂亮的金魚,但這樣的孩子可能是脆弱的,不敢面對挑戰,甚至膚淺的以為,幾株水草,就是全世界。我們應該教出大器的孩子,讓他們在大海裡學習,陪他們對話與思辯,豐富的閱讀,鼓勵獨立思考,目睹他們生命卓越的蛻變。我想看見他們變成大鯨魚,充滿自信地在世界遨遊,只有如大海般,寬廣無限的空間,才裝得下孩子無限的可能。所以,不要怕孩子冒險,帶他們離開金魚缸,進入大海裡吧。
登頂不是課程目標
我剛回國任教時,在美國學的專業完全派不上用場,因為學校教的是一些運動社會學、行銷學與休閒經營等科目。後來有機會才在實務課程中,把以前所學的戶外及平面遊戲帶進課程裡。那時不僅沒有活動器材,連戶外的器材都要向南港國中童軍團借。就這樣開始,一群人慢慢跨到戶外。後來又開了一門課——單車跨北橫,接著加入溯溪、登山、划獨木舟、建造竹筏、建繩索場,也開始接營隊及活動,舉辦冒險治療課程和治療性營隊,帶領學生去幫助中輟生、受家暴性侵的孩子、殘疾人士,以及社會各個弱勢階層。
為了讓學生擁有國際視野,所以我開了海外登山領導課程,先後進行美國國王峽谷冒險計畫、阿拉斯加遠拓獨木舟學習計畫,後來在帶領學生喜馬拉雅登山計畫的同時,也開始嘗試將服務學習放在領導力課程內,讓學生為尼泊爾蓋教室募款、和壢新醫院合作義診。之後,與好朋友成立外展教育學校(OBT),在大家的協助下,成立亞洲體驗教育學會。二00七年,除了戶外體驗教育之外,我增加了服務體驗教育,引導學生們進行各種服務計畫,包括關心全球暖化議題、幫流浪狗結紮、陪讀計畫、募書與閱讀計畫、推動無痕山林等,學生的足跡踏遍台灣各鄉各鎮,以及尼泊爾、甘肅、四川、希臘各地。
團隊合作的學習模式
回首這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一直在思索,要教出什麼樣的孩子。我沒有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模式教學,只是用心貼近學生的生命,去聽他內心深處的故事,挖掘被輕忽的能力。根據學生的需要,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
我帶領一群沒有戶外經驗的學生,經過一學期的準備及訓練,攀登喜馬拉雅山。在過程中,他們一起開會討論,學習登山技巧、訓練體能、打電話募款(學習被拒絕)、主動尋找師資(學習尋求協助與資源)、打包(學會取捨)、與家人溝通、學會風險控管、解決團隊衝突、情境演練(在重要時刻如何做決策)等。登頂不是我的課程目標。重要的是,他們在「團隊合作」模式下學習,有別於傳統競爭學習模式。
過去傳統教育總是教我們要打敗別人,學習就像賽跑,第一名只有一位,只要往前衝,不需要等待,所有人都是敵人。在這種競爭模式下成長,容易養成自私的孩子,不懂團隊合作,也沒有耐心。同事如果跟不上他的速度,就會開始抱怨,認為別人拖慢團隊速度,妨礙他的事業往上爬。這樣的心態,只會讓他失去快樂,失去人對他的敬重。
而在團隊合作模式下學習,我們的目標不是比誰第一個登頂,而是全部隊員要一起登頂。在過程中,速度快的要等慢的,經驗豐富的要等沒經驗的。爬山的時候,他們親密的相處在一起,真誠地關心伙伴的身體狀況,彼此扶持。如果有隊員必須下撤,大家會抱在一起哭泣,捨不得分開。他們眼中不再只有自己,而是會發自內心去關懷人。
在這些冒險挑戰中,學生和我的生命不斷被更新與擴張,我們對生命有新的闡述和認識。雖然說不清楚學生到底學到了什麼,但我確信他們學到的,遠比我想像得更多。
這堂課喚起學生對生命的熱情、對能力的想像,如果一群沒有經驗的人,透過學習可以攀上喜馬拉雅山,還有什麼能阻止他們登上生命的高峰呢?還有什麼能限制他們的夢想呢?
瘋狂期末考
當我成為基督徒後,本來立志要當牧師,但是上帝並沒有開啟這條路,反而帶領我進入國立體育大學教書。也許祂認為我可以把老師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一直希望能教出具有僕人氣息與領袖特質的學生。顯然,這不是用紙筆測驗就能測得出來。
我對研究生出的期末考題,是請他們分組做專題,接著說明評分標準:一、要對社會有幫助;二、要對團隊有挑戰性;三、要有永續性。
根據這三個規則評分,學期中不考試。
若學生無法達成這三項規則,這門課稱不上領導學。我認為在教室裡的學習,不能成為唯一,必須透過實踐、反思,發展自我認同與利他服務,才能使學習內化,彰顯學習的意義與價值。培訓領導力,不是以口頭的方式授課,要學生背誦教科書,最後寫一篇報告,就能夠學會。
你可以想像,這對在傳統紙筆測驗中長大的學生來說,是多大的挑戰。但如果問我,這些年教學最大的感想是什麼,我會回答:永遠都要相信你的學生做得到。老師深信學生做得到,用這樣的信念教學,學生會感受到你對他們的信心,更會激發他們的能力。事實上,他們做得遠比我想像得更好。
在課堂上,我會先分享自己做過什麼,或以前的學長姐做過什麼,有時會邀請一些成功的典範來分享。
有一次,我分享和學生帶領盲人去登山和攀岩。如果盲人可以爬山,還有誰不能爬山。我跟學生說,我曾在喜馬拉雅山上,看見當地七歲的孩子在那裡跑上跑下,根本不當作爬山。他們跟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心臟沒有比較大顆,要相信上帝創造人類的潛能。你現在做不到,並不代表未來無法做到。
然後我雙眼直盯著他們,口氣堅決地說:「你們可以做得更好。」真的,學生們相信了。他們帶領國中生參與社區關懷探訪;有一組募了幾百本書給偏遠國小,並協助整理圖書室;有一組帶四位特殊兒童去爬雪山,帶著小朋友在山上撿垃圾;有人替學校募電腦,替弱勢兒童募集鞋子;有人帶領癌症病人攀岩,結果攀完岩,病人告訴他們還想要去潛水。
有一組學生在西門町放一座巨型監牢,一名學生在裡面讀書,鐵窗外貼著「爸媽!我不要坐牢」的大海報,象徵教育被綁架了十二年。透過街頭的即興表演,傳達「做中學」及「服務學習」的教育理念。
學生們運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心。每一屆學生的經驗會激發下一屆學生的創意,沒有一年的期末考是一樣的。他們付出生命,並影響生命,匯集成巨大的力量。
我聽著期末考報告,學生在過程中成長,從服務對象得到回饋,體認到學習的價值。看見學生生命的轉化,心裡十分感動,眼眶也忍不住泛淚。我的學生真的很棒。
比登頂更重要的事
登山是一件非常耗費體力的活動,尤其是高海拔登山。因為體力與缺氧的緣故,更容易經歷到平地無法經驗的累。到了體力耗盡的臨界點,開始就是一連串的自我對話與自我掙扎。選擇放棄常會是第一個跑出來的念頭,然而接著出來的是更多的自我激勵、自我支持的往前力量。這兩者會在交織過程中彼此衝突,腳步在停停走走之間繼續邁進。如果不小心跌了一跤,放棄的念頭就會像落石一樣,狠狠砸在你頭上,你會望著山頂,停在那裡忍著哭的衝動,想放棄。
在爬喜馬拉雅山那年,我有個學生當時已經快五十歲了,比我年紀還大上幾歲。在登山四千公尺之後,他走路的速度,以及身體各項指數都不是很理想。我一直關心著他的身體狀況,猜想他應該無法登頂。沒想到他最後穿上冰爪,一步一步走上去。他重複揮舞著冰斧、上升、移動,三個動作,一語不發專注讓腳跨出每一步。當他每跨一步,就覺得氣力用盡,好像沒有力氣再跨下一步。但是攻頂的強烈渴望支撐著他,終於踏上銀白色的小小平台。放眼望去,周遭都是七八千公尺的山嶺,連綿不絕,一望無際的雪白。登頂,風景真的很不一樣。
我激動地拍拍他,摟著他的肩膀,除了看著一樣的風景外,還看到一個中年男子的毅力,心裡充滿感動。
人生的第一次下撤
然而不是每一次登山,所有的人都能成功登頂。當峰頂近在眼前時,來到這裡的登山者通常也已筋疲力盡,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和高原反應程度不盡相同。為了增加登頂的機率,我們通常會依據速度,將隊伍分成A、B兩隊;接著看團隊狀況,評估是不是需要將B隊再拆成B、C兩隊。B隊還有機會追上登頂,但若留在C隊,就代表與登頂無望了。
二00八年帶學生去吉力馬札羅山,那是我第一次加入速度較慢的分隊,不是身體狀況不好的緣故,而是為了陪伴太太怡婷。
自從我生病之後,原本不爬山的怡婷開始陪我爬山,因為她怕我在山上會發生意外。
當爬到五千五百公尺高時,B隊需要再拆成兩隊,我很想留在還有機會登頂的B隊。但怡婷的身體不是很理想,她跟我說:「智謀,可以留下來陪我嗎?」語氣盡是疲憊。
我望著相去咫尺的頂峰,再回頭看看氣喘吁吁的妻子,回想起這幾年她對我無怨無悔地照顧,心裡湧起極大的感動──決定這次換我陪著她。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下撤,以往爬山的目的就是為了登頂,然而在那一刻,我察覺人生有比登頂更重要的事。
也因為那一次我沒有離棄她,所以後來幾年去爬喜馬拉雅山、安娜普納峰時,她都願意陪我同行。
登上愛的頂峰
人生的第二次下撤是在二0一0年,我率領團隊陪著六龜育幼院、那瑪夏鄉的孩子遠征六一七八公尺高的青海玉珠峰,為的是幫助他們從莫拉克風災的創傷中走出來,找回重生的力量。
我們從格爾木基地營出發,在四千公尺高的地方待兩晚,完成高度適應後,開車到五千一百公尺高的基地營搭帳棚。那天晚上,我被一陣慌亂聲音驚醒。有位女同學激烈地咳嗽,我先檢查她的嘴唇是否發紺(編注:血管脫氧,使皮膚呈青色徵狀),再聽她的咳嗽是否有鑼音,檢查其心跳、血氧、血壓數據。情況不是很樂觀,我知道再這樣咳下去,恐怕會把肋骨咳斷,只好咬牙立下決定,連同另外一位高原反應嚴重的男同學,一起緊急下撤。
那位男同學和我吵起來,他說:「老師,我可以撐下去,請你相信我。」然而,我已經觀察了他幾天,雖然他的鬥志堅強,可是頭痛、嘔吐等症狀並沒有改善,行動也越來越緩慢,看著他近乎絕望的臉龐,雖然不忍心,我還是堅決命令他下撤。
但是不久前,車子才剛送走一批下撤的學生,等到回來時已是凌晨一點多。我們再度進行下撤,只是司機體力早已透支,所以這回換我開車。一路上大霧濃濃,加上對青藏公路不熟悉,我只能勉強撐起精神開車。同車的女同學知道我的身體狀況也不好,就陪著我聊天、協助注意路況。
到達格爾木基地營已是凌晨五點多,我累壞了,看到床立刻倒下睡著,睡了兩個小時後,司機的體力也恢復一些,才又換他開車載我回到五千公尺的基地營,然而我知道自己體力已到極限,需要好好休息,無法登頂了。
經歷這幾年爬山的經驗,讓我開始對登頂有不一樣的詮釋。過去我是一個登頂狂熱者,爬山就是為了登頂,為了證明自我。然而在陪伴學生的過程中,我體會到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意義,那位女同學說,當她看見我強打精神開車的模樣,彷彿看見一個剛毅的父親形象,給她很大的愛與安全感。從妻子和學生的回饋中,讓我察覺到沒有登頂也沒有關係,下撤也是生命中重要的體驗。不管最後身體有沒有登頂,我們的心靈因著愛,早已攀上頂峰。
當下最好的決定
每當說出「下撤」兩個字的時候,我的語氣總是堅決肯定,不留有商量的空間,但心裡其實充滿不捨。我知道如果心軟把患者留下,就是讓他們的生命置於更危險的狀況。
在高海拔的山上,要下撤隊員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要考量。對一個總領隊來說,要評估可承受的風險程度,是很不容易卻重要的決定。學生們為計畫付出了幾個月的心力與勞力,眼看登峰近在咫尺,身體卻不聽使喚,那種不甘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選擇下撤是不得已的決定,在當下卻是最好的決定。
人生似乎也是如此,當我們全力以赴面對生命的許多挑戰,屢屢無法突破和解決,甚至到了不得不放棄的地步,並不代表自己失敗了。一個人能夠瞭解自己的極限,正視自己的感受,不為成功的虛名強迫自己,不正也是一種自我的突破?
也許這次沒有登頂,不代表下一次不會成功。山永遠矗立在那裡,耐心等著你;山也是你最棒的生命導師,你在探索她的同時,其實也是在探索自己。
師大畢業到國中實習的那一年,我被派去帶領放牛班。可以想像在師大學的「愛的教育」那一套,在這裡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屢勸不聽的學生,我只好用拳頭收服,面對從街頭出身,「實戰」經驗豐富的我,沒有學生能打得過。在暴力威脅之下,他們變得聽話,即便我非常不願意用暴力對待學生,卻也找不到其他辦法。時常學生做完掃除工作跑來問我:「老師,我們可不可以抽根菸?」「別讓我看到就可以。」我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時,覺得自己被困在一個地方,沒有出路,心情極度鬱悶,所以寫了一句話:「屬於大海的動物,需要大一點的空間。」來勉勵自己走出陰霾。沒想到,這句話,竟成為我後半生教學生涯的寫照。
老師的世界有多大,學生的夢想就會有多大
一直以來,我深信如果父母把孩子關在室內教育,他的世界就只有房間那麼大,就算再有錢,頂多也是幾百坪;一個老師的世界倘若只有教室或研究室那麼大,他教出來的學生也不過那樣大的視野。
有些時候,教室如同圍牆一樣,把我們上課內容與時間關起來,學生的創意被上了鎖,夢想的翅膀也被綁住,考試只是像機械化的勞動,把學生的精力消磨掉。圍牆外面,有許多有意義的學習,雖然考試不考,卻是人生樂趣所在。但牆外的東西往往讓我們感到陌生,因為我們被關在牆內長達十二年,甚至更久。常有學生在離開學校後,從此不想學習,因為學習帶給他們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經驗。
我一直努力突破教室的圍牆,把學生帶到戶外,帶入生活,帶向世界。二0一一年的暑假,兩位男同學去攀登布羅德峰,海拔八0五一公尺;五位畢業生帶著十二個藥物濫用的孩子,進行二十一天荒野治療課程;四位畢業生,帶領台大為期十天的冒險領導課程;一位男同學,為急難家庭募款而環島義走;兩位女同學,前往新疆旅行並蒐集夢想與希望;一位女同學在美國流浪四個月;一位聽障男同學去獨攀南湖大山;一位老師帶著十多個學生騎車環島;一位老師帶著八個學生去尼泊爾爬山,並為當地募款蓋社區儲水槽、舉辦夏令營。
這些――都是我的學生,他們見證了學習是寬廣無限的,只要激發他們學習的樂趣,認同學習的意義,他們會願意花三倍的時間來投入學習。
金魚缸裡養不出鯨魚。如果把孩子放在金魚缸裡,層層保護,仔細照料他們,可以養出有禮貌、很漂亮的金魚,但這樣的孩子可能是脆弱的,不敢面對挑戰,甚至膚淺的以為,幾株水草,就是全世界。我們應該教出大器的孩子,讓他們在大海裡學習,陪他們對話與思辯,豐富的閱讀,鼓勵獨立思考,目睹他們生命卓越的蛻變。我想看見他們變成大鯨魚,充滿自信地在世界遨遊,只有如大海般,寬廣無限的空間,才裝得下孩子無限的可能。所以,不要怕孩子冒險,帶他們離開金魚缸,進入大海裡吧。
登頂不是課程目標
我剛回國任教時,在美國學的專業完全派不上用場,因為學校教的是一些運動社會學、行銷學與休閒經營等科目。後來有機會才在實務課程中,把以前所學的戶外及平面遊戲帶進課程裡。那時不僅沒有活動器材,連戶外的器材都要向南港國中童軍團借。就這樣開始,一群人慢慢跨到戶外。後來又開了一門課——單車跨北橫,接著加入溯溪、登山、划獨木舟、建造竹筏、建繩索場,也開始接營隊及活動,舉辦冒險治療課程和治療性營隊,帶領學生去幫助中輟生、受家暴性侵的孩子、殘疾人士,以及社會各個弱勢階層。
為了讓學生擁有國際視野,所以我開了海外登山領導課程,先後進行美國國王峽谷冒險計畫、阿拉斯加遠拓獨木舟學習計畫,後來在帶領學生喜馬拉雅登山計畫的同時,也開始嘗試將服務學習放在領導力課程內,讓學生為尼泊爾蓋教室募款、和壢新醫院合作義診。之後,與好朋友成立外展教育學校(OBT),在大家的協助下,成立亞洲體驗教育學會。二00七年,除了戶外體驗教育之外,我增加了服務體驗教育,引導學生們進行各種服務計畫,包括關心全球暖化議題、幫流浪狗結紮、陪讀計畫、募書與閱讀計畫、推動無痕山林等,學生的足跡踏遍台灣各鄉各鎮,以及尼泊爾、甘肅、四川、希臘各地。
團隊合作的學習模式
回首這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一直在思索,要教出什麼樣的孩子。我沒有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模式教學,只是用心貼近學生的生命,去聽他內心深處的故事,挖掘被輕忽的能力。根據學生的需要,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
我帶領一群沒有戶外經驗的學生,經過一學期的準備及訓練,攀登喜馬拉雅山。在過程中,他們一起開會討論,學習登山技巧、訓練體能、打電話募款(學習被拒絕)、主動尋找師資(學習尋求協助與資源)、打包(學會取捨)、與家人溝通、學會風險控管、解決團隊衝突、情境演練(在重要時刻如何做決策)等。登頂不是我的課程目標。重要的是,他們在「團隊合作」模式下學習,有別於傳統競爭學習模式。
過去傳統教育總是教我們要打敗別人,學習就像賽跑,第一名只有一位,只要往前衝,不需要等待,所有人都是敵人。在這種競爭模式下成長,容易養成自私的孩子,不懂團隊合作,也沒有耐心。同事如果跟不上他的速度,就會開始抱怨,認為別人拖慢團隊速度,妨礙他的事業往上爬。這樣的心態,只會讓他失去快樂,失去人對他的敬重。
而在團隊合作模式下學習,我們的目標不是比誰第一個登頂,而是全部隊員要一起登頂。在過程中,速度快的要等慢的,經驗豐富的要等沒經驗的。爬山的時候,他們親密的相處在一起,真誠地關心伙伴的身體狀況,彼此扶持。如果有隊員必須下撤,大家會抱在一起哭泣,捨不得分開。他們眼中不再只有自己,而是會發自內心去關懷人。
在這些冒險挑戰中,學生和我的生命不斷被更新與擴張,我們對生命有新的闡述和認識。雖然說不清楚學生到底學到了什麼,但我確信他們學到的,遠比我想像得更多。
這堂課喚起學生對生命的熱情、對能力的想像,如果一群沒有經驗的人,透過學習可以攀上喜馬拉雅山,還有什麼能阻止他們登上生命的高峰呢?還有什麼能限制他們的夢想呢?
瘋狂期末考
當我成為基督徒後,本來立志要當牧師,但是上帝並沒有開啟這條路,反而帶領我進入國立體育大學教書。也許祂認為我可以把老師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一直希望能教出具有僕人氣息與領袖特質的學生。顯然,這不是用紙筆測驗就能測得出來。
我對研究生出的期末考題,是請他們分組做專題,接著說明評分標準:一、要對社會有幫助;二、要對團隊有挑戰性;三、要有永續性。
根據這三個規則評分,學期中不考試。
若學生無法達成這三項規則,這門課稱不上領導學。我認為在教室裡的學習,不能成為唯一,必須透過實踐、反思,發展自我認同與利他服務,才能使學習內化,彰顯學習的意義與價值。培訓領導力,不是以口頭的方式授課,要學生背誦教科書,最後寫一篇報告,就能夠學會。
你可以想像,這對在傳統紙筆測驗中長大的學生來說,是多大的挑戰。但如果問我,這些年教學最大的感想是什麼,我會回答:永遠都要相信你的學生做得到。老師深信學生做得到,用這樣的信念教學,學生會感受到你對他們的信心,更會激發他們的能力。事實上,他們做得遠比我想像得更好。
在課堂上,我會先分享自己做過什麼,或以前的學長姐做過什麼,有時會邀請一些成功的典範來分享。
有一次,我分享和學生帶領盲人去登山和攀岩。如果盲人可以爬山,還有誰不能爬山。我跟學生說,我曾在喜馬拉雅山上,看見當地七歲的孩子在那裡跑上跑下,根本不當作爬山。他們跟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心臟沒有比較大顆,要相信上帝創造人類的潛能。你現在做不到,並不代表未來無法做到。
然後我雙眼直盯著他們,口氣堅決地說:「你們可以做得更好。」真的,學生們相信了。他們帶領國中生參與社區關懷探訪;有一組募了幾百本書給偏遠國小,並協助整理圖書室;有一組帶四位特殊兒童去爬雪山,帶著小朋友在山上撿垃圾;有人替學校募電腦,替弱勢兒童募集鞋子;有人帶領癌症病人攀岩,結果攀完岩,病人告訴他們還想要去潛水。
有一組學生在西門町放一座巨型監牢,一名學生在裡面讀書,鐵窗外貼著「爸媽!我不要坐牢」的大海報,象徵教育被綁架了十二年。透過街頭的即興表演,傳達「做中學」及「服務學習」的教育理念。
學生們運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心。每一屆學生的經驗會激發下一屆學生的創意,沒有一年的期末考是一樣的。他們付出生命,並影響生命,匯集成巨大的力量。
我聽著期末考報告,學生在過程中成長,從服務對象得到回饋,體認到學習的價值。看見學生生命的轉化,心裡十分感動,眼眶也忍不住泛淚。我的學生真的很棒。
比登頂更重要的事
登山是一件非常耗費體力的活動,尤其是高海拔登山。因為體力與缺氧的緣故,更容易經歷到平地無法經驗的累。到了體力耗盡的臨界點,開始就是一連串的自我對話與自我掙扎。選擇放棄常會是第一個跑出來的念頭,然而接著出來的是更多的自我激勵、自我支持的往前力量。這兩者會在交織過程中彼此衝突,腳步在停停走走之間繼續邁進。如果不小心跌了一跤,放棄的念頭就會像落石一樣,狠狠砸在你頭上,你會望著山頂,停在那裡忍著哭的衝動,想放棄。
在爬喜馬拉雅山那年,我有個學生當時已經快五十歲了,比我年紀還大上幾歲。在登山四千公尺之後,他走路的速度,以及身體各項指數都不是很理想。我一直關心著他的身體狀況,猜想他應該無法登頂。沒想到他最後穿上冰爪,一步一步走上去。他重複揮舞著冰斧、上升、移動,三個動作,一語不發專注讓腳跨出每一步。當他每跨一步,就覺得氣力用盡,好像沒有力氣再跨下一步。但是攻頂的強烈渴望支撐著他,終於踏上銀白色的小小平台。放眼望去,周遭都是七八千公尺的山嶺,連綿不絕,一望無際的雪白。登頂,風景真的很不一樣。
我激動地拍拍他,摟著他的肩膀,除了看著一樣的風景外,還看到一個中年男子的毅力,心裡充滿感動。
人生的第一次下撤
然而不是每一次登山,所有的人都能成功登頂。當峰頂近在眼前時,來到這裡的登山者通常也已筋疲力盡,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和高原反應程度不盡相同。為了增加登頂的機率,我們通常會依據速度,將隊伍分成A、B兩隊;接著看團隊狀況,評估是不是需要將B隊再拆成B、C兩隊。B隊還有機會追上登頂,但若留在C隊,就代表與登頂無望了。
二00八年帶學生去吉力馬札羅山,那是我第一次加入速度較慢的分隊,不是身體狀況不好的緣故,而是為了陪伴太太怡婷。
自從我生病之後,原本不爬山的怡婷開始陪我爬山,因為她怕我在山上會發生意外。
當爬到五千五百公尺高時,B隊需要再拆成兩隊,我很想留在還有機會登頂的B隊。但怡婷的身體不是很理想,她跟我說:「智謀,可以留下來陪我嗎?」語氣盡是疲憊。
我望著相去咫尺的頂峰,再回頭看看氣喘吁吁的妻子,回想起這幾年她對我無怨無悔地照顧,心裡湧起極大的感動──決定這次換我陪著她。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下撤,以往爬山的目的就是為了登頂,然而在那一刻,我察覺人生有比登頂更重要的事。
也因為那一次我沒有離棄她,所以後來幾年去爬喜馬拉雅山、安娜普納峰時,她都願意陪我同行。
登上愛的頂峰
人生的第二次下撤是在二0一0年,我率領團隊陪著六龜育幼院、那瑪夏鄉的孩子遠征六一七八公尺高的青海玉珠峰,為的是幫助他們從莫拉克風災的創傷中走出來,找回重生的力量。
我們從格爾木基地營出發,在四千公尺高的地方待兩晚,完成高度適應後,開車到五千一百公尺高的基地營搭帳棚。那天晚上,我被一陣慌亂聲音驚醒。有位女同學激烈地咳嗽,我先檢查她的嘴唇是否發紺(編注:血管脫氧,使皮膚呈青色徵狀),再聽她的咳嗽是否有鑼音,檢查其心跳、血氧、血壓數據。情況不是很樂觀,我知道再這樣咳下去,恐怕會把肋骨咳斷,只好咬牙立下決定,連同另外一位高原反應嚴重的男同學,一起緊急下撤。
那位男同學和我吵起來,他說:「老師,我可以撐下去,請你相信我。」然而,我已經觀察了他幾天,雖然他的鬥志堅強,可是頭痛、嘔吐等症狀並沒有改善,行動也越來越緩慢,看著他近乎絕望的臉龐,雖然不忍心,我還是堅決命令他下撤。
但是不久前,車子才剛送走一批下撤的學生,等到回來時已是凌晨一點多。我們再度進行下撤,只是司機體力早已透支,所以這回換我開車。一路上大霧濃濃,加上對青藏公路不熟悉,我只能勉強撐起精神開車。同車的女同學知道我的身體狀況也不好,就陪著我聊天、協助注意路況。
到達格爾木基地營已是凌晨五點多,我累壞了,看到床立刻倒下睡著,睡了兩個小時後,司機的體力也恢復一些,才又換他開車載我回到五千公尺的基地營,然而我知道自己體力已到極限,需要好好休息,無法登頂了。
經歷這幾年爬山的經驗,讓我開始對登頂有不一樣的詮釋。過去我是一個登頂狂熱者,爬山就是為了登頂,為了證明自我。然而在陪伴學生的過程中,我體會到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意義,那位女同學說,當她看見我強打精神開車的模樣,彷彿看見一個剛毅的父親形象,給她很大的愛與安全感。從妻子和學生的回饋中,讓我察覺到沒有登頂也沒有關係,下撤也是生命中重要的體驗。不管最後身體有沒有登頂,我們的心靈因著愛,早已攀上頂峰。
當下最好的決定
每當說出「下撤」兩個字的時候,我的語氣總是堅決肯定,不留有商量的空間,但心裡其實充滿不捨。我知道如果心軟把患者留下,就是讓他們的生命置於更危險的狀況。
在高海拔的山上,要下撤隊員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要考量。對一個總領隊來說,要評估可承受的風險程度,是很不容易卻重要的決定。學生們為計畫付出了幾個月的心力與勞力,眼看登峰近在咫尺,身體卻不聽使喚,那種不甘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選擇下撤是不得已的決定,在當下卻是最好的決定。
人生似乎也是如此,當我們全力以赴面對生命的許多挑戰,屢屢無法突破和解決,甚至到了不得不放棄的地步,並不代表自己失敗了。一個人能夠瞭解自己的極限,正視自己的感受,不為成功的虛名強迫自己,不正也是一種自我的突破?
也許這次沒有登頂,不代表下一次不會成功。山永遠矗立在那裡,耐心等著你;山也是你最棒的生命導師,你在探索她的同時,其實也是在探索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