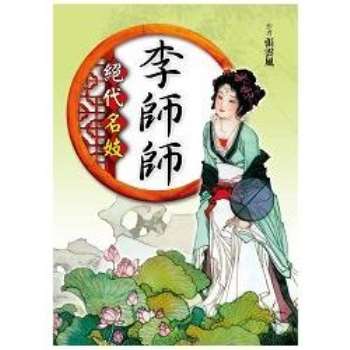第一章 啞丫不啞
西元九六○年農曆正月,後周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宋州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威逼後周皇帝柴宗訓遜位,自己登上皇帝寶座,改國號為宋(北宋),他就是宋太祖。宋代定都開封(今河南開封),開封因此稱東京,開始了一百六十多年夢幻般的崢嶸歲月。所謂「東京夢華」,正是它這一段崢嶸歲月的生動寫照。
開封地處中華腹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春秋時期,鄭莊公在開封附近修築儲糧的倉城,「啟拓封疆」,稱其地為啟封。西漢初為避漢景帝劉啟名諱,啟封更名為開封--這就是開封之名的由來。開封在戰國時曾稱大梁,是「七雄」之一魏國的都城。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郡縣制,大梁降為浚儀縣,隸屬於三川郡。北朝東魏設梁州,下轄陳留、開封、陽夏三郡。北周改梁州為汴州。因此,開封一稱汴、汴梁、汴都、汴京。汴河是開封的主要河流,連通黃河與淮河兩大水系。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中段就是因地制宜地利用了汴河,從而使開封成為南北交通線上的一個樞紐和要衝。唐代中期以後,藩鎮割據,汴州節度使李勉等構築汴州城,奠定了後世開封城的雛形。五代時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均定都開封,標誌著中國政治中心從長安、洛陽東移,具有里程碑意義。宋代東京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包括外城、內城、皇城三大部分,築有三重城郭,鑿有三道護城河。宮殿巍峨,坊市合一,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超過一百萬。史學家常用兩句話形容它的輝煌氣象:「八荒爭湊,萬國咸通。」
宋代東京行政區劃含一府一縣:府為開封府,下設廂、坊,居民主要為城市平民、工商業者和達官權貴;縣為祥符縣,下設鄉、村(里),居民主要為農民。宋哲宗趙熙在位期間,東京外城東二廂永慶坊一條狹長街道上,新開辦一家染坊,門前懸掛黃布黑字招牌,上寫大字:「王記便民染坊」。「王記」,表示染坊的主人姓王。沒錯,染坊的主人的確姓王,單名一個寅字。王寅,二十四五歲,中等身材,方臉寬額,濃眉大眼,胸前和胳膊上的肌肉隆起,身體強壯得像一頭牛。王寅老家原在祥符縣陀螺鎮,母親早已亡故,父親是個染匠,開設王記染坊,以染布染衣謀生。古代人多用棉、麻、葛等原料紡線織布,織出的布基本上是白色的。要把白布變成其他顏色,或把白布衣服變成其他顏色,主要靠染坊用顏料染作。因此,開染坊是很賺錢的,前提是染匠的技藝必須高超,染出的布、衣,色澤要鮮亮,而且要不掉顏色。王父一輩子都和顏料、染缸打交道,在實踐中摸索與累積,練就了一手過硬的染作技藝,在當地算是能人,每天都有收入,家境比較富裕並小有積蓄。
王寅自小在私塾讀過幾年書,可對之乎也哉、子云詩曰之類不感興趣,乾脆輟學,幫助父親經營染坊,也當了染匠。他很聰明,很快把父親的染作技藝全盤掌握,並有所發展,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他十八歲那年,娶了樊姓女子為妻,正式成家立業。樊氏比他小兩歲,身段苗條,肌膚白淨,那體態那容貌那神情,完全可以用一個「美」字來形容;而且性格溫柔,品德賢淑,侍奉丈夫,孝敬公公,那是絕對的好妻子好媳婦。
王記染坊經營得有模有樣,忽然一場大病,奪走了王父的性命。王父死前向兒子兒媳交代兩件事,算是遺囑:一是要把王記染坊開到繁華的京城去,那樣更有「錢」途;二是趕快生個孩子,以免絕了王家香火。王寅含淚,點頭答應,眼看著父親斷了氣。
王寅埋葬了王父,執行第一項遺囑。他把陀螺鎮的染坊及家產全部賣了,加上歷年來的積蓄,在東京外城購買了兩間門面房、一個小院落,開辦了王記便民染坊。王記染坊名稱中加進「便民」二字,顯示了王寅的智慧和精明。他的染坊要在京城立足並有所發展,除了靠染作品質做保證外,還要靠服務態度取勝,而便民正是服務態度的關鍵。
門面房用來承接活計。長長的櫃台,一頭擺放大大小小的瓷罐,瓷罐裡裝滿各種顏料;一頭擺放多種顏色的布料樣子,顧客染布染衣,指定其中任何一種顏色,王寅都能把它調製出來,並把布、衣染成那種顏色。他待客熱情,大到成匹成匹的布,小到一尺二尺的布或一條枕巾一方手帕,所有活計,全都承接,染價低廉,真正貫徹了便利民眾的宗旨。小院落裡有兩間草房,那是王寅夫婦的住所。草房前,壘起多個灶台,架起多口大鍋,那是染坊必備的器物。染坊的染作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先把染物放在清水中浸泡,至少半個時辰;顏料兌水,放在大鍋裡煮沸;把浸泡透了的染物,放進大鍋裡染色,不停地翻轉和攪動,切忌染色輕重不勻;顏料水和染物自然冷卻,將染物撈出,放到清水中再浸泡半個時辰。然後便是晾曬,使染物乾燥,整疊整齊。小院落裡,柴火熊熊,熱氣騰騰,那熱氣散發出顏料在水中煮沸後特有的香味;空中鐵絲縱橫,鐵絲上懸掛晾曬的染物,赤、橙、黃、綠、青、藍、紫、黑,五光十色,鮮豔絢麗。這構成了染坊獨具風情的特色景觀。
王記便民染坊右面緊挨著一家馬記豆腐店,豆腐店也有兩間門面房、幾間草房和一個小院落。主人馬達三十八歲,妻子燕氏二十八歲,人稱馬哥、馬嫂。不知什麼原因,馬嫂長期沒有生育,以致馬哥經常罵她是不下蛋的母雞。馬嫂一個遠房堂弟燕順,在東京當苦力,靠拉平板車給商家運送貨物賺錢,維持生計,住在一座破廟裡。燕順妻子季氏二十歲,身懷六甲已六七個月,住在破廟裡怎麼生孩子?馬嫂可憐堂弟夫婦,徵得丈夫同意,遂讓燕順兩口子,住進自家後院空著的兩間草房裡。燕順感激不盡,想到即將出世的孩子,起早貪黑替商家運貨,力圖多賺些錢。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這天,他沒吃食物,拉了滿滿一車貨物,走著走著,突然雙眼一黑,一頭栽倒在地上,口吐鮮血,瞬間一命嗚呼。
季氏獲知消息,哭得死去活來。馬哥馬嫂哀歎堂弟命薄,買了口薄棺將之埋葬。不久,季氏臨盆,生了個七斤重的胖小子,取名燕青。季氏已是個寡婦,覺得老住在堂姐堂姐夫家不像回事,意欲另外尋地方居住。馬嫂繼續可憐堂弟媳婦,說:「你們孤兒寡母,又能住到哪裡去?住到外面又靠什麼生活?豆腐店正缺人手,我看你不如留下來,幫著幹些雜事,如泡黃豆煮豆漿什麼的,總比像個沒頭的蒼蠅,亂撞一氣強不是?」季氏求之不得,熱淚盈眶,恨不得跪地叩頭,把堂姐叫觀音菩薩。從此,季氏也成了馬記豆腐店的一員,人稱燕嫂。王記便民染坊和馬記豆腐店兩個院落之間,沒有圍牆,只用竹竿編織的籬笆牆隔開。水井是共用的,就在籬笆牆的中段。兩家人沒幾天就混熟了,親親熱熱如一家人。馬嫂燕嫂染布染衣,王寅夫婦絕不收錢;同樣,王寅夫婦喝豆漿吃豆腐,馬哥馬嫂也絕不收錢。馬嫂身材胖些,燕嫂身材瘦些。王寅戲謔地叫一人為胖嫂,一人為瘦嫂。馬嫂和燕嫂爽快答應,毫不介意。這正應了一句俗話:遠親不如近鄰。
王寅執行父親第一項遺囑卓有成效,執行第二項遺囑也有收穫。就在王記便民染坊開張的第二年,樊氏懷孕了;第三年正月,樊氏分娩,生了個小巧玲瓏的女兒。女兒就女兒唄,王寅還是很高興很開心,隨口把女兒叫丫丫,抱她親她,愛不釋手。這一年是宋哲宗元祐八年(西元一○九三年)。宋哲宗是宋神宗趙頊的兒子,九歲登基,在皇位上已坐了八年多,后妃們卻還未生個龍子。皇帝沒有兒子,那會出現皇位危機。因此,很多人都在擔心、焦急著哪!
丫丫降生後發出的第一聲啼哭,在王寅和樊氏聽來,那是天外來音,是世界上最奇妙最美妙的音樂。丫丫與別的初生嬰兒不同,主要是皮膚潔白,晶瑩光潤,如玉如脂。兩天後,他睜開眼睛,雙眼皮,長睫毛,一對眸子又黑又亮,放射出寶石般的光芒,像是天上的星星。她開始吃母親的奶,櫻桃小口噙著乳頭,吮吸有力,吃得很貪婪很香甜。吃著吃著就睡著了,長睫毛合在一起,一副滿足、舒服的樣子,煞是好看。
王寅當了父親,高興開心,渾身上下都是勁。他讓樊氏靜靜躺著,只管餵養女兒,染坊的所有事情,獨自承擔起來。承接活計,擔水燒火,浸泡染物,配製染料,染布染衣,晾曬整疊,付貨收錢,忙得不可開交,真可謂是「眼睛一睜,忙到熄燈」。這樣,他樂意,他喜歡,臉上總是掛著笑,口中還哼著小曲兒。因為他有妻子有女兒,他要透過工作,讓她們母女過上優裕的生活。
王寅看丫丫,長得像她娘。三個月後,丫丫己顯露出美人胚子端倪。五官端正,比例和諧,組合成一個橢圓的面龐,完完美美,白白嫩嫩。小胳膊小腿,勻稱、靈巧,瓷質感很強,像個瓷娃娃。奇怪的是,丫丫自出生那天啼哭過一次外,其後再未啼哭過,好像不會啼哭似的。樊氏教她說話,讓喊爹喊娘。她呢?黑眸轉動,望這望那,就是不出聲。樊氏不由擔心起來:天哪!丫丫該不會是啞巴吧?
王寅說:「別胡說!你我的女兒,怎會是啞巴呢?」樊氏抱著丫丫,把自己的擔心告訴馬嫂和燕嫂。馬嫂和燕嫂寬慰說:「別急!瞧丫丫這樣靈氣,怎會是啞巴呢?嬰兒嘛,有的愛哭,有的不愛哭,有的發聲早,有的發聲遲。丫丫屬於不愛哭、發聲遲類型,再長大些,自會放聲啼哭和開口學話的。」燕嫂懷中抱著燕青。燕青見丫丫,伸手去抓她的小臉。樊氏擔心燕青會弄傷丫丫的眼睛,閃了閃身避開了。
丫丫半歲的時候,樊氏的重要任務,就是教女兒出聲、學話,指指點點,告訴她什麼是天,什麼是地,什麼是太陽,什麼是月亮,什麼是樹,什麼是花,什麼是小鳥,等等。王寅在院落裡工作,把染了色的布、衣從清水中撈出,展開,懸掛到鐵絲上晾曬,眼前頓時出現一個花花綠綠的彩色世界。樊氏告訴丫丫,這是布,這是衣服,這是紅色,這是黃色,這是藍色,這是紫色,這是綠色,這是黑色。丫丫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聽懂了,但抿著小嘴,就是不出聲。樊氏不禁嘆氣,說:「唉,這孩子,到底怎麼回事嘛?」
樊氏接著又發現,丫丫好像也不會笑,因為半歲多了,從未見她笑過。任你怎麼逗她,那怕撓她手心腳心,她也不笑。樊氏急得在房裡轉圈圈,連聲說:「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王寅也著急起來,說:「要不要請郎中瞧瞧?」
轉眼就到八月中秋節。樊氏說:「這樣:中秋節夜間,我們帶丫丫去州橋看水中月亮,對月許願,求月神嫦娥保佑她會哭會笑會說話。據說靈驗得很,許願凡有所求,都能實現。」王寅欣然同意。
汴河自西北向東南,橫貫東京城。汴河上共有十三座橋樑,其中州橋最為雄偉和壯觀。此橋正名叫天漢橋,位於皇城南面御街(一稱天街)中段,長約三十丈,寬約二丈,恰在東京城的中軸線上。站在橋頭,南望內城的朱雀門,北望皇城的宣德門,東、西望汴河水洶湧奔騰,視野開闊。橋墩、橋柱、橋樑、橋面皆為青石材料,橋欄上雕刻各種精美紋飾。橋墩、橋柱、橋樑、橋欄之間,皆用石榫連接,榫榫相扣,全橋形成一個牢固的整體。這裡是東京的中心地帶,橋上整日車水馬龍,行人熙攘。每月中旬,一輪明月倒映水中,月光融融,水光融融,天水一色,恍若仙境。美景總會發人遐想。於是便有人編出故事,說每月望日(十五日)夜間,月神嫦娥必到汴河沐浴,人若登上州橋觀月,對月許願,求妻求壽求子求女求官求財等,嫦娥都會答應。這樣一來,每月中旬夜間,登橋觀月、對月許願的人比平日裡多出數倍,望日夜間尤盛。中秋之夜,月懸中天,金風送爽。王寅、樊氏夫婦抱了丫丫,直奔州橋。到了州橋附近一看,但見汴河兩岸和御街兩邊,商鋪酒樓燈火通明,笙歌簫曲悠悠揚揚;橋南橋北,密密麻麻全是人,摩肩接踵,都想登橋,到橋中央去俯瞰水中皎月,並對月許願。王寅面對人山人海,有點發怵,說:「這麼多人?我看就別登橋了吧?」
樊氏一心想讓女兒哭女兒笑女兒說話,說:「既然來了,哪有不登橋之理?」
王寅一咬牙,說:「那好,我抱丫丫走前面,你緊跟著,到橋中央飛快地觀月許願,然後就往回走,中不?」「中」是東京一帶方言,就是「行」的意思。樊氏點頭說:「中!」
王寅和樊氏硬是擠進了湧動著的人流。擠進去了便後悔。因為人太多,人挨人人擠人,想轉個身都不可能。樊氏原是拉著丈夫上衣後襟的,哪知一擁擠,別人插到了她和丈夫中間。人流緩慢向前挪動,好不容易登上橋頭。橋上更加擁擠,南面的人要向北,北面的人要向南,各不相讓。更有一些流氓無賴,專門擠在人堆裡,抓摸大姑娘乳房和小媳婦屁股。大姑娘和小媳婦發出尖叫。流氓無賴附和著浪叫浪笑,樂不可支。王寅招呼樊氏說:「跟著我,別走散!」樊氏回應說:「沒事,你抱好丫丫!」
天宇澄澈,皓月如盤。人流挪動,聲音嘈雜。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王寅感覺到了橋的中央。明月正倒映在右側水面,人們都往右側擠,在那裡憑欄觀月,最為清晰。王寅懷抱丫丫,只向右側水面看了看,根本沒看到水中月亮,就被人擠到左側,當然也就沒顧上許願。樊氏非常英勇,拼命往右側擠,伸手抓住橫著的橋欄,憑欄俯看水面,只見一輪又大又圓的明月,倒映在水中,搖搖晃晃,玉光閃閃。樊氏認定,那是嫦娥秀美的面龐,忙雙手合什作揖,虔誠地說:「求求嫦娥,保佑我們家丫丫會哭會笑會說話!」她唯恐嫦娥沒有聽清,又把願語重複兩遍。這時,很多人都向右側擠,向橋欄擠。猛聽得「嚓」、「咚」兩聲巨響,右側那一段橫著的橋欄脫榫,掉落河中。王寅看得清楚,包括樊氏在內的二三十人,同時掉落河中。
有人高聲喊道:「橋欄脫榫啦!大橋可能垮坍呀!快跑呀快跑呀!」喊聲尖銳刺耳。橋中央的人出於本能,驚慌失措,分別向橋的兩頭跑。橋頭的人不明底細,仍向橋中央擠。人流與人流相撞,有人惡語相加,有人動起拳腳,有人摔倒,有人被踩掉了鞋,喊聲哭聲謾罵聲,亂成一鍋粥。王寅很想跳河去救樊氏,可丫丫在懷,哪裡能夠?他是隨著人流「流」到岸上的,到了岸上,方才有機會朝下游水中大喊:「樊氏,樊氏!」
汴河水流湍瀧,泛著銀白色浪花,一路東去。王寅沿著河堤向東跑,依然大喊:「樊氏,樊氏!」回答他的,只是嘩嘩的流水聲。他一時不知該做什麼,拔腿往家的方向跑。他顧不上回自己的家,而是狠敲馬哥馬嫂家的門。馬哥馬嫂被驚醒了,燕嫂也被驚醒了。馬哥披衣,打著哈欠,詢問誰在敲門,聽出是王寅的聲音,忙將門打開。王寅懷抱丫丫進門,撲通跪地,拖著哭腔說:「馬哥,樊氏掉進汴河啦!」
馬哥仍打著哈欠,沒聽明白是什麼意思。馬嫂已經起床,忙向前問:「你說什麼?」
「我和樊氏帶著丫丫,去州橋觀月許願,人太多,丫丫她娘,掉,掉進汴河了。」王寅說。
「那你該跳河救她呀!」馬嫂說。
「我懷中還抱著丫丫呀!」王寅說。
燕嫂也起床了,見王寅抱著丫丫,伸手接過,說:「把丫丫給我。」燕嫂看丫丫,長長的睫毛覆蓋著眼睛,小嘴半張,呼吸均勻,睡得很熟很香。
馬哥算是聽明白了,忙穿衣穿鞋,取了一根長竹竿,對王寅說:「快走,我陪你去瞧瞧!」
馬哥和王寅去了州橋。時間已過午夜子時。馬嫂沒好氣地說:「觀月?許願?觀出許出禍事了不是?」
燕嫂說:「丫丫這樣子,王寅樊氏也是病急亂投醫。」馬嫂搖頭說:「樊氏,一個女人,掉進汴河,只怕是凶多吉少。」燕嫂身上打了個冷顫,把熟睡的丫丫抱得更緊些。她想,可憐的丫丫,還不滿周歲,難道就要失去娘麼?
燕嫂把丫丫抱回自己所住的草房。燕青側躺在炕上,睡得正香。燕嫂不管燕青,且管丫丫,取來溫水,給她洗了臉洗了手洗了腳,把她放到炕的最裡面,讓她繼續睡覺。燕嫂靠著炕頭,看著丫丫,毫無睡意。她暗暗向上蒼祈禱,但願樊氏能平平安安歸來,一個嬰兒,寧可沒有爹也不可沒有娘啊!五更時分,馬嫂和燕嫂同時起來,開始勞作做豆腐。第一步是磨黃豆,給小毛驢駕套,蒙上眼罩,讓它拉著石磨轉動。黃豆是頭天浸泡的,脹得很大,加水經石磨碾壓,變成潔白的乳狀物,流在磨槽裡,再由一個小孔,流進木桶裡。第二步是生火煮漿,將乳狀物過濾,去掉豆渣,放進大鍋煮沸,那便是可飲用的豆漿了。第三步,將豆漿轉移至缸裡,點進適量的鹽鹵或石膏水,豆漿呈現出凝固的狀態。把這樣的豆漿迅速用包布包起來,包成四方形,平放在木板上,上面亦放木板,壓上石頭等重物,擠掉包布裡的一些水分。這樣,包布裡的豆漿就成了豆腐,白白嫩嫩,味美可口。豆腐店做豆腐,數量多少用板衡量,一個包布的豆腐稱一板,二尺五寸見方,約三寸厚。馬哥馬嫂原先每天做十板豆腐,自從燕嫂這個廉價勞力加入後,他們每天做十五板豆腐。生產數量增加百分之五十,意味著銷售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年多來,豆腐店賺錢可是不少啊!
燕嫂在磨黃豆、煮豆漿時,回了幾次草房。炕上睡著燕青、丫丫兩個小孩,她不放心,生怕小孩跌到地上。她第五次回草房時,發現丫丫醒了,不哭不鬧,眼睛黑亮,這邊瞧瞧,那邊瞧瞧。她抱起丫丫,端了一泡尿。丫丫把一個手指放在小嘴裡吮吸,顯然是餓了。燕嫂忙去盛了半碗豆漿,晾涼,用小勺餵她。她一直吃她娘的奶,改吃豆漿,竟也吃得津津有味。豆腐做成了。燕嫂又切了半塊豆腐,用小勺餵她。她吃豆腐,同樣吃得津津有味,還用小手抓碗裡的豆腐,往嘴裡送,弄得滿手滿嘴都是豆腐,讓人感到好笑和心疼。
燕青也睡醒了,看到丫丫,奇怪地問:「娘,丫丫怎會在我們家?」燕嫂說:「你王寅叔和樊氏嬸子有事,把丫丫放我們家,讓娘幫著照看一會兒。」丫丫見燕青,眼睛更亮,伸開雙手,好像是要讓燕青抱。燕青才四歲,抱不了她,伸手把丫丫小手拉了拉,說:「丫丫,你快長大,我和你一起玩!」
中午,馬哥和王寅回來了,從二人疲倦、無奈的神情中可以斷定,樊氏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馬嫂還是問:「怎樣?」馬哥搖頭,說:「一個女人,夜間掉進汴河,哪還能活?我們從州橋往下游找,找了快二十里,看到多具屍體,卻未見樊氏屍體。人們都說,水流那樣急,屍體怕是早沖到三四十里開外了,哪裡找去?再說,找到屍體又能怎樣?人死不能復生。所以,我們就回來了。」說罷,他重重歎了口氣:「唉!」一夜又半天光景,王寅像變了個人似的,耷拉著腦袋,目光呆滯,懊惱,萎靡,悲傷。燕嫂把丫丫抱來,遞給他。他直勾勾地看著女兒,眼中滾落豆大的淚珠。他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怎麼管得了才八個多月的嬰兒?他想了想,突然跪地,說:「燕嫂,我現在走投無路,只能把丫丫交給你了,求你餵養她照料她,我每月付給五兩銀子。」
燕嫂沒想到會出現這種情況,忙說:「我可以幫你餵養、照料丫丫,但不能要你的銀子。我和燕青,幸虧馬哥馬嫂收留,才有安身之地。你若給銀子,就給馬哥馬嫂吧!」
王寅回頭看馬哥馬嫂。馬哥說:「鄰里之間,互相幫襯嘛,什麼銀子不銀子的?」馬嫂覺得每月五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忙笑著說:「我看,中!燕嫂反正照管著燕青,再加個丫丫,就是再添一張小嘴吃飯嘛,能吃多少?至於銀子,我們本不當收,不過王寅兄弟要給,我們不收也不好不是?那就這樣,銀子我們就收下,權當給丫丫積攢著,日後給她當嫁妝就是。」
所謂當嫁妝,只是託詞而己,哪能當真?從這一天起,燕嫂就承擔起了餵養、照料丫丫的責任。丫丫還不能吃硬的食物,每天吃的主食,基本上是豆漿、豆花和豆腐。豆花是煮沸的豆漿,點鹽鹵或石膏水後形成的,很白很軟,最適宜嬰兒食用。豆花加少許糖,味道是甜的;加少許鹽、醬油、醋、香油、香菜,味道是鹹的;若再加少許辣椒油,那麼味道則鹹中帶點辣,很好吃。或許是豆漿、豆花和豆腐營養豐富的緣故,所以丫丫一歲多時白白胖胖,更像個瓷娃娃。丫丫會走路了,一顛一顛,跌跌撞撞。王寅送來一些花布。燕嫂縫製花衣花鞋,把丫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馬嫂從每月五兩銀子中取出五十緡錢給燕嫂,作為丫丫的日常花銷之用。王寅自從樊氏死後,生活沒有了規律,工作失去了心勁,作息時間亂了套,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有時整個白天都在睡覺。他很少生火做飯,肚子餓了,大多去飯肆買飯吃,飽吃一頓,然後常常一天或兩天不吃飯。有時拿個碗,向馬哥馬嫂要一碗豆漿一塊豆腐,也算一頓飯。渴了,沒有開水就喝涼水。他學會了喝酒,在飯肆喝,回到家裡還喝,醉時多醒時少,房裡到處都是空酒壜子和空酒瓶子。染坊經營江河日下,名存實亡。一次,一位老婦人前來染三件衣服,說定五天後取,可是五天後,三件衣服原封未動;再說定五天後取,可是五天後,三件衣服染錯顏色,將說定的藍色染成了黑色。老婦人不依不饒,非要藍色衣服不可。王寅被逼得賠了六件衣服的價錢,事情才算了結。老婦人罵罵咧咧,持錢而去,抬眼見懸掛的招牌,想起這是口碑不錯的王記便民染坊,遂朝招牌狠狠唾了一口,說:「呸!什麼便民染坊?該改作坑民染坊、騙民染坊才對!」王寅看得真切,聽得真切,氣惱不已,向前取下招牌,把它撕得粉碎。
西元九六○年農曆正月,後周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宋州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威逼後周皇帝柴宗訓遜位,自己登上皇帝寶座,改國號為宋(北宋),他就是宋太祖。宋代定都開封(今河南開封),開封因此稱東京,開始了一百六十多年夢幻般的崢嶸歲月。所謂「東京夢華」,正是它這一段崢嶸歲月的生動寫照。
開封地處中華腹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春秋時期,鄭莊公在開封附近修築儲糧的倉城,「啟拓封疆」,稱其地為啟封。西漢初為避漢景帝劉啟名諱,啟封更名為開封--這就是開封之名的由來。開封在戰國時曾稱大梁,是「七雄」之一魏國的都城。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郡縣制,大梁降為浚儀縣,隸屬於三川郡。北朝東魏設梁州,下轄陳留、開封、陽夏三郡。北周改梁州為汴州。因此,開封一稱汴、汴梁、汴都、汴京。汴河是開封的主要河流,連通黃河與淮河兩大水系。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中段就是因地制宜地利用了汴河,從而使開封成為南北交通線上的一個樞紐和要衝。唐代中期以後,藩鎮割據,汴州節度使李勉等構築汴州城,奠定了後世開封城的雛形。五代時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均定都開封,標誌著中國政治中心從長安、洛陽東移,具有里程碑意義。宋代東京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包括外城、內城、皇城三大部分,築有三重城郭,鑿有三道護城河。宮殿巍峨,坊市合一,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超過一百萬。史學家常用兩句話形容它的輝煌氣象:「八荒爭湊,萬國咸通。」
宋代東京行政區劃含一府一縣:府為開封府,下設廂、坊,居民主要為城市平民、工商業者和達官權貴;縣為祥符縣,下設鄉、村(里),居民主要為農民。宋哲宗趙熙在位期間,東京外城東二廂永慶坊一條狹長街道上,新開辦一家染坊,門前懸掛黃布黑字招牌,上寫大字:「王記便民染坊」。「王記」,表示染坊的主人姓王。沒錯,染坊的主人的確姓王,單名一個寅字。王寅,二十四五歲,中等身材,方臉寬額,濃眉大眼,胸前和胳膊上的肌肉隆起,身體強壯得像一頭牛。王寅老家原在祥符縣陀螺鎮,母親早已亡故,父親是個染匠,開設王記染坊,以染布染衣謀生。古代人多用棉、麻、葛等原料紡線織布,織出的布基本上是白色的。要把白布變成其他顏色,或把白布衣服變成其他顏色,主要靠染坊用顏料染作。因此,開染坊是很賺錢的,前提是染匠的技藝必須高超,染出的布、衣,色澤要鮮亮,而且要不掉顏色。王父一輩子都和顏料、染缸打交道,在實踐中摸索與累積,練就了一手過硬的染作技藝,在當地算是能人,每天都有收入,家境比較富裕並小有積蓄。
王寅自小在私塾讀過幾年書,可對之乎也哉、子云詩曰之類不感興趣,乾脆輟學,幫助父親經營染坊,也當了染匠。他很聰明,很快把父親的染作技藝全盤掌握,並有所發展,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他十八歲那年,娶了樊姓女子為妻,正式成家立業。樊氏比他小兩歲,身段苗條,肌膚白淨,那體態那容貌那神情,完全可以用一個「美」字來形容;而且性格溫柔,品德賢淑,侍奉丈夫,孝敬公公,那是絕對的好妻子好媳婦。
王記染坊經營得有模有樣,忽然一場大病,奪走了王父的性命。王父死前向兒子兒媳交代兩件事,算是遺囑:一是要把王記染坊開到繁華的京城去,那樣更有「錢」途;二是趕快生個孩子,以免絕了王家香火。王寅含淚,點頭答應,眼看著父親斷了氣。
王寅埋葬了王父,執行第一項遺囑。他把陀螺鎮的染坊及家產全部賣了,加上歷年來的積蓄,在東京外城購買了兩間門面房、一個小院落,開辦了王記便民染坊。王記染坊名稱中加進「便民」二字,顯示了王寅的智慧和精明。他的染坊要在京城立足並有所發展,除了靠染作品質做保證外,還要靠服務態度取勝,而便民正是服務態度的關鍵。
門面房用來承接活計。長長的櫃台,一頭擺放大大小小的瓷罐,瓷罐裡裝滿各種顏料;一頭擺放多種顏色的布料樣子,顧客染布染衣,指定其中任何一種顏色,王寅都能把它調製出來,並把布、衣染成那種顏色。他待客熱情,大到成匹成匹的布,小到一尺二尺的布或一條枕巾一方手帕,所有活計,全都承接,染價低廉,真正貫徹了便利民眾的宗旨。小院落裡有兩間草房,那是王寅夫婦的住所。草房前,壘起多個灶台,架起多口大鍋,那是染坊必備的器物。染坊的染作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先把染物放在清水中浸泡,至少半個時辰;顏料兌水,放在大鍋裡煮沸;把浸泡透了的染物,放進大鍋裡染色,不停地翻轉和攪動,切忌染色輕重不勻;顏料水和染物自然冷卻,將染物撈出,放到清水中再浸泡半個時辰。然後便是晾曬,使染物乾燥,整疊整齊。小院落裡,柴火熊熊,熱氣騰騰,那熱氣散發出顏料在水中煮沸後特有的香味;空中鐵絲縱橫,鐵絲上懸掛晾曬的染物,赤、橙、黃、綠、青、藍、紫、黑,五光十色,鮮豔絢麗。這構成了染坊獨具風情的特色景觀。
王記便民染坊右面緊挨著一家馬記豆腐店,豆腐店也有兩間門面房、幾間草房和一個小院落。主人馬達三十八歲,妻子燕氏二十八歲,人稱馬哥、馬嫂。不知什麼原因,馬嫂長期沒有生育,以致馬哥經常罵她是不下蛋的母雞。馬嫂一個遠房堂弟燕順,在東京當苦力,靠拉平板車給商家運送貨物賺錢,維持生計,住在一座破廟裡。燕順妻子季氏二十歲,身懷六甲已六七個月,住在破廟裡怎麼生孩子?馬嫂可憐堂弟夫婦,徵得丈夫同意,遂讓燕順兩口子,住進自家後院空著的兩間草房裡。燕順感激不盡,想到即將出世的孩子,起早貪黑替商家運貨,力圖多賺些錢。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這天,他沒吃食物,拉了滿滿一車貨物,走著走著,突然雙眼一黑,一頭栽倒在地上,口吐鮮血,瞬間一命嗚呼。
季氏獲知消息,哭得死去活來。馬哥馬嫂哀歎堂弟命薄,買了口薄棺將之埋葬。不久,季氏臨盆,生了個七斤重的胖小子,取名燕青。季氏已是個寡婦,覺得老住在堂姐堂姐夫家不像回事,意欲另外尋地方居住。馬嫂繼續可憐堂弟媳婦,說:「你們孤兒寡母,又能住到哪裡去?住到外面又靠什麼生活?豆腐店正缺人手,我看你不如留下來,幫著幹些雜事,如泡黃豆煮豆漿什麼的,總比像個沒頭的蒼蠅,亂撞一氣強不是?」季氏求之不得,熱淚盈眶,恨不得跪地叩頭,把堂姐叫觀音菩薩。從此,季氏也成了馬記豆腐店的一員,人稱燕嫂。王記便民染坊和馬記豆腐店兩個院落之間,沒有圍牆,只用竹竿編織的籬笆牆隔開。水井是共用的,就在籬笆牆的中段。兩家人沒幾天就混熟了,親親熱熱如一家人。馬嫂燕嫂染布染衣,王寅夫婦絕不收錢;同樣,王寅夫婦喝豆漿吃豆腐,馬哥馬嫂也絕不收錢。馬嫂身材胖些,燕嫂身材瘦些。王寅戲謔地叫一人為胖嫂,一人為瘦嫂。馬嫂和燕嫂爽快答應,毫不介意。這正應了一句俗話:遠親不如近鄰。
王寅執行父親第一項遺囑卓有成效,執行第二項遺囑也有收穫。就在王記便民染坊開張的第二年,樊氏懷孕了;第三年正月,樊氏分娩,生了個小巧玲瓏的女兒。女兒就女兒唄,王寅還是很高興很開心,隨口把女兒叫丫丫,抱她親她,愛不釋手。這一年是宋哲宗元祐八年(西元一○九三年)。宋哲宗是宋神宗趙頊的兒子,九歲登基,在皇位上已坐了八年多,后妃們卻還未生個龍子。皇帝沒有兒子,那會出現皇位危機。因此,很多人都在擔心、焦急著哪!
丫丫降生後發出的第一聲啼哭,在王寅和樊氏聽來,那是天外來音,是世界上最奇妙最美妙的音樂。丫丫與別的初生嬰兒不同,主要是皮膚潔白,晶瑩光潤,如玉如脂。兩天後,他睜開眼睛,雙眼皮,長睫毛,一對眸子又黑又亮,放射出寶石般的光芒,像是天上的星星。她開始吃母親的奶,櫻桃小口噙著乳頭,吮吸有力,吃得很貪婪很香甜。吃著吃著就睡著了,長睫毛合在一起,一副滿足、舒服的樣子,煞是好看。
王寅當了父親,高興開心,渾身上下都是勁。他讓樊氏靜靜躺著,只管餵養女兒,染坊的所有事情,獨自承擔起來。承接活計,擔水燒火,浸泡染物,配製染料,染布染衣,晾曬整疊,付貨收錢,忙得不可開交,真可謂是「眼睛一睜,忙到熄燈」。這樣,他樂意,他喜歡,臉上總是掛著笑,口中還哼著小曲兒。因為他有妻子有女兒,他要透過工作,讓她們母女過上優裕的生活。
王寅看丫丫,長得像她娘。三個月後,丫丫己顯露出美人胚子端倪。五官端正,比例和諧,組合成一個橢圓的面龐,完完美美,白白嫩嫩。小胳膊小腿,勻稱、靈巧,瓷質感很強,像個瓷娃娃。奇怪的是,丫丫自出生那天啼哭過一次外,其後再未啼哭過,好像不會啼哭似的。樊氏教她說話,讓喊爹喊娘。她呢?黑眸轉動,望這望那,就是不出聲。樊氏不由擔心起來:天哪!丫丫該不會是啞巴吧?
王寅說:「別胡說!你我的女兒,怎會是啞巴呢?」樊氏抱著丫丫,把自己的擔心告訴馬嫂和燕嫂。馬嫂和燕嫂寬慰說:「別急!瞧丫丫這樣靈氣,怎會是啞巴呢?嬰兒嘛,有的愛哭,有的不愛哭,有的發聲早,有的發聲遲。丫丫屬於不愛哭、發聲遲類型,再長大些,自會放聲啼哭和開口學話的。」燕嫂懷中抱著燕青。燕青見丫丫,伸手去抓她的小臉。樊氏擔心燕青會弄傷丫丫的眼睛,閃了閃身避開了。
丫丫半歲的時候,樊氏的重要任務,就是教女兒出聲、學話,指指點點,告訴她什麼是天,什麼是地,什麼是太陽,什麼是月亮,什麼是樹,什麼是花,什麼是小鳥,等等。王寅在院落裡工作,把染了色的布、衣從清水中撈出,展開,懸掛到鐵絲上晾曬,眼前頓時出現一個花花綠綠的彩色世界。樊氏告訴丫丫,這是布,這是衣服,這是紅色,這是黃色,這是藍色,這是紫色,這是綠色,這是黑色。丫丫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聽懂了,但抿著小嘴,就是不出聲。樊氏不禁嘆氣,說:「唉,這孩子,到底怎麼回事嘛?」
樊氏接著又發現,丫丫好像也不會笑,因為半歲多了,從未見她笑過。任你怎麼逗她,那怕撓她手心腳心,她也不笑。樊氏急得在房裡轉圈圈,連聲說:「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王寅也著急起來,說:「要不要請郎中瞧瞧?」
轉眼就到八月中秋節。樊氏說:「這樣:中秋節夜間,我們帶丫丫去州橋看水中月亮,對月許願,求月神嫦娥保佑她會哭會笑會說話。據說靈驗得很,許願凡有所求,都能實現。」王寅欣然同意。
汴河自西北向東南,橫貫東京城。汴河上共有十三座橋樑,其中州橋最為雄偉和壯觀。此橋正名叫天漢橋,位於皇城南面御街(一稱天街)中段,長約三十丈,寬約二丈,恰在東京城的中軸線上。站在橋頭,南望內城的朱雀門,北望皇城的宣德門,東、西望汴河水洶湧奔騰,視野開闊。橋墩、橋柱、橋樑、橋面皆為青石材料,橋欄上雕刻各種精美紋飾。橋墩、橋柱、橋樑、橋欄之間,皆用石榫連接,榫榫相扣,全橋形成一個牢固的整體。這裡是東京的中心地帶,橋上整日車水馬龍,行人熙攘。每月中旬,一輪明月倒映水中,月光融融,水光融融,天水一色,恍若仙境。美景總會發人遐想。於是便有人編出故事,說每月望日(十五日)夜間,月神嫦娥必到汴河沐浴,人若登上州橋觀月,對月許願,求妻求壽求子求女求官求財等,嫦娥都會答應。這樣一來,每月中旬夜間,登橋觀月、對月許願的人比平日裡多出數倍,望日夜間尤盛。中秋之夜,月懸中天,金風送爽。王寅、樊氏夫婦抱了丫丫,直奔州橋。到了州橋附近一看,但見汴河兩岸和御街兩邊,商鋪酒樓燈火通明,笙歌簫曲悠悠揚揚;橋南橋北,密密麻麻全是人,摩肩接踵,都想登橋,到橋中央去俯瞰水中皎月,並對月許願。王寅面對人山人海,有點發怵,說:「這麼多人?我看就別登橋了吧?」
樊氏一心想讓女兒哭女兒笑女兒說話,說:「既然來了,哪有不登橋之理?」
王寅一咬牙,說:「那好,我抱丫丫走前面,你緊跟著,到橋中央飛快地觀月許願,然後就往回走,中不?」「中」是東京一帶方言,就是「行」的意思。樊氏點頭說:「中!」
王寅和樊氏硬是擠進了湧動著的人流。擠進去了便後悔。因為人太多,人挨人人擠人,想轉個身都不可能。樊氏原是拉著丈夫上衣後襟的,哪知一擁擠,別人插到了她和丈夫中間。人流緩慢向前挪動,好不容易登上橋頭。橋上更加擁擠,南面的人要向北,北面的人要向南,各不相讓。更有一些流氓無賴,專門擠在人堆裡,抓摸大姑娘乳房和小媳婦屁股。大姑娘和小媳婦發出尖叫。流氓無賴附和著浪叫浪笑,樂不可支。王寅招呼樊氏說:「跟著我,別走散!」樊氏回應說:「沒事,你抱好丫丫!」
天宇澄澈,皓月如盤。人流挪動,聲音嘈雜。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王寅感覺到了橋的中央。明月正倒映在右側水面,人們都往右側擠,在那裡憑欄觀月,最為清晰。王寅懷抱丫丫,只向右側水面看了看,根本沒看到水中月亮,就被人擠到左側,當然也就沒顧上許願。樊氏非常英勇,拼命往右側擠,伸手抓住橫著的橋欄,憑欄俯看水面,只見一輪又大又圓的明月,倒映在水中,搖搖晃晃,玉光閃閃。樊氏認定,那是嫦娥秀美的面龐,忙雙手合什作揖,虔誠地說:「求求嫦娥,保佑我們家丫丫會哭會笑會說話!」她唯恐嫦娥沒有聽清,又把願語重複兩遍。這時,很多人都向右側擠,向橋欄擠。猛聽得「嚓」、「咚」兩聲巨響,右側那一段橫著的橋欄脫榫,掉落河中。王寅看得清楚,包括樊氏在內的二三十人,同時掉落河中。
有人高聲喊道:「橋欄脫榫啦!大橋可能垮坍呀!快跑呀快跑呀!」喊聲尖銳刺耳。橋中央的人出於本能,驚慌失措,分別向橋的兩頭跑。橋頭的人不明底細,仍向橋中央擠。人流與人流相撞,有人惡語相加,有人動起拳腳,有人摔倒,有人被踩掉了鞋,喊聲哭聲謾罵聲,亂成一鍋粥。王寅很想跳河去救樊氏,可丫丫在懷,哪裡能夠?他是隨著人流「流」到岸上的,到了岸上,方才有機會朝下游水中大喊:「樊氏,樊氏!」
汴河水流湍瀧,泛著銀白色浪花,一路東去。王寅沿著河堤向東跑,依然大喊:「樊氏,樊氏!」回答他的,只是嘩嘩的流水聲。他一時不知該做什麼,拔腿往家的方向跑。他顧不上回自己的家,而是狠敲馬哥馬嫂家的門。馬哥馬嫂被驚醒了,燕嫂也被驚醒了。馬哥披衣,打著哈欠,詢問誰在敲門,聽出是王寅的聲音,忙將門打開。王寅懷抱丫丫進門,撲通跪地,拖著哭腔說:「馬哥,樊氏掉進汴河啦!」
馬哥仍打著哈欠,沒聽明白是什麼意思。馬嫂已經起床,忙向前問:「你說什麼?」
「我和樊氏帶著丫丫,去州橋觀月許願,人太多,丫丫她娘,掉,掉進汴河了。」王寅說。
「那你該跳河救她呀!」馬嫂說。
「我懷中還抱著丫丫呀!」王寅說。
燕嫂也起床了,見王寅抱著丫丫,伸手接過,說:「把丫丫給我。」燕嫂看丫丫,長長的睫毛覆蓋著眼睛,小嘴半張,呼吸均勻,睡得很熟很香。
馬哥算是聽明白了,忙穿衣穿鞋,取了一根長竹竿,對王寅說:「快走,我陪你去瞧瞧!」
馬哥和王寅去了州橋。時間已過午夜子時。馬嫂沒好氣地說:「觀月?許願?觀出許出禍事了不是?」
燕嫂說:「丫丫這樣子,王寅樊氏也是病急亂投醫。」馬嫂搖頭說:「樊氏,一個女人,掉進汴河,只怕是凶多吉少。」燕嫂身上打了個冷顫,把熟睡的丫丫抱得更緊些。她想,可憐的丫丫,還不滿周歲,難道就要失去娘麼?
燕嫂把丫丫抱回自己所住的草房。燕青側躺在炕上,睡得正香。燕嫂不管燕青,且管丫丫,取來溫水,給她洗了臉洗了手洗了腳,把她放到炕的最裡面,讓她繼續睡覺。燕嫂靠著炕頭,看著丫丫,毫無睡意。她暗暗向上蒼祈禱,但願樊氏能平平安安歸來,一個嬰兒,寧可沒有爹也不可沒有娘啊!五更時分,馬嫂和燕嫂同時起來,開始勞作做豆腐。第一步是磨黃豆,給小毛驢駕套,蒙上眼罩,讓它拉著石磨轉動。黃豆是頭天浸泡的,脹得很大,加水經石磨碾壓,變成潔白的乳狀物,流在磨槽裡,再由一個小孔,流進木桶裡。第二步是生火煮漿,將乳狀物過濾,去掉豆渣,放進大鍋煮沸,那便是可飲用的豆漿了。第三步,將豆漿轉移至缸裡,點進適量的鹽鹵或石膏水,豆漿呈現出凝固的狀態。把這樣的豆漿迅速用包布包起來,包成四方形,平放在木板上,上面亦放木板,壓上石頭等重物,擠掉包布裡的一些水分。這樣,包布裡的豆漿就成了豆腐,白白嫩嫩,味美可口。豆腐店做豆腐,數量多少用板衡量,一個包布的豆腐稱一板,二尺五寸見方,約三寸厚。馬哥馬嫂原先每天做十板豆腐,自從燕嫂這個廉價勞力加入後,他們每天做十五板豆腐。生產數量增加百分之五十,意味著銷售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年多來,豆腐店賺錢可是不少啊!
燕嫂在磨黃豆、煮豆漿時,回了幾次草房。炕上睡著燕青、丫丫兩個小孩,她不放心,生怕小孩跌到地上。她第五次回草房時,發現丫丫醒了,不哭不鬧,眼睛黑亮,這邊瞧瞧,那邊瞧瞧。她抱起丫丫,端了一泡尿。丫丫把一個手指放在小嘴裡吮吸,顯然是餓了。燕嫂忙去盛了半碗豆漿,晾涼,用小勺餵她。她一直吃她娘的奶,改吃豆漿,竟也吃得津津有味。豆腐做成了。燕嫂又切了半塊豆腐,用小勺餵她。她吃豆腐,同樣吃得津津有味,還用小手抓碗裡的豆腐,往嘴裡送,弄得滿手滿嘴都是豆腐,讓人感到好笑和心疼。
燕青也睡醒了,看到丫丫,奇怪地問:「娘,丫丫怎會在我們家?」燕嫂說:「你王寅叔和樊氏嬸子有事,把丫丫放我們家,讓娘幫著照看一會兒。」丫丫見燕青,眼睛更亮,伸開雙手,好像是要讓燕青抱。燕青才四歲,抱不了她,伸手把丫丫小手拉了拉,說:「丫丫,你快長大,我和你一起玩!」
中午,馬哥和王寅回來了,從二人疲倦、無奈的神情中可以斷定,樊氏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馬嫂還是問:「怎樣?」馬哥搖頭,說:「一個女人,夜間掉進汴河,哪還能活?我們從州橋往下游找,找了快二十里,看到多具屍體,卻未見樊氏屍體。人們都說,水流那樣急,屍體怕是早沖到三四十里開外了,哪裡找去?再說,找到屍體又能怎樣?人死不能復生。所以,我們就回來了。」說罷,他重重歎了口氣:「唉!」一夜又半天光景,王寅像變了個人似的,耷拉著腦袋,目光呆滯,懊惱,萎靡,悲傷。燕嫂把丫丫抱來,遞給他。他直勾勾地看著女兒,眼中滾落豆大的淚珠。他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怎麼管得了才八個多月的嬰兒?他想了想,突然跪地,說:「燕嫂,我現在走投無路,只能把丫丫交給你了,求你餵養她照料她,我每月付給五兩銀子。」
燕嫂沒想到會出現這種情況,忙說:「我可以幫你餵養、照料丫丫,但不能要你的銀子。我和燕青,幸虧馬哥馬嫂收留,才有安身之地。你若給銀子,就給馬哥馬嫂吧!」
王寅回頭看馬哥馬嫂。馬哥說:「鄰里之間,互相幫襯嘛,什麼銀子不銀子的?」馬嫂覺得每月五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忙笑著說:「我看,中!燕嫂反正照管著燕青,再加個丫丫,就是再添一張小嘴吃飯嘛,能吃多少?至於銀子,我們本不當收,不過王寅兄弟要給,我們不收也不好不是?那就這樣,銀子我們就收下,權當給丫丫積攢著,日後給她當嫁妝就是。」
所謂當嫁妝,只是託詞而己,哪能當真?從這一天起,燕嫂就承擔起了餵養、照料丫丫的責任。丫丫還不能吃硬的食物,每天吃的主食,基本上是豆漿、豆花和豆腐。豆花是煮沸的豆漿,點鹽鹵或石膏水後形成的,很白很軟,最適宜嬰兒食用。豆花加少許糖,味道是甜的;加少許鹽、醬油、醋、香油、香菜,味道是鹹的;若再加少許辣椒油,那麼味道則鹹中帶點辣,很好吃。或許是豆漿、豆花和豆腐營養豐富的緣故,所以丫丫一歲多時白白胖胖,更像個瓷娃娃。丫丫會走路了,一顛一顛,跌跌撞撞。王寅送來一些花布。燕嫂縫製花衣花鞋,把丫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馬嫂從每月五兩銀子中取出五十緡錢給燕嫂,作為丫丫的日常花銷之用。王寅自從樊氏死後,生活沒有了規律,工作失去了心勁,作息時間亂了套,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有時整個白天都在睡覺。他很少生火做飯,肚子餓了,大多去飯肆買飯吃,飽吃一頓,然後常常一天或兩天不吃飯。有時拿個碗,向馬哥馬嫂要一碗豆漿一塊豆腐,也算一頓飯。渴了,沒有開水就喝涼水。他學會了喝酒,在飯肆喝,回到家裡還喝,醉時多醒時少,房裡到處都是空酒壜子和空酒瓶子。染坊經營江河日下,名存實亡。一次,一位老婦人前來染三件衣服,說定五天後取,可是五天後,三件衣服原封未動;再說定五天後取,可是五天後,三件衣服染錯顏色,將說定的藍色染成了黑色。老婦人不依不饒,非要藍色衣服不可。王寅被逼得賠了六件衣服的價錢,事情才算了結。老婦人罵罵咧咧,持錢而去,抬眼見懸掛的招牌,想起這是口碑不錯的王記便民染坊,遂朝招牌狠狠唾了一口,說:「呸!什麼便民染坊?該改作坑民染坊、騙民染坊才對!」王寅看得真切,聽得真切,氣惱不已,向前取下招牌,把它撕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