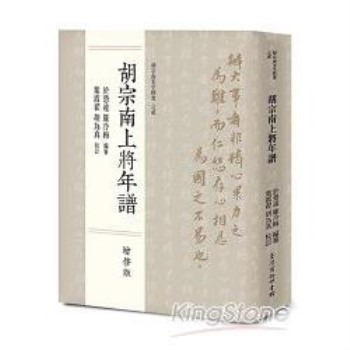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丁丑,西曆一九三七年,公四二歲。
一、公率全軍移駐徐州、歸德間,調整人事,積極作抗日訓練。
雙十二事變解決,公命所部分駐平涼、涇川、靜甯各縣就食,並作短期訓練,四月間奉命東移,五月,全軍抵達徐州,軍部及第一師駐徐州近郊,七十八師駐歸德,兼負津浦、隴海兩路警備任務。西北補充旅,仍開駐蘭州,歸綏署主任朱公紹良節制指揮。
上年第一師擴編為軍,公仍兼任第一師師長,編配未竟,奉命入甘剿共,故未成立軍部,仍就第一師師部原編制為軍部指揮機構,至徐州後,公辭去第一師師長兼職,由李鐵軍繼任,第一旅旅長李正先升副師長,旅長由劉超寰升任。第二旅旅長詹忠言調任為師參謀長,由曹日暉升任旅長,于時團長則為王應尊、楊傑、陳鞠旅、李友梅。七十八師師長丁德隆亦調任,由李文升任師長,副師長仍為羅歷戎、參謀長吳允周,周士冕繼廖昂為二三二旅旅長,李用章仍為二三四旅旅長,團長則為許良玉、謝義鋒、文于一、徐保。第一軍軍部成立後,副軍長為范漢傑,參謀長於達,副參謀長羅列,參謀處長胡長青,副官處長袁杰三,軍需處長蔡翊祺,後改潘廷俊,特別黨部書記長沈上達。
公所部自二十一年秋,追匪徐向前入甘,除二十四年川西剿共,二十五年短期入湘外,在陜、甘達四年之久,公嘗以不得參與淞滬、長城作戰為憾!至徐州後,官兵習聞日本侵我種種暴行,極為憤慨,對宋哲元冀察中立化,尤為憎惡,敵愾心特強。公念中日必出於一戰,而所部頻年剿共,對日作戰,尚乏經驗,乃接受七十八師參謀長吳允周建議,舉辦軍官短期訓練,聘請陸軍大學教官馮龍、曾繼遠等四人,及步兵學校教官四人,自旅、團長至軍士,分別編隊實施戰術戰鬥等研練,以團對抗之實兵演習,為測定訓練之成效,歷時二月餘,全軍訓練完成,遂奠定抗日作戰之基礎。另五月間蔣委員長特召公參加統一國內各派系軍官愛國思想的暑訓籌備工作。(見蔣公五月十四日日記)
二、滬戰發生,公奉命率全軍赴淞滬抗日,苦戰三月餘。
日本軍閥七月七日在蘆溝橋挑釁,侵略我國,八月十四日又侵我上海,全國軍民乃在委員長蔣公指揮之下奮起抗戰。
公奉命率第一軍參加淞滬抗戰,軍部第一師由師長李鐵軍率領,八月三十日由徐州出發,七十八師由師長李文率領,在歸德上車。
日軍當時有鑒於上海閘北、虹口戰事在市區內進行,各國租界林立,大兵團無法運用自如,且敵我均據守高樓大廈,憑險固守,勢將曠日持久,對其不利,乃另調其本土精銳,改由寶山登陸,挾其現代化武器,及陸海空優勢,以戰車為先導,使用突破迂迴攻擊等戰法,擬將我國軍主力,誘集於野戰方面,一舉擊滅後,再向左迴旋,席捲我大上海,達其速戰速決的目的。
當時委員長命令指定全軍在無錫集中,適逢寶山楊步飛六十一師潰敗,夏楚中軍危急,我第一師至無錫,尚未下車,即由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將軍令改東開,就寶山增援。至則夏楚中陣地已失,第一師遂奮勇應戰。
當時日軍以擊破中央嫡系部隊為目標,其主攻方向乃第一軍及陳誠之第十八軍。
九月二日以後,七十八師各旅亦陸續投入戰爭,在毫無工事掩蔽之下,遭日寇陸砲及空軍轟炸,苦戰五晝夜,雖官兵血肉橫飛,而寸土必爭,愈戰愈勇;尤其在顧家鎮之線,第二團團長楊傑、第四團團長李友梅先後陣亡,負傷者尤眾。
九月四日夜奉命移守楊行至羅店之線,旋又轉進劉行,續苦戰半月之久,方調至崑山整補。時淞滬陣地寶山為一線,楊行、羅店為一線,張家樓、大場又為一線,蘊藻濱、北新涇等地屬之。九月中旬,公所部編為第十七軍團,公升任軍團長,羅列任軍團部參謀長,仍就第一軍軍部為指揮機構。由於部隊傷亡太大,在劉行時,曾補充陜兵二千一百人。十月上旬,公又奉命率部守大場,並增援蘊藻濱。第一師團長吳俊率兵四連,與敵激戰,毀敵戰車六輛,排列於我陣地前之敵戰車,不敢衝入我軍陣地,我右翼湘省部隊、左翼廣東部隊,均潰離陣地,我軍與敵軍白刃交鋒,雖受傷而堅守不移。
自蘊藻濱、楊行、顧家鎮、至蘇州河,直徑不過三十里線上,敵我相持三個月,敵軍雖一再增援,仍無法擊退我第一軍。三月亡華之狂語,已成泡影。
公原奉命守蘊藻濱七天,以待後方部署完成,公以殘部和新補之兵,堅守至四十二天。蘇州河之役,雖左右翼友軍退 ,而第一軍兩師陣地,屹立未動,且分兵攔擊,阻敵強渡,以待援軍之至。日寇不得逞,乃自杭州灣北面金山衛登陸,直趨大倉,企圖遮斷我在滬數十萬大軍之歸路。
自日寇發動滬戰以來,以艦砲、飛機日夜轟擊,有時佐以水陸戰車,我軍之守禦者,皆臨時四方調集,對防空防戰車之戰術,講求未深;而滬濱地勢低下多水,工事亦難完固,官兵類以血肉之軀與敵搏擊。公所部經徐州訓練,較勝於他部,而公日夜在戰場指揮巡撫,從未離去,雖經常僅以自行車在戰壕中往來指揮,然官兵見之,無不感奮。後白崇禧總指揮向第三戰區何應欽司令長官報告有云:「桂軍十個師只打一天,只有第一軍能打,該軍兩個師陣地,始終屹立不動。」其時,公亦獲黃杰稅警團八一迫擊砲之助,使日寇無法突進也。
當時中央盱衡全局,以上海抗敵爭取時間及獲得國際同情的目的已達,為長期抗日,決定自動作戰略轉進。十一月八日公交防於桂軍廖磊,奉命開後方整備,旋又改命守蘇州河,苦戰半月後,方奉命撤退,由李玉堂、俞濟時兩部掩護。時軍部正在轉進中,忽遭受溯蘇州河而上之日寇水上挺進隊襲擊,略受損失,特別黨部書記長沈上達溺斃。公至崑山停留一天,收容後撤部隊。至此,公所統率十六個團(約四萬人),苦戰三月餘,補充數次,其中團營長以上負傷前仆後補,多至一百數十人,連排長幾無倖存者。據公日記記載,最後撤退時,「只剩勤務衛士司書書記軍需輸送兵、飼養兵等一千二三百人。」(見《胡宗南先生文存》)
【按:李友梅:廣東五華人軍校四期。歷任連營長,以精悍善戰著稱,在顧家鎮反攻時,身
先士卒,中彈殉職。楊傑:河北省人軍校四期,和平穩練,勤於職守,苦戰陣亡。
沈上達:浙江孝豐人,特別黨部書記長,曾為記者,長於社論文學。蘇州河之役,遭敵挺進
隊襲擾跳河溺斃,後援陣亡例贈恤少將。】
三、公率部續戰於無錫、浦口、滁州各地,旋奉命由皖、豫進駐關中。
公率部十一月十六日至無錫,歸上官雲相指揮,補充新兵一個團,部署初定,而日軍坦克部隊已跟踵追至,步兵繼之,公又率部戰於無錫、常州間,第一旅旅長劉超寰負傷,七十八師李文所部,在無錫苦戰三晝夜,方將敵人拒止。二十日奉命在鎮江渡江,至揚州整理一週,補充新兵三個團,至此,各部稍見充實矣。
【按:公十一月二十日致電戴雨農云:弟刻又在無錫進入陣地矣,此次前方撤退各軍,秩序
紀律毫無。官無鬥志,士多傷亡,吳福線尚不能守,澄錫線更無論矣,黃埔部隊多已打完,
無人撐持,其餘當然望風而潰矣。第二期革命已失敗,吾人必須努力,培養第三期革命幹部
來完成未來之使命也。】
十二月二日公奉召赴京,初命守南京,將畀以南京衛戍副司令,為唐生智之副,令未下,寇已沿江北岸進犯,又命仍回浦口督戰。五日公至浦口,日寇已攻南京,十日分兵掠浦口,公率部擊卻之。十二日首都陷落,十六日奉命在滁州布防,守一週,在滁北白米山擊退來犯之日軍。迄十二月下旬奉命西進,年底至壽州,以後經阜陽、固始、潢川至信陽待命。未幾,調公部駐守關中,於是在信陽整理後率部入陜。
四、公為爭取陷區青年,沿途收容流亡學生千餘人,挈之西行。
公素重視愛護青年,念陷區學生青年決不願從敵從共,供其利用;第交通艱阻,無以自達革命抗戰之地,或有不得已而從敵從共者,公因電邀湖南青年陳大勳等至滬囑其負責組織戰地青年,二十五年夏公駐軍長沙時,湖南教育廳長朱經農先生曾推介各校有領導才能優秀青年江國棟、陳大勳、彭書隱等二十餘人相見,公曾有「有一天抗日戰爭發生,我一定邀你們參加第一線;並希望青年們投筆報國」,至是招之來滬,遂在上海蘇州等地動員一批青年與學校童子軍,成立抗日宣傳隊。後又在湖南組織一青年服務團二百餘人,由李芳蘭、洪同、陳大勳等率領。時共黨已在延安成立「抗日大學」,分遣黨羽四出宣傳,招致青年,頗有受其熒惑者,青年服務團得預備第七師師長曹日暉、政治部主任汪震之助,至信陽會合。在滁州時,曾收容當地青年,組織隨軍服務團,其後在途中又收容徐州中學教員趙觀濤率領四百餘人,壽州又遇安徽童子軍教練官徐康民率領之流亡學生五百餘人,公皆優禮收容,隨軍西進,實為次年成立軍分校與戰幹團之基礎。
五、是年,十二月九日,公父際清先生棄養,壽州軍次聞耗,公至漢口請假奔喪未准。
公在軍日,每年皆乞假歸省,留家一、二日而已,自淞滬戰起,家報亦斷,際清先生遂於是年十二月九日病逝里第,公在壽州方得家報,已踰兩旬矣。公至漢口,乃請假奔喪,奉委員長手諭:「孝豐陷落,道途阻塞,毋庸冒險回籍奔喪!」遂不果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西曆一九三八年,公四三歲。
一、公率部移駐關中,安定關隴,屏蔽川蜀。
公部自本年元月初到達信陽附近,時政府初遷武漢,原擬令公移駐武漢外圍,整理訓練,準備將來保衛武漢之作戰,而西安行營顧祝同主任以為關隴居川蜀上游,第十戰區部隊皆新編成,戰力薄弱,如日寇由晉竄入關中;或共黨居心叵測,乘虛南下,皆足動搖抗戰基礎,以公久駐秦隴,尤為共軍所畏憚,人地最宜,乃建議政府令公統十七軍團所部移駐關中,固守河防,兼顧晉隴,屏蔽川蜀。於是公奉命率第一軍暨胡長青、胡受謙兩補充團,自信陽經南陽逐步西移,入陜後公率僚屬與千餘流亡學生進駐鳳翔,以東湖少數房屋為司令部,中央並派公為隴海路警備司令,公辭未就。
二、公健全幕僚機構,組織軍團司令部。
初公在上海作戰,奉升為第十七軍團軍團長,戰鬥正劇,未嘗另組軍團司令部,僅報請調升羅列為軍團參謀長以為助,移駐關中後,公解除第一軍軍長兼職,由第一師師長李鐵軍升任,而令指揮友軍部隊固守鄭州 靈寶之線,公乃在鳳翔另組軍團部,參謀長羅列、副官處長袁杰三、參謀處長傅維潘、軍需處長蔡翊祺、軍法處長洪友蘭、機要組長王育,軍團部初駐鳳翔東湖,後移西安永寧門外薦福禪寺,即俗稱小雁塔者。公初住西安建國公園,後移住東倉門之下馬陵董子祠,乃漢董仲舒墓前祠屋也。屋僅三間,中有塑像,以紙壁障之為會客進膳之所。公居東頭屋,簡陋殊甚,是年冬乃始賃陵夏新華君房屋會客辦公。(註:夏新華為優秀青年軍官科技人才,任公之侍從參謀多年,忠心耿耿,處事精細,晚年定居美國,仍多次撰文懷念公之生平。)
三、公請於中央成立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招收陷區各省青年,訓練軍事幹部。
自淞滬抗日作戰後,軍中幹部之犧牲極大。第一軍連排長存者不及什一,他部當亦相同。公念抗戰將為長期戰爭,軍政幹部必須大量培育,以資補充。去年在無錫時已有此意,自至關中沿途已收容青年一千餘人,亟須先予訓練,於是請於委座奉准在西安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公乃派羅列、吳允周、羅歷戎、袁杰三、張研田、洪軌等六人為建校籌備委員,先借鳳翔師範為校址,至五月始移西安南部四十里之王曲。學生先考選去年收錄之千餘青年,繼又奉令接收康澤在王曲所辦之特種訓練班,顧希平終南山麓之江蘇抗日青年,編為第十五期第二總隊,李正先為總隊長,同時在冀魯豫等地招錄陷區學生數千名,成立第十五期三四五各總隊。自分校成立,中央軍校校務委員會延公為分校主任,顧希平為副主任,曾擴情為政治部主任,後為王超凡,曾乃調辦公處處長,吳允周為教育處長,袁杰三為總務處長,汪維恆為經理處長、趙立為軍醫處長,隊職官大部由部隊中副職調充,主任教官有張研田、余紀忠、洪軌、張大同、徐直民、淦克超、蕭思滋、林文淵等,政治教官有崔垂言、周天僇、李潤沂、張光祖等,余紀忠以政治部副主任兼主持王曲雜誌等編纂出版事宜,公經常駐宿王曲興隆嶺,主持校務。興隆嶺距王曲校本部約半里,張學良任西北剿共副總司令時所建之別業,有屋數間而已。自滬戰後,無線電通訊人員奇缺,公命在鳳翔設班訓練為第四期,適前無線電管理主任王微回陜,任四十六師軍需主任,公遂命兼任班主任,後併入七分校第二總隊。杭州中央警官學校校長趙龍文,抗戰事起,率部游擊,曾選送浙江青年四百餘人,公為爭取陷區青年,乃先後成立江浙皖鄂贛湘各地招生總隊,為成立第十六期之準備,陷區青年,聞訊亦多有遠道跋涉,自來投考者。
一、公率全軍移駐徐州、歸德間,調整人事,積極作抗日訓練。
雙十二事變解決,公命所部分駐平涼、涇川、靜甯各縣就食,並作短期訓練,四月間奉命東移,五月,全軍抵達徐州,軍部及第一師駐徐州近郊,七十八師駐歸德,兼負津浦、隴海兩路警備任務。西北補充旅,仍開駐蘭州,歸綏署主任朱公紹良節制指揮。
上年第一師擴編為軍,公仍兼任第一師師長,編配未竟,奉命入甘剿共,故未成立軍部,仍就第一師師部原編制為軍部指揮機構,至徐州後,公辭去第一師師長兼職,由李鐵軍繼任,第一旅旅長李正先升副師長,旅長由劉超寰升任。第二旅旅長詹忠言調任為師參謀長,由曹日暉升任旅長,于時團長則為王應尊、楊傑、陳鞠旅、李友梅。七十八師師長丁德隆亦調任,由李文升任師長,副師長仍為羅歷戎、參謀長吳允周,周士冕繼廖昂為二三二旅旅長,李用章仍為二三四旅旅長,團長則為許良玉、謝義鋒、文于一、徐保。第一軍軍部成立後,副軍長為范漢傑,參謀長於達,副參謀長羅列,參謀處長胡長青,副官處長袁杰三,軍需處長蔡翊祺,後改潘廷俊,特別黨部書記長沈上達。
公所部自二十一年秋,追匪徐向前入甘,除二十四年川西剿共,二十五年短期入湘外,在陜、甘達四年之久,公嘗以不得參與淞滬、長城作戰為憾!至徐州後,官兵習聞日本侵我種種暴行,極為憤慨,對宋哲元冀察中立化,尤為憎惡,敵愾心特強。公念中日必出於一戰,而所部頻年剿共,對日作戰,尚乏經驗,乃接受七十八師參謀長吳允周建議,舉辦軍官短期訓練,聘請陸軍大學教官馮龍、曾繼遠等四人,及步兵學校教官四人,自旅、團長至軍士,分別編隊實施戰術戰鬥等研練,以團對抗之實兵演習,為測定訓練之成效,歷時二月餘,全軍訓練完成,遂奠定抗日作戰之基礎。另五月間蔣委員長特召公參加統一國內各派系軍官愛國思想的暑訓籌備工作。(見蔣公五月十四日日記)
二、滬戰發生,公奉命率全軍赴淞滬抗日,苦戰三月餘。
日本軍閥七月七日在蘆溝橋挑釁,侵略我國,八月十四日又侵我上海,全國軍民乃在委員長蔣公指揮之下奮起抗戰。
公奉命率第一軍參加淞滬抗戰,軍部第一師由師長李鐵軍率領,八月三十日由徐州出發,七十八師由師長李文率領,在歸德上車。
日軍當時有鑒於上海閘北、虹口戰事在市區內進行,各國租界林立,大兵團無法運用自如,且敵我均據守高樓大廈,憑險固守,勢將曠日持久,對其不利,乃另調其本土精銳,改由寶山登陸,挾其現代化武器,及陸海空優勢,以戰車為先導,使用突破迂迴攻擊等戰法,擬將我國軍主力,誘集於野戰方面,一舉擊滅後,再向左迴旋,席捲我大上海,達其速戰速決的目的。
當時委員長命令指定全軍在無錫集中,適逢寶山楊步飛六十一師潰敗,夏楚中軍危急,我第一師至無錫,尚未下車,即由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將軍令改東開,就寶山增援。至則夏楚中陣地已失,第一師遂奮勇應戰。
當時日軍以擊破中央嫡系部隊為目標,其主攻方向乃第一軍及陳誠之第十八軍。
九月二日以後,七十八師各旅亦陸續投入戰爭,在毫無工事掩蔽之下,遭日寇陸砲及空軍轟炸,苦戰五晝夜,雖官兵血肉橫飛,而寸土必爭,愈戰愈勇;尤其在顧家鎮之線,第二團團長楊傑、第四團團長李友梅先後陣亡,負傷者尤眾。
九月四日夜奉命移守楊行至羅店之線,旋又轉進劉行,續苦戰半月之久,方調至崑山整補。時淞滬陣地寶山為一線,楊行、羅店為一線,張家樓、大場又為一線,蘊藻濱、北新涇等地屬之。九月中旬,公所部編為第十七軍團,公升任軍團長,羅列任軍團部參謀長,仍就第一軍軍部為指揮機構。由於部隊傷亡太大,在劉行時,曾補充陜兵二千一百人。十月上旬,公又奉命率部守大場,並增援蘊藻濱。第一師團長吳俊率兵四連,與敵激戰,毀敵戰車六輛,排列於我陣地前之敵戰車,不敢衝入我軍陣地,我右翼湘省部隊、左翼廣東部隊,均潰離陣地,我軍與敵軍白刃交鋒,雖受傷而堅守不移。
自蘊藻濱、楊行、顧家鎮、至蘇州河,直徑不過三十里線上,敵我相持三個月,敵軍雖一再增援,仍無法擊退我第一軍。三月亡華之狂語,已成泡影。
公原奉命守蘊藻濱七天,以待後方部署完成,公以殘部和新補之兵,堅守至四十二天。蘇州河之役,雖左右翼友軍退 ,而第一軍兩師陣地,屹立未動,且分兵攔擊,阻敵強渡,以待援軍之至。日寇不得逞,乃自杭州灣北面金山衛登陸,直趨大倉,企圖遮斷我在滬數十萬大軍之歸路。
自日寇發動滬戰以來,以艦砲、飛機日夜轟擊,有時佐以水陸戰車,我軍之守禦者,皆臨時四方調集,對防空防戰車之戰術,講求未深;而滬濱地勢低下多水,工事亦難完固,官兵類以血肉之軀與敵搏擊。公所部經徐州訓練,較勝於他部,而公日夜在戰場指揮巡撫,從未離去,雖經常僅以自行車在戰壕中往來指揮,然官兵見之,無不感奮。後白崇禧總指揮向第三戰區何應欽司令長官報告有云:「桂軍十個師只打一天,只有第一軍能打,該軍兩個師陣地,始終屹立不動。」其時,公亦獲黃杰稅警團八一迫擊砲之助,使日寇無法突進也。
當時中央盱衡全局,以上海抗敵爭取時間及獲得國際同情的目的已達,為長期抗日,決定自動作戰略轉進。十一月八日公交防於桂軍廖磊,奉命開後方整備,旋又改命守蘇州河,苦戰半月後,方奉命撤退,由李玉堂、俞濟時兩部掩護。時軍部正在轉進中,忽遭受溯蘇州河而上之日寇水上挺進隊襲擊,略受損失,特別黨部書記長沈上達溺斃。公至崑山停留一天,收容後撤部隊。至此,公所統率十六個團(約四萬人),苦戰三月餘,補充數次,其中團營長以上負傷前仆後補,多至一百數十人,連排長幾無倖存者。據公日記記載,最後撤退時,「只剩勤務衛士司書書記軍需輸送兵、飼養兵等一千二三百人。」(見《胡宗南先生文存》)
【按:李友梅:廣東五華人軍校四期。歷任連營長,以精悍善戰著稱,在顧家鎮反攻時,身
先士卒,中彈殉職。楊傑:河北省人軍校四期,和平穩練,勤於職守,苦戰陣亡。
沈上達:浙江孝豐人,特別黨部書記長,曾為記者,長於社論文學。蘇州河之役,遭敵挺進
隊襲擾跳河溺斃,後援陣亡例贈恤少將。】
三、公率部續戰於無錫、浦口、滁州各地,旋奉命由皖、豫進駐關中。
公率部十一月十六日至無錫,歸上官雲相指揮,補充新兵一個團,部署初定,而日軍坦克部隊已跟踵追至,步兵繼之,公又率部戰於無錫、常州間,第一旅旅長劉超寰負傷,七十八師李文所部,在無錫苦戰三晝夜,方將敵人拒止。二十日奉命在鎮江渡江,至揚州整理一週,補充新兵三個團,至此,各部稍見充實矣。
【按:公十一月二十日致電戴雨農云:弟刻又在無錫進入陣地矣,此次前方撤退各軍,秩序
紀律毫無。官無鬥志,士多傷亡,吳福線尚不能守,澄錫線更無論矣,黃埔部隊多已打完,
無人撐持,其餘當然望風而潰矣。第二期革命已失敗,吾人必須努力,培養第三期革命幹部
來完成未來之使命也。】
十二月二日公奉召赴京,初命守南京,將畀以南京衛戍副司令,為唐生智之副,令未下,寇已沿江北岸進犯,又命仍回浦口督戰。五日公至浦口,日寇已攻南京,十日分兵掠浦口,公率部擊卻之。十二日首都陷落,十六日奉命在滁州布防,守一週,在滁北白米山擊退來犯之日軍。迄十二月下旬奉命西進,年底至壽州,以後經阜陽、固始、潢川至信陽待命。未幾,調公部駐守關中,於是在信陽整理後率部入陜。
四、公為爭取陷區青年,沿途收容流亡學生千餘人,挈之西行。
公素重視愛護青年,念陷區學生青年決不願從敵從共,供其利用;第交通艱阻,無以自達革命抗戰之地,或有不得已而從敵從共者,公因電邀湖南青年陳大勳等至滬囑其負責組織戰地青年,二十五年夏公駐軍長沙時,湖南教育廳長朱經農先生曾推介各校有領導才能優秀青年江國棟、陳大勳、彭書隱等二十餘人相見,公曾有「有一天抗日戰爭發生,我一定邀你們參加第一線;並希望青年們投筆報國」,至是招之來滬,遂在上海蘇州等地動員一批青年與學校童子軍,成立抗日宣傳隊。後又在湖南組織一青年服務團二百餘人,由李芳蘭、洪同、陳大勳等率領。時共黨已在延安成立「抗日大學」,分遣黨羽四出宣傳,招致青年,頗有受其熒惑者,青年服務團得預備第七師師長曹日暉、政治部主任汪震之助,至信陽會合。在滁州時,曾收容當地青年,組織隨軍服務團,其後在途中又收容徐州中學教員趙觀濤率領四百餘人,壽州又遇安徽童子軍教練官徐康民率領之流亡學生五百餘人,公皆優禮收容,隨軍西進,實為次年成立軍分校與戰幹團之基礎。
五、是年,十二月九日,公父際清先生棄養,壽州軍次聞耗,公至漢口請假奔喪未准。
公在軍日,每年皆乞假歸省,留家一、二日而已,自淞滬戰起,家報亦斷,際清先生遂於是年十二月九日病逝里第,公在壽州方得家報,已踰兩旬矣。公至漢口,乃請假奔喪,奉委員長手諭:「孝豐陷落,道途阻塞,毋庸冒險回籍奔喪!」遂不果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西曆一九三八年,公四三歲。
一、公率部移駐關中,安定關隴,屏蔽川蜀。
公部自本年元月初到達信陽附近,時政府初遷武漢,原擬令公移駐武漢外圍,整理訓練,準備將來保衛武漢之作戰,而西安行營顧祝同主任以為關隴居川蜀上游,第十戰區部隊皆新編成,戰力薄弱,如日寇由晉竄入關中;或共黨居心叵測,乘虛南下,皆足動搖抗戰基礎,以公久駐秦隴,尤為共軍所畏憚,人地最宜,乃建議政府令公統十七軍團所部移駐關中,固守河防,兼顧晉隴,屏蔽川蜀。於是公奉命率第一軍暨胡長青、胡受謙兩補充團,自信陽經南陽逐步西移,入陜後公率僚屬與千餘流亡學生進駐鳳翔,以東湖少數房屋為司令部,中央並派公為隴海路警備司令,公辭未就。
二、公健全幕僚機構,組織軍團司令部。
初公在上海作戰,奉升為第十七軍團軍團長,戰鬥正劇,未嘗另組軍團司令部,僅報請調升羅列為軍團參謀長以為助,移駐關中後,公解除第一軍軍長兼職,由第一師師長李鐵軍升任,而令指揮友軍部隊固守鄭州 靈寶之線,公乃在鳳翔另組軍團部,參謀長羅列、副官處長袁杰三、參謀處長傅維潘、軍需處長蔡翊祺、軍法處長洪友蘭、機要組長王育,軍團部初駐鳳翔東湖,後移西安永寧門外薦福禪寺,即俗稱小雁塔者。公初住西安建國公園,後移住東倉門之下馬陵董子祠,乃漢董仲舒墓前祠屋也。屋僅三間,中有塑像,以紙壁障之為會客進膳之所。公居東頭屋,簡陋殊甚,是年冬乃始賃陵夏新華君房屋會客辦公。(註:夏新華為優秀青年軍官科技人才,任公之侍從參謀多年,忠心耿耿,處事精細,晚年定居美國,仍多次撰文懷念公之生平。)
三、公請於中央成立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招收陷區各省青年,訓練軍事幹部。
自淞滬抗日作戰後,軍中幹部之犧牲極大。第一軍連排長存者不及什一,他部當亦相同。公念抗戰將為長期戰爭,軍政幹部必須大量培育,以資補充。去年在無錫時已有此意,自至關中沿途已收容青年一千餘人,亟須先予訓練,於是請於委座奉准在西安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公乃派羅列、吳允周、羅歷戎、袁杰三、張研田、洪軌等六人為建校籌備委員,先借鳳翔師範為校址,至五月始移西安南部四十里之王曲。學生先考選去年收錄之千餘青年,繼又奉令接收康澤在王曲所辦之特種訓練班,顧希平終南山麓之江蘇抗日青年,編為第十五期第二總隊,李正先為總隊長,同時在冀魯豫等地招錄陷區學生數千名,成立第十五期三四五各總隊。自分校成立,中央軍校校務委員會延公為分校主任,顧希平為副主任,曾擴情為政治部主任,後為王超凡,曾乃調辦公處處長,吳允周為教育處長,袁杰三為總務處長,汪維恆為經理處長、趙立為軍醫處長,隊職官大部由部隊中副職調充,主任教官有張研田、余紀忠、洪軌、張大同、徐直民、淦克超、蕭思滋、林文淵等,政治教官有崔垂言、周天僇、李潤沂、張光祖等,余紀忠以政治部副主任兼主持王曲雜誌等編纂出版事宜,公經常駐宿王曲興隆嶺,主持校務。興隆嶺距王曲校本部約半里,張學良任西北剿共副總司令時所建之別業,有屋數間而已。自滬戰後,無線電通訊人員奇缺,公命在鳳翔設班訓練為第四期,適前無線電管理主任王微回陜,任四十六師軍需主任,公遂命兼任班主任,後併入七分校第二總隊。杭州中央警官學校校長趙龍文,抗戰事起,率部游擊,曾選送浙江青年四百餘人,公為爭取陷區青年,乃先後成立江浙皖鄂贛湘各地招生總隊,為成立第十六期之準備,陷區青年,聞訊亦多有遠道跋涉,自來投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