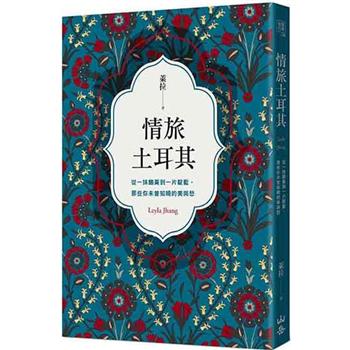伊斯坦堡──遇見世界之都
拿破崙曾說:「若世界是一個國家,那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堡。」
我越過四分之一個地球,來到了世界之都,
遇見了她的現代與傳統,看見了她的繁華與凝滯。
我想,她美好的容貌任誰都會想在有生之年看一眼,
那美麗中帶著憂愁的映像,哪怕只是倉促一瞥……
他就站在那裡,手中拿著一朵浪漫的紅玫瑰,緩緩地朝我走來。這一小段路我們走了三年。
我們的遠距離異國戀曲,最終在媽媽和妹妹的陪同下,於伊斯坦堡的阿塔圖克機場相聚。原本是個浪漫的雙人愛情之旅,就在我帶上媽媽和妹妹後,變成一場名副其實的四人家族旅遊。沒辦法,考量我在異地的人身安全,她們倆是跟定了,於是我們就這樣越過四分之一個地球,來到了伊斯坦堡和塞爾相見。
為了迎接我們清晨五點半抵達的班機,塞爾前一晚睡在機場的長椅上,見面時他的眼睛充滿血絲,可卻精神奕奕地帶著我們展開這趟精采的旅程……
初遇伊斯坦堡
早晨七點半,我們搭著地鐵抵達伊斯坦堡舊城區,空氣十分清新舒適,淡藍的天空還抹上一層冬天的灰。
一大早的舊城街道上,來往的人並不多,我們拖著大行李箱,穿越一個寫著「烤魚三明治四點五里拉*」招牌的巷子,經過一家掛有紅白星月國旗的銀行,它的門窗上照映著一棵枯樹、幾條電車纜線,還有遠方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我們瞬間成了一幅窗上風景畫。
走過幾條鋪有石板路的巷子,行李箱在靜謐的早晨街頭喀喀作響,我們終於來到這兩個星期的落腳處──維瓦旅店。旅店規模不大,但是小巧可愛、應有盡有。付清住宿費,我們搭乘復古式電梯,進入三樓的三人房,放下行李並重新整裝後,我們正式踏上伊斯坦堡──遇見世界之都之旅。
出了旅店的第一個轉角,是一家小型雜貨攤,櫥櫃裡擺滿了各牌菸酒、洋芋片和口香糖,櫃檯上凌亂地放著幾支打火機,塞爾在攤前買了幾瓶水,從厚重的大衣口袋裡取出幾枚銅板,交給一個留著落腮鬍的年輕店員。土耳其沒有「便利商店」,這種雜貨攤算是非常方便,可以買吃的、喝的,或者儲值交通卡。
沿著雙向電車道走,發現街上的藥局、餐館和商店尚未營業,而連接錫爾凱吉火車站(Sirkeci Garı)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那條大街,竟開滿了麥當勞、漢堡王和肯德基這類速食店,不過時差導致我們根本沒有胃口,一心往街道尾端的海岸步去。
天空的灰雲逐漸散去,明淨而蔚藍的海水映入眼簾,接著,一座微彎的橋梁自金角灣旁的海面上劃過,直抵對岸加拉達塔下錯亂交加的矮房前,一旁有好幾艘即將載滿遊客和通勤族的渡輪停靠著,而七輛悠閒的計程車,前後排在懷舊的渡輪站前,司機在車外抽菸,等待今天的第一位乘客。
畫面看上去協調得不得了,但仔細一瞧,又覺得龐雜地令人不知該把重點放在何處,這是我對伊斯坦堡的第一印象。
海岸旁的小徑上,有個賣芝麻圈餅的攤販,和幾個試圖拉客的渡輪公司員工,在冬日刺眼的陽光、凜冽的寒風中辛勤地工作著,雖然他們頭戴厚毛帽,但身上穿的卻是單薄的黑色夾克,還有早已被劃破的牛仔褲。撒在我手心上的冬天日光多麼溫柔,可卻在他們的手掌上割出一道道的細紋。我們遇見的伊斯坦堡是如此不同。
盤旋在空中的海鷗,伴著拋竿後耐心等待魚兒上鉤的釣客,為忙碌的一天拉開序幕。
第一站,我們來到新清真寺(Yeni Camii)旁的香料市集,又名「埃及市集」(Mısır Çarşısı)。建於西元一六六四年,原先是開羅商隊的絲路轉站,因眾多自埃及進口的商品在此交易而得名,同時,它也是伊斯坦堡最主要的香料販售區,因此又有「香料市集」這個名稱。
市集裡陳列著琳瑯滿目的食品、生活用品,店員的叫賣聲此起彼落,遠處一端賣的是五色繽紛的香料、花茶、果乾和香皂;隔壁家賣的是以鄂圖曼藝術結合花草、幾何圖案點綴畫成的杯盤、綢緞和裝飾畫作;回過頭一看,離我最近的店舖裡掛滿了中東風情的閃亮肚皮舞衣。
話說回來,大概只有曾做過文化研究的我,才會在這熙來攘往的市集商店前,試圖對土耳其的歷史、宗教文化抽絲剝繭,而媽媽和妹妹早已被一旁不斷喊著「美女,美女」的土耳其男店員帶進了他們的店舖裡,正開心地試吃著椰棗。不懂土耳其語的媽媽竟拿著計算機用中文開始跟店員殺價,妹妹則在一旁以她熟悉的幾句英語湊湊熱鬧。
幾天下來,我們帶著這般趣味走過了伊斯坦堡的每一個角落:聖索菲亞清真寺(Ayasofya Camii)、藍色清真寺(Sultanahmet Camii)、少女塔(Kız Kulesi)、蘇萊曼清真寺(Süleymaniye Camii)、托普卡匹皇宮(Topkapı Sarayı)和時髦繁華的希什利(Şişli)商業區。伊斯坦堡真是多變。
後來,我們在希什利商業區看見人生的第一場雪,也是伊斯坦堡的第一場冬雪。像棉絮一樣輕輕飄在空中,有時被風吹得四處亂彈,行人莫不快步行走,只有我們待在原地,伸出雙手接下一片片細小的「雪白花片」。那是我們待在伊斯坦堡的最後幾天,幸運地,一場白雪皚皚清楚地勾勒出旅程最後的模樣。
第一口土耳其料理
初至伊斯坦堡,我壓根沒想過要塞進嘴裡的是哪一類食物,只知道是不同於家鄉的西式食物。結果,出乎意料,土耳其的食物既不東方,也不是我們熟悉的西式餐點──它和中國菜、法國菜合稱「世界三大菜系」,土耳其菜在中、法菜系之間自成一格,就如同它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融合了地中海和阿拉伯文化元素。
同一張餐桌上,你可以吃到橄欖、沙拉和乳酪的冷盤料理,也會出現由酸奶熬煮而成的濃湯,還有撒滿香料的烤肉料理。雖然土耳其菜給人的印象,沒有中國菜和法國菜烙印得那麼深刻,可是它以一種極為獨特的樣貌,試圖征服遠道而來的旅人味蕾。
時值寒冷的冬季,我們走進一家海鮮餐廳,點了在伊斯坦堡的第一餐──炸鯷魚。鯷魚,或者土耳其人口中的「Hamsi」,每年十月至隔年三月盛產於土耳其北部的黑海地區,也因此,冬天時走進土耳其北部的海鮮餐廳時,服務生通常會推薦客人選擇當季新鮮的炸鯷魚餐。
每隻鯷魚身長大約十公分,顏色介於黑、銀之間,炸熟後原本銀色的部分會轉為淡淡的焦黃,香氣也在此時瀰漫整間餐廳。土耳其人習慣在炸魚上擠上適量的檸檬汁,搭配著麵包、生洋蔥和生菜一起享用,吃起來外皮酥脆可口,內層的肉質滑嫩鮮美,好一頓黑海鯷魚餐啊!
雖然走在伊斯坦堡街頭,左看右看都是烤肉料理餐廳,但是跟著當地人走,就能吃到所謂的「人間美味」,不過,每個人對食物的敏感度與偏好有所不同,究竟好不好吃真的見仁見智了!
吃遍了土耳其菜,才知道原來土耳其也有印象中的碎肉薄餅(Lahmacun),和道地的土耳其披薩披得(Pide),而聞名世界的沙威瑪(Döner Kebabı)吃起來比想像中的更加油膩,還有一股濃濃的「羊騷味」,並非每個人都能征服它。
在土耳其一條平凡的街道上,賣著夾有白色乳酪和番茄的芝麻圈餅、肉質Q彈的烤牛肉丸(Izgara Köfte)、番茄牛肉燉白扁豆(Etli Kuru Fasulye),還有各種豆類、小麥熬煮而成的濃湯,與多種得喝幾杯無糖土耳其紅茶,才能平衡過來的甜食,對停留一兩星期的旅人來說,足矣。
若你未曾邁出步伐,不會知道世界之大;若你未曾品嘗土耳其菜,不會知道愛恨之分明。對我來說,亞歷山大烤肉(İskender Kebabı)就是如此奇妙的存在。
那是我們在伊斯坦堡吃的第二餐,待服務生端上桌前,塞爾還鄭重地對我們說:「這道烤肉料理比較特別,你們可能不適應或不喜歡,所以我先點一盤讓你們試試。」讓我不禁好奇,究竟是什麼料理,搞得這麼神祕。
幾分鐘後,服務生小心翼翼地將那盤烤肉端上桌,我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抽筋般地眨了幾下──天啊!烤牛肉和烤麵包怎麼會浸泡在白白糊糊的優格裡!雖然我心中有萬分的抗拒,仍然拿起叉子,把一小塊烤牛肉和麵包,沾點優格一口吃下去……
「千萬別再提起這道烤肉的名字……」我低頭揮著手跟塞爾說。一旁的媽媽和妹妹也在吃下一口後放棄,看來它難以被吃慣東亞食物的人們接受。
在我勉強把那口食物吞進肚裡後,正式和亞歷山大烤肉絕交,原因是它整體的味道實在太不對勁。當時的我絕對沒想過……數年後搬到伊斯坦堡定居的我,有天會在某家烤肉餐廳裡,大聲讚美亞歷山大烤肉的絕妙之處,還一邊喝著鹹酸奶(Ayran),一邊說出「亞歷山大烤肉是最好吃的烤肉料理」這句話。
土耳其菜,不是令人恨得徹底,就是讓人愛得瘋狂啊!
伊斯坦堡之旅,本是一場視覺和味蕾的雙重盛宴。為期兩星期的短暫旅程,其實只是伊斯坦堡一個季節裡的一種面貌,真實的她,實在太多變了。在每個季節裡,每條街道上,每家餐廳裡……都會有屬於每個人的伊斯坦堡記憶。
幸運地,我曾踏上伊斯坦堡,今後仍將繼續站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