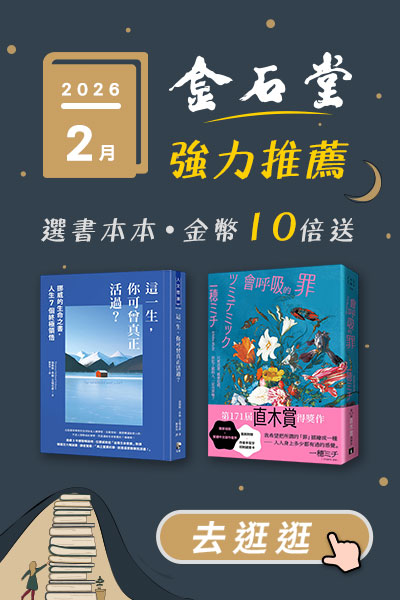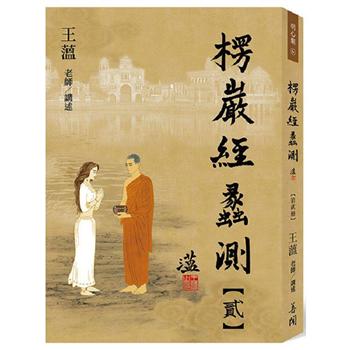【內文節選一】
經過那一次和老居士的結緣,我更確定憨山大師在他的著作中,一批頭直接就講破的重點:「這部經的重點主要是在破除眾生的生死根本,專門指出所有一切眾生的生死根本,其實就在淫念上,以及楞嚴大定的具體要旨上,因為破除魔敵最好的工具就是大定。」一代宗師慧心獨具地直述《楞嚴經》的精髓。
《楞嚴經》整部經的重點和核心,都是在舉說如果要進入首楞嚴大定,最重要的便是要去除淫慾,所以護持淫戒是此部經的最重要處。
在讀閱《楞嚴經》多次以後,按照我個人過往研讀密續或他論的習慣,在細節上也會多加注意,例如說在《楞嚴經》整部經當中,我有去關照到佛陀並不是只有在初時為了要化解阿難的情節才放光而已,《楞嚴經》中佛總共有五次放光,而每一次的放光都有不同的意思和加持,除了從頂門放光之外,有的是從臉部,有的是從心中的卍字,有的是從十方一切佛的佛頂,有的是從五體上面放光。例如是從臉上放光,意義上來說是表示佛智將開的意思;如果是從心輪上的卍字放光,他所表示的意思則是從心顯見;從一切諸佛的頭頂顯現光明,從《華嚴》的義理上來說明,則是表示一多無礙……其他在不同的卷份上,也都有不同的地方放光,這又有不同的意思,這就是佛陀無上智慧之處,這也是佛陀在不同的演會上面,善巧度化不同種姓的眾生所使用的權法。佛在講《金剛經》的時侯,是那麼地生活化,佛已證佛,和僧團同住時,為何還要示現每天仍然穿著法衣?和其他比丘一般隨緣奔走於有緣眾生之中化食?而世尊出外乞食,為何所穿著的是大衣?大衣也就是穿著一般比丘出外的僧服。佛陀的時代穿衣服也有一定的規矩,我們有時侯在不同的經典上,所看到講說的著衣都不太一樣,有時侯說到的是穿著三衣,這又有不同的說法,一般而言是指五條、七條或九條這三種,五條衣通常是用在行持法務或打坐之類的狀態下所穿著,受邀主持一切的法務和講說佛法,這時所要穿著的則是要五條衣以上,再假如要去往人多眾廣和重要的城市以及皇宮,這個時侯所穿著的衣服就要穿著九條衣……這些都有不同的解釋、運用和箇中的意義……佛陀為僧眾製衣,為何沒有選擇地只能在一定的顏色上面,現在我們所看僧眾的衣服,為什麼都只是那幾種顏色而已?黑色、黃色、紫色、青色等,這其中的含意也有蘊含著低調、內斂,不要有顯富、亮彩,引起眾生的煩惱心。
【內文節選二】
話說順治的前世,老和尚的遺徒,遵守了師父臨走前所託付的十二年時間已到,於是徒弟便下山,想要尋找師父的再來人。這時大清江山尚未底定,剛值入關沒多久的時間,那時滿清的年號便叫順治,在清代的歷史上,生世行跡成謎的,最明顯的要屬順治,許多寺廟裡都有掛上順治皇帝出家詩,藉以警惕寺廟中的大眾。但是另外有一種說法,就是他所鍾愛的董鄂妃的離世,打擊甚大,而讓他有出世的想法。為何順治在眾多的後宮獨獨鍾情於董鄂妃?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董鄂妃和其他的貴族女子大不相同,除了精通一切經典詩詞、恪守閨範以外,與生俱來的慈悲心以及來自於大家風範的氣度,讓順治打從心裡邊對她除了愛戀之外,更多了一層的敬重。順治由於年少就登基,初期對於政事上的處理比較草率,但董鄂妃卻是心細如髮的女子,她每每看到順治稍有懈怠,她都會在一旁善巧和婉地建議他,可是她也明瞭大清的律例,後宮是絕對不能參與討論任何政治的,即便順治遇到有奏摺上不能裁定的事件時,董鄂妃也不敢有任何的建言,她日常生活中最要緊的便是安排好順治所喜歡吃的飲食和點心,遇到四季氣侯變化時,她都會細心地照料,也紅袖添香地每每在夜半時分,順治尚在忙於批閱奏章時,董鄂妃便在一旁為其磨墨或者按摩身骨,這點不知羨煞了多少後宮和嬪妃,及一班文武內臣。董鄂妃雖然沒有相信任何的宗教,可是天生便有一股仁愛之心,如果遇到重大案件,瀕臨死刑等人命關天之案,董鄂妃便會不斷地提醒順治要有好生之德。順治因為受其先人的影響,自幼便篤信佛教,因此少不了的,在生活中便會舉些禪門趣事或淺顯的《心經》道理給予閱讀,董鄂妃便也隨喜地予以應答,或者也會把自己閱讀公案心得給予應和,鶼鰈情深,不免令人動容……。【內文節選三】
總而言之,唐代為了刺激朝廷對外的貿易,特別訓練了一批官方的翻譯官,這些人主要是訓練用外語和來往的商人溝通,也幫他們申請查驗需要的文件,另外也有催收胡商納稅的義務,許多胡商食髓知味地密集往返於唐朝,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羅馬人波斯人和中亞地區的外國人,對於中國出產的布匹綢緞,以及中國出產的茶葉跟骨瓷,有著極大的興趣,所以胡商從這些地區中賺取到極大的利益,這也是吸引力之一。可是從許多的遊記中記載著在那個年代裡,絲路其實也充滿了不可預知的危險,這不僅僅是玄奘法師曾經描寫過當時的出家人法顯法師在他的書中也有寫到。在絲路上經常會有撞邪遇鬼,陣陣吹拂上升滾燙的熱風,中年人是無法承受的,一旦碰上了幾乎無人可以全身而退。漫漫沙漠之中,虛空之上見不到半隻飛鳥,片地荒漠裡也見不到半隻走獸,到處充滿了、堆滿死亡多時的枯骨,成堆而置……
也曾看見過一些畫冊,畫中所描繪的大規模的胡商,有時是成千上萬、大規模的駱駝群隊,這中間所描繪出來的畫像清晰可見他們不同的身份,有的是學有專精的文化人,或者是穿著傳教士衣服的宗教家,還有工匠和穿著豔麗的舞孃、表演者……在唐代,有許多中國所看不到的香水、化妝品以及外地才有的奇裝異服和身上所穿戴的手鐲、臂釧、項鍊……等等,轉售給朝中的貴族和殷商、貴婦和眷屬。據說胡商所得到最大的利潤是來自於珠寶相關的項目,因為東西小、方面攜帶,出貨容易,價格又高,因為在當時漢代的有錢人實在太多,只是他們也冒著鋌而走險的危險,不同的胡商駝隊中,如果有出現盜賊,起了盜心,有時他們也會因此而喪生,所以許多奇奇怪怪的匿藏寶珠的奇招都曾出現過……。
在唐朝,由於唐代的幾位皇帝對於歌舞藝術都特別有興趣,尤其是唐玄宗時代,他把藝術和歌舞帶往另外一個高潮,當時最流行的有種胡旋舞和胡騰舞,是唐朝人最喜歡欣賞的,這些舞者和藝人也會隨著胡商的駝隊進入到中原……可見唐代人已經很懂得生活的品質和享受……。我們要知道詳細地去了解,中國的禪開悟最多的以及佛教最鼎盛的時間都是集中於唐宋這兩代,例如惠能大師是生在唐太宗在位的時侯,那時的社會由於體現了貞觀之治,整個國家社會可說是太平之至,皇帝知人善任,朝中大臣文武也都能夠貢獻一己之力使國內安定,邊境穩固。通常處亂世和盛世都容易出身開悟的禪師,可見環境對於參禪的修行人而言,是最佳的外境鍛鍊,所以六祖當日為什麼會因為讀《金剛經》而有省,這個省只是有所了悟,但還不是究竟開悟,還差一大段,這當然和六祖日常生活當中所處的客觀環境、大環境有關係,只要熟讀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便能理解,所以才會有所謂的應無所住,這個意思就是在一切外境環繞著我們的時侯,我們自己內在的心反而可以練習做到一切處無住,無論身處如何的環境,安靜不安靜,熱鬧不熱鬧,心始終不受干擾,無論內情外器如何地瞬息萬變,心始終如如不動,時間久了,工夫熟了,自然可以達到不用刻意特別要心不受干擾,動中也是如此,靜中也是如此,見到一切境也是如此,沒有看到一切境也是如此,到最後了無一切相,如果當時的惠能沒有真正地去用心參究以及融入於現實當中,反觀自性極長一段時間,那麼即便後來碰到了黃梅祖師,再怎麼跟他講也是不會有入處的。因此禪師與弟子之間的因緣和關係也絕非是偶然形成,必須有多生累劫的善緣才有可能。而弟子若無平日的實際理地的參修和煉心,也是無法契入,這也是後來五祖為他另闢密室,點出了其中的關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大師才大夢初醒一般,豁然開解,從此之後百尺竿頭,更上一步,到達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無論是在內心或者是外境都進入了能所雙泯之境,但它的根本還是來自於無住。
【內文節選四】
這道潛既然是開悟的禪師,多少有些神通,他知道他和蘇東坡有著過去世法上的因緣,於是額外地親切對待他,多次除卻一切法務,為的只是探望正在受難中的蘇東坡。道潛雖然是化外之僧,但卻有世俗的俠義心腸,後來在蘇東坡再度被貶往南海時,道潛又刻不容緩地想要去陪伴這位忘年之交,此時的蘇東坡自己知道政治立場極不穩定,也怕會波及到道潛,寫了數封信,勸告道潛勿要前來,以免受其牽連。道潛本就一開化之僧,哪裡會受世俗八法之束縛,非但如此,更提用其不世之詩才,暗諷時政,最後落得和至交好友蘇東坡一般之命運,被迫還俗,長期居住在山東一角,過著融俗不亂之潛修大隱生涯……。
蘇東坡一生中總與佛道有緣,無論得意或失恃時,皆有開悟善宿接引,使其在裘耗金散、落魄時,仍然可以灑然自若,或許來自於過去生之造化吧!不論真假,在許多文章中都曾經提及蘇東坡之前身乃一禪師之轉世,因為此故,才會和諸多大德往從和詩酬。例如他在杭州當通判的時侯,接觸過念佛有成的淨土高僧圓照法師,這段時間蘇東坡幾乎二六時中唸佛不輟,胸前經常配戴的也是阿彌陀佛聖像,一有機緣便勸人唸佛,往生西方。至於他失意於杭州那段時日裡,幾乎一有空閒或心中每每憶及塊壘不快往事,唯一的去處便是走訪杭州周圍大大小小清淨蘭若,這段時間他參禪唸佛都有小悟,閒來無事皆以讀誦《法華》及《楞嚴》為揀擇心性之參究。因為參禪的因緣,也和廬山常總禪師甚密,著名的無情說法公案便是兩人精究之話頭,這段時期所做禪詩傳誦至今,著名的便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著名的荊南尊宿玉泉禪師在當時可謂名震禪林……。舉了這些例子,無非是要說明《楞嚴經》風行於中國久矣,尤其是唐宋以來,幾乎所有的禪師、文人騷客莫不以拜讀《楞嚴經》為風潮,例如:蘇東坡之流。蘇東坡所讀經書不可謂不多,但最令其醉心、瀏覽再三的有《圓覺經》、《維摩詰經》、《金剛經》、般若部一切重要經論,在諸多經論中,蘇東坡就曾經多次地談到他對《楞嚴經》的重視,也可以從他多次為《楞嚴經》所寫的跋,看見他對《楞嚴經》所做的研究已經極為深入且精闢,同時也可以從他所寫的文章片段中知道,《楞嚴經》似乎已經成為蘇東坡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精神食糧,他被貶至儋州的時侯,就曾經用詩做過記錄,其中一句便是「《楞嚴》在床頭,妙偈時仰讀」,可見他幾乎無日不讀《楞嚴經》,無時不參《楞嚴經》……
【內文節選五】
歐陽修和契嵩的因緣主要是因為同是本朝,而一僧一俗皆有文名,起初因兩人立場不同,受到韓愈學說的影響,歐陽修早期亦有宣揚排佛的思想,所以曾經寫了一本《本論》,裡面的內容盡是些他用盡自以為是虛嘴巧舌邪知邪見之綺文用於蠱惑當時之文人及一般士大夫一度如野火般紅火不墜,當時的契嵩禪師也知道歐陽修是一條孽龍,如果將其軟性地降服亦可使其皈命於佛門,於是,契嵩禪師用他高度地智慧發諸於鋒發暢流的文章裡,契嵩本來文學的㡳蘊就不雅於當時歐陽修等這批文學大將,於是,他善巧地融合了儒、釋、道三家之精髓不讀偏於佛教之專論洋洋灑灑、偏偏錦繡地著成了《輔教編》內容深入淺出,從儒家之五倫,佛教之人天基本結合社會一般人之習氣……在當時契嵩禪師的著作文章在坊間及教內本就風行異常,只要有新的文章發表前四眾莫不翹首升踵地殷殷盼望可以一睹為快,歐陽修更是想當然爾地通章閱讀,這一深心閱讀之後竟然讓歐陽修冷汗直冒,原來過去所為皆是謗佛並且對契嵩禪師的人格及文章讚賞有加,不只一次地說到相見恨晚這類的詞句,從此之後歐陽修透過其門徒引見多次聽其開示教理之後佛智大開深深地懊悔未解佛前所作之行徑。從此之後,一反過往的態度經常參訪十方名剎參訪著名禪寺得閒便深入經藏埋首於佛陀的法句之中,平日裡也教導眷屬子弟於日常行誼中勿違背綱常以教誡,對於有緣的同儕部屬也都苦口婆心地勸導轉化其習氣,從無氣餒並且一反常態地用六一居士名諱發表勸人之文一時傳為美談,除此之外和當時契嵩禪師外之諸山悟憎亦有禪誼留有軼事美談流傳於後。
據說歐陽修某一次參禪尋訪善知識去到了嵩山,到達之後便被一位老和尚風采給吸引,原來是著名的開悟禪師在廟裡頭閱讀大藏並且如入定中渾然無視於外境攘之香客如如不動地閱讀經典散發出一股其他出家人所未有的大師風範,那氣質引發了當時怦然心動的歐陽修高度的注意,因此不由自主地趨前問訊攀談:「敢問老和尚在此已經有多久了?」老和尚慈詳和藹地回答歐陽修:「老納在此寺廟已過春秋無數」歐陽修再進一步地問:「那法師平日裡都怎麼用功?」老和尚謙虛地回答:「慚愧,慚愧,虛度光陰而已,每日用《法華經》遮遮眼罷了」歐陽修就這樣一來一往中和這位老和尚很自在地聊將起來,談話過程中歐陽修又想到了心中的問題:「弟子魯昧不斷地在思索一個問題,我閱讀過《高僧傳》及金剛乘中許多成就解脫的修行人為何有許多的行者可以在即將往生時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何時可以解脫,不但沒有為難他人並且自在往生,這是什麼道理?」老和尚很莊重地告訴歐陽修:「可以到達這般境地完全是行者在生前用了長時間的精進用功到達定慧相資的境界才有辦法如此」歐陽修聽了這番話之後心中頗有戚。戚焉,想到自己大半生在宦海裡載浮載沈虛聲浪死,所犯得的也不過是虛名假利和滿身的罪業而已,更何況大多數人每天都忙碌於五斗米之求,終日煩惱不斷,哪有時間顧及到禪定……?
【內文節選六】
「家祖母因為中年喪女,心中所遭受的打擊十分地激烈,那段時間她幾乎都會去廟裡面找廟裡的住持尼姑釋解心中的苦悶,漸漸地也了解這一切都是因果和因緣。由於母親或許是過度地眷戀我和家姐,於是經常入夢於祖母,廟裡的老尼姑便教祖母持誦楞嚴神咒,說也奇怪,祖母唸誦不到三天,之後母親再也未曾入夢,祖母覺得神奇,於是產生了無比的信解心,從此以後,幾乎無論寒暑,天天每到卯時之前,便起身虔敬地誦念楞嚴神咒。大約唸誦了百日之後,有一天母親又來到了祖母的夢中,但這回的情景跟過往完全不同,根據祖母的說法,就在天將要亮之時,母親身上透發著金黃色的光芒,身上所穿著的服裝也不是人世間的服裝,母親很歡喜地來告訴祖母說,感謝她一直以來不斷地持誦神咒,乘此功德,她累劫以來的罪業完全淨化現在要到一個很好的地方,特來感謝……祖母說她做了這個夢完了之後,立即從睡夢中醒過來,但她不覺得這是一場夢,因為太真實了!就如同母親生前和她在聊天一般,並且祖母一覺醒來,一整天精神煥發,毫不疲憊,最重要的是心中充滿了平靜和喜悅,從那天起,祖母便吃長素了,並且每天早晨固定的早課便是楞嚴神咒。我自小茹素的因緣也是深受家祖母的影響,長大以後,我只要一聞到腥臭味,馬上就會有反胃嘔吐的感覺……」
這是老居士一邊回憶,一邊在飯席之間對我們所訴說的一段年少往事。至於為何龍老居士也因為祖母的緣故,小時侯開始識字便唸誦楞嚴咒,他說:「我的祖母雖然不是那種書香門第出身的女性,但也讀過幾年的私塾,對於漢字還是知得的,所以我尚未讀書之前的啟蒙都是來自於祖母。而祖母最早教我最多的便是從楞嚴咒開始,你們說,我和《楞嚴經》的因緣是不是很早就結緣了?」龍老居士講到這裡的時侯,神情是愉悅而又充滿感激的,想必他沿自於祖母的啟發和感應應該是至深的。
經過那一次和老居士的結緣,我更確定憨山大師在他的著作中,一批頭直接就講破的重點:「這部經的重點主要是在破除眾生的生死根本,專門指出所有一切眾生的生死根本,其實就在淫念上,以及楞嚴大定的具體要旨上,因為破除魔敵最好的工具就是大定。」一代宗師慧心獨具地直述《楞嚴經》的精髓。
《楞嚴經》整部經的重點和核心,都是在舉說如果要進入首楞嚴大定,最重要的便是要去除淫慾,所以護持淫戒是此部經的最重要處。
在讀閱《楞嚴經》多次以後,按照我個人過往研讀密續或他論的習慣,在細節上也會多加注意,例如說在《楞嚴經》整部經當中,我有去關照到佛陀並不是只有在初時為了要化解阿難的情節才放光而已,《楞嚴經》中佛總共有五次放光,而每一次的放光都有不同的意思和加持,除了從頂門放光之外,有的是從臉部,有的是從心中的卍字,有的是從十方一切佛的佛頂,有的是從五體上面放光。例如是從臉上放光,意義上來說是表示佛智將開的意思;如果是從心輪上的卍字放光,他所表示的意思則是從心顯見;從一切諸佛的頭頂顯現光明,從《華嚴》的義理上來說明,則是表示一多無礙……其他在不同的卷份上,也都有不同的地方放光,這又有不同的意思,這就是佛陀無上智慧之處,這也是佛陀在不同的演會上面,善巧度化不同種姓的眾生所使用的權法。佛在講《金剛經》的時侯,是那麼地生活化,佛已證佛,和僧團同住時,為何還要示現每天仍然穿著法衣?和其他比丘一般隨緣奔走於有緣眾生之中化食?而世尊出外乞食,為何所穿著的是大衣?大衣也就是穿著一般比丘出外的僧服。佛陀的時代穿衣服也有一定的規矩,我們有時侯在不同的經典上,所看到講說的著衣都不太一樣,有時侯說到的是穿著三衣,這又有不同的說法,一般而言是指五條、七條或九條這三種,五條衣通常是用在行持法務或打坐之類的狀態下所穿著,受邀主持一切的法務和講說佛法,這時所要穿著的則是要五條衣以上,再假如要去往人多眾廣和重要的城市以及皇宮,這個時侯所穿著的衣服就要穿著九條衣……這些都有不同的解釋、運用和箇中的意義……佛陀為僧眾製衣,為何沒有選擇地只能在一定的顏色上面,現在我們所看僧眾的衣服,為什麼都只是那幾種顏色而已?黑色、黃色、紫色、青色等,這其中的含意也有蘊含著低調、內斂,不要有顯富、亮彩,引起眾生的煩惱心。
【內文節選二】
話說順治的前世,老和尚的遺徒,遵守了師父臨走前所託付的十二年時間已到,於是徒弟便下山,想要尋找師父的再來人。這時大清江山尚未底定,剛值入關沒多久的時間,那時滿清的年號便叫順治,在清代的歷史上,生世行跡成謎的,最明顯的要屬順治,許多寺廟裡都有掛上順治皇帝出家詩,藉以警惕寺廟中的大眾。但是另外有一種說法,就是他所鍾愛的董鄂妃的離世,打擊甚大,而讓他有出世的想法。為何順治在眾多的後宮獨獨鍾情於董鄂妃?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董鄂妃和其他的貴族女子大不相同,除了精通一切經典詩詞、恪守閨範以外,與生俱來的慈悲心以及來自於大家風範的氣度,讓順治打從心裡邊對她除了愛戀之外,更多了一層的敬重。順治由於年少就登基,初期對於政事上的處理比較草率,但董鄂妃卻是心細如髮的女子,她每每看到順治稍有懈怠,她都會在一旁善巧和婉地建議他,可是她也明瞭大清的律例,後宮是絕對不能參與討論任何政治的,即便順治遇到有奏摺上不能裁定的事件時,董鄂妃也不敢有任何的建言,她日常生活中最要緊的便是安排好順治所喜歡吃的飲食和點心,遇到四季氣侯變化時,她都會細心地照料,也紅袖添香地每每在夜半時分,順治尚在忙於批閱奏章時,董鄂妃便在一旁為其磨墨或者按摩身骨,這點不知羨煞了多少後宮和嬪妃,及一班文武內臣。董鄂妃雖然沒有相信任何的宗教,可是天生便有一股仁愛之心,如果遇到重大案件,瀕臨死刑等人命關天之案,董鄂妃便會不斷地提醒順治要有好生之德。順治因為受其先人的影響,自幼便篤信佛教,因此少不了的,在生活中便會舉些禪門趣事或淺顯的《心經》道理給予閱讀,董鄂妃便也隨喜地予以應答,或者也會把自己閱讀公案心得給予應和,鶼鰈情深,不免令人動容……。【內文節選三】
總而言之,唐代為了刺激朝廷對外的貿易,特別訓練了一批官方的翻譯官,這些人主要是訓練用外語和來往的商人溝通,也幫他們申請查驗需要的文件,另外也有催收胡商納稅的義務,許多胡商食髓知味地密集往返於唐朝,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羅馬人波斯人和中亞地區的外國人,對於中國出產的布匹綢緞,以及中國出產的茶葉跟骨瓷,有著極大的興趣,所以胡商從這些地區中賺取到極大的利益,這也是吸引力之一。可是從許多的遊記中記載著在那個年代裡,絲路其實也充滿了不可預知的危險,這不僅僅是玄奘法師曾經描寫過當時的出家人法顯法師在他的書中也有寫到。在絲路上經常會有撞邪遇鬼,陣陣吹拂上升滾燙的熱風,中年人是無法承受的,一旦碰上了幾乎無人可以全身而退。漫漫沙漠之中,虛空之上見不到半隻飛鳥,片地荒漠裡也見不到半隻走獸,到處充滿了、堆滿死亡多時的枯骨,成堆而置……
也曾看見過一些畫冊,畫中所描繪的大規模的胡商,有時是成千上萬、大規模的駱駝群隊,這中間所描繪出來的畫像清晰可見他們不同的身份,有的是學有專精的文化人,或者是穿著傳教士衣服的宗教家,還有工匠和穿著豔麗的舞孃、表演者……在唐代,有許多中國所看不到的香水、化妝品以及外地才有的奇裝異服和身上所穿戴的手鐲、臂釧、項鍊……等等,轉售給朝中的貴族和殷商、貴婦和眷屬。據說胡商所得到最大的利潤是來自於珠寶相關的項目,因為東西小、方面攜帶,出貨容易,價格又高,因為在當時漢代的有錢人實在太多,只是他們也冒著鋌而走險的危險,不同的胡商駝隊中,如果有出現盜賊,起了盜心,有時他們也會因此而喪生,所以許多奇奇怪怪的匿藏寶珠的奇招都曾出現過……。
在唐朝,由於唐代的幾位皇帝對於歌舞藝術都特別有興趣,尤其是唐玄宗時代,他把藝術和歌舞帶往另外一個高潮,當時最流行的有種胡旋舞和胡騰舞,是唐朝人最喜歡欣賞的,這些舞者和藝人也會隨著胡商的駝隊進入到中原……可見唐代人已經很懂得生活的品質和享受……。我們要知道詳細地去了解,中國的禪開悟最多的以及佛教最鼎盛的時間都是集中於唐宋這兩代,例如惠能大師是生在唐太宗在位的時侯,那時的社會由於體現了貞觀之治,整個國家社會可說是太平之至,皇帝知人善任,朝中大臣文武也都能夠貢獻一己之力使國內安定,邊境穩固。通常處亂世和盛世都容易出身開悟的禪師,可見環境對於參禪的修行人而言,是最佳的外境鍛鍊,所以六祖當日為什麼會因為讀《金剛經》而有省,這個省只是有所了悟,但還不是究竟開悟,還差一大段,這當然和六祖日常生活當中所處的客觀環境、大環境有關係,只要熟讀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便能理解,所以才會有所謂的應無所住,這個意思就是在一切外境環繞著我們的時侯,我們自己內在的心反而可以練習做到一切處無住,無論身處如何的環境,安靜不安靜,熱鬧不熱鬧,心始終不受干擾,無論內情外器如何地瞬息萬變,心始終如如不動,時間久了,工夫熟了,自然可以達到不用刻意特別要心不受干擾,動中也是如此,靜中也是如此,見到一切境也是如此,沒有看到一切境也是如此,到最後了無一切相,如果當時的惠能沒有真正地去用心參究以及融入於現實當中,反觀自性極長一段時間,那麼即便後來碰到了黃梅祖師,再怎麼跟他講也是不會有入處的。因此禪師與弟子之間的因緣和關係也絕非是偶然形成,必須有多生累劫的善緣才有可能。而弟子若無平日的實際理地的參修和煉心,也是無法契入,這也是後來五祖為他另闢密室,點出了其中的關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大師才大夢初醒一般,豁然開解,從此之後百尺竿頭,更上一步,到達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無論是在內心或者是外境都進入了能所雙泯之境,但它的根本還是來自於無住。
【內文節選四】
這道潛既然是開悟的禪師,多少有些神通,他知道他和蘇東坡有著過去世法上的因緣,於是額外地親切對待他,多次除卻一切法務,為的只是探望正在受難中的蘇東坡。道潛雖然是化外之僧,但卻有世俗的俠義心腸,後來在蘇東坡再度被貶往南海時,道潛又刻不容緩地想要去陪伴這位忘年之交,此時的蘇東坡自己知道政治立場極不穩定,也怕會波及到道潛,寫了數封信,勸告道潛勿要前來,以免受其牽連。道潛本就一開化之僧,哪裡會受世俗八法之束縛,非但如此,更提用其不世之詩才,暗諷時政,最後落得和至交好友蘇東坡一般之命運,被迫還俗,長期居住在山東一角,過著融俗不亂之潛修大隱生涯……。
蘇東坡一生中總與佛道有緣,無論得意或失恃時,皆有開悟善宿接引,使其在裘耗金散、落魄時,仍然可以灑然自若,或許來自於過去生之造化吧!不論真假,在許多文章中都曾經提及蘇東坡之前身乃一禪師之轉世,因為此故,才會和諸多大德往從和詩酬。例如他在杭州當通判的時侯,接觸過念佛有成的淨土高僧圓照法師,這段時間蘇東坡幾乎二六時中唸佛不輟,胸前經常配戴的也是阿彌陀佛聖像,一有機緣便勸人唸佛,往生西方。至於他失意於杭州那段時日裡,幾乎一有空閒或心中每每憶及塊壘不快往事,唯一的去處便是走訪杭州周圍大大小小清淨蘭若,這段時間他參禪唸佛都有小悟,閒來無事皆以讀誦《法華》及《楞嚴》為揀擇心性之參究。因為參禪的因緣,也和廬山常總禪師甚密,著名的無情說法公案便是兩人精究之話頭,這段時期所做禪詩傳誦至今,著名的便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著名的荊南尊宿玉泉禪師在當時可謂名震禪林……。舉了這些例子,無非是要說明《楞嚴經》風行於中國久矣,尤其是唐宋以來,幾乎所有的禪師、文人騷客莫不以拜讀《楞嚴經》為風潮,例如:蘇東坡之流。蘇東坡所讀經書不可謂不多,但最令其醉心、瀏覽再三的有《圓覺經》、《維摩詰經》、《金剛經》、般若部一切重要經論,在諸多經論中,蘇東坡就曾經多次地談到他對《楞嚴經》的重視,也可以從他多次為《楞嚴經》所寫的跋,看見他對《楞嚴經》所做的研究已經極為深入且精闢,同時也可以從他所寫的文章片段中知道,《楞嚴經》似乎已經成為蘇東坡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精神食糧,他被貶至儋州的時侯,就曾經用詩做過記錄,其中一句便是「《楞嚴》在床頭,妙偈時仰讀」,可見他幾乎無日不讀《楞嚴經》,無時不參《楞嚴經》……
【內文節選五】
歐陽修和契嵩的因緣主要是因為同是本朝,而一僧一俗皆有文名,起初因兩人立場不同,受到韓愈學說的影響,歐陽修早期亦有宣揚排佛的思想,所以曾經寫了一本《本論》,裡面的內容盡是些他用盡自以為是虛嘴巧舌邪知邪見之綺文用於蠱惑當時之文人及一般士大夫一度如野火般紅火不墜,當時的契嵩禪師也知道歐陽修是一條孽龍,如果將其軟性地降服亦可使其皈命於佛門,於是,契嵩禪師用他高度地智慧發諸於鋒發暢流的文章裡,契嵩本來文學的㡳蘊就不雅於當時歐陽修等這批文學大將,於是,他善巧地融合了儒、釋、道三家之精髓不讀偏於佛教之專論洋洋灑灑、偏偏錦繡地著成了《輔教編》內容深入淺出,從儒家之五倫,佛教之人天基本結合社會一般人之習氣……在當時契嵩禪師的著作文章在坊間及教內本就風行異常,只要有新的文章發表前四眾莫不翹首升踵地殷殷盼望可以一睹為快,歐陽修更是想當然爾地通章閱讀,這一深心閱讀之後竟然讓歐陽修冷汗直冒,原來過去所為皆是謗佛並且對契嵩禪師的人格及文章讚賞有加,不只一次地說到相見恨晚這類的詞句,從此之後歐陽修透過其門徒引見多次聽其開示教理之後佛智大開深深地懊悔未解佛前所作之行徑。從此之後,一反過往的態度經常參訪十方名剎參訪著名禪寺得閒便深入經藏埋首於佛陀的法句之中,平日裡也教導眷屬子弟於日常行誼中勿違背綱常以教誡,對於有緣的同儕部屬也都苦口婆心地勸導轉化其習氣,從無氣餒並且一反常態地用六一居士名諱發表勸人之文一時傳為美談,除此之外和當時契嵩禪師外之諸山悟憎亦有禪誼留有軼事美談流傳於後。
據說歐陽修某一次參禪尋訪善知識去到了嵩山,到達之後便被一位老和尚風采給吸引,原來是著名的開悟禪師在廟裡頭閱讀大藏並且如入定中渾然無視於外境攘之香客如如不動地閱讀經典散發出一股其他出家人所未有的大師風範,那氣質引發了當時怦然心動的歐陽修高度的注意,因此不由自主地趨前問訊攀談:「敢問老和尚在此已經有多久了?」老和尚慈詳和藹地回答歐陽修:「老納在此寺廟已過春秋無數」歐陽修再進一步地問:「那法師平日裡都怎麼用功?」老和尚謙虛地回答:「慚愧,慚愧,虛度光陰而已,每日用《法華經》遮遮眼罷了」歐陽修就這樣一來一往中和這位老和尚很自在地聊將起來,談話過程中歐陽修又想到了心中的問題:「弟子魯昧不斷地在思索一個問題,我閱讀過《高僧傳》及金剛乘中許多成就解脫的修行人為何有許多的行者可以在即將往生時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何時可以解脫,不但沒有為難他人並且自在往生,這是什麼道理?」老和尚很莊重地告訴歐陽修:「可以到達這般境地完全是行者在生前用了長時間的精進用功到達定慧相資的境界才有辦法如此」歐陽修聽了這番話之後心中頗有戚。戚焉,想到自己大半生在宦海裡載浮載沈虛聲浪死,所犯得的也不過是虛名假利和滿身的罪業而已,更何況大多數人每天都忙碌於五斗米之求,終日煩惱不斷,哪有時間顧及到禪定……?
【內文節選六】
「家祖母因為中年喪女,心中所遭受的打擊十分地激烈,那段時間她幾乎都會去廟裡面找廟裡的住持尼姑釋解心中的苦悶,漸漸地也了解這一切都是因果和因緣。由於母親或許是過度地眷戀我和家姐,於是經常入夢於祖母,廟裡的老尼姑便教祖母持誦楞嚴神咒,說也奇怪,祖母唸誦不到三天,之後母親再也未曾入夢,祖母覺得神奇,於是產生了無比的信解心,從此以後,幾乎無論寒暑,天天每到卯時之前,便起身虔敬地誦念楞嚴神咒。大約唸誦了百日之後,有一天母親又來到了祖母的夢中,但這回的情景跟過往完全不同,根據祖母的說法,就在天將要亮之時,母親身上透發著金黃色的光芒,身上所穿著的服裝也不是人世間的服裝,母親很歡喜地來告訴祖母說,感謝她一直以來不斷地持誦神咒,乘此功德,她累劫以來的罪業完全淨化現在要到一個很好的地方,特來感謝……祖母說她做了這個夢完了之後,立即從睡夢中醒過來,但她不覺得這是一場夢,因為太真實了!就如同母親生前和她在聊天一般,並且祖母一覺醒來,一整天精神煥發,毫不疲憊,最重要的是心中充滿了平靜和喜悅,從那天起,祖母便吃長素了,並且每天早晨固定的早課便是楞嚴神咒。我自小茹素的因緣也是深受家祖母的影響,長大以後,我只要一聞到腥臭味,馬上就會有反胃嘔吐的感覺……」
這是老居士一邊回憶,一邊在飯席之間對我們所訴說的一段年少往事。至於為何龍老居士也因為祖母的緣故,小時侯開始識字便唸誦楞嚴咒,他說:「我的祖母雖然不是那種書香門第出身的女性,但也讀過幾年的私塾,對於漢字還是知得的,所以我尚未讀書之前的啟蒙都是來自於祖母。而祖母最早教我最多的便是從楞嚴咒開始,你們說,我和《楞嚴經》的因緣是不是很早就結緣了?」龍老居士講到這裡的時侯,神情是愉悅而又充滿感激的,想必他沿自於祖母的啟發和感應應該是至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