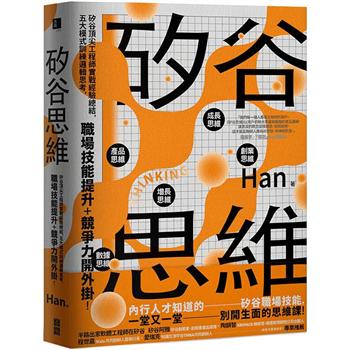1.2矽谷居然流行故意讓產品難用
本節關鍵詞:感知價值、努力錯覺、不流暢度、峰值終值
產品體驗快了還不好
我們在做互聯網產品的時候,無論是一個網頁端產品還是移動端App,都默認整個體驗應該是愈快、愈流暢愈好。所以,我們工程師夜以繼日地工作以提升軟體速度和各項工程指標,設計師和產品經理也努力優化產品流程,省略各種不需要的交互體驗。
但是,在某些時候,過於快速和流暢的體驗可能並不能提高用戶滿意度,反而會讓用戶感覺不爽。我們先從2011年由哈佛商學院學者萊恩・伯爾(Ryan Buell)和麥可・諾頓(Michael Norton)發表在《管理科學》(Management Science)期刊上的著名研究論文《努力錯覺》(The Labor Illusion)說起。
2010年前後,行動網路剛普及,甚至3G技術也才剛剛興起。那時候,大家使用的主要是電腦端的網頁產品,而且因為演算法和很多基礎架構都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完善,產品的運算速度普遍較慢。哈佛大學商學院就進行了一個實驗,想瞭解一下用戶對產品運行速度的感知情況。他們設計了下面這個實驗。
他們虛構了一個機票線上預訂平台Travel Finder,邀請受試者使用。他們把受試者分成了兩組。當受試者點擊「搜尋」按鈕之後,用戶會根據自己所在實驗組的不同,進而得到不同的軟體回應時間。一組用戶會立即看到航班結果,而另一組用戶,則強制有一定的延遲,如故意延遲10秒、20秒等,之後再顯示搜尋結果。其他所有的用戶體驗細節、操作介面等都完全一致,唯一的實驗變量,就是程式的回應時間。
在實驗結束後,他們會要求受試用戶對剛剛的整個過程給出一個分數。滿分為7分,感覺用戶體驗良好,則給分較高;反之,則給分較低。實驗結果如下。
如果頁面的響應時間過長,如60秒,評分會降低很多。這一點非常符合們的預期,畢竟等了這麼久,肯定會煩躁不安,整個用戶體驗就會下降。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如果給予「適當」的回應延遲,用戶體驗的評分居然會升高!比如故意延遲10秒,用戶評分居然提升了2%。不要覺得這個2%很少,因為這個分數別說升高,就算是沒有降低,都已經足夠讓人驚訝和顛覆認知。
哈佛大學在對這些受試者走訪以後,才知道了用戶的想法。原來,他們覺得,如果搜尋結果立刻展示出來,好像系統在騙他們。因為根據人們的認知,進行這麼複雜的全網搜索,還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Uber:對,我們是故意讓它難用的
優步(Uber)公司早年間有一個著名的案例,它因為體驗過於流暢,引發大量不滿和投訴。
Uber當年剛剛推出的時候,創新地提出了一個概念叫作尖峰價格(Surge Price)。對於這個概念,現在的你應該早就能夠理解了。這個跟滴滴的「動態調價」是一樣的,就是經濟學最基本的供需曲線的體現。可是,這個服務模式在Uber剛剛上線的時候,很多人並不知道。
在Uber上市早期,他們在用戶中廣泛宣傳的產品核心是「一鍵叫車」(One Tap To Ride),也就是叫車體驗非常流暢,愈快愈好。所以他們的產品設計就要簡潔、流暢,多餘的步驟一律都要省略。所以在叫車的時候,即使是在尖峰時段,Uber也依然是一鍵叫車。即使出現了價格飆升,他們也不會多做提示,僅僅在網頁頭版(above the fold)標注翻倍金額。
因為叫車體驗太流暢了,很多用戶壓根兒沒有注意價格提升了,直到下車扣款時才發現。雖然這個尖峰價格警告在用戶等車的時候已然顯示,可是用戶就是看不見。這給早期的Uber帶來了非常大的公關壓力。比較著名的例子是,2013年紐約暴雪,Uber價格上漲到8.3倍,好多人急著回家都沒注意加價,到家一看,「20分鐘的車程居然收了500美元!」每逢大型節日活動都是Uber的公關危機。
Uber被很多用戶指責是「騙子」公司,收黑心錢。要知道,對於一般的初創公司,這樣的評論十分危險。
很快Uber就做出了調整,他們推出了下面這一版方案。當出現尖峰價格狀態的時候,Uber不再是「一鍵」叫車,而是「兩鍵」。當用戶在頭版點擊了「叫車」按鈕之後,系統自動額外彈出一頁明顯的加價訊息讓用戶確認。
但是,這個設計上線之後,抱怨聲還是沒有減少,依然有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加價。因為文字太多,金額數字又很小。你想,那些晚上剛從酒吧出來的人,如果喝醉了,文字根本就看不懂。而且,很多用戶以為這就是一個普通的用戶協議,看都沒看就點擊「ok」按鈕了。
沒辦法,Uber又回去更改體驗流程,最終變成了這樣,堪稱忍無可忍的殺手鐧。Uber不僅會導入額外的訊息確認頁面,同時那個翻倍的數字也變得非常醒目,顏色和字體大小都非常明顯。而且關鍵的是,它居然還要讓用戶手動地輸入一遍這個倍數,這簡直是「喪心病狂」。
終於,公關問題解決了。Uber故意讓產品體驗流程變差,卻成功地教育了用戶,化解了危機。其實,矽谷現在有這樣一個概念,叫產品的「不流暢度」(Disfluency)。「讓產品流程變差」就是增加產品的「不流暢度」。
行為經濟學家施洛莫・貝納齊(Shlomo Benartzi)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2017年出版的圖書《螢幕陷阱》(The Smarter Screen)中指出,用戶對產品的「重視程度」和「不流暢度」,呈「倒U形曲線關係」,如下圖所示。
也就是說,太流暢和太複雜的體驗都會喪失用戶的重視。
另外,研究還指出,愈流暢的體驗,愈方便用戶理解,但用戶也愈容易遺忘。這其實符合人類的記憶機制和遺忘規律。
回想一下自己,你是不是這樣,聽了好多音檔課程,當時在聽的時候,覺得理解得好透徹,可是聽過之後,就幾乎忘光了。這背後的一個原因就是,「聽」是比「閱讀」更流暢的一種體驗,所以更容易讓人遺忘。
這可能是因為人都不太珍惜輕易能獲得的東西吧。你看,經常出現很多男生去追同一個女生,這可能是因為「難追」才有意思,太好追了反而沒成就感了。
看了Uber的例子,在產品當中怎樣利用「不流暢性」呢?在你想讓用戶注意的情況下導入。
例如,你的團隊負責一個借款App,為增加借款人的「敬畏心」,讓他及時還款,可以把貸款的流程設計得略微複雜些,可以用額外的視窗來向借款人提醒——「借款期90天,逾期不還,拿磚頭砸你們家玻璃喲!」當然了,這一定會伴隨著中間用戶流失率的提升,但是你們篩選掉了一些不還款的「高風險」用戶,整體看來,未嘗不是一種收益呀。
對了,這裡還要指出,人是會改變的。也就是說,2011年的時候讓用戶等待10秒,跟2019年讓用戶等待10秒,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上面的例子,僅做參考,平時工作時還要根據情況適時應對。
2.1我剛工作就出醜,只因不懂統計學
本節關鍵詞:統計偏差(statistical bias)
從一件糗事說起
話說,當年我剛畢業開始工作的時候,總覺得作為一名軟體工程師,只要做好程式設計(programming)工作就萬事大吉了。可是,我工作出的第一個大醜,卻不是因為程式設計技術不行,而是不懂統計學鬧出的笑話。下面,我就把這個故事分享給你。
那時,我剛剛畢業。進入矽谷工作兩個月後,我人生中第一個重大專案終於完成了。這天傍晚下班前,我們決定向全球發布這個新功能。新功能上線後,效果真的非常不錯,我們可以清晰地可以看到各項指標瘋狂上漲,短短幾個小時,就已經達到了我們對這個季度的業務預期。於是,我就開心得早早回家慶祝了。
第二天早上到公司,我發現,我們團隊辦公桌旁邊牆上掛的數據大螢幕居然壞了——因為數據太好,讓顯示系統崩潰了。我暗自笑笑,悠閒地去吃了個全套英式早餐,之後,優雅地邊喝茶邊發了內部捷報——新產品上線,12小時打破歷史紀錄。
然後,就是各種人故意路過我的辦公桌,給我打招呼恭喜。畢竟,一個剛入職的畢業生,能在兩個月內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十分難得。很快,到下班時間了,當我即將歡快地唱起《難忘今宵》並闔上電腦離開的時候,突然,產品經理給我發訊息——「又是祝賀的消息吧?」我想,「哎,年少成名真的好煩。」——可我定睛一看,這是一個新建的工作群組,群組名稱是「事故調查」,我一下就懵了。
打開群聊一看:「Han,你的產品,出事了。」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啥?不對,不可能,我不信!因為,我可是監測了一天回測數據,全都正常啊!我當然不可能就這樣接受這個消息,畢竟,捷報我都發了,現在有問題,真的是啪啪打臉啊!
但是,事實果然如此:客服部門收到大量用戶投訴,一大部分用戶的App無法正常使用了。透過事故運行記錄分析,確實是因為我寫的那部分程式碼出了問題。我只能緊急地把新產品下線,灰溜溜地低下了頭。這時,我再看同事的目光,隱隱覺得他們的眼神裡流露著嘲笑和諷刺。
哎,工作以後第一次炫耀,就這麼失敗了,以出醜告終。
出了事,就要調查原因。可是,我自己搞了好幾天都沒什麽進展。因為真的是,所有傳回來的數據都表示,用戶沒有任何異常呀!這幾乎是一個悖論:數據顯示沒問題,但是用戶就是會投訴有問題。
肯定是哪裡出錯了。
直到有一天我去公司的咖啡廳,和同事Tommy閒聊。他問起我的近況,我就說了這件事。之後,Tommy語重心長地跟我說:「Han,你聽說過倖存者偏差嗎?」
倖存者偏差
Tommy跟我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空軍為了減少傷亡,分析了所有飛回來的戰鬥機的中彈統計,如下圖所示。
人們發現,安全回來的戰鬥機,都是機翼上彈痕多,而機頭和機身的彈痕分布都不明顯。因此,大家普遍都覺得,為了加固飛機,應該重點關注機翼位置。這時,一個統計學教授亞伯拉罕・沃爾德(Abraham Wald)卻說,不對,最應該加強的部分,不應該是有很多彈痕的地方,而應該是機頭和機身。因為一旦機頭和機身中彈,整個飛機會損壞嚴重而被擊落,根本就沒有機會飛回來。
聽完之後,我靈光乍現,趕緊回去重新調查我的事故。
最終發現,原來,只有對於那些沒問題的用戶,產品數據才會被成功傳回來,系統才有記錄。而對於那些App有問題的用戶,因為App會直接閃退,相關的數據回傳程式碼不會運行,因此我們後台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回傳數據!其實,它們就是那些被提前擊落的戰機啊!所以,這才造成了後端檢測數據一切正常的假象。
「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是一個典型的統計學「統計偏差」概念,也是一個可以在生活中廣泛應用的原理,也可以被理解成「沉默的大多數」理論。其實質就是,在進行統計分析的時候,人們忽略了樣本的隨機性和全面性而造成了錯誤。因為人們只對部分人做了分析,從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而在真實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就是因為一部人沒有發聲,或者不能發聲,從而讓倖存者偏差更容易產生,我們一定要多多注意。
例如「讀書無用論」經常充斥在咱們耳邊。經常有人會說「讀書有什麽用,你看誰誰誰,連小學都沒畢業,不還是成功了。」其實,絕大部分失敗者,因為並沒有被媒體報導,而自己又沒有能力發聲被公眾注意,就等於被迫選擇了沉默,最終大眾並沒有辦法知道。如果能夠得到完整數據,並計算確切的比例,我們可以發現,那些獲得高學歷的人,其實成功的機率更大。
還有,「飛機太不安全了,一天天總出事故」也是錯的。飛機是目前人類發明的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只不過是因為大部分空難都會被報導,讓你知道了,所以你覺得飛機出事的機率很高。而其他的如汽車等交通工具的事故,大多數並沒有被報導,因此就有了誤解。
另外,身邊還會經常出現這種現象:一部電影在影評網站上得分很差,可是周圍朋友對其評價還不錯。其實這同上面說的是一樣的道理。因為覺得電影「還能看得過去」的人,並不會在影評網站發表評論,反而是那些覺得電影很差的人,會怒氣沖沖地到網站上打上很低的分數。
再如,「愛笑的女生運氣都不會差」,其實,運氣差的話根本笑不出來。還有,「為什麽爸媽不挑食」,因為他們在買菜的時候,都已經挑過了。
3.1你們Netflix的人,說話都這麼直接嗎?
本節關鍵詞:高自由度
從雅虎到Netflix的不適應
我先來給你講一個矽谷員工跳槽的故事。
2017年6月,在矽谷屹立22年的老店雅虎,被威訊(Verizon)以45億美元收購。1995年成立的雅虎(Yahoo)作為互聯網先驅,曾經叱吒全球互聯網行業。它以搜索引擎起家,曾經和谷歌二分天下,市值一度超過1000億美元。它還為整個互聯網貢獻了免費服務的「盈利模式」——對用戶免費,向商家收費,利用廣告賺錢。這一模式,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兩大矽谷互聯網巨頭,谷歌和Facebook:直到2018年末,這兩家公司的最大營收來源依然是廣告業務。
除了沒有趕上行動互聯網以及業務布局失敗,這家老店和其他矽谷一線科技企業文化間的不同,可能也是它倒下的原因之一。艾瑞克・柯爾森(Eric Colson)曾經在雅虎負責一個數據分析團隊,在他跳槽到串流媒體巨頭Netflix後,文化的衝擊讓他一時難以適應。
柯爾森在加入Netflix後,很快就發現了兩家企業文化的不同。例如,竟然有底層員工直接在會議上批評他,跟他提出意見:「艾瑞克,你的溝通能力不行,說了半天也沒說到重點。」這種直接的溝通方式一下子讓柯爾森心裡不爽:「哦?我對你們也一堆意見呢!」要知道,他在雅虎的時候,為了照顧底下人的感受,常常要非常迂迴地說事情,自己還曾經為下屬的錯誤買單。
後來,他才知道,原來這麼開誠布公的說話方式,就是Netflix的文化之一。員工之間,上級和下屬之間,坦誠相待非常重要。當面提出問題,當面「挑骨頭」,而不是背後跟別人煽風點火,才是最有效果、成本最低的溝通方式。同時,這也能有效避免辦公室政治。在學會了這一條文化上的不同之後,柯爾森很快地就在3年以內,從普通員工晉升到了數據與工程副總裁的位置。
對於Netflix,有些朋友可能不瞭解。可能僅僅以為它是一家美劇出品公司,因為2013年它製作的一部《紙牌屋》(House of Cards)紅遍全球,也成功闖入大眾視野。
其實,它可是來自矽谷的全球頂尖現代互聯網企業。僅在2018年就頻繁登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封面。美國股票市場將它和其他四家高市值的美國互聯網企業,合稱為FAANG(F代表Facebook,兩個A分別代表亞馬遜和蘋果,N就代表Netflix,G代表谷歌)。2018年,Netflix的市值曾觸頂超過1500億美元,一度超越老牌美國內容巨頭迪士尼公司。它還購買《白夜追凶》版權,創造了外國線上媒體平台購買中國網劇版權的先河。
Netflix是全球頂尖的線上串流媒體平台,中國以它為標竿的公司就是愛奇藝、騰訊視頻和優酷。但是,它和中國影片影音平台的盈利手段又有很多不同。中國的影音媒體通常有兩種盈利模式,也就是付費用戶(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SVOD)和廣告(Advertising Video On Demand,AVOD)。但是Netflix則僅僅使用付費訂閱模式。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Netflix的全球會員數量已經達到了1.37億,位居全球影音訂閱類平台第一。
為什麽Netflix能有這麼強大的戰鬥力?按照Netflix前人力資源總監帕蒂・麥克科德(Patty McCord)在她出版的《給力》(Powerful)圖書中的介紹,Netflix是用21世紀的企業文化在戰鬥,他們完全擺脫了整個20世紀發展起來的、煩人且複雜的管人系統。Netflix希望它的員工能夠上來挑戰領導,無拘無束地提出反駁意見,也希望領導層能以身作則,積極面對挑戰,持續溝通。這樣,才能讓整個組織運轉高效、驅動靈活。
我覺得,鼓勵員工發表自己的觀點,就是讓有創意的想法能夠有機會得以實施。這裡,介紹一個有名的案例。直到今天,很多互聯網平台發布網劇,依然會像傳統電視劇那樣採取「週播」的方式。例如,一個週末播出兩集,而會員可以多看幾集。但是,Netflix從《紙牌屋》開始就開創了一次性撥出一整季的創新策略,目的就是為了讓用戶爽。當然,這必然會對會員留存數據有一定的影響,可能很多人看完節目以後就退訂了。但是,這也正向刺激了公司持續不斷地生產新的優質原創內容。這個「一次性播放一季」的想法,最初就是一個基層員工提出來的,最終被CEO直接採納,並延續至今。
為了激勵大家能夠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Netflix還鼓勵員工經常在開會的時候做一項練習,叫作「開始,停止和繼續」(Start, Stop and Continue)。這可以在一對一的會議中進行: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這段時間的工作表現進行總結,告訴這個人哪裡做得好應該繼續,哪裡做得不好應該停止,還有哪些事情之前沒有做,現在可以做了。這個練習也可以在團隊會議中進行,總結對象就是整個團隊近期的業務表現。
當然,我在這裡一定要指出的是,「說話直接」並不等於不講究溝通的方式方法,而是在強調說話的內容要切中問題和要害。至於流行於矽谷的具體溝通技巧,我將會在本書第五章詳細介紹。
其實,Netflix代表了整個矽谷的最新科技行業企業文化,上面提到的開放式溝通也被其他矽谷企業所推崇。早在2009年,Netflix的CEO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就把企業文化和架構的總結以PPT的形式放在了網上公布。最終,這份被人們稱為「矽谷重要文件」的閱讀和下載量竟然突破了1500萬次。雖然Netflix的企業文化有著它對於串流媒體行業運作的獨特部分,但是其整體思想,依然是整個矽谷互聯網企業所廣泛推崇的。總結起來就是給員工足夠的自由,包括給上級隨時指出問題的自由。
本節關鍵詞:感知價值、努力錯覺、不流暢度、峰值終值
產品體驗快了還不好
我們在做互聯網產品的時候,無論是一個網頁端產品還是移動端App,都默認整個體驗應該是愈快、愈流暢愈好。所以,我們工程師夜以繼日地工作以提升軟體速度和各項工程指標,設計師和產品經理也努力優化產品流程,省略各種不需要的交互體驗。
但是,在某些時候,過於快速和流暢的體驗可能並不能提高用戶滿意度,反而會讓用戶感覺不爽。我們先從2011年由哈佛商學院學者萊恩・伯爾(Ryan Buell)和麥可・諾頓(Michael Norton)發表在《管理科學》(Management Science)期刊上的著名研究論文《努力錯覺》(The Labor Illusion)說起。
2010年前後,行動網路剛普及,甚至3G技術也才剛剛興起。那時候,大家使用的主要是電腦端的網頁產品,而且因為演算法和很多基礎架構都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完善,產品的運算速度普遍較慢。哈佛大學商學院就進行了一個實驗,想瞭解一下用戶對產品運行速度的感知情況。他們設計了下面這個實驗。
他們虛構了一個機票線上預訂平台Travel Finder,邀請受試者使用。他們把受試者分成了兩組。當受試者點擊「搜尋」按鈕之後,用戶會根據自己所在實驗組的不同,進而得到不同的軟體回應時間。一組用戶會立即看到航班結果,而另一組用戶,則強制有一定的延遲,如故意延遲10秒、20秒等,之後再顯示搜尋結果。其他所有的用戶體驗細節、操作介面等都完全一致,唯一的實驗變量,就是程式的回應時間。
在實驗結束後,他們會要求受試用戶對剛剛的整個過程給出一個分數。滿分為7分,感覺用戶體驗良好,則給分較高;反之,則給分較低。實驗結果如下。
如果頁面的響應時間過長,如60秒,評分會降低很多。這一點非常符合們的預期,畢竟等了這麼久,肯定會煩躁不安,整個用戶體驗就會下降。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如果給予「適當」的回應延遲,用戶體驗的評分居然會升高!比如故意延遲10秒,用戶評分居然提升了2%。不要覺得這個2%很少,因為這個分數別說升高,就算是沒有降低,都已經足夠讓人驚訝和顛覆認知。
哈佛大學在對這些受試者走訪以後,才知道了用戶的想法。原來,他們覺得,如果搜尋結果立刻展示出來,好像系統在騙他們。因為根據人們的認知,進行這麼複雜的全網搜索,還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Uber:對,我們是故意讓它難用的
優步(Uber)公司早年間有一個著名的案例,它因為體驗過於流暢,引發大量不滿和投訴。
Uber當年剛剛推出的時候,創新地提出了一個概念叫作尖峰價格(Surge Price)。對於這個概念,現在的你應該早就能夠理解了。這個跟滴滴的「動態調價」是一樣的,就是經濟學最基本的供需曲線的體現。可是,這個服務模式在Uber剛剛上線的時候,很多人並不知道。
在Uber上市早期,他們在用戶中廣泛宣傳的產品核心是「一鍵叫車」(One Tap To Ride),也就是叫車體驗非常流暢,愈快愈好。所以他們的產品設計就要簡潔、流暢,多餘的步驟一律都要省略。所以在叫車的時候,即使是在尖峰時段,Uber也依然是一鍵叫車。即使出現了價格飆升,他們也不會多做提示,僅僅在網頁頭版(above the fold)標注翻倍金額。
因為叫車體驗太流暢了,很多用戶壓根兒沒有注意價格提升了,直到下車扣款時才發現。雖然這個尖峰價格警告在用戶等車的時候已然顯示,可是用戶就是看不見。這給早期的Uber帶來了非常大的公關壓力。比較著名的例子是,2013年紐約暴雪,Uber價格上漲到8.3倍,好多人急著回家都沒注意加價,到家一看,「20分鐘的車程居然收了500美元!」每逢大型節日活動都是Uber的公關危機。
Uber被很多用戶指責是「騙子」公司,收黑心錢。要知道,對於一般的初創公司,這樣的評論十分危險。
很快Uber就做出了調整,他們推出了下面這一版方案。當出現尖峰價格狀態的時候,Uber不再是「一鍵」叫車,而是「兩鍵」。當用戶在頭版點擊了「叫車」按鈕之後,系統自動額外彈出一頁明顯的加價訊息讓用戶確認。
但是,這個設計上線之後,抱怨聲還是沒有減少,依然有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加價。因為文字太多,金額數字又很小。你想,那些晚上剛從酒吧出來的人,如果喝醉了,文字根本就看不懂。而且,很多用戶以為這就是一個普通的用戶協議,看都沒看就點擊「ok」按鈕了。
沒辦法,Uber又回去更改體驗流程,最終變成了這樣,堪稱忍無可忍的殺手鐧。Uber不僅會導入額外的訊息確認頁面,同時那個翻倍的數字也變得非常醒目,顏色和字體大小都非常明顯。而且關鍵的是,它居然還要讓用戶手動地輸入一遍這個倍數,這簡直是「喪心病狂」。
終於,公關問題解決了。Uber故意讓產品體驗流程變差,卻成功地教育了用戶,化解了危機。其實,矽谷現在有這樣一個概念,叫產品的「不流暢度」(Disfluency)。「讓產品流程變差」就是增加產品的「不流暢度」。
行為經濟學家施洛莫・貝納齊(Shlomo Benartzi)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2017年出版的圖書《螢幕陷阱》(The Smarter Screen)中指出,用戶對產品的「重視程度」和「不流暢度」,呈「倒U形曲線關係」,如下圖所示。
也就是說,太流暢和太複雜的體驗都會喪失用戶的重視。
另外,研究還指出,愈流暢的體驗,愈方便用戶理解,但用戶也愈容易遺忘。這其實符合人類的記憶機制和遺忘規律。
回想一下自己,你是不是這樣,聽了好多音檔課程,當時在聽的時候,覺得理解得好透徹,可是聽過之後,就幾乎忘光了。這背後的一個原因就是,「聽」是比「閱讀」更流暢的一種體驗,所以更容易讓人遺忘。
這可能是因為人都不太珍惜輕易能獲得的東西吧。你看,經常出現很多男生去追同一個女生,這可能是因為「難追」才有意思,太好追了反而沒成就感了。
看了Uber的例子,在產品當中怎樣利用「不流暢性」呢?在你想讓用戶注意的情況下導入。
例如,你的團隊負責一個借款App,為增加借款人的「敬畏心」,讓他及時還款,可以把貸款的流程設計得略微複雜些,可以用額外的視窗來向借款人提醒——「借款期90天,逾期不還,拿磚頭砸你們家玻璃喲!」當然了,這一定會伴隨著中間用戶流失率的提升,但是你們篩選掉了一些不還款的「高風險」用戶,整體看來,未嘗不是一種收益呀。
對了,這裡還要指出,人是會改變的。也就是說,2011年的時候讓用戶等待10秒,跟2019年讓用戶等待10秒,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上面的例子,僅做參考,平時工作時還要根據情況適時應對。
2.1我剛工作就出醜,只因不懂統計學
本節關鍵詞:統計偏差(statistical bias)
從一件糗事說起
話說,當年我剛畢業開始工作的時候,總覺得作為一名軟體工程師,只要做好程式設計(programming)工作就萬事大吉了。可是,我工作出的第一個大醜,卻不是因為程式設計技術不行,而是不懂統計學鬧出的笑話。下面,我就把這個故事分享給你。
那時,我剛剛畢業。進入矽谷工作兩個月後,我人生中第一個重大專案終於完成了。這天傍晚下班前,我們決定向全球發布這個新功能。新功能上線後,效果真的非常不錯,我們可以清晰地可以看到各項指標瘋狂上漲,短短幾個小時,就已經達到了我們對這個季度的業務預期。於是,我就開心得早早回家慶祝了。
第二天早上到公司,我發現,我們團隊辦公桌旁邊牆上掛的數據大螢幕居然壞了——因為數據太好,讓顯示系統崩潰了。我暗自笑笑,悠閒地去吃了個全套英式早餐,之後,優雅地邊喝茶邊發了內部捷報——新產品上線,12小時打破歷史紀錄。
然後,就是各種人故意路過我的辦公桌,給我打招呼恭喜。畢竟,一個剛入職的畢業生,能在兩個月內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十分難得。很快,到下班時間了,當我即將歡快地唱起《難忘今宵》並闔上電腦離開的時候,突然,產品經理給我發訊息——「又是祝賀的消息吧?」我想,「哎,年少成名真的好煩。」——可我定睛一看,這是一個新建的工作群組,群組名稱是「事故調查」,我一下就懵了。
打開群聊一看:「Han,你的產品,出事了。」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啥?不對,不可能,我不信!因為,我可是監測了一天回測數據,全都正常啊!我當然不可能就這樣接受這個消息,畢竟,捷報我都發了,現在有問題,真的是啪啪打臉啊!
但是,事實果然如此:客服部門收到大量用戶投訴,一大部分用戶的App無法正常使用了。透過事故運行記錄分析,確實是因為我寫的那部分程式碼出了問題。我只能緊急地把新產品下線,灰溜溜地低下了頭。這時,我再看同事的目光,隱隱覺得他們的眼神裡流露著嘲笑和諷刺。
哎,工作以後第一次炫耀,就這麼失敗了,以出醜告終。
出了事,就要調查原因。可是,我自己搞了好幾天都沒什麽進展。因為真的是,所有傳回來的數據都表示,用戶沒有任何異常呀!這幾乎是一個悖論:數據顯示沒問題,但是用戶就是會投訴有問題。
肯定是哪裡出錯了。
直到有一天我去公司的咖啡廳,和同事Tommy閒聊。他問起我的近況,我就說了這件事。之後,Tommy語重心長地跟我說:「Han,你聽說過倖存者偏差嗎?」
倖存者偏差
Tommy跟我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空軍為了減少傷亡,分析了所有飛回來的戰鬥機的中彈統計,如下圖所示。
人們發現,安全回來的戰鬥機,都是機翼上彈痕多,而機頭和機身的彈痕分布都不明顯。因此,大家普遍都覺得,為了加固飛機,應該重點關注機翼位置。這時,一個統計學教授亞伯拉罕・沃爾德(Abraham Wald)卻說,不對,最應該加強的部分,不應該是有很多彈痕的地方,而應該是機頭和機身。因為一旦機頭和機身中彈,整個飛機會損壞嚴重而被擊落,根本就沒有機會飛回來。
聽完之後,我靈光乍現,趕緊回去重新調查我的事故。
最終發現,原來,只有對於那些沒問題的用戶,產品數據才會被成功傳回來,系統才有記錄。而對於那些App有問題的用戶,因為App會直接閃退,相關的數據回傳程式碼不會運行,因此我們後台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回傳數據!其實,它們就是那些被提前擊落的戰機啊!所以,這才造成了後端檢測數據一切正常的假象。
「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是一個典型的統計學「統計偏差」概念,也是一個可以在生活中廣泛應用的原理,也可以被理解成「沉默的大多數」理論。其實質就是,在進行統計分析的時候,人們忽略了樣本的隨機性和全面性而造成了錯誤。因為人們只對部分人做了分析,從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而在真實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就是因為一部人沒有發聲,或者不能發聲,從而讓倖存者偏差更容易產生,我們一定要多多注意。
例如「讀書無用論」經常充斥在咱們耳邊。經常有人會說「讀書有什麽用,你看誰誰誰,連小學都沒畢業,不還是成功了。」其實,絕大部分失敗者,因為並沒有被媒體報導,而自己又沒有能力發聲被公眾注意,就等於被迫選擇了沉默,最終大眾並沒有辦法知道。如果能夠得到完整數據,並計算確切的比例,我們可以發現,那些獲得高學歷的人,其實成功的機率更大。
還有,「飛機太不安全了,一天天總出事故」也是錯的。飛機是目前人類發明的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只不過是因為大部分空難都會被報導,讓你知道了,所以你覺得飛機出事的機率很高。而其他的如汽車等交通工具的事故,大多數並沒有被報導,因此就有了誤解。
另外,身邊還會經常出現這種現象:一部電影在影評網站上得分很差,可是周圍朋友對其評價還不錯。其實這同上面說的是一樣的道理。因為覺得電影「還能看得過去」的人,並不會在影評網站發表評論,反而是那些覺得電影很差的人,會怒氣沖沖地到網站上打上很低的分數。
再如,「愛笑的女生運氣都不會差」,其實,運氣差的話根本笑不出來。還有,「為什麽爸媽不挑食」,因為他們在買菜的時候,都已經挑過了。
3.1你們Netflix的人,說話都這麼直接嗎?
本節關鍵詞:高自由度
從雅虎到Netflix的不適應
我先來給你講一個矽谷員工跳槽的故事。
2017年6月,在矽谷屹立22年的老店雅虎,被威訊(Verizon)以45億美元收購。1995年成立的雅虎(Yahoo)作為互聯網先驅,曾經叱吒全球互聯網行業。它以搜索引擎起家,曾經和谷歌二分天下,市值一度超過1000億美元。它還為整個互聯網貢獻了免費服務的「盈利模式」——對用戶免費,向商家收費,利用廣告賺錢。這一模式,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兩大矽谷互聯網巨頭,谷歌和Facebook:直到2018年末,這兩家公司的最大營收來源依然是廣告業務。
除了沒有趕上行動互聯網以及業務布局失敗,這家老店和其他矽谷一線科技企業文化間的不同,可能也是它倒下的原因之一。艾瑞克・柯爾森(Eric Colson)曾經在雅虎負責一個數據分析團隊,在他跳槽到串流媒體巨頭Netflix後,文化的衝擊讓他一時難以適應。
柯爾森在加入Netflix後,很快就發現了兩家企業文化的不同。例如,竟然有底層員工直接在會議上批評他,跟他提出意見:「艾瑞克,你的溝通能力不行,說了半天也沒說到重點。」這種直接的溝通方式一下子讓柯爾森心裡不爽:「哦?我對你們也一堆意見呢!」要知道,他在雅虎的時候,為了照顧底下人的感受,常常要非常迂迴地說事情,自己還曾經為下屬的錯誤買單。
後來,他才知道,原來這麼開誠布公的說話方式,就是Netflix的文化之一。員工之間,上級和下屬之間,坦誠相待非常重要。當面提出問題,當面「挑骨頭」,而不是背後跟別人煽風點火,才是最有效果、成本最低的溝通方式。同時,這也能有效避免辦公室政治。在學會了這一條文化上的不同之後,柯爾森很快地就在3年以內,從普通員工晉升到了數據與工程副總裁的位置。
對於Netflix,有些朋友可能不瞭解。可能僅僅以為它是一家美劇出品公司,因為2013年它製作的一部《紙牌屋》(House of Cards)紅遍全球,也成功闖入大眾視野。
其實,它可是來自矽谷的全球頂尖現代互聯網企業。僅在2018年就頻繁登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封面。美國股票市場將它和其他四家高市值的美國互聯網企業,合稱為FAANG(F代表Facebook,兩個A分別代表亞馬遜和蘋果,N就代表Netflix,G代表谷歌)。2018年,Netflix的市值曾觸頂超過1500億美元,一度超越老牌美國內容巨頭迪士尼公司。它還購買《白夜追凶》版權,創造了外國線上媒體平台購買中國網劇版權的先河。
Netflix是全球頂尖的線上串流媒體平台,中國以它為標竿的公司就是愛奇藝、騰訊視頻和優酷。但是,它和中國影片影音平台的盈利手段又有很多不同。中國的影音媒體通常有兩種盈利模式,也就是付費用戶(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SVOD)和廣告(Advertising Video On Demand,AVOD)。但是Netflix則僅僅使用付費訂閱模式。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Netflix的全球會員數量已經達到了1.37億,位居全球影音訂閱類平台第一。
為什麽Netflix能有這麼強大的戰鬥力?按照Netflix前人力資源總監帕蒂・麥克科德(Patty McCord)在她出版的《給力》(Powerful)圖書中的介紹,Netflix是用21世紀的企業文化在戰鬥,他們完全擺脫了整個20世紀發展起來的、煩人且複雜的管人系統。Netflix希望它的員工能夠上來挑戰領導,無拘無束地提出反駁意見,也希望領導層能以身作則,積極面對挑戰,持續溝通。這樣,才能讓整個組織運轉高效、驅動靈活。
我覺得,鼓勵員工發表自己的觀點,就是讓有創意的想法能夠有機會得以實施。這裡,介紹一個有名的案例。直到今天,很多互聯網平台發布網劇,依然會像傳統電視劇那樣採取「週播」的方式。例如,一個週末播出兩集,而會員可以多看幾集。但是,Netflix從《紙牌屋》開始就開創了一次性撥出一整季的創新策略,目的就是為了讓用戶爽。當然,這必然會對會員留存數據有一定的影響,可能很多人看完節目以後就退訂了。但是,這也正向刺激了公司持續不斷地生產新的優質原創內容。這個「一次性播放一季」的想法,最初就是一個基層員工提出來的,最終被CEO直接採納,並延續至今。
為了激勵大家能夠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Netflix還鼓勵員工經常在開會的時候做一項練習,叫作「開始,停止和繼續」(Start, Stop and Continue)。這可以在一對一的會議中進行: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這段時間的工作表現進行總結,告訴這個人哪裡做得好應該繼續,哪裡做得不好應該停止,還有哪些事情之前沒有做,現在可以做了。這個練習也可以在團隊會議中進行,總結對象就是整個團隊近期的業務表現。
當然,我在這裡一定要指出的是,「說話直接」並不等於不講究溝通的方式方法,而是在強調說話的內容要切中問題和要害。至於流行於矽谷的具體溝通技巧,我將會在本書第五章詳細介紹。
其實,Netflix代表了整個矽谷的最新科技行業企業文化,上面提到的開放式溝通也被其他矽谷企業所推崇。早在2009年,Netflix的CEO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就把企業文化和架構的總結以PPT的形式放在了網上公布。最終,這份被人們稱為「矽谷重要文件」的閱讀和下載量竟然突破了1500萬次。雖然Netflix的企業文化有著它對於串流媒體行業運作的獨特部分,但是其整體思想,依然是整個矽谷互聯網企業所廣泛推崇的。總結起來就是給員工足夠的自由,包括給上級隨時指出問題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