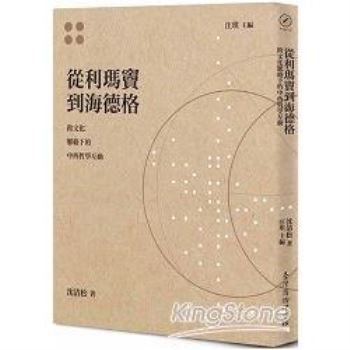第一講
引言
一、從比較哲學轉向跨文化哲學
本書所關心的是中、西兩方文明自從西方現代性開始形成以來,彼此核心思想的互動、互譯和對談;我主要是從跨文化哲學(intercultural philosophy)的角度來探討,不同於過去所謂中西比較哲學,僅滿足於比較中、西哲學的同與異,然後再判斷何優、何劣。我認為處於今日全球化時代,我們不能再滿足於比較哲學。我要追問:到底是為了什麼而進行比較?
對我而言,之所以要進行比較,其實是為了進一步彼此互動、交談,甚至進一步達到相互豐富,而不只是為比較而比較。由此可見,某種跨文化互動的意圖,應優先於不同的文化/哲學/宗教比較研究。過去的比較研究,要不是在國家主義或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主導下,認為透過比較,可以顯出自己比別人優越,這其實已經有了自我中心的預設觀點;要不然,則是在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主導下,不管是文化殖民或學術殖民,甚至產生了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所謂「東方主義」(orientalism)。過去西方研究近東、中東、遠東,乃至中國的漢學,往往建構了一套讓對方藉以達成自我瞭解的學術眼鏡,讓對方戴著這套眼鏡來看自己,甚至瞭解自我。中國過去也曾遭受如此對待,而世界上許多國家也常在東方主義籠罩下,透過西方學者建構的觀點,不論是英國、歐陸或美國學術的框架,來進行自我瞭解,甚至以此為榮。例如:最近我在中國大陸曾遇到一些專研西方哲學的學者,只因為自己懂得外國語文,會講論西方哲學,便有意無意的睥睨專研中國哲學的同事,使我驚覺某種自作自受的新東方主義的陰影。其實,如此崇洋媚外的態度已經不再合適於今日。今日我們應透過跨文化互動,既以多元他者之優點豐富自己,也以自己之長處豐富多元他者。
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不能再沉溺於過去那種殖民主義壓迫下的自戀式悲情,認為當今一切問題都是出自過去承受殖民壓迫的結果。無論如何,總是帶著多重悲情討論問題。如今中華人民已經站立腳跟,且世界已然進入全球化時代,我們應避免再度任憑別人甚或自己組構新東方主義眼鏡。如今,無論接受或進行學術殖民,都已不再是公正的學術行為。
由於前述國家主義與東方主義的殘餘影響所造成的陰影仍在,我們應該正式審視我們與多元他者的關係。我用「多元他者」(many others)這一概念來代替後現代主義所侈言的「他者」(the Other),尤其是法國後現代主義,像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雷味納思(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這些人所強調的「他者」(L’autre, l’alterité)。對我而言,實際在人類生活中環繞著我們的,並不是一抽象的「他者」,而是實實在在的多元他者。所謂「他者」是哲學抽象的結果,而且多少隱含某種「自我」和「他者」之間的二元對立。這是「他者」概念無法避免的。我主張「多元他者」,這在中國哲學裡也有其根源。無論道家講的「萬物」、佛家講的「眾生」,或是儒家講「五倫」,甚至還可增加到第六倫、第七倫、甚或第八倫等等,無論如何,中國哲學無論儒、釋、道,講的都是多元他者,而不是抽象的、單純的他者。當前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所遭遇到都是多元他者。
不過,若就「現代性」(modernity)的習取來講,我們必須知道,現代性的形成有其歷史參照點,那就是西方自從西歐文藝復興以後逐漸形成的近代世界。雖然我們現在用「現代性」(modernities)這一語詞已經是多數、多元意義的,而且世界各國因著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資源,都可以有不同的資源進入現代性。也因此,我要從正面、積極的觀點來提倡「中華現代性」1。但我們仍須以歐洲文藝復興乃至啟蒙運動以後逐漸形成的西方現代性為參考架構。因此,我雖然主張在全球化過程中進行與多元他者的互動,但事實上,大家仍面對著如何超越現代性困境的挑戰。這也是中國近兩百年歷史所遭受的挑戰,也就是現代性的衝擊、習取以及超越的大問題。中國在被納入西方現代性軌跡過程中,曾遭遇到種種問題。就現代性的追求、困境和超越這條主線來講,西方的確是華人的「他者」,雖然我們與這一「他者」並不一定要成為「對立」的,反而應該是「對話」的。
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主張「互認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他的這一概念類似從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主奴關係」轉來的「互認關係」(Anerkennung),也就是超越主人對奴隸的宰制,轉變為主體對主體的尊重。我認為泰勒本是研究黑格爾的,並由此發展出「互認的政治」概念,大體說來也只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概念的延伸。然而,在我看來,「互為主體」概念仍然只是近代「主體性」(subjectivity)概念進一步的延伸,由「主體」轉為「互為主體」,也就是:你是主體,我也是主體,我們相互承認主體的地位。如此的互認,我認為僅只是一最低限度的要求,其實仍然不足。因為我觀察當前許多民族之間的關係,尤其某些國家針對其原住民,主政或當道的民族雖然可以承認你,不過仍然任憑你自己以主體的地位自生自滅;既不以我的文化豐富你,也不習取你的文化長處。例如,不習取原住民與自然相處的環保經驗,也不教導原住民適宜的現代性精粹。原住民本來在田野裡奔跑之時都是英雄,可是由於缺乏現代的知識與技能,在大都會裡不易適應,甚或淪為無業遊民。我要說的,是多元文化政策不能僅止於承認他們,還要設法豐富他們,也以他們的質樸精神和與大地的親和關係,豐富這日愈疏離的都市文明。
所以,我主張從最低要求的「相互承認」邁向最佳化(optimal)的「相互豐富」。在全球化過程中,這才是真正的最佳態度。我的意思是:希望能超越主體哲學的弊端,邁向多元他者但仍不必放棄主體。為甚麼不像後現代所提倡的,乾脆從「主體」轉向「他者」呢?因為對我而言,近代哲學最大的遺產之一就是對主體性的肯定與開發。我也不願自限於互為主體,只肯定自己的主體性也肯定別人的主體性而已,而是更要向多元他者開放,並追求相互豐富。的確,後現代主義揭示從「主體」轉向「他者」;我則更要由「他者」轉向「多元他者」。然而,在我的「多元他者」概念裡面,仍然有著主體和互為主體的地位,因為每一位多元的他者都仍是主體,也都應該以互為主體相待;然而,每一位主體都不該自我封限於己,相反的,卻都要能超越自我封限並慷慨走出,邁向多元他者;走出互為主體,朝向其他的陌生人開放。心中常存多元他者,進行外推,並在相互外推的過程中相互交談,甚至達至相互豐富。這是我主要的想法。
在此,涉及我所謂的外推策略,依順序可以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要進行「語言的外推」,就是把自己的哲學與文化傳統中的論述或語言翻譯成其他哲學與文化傳統的論述或語言,或其他傳統所能夠了解的語言,看它是否能藉此獲得理解或因此反而變得荒謬。如果是可獲理解,這代表此一哲學與文化傳統有更大的可普化性;如果是後者,則必須對這傳統進行反省和自我批判,而沒有必要採取自衛或其他更激進的護教形式。當然,這其中總會有一些不能翻譯的殘餘或意義的硬核,但其中可共同分享的可理解性便足以證明它自身的可普化性。如果人們只能在自己的傳統中誇耀自家的哲學多麼有意義,就像一些國粹派哲學家所堅持和宣稱的那樣,這至多只證明了它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它的優越性。
外推的第二步,是「實踐的外推」。藉此我們可以把某一種文化脈絡中的哲學理念或文化價值或表達方式,從其原先的文化脈絡或實踐組織中抽出,移入到另一文化或組織脈絡中,看看它在新的脈絡中是否仍然是可理解或可行,或是不能適應新的脈絡,反而變得無效。如果它仍然能起作用,這就意味著它有更多實踐的可能性,並在實踐上有更高的可普化性。否則,它就應該對自己的局限進行反省和自我批判。
外推的第三步,是「本體的外推」。藉此我們從一個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出發,經由對於實在本身的直接接觸或經由終極實在的開顯的迂迴,進入到另一個微世界、文化世界、宗教世界。尤其當在該傳統中具有某種宗教向度之時,或者當人們進行宗教間的對話時,這一階段的外推就顯得特別重要。如果對話者本身沒有參與終極實在的體驗,宗教交談往往會流於膚淺表面。我們對於終極實在的體驗,如果確實是終極的,就該具有可普化性和可分享性,否則若只自我封閉地一味堅持自己的真理唯一,這至多只能是宗教排他主義的一個藉口而已。
哲學與宗教的交談,應該建立在相互外推的基礎上。詳言之,在A群體和B群體的交談中,在語言外推的層面上,A應該把他主張的命題或理念、價值、信仰系統轉換成B的語言或對於B來說能夠理解的語言。同時,B也應把自己主張的命題或理念、價值、信仰系統用A的語言表達或轉化成A能理解的語言。在實踐的外推層面,A應該把自己主張的命題、設定的真理、文化表達形式、價值、宗教信仰等從自己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抽出,將它重新放置於B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同時,B也應該把自己的主張、設定的真理、文化表達形式、價值、宗教信仰等從自己的社會、組織、實踐的脈絡中抽出,並將它重置於A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在本體外推的層面,A應致力於經由實在本身的迂迴,如對人、對某一社會群體、對自然或終極實在的親身體驗,進入B的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同時,B也應該努力經由實在本身的迂迴,進入A的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
在以上透過相互外推以達至相互豐富的基本想法下,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中」與「西」的概念的歷史形成,也可以藉此貞定,他們為何在過去歷史中,未能達至理想狀態的互動關係。
1參見沈清松主編,《中華現代性的探索:檢討與展望》,台北:政大出版社,二○一三年。
引言
一、從比較哲學轉向跨文化哲學
本書所關心的是中、西兩方文明自從西方現代性開始形成以來,彼此核心思想的互動、互譯和對談;我主要是從跨文化哲學(intercultural philosophy)的角度來探討,不同於過去所謂中西比較哲學,僅滿足於比較中、西哲學的同與異,然後再判斷何優、何劣。我認為處於今日全球化時代,我們不能再滿足於比較哲學。我要追問:到底是為了什麼而進行比較?
對我而言,之所以要進行比較,其實是為了進一步彼此互動、交談,甚至進一步達到相互豐富,而不只是為比較而比較。由此可見,某種跨文化互動的意圖,應優先於不同的文化/哲學/宗教比較研究。過去的比較研究,要不是在國家主義或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主導下,認為透過比較,可以顯出自己比別人優越,這其實已經有了自我中心的預設觀點;要不然,則是在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主導下,不管是文化殖民或學術殖民,甚至產生了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所謂「東方主義」(orientalism)。過去西方研究近東、中東、遠東,乃至中國的漢學,往往建構了一套讓對方藉以達成自我瞭解的學術眼鏡,讓對方戴著這套眼鏡來看自己,甚至瞭解自我。中國過去也曾遭受如此對待,而世界上許多國家也常在東方主義籠罩下,透過西方學者建構的觀點,不論是英國、歐陸或美國學術的框架,來進行自我瞭解,甚至以此為榮。例如:最近我在中國大陸曾遇到一些專研西方哲學的學者,只因為自己懂得外國語文,會講論西方哲學,便有意無意的睥睨專研中國哲學的同事,使我驚覺某種自作自受的新東方主義的陰影。其實,如此崇洋媚外的態度已經不再合適於今日。今日我們應透過跨文化互動,既以多元他者之優點豐富自己,也以自己之長處豐富多元他者。
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不能再沉溺於過去那種殖民主義壓迫下的自戀式悲情,認為當今一切問題都是出自過去承受殖民壓迫的結果。無論如何,總是帶著多重悲情討論問題。如今中華人民已經站立腳跟,且世界已然進入全球化時代,我們應避免再度任憑別人甚或自己組構新東方主義眼鏡。如今,無論接受或進行學術殖民,都已不再是公正的學術行為。
由於前述國家主義與東方主義的殘餘影響所造成的陰影仍在,我們應該正式審視我們與多元他者的關係。我用「多元他者」(many others)這一概念來代替後現代主義所侈言的「他者」(the Other),尤其是法國後現代主義,像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雷味納思(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這些人所強調的「他者」(L’autre, l’alterité)。對我而言,實際在人類生活中環繞著我們的,並不是一抽象的「他者」,而是實實在在的多元他者。所謂「他者」是哲學抽象的結果,而且多少隱含某種「自我」和「他者」之間的二元對立。這是「他者」概念無法避免的。我主張「多元他者」,這在中國哲學裡也有其根源。無論道家講的「萬物」、佛家講的「眾生」,或是儒家講「五倫」,甚至還可增加到第六倫、第七倫、甚或第八倫等等,無論如何,中國哲學無論儒、釋、道,講的都是多元他者,而不是抽象的、單純的他者。當前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所遭遇到都是多元他者。
不過,若就「現代性」(modernity)的習取來講,我們必須知道,現代性的形成有其歷史參照點,那就是西方自從西歐文藝復興以後逐漸形成的近代世界。雖然我們現在用「現代性」(modernities)這一語詞已經是多數、多元意義的,而且世界各國因著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資源,都可以有不同的資源進入現代性。也因此,我要從正面、積極的觀點來提倡「中華現代性」1。但我們仍須以歐洲文藝復興乃至啟蒙運動以後逐漸形成的西方現代性為參考架構。因此,我雖然主張在全球化過程中進行與多元他者的互動,但事實上,大家仍面對著如何超越現代性困境的挑戰。這也是中國近兩百年歷史所遭受的挑戰,也就是現代性的衝擊、習取以及超越的大問題。中國在被納入西方現代性軌跡過程中,曾遭遇到種種問題。就現代性的追求、困境和超越這條主線來講,西方的確是華人的「他者」,雖然我們與這一「他者」並不一定要成為「對立」的,反而應該是「對話」的。
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主張「互認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他的這一概念類似從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主奴關係」轉來的「互認關係」(Anerkennung),也就是超越主人對奴隸的宰制,轉變為主體對主體的尊重。我認為泰勒本是研究黑格爾的,並由此發展出「互認的政治」概念,大體說來也只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概念的延伸。然而,在我看來,「互為主體」概念仍然只是近代「主體性」(subjectivity)概念進一步的延伸,由「主體」轉為「互為主體」,也就是:你是主體,我也是主體,我們相互承認主體的地位。如此的互認,我認為僅只是一最低限度的要求,其實仍然不足。因為我觀察當前許多民族之間的關係,尤其某些國家針對其原住民,主政或當道的民族雖然可以承認你,不過仍然任憑你自己以主體的地位自生自滅;既不以我的文化豐富你,也不習取你的文化長處。例如,不習取原住民與自然相處的環保經驗,也不教導原住民適宜的現代性精粹。原住民本來在田野裡奔跑之時都是英雄,可是由於缺乏現代的知識與技能,在大都會裡不易適應,甚或淪為無業遊民。我要說的,是多元文化政策不能僅止於承認他們,還要設法豐富他們,也以他們的質樸精神和與大地的親和關係,豐富這日愈疏離的都市文明。
所以,我主張從最低要求的「相互承認」邁向最佳化(optimal)的「相互豐富」。在全球化過程中,這才是真正的最佳態度。我的意思是:希望能超越主體哲學的弊端,邁向多元他者但仍不必放棄主體。為甚麼不像後現代所提倡的,乾脆從「主體」轉向「他者」呢?因為對我而言,近代哲學最大的遺產之一就是對主體性的肯定與開發。我也不願自限於互為主體,只肯定自己的主體性也肯定別人的主體性而已,而是更要向多元他者開放,並追求相互豐富。的確,後現代主義揭示從「主體」轉向「他者」;我則更要由「他者」轉向「多元他者」。然而,在我的「多元他者」概念裡面,仍然有著主體和互為主體的地位,因為每一位多元的他者都仍是主體,也都應該以互為主體相待;然而,每一位主體都不該自我封限於己,相反的,卻都要能超越自我封限並慷慨走出,邁向多元他者;走出互為主體,朝向其他的陌生人開放。心中常存多元他者,進行外推,並在相互外推的過程中相互交談,甚至達至相互豐富。這是我主要的想法。
在此,涉及我所謂的外推策略,依順序可以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要進行「語言的外推」,就是把自己的哲學與文化傳統中的論述或語言翻譯成其他哲學與文化傳統的論述或語言,或其他傳統所能夠了解的語言,看它是否能藉此獲得理解或因此反而變得荒謬。如果是可獲理解,這代表此一哲學與文化傳統有更大的可普化性;如果是後者,則必須對這傳統進行反省和自我批判,而沒有必要採取自衛或其他更激進的護教形式。當然,這其中總會有一些不能翻譯的殘餘或意義的硬核,但其中可共同分享的可理解性便足以證明它自身的可普化性。如果人們只能在自己的傳統中誇耀自家的哲學多麼有意義,就像一些國粹派哲學家所堅持和宣稱的那樣,這至多只證明了它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它的優越性。
外推的第二步,是「實踐的外推」。藉此我們可以把某一種文化脈絡中的哲學理念或文化價值或表達方式,從其原先的文化脈絡或實踐組織中抽出,移入到另一文化或組織脈絡中,看看它在新的脈絡中是否仍然是可理解或可行,或是不能適應新的脈絡,反而變得無效。如果它仍然能起作用,這就意味著它有更多實踐的可能性,並在實踐上有更高的可普化性。否則,它就應該對自己的局限進行反省和自我批判。
外推的第三步,是「本體的外推」。藉此我們從一個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出發,經由對於實在本身的直接接觸或經由終極實在的開顯的迂迴,進入到另一個微世界、文化世界、宗教世界。尤其當在該傳統中具有某種宗教向度之時,或者當人們進行宗教間的對話時,這一階段的外推就顯得特別重要。如果對話者本身沒有參與終極實在的體驗,宗教交談往往會流於膚淺表面。我們對於終極實在的體驗,如果確實是終極的,就該具有可普化性和可分享性,否則若只自我封閉地一味堅持自己的真理唯一,這至多只能是宗教排他主義的一個藉口而已。
哲學與宗教的交談,應該建立在相互外推的基礎上。詳言之,在A群體和B群體的交談中,在語言外推的層面上,A應該把他主張的命題或理念、價值、信仰系統轉換成B的語言或對於B來說能夠理解的語言。同時,B也應把自己主張的命題或理念、價值、信仰系統用A的語言表達或轉化成A能理解的語言。在實踐的外推層面,A應該把自己主張的命題、設定的真理、文化表達形式、價值、宗教信仰等從自己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抽出,將它重新放置於B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同時,B也應該把自己的主張、設定的真理、文化表達形式、價值、宗教信仰等從自己的社會、組織、實踐的脈絡中抽出,並將它重置於A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在本體外推的層面,A應致力於經由實在本身的迂迴,如對人、對某一社會群體、對自然或終極實在的親身體驗,進入B的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同時,B也應該努力經由實在本身的迂迴,進入A的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
在以上透過相互外推以達至相互豐富的基本想法下,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中」與「西」的概念的歷史形成,也可以藉此貞定,他們為何在過去歷史中,未能達至理想狀態的互動關係。
1參見沈清松主編,《中華現代性的探索:檢討與展望》,台北:政大出版社,二○一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