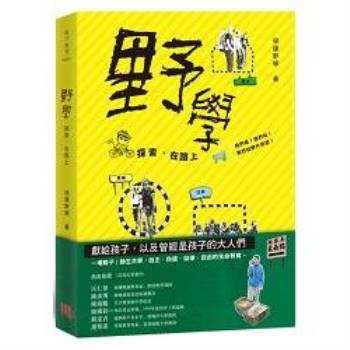■向未知出發
「要找一些憨膽的老師,其實不是很容易,把十幾個學生騙去環島,老師陪著騎,多想幾個萬一,這件事就做不成了,還好我們的老師裡,有這樣熱情的老師。」徐匯中學的校長陳海鵬在二○一四年少年風火輪環島結束後,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其實,最有憨膽的人,就是校長自己。
「一般的校長根本不會鼓勵這樣的活動,很危險,也替自己找麻煩,不是嗎?」許多學生家長都提到,校長敢放手,還強調「這是滿有意義的活動」,建議學生、家長有機會就參加。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旅程都有校長的身影,他再怎麼忙,都會看完學生騎上最危險的壽卡段、攻上雪山頂、玉山頂,或站在岸邊點點人頭,才安心離開。過程裡不干涉帶隊老師,默默地看。
成功,需要一點憨膽
帶孩子騎車、登百岳、泳渡日月潭、泛舟……哪一項不危險?哪一間學校的校長有那麼大膽量?而且,支持一次不打緊,還一回又一回地答應活動繼續辦!只要他說一次「不」,野學帶頭的Dargo老師再怎麼瘋,也很難「光明正大」瘋下去。
在更早更早以前,Dargo老師只能「低調」帶班上學生出門,人數少,不跑遠。爬爬七星山、觀音山,在台北郊區騎騎車,看到孩子們能行光合作用、流流汗,就心滿意足。或者是,每年一次邀請班上學生到家裡作客,採不強迫的預約制,幾個人一組帶著盥洗衣物、書包到家裡打地鋪、聊天,第二天吃他親手做的香噴噴早餐,再一起搭捷運到學校上課。這就是他早些年能為學生在課堂外做到的事。
直到二○一三年,徐匯中學出了一本復校五十周年的紀念專書《熱血男校》,Dargo老師回想起自己就讀徐匯時所遇到的神父與教師,曾經是那麼無私地陪伴孩子,才終於鼓起勇氣要把環島行程帶進教育現場,想要陪著青春少年們在狂飆的歲月裡,「有另類的引導,以及有體驗與學習的機會」。熱血沸騰的他,根本沒想過什麼叫害怕,因為「渴望帶孩子們出去走走看看的心情,已經大過恐懼」。
心臟比大顆
「自從我進徐匯之後,我遇到了一個史上最瘋狂的老師,他舉辦很多正常學校不會辦的活動。」
「崇拜Dargo老師啊!辦這麼多活動,不怕死,只要有一個人受傷就完蛋了,可是他都不怕,帶我們出去玩。」
「Dargo老師像獅子,很敢衝,什麼都不怕,不會擔心後果;可是也很負責,如果發生事情,他會第一個衝出來保護我們。」小孩在路上跑,大人的心揣在口袋裡。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若問:「發生事情怎麼辦?」,「發生就處理啊!」Dargo老師一再地提醒「大人不要忘了自己曾經是小孩」,小孩終究是小孩,如果在騎乘中想嘗試放開雙手,雖然結果有可能頭破血流,大人都要接受。孩子跌倒了就慢慢站起來,迷路了就自己問路回到集合點,輪胎破了就補,「不然呢?」Dargo老師一點也不緊張。
「打從少年風火輪開始,我家老爺就說Dargo老師的心臟鐵定不小顆」,男孩郭宇衡的媽媽Teresa為Dargo老師下了絕佳註解。
校長:「你覺得這個活動怎麼樣啊?明年是否……」
Dargo老師:「腦袋不清楚的時候,再考慮考慮吧!」
第一年少年風火輪環台活動結束,校長與Dargo老師兩人滴滴咕咕。其實,這兩個人的腦袋都不清楚,心臟一個比一個大顆。
■老師,我要報名
二○一五年十二月,野學男孩們一整個月興高采烈的,不是為了過聖誕節,也不是瘋跨年,而是老師、家長們打算要帶大家從木柵動物園踏騎到福隆,月底還有寒假要成行的三百三十公里騎程「花東旭墾」,也即將秒殺報名。
在野學初期,男孩們對報名的反應並不熱烈,通常都是爸媽自做主張,孩子才勉強參加。報名機制也還在摸索中,「報名方式不公平」、「不想輸別人才強迫孩子出門」的雜音紛起;主辦老師與家長們在活動中一起學習怎麼帶孩子,經過逐次修正才找到公平、民主,及對孩子最好的方法。現在,男孩們想參加活動,必須自己索取報名表,並且有一周的時間跟爸媽討論;想通了以後則自己填表、報名、繳費,不再能讓爸媽代勞。
「當我聽到野學要辦花東旭墾活動,我馬上就拿著報名表去跟爸爸說要報名」,男孩張昱閎報名當天,比往常都還要早起床,興奮、期待的心情自是不言而喻。
「自從騎完金山之後,我就開始慢慢地對騎腳踏車有了興趣」,男孩陳義昇說。
「報名的人很多,一下課就有一堆人往外衝。我期待已久的花東旭墾的活動終於到來了」,男孩黃戎瑍說。男孩們都表示,喜歡騎車的速度感,快慢可以自己控制,還能跟好朋友分享過程的辛苦,以及隨著一次又一次的長騎,明顯感受「變得更堅強,不斷超越自我」,騎車比登山的成就感更即時。(有男孩打槍說,「是看太多勵志書了嗎?」)
如今只要野學一發起新活動,報名參與的人數比初次少年風火輪的二十幾人,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的急速爆增,例如:九十九人去了福隆,八十人去了花東旭墾,要不是控制人數,規模恐怕難以想像。
男孩謝忻恩跟媽媽是福隆踏騎的補給車小組之一,擔任沿途看照同學安全與飲食的任務,並不需要加入爭搶名額的激戰中。可是,他對報名這回事也是緊張萬分,深怕好友沒跟上。報名前一日,謝昕恩再三提醒同班同學,並且交代隔壁班的要好朋友,下課不能去打籃球,務必記得先去找Dargo老師報到。
「老師,等一下要準時下課喔,我們要去報名野學!」當天第一堂課,謝忻恩備戰,怕同學出差錯,乾脆自告奮勇先收齊六人份報名表與費用,再跟該堂老師打招呼,鐘一響立即奔出教室。「老師,我要報名」,算算前面的排隊人數,謝昕恩前面只有九個人,好險!
當然,想成功報名不光是比誰衝得快,野學有規定,只要日常生活中有犯規記過的情況,就得停權兩次。因此,男孩們為了要順利參加野學活動,每一位都很在乎個人的日常行為。
但是,就像老師形容的,男孩們都還在「長身體,不長腦袋」的青春期,很容易爆衝,打架、互嗆、踹人等違紀事件很常見。
「拜託幫我跟教官說,好不好?我願意被記過,不想被野學停權,我想去福隆!」某日夜裡,有位男孩到處跟家長、老師們討救兵,因為他那天為了同學偷吃他的餅乾,踹了人,被送到教官室。教官與班導師商量許久,竟然做出「不記過,但野學停權」的決定,一拳打中他的要害。男孩極度渴望參加,不斷地說:「我願意被記過」、「不然,我一個人跟在隊伍後面騎,可以嗎?」無奈,教官一句:「我要讓你的記憶裡沒有『福隆』這兩個字!」重重切斷他的癡心妄想。大人們當時覺得,「這個處分,比記過有效,會讓孩子一輩子都記取教訓」。不過,隨著活動次數多了,老師們回頭檢討:野學不是用品性、成績來衡量要不要讓孩子參加,那麼「犯錯者不能報名」,這做法對嗎?如果孩子在體制內犯錯受處罰,野學又拒絕在外,他們要去哪裡?會不會因為大人剝奪孩子的機會,就改變他們的未來?
阿金老師開始視情節放寬,留給孩子們反省的機會,例如,有位男孩在課堂上吃冰並且大聲嗆他,阿金老師最後也接受男孩真心誠意的道歉,沒取消他野學的報名資格。而Dargo老師聽聞一位男孩現況不穩,常常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於是用了最肉痲的方式安撫他:「過來,抱一下,抱一下!聽話,聽話!」強摘的瓜不甜,強壓下的孩子也無法出頭,愛孩子,就多親近、多理解、多包容他們吧──老師們是這麼想的。
■「陪伴」也是一種關心
野學的活動不走高級行程,所以報名費其實相當便宜,「重要的是去體驗」。花東旭墾要騎五天四夜的費用,自備車只要四千五百元,若需租車則只要六千元;金山踏騎兩天一夜只要一千元;十一天環島四千六百五十元……
雖然野學活動安排不希望受限於體制內的框架,但參與者無論是大人、小孩,對它還是充滿無限想像。前提是,「野學不是徐匯中學附屬旅行社,活動不是廉價旅行團,參加者不能呼來喚去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帶隊的Dargo老師及阿金老師兩人一再強調,野學秉持的是:「付出不營利,體驗非享受」。帶隊老師要繳錢,出力的爸媽要繳錢,校長的錢也要收,大家一起平均分攤費用。甚至,有時經費不足,出錢又出力的家長還得再自掏腰包,負擔沿途支出。
野學,專挑困難的路走
爬新北市郊區的觀音山時,大夥兒不是踩在安山岩修築的人工步道上,而是得走天然的泥土石頭路,也就是「走路要選難路走,挑擔要選重擔挑」的道理。那天爬完山,男孩張育睿回家後跟媽媽說:「爬觀音山第一次這麼累,為何老師有這麼特別的路,跟我們去爬的路線都不一樣!」
野學第一次嘗試泛舟,Dargo老師說:「生命裡有太多的懼怕要超越,在不安全不穩定中見真章,不要怕踏出去。」最常舉辦的騎單車,阿金老師說它包含「人生亦同」的哲理,例如:*看遠方目標,才不會迷失。
*看近的障礙,才不會跌倒受傷。
*不斷地堅持,才可以到目的地。
*時時戰兢保持平衡才不會跌倒。
*平時保養好車子,用時才不會拋錨故障;隨時做好準備,才能抓住機會。
*上坡雖費力,卻安全;下坡,雖省力易危險。
*逆境,雖艱苦卻甘美;順境,雖樂極易生悲。
野學不當旅行團,要帶孩子、大人用雙腳踏行走遍台灣,在體驗之間替小孩建立生命的記憶,建立父母陪伴孩子或孩子陪伴父母的記憶。
陳逸文陳爸帶著一家大小跟著野學跑,無役不與。陳爸說:「家裡以前很窮,唸書時都在打工賺錢,從來沒出去玩過;現在,和兒子一起參加,某種程度是彌補了學生時代的遺憾。」至於陪著爸爸填補青春記憶的兒子陳岳廷,則謝謝爸爸的一路陪伴。陳爸說雖然有時候也想要自由,但是更感謝「帶著這樣走,不會說放著都不管,至少有關心到!」
登雪山時,男孩張雲翔和爸爸相依相伴,張雲翔成了照顧者,細心幫爸爸戴好頭巾,再扛上兩人的大背包;爸爸只管拄著登山杖往前走,其餘由兒子打點。另一位爸爸許皓威,在三六九山莊時就開始盤算兒子許嶢佑如果放棄攻頂,他就可以順理成章藉著「護送」之名撤退,不必再苦苦地陪著爬山;沒想到兒子不放棄,當爸爸的也只能一路相隨。兩位父親在那趟行程裡,都對自己的兒子刮目相看。
「野學做到的,比要求成績來的有感情!」媽媽江維淨與兒子陳加㯋登雪山後,也是心有所感。她說,當兒子問一句:「媽,你衣服有沒有帶夠?」再加上看到另一位男孩李明喆一直陪著落後的媽媽,似乎也在擔心媽媽時,她就「懂了」。
陪小孩到山上走走,小孩子能看見什麼?去騎車真的會體悟人生哲理?泛舟玩水,是要做什麼?「我不知道!」二十幾年來都在男孩堆裡打滾的Dargo老師都這麼說了,「吾家有兒初長成」的野學爸媽當然更懞懂,但是,他們都相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年少時所記憶的山林印象,自當成為年長時前進的記憶,對日後成長應是難以估計的珍貴價值」。
◎Box:自主訓練
假日的大台北近郊,在巴拉卡公路、二重疏洪道、淡水河左岸等地,如果注意看,很容易看見穿著綠T恤的徐匯男孩,大大「野學」兩個字就印在衣服上面。他們或許是三五好友結隊,或許是跟著爸媽幾個家庭一起出門。男孩們說,這叫「約騎」,是一項野學的自主練習活動,平日就要保持體能,到時才不會騎不動。男孩施奇陞和爸媽報名花東縱騎後,用了三周的周末一起集訓。男孩說:「其實這對他們(爸媽)是個極大的挑戰,因為老了骨頭不好了。」
至於登百岳前的訓練,只要能爬幾回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七星山,體能大抵不會有問題。徐匯中學每年五月第二次段考結束的隔天,都會帶新進小國一去爬七星山,釋放考試的壓力。二○一五年五月,野學要登雪山前,正好遇上每年例行的小國一登七星山,恰巧作為行前訓練。男孩王信杰無敵打拚,沿途背了六個同學的書包,要當「雪山,我來了」的負重練習。「累啊!」,王信杰說。
■旅途中的特別任務
二○一五年東花縱騎,阿金老師指派了特殊任務,要每隊在第二天去找大樹、百年教堂,以及和藹可親、有皺紋的老阿公或老阿嬤,並且拍照。一來,希望不只是單純騎車;再來,以小隊做分派,可發揮合作精神。
男孩們一小隊一小隊出發,從台東池上往花蓮光復高職的途中必須完成任務。出發前,老師已提點,老教堂在花蓮的富里小鎮;找到老教堂,就能順道發現周圍有棵大樹;至於老阿公或老阿嬤,則要機靈、有禮地提出拍照邀請。
聽起來,任務很簡單,可惜大部分男孩只顧騎車,順著大路走,不看路標,衝著衝著,小隊一隊隊散掉,錯過進入小鎮的岔路,錯過老教堂與老樹。只有男孩林瑋軒、黄偉哲、陳岳廷等人進入富里,在一家雜貨店買飲料,跟店裡「應該已經有八十歲的老阿嬤很開心地拍照」,是少數完成任務的小組。
那一天達標的沒幾組,完成任務的隊伍可獲頒乖乖桶一桶。Dargo老師說:「這就是孩子,會直接衝,過頭就算了。」於是少數努力完成任務的人,更是值得大家為他們鼓掌。
不可能的任務:寫作文?
旅途中,孩子們覺得「最痛苦的任務是寫作文」。
「怎麼辦,老師竟然說要寫作文耶!」
「別開玩笑!」
少年風火輪環台時,男孩們騎到第九天,回到台灣北端的福隆,Dargo老師集合大人小孩,要求每人交出六百字心得,沒寫完不淮回房睡覺,老師、家長、男孩一視同仁,沒有例外。到了阿金老師加入野學,更堅持所有參與者要「寫作文」,無論登山或騎車,他都希孩男孩們有機會透過文字來自省。於是,在東花縱騎時,車隊投宿光復高職,只見男孩趴在體育館的地板上,振筆疾書。「寫完作文,來換雞排」,潘吉松潘爸與孩子們口中的頴近阿姨買了雞排當宵夜,作為「寫作的動力」,為了吃,誰會不寫呢?
到了花東旭墾的最後一天,幾十個男孩入住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猜想應該會吵雜嬉鬧,然而媽媽邱妤蓁從外面回來,卻發現「鴉雀無聲」、「萬人空巷」,人人都埋頭寫作。原來,那一晚是難得的自由時間,逛墾丁大街比任何事重要,早交差才有時間出去玩。
男孩們覺得寫作文「很痛苦」,對大人來說又何嘗不是。孩子交稿解脫,去逛墾丁大街了,卻還有一群婆媽「在青年活動中心的川堂,擠不出一個字」,媽媽曾頴近、靜娟老師以及慈芳老師只能看著Dargo老師用LINE傳來的食物照片餓肚子。「所以啊,我們的途中任務是不分大人或小孩的」,寫不出來的大人強調,他們也沒有特權。
值日生、出公差
值日生與出公差也是途中重要事項。
離開住宿的地方、用完餐,值日生要幫忙收拾。幾十個人吃完的便當,環保分類、整整齊齊的堆疊,連一條橡皮筋也沒有掉在地上,像串項鍊似地收集起來。
花東旭墾借住公東高工,早晨出發前老師在操場集合所有人,說明當天的行程與注意事項;後方則有值日生提著大包垃圾往垃圾場去,不為好心留宿大家的公東高工帶來困擾。
出公差則是視情況,熱心的男孩並不會視捉公差為畏途。東花縱騎時,車隊來到池上國中,老師宣布要找公差,林瑋軒說:「我們第二組很團結地舉手,到體育場打掃拖地」,那裡是男孩們當晚要睡覺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很認真,也很開心,當然掃得很乾淨。」
邊野學,邊公益
二○一六年二月二日,屏東縣滿州鄉九棚社區課輔班在臉書上寫著:「非常感謝徐匯中學的來訪。我們課輔班的小朋友們非常喜歡你們給的禮物。還有,九棚社區隨時歡迎你們來玩!」野學帶著籃球、羽球、排球、跳繩等運動用品去拜訪,那一天是大夥人第二次到九棚社區。前一年第一次去時,是逸年老師準備書、筆以及鉛筆盒等文具,帶著大園高中的幾位年輕老師、野學的男孩一起前往。「旭海往九棚途中,在天涯海角。」
「如果不是老師帶,搞不好我們都不會來呢!」
九棚社區在地理位置上是偏鄉中的偏鄉,到市區至少得花上兩個小時車程,當地教育資源匱乏,各方面的學習教具也不多,因此,野學一直很關心社區課輔班的狀況,只要行程順路都會繞進去看一下。這樣的安排除了讓男孩們在旅途中能夠自我挑戰外,也增加了一份「做愛心」的心意,「讓孩子在未來有能力幫助別人時,多了一個機會與對象」,Dargo老師說。
在老師的安排下,每一種任務都是希望孩子在過程裡有所成長,課堂之外、行程之中,無時無刻都是成長的機會;野學是平台,提供給願意擺上自己一份的人,不論是小孩還是大人。逸年老師說:「這些孩子們的成長活動,有核心教師的構思,家長用心規劃細節,以及願意陪伴孩子一起挑戰的父母親」,當他們離開溫暖安全的被窩時,已經為未來埋下無限的可能。
「要找一些憨膽的老師,其實不是很容易,把十幾個學生騙去環島,老師陪著騎,多想幾個萬一,這件事就做不成了,還好我們的老師裡,有這樣熱情的老師。」徐匯中學的校長陳海鵬在二○一四年少年風火輪環島結束後,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其實,最有憨膽的人,就是校長自己。
「一般的校長根本不會鼓勵這樣的活動,很危險,也替自己找麻煩,不是嗎?」許多學生家長都提到,校長敢放手,還強調「這是滿有意義的活動」,建議學生、家長有機會就參加。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旅程都有校長的身影,他再怎麼忙,都會看完學生騎上最危險的壽卡段、攻上雪山頂、玉山頂,或站在岸邊點點人頭,才安心離開。過程裡不干涉帶隊老師,默默地看。
成功,需要一點憨膽
帶孩子騎車、登百岳、泳渡日月潭、泛舟……哪一項不危險?哪一間學校的校長有那麼大膽量?而且,支持一次不打緊,還一回又一回地答應活動繼續辦!只要他說一次「不」,野學帶頭的Dargo老師再怎麼瘋,也很難「光明正大」瘋下去。
在更早更早以前,Dargo老師只能「低調」帶班上學生出門,人數少,不跑遠。爬爬七星山、觀音山,在台北郊區騎騎車,看到孩子們能行光合作用、流流汗,就心滿意足。或者是,每年一次邀請班上學生到家裡作客,採不強迫的預約制,幾個人一組帶著盥洗衣物、書包到家裡打地鋪、聊天,第二天吃他親手做的香噴噴早餐,再一起搭捷運到學校上課。這就是他早些年能為學生在課堂外做到的事。
直到二○一三年,徐匯中學出了一本復校五十周年的紀念專書《熱血男校》,Dargo老師回想起自己就讀徐匯時所遇到的神父與教師,曾經是那麼無私地陪伴孩子,才終於鼓起勇氣要把環島行程帶進教育現場,想要陪著青春少年們在狂飆的歲月裡,「有另類的引導,以及有體驗與學習的機會」。熱血沸騰的他,根本沒想過什麼叫害怕,因為「渴望帶孩子們出去走走看看的心情,已經大過恐懼」。
心臟比大顆
「自從我進徐匯之後,我遇到了一個史上最瘋狂的老師,他舉辦很多正常學校不會辦的活動。」
「崇拜Dargo老師啊!辦這麼多活動,不怕死,只要有一個人受傷就完蛋了,可是他都不怕,帶我們出去玩。」
「Dargo老師像獅子,很敢衝,什麼都不怕,不會擔心後果;可是也很負責,如果發生事情,他會第一個衝出來保護我們。」小孩在路上跑,大人的心揣在口袋裡。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若問:「發生事情怎麼辦?」,「發生就處理啊!」Dargo老師一再地提醒「大人不要忘了自己曾經是小孩」,小孩終究是小孩,如果在騎乘中想嘗試放開雙手,雖然結果有可能頭破血流,大人都要接受。孩子跌倒了就慢慢站起來,迷路了就自己問路回到集合點,輪胎破了就補,「不然呢?」Dargo老師一點也不緊張。
「打從少年風火輪開始,我家老爺就說Dargo老師的心臟鐵定不小顆」,男孩郭宇衡的媽媽Teresa為Dargo老師下了絕佳註解。
校長:「你覺得這個活動怎麼樣啊?明年是否……」
Dargo老師:「腦袋不清楚的時候,再考慮考慮吧!」
第一年少年風火輪環台活動結束,校長與Dargo老師兩人滴滴咕咕。其實,這兩個人的腦袋都不清楚,心臟一個比一個大顆。
■老師,我要報名
二○一五年十二月,野學男孩們一整個月興高采烈的,不是為了過聖誕節,也不是瘋跨年,而是老師、家長們打算要帶大家從木柵動物園踏騎到福隆,月底還有寒假要成行的三百三十公里騎程「花東旭墾」,也即將秒殺報名。
在野學初期,男孩們對報名的反應並不熱烈,通常都是爸媽自做主張,孩子才勉強參加。報名機制也還在摸索中,「報名方式不公平」、「不想輸別人才強迫孩子出門」的雜音紛起;主辦老師與家長們在活動中一起學習怎麼帶孩子,經過逐次修正才找到公平、民主,及對孩子最好的方法。現在,男孩們想參加活動,必須自己索取報名表,並且有一周的時間跟爸媽討論;想通了以後則自己填表、報名、繳費,不再能讓爸媽代勞。
「當我聽到野學要辦花東旭墾活動,我馬上就拿著報名表去跟爸爸說要報名」,男孩張昱閎報名當天,比往常都還要早起床,興奮、期待的心情自是不言而喻。
「自從騎完金山之後,我就開始慢慢地對騎腳踏車有了興趣」,男孩陳義昇說。
「報名的人很多,一下課就有一堆人往外衝。我期待已久的花東旭墾的活動終於到來了」,男孩黃戎瑍說。男孩們都表示,喜歡騎車的速度感,快慢可以自己控制,還能跟好朋友分享過程的辛苦,以及隨著一次又一次的長騎,明顯感受「變得更堅強,不斷超越自我」,騎車比登山的成就感更即時。(有男孩打槍說,「是看太多勵志書了嗎?」)
如今只要野學一發起新活動,報名參與的人數比初次少年風火輪的二十幾人,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的急速爆增,例如:九十九人去了福隆,八十人去了花東旭墾,要不是控制人數,規模恐怕難以想像。
男孩謝忻恩跟媽媽是福隆踏騎的補給車小組之一,擔任沿途看照同學安全與飲食的任務,並不需要加入爭搶名額的激戰中。可是,他對報名這回事也是緊張萬分,深怕好友沒跟上。報名前一日,謝昕恩再三提醒同班同學,並且交代隔壁班的要好朋友,下課不能去打籃球,務必記得先去找Dargo老師報到。
「老師,等一下要準時下課喔,我們要去報名野學!」當天第一堂課,謝忻恩備戰,怕同學出差錯,乾脆自告奮勇先收齊六人份報名表與費用,再跟該堂老師打招呼,鐘一響立即奔出教室。「老師,我要報名」,算算前面的排隊人數,謝昕恩前面只有九個人,好險!
當然,想成功報名不光是比誰衝得快,野學有規定,只要日常生活中有犯規記過的情況,就得停權兩次。因此,男孩們為了要順利參加野學活動,每一位都很在乎個人的日常行為。
但是,就像老師形容的,男孩們都還在「長身體,不長腦袋」的青春期,很容易爆衝,打架、互嗆、踹人等違紀事件很常見。
「拜託幫我跟教官說,好不好?我願意被記過,不想被野學停權,我想去福隆!」某日夜裡,有位男孩到處跟家長、老師們討救兵,因為他那天為了同學偷吃他的餅乾,踹了人,被送到教官室。教官與班導師商量許久,竟然做出「不記過,但野學停權」的決定,一拳打中他的要害。男孩極度渴望參加,不斷地說:「我願意被記過」、「不然,我一個人跟在隊伍後面騎,可以嗎?」無奈,教官一句:「我要讓你的記憶裡沒有『福隆』這兩個字!」重重切斷他的癡心妄想。大人們當時覺得,「這個處分,比記過有效,會讓孩子一輩子都記取教訓」。不過,隨著活動次數多了,老師們回頭檢討:野學不是用品性、成績來衡量要不要讓孩子參加,那麼「犯錯者不能報名」,這做法對嗎?如果孩子在體制內犯錯受處罰,野學又拒絕在外,他們要去哪裡?會不會因為大人剝奪孩子的機會,就改變他們的未來?
阿金老師開始視情節放寬,留給孩子們反省的機會,例如,有位男孩在課堂上吃冰並且大聲嗆他,阿金老師最後也接受男孩真心誠意的道歉,沒取消他野學的報名資格。而Dargo老師聽聞一位男孩現況不穩,常常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於是用了最肉痲的方式安撫他:「過來,抱一下,抱一下!聽話,聽話!」強摘的瓜不甜,強壓下的孩子也無法出頭,愛孩子,就多親近、多理解、多包容他們吧──老師們是這麼想的。
■「陪伴」也是一種關心
野學的活動不走高級行程,所以報名費其實相當便宜,「重要的是去體驗」。花東旭墾要騎五天四夜的費用,自備車只要四千五百元,若需租車則只要六千元;金山踏騎兩天一夜只要一千元;十一天環島四千六百五十元……
雖然野學活動安排不希望受限於體制內的框架,但參與者無論是大人、小孩,對它還是充滿無限想像。前提是,「野學不是徐匯中學附屬旅行社,活動不是廉價旅行團,參加者不能呼來喚去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帶隊的Dargo老師及阿金老師兩人一再強調,野學秉持的是:「付出不營利,體驗非享受」。帶隊老師要繳錢,出力的爸媽要繳錢,校長的錢也要收,大家一起平均分攤費用。甚至,有時經費不足,出錢又出力的家長還得再自掏腰包,負擔沿途支出。
野學,專挑困難的路走
爬新北市郊區的觀音山時,大夥兒不是踩在安山岩修築的人工步道上,而是得走天然的泥土石頭路,也就是「走路要選難路走,挑擔要選重擔挑」的道理。那天爬完山,男孩張育睿回家後跟媽媽說:「爬觀音山第一次這麼累,為何老師有這麼特別的路,跟我們去爬的路線都不一樣!」
野學第一次嘗試泛舟,Dargo老師說:「生命裡有太多的懼怕要超越,在不安全不穩定中見真章,不要怕踏出去。」最常舉辦的騎單車,阿金老師說它包含「人生亦同」的哲理,例如:*看遠方目標,才不會迷失。
*看近的障礙,才不會跌倒受傷。
*不斷地堅持,才可以到目的地。
*時時戰兢保持平衡才不會跌倒。
*平時保養好車子,用時才不會拋錨故障;隨時做好準備,才能抓住機會。
*上坡雖費力,卻安全;下坡,雖省力易危險。
*逆境,雖艱苦卻甘美;順境,雖樂極易生悲。
野學不當旅行團,要帶孩子、大人用雙腳踏行走遍台灣,在體驗之間替小孩建立生命的記憶,建立父母陪伴孩子或孩子陪伴父母的記憶。
陳逸文陳爸帶著一家大小跟著野學跑,無役不與。陳爸說:「家裡以前很窮,唸書時都在打工賺錢,從來沒出去玩過;現在,和兒子一起參加,某種程度是彌補了學生時代的遺憾。」至於陪著爸爸填補青春記憶的兒子陳岳廷,則謝謝爸爸的一路陪伴。陳爸說雖然有時候也想要自由,但是更感謝「帶著這樣走,不會說放著都不管,至少有關心到!」
登雪山時,男孩張雲翔和爸爸相依相伴,張雲翔成了照顧者,細心幫爸爸戴好頭巾,再扛上兩人的大背包;爸爸只管拄著登山杖往前走,其餘由兒子打點。另一位爸爸許皓威,在三六九山莊時就開始盤算兒子許嶢佑如果放棄攻頂,他就可以順理成章藉著「護送」之名撤退,不必再苦苦地陪著爬山;沒想到兒子不放棄,當爸爸的也只能一路相隨。兩位父親在那趟行程裡,都對自己的兒子刮目相看。
「野學做到的,比要求成績來的有感情!」媽媽江維淨與兒子陳加㯋登雪山後,也是心有所感。她說,當兒子問一句:「媽,你衣服有沒有帶夠?」再加上看到另一位男孩李明喆一直陪著落後的媽媽,似乎也在擔心媽媽時,她就「懂了」。
陪小孩到山上走走,小孩子能看見什麼?去騎車真的會體悟人生哲理?泛舟玩水,是要做什麼?「我不知道!」二十幾年來都在男孩堆裡打滾的Dargo老師都這麼說了,「吾家有兒初長成」的野學爸媽當然更懞懂,但是,他們都相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年少時所記憶的山林印象,自當成為年長時前進的記憶,對日後成長應是難以估計的珍貴價值」。
◎Box:自主訓練
假日的大台北近郊,在巴拉卡公路、二重疏洪道、淡水河左岸等地,如果注意看,很容易看見穿著綠T恤的徐匯男孩,大大「野學」兩個字就印在衣服上面。他們或許是三五好友結隊,或許是跟著爸媽幾個家庭一起出門。男孩們說,這叫「約騎」,是一項野學的自主練習活動,平日就要保持體能,到時才不會騎不動。男孩施奇陞和爸媽報名花東縱騎後,用了三周的周末一起集訓。男孩說:「其實這對他們(爸媽)是個極大的挑戰,因為老了骨頭不好了。」
至於登百岳前的訓練,只要能爬幾回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七星山,體能大抵不會有問題。徐匯中學每年五月第二次段考結束的隔天,都會帶新進小國一去爬七星山,釋放考試的壓力。二○一五年五月,野學要登雪山前,正好遇上每年例行的小國一登七星山,恰巧作為行前訓練。男孩王信杰無敵打拚,沿途背了六個同學的書包,要當「雪山,我來了」的負重練習。「累啊!」,王信杰說。
■旅途中的特別任務
二○一五年東花縱騎,阿金老師指派了特殊任務,要每隊在第二天去找大樹、百年教堂,以及和藹可親、有皺紋的老阿公或老阿嬤,並且拍照。一來,希望不只是單純騎車;再來,以小隊做分派,可發揮合作精神。
男孩們一小隊一小隊出發,從台東池上往花蓮光復高職的途中必須完成任務。出發前,老師已提點,老教堂在花蓮的富里小鎮;找到老教堂,就能順道發現周圍有棵大樹;至於老阿公或老阿嬤,則要機靈、有禮地提出拍照邀請。
聽起來,任務很簡單,可惜大部分男孩只顧騎車,順著大路走,不看路標,衝著衝著,小隊一隊隊散掉,錯過進入小鎮的岔路,錯過老教堂與老樹。只有男孩林瑋軒、黄偉哲、陳岳廷等人進入富里,在一家雜貨店買飲料,跟店裡「應該已經有八十歲的老阿嬤很開心地拍照」,是少數完成任務的小組。
那一天達標的沒幾組,完成任務的隊伍可獲頒乖乖桶一桶。Dargo老師說:「這就是孩子,會直接衝,過頭就算了。」於是少數努力完成任務的人,更是值得大家為他們鼓掌。
不可能的任務:寫作文?
旅途中,孩子們覺得「最痛苦的任務是寫作文」。
「怎麼辦,老師竟然說要寫作文耶!」
「別開玩笑!」
少年風火輪環台時,男孩們騎到第九天,回到台灣北端的福隆,Dargo老師集合大人小孩,要求每人交出六百字心得,沒寫完不淮回房睡覺,老師、家長、男孩一視同仁,沒有例外。到了阿金老師加入野學,更堅持所有參與者要「寫作文」,無論登山或騎車,他都希孩男孩們有機會透過文字來自省。於是,在東花縱騎時,車隊投宿光復高職,只見男孩趴在體育館的地板上,振筆疾書。「寫完作文,來換雞排」,潘吉松潘爸與孩子們口中的頴近阿姨買了雞排當宵夜,作為「寫作的動力」,為了吃,誰會不寫呢?
到了花東旭墾的最後一天,幾十個男孩入住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猜想應該會吵雜嬉鬧,然而媽媽邱妤蓁從外面回來,卻發現「鴉雀無聲」、「萬人空巷」,人人都埋頭寫作。原來,那一晚是難得的自由時間,逛墾丁大街比任何事重要,早交差才有時間出去玩。
男孩們覺得寫作文「很痛苦」,對大人來說又何嘗不是。孩子交稿解脫,去逛墾丁大街了,卻還有一群婆媽「在青年活動中心的川堂,擠不出一個字」,媽媽曾頴近、靜娟老師以及慈芳老師只能看著Dargo老師用LINE傳來的食物照片餓肚子。「所以啊,我們的途中任務是不分大人或小孩的」,寫不出來的大人強調,他們也沒有特權。
值日生、出公差
值日生與出公差也是途中重要事項。
離開住宿的地方、用完餐,值日生要幫忙收拾。幾十個人吃完的便當,環保分類、整整齊齊的堆疊,連一條橡皮筋也沒有掉在地上,像串項鍊似地收集起來。
花東旭墾借住公東高工,早晨出發前老師在操場集合所有人,說明當天的行程與注意事項;後方則有值日生提著大包垃圾往垃圾場去,不為好心留宿大家的公東高工帶來困擾。
出公差則是視情況,熱心的男孩並不會視捉公差為畏途。東花縱騎時,車隊來到池上國中,老師宣布要找公差,林瑋軒說:「我們第二組很團結地舉手,到體育場打掃拖地」,那裡是男孩們當晚要睡覺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很認真,也很開心,當然掃得很乾淨。」
邊野學,邊公益
二○一六年二月二日,屏東縣滿州鄉九棚社區課輔班在臉書上寫著:「非常感謝徐匯中學的來訪。我們課輔班的小朋友們非常喜歡你們給的禮物。還有,九棚社區隨時歡迎你們來玩!」野學帶著籃球、羽球、排球、跳繩等運動用品去拜訪,那一天是大夥人第二次到九棚社區。前一年第一次去時,是逸年老師準備書、筆以及鉛筆盒等文具,帶著大園高中的幾位年輕老師、野學的男孩一起前往。「旭海往九棚途中,在天涯海角。」
「如果不是老師帶,搞不好我們都不會來呢!」
九棚社區在地理位置上是偏鄉中的偏鄉,到市區至少得花上兩個小時車程,當地教育資源匱乏,各方面的學習教具也不多,因此,野學一直很關心社區課輔班的狀況,只要行程順路都會繞進去看一下。這樣的安排除了讓男孩們在旅途中能夠自我挑戰外,也增加了一份「做愛心」的心意,「讓孩子在未來有能力幫助別人時,多了一個機會與對象」,Dargo老師說。
在老師的安排下,每一種任務都是希望孩子在過程裡有所成長,課堂之外、行程之中,無時無刻都是成長的機會;野學是平台,提供給願意擺上自己一份的人,不論是小孩還是大人。逸年老師說:「這些孩子們的成長活動,有核心教師的構思,家長用心規劃細節,以及願意陪伴孩子一起挑戰的父母親」,當他們離開溫暖安全的被窩時,已經為未來埋下無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