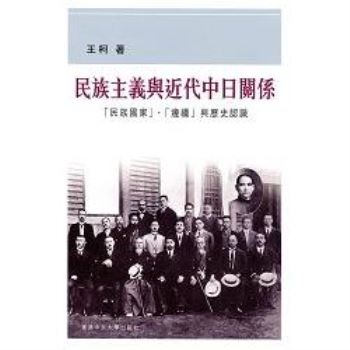第五章 從「勤王大清」到「滿蒙獨立」──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運動」
當代日本研究中日關係的著名學者衛藤瀋吉,曾經分析過明治後期以來日本社會關於中日關係認識的歷史變遷過程:一,出於對「唇亡齒寒」的擔心,關心中國未來前途的日本人分為主張清國應該實施「攘夷」和主張清國應該實施「開國」兩派,而最後主張清國開國派佔了上風;二,由於看到清國遲遲不肯放棄天朝體制,於是主張清國開國派又分為認為清國可能開國和清國不可能開國兩派,而最後認為清國不可能開國派佔了上風;三,與其坐視鎖國的清朝最終落入西方列強之手,不如由日本主動採取行動,於是認為清國不可能開國派再次分為支持日本征服中國和支援中國革命兩派。1衛藤瀋吉對近代中日關係歷史走向的這一概括,代表了許多日本學者的觀點,也確實點出近代中日歷史關係衍變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特徵。然而,從最初的與人為善的期待到最終採取不惜傷害對方的行動之間,其實並不存在這樣一條順理成章的自然轉移法則。很明顯,這一觀點同時有著成為替日本侵略中國進行辯護之口實的可能。原因在於它沒有指出,支持日本征服中國或是支援中國革命兩派的真正分歧點,只是在於應該以何種手段才能為日本國家博取最大利益的認識上的不同。這也是為甚麼當年支持孫中山進行革命的勢力,之後甚至是當時也會積極支持和支援日本侵略中國行為的原因。
說到底,支援中國革命與支持日本征服中國兩派之間的區別,只是在於手段的不同。如果從手段上對支持日本在中國擴大勢力範圍的日本人進行分類,其實還會衍生更多的層次和選項。大正三年(1913)2月,研究中國的青柳篤恒在《太陽》第19卷第3號上發表的〈我日本對支那之根本方針〉(上)一文中談到:辛亥革命發生之後,日本社會中關於中國領土的輿論大致可以分為「分割論」、「吞併論」與「保全論」三種,而其中的「分割論」又可分為三種。第一種為「將南滿洲和內蒙古收入我手」,第二種為「將南滿洲、內蒙古和黃河以北地區收入我日本之手」,第三種為「將南滿洲、內蒙古、黃河以北之地及江蘇浙江地區割讓給我日本」。2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一種領土「分割論」,首當其衝被認為應該「收入日本之手」或者直接割讓給日本的地區都是「南滿洲」與「內蒙古」,也就是所謂的「滿蒙」地區。青柳篤恒的分析清楚證明,二十世紀以來日本染指中國邊疆地區的活動大多始於「滿蒙」,即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地區。3
說到日本對滿洲產生侵略野心的淵源,一般都會提到佐藤信淵在其1823年所著《宇內混同秘策》中所提到的「所有經略他國之法,以從薄弱和易取之處開始為道。而於皇國而言,當今世界萬國中最易攻取的土地非支那國的滿洲莫屬」一語。而近代日本對「滿洲」產生直接關心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末,它開始侵略朝鮮半島,即開始侵略大陸之初。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這兩場與「滿洲」分不開的戰爭,為日本提供了「大陸國家化」的堅實跳板。4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後的《馬關條約》中,日本就提出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領土要求。但是俄羅斯、德國與法國「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不得不將遼東半島交還給清朝,然而1900年的「庚子事變」之後,俄羅斯卻佔領了東北地區。「三國干涉還遼」帶來的「屈辱」感,令日本對「滿洲」地區的權益一直耿耿於懷。直到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才通過《朴茨茅斯合約》在「滿洲」南部落下了腳跟,俄國將自己從清政府得到的旅大租借地、中東鐵路長春至旅順段及二者附屬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時期,作為覬覦大陸領土的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話語,「滿洲」卻變成了「滿蒙」。
這個問題當然也涉及到清末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下展開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性質的問題:一個「民族國家」何以具有維持「天下」體制的合法性?1911年10月、11月間,梁啟超在〈新中國建設之問題〉中就明確質問:「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訓於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中國如果從一個傳統的多民族的帝國構造向一個近代「民族國家」轉型,「滿」與「蒙」自然都是可以被「中華」所放棄的「韃虜」。但是在這一時期,「滿」與「蒙」之所以能夠被合為一體,更重要的還是由於日本勢力的染指所造成。正如衛藤瀋吉所指出的那樣,除了支持中國革命一派以外,還有部分日本人和日本政治勢力為了擴張日本勢力範圍而參加分裂中國的行動。本章研究的對象就是由大陸浪人川島浪速教唆和推動的「滿蒙獨立運動」,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支援中國革命的日本人,也同時參加了分裂中國的活動。
第一節 川島浪速與「滿蒙獨立運動」的發生
出生於長野縣的川島浪速,在義和團事件(又稱庚子事變)發生期間,隨著他的同鄉──當時被任命為日本臨時派遣隊司令官、參與鎮壓義和團運動的著名情報軍人福島安正少將作為「通事」(即翻譯)來到了北京。他借助自己當年在興亞會下外國語學校支那語科掌握的中文能力,在事變發生時中成功地勸說在紫禁城中2,000餘名清朝宮廷人員放棄籠城固守,因此得到八國聯軍當局的信任。而被八國聯軍統治北京當局任命為皇宮總監的川島浪速,又因保護紫禁城使其沒有受到過多損害,得到清王朝的信任。之後,進入八國聯軍統治北京當局軍政署警察部門的川島浪速,借助列強和日本軍方的支持,在事變期間盡力維持北京的治安,還參與設立北京警務學校,因此在清皇室返回北京後,又被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聘用來幫助建立現代警察制度。5當時,與川島交好的肅親王善耆為步軍統領和民政部尚書。
儘管有人對「在北京政界中川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相當勢力」一說表示出極大的懷疑,6但是毫無疑問,川島浪速的確得到了清朝政府高層的極大信任。關於這一點,我們能夠通過以下材料得到證明。1901年,川島希望回國度假,然而清朝政府的總理衙門居然向日本駐軍提督山口素臣(第五師團長)發函,請求山口出面挽留:「該員自到京以來,辦理一切事宜,善體幫教,悉臻妥恰,本爵極為欣慰。若一旦言旋,諸多未便,擬請貴軍門轉致該員,暫緩時日,再定歸期,實於公務裨益良多,不勝殷盼之至。」7作為處理清王朝外交事務的最高機關,居然會為這樣一件小事發出專函請求,足見清朝政府對川島浪速之重視。
下面這件事也可以證明川島浪速在北京政界中的地位。1908年11月11日,川島前往黃寺拜見來到北京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與達賴之間有過一段交談:
[達賴說道—筆者]從前日本和尚有赴西藏者,我曾見過,今日又與君相見,也很喜歡。達賴問:君何時到京?川島答:到了沒有幾天。達賴問:從日本到北京走幾天?川島答:多則十天,少則七八天。達賴問:君先後到北京幾多年?川島答:在京共八年。達賴問:聞君從前在北京曾與喇嘛往來?[川島答:]從前在京見過喇嘛,與談佛教,深蒙指教。達賴問:貴國大皇帝安否?地方安否?川島答:託福,敝國大皇帝很康健,收成也好。達賴讓茶並命堪布送川島藏棗及蘋果各一盤。川島辭出攜所賜藏棗蘋果去。8此次達賴喇嘛在北京停留近三個月,但是能夠見到達賴的日本人絕大多數為外交官僚並且屈指可數,而達賴喇嘛的隨從羅桑旦增(堪布)卻在川島浪速前來拜見之前,還親自上門拜訪了川島浪速。9川島浪速曾經兩次得到過清王朝的授勳。第一次是在光緒28年(1904,明治36年)12月15日,「大日本國元陸軍通譯」川島浪速獲得由清國「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奕劻頒發的「三等第二寶星」勳章;10第二次是在光緒29年12月4日,「大日本國人警務學堂監督」川島浪速再次得到「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奕劻頒發「二等第二寶星」勳章。11可見川島浪速在與清朝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越來越受到清朝王公們的信賴。也正因為這種關係,企圖在北京通過扶大廈於將傾的活動展示能力,以接近清朝皇族、借機為日本謀取利益的川島浪速,很早就對野心家袁世凱抱有戒心。
按照《川島浪速翁》一書的說法,在得知袁世凱被焦頭爛額的清王朝重新啟用之後,川島浪速曾經三次組織暗殺袁世凱的行動,企圖將袁世凱殺害於從河南到北京就任的途中。其中兩次還得到在北京日本公使館中日本陸軍軍官的支援,他們甚至直接參加了暗殺行動,但是卻都沒有取得成功。12 1911年12月7日,川島浪速在從北京發給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福島安正中將的電報中談到:
袁世凱陰謀逐漸膨脹,逼攝政王退位,欺負他人之寡婦孤兒,借太后垂簾之名壟斷君權於一身。為盜取大清之天下,斷朝廷之手足而植以自家羽翼,愈加示威於宮中、府中,毫無忌憚之處,遭到激烈反對。滿人之憤懣已達其極。北京不日將化為禍亂之巷街,而其亂當自今日始也。13
川島浪速筆下的袁世凱,一副活生生的小人得志倡狂的形象。這段文字,反映出川島浪速對袁世凱借機要脅清朝皇室、逼皇室退位這一做法的強烈反感。然而這段話也反映出川島浪速的立腳點,不是清朝而是清皇室。川島浪速之所以站在清朝皇室的立場上,與他在北京得到清朝皇親貴戚的賞識有著直接的關係。當時日本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宇都宮太郎就認為,川島「作為肅親王等人的顧問得到非常信任」。14
為對付袁世凱的步步進逼,良弼、毓朗、溥偉、載濤、載澤、鐵良等一批滿清權貴於1912年1月12日集會,19日組織了「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要求隆裕太后堅持君主制政權,反對共和制。他們密謀驅除袁世凱,以毓朗、載澤出面組閣,鐵良出任清軍總司令,然後與南方革命軍決一死戰。但是,袁世凱通過汪精衛聯繫到同盟會,1月26日同盟會彭家珍炸死了宗社黨首領良弼,宗社黨遂告鳥獸散。對於袁世凱回到北京以後的各種活動,川島浪速早在1月22日給日本參謀本部發出的電報中,就已經直言這是袁世凱和孫中山在演雙簧戲。15
辛亥革命爆發前後,將中國大陸作為自己活動舞台的日本大陸浪人,基本上都十分仇視袁世凱。在這一點上,日本大陸浪人其實與革命黨人非常接近。然而,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將日本浪人們對袁世凱的憎恨與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憎恨二者完全等同。因為同情和支持革命黨人的日本浪人之所以憎恨袁世凱,與其說是憎恨他竊取了革命的勝利成果,還不如說是因為他們明白比起革命黨人來,日本從狡詐的袁世凱處必將更加難以在中國獲得他們所想獲得的利益。更有一部分日本大陸浪人,他們既不喜歡袁世凱也不喜歡革命派,因為他們認為只有在清王朝的統治體制下,他們才能在中國有更大的活動空間。所以他們原本就沒有接近過革命派,也不希望看到「革命」的發生,而對袁世凱的憎恨也是因為看到袁世凱已經成為對清王朝統治體制的極大威脅,成為他們操縱和利用清王朝權貴的絆腳石,川島浪速就屬於後一種。
按照川島浪速的說法,面對袁世凱的「老獪不忠」,清朝皇族中的醇親王載灃(攝政王)、恭親王溥偉及肅親王善耆開始密謀利用日本力量,維護清王朝統治體制。與川島浪速建立起密切關係的肅親王善耆,1912年1月22日晚親自找到川島商談是否有得到日本的援助,借助日本的力量逼袁世凱辭職離開北京的可能。16儘管東北地區的滿人社會和以喀喇沁旗王為首的內蒙古東部蒙古王公表示願意組織軍隊進行「勤王」,17川島浪速也勸說日本軍方向「蒙古勤王軍」支援軍火,18然而川島也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怎麼做,清王朝都逃脫不了日益走向滅亡的命運,日本方面能夠做到的也僅此而已。因此他在1月29日開始策劃並規勸肅親王等首先謀求將「滿蒙」地區變成一個日後再起的根據地:「組織滿蒙勤王軍,通過標榜無論如何都要守住祖先故土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義,暫以滿蒙為根據地蓄養實力,靜等民國自亂,必有再出中原之時。宣統退位之罪在於奸臣和失去良心的王公們,可以替祖宗聲討此罪,借此告知天下保存大清之名義。」他進而向日本說明這樣做的好處:「此一於北方興起之國,其首腦當然明白只能靠日本的掩護才能生存。我國可以利用此點為我機關所用。所以應該盡一切可能給予援助。」19這應該是川島浪速關於他策劃的所謂「滿蒙獨立運動」構想的最早表述,但是可以看到,因為具有「勤王」的因素,直到此時還沒見到「獨立」二字。第二節 蒙古王公的「勤王」與「獨立」
1912年2月,在得知清王朝皇室已經決定遜位後,川島浪速馬上開始行動,在川島的計劃和具體安排之下,肅親王善耆於2月2日逃出北京,由天津乘坐日本郵船「渤海丸」,於6日到達當時在日本控制之下的旅順。20之後,川島浪速又設計讓在北京的蒙古王公逃離北京,以便回到內蒙古東部可以「舉事」、「勤王」。
有趣的是,即使在1911年底、1912年初這個敏感的時點,被川島浪速用來將「滿」「蒙」兩個民族集團的社會上層一起糅合的歷史和政治因素,仍然是即將謝幕的「大清」。包括清王朝在內,中國歷史上由非漢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為主人公的征服王朝。這些王朝,因為在進入「中國」建立政權之後認識到無法用自己「民族」的統治方式統治「中國」,逐漸都會向中華王朝轉化。然而,由於這些政權是通過武力征服的方式進入「中國」,最初都會與「中國」的民眾之間存在嚴重的民族隔閡或民族對立,這使得它不得不在以中華文明方式統治「中國」的同時,又都採用了以周邊的「民族」集團牽制「中國」,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征服王朝的「多元式天下」的傳統。21而在清王朝以民族等級制度為基礎的「多元式天下」構造中,蒙古社會上層被賦予特殊的地位。所以,作為清王朝的一個特權階層,在面臨清王朝全面崩潰的時刻,蒙古社會上層也就對清王朝表示出那麼一點的「忠誠」。例如辛亥革命時期,曾任陝甘總督的蒙古人昇允率舊部反抗,他曾經作過這樣一首詩以表明心態:「老臣猶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蘇武書。」22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由蒙古王公所提出的「勤王」──組織軍隊進軍北京以支撐清王朝的統治體制,最初並不是出自於內蒙,而是出自於外蒙。1911年11月8日(舊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接到(外蒙古)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來信,內稱:「現聞內地各省,相繼獨立。革命黨人,已帶兵取道張家口來庫,希圖擾亂蒙疆。我喀爾喀四部蒙眾,受大清恩惠二百餘年,不忍坐視。我佛哲布尊巴呼圖克圖,已傳檄徵調四盟騎兵四千名,進京保護大清皇帝。請即日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以便起行。是否照準,限本日三小時內,明白批示。」23
外蒙古四盟王公在信中所提出的「勤王」條件──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事實上是當時庫倫大臣所根本無法辦到的。因為外蒙古王公已於一年前開始暗中交接俄國勢力籌畫獨立,所以說,這封信中所提出的「勤王」,只不過是為其之後進行分裂活動製造一個正當性理由而已。果不其然,當天晚上7時,三多再接哲布尊巴呼圖克圖宣佈外蒙古獨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朝恩遇,不為不厚。……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佈獨立,以期完全。⋯⋯庫倫地方,已無需用中國官吏之處,自應全數驅逐,以杜後患。24
不能「勤王」就要獨立,從這種做法中可以看出蒙古王公們的一個邏輯:蒙古是清王朝版圖的一部分卻不是中國的領土,蒙古人是大清國的臣民卻不是中國的國民。因此,清王朝一旦滅亡,蒙古與清王朝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也就隨之煙消雲散,而蒙古也就與中國沒有關係。鼓吹蒙古獨立的人們將清王朝與「中國」做了區分,既然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內地各省都可以與清朝政府脫離關係而實現獨立,那麼與各省同為大清國組成部分的蒙古,如果無法通過「勤王」的手段去保護作為母體的清王朝,那就只能與中國內地各省同樣選擇自保的方法,與清王朝脫離關係宣佈獨立。然而,為甚麼勤王得以作為分裂的正當性根據一事,值得引起注意。
外蒙古的獨立運動,開中國近代民族分裂活動之濫觴。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中國近代民族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的發生,與中國政治和社會體制發生翻天覆地的劇變,二者之間的關係絕不僅只是時間上的巧合,而與當年清王朝採用「多元式天下」思想所構築的王朝的政治地理、如今革命家所提倡和追求的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思想及行動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25蒙古王公之所以提出「勤王」遭拒為提出「獨立」的正當性依據,就在於清王朝統治中國的政治構造曾經具備「滿族聯合蒙、藏、回以牽制漢人」的性質。正因為以上關係,蒙古王公在意識到清王朝已經無法扭轉滅亡之趨勢的情況下所提出的「勤王」口號,實質上就是「民族獨立」的前奏。口頭上喊著「勤王」,實質上想的卻是「民族獨立」,內蒙古的王公們在武昌起義爆發後的活動,同樣也是這種情形。不同的只是內蒙古王公們的「勤王」得到了日本勢力的支持,而外蒙古的分裂活動具有帝俄的背景。
汪炳明的〈清朝覆亡之際駐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動〉利用諸多檔案,記述了這一時期在北京蒙古王公的活動特徵。以那彥圖(喀爾喀親王,清廷御前大臣,八旗鑲紅旗都統)、貢桑諾爾布(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世襲扎薩克親王,卓索圖盟盟長,肅親王善耆的妹夫)、博迪蘇(哲里木盟科爾沁左翼後旗扎薩克博多勒噶台親王伯彥訥謨祐第三子,輔國公,御前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兼署正紅旗滿洲都統)、多爾濟帕拉穆(喀爾喀車臣汗部中右旗扎薩克多羅郡王,車臣汗部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盟長)、帕勒塔(土爾扈特東部落六世君王巴雅爾之生子,襲封扎薩克郡王,科布多辦事大臣)為首,當時在北京清廷中有二十幾名蒙古王公。26此時這些蒙古王公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和活動特徵,一言蔽之,就是激烈反對清帝退位和實行共和。
當代日本研究中日關係的著名學者衛藤瀋吉,曾經分析過明治後期以來日本社會關於中日關係認識的歷史變遷過程:一,出於對「唇亡齒寒」的擔心,關心中國未來前途的日本人分為主張清國應該實施「攘夷」和主張清國應該實施「開國」兩派,而最後主張清國開國派佔了上風;二,由於看到清國遲遲不肯放棄天朝體制,於是主張清國開國派又分為認為清國可能開國和清國不可能開國兩派,而最後認為清國不可能開國派佔了上風;三,與其坐視鎖國的清朝最終落入西方列強之手,不如由日本主動採取行動,於是認為清國不可能開國派再次分為支持日本征服中國和支援中國革命兩派。1衛藤瀋吉對近代中日關係歷史走向的這一概括,代表了許多日本學者的觀點,也確實點出近代中日歷史關係衍變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特徵。然而,從最初的與人為善的期待到最終採取不惜傷害對方的行動之間,其實並不存在這樣一條順理成章的自然轉移法則。很明顯,這一觀點同時有著成為替日本侵略中國進行辯護之口實的可能。原因在於它沒有指出,支持日本征服中國或是支援中國革命兩派的真正分歧點,只是在於應該以何種手段才能為日本國家博取最大利益的認識上的不同。這也是為甚麼當年支持孫中山進行革命的勢力,之後甚至是當時也會積極支持和支援日本侵略中國行為的原因。
說到底,支援中國革命與支持日本征服中國兩派之間的區別,只是在於手段的不同。如果從手段上對支持日本在中國擴大勢力範圍的日本人進行分類,其實還會衍生更多的層次和選項。大正三年(1913)2月,研究中國的青柳篤恒在《太陽》第19卷第3號上發表的〈我日本對支那之根本方針〉(上)一文中談到:辛亥革命發生之後,日本社會中關於中國領土的輿論大致可以分為「分割論」、「吞併論」與「保全論」三種,而其中的「分割論」又可分為三種。第一種為「將南滿洲和內蒙古收入我手」,第二種為「將南滿洲、內蒙古和黃河以北地區收入我日本之手」,第三種為「將南滿洲、內蒙古、黃河以北之地及江蘇浙江地區割讓給我日本」。2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一種領土「分割論」,首當其衝被認為應該「收入日本之手」或者直接割讓給日本的地區都是「南滿洲」與「內蒙古」,也就是所謂的「滿蒙」地區。青柳篤恒的分析清楚證明,二十世紀以來日本染指中國邊疆地區的活動大多始於「滿蒙」,即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地區。3
說到日本對滿洲產生侵略野心的淵源,一般都會提到佐藤信淵在其1823年所著《宇內混同秘策》中所提到的「所有經略他國之法,以從薄弱和易取之處開始為道。而於皇國而言,當今世界萬國中最易攻取的土地非支那國的滿洲莫屬」一語。而近代日本對「滿洲」產生直接關心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末,它開始侵略朝鮮半島,即開始侵略大陸之初。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這兩場與「滿洲」分不開的戰爭,為日本提供了「大陸國家化」的堅實跳板。4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後的《馬關條約》中,日本就提出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領土要求。但是俄羅斯、德國與法國「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不得不將遼東半島交還給清朝,然而1900年的「庚子事變」之後,俄羅斯卻佔領了東北地區。「三國干涉還遼」帶來的「屈辱」感,令日本對「滿洲」地區的權益一直耿耿於懷。直到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才通過《朴茨茅斯合約》在「滿洲」南部落下了腳跟,俄國將自己從清政府得到的旅大租借地、中東鐵路長春至旅順段及二者附屬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時期,作為覬覦大陸領土的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話語,「滿洲」卻變成了「滿蒙」。
這個問題當然也涉及到清末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下展開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性質的問題:一個「民族國家」何以具有維持「天下」體制的合法性?1911年10月、11月間,梁啟超在〈新中國建設之問題〉中就明確質問:「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訓於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中國如果從一個傳統的多民族的帝國構造向一個近代「民族國家」轉型,「滿」與「蒙」自然都是可以被「中華」所放棄的「韃虜」。但是在這一時期,「滿」與「蒙」之所以能夠被合為一體,更重要的還是由於日本勢力的染指所造成。正如衛藤瀋吉所指出的那樣,除了支持中國革命一派以外,還有部分日本人和日本政治勢力為了擴張日本勢力範圍而參加分裂中國的行動。本章研究的對象就是由大陸浪人川島浪速教唆和推動的「滿蒙獨立運動」,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支援中國革命的日本人,也同時參加了分裂中國的活動。
第一節 川島浪速與「滿蒙獨立運動」的發生
出生於長野縣的川島浪速,在義和團事件(又稱庚子事變)發生期間,隨著他的同鄉──當時被任命為日本臨時派遣隊司令官、參與鎮壓義和團運動的著名情報軍人福島安正少將作為「通事」(即翻譯)來到了北京。他借助自己當年在興亞會下外國語學校支那語科掌握的中文能力,在事變發生時中成功地勸說在紫禁城中2,000餘名清朝宮廷人員放棄籠城固守,因此得到八國聯軍當局的信任。而被八國聯軍統治北京當局任命為皇宮總監的川島浪速,又因保護紫禁城使其沒有受到過多損害,得到清王朝的信任。之後,進入八國聯軍統治北京當局軍政署警察部門的川島浪速,借助列強和日本軍方的支持,在事變期間盡力維持北京的治安,還參與設立北京警務學校,因此在清皇室返回北京後,又被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聘用來幫助建立現代警察制度。5當時,與川島交好的肅親王善耆為步軍統領和民政部尚書。
儘管有人對「在北京政界中川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相當勢力」一說表示出極大的懷疑,6但是毫無疑問,川島浪速的確得到了清朝政府高層的極大信任。關於這一點,我們能夠通過以下材料得到證明。1901年,川島希望回國度假,然而清朝政府的總理衙門居然向日本駐軍提督山口素臣(第五師團長)發函,請求山口出面挽留:「該員自到京以來,辦理一切事宜,善體幫教,悉臻妥恰,本爵極為欣慰。若一旦言旋,諸多未便,擬請貴軍門轉致該員,暫緩時日,再定歸期,實於公務裨益良多,不勝殷盼之至。」7作為處理清王朝外交事務的最高機關,居然會為這樣一件小事發出專函請求,足見清朝政府對川島浪速之重視。
下面這件事也可以證明川島浪速在北京政界中的地位。1908年11月11日,川島前往黃寺拜見來到北京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與達賴之間有過一段交談:
[達賴說道—筆者]從前日本和尚有赴西藏者,我曾見過,今日又與君相見,也很喜歡。達賴問:君何時到京?川島答:到了沒有幾天。達賴問:從日本到北京走幾天?川島答:多則十天,少則七八天。達賴問:君先後到北京幾多年?川島答:在京共八年。達賴問:聞君從前在北京曾與喇嘛往來?[川島答:]從前在京見過喇嘛,與談佛教,深蒙指教。達賴問:貴國大皇帝安否?地方安否?川島答:託福,敝國大皇帝很康健,收成也好。達賴讓茶並命堪布送川島藏棗及蘋果各一盤。川島辭出攜所賜藏棗蘋果去。8此次達賴喇嘛在北京停留近三個月,但是能夠見到達賴的日本人絕大多數為外交官僚並且屈指可數,而達賴喇嘛的隨從羅桑旦增(堪布)卻在川島浪速前來拜見之前,還親自上門拜訪了川島浪速。9川島浪速曾經兩次得到過清王朝的授勳。第一次是在光緒28年(1904,明治36年)12月15日,「大日本國元陸軍通譯」川島浪速獲得由清國「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奕劻頒發的「三等第二寶星」勳章;10第二次是在光緒29年12月4日,「大日本國人警務學堂監督」川島浪速再次得到「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奕劻頒發「二等第二寶星」勳章。11可見川島浪速在與清朝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越來越受到清朝王公們的信賴。也正因為這種關係,企圖在北京通過扶大廈於將傾的活動展示能力,以接近清朝皇族、借機為日本謀取利益的川島浪速,很早就對野心家袁世凱抱有戒心。
按照《川島浪速翁》一書的說法,在得知袁世凱被焦頭爛額的清王朝重新啟用之後,川島浪速曾經三次組織暗殺袁世凱的行動,企圖將袁世凱殺害於從河南到北京就任的途中。其中兩次還得到在北京日本公使館中日本陸軍軍官的支援,他們甚至直接參加了暗殺行動,但是卻都沒有取得成功。12 1911年12月7日,川島浪速在從北京發給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福島安正中將的電報中談到:
袁世凱陰謀逐漸膨脹,逼攝政王退位,欺負他人之寡婦孤兒,借太后垂簾之名壟斷君權於一身。為盜取大清之天下,斷朝廷之手足而植以自家羽翼,愈加示威於宮中、府中,毫無忌憚之處,遭到激烈反對。滿人之憤懣已達其極。北京不日將化為禍亂之巷街,而其亂當自今日始也。13
川島浪速筆下的袁世凱,一副活生生的小人得志倡狂的形象。這段文字,反映出川島浪速對袁世凱借機要脅清朝皇室、逼皇室退位這一做法的強烈反感。然而這段話也反映出川島浪速的立腳點,不是清朝而是清皇室。川島浪速之所以站在清朝皇室的立場上,與他在北京得到清朝皇親貴戚的賞識有著直接的關係。當時日本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宇都宮太郎就認為,川島「作為肅親王等人的顧問得到非常信任」。14
為對付袁世凱的步步進逼,良弼、毓朗、溥偉、載濤、載澤、鐵良等一批滿清權貴於1912年1月12日集會,19日組織了「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要求隆裕太后堅持君主制政權,反對共和制。他們密謀驅除袁世凱,以毓朗、載澤出面組閣,鐵良出任清軍總司令,然後與南方革命軍決一死戰。但是,袁世凱通過汪精衛聯繫到同盟會,1月26日同盟會彭家珍炸死了宗社黨首領良弼,宗社黨遂告鳥獸散。對於袁世凱回到北京以後的各種活動,川島浪速早在1月22日給日本參謀本部發出的電報中,就已經直言這是袁世凱和孫中山在演雙簧戲。15
辛亥革命爆發前後,將中國大陸作為自己活動舞台的日本大陸浪人,基本上都十分仇視袁世凱。在這一點上,日本大陸浪人其實與革命黨人非常接近。然而,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將日本浪人們對袁世凱的憎恨與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憎恨二者完全等同。因為同情和支持革命黨人的日本浪人之所以憎恨袁世凱,與其說是憎恨他竊取了革命的勝利成果,還不如說是因為他們明白比起革命黨人來,日本從狡詐的袁世凱處必將更加難以在中國獲得他們所想獲得的利益。更有一部分日本大陸浪人,他們既不喜歡袁世凱也不喜歡革命派,因為他們認為只有在清王朝的統治體制下,他們才能在中國有更大的活動空間。所以他們原本就沒有接近過革命派,也不希望看到「革命」的發生,而對袁世凱的憎恨也是因為看到袁世凱已經成為對清王朝統治體制的極大威脅,成為他們操縱和利用清王朝權貴的絆腳石,川島浪速就屬於後一種。
按照川島浪速的說法,面對袁世凱的「老獪不忠」,清朝皇族中的醇親王載灃(攝政王)、恭親王溥偉及肅親王善耆開始密謀利用日本力量,維護清王朝統治體制。與川島浪速建立起密切關係的肅親王善耆,1912年1月22日晚親自找到川島商談是否有得到日本的援助,借助日本的力量逼袁世凱辭職離開北京的可能。16儘管東北地區的滿人社會和以喀喇沁旗王為首的內蒙古東部蒙古王公表示願意組織軍隊進行「勤王」,17川島浪速也勸說日本軍方向「蒙古勤王軍」支援軍火,18然而川島也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怎麼做,清王朝都逃脫不了日益走向滅亡的命運,日本方面能夠做到的也僅此而已。因此他在1月29日開始策劃並規勸肅親王等首先謀求將「滿蒙」地區變成一個日後再起的根據地:「組織滿蒙勤王軍,通過標榜無論如何都要守住祖先故土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義,暫以滿蒙為根據地蓄養實力,靜等民國自亂,必有再出中原之時。宣統退位之罪在於奸臣和失去良心的王公們,可以替祖宗聲討此罪,借此告知天下保存大清之名義。」他進而向日本說明這樣做的好處:「此一於北方興起之國,其首腦當然明白只能靠日本的掩護才能生存。我國可以利用此點為我機關所用。所以應該盡一切可能給予援助。」19這應該是川島浪速關於他策劃的所謂「滿蒙獨立運動」構想的最早表述,但是可以看到,因為具有「勤王」的因素,直到此時還沒見到「獨立」二字。第二節 蒙古王公的「勤王」與「獨立」
1912年2月,在得知清王朝皇室已經決定遜位後,川島浪速馬上開始行動,在川島的計劃和具體安排之下,肅親王善耆於2月2日逃出北京,由天津乘坐日本郵船「渤海丸」,於6日到達當時在日本控制之下的旅順。20之後,川島浪速又設計讓在北京的蒙古王公逃離北京,以便回到內蒙古東部可以「舉事」、「勤王」。
有趣的是,即使在1911年底、1912年初這個敏感的時點,被川島浪速用來將「滿」「蒙」兩個民族集團的社會上層一起糅合的歷史和政治因素,仍然是即將謝幕的「大清」。包括清王朝在內,中國歷史上由非漢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為主人公的征服王朝。這些王朝,因為在進入「中國」建立政權之後認識到無法用自己「民族」的統治方式統治「中國」,逐漸都會向中華王朝轉化。然而,由於這些政權是通過武力征服的方式進入「中國」,最初都會與「中國」的民眾之間存在嚴重的民族隔閡或民族對立,這使得它不得不在以中華文明方式統治「中國」的同時,又都採用了以周邊的「民族」集團牽制「中國」,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征服王朝的「多元式天下」的傳統。21而在清王朝以民族等級制度為基礎的「多元式天下」構造中,蒙古社會上層被賦予特殊的地位。所以,作為清王朝的一個特權階層,在面臨清王朝全面崩潰的時刻,蒙古社會上層也就對清王朝表示出那麼一點的「忠誠」。例如辛亥革命時期,曾任陝甘總督的蒙古人昇允率舊部反抗,他曾經作過這樣一首詩以表明心態:「老臣猶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蘇武書。」22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由蒙古王公所提出的「勤王」──組織軍隊進軍北京以支撐清王朝的統治體制,最初並不是出自於內蒙,而是出自於外蒙。1911年11月8日(舊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接到(外蒙古)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來信,內稱:「現聞內地各省,相繼獨立。革命黨人,已帶兵取道張家口來庫,希圖擾亂蒙疆。我喀爾喀四部蒙眾,受大清恩惠二百餘年,不忍坐視。我佛哲布尊巴呼圖克圖,已傳檄徵調四盟騎兵四千名,進京保護大清皇帝。請即日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以便起行。是否照準,限本日三小時內,明白批示。」23
外蒙古四盟王公在信中所提出的「勤王」條件──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事實上是當時庫倫大臣所根本無法辦到的。因為外蒙古王公已於一年前開始暗中交接俄國勢力籌畫獨立,所以說,這封信中所提出的「勤王」,只不過是為其之後進行分裂活動製造一個正當性理由而已。果不其然,當天晚上7時,三多再接哲布尊巴呼圖克圖宣佈外蒙古獨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朝恩遇,不為不厚。……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佈獨立,以期完全。⋯⋯庫倫地方,已無需用中國官吏之處,自應全數驅逐,以杜後患。24
不能「勤王」就要獨立,從這種做法中可以看出蒙古王公們的一個邏輯:蒙古是清王朝版圖的一部分卻不是中國的領土,蒙古人是大清國的臣民卻不是中國的國民。因此,清王朝一旦滅亡,蒙古與清王朝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也就隨之煙消雲散,而蒙古也就與中國沒有關係。鼓吹蒙古獨立的人們將清王朝與「中國」做了區分,既然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內地各省都可以與清朝政府脫離關係而實現獨立,那麼與各省同為大清國組成部分的蒙古,如果無法通過「勤王」的手段去保護作為母體的清王朝,那就只能與中國內地各省同樣選擇自保的方法,與清王朝脫離關係宣佈獨立。然而,為甚麼勤王得以作為分裂的正當性根據一事,值得引起注意。
外蒙古的獨立運動,開中國近代民族分裂活動之濫觴。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中國近代民族分裂主義思想和運動的發生,與中國政治和社會體制發生翻天覆地的劇變,二者之間的關係絕不僅只是時間上的巧合,而與當年清王朝採用「多元式天下」思想所構築的王朝的政治地理、如今革命家所提倡和追求的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思想及行動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25蒙古王公之所以提出「勤王」遭拒為提出「獨立」的正當性依據,就在於清王朝統治中國的政治構造曾經具備「滿族聯合蒙、藏、回以牽制漢人」的性質。正因為以上關係,蒙古王公在意識到清王朝已經無法扭轉滅亡之趨勢的情況下所提出的「勤王」口號,實質上就是「民族獨立」的前奏。口頭上喊著「勤王」,實質上想的卻是「民族獨立」,內蒙古的王公們在武昌起義爆發後的活動,同樣也是這種情形。不同的只是內蒙古王公們的「勤王」得到了日本勢力的支持,而外蒙古的分裂活動具有帝俄的背景。
汪炳明的〈清朝覆亡之際駐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動〉利用諸多檔案,記述了這一時期在北京蒙古王公的活動特徵。以那彥圖(喀爾喀親王,清廷御前大臣,八旗鑲紅旗都統)、貢桑諾爾布(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世襲扎薩克親王,卓索圖盟盟長,肅親王善耆的妹夫)、博迪蘇(哲里木盟科爾沁左翼後旗扎薩克博多勒噶台親王伯彥訥謨祐第三子,輔國公,御前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兼署正紅旗滿洲都統)、多爾濟帕拉穆(喀爾喀車臣汗部中右旗扎薩克多羅郡王,車臣汗部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盟長)、帕勒塔(土爾扈特東部落六世君王巴雅爾之生子,襲封扎薩克郡王,科布多辦事大臣)為首,當時在北京清廷中有二十幾名蒙古王公。26此時這些蒙古王公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和活動特徵,一言蔽之,就是激烈反對清帝退位和實行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