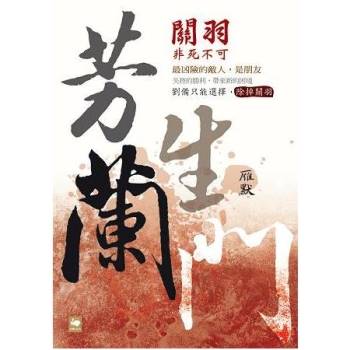二、單刀會——魯肅
建安二十年,荊州益陽
吳蜀兩軍對峙,在雙方相距奔馬百步的中線,吳帥魯肅與蜀將關羽展開荊州歸屬的談判,兩個指揮官相約只帶著數名侍衛與幕僚,單刀與會。
土地,有德者居之,哪能說一定是誰的?
關羽方面一名軍官在雙方激辯中,突發此語。
原本主帥魯肅和關羽,只是默默注視雙方幕僚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此言一出,卻見魯肅倏地拔出單刀:「說得什麼話!?」他聲色俱厲地怒斥那名軍官,頓時雙方都安靜下來。魯肅平時沉穩而溫和,治軍雖嚴而待人以寬,文武部屬甚少見他發怒,而關羽以及其幕僚,即便在兩方常常為軍事邊界的衝突而鬧得不愉快時,向來也只見溫言相待的魯肅,未曾見過他一絲怒容,更別說此刻的高聲長嘯,拔刀而起了。因而吳蜀兩方文武隨從,同時都為魯肅罕見的氣勢所震懾。
發言者看來是一名中階軍官,第一次在這種場合見識敵方主帥猛虎般的威怒,雖一人,僅一刻,攝人程度竟如千軍萬馬,不免心下稍畏,但仍努力保持鎮定。
關羽見此變故,愣了一會兒,隨即回神,他身為主帥不能保持沉默,便也抽出單刀,厲聲呵叱該軍官:「國之大事,你懂什麼,退下!」關羽雖高聲厲喝,卻以眼神示意軍官離開會場,魯肅見狀,便知關羽心口不一,幕僚敢在這麼敏感的場合驟發此論,自是早有安排,以中階軍官表明蜀營的真實立場,測試吳方的底線,高層則保持表面的盟好姿態,不說死,留些退路。
孫權與劉備結盟挺過赤壁戰後,至今已七年,兩方從友好到兵戎相見,為得是劉備曾嚴詞拒絕孫權的邀請,聯軍侵蜀,然而孫權才打消念頭沒多久,劉備就率軍獨自入蜀,並取得了益州。遭盟友欺騙,孫權怒不可抑,以諸葛瑾為使者,至成都要求劉備歸還荊州,卻碰了個軟釘子,劉備聲稱,等蜀方取得涼州後,便會奉還荊州。上一次當,還能怪騙子無良,再上當就只能怪自己愚蠢了,狡詐的老賊還想騙!見劉備耍賴,孫權立刻展開索討荊州的實際行動,直接派遣官吏至荊州三個郡走馬上任。
不出所料,東吳派遣的官吏,一一都被鎮守荊州的關羽趕回江東,硬是不還。於是孫權便不客氣了,派大將呂蒙揮兵入荊,硬碰硬,乾脆以武力強占了三郡。既然劃下道兒,吳蜀兩方當下便是決裂了,劉備立刻要求關羽率兵搶回三郡,而魯肅的任務,便是率領上萬大軍在益陽阻擋關羽的攻勢。吳蜀的同盟與決裂,魯肅是最關鍵的人物。協助孫權擺平國內一片降曹聲浪,採取抗曹政策的是他,策劃與劉備聯手擊曹於赤壁的也是他,主張借荊州給劉備的還是他,三國鼎立,可說是魯肅一手擘畫的局面。雖然時局不斷變化,國與國的同盟不可能永遠保持友好如初,但兩小國共同抵禦大國在方向上的正確性不會改變。這簡單的道理,凡人也能明白,但魯肅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不但能認清東吳不可能獨立抗曹的現實,還能將之化為信念,不為任何政治變數所動搖。
連劉抗曹的第一個變數,是江東大族的政治勢力是否會政變,向曹操奉上孫權項上人頭,以換取身家性命。所以魯肅勸孫權急召周瑜率兵前來護駕,確保降曹勢力不敢輕舉妄動,因而安然度過第一關。
第二個變數,是兩造是否真能攜手成功抵禦曹操的進逼。因周瑜善戰,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擊退強敵於前,而因劉備弱小,只能為共同目標拼命奪取南荊州於後,才在驚濤駭浪的赤壁度過了第二關。
第三個變數,是赤壁戰後,最大功臣周瑜對劉備陣營的敵視。雖然周瑜是魯肅生命中的貴人,兩人對世局的看法也雷同,相互賞識,情同手足,但魯肅與周瑜在處理劉備問題上,卻是兩異,周瑜主張趁機消滅劉備,魯肅則不改連劉抗曹的路線。其實,劉備的不可信任,眾所皆知,魯肅並非押寶在劉備的忠誠上,只是他比周瑜更為認清東吳與曹魏實力的落差。周瑜充滿自信,認為東吳可獨立抗魏,無須他人牽制曹操,更何況,別說合作,劉備扯後腿的可能性還更大。以當時的態勢,兩種看法誰也說不準哪一方較為正確,所以劉備開口借荊州,等於給了孫權一個大難題。然而躊躇間,周瑜卻死了,難題也解了,孫權決定走魯肅建議的路線試試看,聯盟才算度過第三關。
聯盟未滿三年,孫劉關係面臨第四個變數,建安十六年,曹操欲西向取漢中,益州牧劉璋聽從了幕僚的建議,迎劉備入蜀,聯軍抗曹。劉備在欺瞞東吳的狀況下,率軍入益州,獨自展開陰謀侵蜀行動。放下孫權寫來的信,魯肅支手撐額,閉目長考,他能理解孫權的震怒,遭盟友背叛,傷害比遭敵人攻擊還大得多。年輕的孫權立刻就想出兵奪回荊州,討回公道,並要求魯肅表態。魯肅無意改變初衷,打破目前的結盟狀態。一則劉備入蜀成敗未知,結果不見得對東吳不利,二則針對東邊的孫吳,荊州留守早已佈置成備戰態勢,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尚在,十分難對付,馬上決裂的成本太高。
魯肅回信,將大勢一一向孫權分析,並確立了吳方的政治回應,先結束聯姻,以示不滿,然後靜觀其變。東吳可趁曹操主力西向取蜀之際,繼續北伐步調,而魯肅自己,自然承擔起吳蜀邊防重責,監視荊州動態。君臣二人並決定,日後劉備若僥倖獲勝,拿下益州之日,便是東吳索討荊州之日。
劉備得以率軍入蜀的主因,是因為曹操開始對益州北部的漢中採取軍事行動。漢中為張魯所據,長期與益州牧劉璋交戰,曹軍西向,使得劉璋決定引劉備為援,屯兵於葭萌,緊盯漢中局勢。然而無論張魯是降是戰,劉備都無意與曹軍交鋒,他的目標是趕走劉璋,那個當年他向孫權聲稱,要堅決守護的人。曹操的西向不但改變了益州的命運,也間接重創了孫劉聯盟。
東吳兵鋒維持在北向,而未對劉備入蜀採取過激的行動,事後證明是正確的,因為隔年,曹操便欲再度大舉南征東吳,孫權無暇處理劉備問題,只能嚴整以待曹操大軍。另一方面,劉備利用了曹軍擊吳的訊息,藉口要回荊州協助盟友孫權,要求劉璋資助軍隊與糧食,但劉璋無法滿足劉備的獅子大開口,只答應供給一半,劉備便以此為由翻臉,正式發動侵蜀戰爭。
時局變幻莫測,建安十七年,曹操號稱步騎四十萬,大舉征吳,孫權以七萬部隊回應,規模雖大,雙方卻僅對峙一個多月,曹軍便撤,雷聲大雨點小。相對於此,益州戰況激烈,劉璋軍或敗或叛或降,兵敗如山倒,劉備軍勢如破竹,兵圍雒城。
建安十八年,鳳雛龐統戰死在圍城戰中,但終於攻陷雒城,劉備進一步兵圍成都,距離勝利只剩臨門一腳,諸葛亮,張飛,趙雲受命溯江西上支援,關羽則留守荊州。建安十八年,荊州陸口
收到消息時,魯肅正策馬視察邊境軍務,他眉頭深鎖,目光轉向江陵,怔了半响。
孔明離開了。
益州情勢急轉直下,讓魯肅感到意外,而諸葛亮入蜀,荊州由關羽一人掌握,則令他憂慮。
堅定支持孫劉聯盟者,其實在兩方陣營並不多,劉備方面的要角是諸葛亮,也是幾年下來魯肅的主要對口。他們一東一西同是鴿派,賣力地維持著孫劉間的和睦,而時局的變化卻與他們的理念背道而馳,孫劉間的矛盾愈深,合作的空間便愈縮,最終使兩人深陷於夾縫之中。前年孫權聽魯肅建議,結束聯姻,派遣戰艦至荊州,將他嫁給劉備的妹妹接回江東,孫夫人性烈而強悍,擄了阿斗上船便走,所幸諸葛亮讓趙雲攔截,僅留下阿斗,放行吳艦,事情也船過水無痕。繼承人被綁架,此事可大可小,若由關羽處理,恐怕不會輕易甘休,後果不堪設想。
諸葛亮識大體,雖各為其主,卻是魯肅唯一能說得上話的對手,有他在,魯肅才不至於在堅持同盟的立場上孤軍奮戰。現下,值得憂慮的不只是鴿派的離去,還有以關羽留守而非諸葛亮留守這個事實。此舉意味著劉備送給孫權一個清楚的訊息,荊州已不再是同盟的象徵,也不是兩方的政治緩衝處,而是劉家後院,由「不識大體」的武人看管,莫要輕舉妄動。
同盟關係至此,等於敲了喪鐘。
若只是兩方撕破臉,戰場上決勝負,這簡單,不需要智計之士,但魯肅存在的目的,便是能為國家看得更遠,無論是戰是和,現下的決定必須顧慮到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後的未來。在魯肅的思維裡,荊州對東吳的重要性,遠低於聯盟的重要性,因為即便擁有荊州,也未必對北伐大業有更多的幫助,反而,東吳必須將有限的軍力調撥至更多的據點,這也是當初主張借荊州給劉備最主要的因素。
然而,這樣的看法在劉備取得益州之後,必須有所調整,因為跨有荊,益者,無論是向北逐鹿中原,或向東蠶食江表,都有益州作為退路,相對地,東吳卻沒有。既如此,荊州就成了東吳必爭之地,而且事不宜遲。有鑑於此,魯肅面臨的挑戰則是如何取得荊州,又能保持聯盟關係。諸葛亮離開後,魯肅身處兩方陣營邊境,立即就感到氣氛的驟變,首當其衝的便是邊防守軍。兩邊的部隊因細故而起的衝突愈來愈多,邊境防衛趨於緊張,關羽那方時有責問的書信傳來,一而再,再而三,不斷考驗魯肅的耐性與政治智慧。面對荊州的新情勢,兩國間的衝突升高,即便他能以大局為重,讓步以消弭戰爭,但孫權可忍一步退,卻不能忍步步退,因為若退無可退時才予以還擊,結果只有更糟。
魯肅左想右想前想後想,無論怎麼想,答案都是「必須先拔除關羽這根釘。」
重點在於,用什麼方式對東吳衝擊最小。
退後是為了向前……。
飯吃了一半,魯肅腦中突然靈光一閃,停下筷子低喃了一句,便轉頭吩咐僕從:「明日去建業,準備一下。」
建安十八年,揚州建業
孫權低頭抱胸,來回踱步,時而抬頭並不耐地瞪著魯肅,因劉備拿下成都只是時間問題,眼睜睜看著叛徒得志,令他極為不快,連帶也對始終要求他按兵不動的魯肅心生不滿。
魯肅裝作沒看見,慢條斯理地向孫權解釋,若雙方現在翻臉,我方出兵強取荊州,結果只會迫使劉備分兵援助,一旦戰況膠著,最終是兩敗俱傷,讓曹操撿了便宜……
孫權低頭抱胸,來回踱步。
「關羽強橫善戰,若力敵,我方將付出太大代價,因而只能智取……」
魯肅繼續說明。
孫權低頭抱胸,來回踱步,還不時咬著手指甲。
「所謂智取,就是將關羽孤立……」
魯肅不疾不徐,繼續解釋。
孫權聽出了點意思,停下腳步,在魯肅面前站定。
魯肅將話打住,啜了口茶,清清喉嚨,孫權抖起腳來,喉間發出不明悶聲。
「結親。」(p211)
孫權在魯肅面前坐了下來,圓睜雙眼盯著魯肅的臉。一開始他還懷疑自己聽錯,然而魯肅不言不笑,容色淡然。
「和關羽結親。」
魯肅補了一句。
孫權眨了眨眼,半晌不說話。
孫權實際上為一國之君,政治聯姻只限於最信任的重臣將帥,或必須依賴的盟友,且當初將自己妹妹嫁給劉備,結果賠了夫人還遭欺,現下關羽擺明了是敵人丟到門口來對付自己的鷹犬,什麼道理再送塊肉去討好?
「孤立……。」
魯肅見孫權臉色陰晴不定,再暗示一句。
只見孫權臉色由紅轉白,嘴角微微上揚,圓眼逐漸瞇成了一條線。
「這下懂了……。」魯肅暗暗鬆了口氣,向似笑非笑的孫權點了點頭。
孤立關羽最好的方式是籠絡,但劉關二人情同父子,休戚與共,連曹操都沒輒,因而若暗地裡收買他,只能是愚蠢,關羽永遠不可能為己所用。然而,高調而公開地籠絡,其效果便是離間,讓劉備對他的第一大將產生疑心。以孫權的身分開口,這門親事無論關羽接不接受,無形中其一介武人的身分也大幅提升,魯肅的目的,便是將關羽的地位提升到劉備不能不警覺的程度。一旦劉關之間產生裂縫,哪怕是多麼細微的縫,東吳都能不費一兵一卒,取得實質的好處。再者,對關羽採取這麼低的姿態,能令其鬆懈對己方的防備,將軍事重心轉回到北邊的曹營。若能慫恿關羽北伐,離開荊州,則是最好的結果。三者,關羽不是傻子,不可能接受孫權提親,他必須拒絕,而且必須高聲拒絕,以對遠方的劉備顯示忠誠,但如此一來,形同羞辱孫權,並激怒東吳朝野。舉國上下敵視關羽,有利於統一輿論,加強國內討回荊州的集體意志。
最終目標只有一個,奪回荊州。
想辦法容易,但說服孫權使用這個辦法卻難。向敵人示好,需要高度的自制與包容,尤其在劉備不但背盟,還讓關羽強硬對待東吳的狀況下,魯肅心知要孫權低聲下氣難度甚高,唯有以策略的角度才能說服這個年輕的君主。
退後是為了向前。
「痛快,」孫權大笑說,「痛快。」
方向既定,在陸口的魯肅,對邊境糾紛一律採取退讓的姿態,在建業的孫權,則派遣使者前往江陵,向關羽提親。而結果不出預料,使者遭關羽辱罵而還。孫權以子配關羽之女,東吳朝野已認為是一種屈就,結果對方不但拒絕,還羞辱我使,是可忍,孰不可忍,魯肅之計果然使得國內群情激憤。
這日,文臣武將齊聚,在孫權面前掀起了討伐關羽的聲浪。孫權在人前表現得憤怒不已,心中則暗喜得計,正待尋思下一步,這時卻收到魯肅自陸口傳來的情報。
劉璋出降,劉備已破成都。
孫權放下書信,轉頭望向諸葛瑾與呂蒙。
建安二十年,荊州益陽
支開了「失言」的軍官以後,關羽收刀拱手,請魯肅入座。魯肅見關羽緊繃著他那張棗紅色的臉,未再多言,便也退了一步,收刀入席,會場氣氛才緩和下來。
此前該軍官之所以會說那番話打斷魯肅發言,是因為魯肅所表述的東吳立場:「當初,曹操大軍攻擊荊州,貴國劉主大敗而落魄南奔,窘迫的狀況可說已是朝不保夕,幸賴東吳伸出援手,在聯手擊退曹軍後,還將荊州出借,以協助盟友得以休養壯大。然而,如今貴國已取得沃野千里的益州,卻不願歸還荊州,我主願退而只求歸還荊州三郡,仍遭拒絕,有借無還,實在說不過去。貴我本同盟之國,攜手只為滅曹,現下鬧到兵戎相見,只怕樂了曹公而已。」
魯肅特別稱曹操為曹公,而不直稱其曹操或曹賊,是因關羽曾受曹操厚遇,是反曹陣營裡罕見與曹操有過君臣之情的人,而曹操在去年進爵為魏公。
關羽雖非文人,並出身寒微,但畢竟也歷經大風大浪,在這種場合也是特別小心用詞,他站在劉備的立場回應魯肅:
「赤壁戰時,我主無一日不身在行伍之間與士卒共飲食,與部隊在站在最前線,就寢時連鞋也不脫,隨時準備應付敵人夜襲。此役我等在荊州也是獨力與曹軍周旋,夙夜匪懈,取勝絕非僥倖,難道只是徒勞一場?我等費盡心力,犧牲士卒,怎能一塊土地也沒有?」
這番說詞該怎麼回應,魯肅早有腹案:
「當年在當陽長阪與劉主一起出入營陳,貴營的總兵員數目,不滿兩千,面對排山倒海的曹軍,拿不出一點辦法,唯有往更遠的地方流竄一途。我主不忍劉主一世之英,卻無寸土容身之所,始終寄人籬下,因而雖贏得半壁荊州,寧可虧待用性命掙來土地的將士,將荊州借與劉主發展。如今貴國既得益州,又要荊州,販夫走卒都不好意思這麼幹,劉主氣量宏遠,如此實為下策。古言貪而棄義,必為禍階,我倆肩負荷國之重任,必須明理以輔佐主上,況且以弱擊強,師出之名又不正,一旦戰事拖延,對貴國百害而無一利。」
關羽欲言又止,沉默了起來。事實上,關羽和魯肅心裡都清楚,今日能有這半面荊州,是因為當年周瑜擋住了曹軍主力,劉備方面才得以趁亂攻下了荊南四個郡。若非周瑜,劉備一點點兵力無濟於事,終歸要灰飛煙滅於曹操南征大軍的鐵蹄下。簡單地說,對東吳而言,劉備只是助攻而已。但對關羽而言,此役之功主要在東吳是事實,但他是武人,武人的觀念是,以自己力量掙來的地盤,當然就是他的,就這麼簡單,不可能接受政治性的權宜看法。因而,關羽辯解得很技巧,明明我們也流血流汗,「怎能一塊土都沒分到呢?」而不是說「荊州都是我們打下來的」。魯肅的答辯則是技巧性迴避荊南四郡的問題,而是將問題追本溯源,「你們當時都要被滅了,若不是我們出手相助,今天哪有你們在這裡鬧事的份兒?」。
關羽在這個問題上比較吃虧是肯定的,因為若不是他面前的魯肅力爭,孫權根本不可能違逆眾意,將荊州借給劉備。而劉備以下所有人,能有個著力之處奮力上跳,其實都拜魯肅之賜,而欠他這個大人情。兩造於會中雖不乏外交辭令,但在關鍵處魯肅能夠直言不諱,便是有此背景之故。再者,對手關羽是武人,面對武人,有話直說反而更好溝通。
魯肅溫言向關羽說,你我身負兩國國運的重任,現下曹公動向未明,我們於此決戰,真的是劉主所樂見的嗎?
關羽別過頭去,並未回應。其實此次兩方兵戎相見,都意在宣示武力,而非真要拼搏出一個荊州歸屬,魯肅此問,便是想從關羽的反應中確認這點,而答案看來正是如此。劉備才拿下益州,人心浮動,百廢待舉,根本不是與東吳攤牌的好時機。
雙方立場已表達清楚,魯肅正要提議散會,彼此按兵不動,並嚴正約束部屬。
「敢問閣下,孫主向關某提親,是何用意?」
關羽冷不防向魯肅提問,眼中滿是敵意。
魯肅並未料到關羽會在這種場合丟出這個問題,心裡打了個突,抬起頭來和關羽四目相交。
「善意。」
魯肅留下兩個字與一抹淡然的笑意,向關羽行了告別禮,率領隨從步出會場。
和親的目的對他而言,確實是為了吳、蜀兩國的關係,只是對關羽而言並非如此罷了。
建安二十年,荊州益陽
吳蜀兩軍對峙,在雙方相距奔馬百步的中線,吳帥魯肅與蜀將關羽展開荊州歸屬的談判,兩個指揮官相約只帶著數名侍衛與幕僚,單刀與會。
土地,有德者居之,哪能說一定是誰的?
關羽方面一名軍官在雙方激辯中,突發此語。
原本主帥魯肅和關羽,只是默默注視雙方幕僚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此言一出,卻見魯肅倏地拔出單刀:「說得什麼話!?」他聲色俱厲地怒斥那名軍官,頓時雙方都安靜下來。魯肅平時沉穩而溫和,治軍雖嚴而待人以寬,文武部屬甚少見他發怒,而關羽以及其幕僚,即便在兩方常常為軍事邊界的衝突而鬧得不愉快時,向來也只見溫言相待的魯肅,未曾見過他一絲怒容,更別說此刻的高聲長嘯,拔刀而起了。因而吳蜀兩方文武隨從,同時都為魯肅罕見的氣勢所震懾。
發言者看來是一名中階軍官,第一次在這種場合見識敵方主帥猛虎般的威怒,雖一人,僅一刻,攝人程度竟如千軍萬馬,不免心下稍畏,但仍努力保持鎮定。
關羽見此變故,愣了一會兒,隨即回神,他身為主帥不能保持沉默,便也抽出單刀,厲聲呵叱該軍官:「國之大事,你懂什麼,退下!」關羽雖高聲厲喝,卻以眼神示意軍官離開會場,魯肅見狀,便知關羽心口不一,幕僚敢在這麼敏感的場合驟發此論,自是早有安排,以中階軍官表明蜀營的真實立場,測試吳方的底線,高層則保持表面的盟好姿態,不說死,留些退路。
孫權與劉備結盟挺過赤壁戰後,至今已七年,兩方從友好到兵戎相見,為得是劉備曾嚴詞拒絕孫權的邀請,聯軍侵蜀,然而孫權才打消念頭沒多久,劉備就率軍獨自入蜀,並取得了益州。遭盟友欺騙,孫權怒不可抑,以諸葛瑾為使者,至成都要求劉備歸還荊州,卻碰了個軟釘子,劉備聲稱,等蜀方取得涼州後,便會奉還荊州。上一次當,還能怪騙子無良,再上當就只能怪自己愚蠢了,狡詐的老賊還想騙!見劉備耍賴,孫權立刻展開索討荊州的實際行動,直接派遣官吏至荊州三個郡走馬上任。
不出所料,東吳派遣的官吏,一一都被鎮守荊州的關羽趕回江東,硬是不還。於是孫權便不客氣了,派大將呂蒙揮兵入荊,硬碰硬,乾脆以武力強占了三郡。既然劃下道兒,吳蜀兩方當下便是決裂了,劉備立刻要求關羽率兵搶回三郡,而魯肅的任務,便是率領上萬大軍在益陽阻擋關羽的攻勢。吳蜀的同盟與決裂,魯肅是最關鍵的人物。協助孫權擺平國內一片降曹聲浪,採取抗曹政策的是他,策劃與劉備聯手擊曹於赤壁的也是他,主張借荊州給劉備的還是他,三國鼎立,可說是魯肅一手擘畫的局面。雖然時局不斷變化,國與國的同盟不可能永遠保持友好如初,但兩小國共同抵禦大國在方向上的正確性不會改變。這簡單的道理,凡人也能明白,但魯肅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不但能認清東吳不可能獨立抗曹的現實,還能將之化為信念,不為任何政治變數所動搖。
連劉抗曹的第一個變數,是江東大族的政治勢力是否會政變,向曹操奉上孫權項上人頭,以換取身家性命。所以魯肅勸孫權急召周瑜率兵前來護駕,確保降曹勢力不敢輕舉妄動,因而安然度過第一關。
第二個變數,是兩造是否真能攜手成功抵禦曹操的進逼。因周瑜善戰,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擊退強敵於前,而因劉備弱小,只能為共同目標拼命奪取南荊州於後,才在驚濤駭浪的赤壁度過了第二關。
第三個變數,是赤壁戰後,最大功臣周瑜對劉備陣營的敵視。雖然周瑜是魯肅生命中的貴人,兩人對世局的看法也雷同,相互賞識,情同手足,但魯肅與周瑜在處理劉備問題上,卻是兩異,周瑜主張趁機消滅劉備,魯肅則不改連劉抗曹的路線。其實,劉備的不可信任,眾所皆知,魯肅並非押寶在劉備的忠誠上,只是他比周瑜更為認清東吳與曹魏實力的落差。周瑜充滿自信,認為東吳可獨立抗魏,無須他人牽制曹操,更何況,別說合作,劉備扯後腿的可能性還更大。以當時的態勢,兩種看法誰也說不準哪一方較為正確,所以劉備開口借荊州,等於給了孫權一個大難題。然而躊躇間,周瑜卻死了,難題也解了,孫權決定走魯肅建議的路線試試看,聯盟才算度過第三關。
聯盟未滿三年,孫劉關係面臨第四個變數,建安十六年,曹操欲西向取漢中,益州牧劉璋聽從了幕僚的建議,迎劉備入蜀,聯軍抗曹。劉備在欺瞞東吳的狀況下,率軍入益州,獨自展開陰謀侵蜀行動。放下孫權寫來的信,魯肅支手撐額,閉目長考,他能理解孫權的震怒,遭盟友背叛,傷害比遭敵人攻擊還大得多。年輕的孫權立刻就想出兵奪回荊州,討回公道,並要求魯肅表態。魯肅無意改變初衷,打破目前的結盟狀態。一則劉備入蜀成敗未知,結果不見得對東吳不利,二則針對東邊的孫吳,荊州留守早已佈置成備戰態勢,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尚在,十分難對付,馬上決裂的成本太高。
魯肅回信,將大勢一一向孫權分析,並確立了吳方的政治回應,先結束聯姻,以示不滿,然後靜觀其變。東吳可趁曹操主力西向取蜀之際,繼續北伐步調,而魯肅自己,自然承擔起吳蜀邊防重責,監視荊州動態。君臣二人並決定,日後劉備若僥倖獲勝,拿下益州之日,便是東吳索討荊州之日。
劉備得以率軍入蜀的主因,是因為曹操開始對益州北部的漢中採取軍事行動。漢中為張魯所據,長期與益州牧劉璋交戰,曹軍西向,使得劉璋決定引劉備為援,屯兵於葭萌,緊盯漢中局勢。然而無論張魯是降是戰,劉備都無意與曹軍交鋒,他的目標是趕走劉璋,那個當年他向孫權聲稱,要堅決守護的人。曹操的西向不但改變了益州的命運,也間接重創了孫劉聯盟。
東吳兵鋒維持在北向,而未對劉備入蜀採取過激的行動,事後證明是正確的,因為隔年,曹操便欲再度大舉南征東吳,孫權無暇處理劉備問題,只能嚴整以待曹操大軍。另一方面,劉備利用了曹軍擊吳的訊息,藉口要回荊州協助盟友孫權,要求劉璋資助軍隊與糧食,但劉璋無法滿足劉備的獅子大開口,只答應供給一半,劉備便以此為由翻臉,正式發動侵蜀戰爭。
時局變幻莫測,建安十七年,曹操號稱步騎四十萬,大舉征吳,孫權以七萬部隊回應,規模雖大,雙方卻僅對峙一個多月,曹軍便撤,雷聲大雨點小。相對於此,益州戰況激烈,劉璋軍或敗或叛或降,兵敗如山倒,劉備軍勢如破竹,兵圍雒城。
建安十八年,鳳雛龐統戰死在圍城戰中,但終於攻陷雒城,劉備進一步兵圍成都,距離勝利只剩臨門一腳,諸葛亮,張飛,趙雲受命溯江西上支援,關羽則留守荊州。建安十八年,荊州陸口
收到消息時,魯肅正策馬視察邊境軍務,他眉頭深鎖,目光轉向江陵,怔了半响。
孔明離開了。
益州情勢急轉直下,讓魯肅感到意外,而諸葛亮入蜀,荊州由關羽一人掌握,則令他憂慮。
堅定支持孫劉聯盟者,其實在兩方陣營並不多,劉備方面的要角是諸葛亮,也是幾年下來魯肅的主要對口。他們一東一西同是鴿派,賣力地維持著孫劉間的和睦,而時局的變化卻與他們的理念背道而馳,孫劉間的矛盾愈深,合作的空間便愈縮,最終使兩人深陷於夾縫之中。前年孫權聽魯肅建議,結束聯姻,派遣戰艦至荊州,將他嫁給劉備的妹妹接回江東,孫夫人性烈而強悍,擄了阿斗上船便走,所幸諸葛亮讓趙雲攔截,僅留下阿斗,放行吳艦,事情也船過水無痕。繼承人被綁架,此事可大可小,若由關羽處理,恐怕不會輕易甘休,後果不堪設想。
諸葛亮識大體,雖各為其主,卻是魯肅唯一能說得上話的對手,有他在,魯肅才不至於在堅持同盟的立場上孤軍奮戰。現下,值得憂慮的不只是鴿派的離去,還有以關羽留守而非諸葛亮留守這個事實。此舉意味著劉備送給孫權一個清楚的訊息,荊州已不再是同盟的象徵,也不是兩方的政治緩衝處,而是劉家後院,由「不識大體」的武人看管,莫要輕舉妄動。
同盟關係至此,等於敲了喪鐘。
若只是兩方撕破臉,戰場上決勝負,這簡單,不需要智計之士,但魯肅存在的目的,便是能為國家看得更遠,無論是戰是和,現下的決定必須顧慮到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後的未來。在魯肅的思維裡,荊州對東吳的重要性,遠低於聯盟的重要性,因為即便擁有荊州,也未必對北伐大業有更多的幫助,反而,東吳必須將有限的軍力調撥至更多的據點,這也是當初主張借荊州給劉備最主要的因素。
然而,這樣的看法在劉備取得益州之後,必須有所調整,因為跨有荊,益者,無論是向北逐鹿中原,或向東蠶食江表,都有益州作為退路,相對地,東吳卻沒有。既如此,荊州就成了東吳必爭之地,而且事不宜遲。有鑑於此,魯肅面臨的挑戰則是如何取得荊州,又能保持聯盟關係。諸葛亮離開後,魯肅身處兩方陣營邊境,立即就感到氣氛的驟變,首當其衝的便是邊防守軍。兩邊的部隊因細故而起的衝突愈來愈多,邊境防衛趨於緊張,關羽那方時有責問的書信傳來,一而再,再而三,不斷考驗魯肅的耐性與政治智慧。面對荊州的新情勢,兩國間的衝突升高,即便他能以大局為重,讓步以消弭戰爭,但孫權可忍一步退,卻不能忍步步退,因為若退無可退時才予以還擊,結果只有更糟。
魯肅左想右想前想後想,無論怎麼想,答案都是「必須先拔除關羽這根釘。」
重點在於,用什麼方式對東吳衝擊最小。
退後是為了向前……。
飯吃了一半,魯肅腦中突然靈光一閃,停下筷子低喃了一句,便轉頭吩咐僕從:「明日去建業,準備一下。」
建安十八年,揚州建業
孫權低頭抱胸,來回踱步,時而抬頭並不耐地瞪著魯肅,因劉備拿下成都只是時間問題,眼睜睜看著叛徒得志,令他極為不快,連帶也對始終要求他按兵不動的魯肅心生不滿。
魯肅裝作沒看見,慢條斯理地向孫權解釋,若雙方現在翻臉,我方出兵強取荊州,結果只會迫使劉備分兵援助,一旦戰況膠著,最終是兩敗俱傷,讓曹操撿了便宜……
孫權低頭抱胸,來回踱步。
「關羽強橫善戰,若力敵,我方將付出太大代價,因而只能智取……」
魯肅繼續說明。
孫權低頭抱胸,來回踱步,還不時咬著手指甲。
「所謂智取,就是將關羽孤立……」
魯肅不疾不徐,繼續解釋。
孫權聽出了點意思,停下腳步,在魯肅面前站定。
魯肅將話打住,啜了口茶,清清喉嚨,孫權抖起腳來,喉間發出不明悶聲。
「結親。」(p211)
孫權在魯肅面前坐了下來,圓睜雙眼盯著魯肅的臉。一開始他還懷疑自己聽錯,然而魯肅不言不笑,容色淡然。
「和關羽結親。」
魯肅補了一句。
孫權眨了眨眼,半晌不說話。
孫權實際上為一國之君,政治聯姻只限於最信任的重臣將帥,或必須依賴的盟友,且當初將自己妹妹嫁給劉備,結果賠了夫人還遭欺,現下關羽擺明了是敵人丟到門口來對付自己的鷹犬,什麼道理再送塊肉去討好?
「孤立……。」
魯肅見孫權臉色陰晴不定,再暗示一句。
只見孫權臉色由紅轉白,嘴角微微上揚,圓眼逐漸瞇成了一條線。
「這下懂了……。」魯肅暗暗鬆了口氣,向似笑非笑的孫權點了點頭。
孤立關羽最好的方式是籠絡,但劉關二人情同父子,休戚與共,連曹操都沒輒,因而若暗地裡收買他,只能是愚蠢,關羽永遠不可能為己所用。然而,高調而公開地籠絡,其效果便是離間,讓劉備對他的第一大將產生疑心。以孫權的身分開口,這門親事無論關羽接不接受,無形中其一介武人的身分也大幅提升,魯肅的目的,便是將關羽的地位提升到劉備不能不警覺的程度。一旦劉關之間產生裂縫,哪怕是多麼細微的縫,東吳都能不費一兵一卒,取得實質的好處。再者,對關羽採取這麼低的姿態,能令其鬆懈對己方的防備,將軍事重心轉回到北邊的曹營。若能慫恿關羽北伐,離開荊州,則是最好的結果。三者,關羽不是傻子,不可能接受孫權提親,他必須拒絕,而且必須高聲拒絕,以對遠方的劉備顯示忠誠,但如此一來,形同羞辱孫權,並激怒東吳朝野。舉國上下敵視關羽,有利於統一輿論,加強國內討回荊州的集體意志。
最終目標只有一個,奪回荊州。
想辦法容易,但說服孫權使用這個辦法卻難。向敵人示好,需要高度的自制與包容,尤其在劉備不但背盟,還讓關羽強硬對待東吳的狀況下,魯肅心知要孫權低聲下氣難度甚高,唯有以策略的角度才能說服這個年輕的君主。
退後是為了向前。
「痛快,」孫權大笑說,「痛快。」
方向既定,在陸口的魯肅,對邊境糾紛一律採取退讓的姿態,在建業的孫權,則派遣使者前往江陵,向關羽提親。而結果不出預料,使者遭關羽辱罵而還。孫權以子配關羽之女,東吳朝野已認為是一種屈就,結果對方不但拒絕,還羞辱我使,是可忍,孰不可忍,魯肅之計果然使得國內群情激憤。
這日,文臣武將齊聚,在孫權面前掀起了討伐關羽的聲浪。孫權在人前表現得憤怒不已,心中則暗喜得計,正待尋思下一步,這時卻收到魯肅自陸口傳來的情報。
劉璋出降,劉備已破成都。
孫權放下書信,轉頭望向諸葛瑾與呂蒙。
建安二十年,荊州益陽
支開了「失言」的軍官以後,關羽收刀拱手,請魯肅入座。魯肅見關羽緊繃著他那張棗紅色的臉,未再多言,便也退了一步,收刀入席,會場氣氛才緩和下來。
此前該軍官之所以會說那番話打斷魯肅發言,是因為魯肅所表述的東吳立場:「當初,曹操大軍攻擊荊州,貴國劉主大敗而落魄南奔,窘迫的狀況可說已是朝不保夕,幸賴東吳伸出援手,在聯手擊退曹軍後,還將荊州出借,以協助盟友得以休養壯大。然而,如今貴國已取得沃野千里的益州,卻不願歸還荊州,我主願退而只求歸還荊州三郡,仍遭拒絕,有借無還,實在說不過去。貴我本同盟之國,攜手只為滅曹,現下鬧到兵戎相見,只怕樂了曹公而已。」
魯肅特別稱曹操為曹公,而不直稱其曹操或曹賊,是因關羽曾受曹操厚遇,是反曹陣營裡罕見與曹操有過君臣之情的人,而曹操在去年進爵為魏公。
關羽雖非文人,並出身寒微,但畢竟也歷經大風大浪,在這種場合也是特別小心用詞,他站在劉備的立場回應魯肅:
「赤壁戰時,我主無一日不身在行伍之間與士卒共飲食,與部隊在站在最前線,就寢時連鞋也不脫,隨時準備應付敵人夜襲。此役我等在荊州也是獨力與曹軍周旋,夙夜匪懈,取勝絕非僥倖,難道只是徒勞一場?我等費盡心力,犧牲士卒,怎能一塊土地也沒有?」
這番說詞該怎麼回應,魯肅早有腹案:
「當年在當陽長阪與劉主一起出入營陳,貴營的總兵員數目,不滿兩千,面對排山倒海的曹軍,拿不出一點辦法,唯有往更遠的地方流竄一途。我主不忍劉主一世之英,卻無寸土容身之所,始終寄人籬下,因而雖贏得半壁荊州,寧可虧待用性命掙來土地的將士,將荊州借與劉主發展。如今貴國既得益州,又要荊州,販夫走卒都不好意思這麼幹,劉主氣量宏遠,如此實為下策。古言貪而棄義,必為禍階,我倆肩負荷國之重任,必須明理以輔佐主上,況且以弱擊強,師出之名又不正,一旦戰事拖延,對貴國百害而無一利。」
關羽欲言又止,沉默了起來。事實上,關羽和魯肅心裡都清楚,今日能有這半面荊州,是因為當年周瑜擋住了曹軍主力,劉備方面才得以趁亂攻下了荊南四個郡。若非周瑜,劉備一點點兵力無濟於事,終歸要灰飛煙滅於曹操南征大軍的鐵蹄下。簡單地說,對東吳而言,劉備只是助攻而已。但對關羽而言,此役之功主要在東吳是事實,但他是武人,武人的觀念是,以自己力量掙來的地盤,當然就是他的,就這麼簡單,不可能接受政治性的權宜看法。因而,關羽辯解得很技巧,明明我們也流血流汗,「怎能一塊土都沒分到呢?」而不是說「荊州都是我們打下來的」。魯肅的答辯則是技巧性迴避荊南四郡的問題,而是將問題追本溯源,「你們當時都要被滅了,若不是我們出手相助,今天哪有你們在這裡鬧事的份兒?」。
關羽在這個問題上比較吃虧是肯定的,因為若不是他面前的魯肅力爭,孫權根本不可能違逆眾意,將荊州借給劉備。而劉備以下所有人,能有個著力之處奮力上跳,其實都拜魯肅之賜,而欠他這個大人情。兩造於會中雖不乏外交辭令,但在關鍵處魯肅能夠直言不諱,便是有此背景之故。再者,對手關羽是武人,面對武人,有話直說反而更好溝通。
魯肅溫言向關羽說,你我身負兩國國運的重任,現下曹公動向未明,我們於此決戰,真的是劉主所樂見的嗎?
關羽別過頭去,並未回應。其實此次兩方兵戎相見,都意在宣示武力,而非真要拼搏出一個荊州歸屬,魯肅此問,便是想從關羽的反應中確認這點,而答案看來正是如此。劉備才拿下益州,人心浮動,百廢待舉,根本不是與東吳攤牌的好時機。
雙方立場已表達清楚,魯肅正要提議散會,彼此按兵不動,並嚴正約束部屬。
「敢問閣下,孫主向關某提親,是何用意?」
關羽冷不防向魯肅提問,眼中滿是敵意。
魯肅並未料到關羽會在這種場合丟出這個問題,心裡打了個突,抬起頭來和關羽四目相交。
「善意。」
魯肅留下兩個字與一抹淡然的笑意,向關羽行了告別禮,率領隨從步出會場。
和親的目的對他而言,確實是為了吳、蜀兩國的關係,只是對關羽而言並非如此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