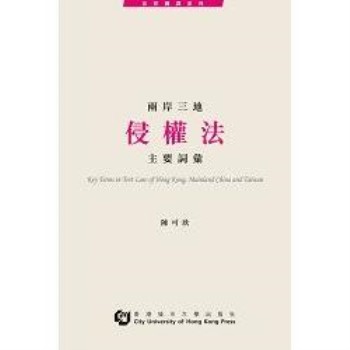在兩岸三地,“tort”一詞均翻譯為「侵權」,意指「違反合約範疇外法律責任所引致之民事錯失」。
其原為法文詞語,源自拉丁詞t orq u e re ,含有「扭曲」(twisted) 之意(薛波,2003:1348; Garner,2009:1626; Heuston and Buckley, 1996:13; Law and Martin,2009:551)。侵權法則實源於刑法,因此不少刑事行為可構成侵權行為,譬如「襲擊」(assault)、「毆打」(battery)(見第三章07“Assault and Battery”)、「永久形式誹謗」(libel)(見第三章06“Defamation”)等。
本文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中國古代侵權觀念及法制之發展,以及其為西法取代之背景。第二部分概述近代兩岸三地吸納西方侵權法之原因,及現代侵權法之功能。第三部分則分析中港台侵權法制度之主要差異。
1. 中國古代侵權法制之興衰
1.1 中國古代侵權法律與侵權行為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古代〔1〕法律系統主要集中於刑事範疇,缺乏民事法律(Chen, 2011:18)。古人觀念中刑、法、律不分(張中秋,2001:80–84)。《爾雅‧釋詁》云:「刑,法也;律,法也。」主宰中國古代法學之法家學說(Legalism),則強調「以吏為師」,使刑法治國家,行權術控臣民(沈家本,1985:2243;張國華,1982:126, 131–133;陳秉才,2007)。至於「民事」之紛爭衝突,則似未受到重視。
究中國古代刑法較民法完善之因,與傳統文化推崇「無訟」有莫大關係。萬世師表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訴訟損害情誼,不利社會。胡石壁於《宋明公書判清明集》(1987:123,引自劉硯冰,2002:139),清晰寫出當時社會對訴訟之負面評價:詞訟之興,初非美事,荒廢本業,破不家財,管吏誅求,卒徒斥辱,道途奔走,稈獄拘囚。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傷鄉黨之誼。幸而獲勝,所損已多;不幸而輸,雖悔何及。
古人懼怕為民事糾紛告上官衙,除了訴訟會帶來情財損失,亦因他們深受「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之觀念影響。國人一直忽視「侵權」概念,亦因傳統以來認為,「權利」與「仁義」對立,頗有貶義(張晉藩,2003:367)。真正規管民間行為之「執法系統」,乃是「人際關係」(guanxi) (Chen,2011:18; Li and Li, 2013:25–26)。「侵權」一詞屬舶來品,至晚清改革時期(公元1908–1911 年)修訂《大清民律草案》時,始引入中國(陳濤、高在敏,1995:48)。儘管中國有上述傳統思想,但自古以來卻有民事侵權律例之史實。據考證,規管民間侵權行為之法典,源於原始社會「同態復仇習俗」(陳濤、高在敏,1995:48)。
商朝時期(約公元前17 世紀– 公元前1122 年)或已有侵權法規。最早之侵權案件記載,見於周朝(公元前1122 年– 公元前256 年)《曶鼎銘》:某年匡(人名)指示其奴隸搶奪曶(人名)十株禾,曶遂訴匡於東宮;東宮其後判匡歸還十株禾予曶,並額外賠償十株禾為懲罰(《曶鼎銘》,引自陳濤、高在敏,1995:48–49)。
此頗有今日懲罰性賠償(exemplary or punitive damages)之作用。然而,當時官府處理侵權行為,主要還是採用刑法制裁而非物質賠償。無論如何,古代中國統治者已有整治侵權行為之概念,只是相關規範準則尚未發展而已(陳濤、高在敏,1995:48–49)。
唐朝(公元618–907 年)在中國古代侵權法制史,具有承上啟下地位(明輝,2010:71;陳濤、高在敏,1995:53)。相較以往各朝法典,唐律侵權規則較有系統規範,侵權種類亦始予細分。譬如,《唐律疏議》第206 條規定:「以犬能噬囓,主須制之,為主不制,故令償減價。『餘畜』,除犬之外,皆是。」(長孫無忌等,1993:285)飼養人須負注意義務,確保其飼養動物不會傷人,與現今兩岸三地「飼養動物責任」之意義相近(見第三章03“Animal’s Liability”)。
唐律一大進步之處,乃其侵權罰則從刑事過渡至民事範疇(張晉藩,2003:368)。《唐律疏議》中多條規定,以物質(金錢)賠償受害方,而不像歷朝只以武力懲罰侵權方,以圖安慰受害方心靈。更重要是唐律制定免責準則,如《唐律疏議》第204 條言明,「其畜產有觝囓人者,若其欲來觝囓人,當即殺傷,不坐、不償。」是則被告能以自救自衛,作為殺傷原告私畜之抗辯理由(長孫無忌等,1993:283–284)。此外,第427 條規定,「諸傳人行船、茹船、寫漏、安標宿止不如法」,即「笞五十」,但若「卒遇風浪者,勿論。」(長孫無忌等,1993:507–508)。此規定類似今西法之「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及「天災」(act of god) 免責理由。由論之,至唐朝時期,中國侵權規範體制已漸見成熟。其後宋(公元960–1279 年)、元(公元1271–1368 年)、明(公元1368–1644 年)、清(公元1644–1911 年)四代,皆以唐律為藍本,稍作修改整理,即成適用於當朝之法典(明輝,2010:77–78;陳濤、高在敏,1995:49)。以損害賠償為例,自盛唐至清末,制度發展逐漸完善,計分五類:(一)盜罪、(二)傷害牲畜之「減價」、(三)水火而致損害、(四)畜產、莊稼,及(五)損毀公私器具(陳濤、高在敏,1995:51)。其中在元朝引入之蒙古風俗「燒埋銀」,明確訂定受害人身故賠償制度,有效填補唐律之不足(《大元聖政朝典章》卷43,1998:1623;明輝,2010:71–76;張群,2002:63)。
該規定在明清時期繼續深化發展(明輝,2010:69–78)〔2〕。
整體而言,中國古代侵權法則已頗具規模,其中有與現代西法相近之處,實遠超乎今人想像。
1.2 中國學習西法之因
今天,兩岸三地侵權法之概念皆源於西方。香港承襲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法學理論取自英國法(England andWales)。內地台灣兩地則採大陸法(continental law,又稱civillaw「民法」),侵權概念可追溯至清末新政法律改革。既然上文提及中國古代侵權法自成一格,且具規模,何以如今三地皆摒棄不用?箇中緣由,實因其有先天之不足,不能適應近代社會經濟環境。清末期間國際環境急劇轉變,則為三地採用西洋法制之近因。1.2.1 遠因—中國傳統侵權法之不足
中國傳統之侵權規範,可謂有三大缺憾。首先,在法學理論層面,中國歷代並無獨立侵權法則,所有法律皆以維護「君權」(sovereign) 為本,服務統治者。漢武帝(公元前157– 公元前87 年)表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儒表法裏」,提倡儒家思想鼓勵人民以「禮」相待,又用法家思想治國,即奉「以法治人」(rule by law) 原則施政,律例旨在擁護君權(李孔懷,2009:138–139)。其後歷朝皆以該原則為治國方針,頒布律例。因此,中國古時並無獨立之民事侵權法則,可謂「刑民不分」,如賠償責任屬「民事附屬刑事」模式(陳濤、高在敏,1995:53;楊竹喧,2008:307–308;羅明舉、李仁真,1989:4)。此堪為古中國民法體制最缺失之處。
第二,過度重視「君權」,令審判程序過於簡化,易生不公。侵權等民事糾紛一般不會引起社會動盪,亦不會對政權造成衝擊。故此,官府處理該類案件,主要實行「一審終審制」,即控辯雙方均無上訴權利(徐振華,2012:8)。從現代角度分析,「一審終審制」非常簡陋粗疏,各種因素如金錢、人情及權力等,容易左右司法公正,予人以侵權行為獲利之誘惑(楊竹喧,2008:308)。而且,中國古代父母官集行政執法權於一身,亦往往未有充足之司法訓練。由此論之,縱使中國古代侵權法制已具規模,實踐而言亦不符合現代法律標準。最後,賠償制度有兩大問題。第一,中國古代侵權律例,對特定民事侵權行為有劃一之賠償標準。譬如明初《大明令‧刑令》規定:「凡殺人償命者,征燒埋銀一十兩。不償者,征銀二十兩。應償命而遇赦原者,亦追二十兩。同謀手下人,驗數均征,給付死者家屬。」(引自明輝,2010:71)即不論死者生前從事職業及生產能力,殺人者皆須賠償死者家屬十兩銀。該類統一規定在古代社會並無不妥,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農抑商,經濟發展單一,人民以務農為主,生產能力相距不大。然而,現代經濟產業多元,生產能力隨知識技能、產業發展環境等而存有巨大差異。因此,法院決定損害賠償金額,理應考慮受害方因侵權事故所受之經濟及精神損失,包括醫療費用、未來收入轉變等因素(Li and Poon, 2013:98–99)。在經濟學層面而論,現代賠償法制能平衡賠償過多及過少之問題,充分照顧到侵權方、受害方,以至整體社會的利益。反之,中國古代劃一賠償規定,顯然不適合現代社會經濟環境。
第二,中國古代賠償制度有一畸型現象:官府制定賠償,須判斷受損物件為官物或私物。換言之,儘管兩件同類物件本身價值及毀損程度相同,物主是私人還是官府,會大為影響侵權方所受之懲罰。若屬官物,侵權方將受較重刑罰。例如,《明律箋釋》規定,「夫遺失、誤毀,在私物則只賠償,在官物則仍坐罪。以過失所當原,而官物則不可誤也。」(引自陳濤、高在敏,1995:54)顯然,此等「君權高於一切」之思想,致使古代侵權律例因襲殘缺,未符現代世界需求。
總括而言,現代社會居住及工作環境愈趨複雜,城市及工業發展等導致人口密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侵權行為自然更多。侵權行為除了帶來直接損失(direct loss),亦帶來間接損失(indirect loss),例如調查事件所產生之開銷、企業形象損失等(Li and Poon, 2013:98)。今日兩岸三地均摒棄舊制,可借用歷史學家黃仁宇(2006:205)之論解釋原因: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黃氏認為,中國法制在明朝萬曆年間(公元1573–1620 年)已經落後,嚴重限制國家發展。然而滿清入關以後,仍因循舊制,對其陳腐之況一無所知,及至清末才着手改革。可以說,此番改革足足遲來了三百年!
1.2.2 近因—國際環境轉變
今日中港台俱採用西方法制,與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之國際環境變化,有莫大關係。香港因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公元1842 年)而成為英國殖民地,承襲英制奉行普通法。即使其於1997 年回歸中國,仍沿用英制,並無改行內地大陸法制。至於內地及台灣採西法之緣由,則可追溯至清朝末年。中國自明朝以來緊閉之門戶,隨着兩次「鴉片戰爭」〔3〕被西方帝國主義強行打開,有識之士始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知識,取長補短,力求重回世界強國之列。其後清廷展開「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公元1861–1895 年),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要學習西方工業技術,卻排斥西方制度文明,對西法之認識,僅限於規管國家行為之《萬國律例》(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呂理州,2007:234–235; Teng and Fairbank,1982:98, 142)。隨着清廷於甲午戰爭(公元1894–1895 年)慘敗,中國領導階層及部分社會名流開始意識到,興辦洋務學習西方技術而不改革制度,其所帶來之所謂「中興」( restorat ion) 不過是「迴光返照」,而非「小陽春」( Indian Summer)(徐中約,2001:261–262; Hsu, 2008:262)。
「八國聯軍之役」(公元1900–1901 年)後,滿清政府與知識分子終於意會到列強成功之一大基石,在於「公正不偏」之法律觀念(impartial justice)(徐中約,2008:425–428)。另一方面,近代中國經濟逐漸發展,人民流動性日漸增加,原來約束民間行為之「人際關係」亦逐漸失去效用(陳可欣,2014:4;Li and Li, 2013:25–26)。故此,清政府終為輿論及現實所逼,在晚清改革(Late Qing Reform,公元1908–1911 年)期間,正式將法律改革列入議程,全面引進西方法律制度,取代舊制。此即為中國沿用西方侵權法則之始。現代不少學者認為,西方在八國聯軍之役後的對華態度,亦為中國引進西法之重要原因。在該戰役期間,沙俄進駐中國東三省,企圖在該地建立「布哈拉」(Bukhara,意指「沙俄殖民地前進基地」),令西方列強愈發擔憂俄國會吞併中國,各國間亦因貿易、結盟、軍備競賽、殖民地爭奪及巴爾幹半島(The Balkans) 等問題,日益相互猜忌及競爭(Thomson, 1990:457–544)。為此,列強逐漸達成共識,認同與其瓜分中國,倒不如用西方思想扶植親西方之中國政權,以維持其「半殖民地」狀態(徐中約,2008:402–404)。所謂「半殖民地」,可體現於中國給予西方列強「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4〕,因而喪失以本國法律審理涉外案件之權利。
英美等國於公元1902 年,許諾中國以司法改良換取列強放棄在華「治外法權」,更見西方有意以思想改造中國。可以說,中國近代採用西方法制,與列強提供之利益誘因關係殊深(蔡曉榮,2009:100)。由此推論,近世國際政治環境急劇轉變,加速中國吸收西方侵權法則,以補自身之不足。
其原為法文詞語,源自拉丁詞t orq u e re ,含有「扭曲」(twisted) 之意(薛波,2003:1348; Garner,2009:1626; Heuston and Buckley, 1996:13; Law and Martin,2009:551)。侵權法則實源於刑法,因此不少刑事行為可構成侵權行為,譬如「襲擊」(assault)、「毆打」(battery)(見第三章07“Assault and Battery”)、「永久形式誹謗」(libel)(見第三章06“Defamation”)等。
本文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中國古代侵權觀念及法制之發展,以及其為西法取代之背景。第二部分概述近代兩岸三地吸納西方侵權法之原因,及現代侵權法之功能。第三部分則分析中港台侵權法制度之主要差異。
1. 中國古代侵權法制之興衰
1.1 中國古代侵權法律與侵權行為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古代〔1〕法律系統主要集中於刑事範疇,缺乏民事法律(Chen, 2011:18)。古人觀念中刑、法、律不分(張中秋,2001:80–84)。《爾雅‧釋詁》云:「刑,法也;律,法也。」主宰中國古代法學之法家學說(Legalism),則強調「以吏為師」,使刑法治國家,行權術控臣民(沈家本,1985:2243;張國華,1982:126, 131–133;陳秉才,2007)。至於「民事」之紛爭衝突,則似未受到重視。
究中國古代刑法較民法完善之因,與傳統文化推崇「無訟」有莫大關係。萬世師表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訴訟損害情誼,不利社會。胡石壁於《宋明公書判清明集》(1987:123,引自劉硯冰,2002:139),清晰寫出當時社會對訴訟之負面評價:詞訟之興,初非美事,荒廢本業,破不家財,管吏誅求,卒徒斥辱,道途奔走,稈獄拘囚。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傷鄉黨之誼。幸而獲勝,所損已多;不幸而輸,雖悔何及。
古人懼怕為民事糾紛告上官衙,除了訴訟會帶來情財損失,亦因他們深受「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之觀念影響。國人一直忽視「侵權」概念,亦因傳統以來認為,「權利」與「仁義」對立,頗有貶義(張晉藩,2003:367)。真正規管民間行為之「執法系統」,乃是「人際關係」(guanxi) (Chen,2011:18; Li and Li, 2013:25–26)。「侵權」一詞屬舶來品,至晚清改革時期(公元1908–1911 年)修訂《大清民律草案》時,始引入中國(陳濤、高在敏,1995:48)。儘管中國有上述傳統思想,但自古以來卻有民事侵權律例之史實。據考證,規管民間侵權行為之法典,源於原始社會「同態復仇習俗」(陳濤、高在敏,1995:48)。
商朝時期(約公元前17 世紀– 公元前1122 年)或已有侵權法規。最早之侵權案件記載,見於周朝(公元前1122 年– 公元前256 年)《曶鼎銘》:某年匡(人名)指示其奴隸搶奪曶(人名)十株禾,曶遂訴匡於東宮;東宮其後判匡歸還十株禾予曶,並額外賠償十株禾為懲罰(《曶鼎銘》,引自陳濤、高在敏,1995:48–49)。
此頗有今日懲罰性賠償(exemplary or punitive damages)之作用。然而,當時官府處理侵權行為,主要還是採用刑法制裁而非物質賠償。無論如何,古代中國統治者已有整治侵權行為之概念,只是相關規範準則尚未發展而已(陳濤、高在敏,1995:48–49)。
唐朝(公元618–907 年)在中國古代侵權法制史,具有承上啟下地位(明輝,2010:71;陳濤、高在敏,1995:53)。相較以往各朝法典,唐律侵權規則較有系統規範,侵權種類亦始予細分。譬如,《唐律疏議》第206 條規定:「以犬能噬囓,主須制之,為主不制,故令償減價。『餘畜』,除犬之外,皆是。」(長孫無忌等,1993:285)飼養人須負注意義務,確保其飼養動物不會傷人,與現今兩岸三地「飼養動物責任」之意義相近(見第三章03“Animal’s Liability”)。
唐律一大進步之處,乃其侵權罰則從刑事過渡至民事範疇(張晉藩,2003:368)。《唐律疏議》中多條規定,以物質(金錢)賠償受害方,而不像歷朝只以武力懲罰侵權方,以圖安慰受害方心靈。更重要是唐律制定免責準則,如《唐律疏議》第204 條言明,「其畜產有觝囓人者,若其欲來觝囓人,當即殺傷,不坐、不償。」是則被告能以自救自衛,作為殺傷原告私畜之抗辯理由(長孫無忌等,1993:283–284)。此外,第427 條規定,「諸傳人行船、茹船、寫漏、安標宿止不如法」,即「笞五十」,但若「卒遇風浪者,勿論。」(長孫無忌等,1993:507–508)。此規定類似今西法之「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及「天災」(act of god) 免責理由。由論之,至唐朝時期,中國侵權規範體制已漸見成熟。其後宋(公元960–1279 年)、元(公元1271–1368 年)、明(公元1368–1644 年)、清(公元1644–1911 年)四代,皆以唐律為藍本,稍作修改整理,即成適用於當朝之法典(明輝,2010:77–78;陳濤、高在敏,1995:49)。以損害賠償為例,自盛唐至清末,制度發展逐漸完善,計分五類:(一)盜罪、(二)傷害牲畜之「減價」、(三)水火而致損害、(四)畜產、莊稼,及(五)損毀公私器具(陳濤、高在敏,1995:51)。其中在元朝引入之蒙古風俗「燒埋銀」,明確訂定受害人身故賠償制度,有效填補唐律之不足(《大元聖政朝典章》卷43,1998:1623;明輝,2010:71–76;張群,2002:63)。
該規定在明清時期繼續深化發展(明輝,2010:69–78)〔2〕。
整體而言,中國古代侵權法則已頗具規模,其中有與現代西法相近之處,實遠超乎今人想像。
1.2 中國學習西法之因
今天,兩岸三地侵權法之概念皆源於西方。香港承襲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法學理論取自英國法(England andWales)。內地台灣兩地則採大陸法(continental law,又稱civillaw「民法」),侵權概念可追溯至清末新政法律改革。既然上文提及中國古代侵權法自成一格,且具規模,何以如今三地皆摒棄不用?箇中緣由,實因其有先天之不足,不能適應近代社會經濟環境。清末期間國際環境急劇轉變,則為三地採用西洋法制之近因。1.2.1 遠因—中國傳統侵權法之不足
中國傳統之侵權規範,可謂有三大缺憾。首先,在法學理論層面,中國歷代並無獨立侵權法則,所有法律皆以維護「君權」(sovereign) 為本,服務統治者。漢武帝(公元前157– 公元前87 年)表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儒表法裏」,提倡儒家思想鼓勵人民以「禮」相待,又用法家思想治國,即奉「以法治人」(rule by law) 原則施政,律例旨在擁護君權(李孔懷,2009:138–139)。其後歷朝皆以該原則為治國方針,頒布律例。因此,中國古時並無獨立之民事侵權法則,可謂「刑民不分」,如賠償責任屬「民事附屬刑事」模式(陳濤、高在敏,1995:53;楊竹喧,2008:307–308;羅明舉、李仁真,1989:4)。此堪為古中國民法體制最缺失之處。
第二,過度重視「君權」,令審判程序過於簡化,易生不公。侵權等民事糾紛一般不會引起社會動盪,亦不會對政權造成衝擊。故此,官府處理該類案件,主要實行「一審終審制」,即控辯雙方均無上訴權利(徐振華,2012:8)。從現代角度分析,「一審終審制」非常簡陋粗疏,各種因素如金錢、人情及權力等,容易左右司法公正,予人以侵權行為獲利之誘惑(楊竹喧,2008:308)。而且,中國古代父母官集行政執法權於一身,亦往往未有充足之司法訓練。由此論之,縱使中國古代侵權法制已具規模,實踐而言亦不符合現代法律標準。最後,賠償制度有兩大問題。第一,中國古代侵權律例,對特定民事侵權行為有劃一之賠償標準。譬如明初《大明令‧刑令》規定:「凡殺人償命者,征燒埋銀一十兩。不償者,征銀二十兩。應償命而遇赦原者,亦追二十兩。同謀手下人,驗數均征,給付死者家屬。」(引自明輝,2010:71)即不論死者生前從事職業及生產能力,殺人者皆須賠償死者家屬十兩銀。該類統一規定在古代社會並無不妥,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農抑商,經濟發展單一,人民以務農為主,生產能力相距不大。然而,現代經濟產業多元,生產能力隨知識技能、產業發展環境等而存有巨大差異。因此,法院決定損害賠償金額,理應考慮受害方因侵權事故所受之經濟及精神損失,包括醫療費用、未來收入轉變等因素(Li and Poon, 2013:98–99)。在經濟學層面而論,現代賠償法制能平衡賠償過多及過少之問題,充分照顧到侵權方、受害方,以至整體社會的利益。反之,中國古代劃一賠償規定,顯然不適合現代社會經濟環境。
第二,中國古代賠償制度有一畸型現象:官府制定賠償,須判斷受損物件為官物或私物。換言之,儘管兩件同類物件本身價值及毀損程度相同,物主是私人還是官府,會大為影響侵權方所受之懲罰。若屬官物,侵權方將受較重刑罰。例如,《明律箋釋》規定,「夫遺失、誤毀,在私物則只賠償,在官物則仍坐罪。以過失所當原,而官物則不可誤也。」(引自陳濤、高在敏,1995:54)顯然,此等「君權高於一切」之思想,致使古代侵權律例因襲殘缺,未符現代世界需求。
總括而言,現代社會居住及工作環境愈趨複雜,城市及工業發展等導致人口密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侵權行為自然更多。侵權行為除了帶來直接損失(direct loss),亦帶來間接損失(indirect loss),例如調查事件所產生之開銷、企業形象損失等(Li and Poon, 2013:98)。今日兩岸三地均摒棄舊制,可借用歷史學家黃仁宇(2006:205)之論解釋原因: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黃氏認為,中國法制在明朝萬曆年間(公元1573–1620 年)已經落後,嚴重限制國家發展。然而滿清入關以後,仍因循舊制,對其陳腐之況一無所知,及至清末才着手改革。可以說,此番改革足足遲來了三百年!
1.2.2 近因—國際環境轉變
今日中港台俱採用西方法制,與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之國際環境變化,有莫大關係。香港因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公元1842 年)而成為英國殖民地,承襲英制奉行普通法。即使其於1997 年回歸中國,仍沿用英制,並無改行內地大陸法制。至於內地及台灣採西法之緣由,則可追溯至清朝末年。中國自明朝以來緊閉之門戶,隨着兩次「鴉片戰爭」〔3〕被西方帝國主義強行打開,有識之士始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知識,取長補短,力求重回世界強國之列。其後清廷展開「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公元1861–1895 年),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要學習西方工業技術,卻排斥西方制度文明,對西法之認識,僅限於規管國家行為之《萬國律例》(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呂理州,2007:234–235; Teng and Fairbank,1982:98, 142)。隨着清廷於甲午戰爭(公元1894–1895 年)慘敗,中國領導階層及部分社會名流開始意識到,興辦洋務學習西方技術而不改革制度,其所帶來之所謂「中興」( restorat ion) 不過是「迴光返照」,而非「小陽春」( Indian Summer)(徐中約,2001:261–262; Hsu, 2008:262)。
「八國聯軍之役」(公元1900–1901 年)後,滿清政府與知識分子終於意會到列強成功之一大基石,在於「公正不偏」之法律觀念(impartial justice)(徐中約,2008:425–428)。另一方面,近代中國經濟逐漸發展,人民流動性日漸增加,原來約束民間行為之「人際關係」亦逐漸失去效用(陳可欣,2014:4;Li and Li, 2013:25–26)。故此,清政府終為輿論及現實所逼,在晚清改革(Late Qing Reform,公元1908–1911 年)期間,正式將法律改革列入議程,全面引進西方法律制度,取代舊制。此即為中國沿用西方侵權法則之始。現代不少學者認為,西方在八國聯軍之役後的對華態度,亦為中國引進西法之重要原因。在該戰役期間,沙俄進駐中國東三省,企圖在該地建立「布哈拉」(Bukhara,意指「沙俄殖民地前進基地」),令西方列強愈發擔憂俄國會吞併中國,各國間亦因貿易、結盟、軍備競賽、殖民地爭奪及巴爾幹半島(The Balkans) 等問題,日益相互猜忌及競爭(Thomson, 1990:457–544)。為此,列強逐漸達成共識,認同與其瓜分中國,倒不如用西方思想扶植親西方之中國政權,以維持其「半殖民地」狀態(徐中約,2008:402–404)。所謂「半殖民地」,可體現於中國給予西方列強「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4〕,因而喪失以本國法律審理涉外案件之權利。
英美等國於公元1902 年,許諾中國以司法改良換取列強放棄在華「治外法權」,更見西方有意以思想改造中國。可以說,中國近代採用西方法制,與列強提供之利益誘因關係殊深(蔡曉榮,2009:100)。由此推論,近世國際政治環境急劇轉變,加速中國吸收西方侵權法則,以補自身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