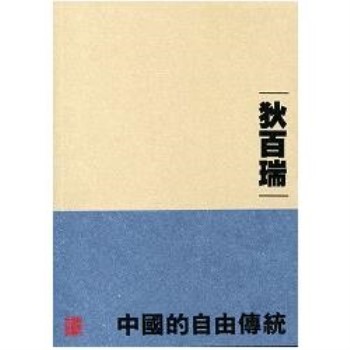第一講 人之更新與道統
一般的新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學」,是在北宋(960-1127)的偉大改革運動中興起的。在政治上,這些改革運動在王安石(1021-1086)決心推行「新法」(或新制、新政)的努力中達到了高潮。但是,此處的關鍵是「新」這個字,因為「新」似乎與宋代那種顯著的復古主義理想所表現的傳統相扞格,也就是説與那種認為應恢復古周制,於十一世紀的宋代實行的想法相衝突。但是事實上,這裏所表現的是因襲與革新齊頭並進,而非背道而馳。王安石之所以援引儒家經典,特別是《周官》來作為他激進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因為這種形態的傳統提供了他攻擊現存制度的有力理由,而不是因為他的新制與《周官》書中相傳的典範有任何近似之處。
王安石感到必須替《周官》寫一本新的注解,並稱之為《周官新義》。這個書名頗有啟示性,正證明了當時人是努力於將傳統拿來作創新的運用。對經典的再詮釋援引了新的批評方法,以新的經學主張來為改革的目標效勞。因此,「復古」的主張恢復了,而三代的「聖王之道」也在實踐中變成新的可行之道。
王安石在追求他的目標時,雖因其所採用的權威式的做法與獨斷的態度而為人詬病,但是王安石深信從古制中可以尋獲新制的基礎,這一點在他同時代的大儒中則並非特例。例如哲學家程頤便曾用近似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詞彙,説在他們那個時代,需要大改革以興「大制」或「大利」,1其語氣之堅定稍不遑王安石。程頤在政治上舆王安石水火不容,但在引經據典以證明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權威性這一點上,他與王安石一樣地獨斷。這種情形對王安石和程頤而言,都是很可能發生的,因為他們都認為「道」並非僵死於過去,反而對人類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與適應性。
宋代儒學中鼓舞這種想法的一個支派,就是對《易經》的研究。《易經》的繋辭傳特別強調「道」具有生生不已的活力與創造性。對道學早期的大師程頤而言,這個觀念正好與佛教以「變」為無常、以「道」為了脱生死輪迴的看法構成對比。《易經》書中所呈現的儒家形上學對於道提供了一個正面的看法,認為「道」永遠可為人類所理解,也永遠能適應一般人的需要。因此,在程頤的新古典主義思想中,再現與再生乃成為重要價值。真理可以直接從經典中找到,而且當下可以應用到人生的再生之上。程頤很有自覺地説,大學之道「在新民」。程頤以「新民」取代古本的「親民」。2朱子在《大學章句》裏,十分強調「自新」這個觀念,認為它是更廣大的人群之再生之基礎。接著,元明兩代早期新儒學運動的動力就深深地植根於這個觀念上,因為這項社會新生的希望,正是建立在朱子對於人的道德性與個人完美性的新詮釋之上。3
如果我們把歷史的「進步」觀當作是朝向某種更新階段的直線發展的話,我們便不能認為以上所説的強調再新或革新的説法一定是一種歷史「進步」觀。它的「新」正如新年或春季的再生,這種再生也許包涵了演化的過程,但是它不一定就非有演化不可。我們也不可以把這裏所説的「活力」(生)或「創造性」(新)理解成西方的「原創性」(originality)一樣帶有西方人所重視的極端獨特性的意味。「生」(活力)或「新」(創造性)是建構在對人性之相同的強烈信念之上的,因此程頤的「新民」是以人類所共有的仁道為其立論之基礎。
不過當程頤在論及人之修道時,他頗承認某些人物曾作出突出的個別貢獻。誠然,如果不是由於少數這種人物的慧識與獨立的努力,聖人之道可能已經完全絕滅了。這些少數人物當然包括孔子、孟子。但是,程頤認為在孟子之後,道之不行也久矣,直到其兄程顥「生千四百年之後……,志將以斯道覺斯民」、「謂孟子歿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4
後來,朱子撰《中庸》序,也以同樣的説法來解釋道統的性質。在敘述了自聖王以下道統如何傳承之後,道: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歿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説,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千載不傳之緒。從上引文字看來,作者所強調的並不是經由不絕如縷的先知或主教人物之傳承而維繁道統於不墜;而是,第一、道統曾間斷頗久;第二、道統由具有異稟的人重新發現;第三、在衰敗的時代中,捍衛道統須有英雄式的獻身行動。內在的激勵與個人的奉獻是拯救道統於湮滅之際的英雄式人物的特徵。6
朱子之後,道學的領袖人物為真德秀(1178-1235)。他繼續發揚有宋一代復興道學的儒者所共有的資質;但卻不強調他們那種特異的(幾乎是超自然的)稟賦。真德秀説:「必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他談到周敦頤、二程及朱子的慧識時,説:「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説,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7
真德秀在〈明道先生書堂記〉中,以相近的文字稱許明道先生重現「天理」之道。他説,孟子之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而「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發幽微,益明益章。」又説:「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8真德秀在另一篇紀念文字中,則更細膩地說明之不可思議的創造性:「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9
在《道學與心學》(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一書中,我曾說上述的這種觀念是道學思想中的「先知式的」(prophetic)成分。我的意思是指:通往真理的特殊途徑並非人人可得,這條途徑乃由內在的靈感或獨特的認知而取得,而非由經典所提供;它又訴諸更高層次的真理來對某些文化價值或經典文獻賦予新的解釋、意義與重要性。儒家傳統一般不認為這種啟示是「超自然的」,但是它確有一種不可預測、不可思議足以印證天的神聖非凡的創造性之稟性。但比諸「先知式的」,則我寧可說訴諸由歷代相承所形成的權威乃是「學術式的」(scholastic)。它之所以能為人接受,認為正確有效,乃是因為它強調必須有外在或群眾的接受作為基礎。10
儒家與猶太世界那種較具神學色彩的傳統,其背景當然有很明顯的差別。在猶太世界中,先知説「神的道高過人的道」,神以恐怖的結局來要求人服從,並以此來審判人的行為。然而這種差異不應該使我們看不到新儒家道德觀中的內在取向性;也不應該使我們看不見天是如何影響人的良心,使人在理想層次與實際境遇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緊張關係──亦即是指天如何對人的境況能有控制的能力,這一點是韋伯派學者(Weberian)對儒家思想的分析所未及討論的。
「先知式的」與「學術式的」這兩種對比的態度,也許也可以用來説明新儒家思想中自由的與保守的兩種傾向。我們在此必須小心,以免太輕率地在兩者之間劃上等號。東西兩方的「先知的」態度都對現存制度作激烈批判,或對社會的放縱作出返本主義(fundamentalist)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追求中庸之道的儒家自由主義(中庸之道可以與佛蘭克所説的「由中庸、自制或妥協所表現出來的自由性格或風格」相應),將會轉而求之於學術傳統中的練達智慧,拿文獻記載或正式制度中所呈現的集體經驗來衡量自己良心的激切呼唤。
雖説我承認這兩種傾向會互相抵銷,我還是要指出:道統這個觀念在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家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新儒家思想的正統傳統而言,實居中心地位。改革派及其反對派都一再寄望於英雄人物的再顯道統、印證道統。每個時代幾乎都可以找到顯著的例子,如宋末的真德秀,元代的許衡、劉因、吳澄,明代的吳與弼、陳獻章、何心隱及林兆恩。我們在此以最為人所知的王陽明為例來作説明。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陽明弟子王棟(1503-1581)如此説道:
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遣經者起為經師,更相授受於此。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矣。11
這段文字雖然略帶王陽明學派某種社會及哲學的色彩,但我們在此又看到了稟賦特異的個人,扮演著神秘的角色,重振道統、再新人類。王陽明所扮演的就是這種典型。有些批評者可能懷疑王陽明是否夠稱為儒學的正統,也有人可能會在學術的持續重要性上反對王陽明,但是陽明為道所作的詮釋究竟還是用了正統而流行的話語,認為他説的仍不外是「道統」及「新民」。
幾乎所有重要的新儒家都適合這種説法。在元明兩代,這些有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一再地出現於各色各樣新儒家著作之中。這項事實正説明了這些典型人物是傳統能夠再生的有力象徵;傳統又隨之不斷地迫使正統的領域向外伸展。
一般的新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學」,是在北宋(960-1127)的偉大改革運動中興起的。在政治上,這些改革運動在王安石(1021-1086)決心推行「新法」(或新制、新政)的努力中達到了高潮。但是,此處的關鍵是「新」這個字,因為「新」似乎與宋代那種顯著的復古主義理想所表現的傳統相扞格,也就是説與那種認為應恢復古周制,於十一世紀的宋代實行的想法相衝突。但是事實上,這裏所表現的是因襲與革新齊頭並進,而非背道而馳。王安石之所以援引儒家經典,特別是《周官》來作為他激進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因為這種形態的傳統提供了他攻擊現存制度的有力理由,而不是因為他的新制與《周官》書中相傳的典範有任何近似之處。
王安石感到必須替《周官》寫一本新的注解,並稱之為《周官新義》。這個書名頗有啟示性,正證明了當時人是努力於將傳統拿來作創新的運用。對經典的再詮釋援引了新的批評方法,以新的經學主張來為改革的目標效勞。因此,「復古」的主張恢復了,而三代的「聖王之道」也在實踐中變成新的可行之道。
王安石在追求他的目標時,雖因其所採用的權威式的做法與獨斷的態度而為人詬病,但是王安石深信從古制中可以尋獲新制的基礎,這一點在他同時代的大儒中則並非特例。例如哲學家程頤便曾用近似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詞彙,説在他們那個時代,需要大改革以興「大制」或「大利」,1其語氣之堅定稍不遑王安石。程頤在政治上舆王安石水火不容,但在引經據典以證明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權威性這一點上,他與王安石一樣地獨斷。這種情形對王安石和程頤而言,都是很可能發生的,因為他們都認為「道」並非僵死於過去,反而對人類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與適應性。
宋代儒學中鼓舞這種想法的一個支派,就是對《易經》的研究。《易經》的繋辭傳特別強調「道」具有生生不已的活力與創造性。對道學早期的大師程頤而言,這個觀念正好與佛教以「變」為無常、以「道」為了脱生死輪迴的看法構成對比。《易經》書中所呈現的儒家形上學對於道提供了一個正面的看法,認為「道」永遠可為人類所理解,也永遠能適應一般人的需要。因此,在程頤的新古典主義思想中,再現與再生乃成為重要價值。真理可以直接從經典中找到,而且當下可以應用到人生的再生之上。程頤很有自覺地説,大學之道「在新民」。程頤以「新民」取代古本的「親民」。2朱子在《大學章句》裏,十分強調「自新」這個觀念,認為它是更廣大的人群之再生之基礎。接著,元明兩代早期新儒學運動的動力就深深地植根於這個觀念上,因為這項社會新生的希望,正是建立在朱子對於人的道德性與個人完美性的新詮釋之上。3
如果我們把歷史的「進步」觀當作是朝向某種更新階段的直線發展的話,我們便不能認為以上所説的強調再新或革新的説法一定是一種歷史「進步」觀。它的「新」正如新年或春季的再生,這種再生也許包涵了演化的過程,但是它不一定就非有演化不可。我們也不可以把這裏所説的「活力」(生)或「創造性」(新)理解成西方的「原創性」(originality)一樣帶有西方人所重視的極端獨特性的意味。「生」(活力)或「新」(創造性)是建構在對人性之相同的強烈信念之上的,因此程頤的「新民」是以人類所共有的仁道為其立論之基礎。
不過當程頤在論及人之修道時,他頗承認某些人物曾作出突出的個別貢獻。誠然,如果不是由於少數這種人物的慧識與獨立的努力,聖人之道可能已經完全絕滅了。這些少數人物當然包括孔子、孟子。但是,程頤認為在孟子之後,道之不行也久矣,直到其兄程顥「生千四百年之後……,志將以斯道覺斯民」、「謂孟子歿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4
後來,朱子撰《中庸》序,也以同樣的説法來解釋道統的性質。在敘述了自聖王以下道統如何傳承之後,道: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歿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説,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千載不傳之緒。從上引文字看來,作者所強調的並不是經由不絕如縷的先知或主教人物之傳承而維繁道統於不墜;而是,第一、道統曾間斷頗久;第二、道統由具有異稟的人重新發現;第三、在衰敗的時代中,捍衛道統須有英雄式的獻身行動。內在的激勵與個人的奉獻是拯救道統於湮滅之際的英雄式人物的特徵。6
朱子之後,道學的領袖人物為真德秀(1178-1235)。他繼續發揚有宋一代復興道學的儒者所共有的資質;但卻不強調他們那種特異的(幾乎是超自然的)稟賦。真德秀説:「必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他談到周敦頤、二程及朱子的慧識時,説:「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説,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7
真德秀在〈明道先生書堂記〉中,以相近的文字稱許明道先生重現「天理」之道。他説,孟子之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而「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發幽微,益明益章。」又説:「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8真德秀在另一篇紀念文字中,則更細膩地說明之不可思議的創造性:「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9
在《道學與心學》(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一書中,我曾說上述的這種觀念是道學思想中的「先知式的」(prophetic)成分。我的意思是指:通往真理的特殊途徑並非人人可得,這條途徑乃由內在的靈感或獨特的認知而取得,而非由經典所提供;它又訴諸更高層次的真理來對某些文化價值或經典文獻賦予新的解釋、意義與重要性。儒家傳統一般不認為這種啟示是「超自然的」,但是它確有一種不可預測、不可思議足以印證天的神聖非凡的創造性之稟性。但比諸「先知式的」,則我寧可說訴諸由歷代相承所形成的權威乃是「學術式的」(scholastic)。它之所以能為人接受,認為正確有效,乃是因為它強調必須有外在或群眾的接受作為基礎。10
儒家與猶太世界那種較具神學色彩的傳統,其背景當然有很明顯的差別。在猶太世界中,先知説「神的道高過人的道」,神以恐怖的結局來要求人服從,並以此來審判人的行為。然而這種差異不應該使我們看不到新儒家道德觀中的內在取向性;也不應該使我們看不見天是如何影響人的良心,使人在理想層次與實際境遇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緊張關係──亦即是指天如何對人的境況能有控制的能力,這一點是韋伯派學者(Weberian)對儒家思想的分析所未及討論的。
「先知式的」與「學術式的」這兩種對比的態度,也許也可以用來説明新儒家思想中自由的與保守的兩種傾向。我們在此必須小心,以免太輕率地在兩者之間劃上等號。東西兩方的「先知的」態度都對現存制度作激烈批判,或對社會的放縱作出返本主義(fundamentalist)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追求中庸之道的儒家自由主義(中庸之道可以與佛蘭克所説的「由中庸、自制或妥協所表現出來的自由性格或風格」相應),將會轉而求之於學術傳統中的練達智慧,拿文獻記載或正式制度中所呈現的集體經驗來衡量自己良心的激切呼唤。
雖説我承認這兩種傾向會互相抵銷,我還是要指出:道統這個觀念在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家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新儒家思想的正統傳統而言,實居中心地位。改革派及其反對派都一再寄望於英雄人物的再顯道統、印證道統。每個時代幾乎都可以找到顯著的例子,如宋末的真德秀,元代的許衡、劉因、吳澄,明代的吳與弼、陳獻章、何心隱及林兆恩。我們在此以最為人所知的王陽明為例來作説明。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陽明弟子王棟(1503-1581)如此説道:
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遣經者起為經師,更相授受於此。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矣。11
這段文字雖然略帶王陽明學派某種社會及哲學的色彩,但我們在此又看到了稟賦特異的個人,扮演著神秘的角色,重振道統、再新人類。王陽明所扮演的就是這種典型。有些批評者可能懷疑王陽明是否夠稱為儒學的正統,也有人可能會在學術的持續重要性上反對王陽明,但是陽明為道所作的詮釋究竟還是用了正統而流行的話語,認為他説的仍不外是「道統」及「新民」。
幾乎所有重要的新儒家都適合這種説法。在元明兩代,這些有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一再地出現於各色各樣新儒家著作之中。這項事實正説明了這些典型人物是傳統能夠再生的有力象徵;傳統又隨之不斷地迫使正統的領域向外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