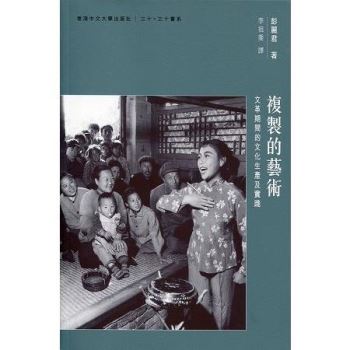秩序與失序
如果現代的歐洲藝術靠詩和藝術去觸及秩序世界的背後,毛式藝術的任務卻是相反,是要去建構秩序。毛式藝術的責任,是要在一個高度散亂的政治現實中,提供一些情感和美學上的碇泊處(affective aesthetic anchorages),建構一個相對於政治混戰來說比較連貫的存在領域。毛式藝術試圖為人們提供一個安穩的象徵,讓人確信萬物的背後存在一個超越性的結構。如果法國大革命是打造出歐洲浪漫主義的催化劑,所回應的是人們對啟蒙理性的幻滅;那麼,毛式浪漫主義則要呈現一種「準理性」(quasi-reason),作為一種可以合理解釋現實生活為何如此混亂的想像力。可以說,高度不穩定的政治環境,是文革藝術充滿力量的原因,因為它們有助把分散的政治能量拉在一起。
毛式浪漫主義有其超現實主義的面向。即是說,這種美學能夠超越物質性的現實。例如,在電影《紅色娘子軍》原版本的處決一幕中,我們看到男主角洪常青在飽受折磨後,拖著滿身傷痕的身體就義。但是,在樣板芭蕾舞劇中,江青要求製作團隊把他刻劃成強壯有力,給他安排一些充滿力量的舞蹈,如同一隻準備一飛衝天的鷹。19我們看到一個超現實的洪常青,面對死亡仍然充滿力量和勇氣、不屈不撓,展示出強大的毛澤東精神。這種安排,肯定會使那些稱許《聖女貞德蒙難記》(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1928年由德萊葉[Carl-Theodor Dreyer]執導)的西方觀眾感到煩厭。不過,《紅色娘子軍》卻是在當時被確認為既「現實」又「浪漫」的新中國模範作品。我們可以說,刻劃洪常青的整體的情感強度違反常理。但是,不屈不撓的英雄和壯觀的美學,可以為迷失方向的社會提供一層額外的現實,使人在其中找到慰藉。如果說,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1964年到1979年是最變化無常的一段時期;那麼,宣傳文化中所展示的浪漫氛圍,則穩定和持久得多了。
不過,不論毛式浪漫主義有多穩定,藝術所帶來的強烈想像力,也難免會使人越界,讓平民百姓探索日常之外的世界。在毛式藝術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秩序和失序之間的巨大張力。不論毛式浪漫主義有多偏離歐洲浪漫主義,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這觀念,畢竟是因為他相信想像力可以提供全新的視野,而他也希望鼓勵人民去探索陌生和難以預知的領域。說到底,這正正是大躍進和文革背後的精神。文革的浪漫,確實是無法徹底表達真正超越的震撼和感動,因為真正的浪漫有可能直接威脅革命的獨一性和權威。但是,浪漫主義可以加深個體跟歷史和人民的關係,讓人看到自己的種種可能。恰恰是主動投入集體,個體才得以感受到無拘無束的自由。歐洲浪漫主義提供新的方法,去想像和連結語言和自然;相比之下,毛式藝術則著重人民的超越性統一(transcendental unity)。
讓我舉一個例子。於文革時期,陳益南是一個在長沙市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和派系鬥爭的工人。按他憶述,在1967年2月、3月期間,各派佔領長沙市的街道以表達政見,非常刺激。20在當時,大型武鬥尚未成為主流,各方仍然以宣傳活動去爭取支持。兩個鬥爭的派別,由高師(主要由大學生組成)和湘江風雷(主要由工廠工人組成)主導。高師的教育程度比較高,更懂得寫大字報和演講。但有趣的是,即使高師在宣傳活動中較有優勢(而且在後來得到黨中央的支持),工人卻會在晚上佔據街道,反佔上風。在晚上,大部分工人下班,就會把平常的餘暇用來參與政治活動。那些在白天被精英學生排擠的人,到了晚上便活躍起來。一些工人裝飾自己的宣傳車,裝上麥克風和擴音器,巡迴全市宣傳政治訴求。其他人則在街上聚集唱歌,躺在街上,阻止敵對派系的宣傳車靠近自己的宣傳車。陳益南回憶時說:
用骨肉之軀阻止了對方隆隆車輛的進攻;
以不畏死的決心保衛了我們造反派的聲音;
當時,我覺得自己很有點「英雄」的味兒,也感到了悲壯的衝動。
白天,大學生藉秀麗的書法和觸目的畫作引人注目;到了晚上,則是唱歌和叫陣的時間。在這些視覺與聲音的戰鬥之中,我們可見美學能夠產生迷人的力量。不同感官之間的競賽,為革命賦予動力。
藝術被用作毛主義者的工具,固然十分明顯。但一不小心,這種美學性的力量便會失控:人民可能安於現狀而缺乏革命熱情,但也有可能被激發得要挑戰終極權威。基於這種既要挑撥情感、又要平息情感的矛盾,我們有時候可以察覺到文革的宣傳藝術裏有一些「自我反省」(selfreflexive)的時刻,這也證明了當時的藝術有多混亂。以下是1974年的小說《劍河浪》裏的其中一段:劉瀏是一個剛剛下鄉的青年,被派去負責為農民煮飯。有一次,他太過投入看著名的革命小說《豔陽天》,燒焦了窩窩頭。第二天,他在煮晚飯時又再看《豔陽天》,突然看到一隻狼(後來被發現是一位找食物的階級敵人所假扮)。劉瀏隨手拿起一件東西敲打,以聲音把狼嚇退,卻拿錯了全村唯一一件水準儀,因而被批判。
後來,下鄉青年的領袖、也是小說主角的柳竹惠,跟劉瀏開展了一場平和的長篇對話。柳竹惠告訴劉瀏,她自己小時候也曾經沉迷繪畫。但是,她在最後卻從老師身上明白到,每人也需要忠於黨、聽黨的命令,而且無可避免要放棄個人利益和野心。22柳竹惠說,如果藝術活動有助革命,當然值得鼓勵。但是,劉瀏如此沉迷小說,卻必須被斥責,就正如柳竹惠自己小時候過分投入繪畫一樣。原因是藝術會使人忘記了全心為人民服務的責任。這是一段複雜的後設文學情節:一本革命小說(《劍河浪》)正在嘗試批判革命小說(劉瀏過分沉迷的《豔陽天》)。小說的作者汪雷,本身是下鄉青年。我們也可以保守假設,小說的讀者有不少下鄉青年。故此,柳竹惠批評劉瀏,可被視為青年間的自我批評。這展示出當時的藝術和青年如何共同糾纏於一起,既相輔相成、又互相拖累。如果宣傳文化(小說中以《豔陽天》為代表)僅僅有政治傳播的功能,那就沒有理由不讓青年沉迷下去。正正是由於藝術同時可以安撫讀者、宣洩情感和產生快感,才證明藝術存在一些逃離意識形態支配的殘留物。這些殘留物,恰恰是宣傳文化最害怕的東西。
盧卡奇(Georg Lukács)說過,西方小說往往傾向完滿地完成英雄的整個生命,展示出一種史詩般的統一結局。23文革小說卻似乎展示出不同的傾向:意識形態是統一的,代價卻是各種自我否定,包括藝術形式和英雄主角的自我完成,使小說和主角都無法順暢地提供一種完滿的感覺。如果歐洲浪漫主義可以跟毛式浪漫主義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後者比前者更渴望追求思維先行,更傾向以思維去決定和框定藝術的感官面向。不過,那些潛藏的政治意向永遠無法完全控制感官和想像的世界。毛式藝術的作品,的確永遠不會被容許涉足那豐富多元的語言和美學;但是,浪漫主義負載了那些可以觸及抽象美和超越日常的志向。故此,毛式藝術也有潛能去克服意識形態。
美學的驅力
詹明信曾經討論過文化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太像一般的文化革命,而是一段個別的歷史經驗。據詹明信所言,中國的文革有一個其他文化革命都沒有的特點:世代衝突。文革身處於一個繼承了舊封建制度的世代制度之中。青年以暴力去宣示自身的不滿,認為老人的權威和儒家的家庭系統難以忍受。
雖然詹明信的看法簡短和簡化,卻可以和我的文革研究互相參照。詹明信強調的世代衝突,就意味著結構性的美學轉化。青年往往以其風格(style)去標示自己跟體制有所不同。不過,文革並沒有展示出一種真正全新和令人震撼的美學。詹明信在另一本著作中也說過:「即使是我們最狂野的想像,也必須依附於既有的經驗,所以通常是當下東拼西湊的建構物。」25很多激進的另類想像,往往只是投射了我們的集體時刻、歷史處境和主觀位置,再加上一點點其他元素。所以,對所有革命來說都極之重要的烏托邦敘事(utopian narratives),其實是反映了我們當下的想像的限度,也間接揭示了有甚麼是無法被想像,又有甚麼是無法被理解。26對詹明信來說,烏托邦敘事最政治性的地方不是內容,而在於它們能夠重新組織當下的世界。
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文化傳統,批判了藝術自由。文革也把某些舊文化活化,以展示新世界的新形象。但這些「新」的風格實在不算新。例如,在1966–1967年期間,大部分出版社停工,而革命群眾卻可以實踐其出版的自由,出版自己的報紙、小冊子和海報。木刻版畫成為最主要的視覺形式。技術所限,蠟紙油印成為最易找到的印刷技術。但是,這種「新」的風格,其實也是把延安的宣傳文化循環再用,使人感到革命既新鮮、又熟悉。除了革命群眾因技術原因而運用以上的風格之外,復工後的出版社,也同樣採用了木刻版畫去展示新世界的秩序(圖1.1)。這些作品的實際內容,可能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些經循環再用而成的新外觀可以造成的效果。
胡志德(Ted Huters)認為,中國自晚清起,便開始打造「民族特色」的文化工程,但一直是聲勢浩大,卻不著邊際;文革聲稱創立和發展了中國式的風格和精神,可算是這項民族特色工程的終極體現。27施拉姆在其討論毛澤東思想的著作中,也提醒過我們「風格」在毛主義的思維中有多重要。他引用毛澤東在1959年3月的的一篇演講辭:「有些東西不要甚麼民族風格,如火車、飛機、大炮,但政治、藝術可以有民族風格。」28在這裏,毛澤東不只展示了「中國特色」的重要性,他也指出了政治和藝術的相似之處,即兩者都要找尋風格,都要以獨特的方式去展示和組織。吳一慶也指出,毛澤東往往以獨特的方法理解平等主義。毛澤東比較少關心實際的權力分配,而是更喜歡控制人民展示和表演權力的方法。他更感興趣的,似乎是人民公開地表演權力的各種方式,而非瓦解權力的層級結構。
那時候,新形象既被壓抑、又被提倡。時裝大致上被壓抑。人們也清楚知道,只要穿得稍為標奇立異,也有可能帶來政治上的風險。30但革命也往往就是對新形象的追求。於是乎,重整外觀(reordering of the appearance)就是可以最有力地表達意識形態和物質世界需要被重整的方法。受當時的社會條件所限,人們也許無法想像一個極之不同的世界。但是,人們嘗試把當時既有的詞語和觀念重新展現和包裝,以確立自己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