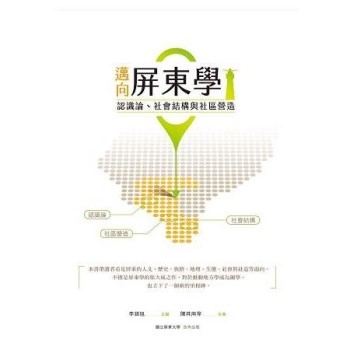地方誌、博物學與屏東知識圖像
─ 文獻與書寫類型的轉換軌跡 ─
陳其南
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兼任教授
一、前言
位在臺灣島最南端的屏東,在近代臺灣史上一直被認為是邊緣地區,直到今天仍然多少受制於下淡水溪的阻絕而與臺灣的政治經濟中心有一段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但是如果從歷史上來探索,將會發現在臺灣早期歷史的發展中,屏東地區曾經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紀錄中,即將所統治的地區以熱蘭遮城為中心分為南北兩區,而「南區」即指今日屏東地區的範圍,從記錄中可以看出其村社數目佔有荷蘭人統治底下的半壁江山。這個形勢到了清朝領有臺灣初期並未改變,可以從《番俗六考》作者黃叔璥的描述中看出來。到了清末時期,因為西方船隻不時在南臺灣海域發生船難漂流上岸而被當地漢番居民擄殺事件,不只引發美國領事李仙德自己進入恆春半島與當地原住民協商簽約,接著即發生1874年明治日本出兵南臺灣事件,是影響日本和清代中國的重要歷史事件。而有關這些事件的英文和日文文獻也突然暴增。事後清廷即將小小恆春設立縣治,更促成了清代臺灣最後一部地方志《恆春縣志》的出現。在自然方面,因為恆春半島地質和植被的特殊現象,使得有關這一地區的地質學和植物分布調查研究報告數量遠超過臺灣其他地區。
作者在前些時候參與《屏東縣志》的重修工作,曾經就「地質地形」、「本草博物」和「原初社會」三個領域,即傳統上被稱為「自然史」或「博物學」(natural history)的三分科,來探討影響過去屏東知識文獻累積的幾個重要歷史階段和事件。從十七世紀初開始,前後歷經荷蘭人、清代中國人、日本人、當代臺灣人和國際學者約四百年間的耕耘,可以看出不同背景和不同時代的探究者,針對不同領域所建構的知識類型風格。本文即嘗試以縣志編撰過程中所發現的一些具體案例來說明這個地方知識史發展的軌跡。
首先要說明,屏東的地理空間構成很清楚也很簡單。從空照圖或地形圖上看,以下淡水溪(或稱高屏溪)為界線,就可以將屏東縣的行政區範圍從整個臺灣島劃分出來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單位,是貨真價實的「南臺灣」。在這個範圍內明顯可辨識出平原區、山地區和恆春半島等三個區塊和小琉球嶼一個離島。平原區呈長方形,西以高屏溪、東以潮州斷層為界,南北長約60公里,東西寬約20公里,面積大約有1,140平方公里。其規模在臺灣僅次於嘉南平原,也是早期「鳳山八社」活動 的舞臺。平原區和中央山脈之間的界線是一條由北到南像經線一樣筆直的「潮州大斷層」。斷層以東的大武山塊是中央山脈的南段,曾被稱為「傀儡山」,歷來是魯凱族和排灣族的傳統生活領域。由此再往南延伸就是恆春半島,從楓港、大武一線以南的恆春半島,是早期瑯嶠上下十八社的領地。由此可見,屏東地區的自然地理區界與人文歷史發展型態兩者之間有相當大的重疊性。
(以下略)
地方學的形塑:南方經驗的反思
李錦旭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摘錄)
一、社區大學和公益團體的經驗:從地方學到臺灣學
社大脈絡下的地方學是怎麼來的?王御風(2016)這樣說:
在199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下,以傳統鄉鎮志修撰的翻新、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展,各地文化局的成立,加上教育改革下的各地廣設大學、社區大學的成立,多股力量下,催生了「地方學」。也因此,「地方學」的開始,融合了學術、社造、教育等多元面向,與傳統歷史學的純學術修撰又有不同,偏向帶動社區或各縣市、鄉鎮民眾一起探討自身的歷史、文化等傳統,「實作」方式比較濃厚,「大家來寫村史」就是個好範例。
臺灣自1998年9月28日第一所社區大學成立以來,秉持「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精神,與地方社區及社區營造密切結合,各縣市紛紛成立社區大學,至2017年已有86所(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2017),建立各地的地方學成為社大的願景之一(王御風,2008)。然而,社區大學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承接1994年10月以來由中央政府文化建設委員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培育其人才和建立所需的公民社會。
因此,社區大學的旨趣,不只是知識的,她還特重行動,其所建立的地方學程,理應揉合知識與行動。這就誠如屏東學的創建者李國銘(2001a)所說的:
對於「屏東」,我們除了有感性的情感認同之外,同時也會產生理性的求知慾望。「屏東學學程」的安排,即透過一系列課程之設計,引導選修課程的學員有組織、有系統地認識屏東。並試圖從教與學的過程中,尋求建構屏東在地知識體系與在地論述的可能性。
這樣的提法,側重在「屏東在地知識體系與在地論述」的建構。然而,屏北社大周芬姿(2006b)則有將重點轉移到「行動」的提法:
其(按指地方學)企圖超乎過去區域研究或方志學、社區鄉土史、縣志的企圖。它不只是知識的,更是號召行動的;它不只是經濟的,更是生命永續與環境永續的意義之所存。它不只是資料的蒐集,更是組構起人與知識形成與所居住地方的付出之間的積極關係。
社大幹部們鑒於地方學的重要,於2007年成立「台灣地方學研究發展學會」,主要任務包括:1.與社區大學結合,推動地方學之知識與公民行動;2.推動地方學之研究社群與在地實踐及國際交流;3.發展地理資訊系統(GIS)平台以及地方學研究,並建置地方學研究資料;4.出版地方學相關刊物、書籍與多媒體作品;5.整合政府、學界與民間團體資源,培力地方學人才;6.其他與地方學發展相關之事務(台灣地方學研究發展學會,2007)。
該學會理事長黃申在 將地方學定義如下(2009:5):
地方學一詞及實質內涵,應有多種意義理解與詮釋觀點,是多元多層次的,也是不斷變動流動與混成的,本身可能就需要不斷的再理解,再詮釋辯證;在此,我們僅先簡化區隔「地方」與「學」二詞,前者指涉有關「地方」的定義性論述意涵,及與「地方」有關的知識,包括事實知識、概念知識、技能知識與後設知識;後者,相較於「研究」活動,重點在個人體驗式學習,更著眼於機構性與系統性的學習活動,包括學院及終身學習體系;實踐情境上,則特別關注於社區大學推動地方學的各項措施,尤其在課程層級之規劃設計與實施的作為。「地方」一詞是常識性用語,如區域或地區、本地或當地、中央vs.地方、處所、部分等,看似著重某種「空間」或相對性,好像不涉及人,其實關注的正是人類的活動,亦即「地方/空間」作為人類活動展現與刻畫痕跡的場域,不論是過去、現在與未來。
這裡的「學」字好像不是英文字尾「ology」(指有系統的學問)的意思。然而其官方網站的「地方學」英文(造字?)的確是「localogy」。
不過,由於社區大學人力不足,其地方學程的師資往往需要借重文史團體和學院的人才。而文史團體和學院的人才則往往比較關心知識系統的建立,使其授課常常曲高和寡。例如:屏北社區大學的屏東學程就有因招生不足難以開課的現象(黃啟訓,2008)。高雄第一社大有關的課程也有逐漸萎縮的現象(參考: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2009)。嘉義市社大同樣難以形成有系統的地方學(參考:嘉義市社區大學,2009)。王御風(2011)也在其〈地方學的發展與挑戰〉一文中對此做出剴切的檢討。
臺南市新營社大主任張文彬(2012)在他的碩士論文則說「地方學是社區大學的天命」、「社區大學推動的地方學有別於地方政府、體制內大學及其他民間團體,具備行動取向」。
另一方面,有鑒於社區大學在「知識生產」方面,始終停留在比較淺層的論述上,無法真正突顯出社區大學的核心價值,社區大學自2008年年底開始推動「臺灣學」。這個構想的提出者顧忠華(2010)認為,「臺灣學」企圖由地方學的角度來重塑我們的自我認識,但又希望能夠在知識論及方法論上有所超越,承認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自我觀想和集體夢想,都屬於臺灣人歷史記憶的總合,都應該受到重視,如此才不會陷入零碎和自我封閉。期許「臺灣學」能夠使臺灣人的努力與世界相交流、會通、共成長,昂揚出各地台灣人的自信。他說:
「台灣學」意味著:以台灣這個空間作為座標,時間貫穿過去、現在和未來,主角則是所有住在這個島上的人們,凡是我們的思想、行為、遐想、願望,都可以成為「台灣學」觀察分析的對象,並且創造出種種「經驗知識」的內涵。
然而,「臺灣學」並不等於地方學,因為臺灣作為一個知識和行動的「場所」,本來便是與世界聲氣相應、密切連結的,臺灣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空間,就像臺灣每個鄉鎮、城市,也都是臺灣整體文化的一部分般,臺灣是全球的一部分,「臺灣學」也應該有一種全球化的視野,而不是劃地自限。尤其社區大學設立的初衷,是將學院的知識解放到民眾可就近學習的社區,因此更帶有擴大常民世界觀的目的。
這種說法,很容易令人想起美國教育哲學家John Dewey(1859-1952)的主張,他認為教育應從個人的生活經驗出發,卻又必須擴寬學生的視野,使其不會被個人生活經驗所侷限。不過,Dewey討論的學生主要是指未成年者,而臺灣的社大學生則都已經成年了。
在臺灣學的理念下,配合2009年88莫拉克風災水災,社大提出「臺灣水學」的想法,希望結合學院學者和民間經驗的力量來落實。其基本想法如下:
學院派知識的盲點,在於習慣以「套裝」方式傳授,不具備與常民溝通的同理心。相對地,台灣有多所社區大學積極發展「地方學」,即是尊重經驗知識,推廣常民科學,更準備提出跨域整合的「台灣水學」,以應用河川地理資訊系統於河川守護上的實踐經驗,來與社會進行對話。類似這種由下而上的知識解放,可能在風險知識的累積和運用上,反而可以發揮比五年五百億更大的效益,台灣的未來,也許要靠知識上的「自力救濟」吧!(顧忠華,2009b)
大政策的基礎應是在地的生活經驗知識,經驗知識的解構與建構正是社區大學立校之基。台灣學要從洪患中,整理出台灣洪範,要從在地聚落與河川進行水文、生文、人文調查,建構愛鄉護水的常民科學知識,要從細微處去看見生活與生態共存的安身立命之學。最後,有志之士應當結社成群,進行論辯,進行實踐,遊說政策,改革制度,才能為台灣百代子孫訂定永續的國土政策。(吳茂成,2009)
另一方面,作為社大的新典範「大廟興學」,自2007年3月推動以來也企圖結合村廟的傳統,發揮現代功能,並以第二次鄉土運動自期(吳茂成,2008)。這個運動也與臺灣學、地方學的構想匯流。
由以上的說明來看,社大及其相關公益團體對地方學的旨趣,比較像是一種行動的學問,企圖結合知識與行動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