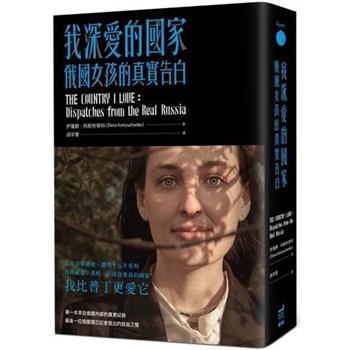我五歲,在上幼稚園。那是冬天,我們在玩打仗。高高的雪堆是堡壘,裡面全是德國人。我們發動猛攻。敵人不多,因為誰想當法西斯。至少他們擁有戰術優勢,畢竟防衛堡壘簡單多了。雪球飛來飛去。所有的男生都是戰士。我也想當戰士,但他們只讓我當護士,因為我是女生。我把傷者從戰場拖走,傷者全身是雪,放聲大笑。
我六歲。媽媽告訴我外公曾經打過戰爭,在法西斯攻擊我們國家時挺身捍衛。他志願到前線去,在那裡擔任砲兵。他受了傷,然後他復原,又回去打仗,這次是跟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在幫法西斯。這場戰爭名為「偉大的衛國戰爭」,因為是為我們的祖國而戰。為什麼偉大?因為幾乎所有男人和許多女人都參與其中,媽媽說。死了一千一百萬人。那是多少人?媽媽動了動嘴唇,悄悄計算著。等於十六個雅羅斯拉夫那麼多的人。想像我們的城市裡沒有人活下來。再想像其他十五個跟我們一樣的城市,沒有人活下來。一個都沒有,全部殺光光。
我想像那些死亡之城。
我八歲,這天是勝利日。我們要去鄰居彤亞阿姨家。她打過衛國戰爭。我們幫她買了蛋糕與紅色康乃馨。彤亞阿姨穿著藍色的自製洋裝,胸前佩戴勳章。看到我們和蛋糕她很開心,走過來擁抱我。我不喜歡彤亞阿姨,她聞起來臭臭的。她也耳背得厲害,跟她說話要很大聲,而且嘴巴要誇張的開合,才能讓她聽懂。還有她的公寓,每樣東西都閃閃發光,一塵不染,乾淨的讓我害怕,因為那不正常。彤亞阿姨很寵愛我。她會問我在學校過得好不好(很糟,但你得說很好)。媽媽倒了茶,我們舉杯祝賀。媽媽會說:「致和平。」
我十歲,看了場電影。電影名為《只有老兵去打仗》,講的是年輕瀟灑的勇敢飛行員,在天上駕駛戰機與法西斯作戰的故事。電影是黑白的,裡面每一張臉似乎都是從光雕塑而成。飛行員聚在一起,合唱著美好歌曲。他們死去,但死得英勇壯烈,在一朵朵黑色煙霧中灰飛煙滅。電影裡也有浪漫愛情,對象是女飛行員。她們死去,男飛行員會來到她們墓前,承諾戰爭結束後會再回來,再次合唱他們鍾愛的歌曲。我沒有在思考,情感不經大腦:哇,這太棒了,好精采的人生。
我十一歲,我問媽媽,外公是怎麼說戰爭的?她說,什麼都不說。一點都不說?一點都不說。他有勳章嗎?有,但他從來不戴,他把勳章都給了我。那時我還小,把勳章拿來玩,埋在沙裡,最後全弄丟了。真是可惜,太可惜了。他是怎麼死的?心跳停止。外婆喊他吃晚飯,但沒人答應。他就坐在這,死了,就這個位置。
我十二歲時去彤亞阿姨家。見到我她好高興。我問,彤亞阿姨,跟我說說戰爭的事情。她說,我聽不到你講話。彤亞阿姨,跟我說戰爭的事情!我什麼也聽不到,小蓮娜,我一定是全聾啦。戰爭的事!什麼,蘇聯的事嗎?蘇聯,那是個好國家。戰.爭.的.事!我一點也聽不到你說什麼,助聽器一定是壞啦。彤亞阿姨把助聽器拿出來後跟我說,阿姨累了,得去躺一會。再見,蓮娜。
我十二歲時去圖書館。我要找關於戰爭的書,他們好像給了我五本,我全都讀完了。我又借了五本,然後再五本。書中的戰爭不像電影裡那麼歡樂,但有更多英雄事蹟,而且可以慢慢細讀,好好感受一切。在卡雷利亞的森林裡,瓦斯科夫士官指揮著五名女高射砲手,試圖擊敗悄悄潛入的法西斯間諜,阻止他們前往具有戰略價值的運河。最後所有女孩都死了,最優秀的一個臨死前還說,「我們祖國的起點並不是這些運河,也完全不是由這些運河所孕育。我們捍衛運河是為了捍衛祖國,因為先有祖國,才有運河。」我為這段話痛哭,淚水如此甜美。那些運河當然連我摯愛祖國的一小角都算不上。
我十二歲時曾經想過,如果又有一場戰爭呢?如果我們的國家受到攻擊怎麼辦?我當然會捍衛它。如果我能快快長大就好了,我就能當狙擊手,殺光法西斯。為什麼是法西斯?我也不知道,那是我唯一想到的敵人。也許我會陣亡,年紀輕輕就死去。媽媽會哭泣,但也會深深以我為榮,平靜抱持某種低調但驕傲的哀愁。我只有兩個朋友,他們想必會逢人便說我們曾一起上學,告訴人們我是怎樣的人。這份幻想唯一的阻礙是,我是班上個頭最小的女生,一窩裡最瘦小的那一個,弱者。沒關係,我扛得動狙擊步槍。
我十三歲,我們街上有一場葬禮。一名年輕男子遇害——昨天還只是個學童的他,被徵募,被送去車臣,然後被殺。我問鄰居蓮亞是誰殺了他。車臣人。為什麼?因為那裡在打仗。跟誰?跟恐怖分子。哇,我心想,可憐的傢伙,是個真英雄。但蓮亞稱之為戰爭還是太誇大了,電視上說那是「反恐行動」。如果真的打仗,我們不會沒有聽說。
我十四歲,正在讀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關於車臣的報導。哇操。
我十四歲,正在讀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的書。哇靠。
我十七歲,就讀新聞系。我旁觀了一場跨國參與的權利策略比賽,各院校的新聞系都派出隊伍。車臣隊的成員是兩個女孩,阿絲亞與瑪莉卡。我在賽後邀請她們來宿舍,並在房內替她們泡茶。我非常想讓她們喜歡我。我說,讓我帶你們逛莫斯科!話還沒說完,外頭就放起煙火,彷彿早有預謀。你們看,是煙火!快看!我指著窗外說,煙火在莫斯科常常見到。她們沒有答話。我轉身一看,人早已不見蹤影。去哪了?原來在桌子底下。
我二十歲,俄羅斯入侵喬治亞。總統說這是維和任務,因為喬治亞攻擊了南奧塞提亞與阿布哈茲。《新報》派出三名記者前往當地,但我和其他三個女孩分到的工作是監看新聞來源。我連續三天晚上都睡不著。到了第四天,眼前開始有透明的光影閃爍,雙腿也開始不聽使喚。其他女孩說,蓮娜,睡覺去,我們會負責監看。我在辦公室沙發躺下來,蓋上被子,手機放在臉頰下。我沉沉睡去,直到有人碰了碰我肩膀。我驚跳起來。怎麼了?戰爭結束了。
我的手機從此無法離手,少了它我會害怕。
我二十三歲,副總編輯說,你永遠不會被派去報導戰爭。這是男人的工作,而你是位女孩。我在心裡頭回嗆,你他媽瘋了。
我二十四歲,前往埃及報導革命。我看到有人被汽油彈砸中後活活燒起來;我看到飛過空中的石頭撕裂人的手指及耳朵,弄得頭破血流。然後是槍聲響起。
我二十六歲,頓巴斯戰爭開打。烏克蘭境內的頓內次克與盧甘斯克地區宣布獨立,成為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與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烏克蘭於是展開自己的「反恐行動」,兩個「共和國」也以相同的手段回敬。俄羅斯政府宣稱當地沒有半個俄軍,說烏克蘭在打自己的公民。我四處尋找俄軍士兵的遺體(都被藏匿起來),而我找到了。
我二十七歲,前往頓巴斯。我從飛機上打電話給母親,因為不敢事先跟她說。我以為我媽會大哭大鬧,結果她只是問:我的聯絡資訊有寫在護照裡了嗎?記得把護照用保鮮膜包著,隨身攜帶,但不要放進包包,要放在衣服裡。試著一天至少跟我聯絡一次,簡訊也好。記得喝水,保持溫暖,待在醫院旁邊,避開軍車。你有帶抗生素嗎?記得弄些止血帶。
我終於見到了戰爭。我讀過的書沒有一本告訴我,戰爭就是泥土。重型機具破壞表土,淺褐色的泥漿就從裂縫中湧出。泥漿覆蓋一切,覆蓋人、車、建築、狗。好多好多被遺棄的狗,好多好多帶著武器失眠的人。
我兩度置身砲火,我學到逃跑時可以四肢並用。我手舞足蹈,邊滑行邊跳,宛如做夢一般,身體變得輕盈柔軟。我不覺得我會死。
我兩度回到頓巴斯。
我寫下許多文章,沒有一篇讓我想重讀。
我三十一歲,在紐約市立大學新聞學院修課,艾莉亞正在教授國際新聞。她是敘利亞人,美麗無比且機智過人。我為這門課花得準備功夫比其他課都多,只希望她能注意到我,但我沒什麼可以讓她產生印象之處。我書讀不多,思考也慢。艾莉亞要我們謹慎而誠實地寫作,教導我們要專注聆聽與保持謙卑。最後一堂課,她帶了百里香糕餅和阿拉伯甜點給我們。大家一邊吃,一邊輪流播放自己喜愛的歌曲。我上前告訴艾莉亞,我就要返回莫斯科了,歡迎來造訪。艾莉亞的臉變得好蒼白,彷彿有人切換了房裡的光線。她俯身靠近我,悄悄聲地說:我永遠不會去莫斯科,你們的軍人正在屠殺我愛的人。
我三十四歲,我母親得了新冠肺炎,我回來照顧她。我們坐在電視機前面聽普丁講話,他說俄羅斯承認頓巴斯與盧甘斯克共和國的獨立地位。我出去抽根煙,順便買了台洗衣機。我對自己說,還好我的公寓已經整修好了。轉念一想,我還真他媽的實際啊,簡直噁心。盧布這下慘了,我跟我媽說。她問我之後會怎麼樣,我告訴她,政府會派軍隊進入頓內次克與盧甘斯克,至少這回是正式出兵。也就是說,會有更多戰爭。我媽接話說,但至少他們會保護俄國人。你知道有多少俄國人住在那裡嗎?我接著告訴她,我必須趕回莫斯科。但我真正的意思是,我得去一趟頓內次克。我媽只要我帶著外公的照片。把檔案弄好,印大張一點,好嗎?好。我把外公的照片夾進護照。
回到莫斯科之後,我開始做起栩栩如生的夢。美麗異常,但也鮮明到幾乎令人痛苦。我起身抽煙,再回到房間。女友坐在床上讀手機,我讀不出她的表情。你為什麼不睡?他們在轟炸基輔。什麼?他們在轟炸基輔和烏克蘭所有大城市。我們在轟炸他們?我們在轟炸他們。
我強迫自己再睡兩小時,然後穿好衣服去上班。同事問我,你準備好了嗎?我當然準備好了。
說真的,要準備好當法西斯是不可能的,我一點準備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