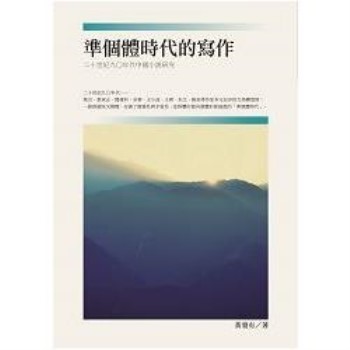導言 準個體時代的寫作
二十世紀九○年代只是自然的時間概念,我個人也無意將它視為具有充分的自足性的文學史時間。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身的特點,但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可能特殊到獨立顯現的程度,沒有了繼往開來,沒有了歷史視野中的相互參照,任何一個時代的自我記錄都只能是一筆糊塗帳。正如魯迅所言:「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 在我個人看來,這種「中間物」意識是理解九○年代和九○年代小說的關鍵所在。傳統史學有隔代修史的說法,一者生活在自己的時代中的人容易當局者迷,二者一個時代的真正面貌只有在其歷史後效顯現出來之後,才能獲得相對客觀的歷史評價。但是,「當代」研究的進行狀態往往給歷史留下鮮活的痕跡,也是生活其中的主體的一種存在方式。九○年代的中國是價值大碰撞、文化大轉型的年代,炒得沸沸揚揚的「世紀末」概念與對象自身常常是南轅北轍,我個人喜歡的只是辭舊迎新的「再生」意味,但「再生」並不代表「終結」或「斷裂」,它更多地寄予了生活其中的人的一種願望,我們的未來還是要承擔起歷史的連續性。九○年代自身並不是一個大時代,我更願意將它理解成一個文化準備期和精神過渡期,甚至算得上是前奏或序曲。面對著與自己共同度過的歲月,時間、主體、文本、記憶是我的幾把鑰匙。
一、被遮蔽的時間九○年代中國人文學界對於時間的敏感無疑是驚人的,這突出表現在眾多闖將高舉理論刀叉,對時間進行蠻橫的、隨意的切割。於是,命名者似乎在自己的盤中盛下了一段誓死捍衛的、別人不能覬覦的「時間香腸」。為了警告僭越者,許多命名者都連篇累牘地重申自己的發明權,甚至為此而故意挑起唇槍舌戰,以「廣而告之」。這些高戴「新」與「後」的王冠的時間斷片前呼後擁,試圖把主體從穿胸而過的時間箭矢中解救出來,但這些基於當代生活的表象甚至是假象的命名大都落入了障眼遊戲的俗套,這些蕪雜的詞語在互不買帳的拚殺中共同擁有著一種侵入骨髓的焦慮,那就是對於統攝現實的歷史後效的恐懼。這種試圖擺脫歷史與現實的重壓,疾行於時間之前的衝動造成主體的前撲姿態,儘管上身向前飛翔,但雙腳卻被牢牢地吸附在現實的門檻之內。這種抗爭宿命的精神越獄最終往往不幸地使失衡的身姿處於匍匐狀態,淪落成時間牢籠裡的囚徒。
「影響的焦慮」是如此地深重,以至於知識者不管如何掙扎,都無法繞過前人布下的強大精神磁場。於是,九○年代中國的人文知識份子為了不使自己被淹沒於歷史的汪洋之中,只好高舉「打倒」、「超越」、「告別」的旗幟,宣判舊歷史的「終結」和「死亡」,但這道人為的鴻溝並不能阻斷歷史的綿延。為了獲得苟且的安慰,為了不被「創新的狗」攆上,命名家們只好在幻念中不斷地構築「紙上的未來」,這就如同給尚未受孕的嬰兒所舉行的隆重的「提前命名」儀式。後現代、後殖民、後寓言、後國學、後革命、後烏托邦、後知識份子、新東方、新儒家、新保守主義、新啟蒙……,這些讓人眼花繚亂的命名都齊刷刷地將矛頭對準無辜的時間,對時間進行隨意的切割,而命名者似乎在自己的盤中盛下了一段別人不能覬覦的「時間香腸」。就文學而言,後新時期、後批評、後先鋒、新寫實、新歷史、新體驗、新狀態、新市民、新現實主義……,它們毫不例外地披著「新」與「後」的花衣裳。面對著這種方式單一的名詞轟炸,我常常為「新爺後主」們的想像力的枯竭而羞愧。隨後總算又出臺了新花樣,那就是以「代」來分割文學,諸如六○年代作家群、七○年代作家群、晚生代、新生代、「文革」後一代、更新代……。在世紀交替的關鍵時刻,敏銳的人們自然不會放過作秀亮相的天賜良機,於是,「跨世紀××」、「世紀末××」、「新世紀××」等名詞又被熱氣騰騰地烘製出爐。但繞來繞去,還是無法捨棄時間這塊肥肉。說穿了,這些勃發著解構理性、主體、意義、歷史等「後現代」熱忱的命名,無非是建構在由「前現代」向「現代」過渡的現實地基上的「後神話」,無非是透支未來的「時間烏托邦」而已。
儘管奇招迭出,但這些志在「創造新紀元」的命名實際上是萬變不離其宗,或曰殊途同歸。它們不約而同地倒入再生的時間觀念的懷抱。古希臘的斯多噶學派認為宇宙是由一定週期以後的幾個惑星排列於固定位置上所構成的,然後宇宙被一場大災難所完全破壞,在經過再度重建的過程後,這些惑星再回到原來的軌道上運行,一切回到原來的秩序。中美洲的瑪雅人更是相信歷史每二百六十年重複一次,這個週期被叫做拉瑪特,是其日曆的基本單元。這種圓形的時間觀念孕育了永恆回歸、一切再生的信仰。《老子》中的「復歸於嬰兒」、「比於赤子」、「能嬰兒乎」,《莊子》中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這些語句同樣鮮明地反映了一種希望時間能夠回歸原始起點的內在願望。在圓形循環迴圈的時間信仰下,古代人認為時間具有死與再生的本質,「年」、「季節」、「月」和「日」在古代人的觀念裡都不僅僅是一個時間記號,而是有其由俗到聖的通過意義。年是一定俗性時間的結束(除夕)和一定聖性時間的開始(正月),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復始是讓時間再從最初開始,是為了重返宇宙開始的神話時間,這種回歸於神話、元始、純粹、創造的瞬間,正是古代人的時間的再生儀式。弗雷澤在其名著《金枝》中詳述了歐洲「埋葬狂歡節」的傳統,通過「送死神」使春神在假象的死亡後復甦,並有「迎夏」、演示「夏冬之戰」的習俗 。這和中國的許多節日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渴望永恆回歸、一切再生的時間觀念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基督教直線時間觀念的確立動搖了它在西方世界的基座,但「復歸於嬰兒」的精神籲求在東方世界卻一直綿延不絕。只有將命名的輝煌大廈建築在再生信仰的神奇地基之上,許多令人難以理喻之處才能豁然貫通。不然,你如何能夠理解八○年代的最後一刻屬於「群體主義時代」,而九○年代的最初一刻卻屬於有天壤之別的「個體主義時代」呢?又如何能理解某一時間記號竟然成了「前」與「後」、「舊」與「新」的分水嶺呢?隨著六○年代的時鐘的最後一聲「滴答」響起,一切又重新開始,因而,七○年代出生的作家們自然不能不稟有六○年代作家自愧弗如的新質。季羨林先生曾聲稱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世紀,後來也猶疑過:「二十一世紀是一塊還沒掛出來的匾,匾上的字是什麼,誰也說不清。」但最終還是不甘心:「世界文化到底是以西方文化為主還是以東方文化為主,這是不能含糊的,我認為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應以東方文化為主流。」 這算得上是「提前掛匾」了。按照「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古訓,世界是一個輪回不止的大圓盤,因此,二十世紀的最後一記鐘聲理應公平地將世界帶入「東方的世紀」!這樣的邏輯依稀地展現出禪宗的高妙境界,即從山窮水盡轉向柳暗花明的爆發性突破,也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頓悟。禪宗常說的一句話是:「必須大死一番,方能悟得正道。」這是要求人們在修煉中必須下狠心割捨紛擾的雜念,將意識集中到「一念一想」,從而得以在石破天驚中進入「無念無想」的境地,實現從以前的生命(俗性時間)到另一個生命(聖性時間)的轉折。命名家們正是將歷史視成了可以在刹那間發生突變的變色龍,他們的論證也往往是對制約歷史發展的紛繁複雜的關係進行大刀闊斧的刪削,將意識凝聚於「一念一想」,在想像中體驗狂飆突進的顫慄與狂歡。說穿了,無非是以偏概全,以蠡測海,以想像代替本質,在割斷鮮活而沉重的歷史和現實的前提下沉迷於渺渺茫茫的白日夢。命名儀式成了遺忘儀式!讓脆弱的生命不堪重負的真實被拋擲到了陰冷的角落。也許正是由於二十世紀的中國遍布荊棘與暗礁,外寇入侵的綿延戰火和史無前例的「文革」創痛如千鈞壓頂,那麼多的知識精英才急於甩脫這百年的陰影,渴望進入一個純粹的世紀。也許正是由於中國與西方的距離讓人太難堪,命名者才急於與西方接軌,迫不及待地將中國提前送入「後現代社會」。良好的願望絕不是壞事,但當它的幻想油彩塗蓋了歷史和現實的本質,成了逃避真實的藉口時,這種預約「黃金世界」的努力就變成了一場紙上的「大躍進」。
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認為,傳統史學對重建某一時代「總體面貌」的追求,導致了對歷史中固有的非連續性的曲解、簡約和擦除,以便使歷史呈現出連續性。為了矯正這種偏失,福柯提出了新的歷史研究和哲學研究的思維方式,論證了非連續性、轉換生成、界限、斷裂、印痕、歷史的差異性原則、非主體性原則等新史學觀念範疇的認識論基礎。但中國的命名家們顯然矯枉過正,將歷史視成了可以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儘管在二十世紀五、六○年代,一統天下的宏大敘事內在地具有壓抑自由和個性的意識形態功能,但九○年代的文學領地並不能因此而讓位於藏污納垢的「私人敘事」。其實,宏大敘事和私人敘事本身並沒有高下優劣之分,但是,命名家們卻總是在倒洗澡水時也將澡盆裡的孩子一起倒掉。試圖將歷史連續性連根拔除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對歷史和時間的謀殺。非連續性固然已經與歷史學家的話語融為一體,不再扮演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婢角色,但它並不是可以憑空捏造、無中生有的。命名家們在宣揚自己的「新生嬰兒」時,總是唾沫橫飛地標榜其性能的截然不同,似乎只須他們揮舞著理論魔棒大喝一聲「變」,歷史就能掙脫外部和內部的制約瞬息萬變。這就如各民族史前時期普遍存在過的「成年禮」儀式,未成年人只要在人為的磨難和考驗中經歷象徵性的「死亡」體驗,便能贏得再生,從自然生命狀態蛻變為社會生命狀態。但這樣的命名和加冠禮只能是一種巫術,而絕非堂堂正正的學術。國外的新史學強調非連續性時總是一再強調其偏差、消散、迴旋等豐富內涵,但中國的命名家們卻絕非循規蹈矩的乖孩子,他們總是擅長掐頭去尾、移花接木的高超本領。他們將目的論投射於歷史,藉以強調歷史的進化。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中的「進化」一詞分明含有「萬化周流,有其隆升,則亦有其污降」的辯證含義,但時下的命名家們自然不信那一套,偏愛所向無敵、一路攀升的進化。於是,「後現代」遠勝於「現代」,「新歷史」必勝於「舊歷史」,而七○年代出生的作家自然會把六○年代出生的作家拋在後面,八○年代出生的作家更是當仁不讓。陳四益在由丁聰配畫的《後新新紅學》中說:「在《紅樓夢》中看見《易》、看見淫、看見纏綿、看見排滿、看見宮闈祕事的是舊紅學;在《紅樓夢》中看見曹雪芹家史、家世的是新紅學;看到啟蒙主義、民主主義、四大家族興衰史的是新新紅學,那麼今天的紅學套一個時髦名詞便應當是後新新紅學了。」 這就像俄羅斯的木製套娃娃,重重疊疊,一個將一個套在肚子裡,最裡面的一個是絕難看清了。
把二十世紀九○年代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學史時間進行考察,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命名家們的「時間拼盤」,這些斑斕的標籤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構成了「理解九○年代」的首要障礙。在「今天遠勝於昨天」、「一日千里」的時間意識中,蘊含著一種潛在的樂觀精神,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樂觀精神與魯迅所說的「瞞」和「騙」沒有什麼本質區別。而且,九○年代的文學理論界與創作界總是在「求新求變」中焦躁不安,理論界不斷地搬弄著諸如後現代、後殖民、新歷史、新批評、法蘭克福學派等等西方話語,進行生硬的移植與命名;創作界則是模仿成風,似乎每個成名的作家都必須有個國外的精神導師才能心安理得。宗仁發在評價「七○年代人」的創作時說了一席話,他認為他們「生不逢時」,在各種文學觀念粉墨登場,輪番轟炸二十年以後,他們的出場面臨著雙重疲憊,一重是模仿的疲憊,現在誰再模仿卡夫卡、瑪律克斯、加繆、博爾赫斯,誰就會被喝倒采,但八○年代這類模仿是被人們誇讚的。連卡爾維諾、巴塞爾姆也模仿不得,前面也有人仿過了,「七○年代人」已喪失了「第一模仿權」。另一重疲憊是他們也不能緊跟與他們年齡相近的那些作家 。這段話反映出九○年代作家原創性的匱乏。當文學觀念、形式甚至是細節描寫都被籠罩在「模仿」的陰影之下時,九○年代的作品還能貼切地反映中國本土活生生的現實嗎?
九○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學就表面看來,充溢著過剩的「時間意識」與「現實精神」。新寫實的審美品格在後起的新生代作家的筆下,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只是在那種「無可奈何」的認同中摻雜了一點「玩世不恭」,而以劉醒龍、談歌、何申、關仁山、周梅森等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在把最初的那點真誠消耗之後,逐漸地把「騎牆」的功夫煉得爐火純青。還有那些曇花一現的「新體驗」、「新新聞」、「新狀態」、「新移民」小說,在文學的體式上都偏重寫實甚至具有紀實品格,但在骨子裡卻充滿了一種游離於現實之外的草率與輕浮。隨著文化市場的逐步擴張,文學消費與消費文學成為制約作家自由創作的重要因素,商業化敘事大行其道,「現實」與「真實」也開始成為作家出售的一種精神商品,而且還是贗品。因此,九○年代文學中充斥著的是「偽時間意識」與「偽現實精神」,這些貌似敏感的時間判斷與現實關懷遮蔽了真相。當贗品廣為流行時,真品反而要被淘汰,價值不高的物品將價值較高的物品擠出了流通領域,這就是經濟領域的「格雷欣法則」,國內許多商家在假冒偽劣產品的圍困下倒閉的例證可謂比比皆是,九○年代思想界的境遇與此不無相似之處。
九○年代文學界從不缺乏奇談怪論,最缺乏的偏偏是常識。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問題》中說:「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作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乏想像力。」王小波的意義正在於他說出了眾人皆知但許多人不屑說或不願說的常識。其實,當很多新潮文學家沉迷於「新」與「後」的遊戲時,甘於寂寞的人們只要稍稍關注「舊」與「前」的問題,便會發現常識的沉重。比如,「五四」一代的現代性籲求和啟蒙任務,他們所宣導的科學和民主精神,在九○年代依然處於未完成狀態。對個性與自由的嚮往成了折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創傷。很多被命名家們吹得神乎其神的新現象,其實是老問題遇到了新情況。漫長的封建歷史所投下的現實陰影,常常改頭換面地出現在各種各樣的新舞臺。而廣大的中國農村的「前現代」現實,在許多所謂的思想家眼裡遠不如一個舶來的術語來得重要。我們在繼承歷史遺產的同時,也必須承擔歷史賦予的責任,割斷歷史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文化逃避。九○年代不僅要背負八○年代的精神舊帳,還必須承擔從二十世紀上溯到整個五千年文明的歷史連續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認清自己的歷史處境與歷史任務。
二、困難的個人
將九○年代命名為「個人化時代」或「個體文化時代」,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時尚。這種觀點認為作為群體時代或非個人化時代的八○年代存在一系列文化範式或共同的話語系統,儘管社會的外部形態在八○年代中後期出現了個人化的萌芽,但話語指向仍然聚斂和集束於人道主義關懷、文化啟蒙等共同目標。也就是說,發揮統攝性作用的仍然是中國傳統體制之下的以長老、家國為中心的的文化形態。而九○年代則是一個價值多元、文化失範的年代,中心崩潰,傳統離析,呈現出零散化、拼貼化的混亂狀態,個人性正是在碎片化的縫隙中逐漸確立,文化形態也就在市場經濟的助推之下順理成章地過渡為以個體為本位的文化。如果說把八○年代概括為群體主義時代還算差強人意的話,將九○年代命名為「個人化時代」就只能是牽強附會了。九○年代在表象層次上確實呈現出零散化、拼貼化的混亂,市場經濟將個體從舊有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政治權力話語相對有所削弱,價值取向也從大一統的轄制中游離出來,但統攝八○年代的文化邏輯依然存在,其新變是逐漸潛化,變得更加隱蔽和複雜,滲透進盤根錯節的文化根系。商業主義、技術主義話語的喧嘩並沒有摧毀原有的價值體系,它們的抛頭露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為之提供了一種掩護。新舊雜陳的狀態並非毫無秩序,準確而言,這是一種層積格局,新觀念漂浮於舊觀念之上,前者的現實化必須依賴後者的作用機制的運轉。「權威主義」、「非理性」、「缺少對科學的尊重」、「迷信盛行」、「缺少積累精神」等文化幽靈成了阻礙社會的現代化和人格的個體化的人文因素 。這種傳統心態的影響之所以頑強有力,原因就在於這種觀念是在歷史上形成的,來自於過去的經驗,並成為一種心理的力量。雖然過去的經驗和環境已經有了變化,但這種心態仍然保存下來。「一個社會與其過去的紐帶關係永遠不可能完全斷裂,如果不在某種最小的程度上存在這種紐帶,一個社會就不成其為社會了。」 而且,商業在釋放解放個人的力量時,也滾動著削磨個人性的圓形刀片,這使從「文革」重軛下匍匐出來的人們在還沒伸直脊樑時就被納入另一種控制,文化轉型的撕扯把個性覺醒的過程推入進退維艱的的困境。
二十世紀九○年代只是自然的時間概念,我個人也無意將它視為具有充分的自足性的文學史時間。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身的特點,但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可能特殊到獨立顯現的程度,沒有了繼往開來,沒有了歷史視野中的相互參照,任何一個時代的自我記錄都只能是一筆糊塗帳。正如魯迅所言:「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 在我個人看來,這種「中間物」意識是理解九○年代和九○年代小說的關鍵所在。傳統史學有隔代修史的說法,一者生活在自己的時代中的人容易當局者迷,二者一個時代的真正面貌只有在其歷史後效顯現出來之後,才能獲得相對客觀的歷史評價。但是,「當代」研究的進行狀態往往給歷史留下鮮活的痕跡,也是生活其中的主體的一種存在方式。九○年代的中國是價值大碰撞、文化大轉型的年代,炒得沸沸揚揚的「世紀末」概念與對象自身常常是南轅北轍,我個人喜歡的只是辭舊迎新的「再生」意味,但「再生」並不代表「終結」或「斷裂」,它更多地寄予了生活其中的人的一種願望,我們的未來還是要承擔起歷史的連續性。九○年代自身並不是一個大時代,我更願意將它理解成一個文化準備期和精神過渡期,甚至算得上是前奏或序曲。面對著與自己共同度過的歲月,時間、主體、文本、記憶是我的幾把鑰匙。
一、被遮蔽的時間九○年代中國人文學界對於時間的敏感無疑是驚人的,這突出表現在眾多闖將高舉理論刀叉,對時間進行蠻橫的、隨意的切割。於是,命名者似乎在自己的盤中盛下了一段誓死捍衛的、別人不能覬覦的「時間香腸」。為了警告僭越者,許多命名者都連篇累牘地重申自己的發明權,甚至為此而故意挑起唇槍舌戰,以「廣而告之」。這些高戴「新」與「後」的王冠的時間斷片前呼後擁,試圖把主體從穿胸而過的時間箭矢中解救出來,但這些基於當代生活的表象甚至是假象的命名大都落入了障眼遊戲的俗套,這些蕪雜的詞語在互不買帳的拚殺中共同擁有著一種侵入骨髓的焦慮,那就是對於統攝現實的歷史後效的恐懼。這種試圖擺脫歷史與現實的重壓,疾行於時間之前的衝動造成主體的前撲姿態,儘管上身向前飛翔,但雙腳卻被牢牢地吸附在現實的門檻之內。這種抗爭宿命的精神越獄最終往往不幸地使失衡的身姿處於匍匐狀態,淪落成時間牢籠裡的囚徒。
「影響的焦慮」是如此地深重,以至於知識者不管如何掙扎,都無法繞過前人布下的強大精神磁場。於是,九○年代中國的人文知識份子為了不使自己被淹沒於歷史的汪洋之中,只好高舉「打倒」、「超越」、「告別」的旗幟,宣判舊歷史的「終結」和「死亡」,但這道人為的鴻溝並不能阻斷歷史的綿延。為了獲得苟且的安慰,為了不被「創新的狗」攆上,命名家們只好在幻念中不斷地構築「紙上的未來」,這就如同給尚未受孕的嬰兒所舉行的隆重的「提前命名」儀式。後現代、後殖民、後寓言、後國學、後革命、後烏托邦、後知識份子、新東方、新儒家、新保守主義、新啟蒙……,這些讓人眼花繚亂的命名都齊刷刷地將矛頭對準無辜的時間,對時間進行隨意的切割,而命名者似乎在自己的盤中盛下了一段別人不能覬覦的「時間香腸」。就文學而言,後新時期、後批評、後先鋒、新寫實、新歷史、新體驗、新狀態、新市民、新現實主義……,它們毫不例外地披著「新」與「後」的花衣裳。面對著這種方式單一的名詞轟炸,我常常為「新爺後主」們的想像力的枯竭而羞愧。隨後總算又出臺了新花樣,那就是以「代」來分割文學,諸如六○年代作家群、七○年代作家群、晚生代、新生代、「文革」後一代、更新代……。在世紀交替的關鍵時刻,敏銳的人們自然不會放過作秀亮相的天賜良機,於是,「跨世紀××」、「世紀末××」、「新世紀××」等名詞又被熱氣騰騰地烘製出爐。但繞來繞去,還是無法捨棄時間這塊肥肉。說穿了,這些勃發著解構理性、主體、意義、歷史等「後現代」熱忱的命名,無非是建構在由「前現代」向「現代」過渡的現實地基上的「後神話」,無非是透支未來的「時間烏托邦」而已。
儘管奇招迭出,但這些志在「創造新紀元」的命名實際上是萬變不離其宗,或曰殊途同歸。它們不約而同地倒入再生的時間觀念的懷抱。古希臘的斯多噶學派認為宇宙是由一定週期以後的幾個惑星排列於固定位置上所構成的,然後宇宙被一場大災難所完全破壞,在經過再度重建的過程後,這些惑星再回到原來的軌道上運行,一切回到原來的秩序。中美洲的瑪雅人更是相信歷史每二百六十年重複一次,這個週期被叫做拉瑪特,是其日曆的基本單元。這種圓形的時間觀念孕育了永恆回歸、一切再生的信仰。《老子》中的「復歸於嬰兒」、「比於赤子」、「能嬰兒乎」,《莊子》中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這些語句同樣鮮明地反映了一種希望時間能夠回歸原始起點的內在願望。在圓形循環迴圈的時間信仰下,古代人認為時間具有死與再生的本質,「年」、「季節」、「月」和「日」在古代人的觀念裡都不僅僅是一個時間記號,而是有其由俗到聖的通過意義。年是一定俗性時間的結束(除夕)和一定聖性時間的開始(正月),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復始是讓時間再從最初開始,是為了重返宇宙開始的神話時間,這種回歸於神話、元始、純粹、創造的瞬間,正是古代人的時間的再生儀式。弗雷澤在其名著《金枝》中詳述了歐洲「埋葬狂歡節」的傳統,通過「送死神」使春神在假象的死亡後復甦,並有「迎夏」、演示「夏冬之戰」的習俗 。這和中國的許多節日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渴望永恆回歸、一切再生的時間觀念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基督教直線時間觀念的確立動搖了它在西方世界的基座,但「復歸於嬰兒」的精神籲求在東方世界卻一直綿延不絕。只有將命名的輝煌大廈建築在再生信仰的神奇地基之上,許多令人難以理喻之處才能豁然貫通。不然,你如何能夠理解八○年代的最後一刻屬於「群體主義時代」,而九○年代的最初一刻卻屬於有天壤之別的「個體主義時代」呢?又如何能理解某一時間記號竟然成了「前」與「後」、「舊」與「新」的分水嶺呢?隨著六○年代的時鐘的最後一聲「滴答」響起,一切又重新開始,因而,七○年代出生的作家們自然不能不稟有六○年代作家自愧弗如的新質。季羨林先生曾聲稱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世紀,後來也猶疑過:「二十一世紀是一塊還沒掛出來的匾,匾上的字是什麼,誰也說不清。」但最終還是不甘心:「世界文化到底是以西方文化為主還是以東方文化為主,這是不能含糊的,我認為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應以東方文化為主流。」 這算得上是「提前掛匾」了。按照「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古訓,世界是一個輪回不止的大圓盤,因此,二十世紀的最後一記鐘聲理應公平地將世界帶入「東方的世紀」!這樣的邏輯依稀地展現出禪宗的高妙境界,即從山窮水盡轉向柳暗花明的爆發性突破,也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頓悟。禪宗常說的一句話是:「必須大死一番,方能悟得正道。」這是要求人們在修煉中必須下狠心割捨紛擾的雜念,將意識集中到「一念一想」,從而得以在石破天驚中進入「無念無想」的境地,實現從以前的生命(俗性時間)到另一個生命(聖性時間)的轉折。命名家們正是將歷史視成了可以在刹那間發生突變的變色龍,他們的論證也往往是對制約歷史發展的紛繁複雜的關係進行大刀闊斧的刪削,將意識凝聚於「一念一想」,在想像中體驗狂飆突進的顫慄與狂歡。說穿了,無非是以偏概全,以蠡測海,以想像代替本質,在割斷鮮活而沉重的歷史和現實的前提下沉迷於渺渺茫茫的白日夢。命名儀式成了遺忘儀式!讓脆弱的生命不堪重負的真實被拋擲到了陰冷的角落。也許正是由於二十世紀的中國遍布荊棘與暗礁,外寇入侵的綿延戰火和史無前例的「文革」創痛如千鈞壓頂,那麼多的知識精英才急於甩脫這百年的陰影,渴望進入一個純粹的世紀。也許正是由於中國與西方的距離讓人太難堪,命名者才急於與西方接軌,迫不及待地將中國提前送入「後現代社會」。良好的願望絕不是壞事,但當它的幻想油彩塗蓋了歷史和現實的本質,成了逃避真實的藉口時,這種預約「黃金世界」的努力就變成了一場紙上的「大躍進」。
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認為,傳統史學對重建某一時代「總體面貌」的追求,導致了對歷史中固有的非連續性的曲解、簡約和擦除,以便使歷史呈現出連續性。為了矯正這種偏失,福柯提出了新的歷史研究和哲學研究的思維方式,論證了非連續性、轉換生成、界限、斷裂、印痕、歷史的差異性原則、非主體性原則等新史學觀念範疇的認識論基礎。但中國的命名家們顯然矯枉過正,將歷史視成了可以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儘管在二十世紀五、六○年代,一統天下的宏大敘事內在地具有壓抑自由和個性的意識形態功能,但九○年代的文學領地並不能因此而讓位於藏污納垢的「私人敘事」。其實,宏大敘事和私人敘事本身並沒有高下優劣之分,但是,命名家們卻總是在倒洗澡水時也將澡盆裡的孩子一起倒掉。試圖將歷史連續性連根拔除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對歷史和時間的謀殺。非連續性固然已經與歷史學家的話語融為一體,不再扮演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婢角色,但它並不是可以憑空捏造、無中生有的。命名家們在宣揚自己的「新生嬰兒」時,總是唾沫橫飛地標榜其性能的截然不同,似乎只須他們揮舞著理論魔棒大喝一聲「變」,歷史就能掙脫外部和內部的制約瞬息萬變。這就如各民族史前時期普遍存在過的「成年禮」儀式,未成年人只要在人為的磨難和考驗中經歷象徵性的「死亡」體驗,便能贏得再生,從自然生命狀態蛻變為社會生命狀態。但這樣的命名和加冠禮只能是一種巫術,而絕非堂堂正正的學術。國外的新史學強調非連續性時總是一再強調其偏差、消散、迴旋等豐富內涵,但中國的命名家們卻絕非循規蹈矩的乖孩子,他們總是擅長掐頭去尾、移花接木的高超本領。他們將目的論投射於歷史,藉以強調歷史的進化。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中的「進化」一詞分明含有「萬化周流,有其隆升,則亦有其污降」的辯證含義,但時下的命名家們自然不信那一套,偏愛所向無敵、一路攀升的進化。於是,「後現代」遠勝於「現代」,「新歷史」必勝於「舊歷史」,而七○年代出生的作家自然會把六○年代出生的作家拋在後面,八○年代出生的作家更是當仁不讓。陳四益在由丁聰配畫的《後新新紅學》中說:「在《紅樓夢》中看見《易》、看見淫、看見纏綿、看見排滿、看見宮闈祕事的是舊紅學;在《紅樓夢》中看見曹雪芹家史、家世的是新紅學;看到啟蒙主義、民主主義、四大家族興衰史的是新新紅學,那麼今天的紅學套一個時髦名詞便應當是後新新紅學了。」 這就像俄羅斯的木製套娃娃,重重疊疊,一個將一個套在肚子裡,最裡面的一個是絕難看清了。
把二十世紀九○年代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學史時間進行考察,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命名家們的「時間拼盤」,這些斑斕的標籤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構成了「理解九○年代」的首要障礙。在「今天遠勝於昨天」、「一日千里」的時間意識中,蘊含著一種潛在的樂觀精神,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樂觀精神與魯迅所說的「瞞」和「騙」沒有什麼本質區別。而且,九○年代的文學理論界與創作界總是在「求新求變」中焦躁不安,理論界不斷地搬弄著諸如後現代、後殖民、新歷史、新批評、法蘭克福學派等等西方話語,進行生硬的移植與命名;創作界則是模仿成風,似乎每個成名的作家都必須有個國外的精神導師才能心安理得。宗仁發在評價「七○年代人」的創作時說了一席話,他認為他們「生不逢時」,在各種文學觀念粉墨登場,輪番轟炸二十年以後,他們的出場面臨著雙重疲憊,一重是模仿的疲憊,現在誰再模仿卡夫卡、瑪律克斯、加繆、博爾赫斯,誰就會被喝倒采,但八○年代這類模仿是被人們誇讚的。連卡爾維諾、巴塞爾姆也模仿不得,前面也有人仿過了,「七○年代人」已喪失了「第一模仿權」。另一重疲憊是他們也不能緊跟與他們年齡相近的那些作家 。這段話反映出九○年代作家原創性的匱乏。當文學觀念、形式甚至是細節描寫都被籠罩在「模仿」的陰影之下時,九○年代的作品還能貼切地反映中國本土活生生的現實嗎?
九○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學就表面看來,充溢著過剩的「時間意識」與「現實精神」。新寫實的審美品格在後起的新生代作家的筆下,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只是在那種「無可奈何」的認同中摻雜了一點「玩世不恭」,而以劉醒龍、談歌、何申、關仁山、周梅森等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在把最初的那點真誠消耗之後,逐漸地把「騎牆」的功夫煉得爐火純青。還有那些曇花一現的「新體驗」、「新新聞」、「新狀態」、「新移民」小說,在文學的體式上都偏重寫實甚至具有紀實品格,但在骨子裡卻充滿了一種游離於現實之外的草率與輕浮。隨著文化市場的逐步擴張,文學消費與消費文學成為制約作家自由創作的重要因素,商業化敘事大行其道,「現實」與「真實」也開始成為作家出售的一種精神商品,而且還是贗品。因此,九○年代文學中充斥著的是「偽時間意識」與「偽現實精神」,這些貌似敏感的時間判斷與現實關懷遮蔽了真相。當贗品廣為流行時,真品反而要被淘汰,價值不高的物品將價值較高的物品擠出了流通領域,這就是經濟領域的「格雷欣法則」,國內許多商家在假冒偽劣產品的圍困下倒閉的例證可謂比比皆是,九○年代思想界的境遇與此不無相似之處。
九○年代文學界從不缺乏奇談怪論,最缺乏的偏偏是常識。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問題》中說:「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作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乏想像力。」王小波的意義正在於他說出了眾人皆知但許多人不屑說或不願說的常識。其實,當很多新潮文學家沉迷於「新」與「後」的遊戲時,甘於寂寞的人們只要稍稍關注「舊」與「前」的問題,便會發現常識的沉重。比如,「五四」一代的現代性籲求和啟蒙任務,他們所宣導的科學和民主精神,在九○年代依然處於未完成狀態。對個性與自由的嚮往成了折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創傷。很多被命名家們吹得神乎其神的新現象,其實是老問題遇到了新情況。漫長的封建歷史所投下的現實陰影,常常改頭換面地出現在各種各樣的新舞臺。而廣大的中國農村的「前現代」現實,在許多所謂的思想家眼裡遠不如一個舶來的術語來得重要。我們在繼承歷史遺產的同時,也必須承擔歷史賦予的責任,割斷歷史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文化逃避。九○年代不僅要背負八○年代的精神舊帳,還必須承擔從二十世紀上溯到整個五千年文明的歷史連續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認清自己的歷史處境與歷史任務。
二、困難的個人
將九○年代命名為「個人化時代」或「個體文化時代」,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時尚。這種觀點認為作為群體時代或非個人化時代的八○年代存在一系列文化範式或共同的話語系統,儘管社會的外部形態在八○年代中後期出現了個人化的萌芽,但話語指向仍然聚斂和集束於人道主義關懷、文化啟蒙等共同目標。也就是說,發揮統攝性作用的仍然是中國傳統體制之下的以長老、家國為中心的的文化形態。而九○年代則是一個價值多元、文化失範的年代,中心崩潰,傳統離析,呈現出零散化、拼貼化的混亂狀態,個人性正是在碎片化的縫隙中逐漸確立,文化形態也就在市場經濟的助推之下順理成章地過渡為以個體為本位的文化。如果說把八○年代概括為群體主義時代還算差強人意的話,將九○年代命名為「個人化時代」就只能是牽強附會了。九○年代在表象層次上確實呈現出零散化、拼貼化的混亂,市場經濟將個體從舊有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政治權力話語相對有所削弱,價值取向也從大一統的轄制中游離出來,但統攝八○年代的文化邏輯依然存在,其新變是逐漸潛化,變得更加隱蔽和複雜,滲透進盤根錯節的文化根系。商業主義、技術主義話語的喧嘩並沒有摧毀原有的價值體系,它們的抛頭露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為之提供了一種掩護。新舊雜陳的狀態並非毫無秩序,準確而言,這是一種層積格局,新觀念漂浮於舊觀念之上,前者的現實化必須依賴後者的作用機制的運轉。「權威主義」、「非理性」、「缺少對科學的尊重」、「迷信盛行」、「缺少積累精神」等文化幽靈成了阻礙社會的現代化和人格的個體化的人文因素 。這種傳統心態的影響之所以頑強有力,原因就在於這種觀念是在歷史上形成的,來自於過去的經驗,並成為一種心理的力量。雖然過去的經驗和環境已經有了變化,但這種心態仍然保存下來。「一個社會與其過去的紐帶關係永遠不可能完全斷裂,如果不在某種最小的程度上存在這種紐帶,一個社會就不成其為社會了。」 而且,商業在釋放解放個人的力量時,也滾動著削磨個人性的圓形刀片,這使從「文革」重軛下匍匐出來的人們在還沒伸直脊樑時就被納入另一種控制,文化轉型的撕扯把個性覺醒的過程推入進退維艱的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