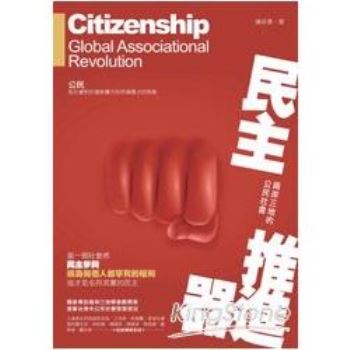西方學者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說:「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眾所皆知,政府制度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和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美國學者策略大師麥可‧波特認為現在政府要實施的優先政策太多,無法同時推進這些效率;而適宜的政府政策和優先順序隨著國家本身的變化而變化;且國際局勢也在變化。在這些複雜性的前提下,政府應努力思考如何讓政府運作既可減少失靈,又能提高行政效率,爭取人民的支持,以因應環境的變遷與挑戰。
政府必須在政策上與制度上為公民社會建構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使民間組織能夠健康發展,才能讓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反之,政府如果仍然因循苟且,無法體認環境的現實與人民的需求,仍採取靜態治理模式去治理國家與社會,不僅將錯失在兩岸三地競爭的優勢,甚至可能被超越,影響國家整體的發展與國際競爭力。
首先,建構完善的法規環境。台灣於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後,民間組織發揮極大的組織力與動員力,自動自發投入救災行動,讓政府與國際有目共睹,但現行人民團體法仍有太多行政管制,影響民間組織的發展。像鄰國日本於1995年發生阪神大地震後,短短三年的時間制定相關法規與制度,於1998年通過《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以鼓勵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但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已逾十年,政府的法規仍然在原地踏步,未積極檢討研修不合時宜之法規。因此,政府必須全面檢視人民團體法等相關法規,將不符合時勢潮流與社會環境的需要,予以大幅鬆綁或簡化,使之與時俱進。
甚至制定《非營利組織促進法》或《社會團體法》或《結社法》作為人民結社之基本法,以取代具有濃厚「戒嚴時期」色彩的《人民團體法》,讓結社朝簡易、公開、透明、自主等。同時讓職業團體依其各別法規運作,將政黨及政治團體納入《政黨法》中規範,並在稅法上予以立案團體賦稅上的優惠,為社會注入新氣象,以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此外,台灣社會欠缺捐款風氣,導致非營利組織要進行募款相當困難,不利團體的健全發展。民國95年公布施行的《公益勸募條例》雖填補了這個問題,但該法在歷經幾次重大天然災害,對於勸募團體的募款管理機制是否已經出現漏洞或缺陷,有能力募款之團體寥寥可數,絕大多數團體均募不到款,僅集中在極少數的團體,造成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應即檢討修法之必要。
此外,為協助非營利組織健全發展,應讓非營利組織資訊公開及財務透明,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鼓勵企業與社會大眾捐贈,稅法上的優惠與減免亦應配合檢討放寬。
其次,成立專責單位,統一事權。依人民團體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受到戒嚴的影響,人民組織團體受到嚴重的抑制,非經政府許可不得成立,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解嚴前全國社會團體僅七百多個,在團體數與業務量少之前提下,在中央主管機關並未成立一個專責單位負責承辦該項業務。而將其置於主管社會福利的社會司下分科辦事,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更是以兼辦人力辦理該項業務。但解嚴後,人民團體數量呈現45度仰角成長,從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短短20幾年間臺灣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團體發展,自民國76年解嚴的1萬多個發展到102年4.1萬多個,20幾年間成長約4倍。
若從地方政府所轄地方性社會團體數觀之,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從民國68年的3265個至民國101年的2.9萬個,地方性社會團體成長近10倍;若就中央政府所轄全國性社會團體數來看,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66年的486個發展至民國76年解嚴前的734個,成長近一倍,而從民國76年解嚴後至民國102年6月底全國性社會團體數為1.1萬多個,約佔全國社會團體總數的三分之一,成長高達15倍之多,尤其是全國性社會團體從民國97年起每年更以近七百個社團申請成立,顯示人民籌組全國性社會團體,提升組織層級,擴大組織範圍,強化組織影響力的意願高於地方性社會團體。這可從民國100年及101年全國性社會團體申請設立更連續兩年突破一千個,這些不僅僅是數字的變化而已,進一步言,實肇於台灣實施政治民主的一種體現,加以社會開放、自由、多元發展、經濟水平提高及教育普及等因素下加速催化此一民主成果,顯示在政治民主及社會開放下台灣人民對結社的重視與需求,深具意義。
民間團體的蓬勃發展,在型態上也呈現多元化與多角化,但依序仍以社會慈善類、學術文化類、經濟類、宗教類、醫療衛生類、體育類等六大類為最,約佔九成。社會團體不僅蓬勃發展,其對社會的影響力與功能也與日俱增,正所謂質與量的增加,意指團體影響力不斷的增加,相對的政府管理弧度亦為之擴大。但作者研究發現,政府並未在政策或制度上適時調整,以符合時代潮流及回應民間的需求。
而值政府組織改造,政策上政府雖已決定在行政院內政部下設立一個專責單位,惟名稱上卻捨「公民社會司」或第三部門司」或「民間組織司」或「民間團體司」或「社會組織司」或「社會發展司」等,既宏觀也符合國際潮流的治理單位,而就「合作及人民團體司」此一狹隘格局的名稱,殊為可惜!(目前大陸是於國務院民政部下設立「民間組織管理局」統一管理事權)並將目前分散在中央各個部會為主管機關的財團法人(指基金會)業務予以納入該新成立單位輔導管理,以收事權統一之效。畢竟基金會之業務在中央各部會大多數係依附在機關內部的某一單位兼辦,這樣的安排,顯非妥適!
第三,培養專業人力,理論與實務並重。如前述,政府並不重視民間組織蓬勃發展的事實,加上非營利組織在台灣社會無法像西方發達國家蔚為一個就業市場,以至無法獲得學術教育機構的響應,培訓專業知識與人力,導致非營利組織不僅欠缺專業人力,在工作不穩定,待遇少,又無相關福利保障下,雖然民國98年5月1日起,人民團體之工作人員適動基準法,看似多了一些保障,其實是不夠與不足的,故工作人員的流失率偏高,導致民間組織出現諸多會(業)務運作上的問題,影響團體的發展與和譪;反觀,在政府機關內部負責的人員儘管累積豐厚的實務經驗,惟專業知識不足,在組織內部又被邊緣化,無視業務與人力配置的不當,影響政府行政效率,而組織成員欠缺政策規劃能力與不具宏觀的視界,難以提高服務品質及政府形象,不利於公民社會的發展。
第四,培養公民性,建立合作與互補關係。公民社會是各種人際關係、團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它與國家及市場的關係的一種集合,這些皆屬外顯方面。然而,這些關係所賴以建立的價值,主要藉由內在的培養所促成的,這個內在的英文Civility被譯為「公民性」、「公民習性」或「公民精神」,主要包括兩個意義,一是指個人的修養。二是指社會集體的價值。它的內涵是由日常中培養的禮讓習慣擴及為共同的集體自我意識。在這方面作者觀察到台灣社會雖然已經實施政治民主二十多年,社會開放並朝多元發展,但民眾對於民主的素養並未隨之提升,尤其對於「自由」的真諦,更常被輿論形容為自由過度,缺乏自律,還好台灣社會是一個「感性大於理性」的社會。是以,並未對社會構成嚴重的威脅與影響。至於香港受殖民因素的影響,較具國際化,公民性也較強;大陸由於長期受到中央集權統制的影響,加上教育並不普及,公民性的培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公民社會的目標之一是改變現代社會權力結構,促進窮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福利的增進,並非為對抗政府與企業。公民社會的發展需要政府的重視與一套健全的法規制度,使非營利組織得以健全發展。少了這項關鍵因素,公民社會將不可能實現。無論如何,具有主體性的公民與倡導性的多元化公民社會組織,如能與國家與企業建立獨立而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是公民社會發展的目的和方向,也是讓國家走向強盛與文明之鑰。
政府必須在政策上與制度上為公民社會建構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使民間組織能夠健康發展,才能讓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反之,政府如果仍然因循苟且,無法體認環境的現實與人民的需求,仍採取靜態治理模式去治理國家與社會,不僅將錯失在兩岸三地競爭的優勢,甚至可能被超越,影響國家整體的發展與國際競爭力。
首先,建構完善的法規環境。台灣於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後,民間組織發揮極大的組織力與動員力,自動自發投入救災行動,讓政府與國際有目共睹,但現行人民團體法仍有太多行政管制,影響民間組織的發展。像鄰國日本於1995年發生阪神大地震後,短短三年的時間制定相關法規與制度,於1998年通過《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以鼓勵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但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已逾十年,政府的法規仍然在原地踏步,未積極檢討研修不合時宜之法規。因此,政府必須全面檢視人民團體法等相關法規,將不符合時勢潮流與社會環境的需要,予以大幅鬆綁或簡化,使之與時俱進。
甚至制定《非營利組織促進法》或《社會團體法》或《結社法》作為人民結社之基本法,以取代具有濃厚「戒嚴時期」色彩的《人民團體法》,讓結社朝簡易、公開、透明、自主等。同時讓職業團體依其各別法規運作,將政黨及政治團體納入《政黨法》中規範,並在稅法上予以立案團體賦稅上的優惠,為社會注入新氣象,以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此外,台灣社會欠缺捐款風氣,導致非營利組織要進行募款相當困難,不利團體的健全發展。民國95年公布施行的《公益勸募條例》雖填補了這個問題,但該法在歷經幾次重大天然災害,對於勸募團體的募款管理機制是否已經出現漏洞或缺陷,有能力募款之團體寥寥可數,絕大多數團體均募不到款,僅集中在極少數的團體,造成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應即檢討修法之必要。
此外,為協助非營利組織健全發展,應讓非營利組織資訊公開及財務透明,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鼓勵企業與社會大眾捐贈,稅法上的優惠與減免亦應配合檢討放寬。
其次,成立專責單位,統一事權。依人民團體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受到戒嚴的影響,人民組織團體受到嚴重的抑制,非經政府許可不得成立,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解嚴前全國社會團體僅七百多個,在團體數與業務量少之前提下,在中央主管機關並未成立一個專責單位負責承辦該項業務。而將其置於主管社會福利的社會司下分科辦事,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更是以兼辦人力辦理該項業務。但解嚴後,人民團體數量呈現45度仰角成長,從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短短20幾年間臺灣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團體發展,自民國76年解嚴的1萬多個發展到102年4.1萬多個,20幾年間成長約4倍。
若從地方政府所轄地方性社會團體數觀之,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從民國68年的3265個至民國101年的2.9萬個,地方性社會團體成長近10倍;若就中央政府所轄全國性社會團體數來看,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66年的486個發展至民國76年解嚴前的734個,成長近一倍,而從民國76年解嚴後至民國102年6月底全國性社會團體數為1.1萬多個,約佔全國社會團體總數的三分之一,成長高達15倍之多,尤其是全國性社會團體從民國97年起每年更以近七百個社團申請成立,顯示人民籌組全國性社會團體,提升組織層級,擴大組織範圍,強化組織影響力的意願高於地方性社會團體。這可從民國100年及101年全國性社會團體申請設立更連續兩年突破一千個,這些不僅僅是數字的變化而已,進一步言,實肇於台灣實施政治民主的一種體現,加以社會開放、自由、多元發展、經濟水平提高及教育普及等因素下加速催化此一民主成果,顯示在政治民主及社會開放下台灣人民對結社的重視與需求,深具意義。
民間團體的蓬勃發展,在型態上也呈現多元化與多角化,但依序仍以社會慈善類、學術文化類、經濟類、宗教類、醫療衛生類、體育類等六大類為最,約佔九成。社會團體不僅蓬勃發展,其對社會的影響力與功能也與日俱增,正所謂質與量的增加,意指團體影響力不斷的增加,相對的政府管理弧度亦為之擴大。但作者研究發現,政府並未在政策或制度上適時調整,以符合時代潮流及回應民間的需求。
而值政府組織改造,政策上政府雖已決定在行政院內政部下設立一個專責單位,惟名稱上卻捨「公民社會司」或第三部門司」或「民間組織司」或「民間團體司」或「社會組織司」或「社會發展司」等,既宏觀也符合國際潮流的治理單位,而就「合作及人民團體司」此一狹隘格局的名稱,殊為可惜!(目前大陸是於國務院民政部下設立「民間組織管理局」統一管理事權)並將目前分散在中央各個部會為主管機關的財團法人(指基金會)業務予以納入該新成立單位輔導管理,以收事權統一之效。畢竟基金會之業務在中央各部會大多數係依附在機關內部的某一單位兼辦,這樣的安排,顯非妥適!
第三,培養專業人力,理論與實務並重。如前述,政府並不重視民間組織蓬勃發展的事實,加上非營利組織在台灣社會無法像西方發達國家蔚為一個就業市場,以至無法獲得學術教育機構的響應,培訓專業知識與人力,導致非營利組織不僅欠缺專業人力,在工作不穩定,待遇少,又無相關福利保障下,雖然民國98年5月1日起,人民團體之工作人員適動基準法,看似多了一些保障,其實是不夠與不足的,故工作人員的流失率偏高,導致民間組織出現諸多會(業)務運作上的問題,影響團體的發展與和譪;反觀,在政府機關內部負責的人員儘管累積豐厚的實務經驗,惟專業知識不足,在組織內部又被邊緣化,無視業務與人力配置的不當,影響政府行政效率,而組織成員欠缺政策規劃能力與不具宏觀的視界,難以提高服務品質及政府形象,不利於公民社會的發展。
第四,培養公民性,建立合作與互補關係。公民社會是各種人際關係、團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它與國家及市場的關係的一種集合,這些皆屬外顯方面。然而,這些關係所賴以建立的價值,主要藉由內在的培養所促成的,這個內在的英文Civility被譯為「公民性」、「公民習性」或「公民精神」,主要包括兩個意義,一是指個人的修養。二是指社會集體的價值。它的內涵是由日常中培養的禮讓習慣擴及為共同的集體自我意識。在這方面作者觀察到台灣社會雖然已經實施政治民主二十多年,社會開放並朝多元發展,但民眾對於民主的素養並未隨之提升,尤其對於「自由」的真諦,更常被輿論形容為自由過度,缺乏自律,還好台灣社會是一個「感性大於理性」的社會。是以,並未對社會構成嚴重的威脅與影響。至於香港受殖民因素的影響,較具國際化,公民性也較強;大陸由於長期受到中央集權統制的影響,加上教育並不普及,公民性的培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公民社會的目標之一是改變現代社會權力結構,促進窮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福利的增進,並非為對抗政府與企業。公民社會的發展需要政府的重視與一套健全的法規制度,使非營利組織得以健全發展。少了這項關鍵因素,公民社會將不可能實現。無論如何,具有主體性的公民與倡導性的多元化公民社會組織,如能與國家與企業建立獨立而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是公民社會發展的目的和方向,也是讓國家走向強盛與文明之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