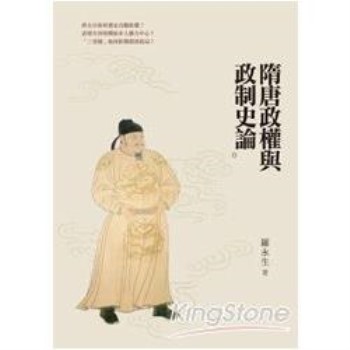〈小結:武則天參政的背景〉
按照舊史說法,武則天的得勢,或者可以分為幾個階段:首階段起始是如《唐會要》卷三所記:顯慶五年十月,上苦風眩,表奏時令皇后詳決,自此參預朝政幾三十年,當時畏威,稱為二聖。
這裡所記,與《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所記,「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並不完全相同。
從前者所記高宗不適時間與武后參政日子長短均較確切一點來看,應較後者更接近原始記錄。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後者所記中,多苦風疾的「多」,皆委天后的「皆」,可能是為後人妄加的斷語,《新唐書‧則天皇后紀》便沿襲了「多苦風疾」一句,但述及奏事時,則謂「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較接近《唐會要》記錄。另外,《資治通鑑》的記錄則作:「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言外之意,亦是高宗長期有風眩。考慮到《通鑑》的書法,所謂「目不能視」四字,或有可能不是一手史料,而是司馬光根據某些已經失傳記載的加筆。事實上,就史料所見,除了臨終時之前的一段時期外,高宗小病記錄,只有咸亨四年(六七三年)八月一次,當時高宗患了瘧疾,「令太子弘於延福殿內受諸司啟事」,這樣或可理解為高宗身體狀況並不太差。另外,高宗曾在乾封二年(六六七年)九月和永隆二年(六八四年)閏七月,兩次以服餌為原因,令皇太子監國,不過時間相信十分短。另外,咸亨二年(六七一年)正月因幸東都,儀鳳四年(六七九年)五月因不明原因,均分令太子賢國。
總之,武后得以參政,與其如舊史說是因高宗長期不適,以至不得不倚靠武后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因高宗健康出現毛病,而使武后偶然得到的參政機會,似更為妥當。
武則天邁向權力中心的另一步,與誅上官儀事可以說有密切關係。《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上元二年三月條的說法是:「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
《新唐書》卷一百五〈上官儀傳〉更云:「由是天下之政歸於武后,而帝手矣。」
根據這裡的說法,上官儀是個忠臣,他的失勢由始至終均與武后有關。首先是武后好道術,上官儀建議廢后,後來是武后訴冤,高宗後悔,反指是上官儀教唆,最後是武后通過許敬宗下毒手。不過《舊唐書》卷八十〈上官儀傳〉卻完全沒有提到武后,只說上官儀貴顯後,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結果被許敬宗冤枉他與梁王忠有陰謀,下獄而死,兩處所記,頗有差異。
《資治通鑑》則採納了《新唐書》所記。
參《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所記,此事當出於國史,並非來於私史小說。
從武后日後所為來看,可以肯定道士出入後宮是應有其事,而高宗因這事而大怒以致廢后,亦是可以理解。因為厭勝之術是古代社會不容許的行為,武則天當年便曾以這個理由打擊王皇后而引起後宮鬥爭,故此這次武后亦知事情不妙,不得不向高宗「申訴」,亦即「解釋求情」之意。不過新書上官儀傳所載另一個廢后的原因,即「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則可能是歐陽修無甚根據的猜測和加筆,而《資治通鑑》所記武后「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作為,動為后所制」,無非是把《新書》所述傳抄和進一步引申。高宗一時衝動,聽了上官儀之言,有意廢后,但冷靜下來,再加上武后的「感情牌」,最終反悔,亦不為奇。
事實上,上官儀在與高宗的密議中,大概有如《新唐書》本傳中所記,提出過廢后之議,但他是否說過「皇后專恣,海內失望」一類的話,多少有保留之處。《舊唐書》本傳記他恃才任勢,並不似是虛言,上官儀以文才自恃,與老一輩的才子許敬宗有所不和,並不難想像。他之所以膽敢向高宗建廢后之議,或可能是出於他的私心,希望藉此可以打擊和他同任宰相的許敬宗一派。而《冊府元龜》的記錄並未提及武后是許敬宗陷害上官儀的後台,但不管如何,從上官儀的失勢確實牽涉到一大班官員下台,這不是一場後宮鬥爭的延續,而是另一場朝廷掌權者的政治角力。
由此看來,與其說武后是上官儀事件中的主角,不如說她尋找了一個政爭的藉口和理由,似更為接近事實。她的皇后寶座一度岌岌可危的經歷,相信是令她以後更積極參與前台政治的原因。誅上官儀事在麟德元年(六六四年),換言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自顯慶以後到麟德以前的武則天,仍然未有「政事大小皆預聞之」的能耐,但誅上官儀後,她積極參預政事,經過約十年的歷練後,武則天先取得了「天后」封號,續而與高宗並稱「二聖」。如前引《唐會要》卷三和《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中的「當時」都沒有明記日期,但《新唐書》紀則有更詳盡說法:「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謂之『二聖』。」
應該指出,「二聖」稱號的出現,並不是高宗與則天所首創發明的,隋文帝與獨孤皇后便是先例。《隋書》卷三十六〈后妃傳〉便稱「(獨孤)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
《隋書》只謂「宮中」,而武則天的記錄則謂「內外」以至「天下之人」,事實大概亦是名號先流傳宮中,再由宮人傳出廷外。我們不能確定二聖稱號是褒詞又或貶詞,但考慮到公開對皇族不敬的可能性並不太高的因素,這個稱呼背後的意義或可不言而喻。
如果說武則天積極參政是她本身個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而出現的話,則其中一個客觀條件,無疑是李氏皇室的健康。不過論者每多提及高宗,而少顧及他的兒子。前面曾記咸亨四年高宗不豫時太子曾受諸司啟事,但太子身體比父親似乎更壞,他的肺癆病早在咸亨二年已令他在京師監國時不能親問政事,四年後更一病嗚呼。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武則天得到機會發揮她的本領。
李氏皇室的健康,或許是武則天積極參政的誘因,但並不能說是決定性因素。武后能夠成為二聖,實在主要是拜李治之賜。武則天吸引李治之處,相信是感性多於理性。我們知道武氏入宮後不久即懷了高宗骨肉,卻沒有明顯地方看出這時她可以有甚麼機會表現她的治國能力。高宗發現武氏具備這方潛質,相信大概是在武氏有機會實際決定奏事以後,亦即是說,在顯慶末年又或麟德元年上官儀事件發生後。當時高宗已經當了皇帝十多年,雖然不能說他已經疲乏以至厭倦,但如果說沒有初登位時一般積極,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龍朔三年(六六三年)二月,他雖然親自重審死囚,但卻出現了「不盡者令皇太子錄之」的現象。
同年十月,他又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
這些都是給予皇太子熟習政事的機會,所以其他皇子沒有份兒。但咸亨二年六月,高宗在洛陽以旱親錄囚徒時,又出現令兒子李賢和李顯分慮諸司和洛州及兩縣囚的情形,這當然不能用以作為高宗疏於政事的證據,不過若認為類似的情形間中會出現在朝廷中,即武則天和諸皇子在慮囚事上一樣,擔起輔助甚或更重要角色,是完全可能的。就目前的記載所見,高宗直至去世前一年,差不多每年均有巡幸,可知身體並不太壞。要解釋武則天的積極參政,以高宗的健康為唯一理由,顯然說服力不足,必須同時注意到高宗的心態,始能找到較佳的解釋。
按照舊史說法,武則天的得勢,或者可以分為幾個階段:首階段起始是如《唐會要》卷三所記:顯慶五年十月,上苦風眩,表奏時令皇后詳決,自此參預朝政幾三十年,當時畏威,稱為二聖。
這裡所記,與《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所記,「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並不完全相同。
從前者所記高宗不適時間與武后參政日子長短均較確切一點來看,應較後者更接近原始記錄。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後者所記中,多苦風疾的「多」,皆委天后的「皆」,可能是為後人妄加的斷語,《新唐書‧則天皇后紀》便沿襲了「多苦風疾」一句,但述及奏事時,則謂「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較接近《唐會要》記錄。另外,《資治通鑑》的記錄則作:「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言外之意,亦是高宗長期有風眩。考慮到《通鑑》的書法,所謂「目不能視」四字,或有可能不是一手史料,而是司馬光根據某些已經失傳記載的加筆。事實上,就史料所見,除了臨終時之前的一段時期外,高宗小病記錄,只有咸亨四年(六七三年)八月一次,當時高宗患了瘧疾,「令太子弘於延福殿內受諸司啟事」,這樣或可理解為高宗身體狀況並不太差。另外,高宗曾在乾封二年(六六七年)九月和永隆二年(六八四年)閏七月,兩次以服餌為原因,令皇太子監國,不過時間相信十分短。另外,咸亨二年(六七一年)正月因幸東都,儀鳳四年(六七九年)五月因不明原因,均分令太子賢國。
總之,武后得以參政,與其如舊史說是因高宗長期不適,以至不得不倚靠武后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因高宗健康出現毛病,而使武后偶然得到的參政機會,似更為妥當。
武則天邁向權力中心的另一步,與誅上官儀事可以說有密切關係。《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上元二年三月條的說法是:「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
《新唐書》卷一百五〈上官儀傳〉更云:「由是天下之政歸於武后,而帝手矣。」
根據這裡的說法,上官儀是個忠臣,他的失勢由始至終均與武后有關。首先是武后好道術,上官儀建議廢后,後來是武后訴冤,高宗後悔,反指是上官儀教唆,最後是武后通過許敬宗下毒手。不過《舊唐書》卷八十〈上官儀傳〉卻完全沒有提到武后,只說上官儀貴顯後,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結果被許敬宗冤枉他與梁王忠有陰謀,下獄而死,兩處所記,頗有差異。
《資治通鑑》則採納了《新唐書》所記。
參《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所記,此事當出於國史,並非來於私史小說。
從武后日後所為來看,可以肯定道士出入後宮是應有其事,而高宗因這事而大怒以致廢后,亦是可以理解。因為厭勝之術是古代社會不容許的行為,武則天當年便曾以這個理由打擊王皇后而引起後宮鬥爭,故此這次武后亦知事情不妙,不得不向高宗「申訴」,亦即「解釋求情」之意。不過新書上官儀傳所載另一個廢后的原因,即「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則可能是歐陽修無甚根據的猜測和加筆,而《資治通鑑》所記武后「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作為,動為后所制」,無非是把《新書》所述傳抄和進一步引申。高宗一時衝動,聽了上官儀之言,有意廢后,但冷靜下來,再加上武后的「感情牌」,最終反悔,亦不為奇。
事實上,上官儀在與高宗的密議中,大概有如《新唐書》本傳中所記,提出過廢后之議,但他是否說過「皇后專恣,海內失望」一類的話,多少有保留之處。《舊唐書》本傳記他恃才任勢,並不似是虛言,上官儀以文才自恃,與老一輩的才子許敬宗有所不和,並不難想像。他之所以膽敢向高宗建廢后之議,或可能是出於他的私心,希望藉此可以打擊和他同任宰相的許敬宗一派。而《冊府元龜》的記錄並未提及武后是許敬宗陷害上官儀的後台,但不管如何,從上官儀的失勢確實牽涉到一大班官員下台,這不是一場後宮鬥爭的延續,而是另一場朝廷掌權者的政治角力。
由此看來,與其說武后是上官儀事件中的主角,不如說她尋找了一個政爭的藉口和理由,似更為接近事實。她的皇后寶座一度岌岌可危的經歷,相信是令她以後更積極參與前台政治的原因。誅上官儀事在麟德元年(六六四年),換言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自顯慶以後到麟德以前的武則天,仍然未有「政事大小皆預聞之」的能耐,但誅上官儀後,她積極參預政事,經過約十年的歷練後,武則天先取得了「天后」封號,續而與高宗並稱「二聖」。如前引《唐會要》卷三和《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中的「當時」都沒有明記日期,但《新唐書》紀則有更詳盡說法:「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謂之『二聖』。」
應該指出,「二聖」稱號的出現,並不是高宗與則天所首創發明的,隋文帝與獨孤皇后便是先例。《隋書》卷三十六〈后妃傳〉便稱「(獨孤)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
《隋書》只謂「宮中」,而武則天的記錄則謂「內外」以至「天下之人」,事實大概亦是名號先流傳宮中,再由宮人傳出廷外。我們不能確定二聖稱號是褒詞又或貶詞,但考慮到公開對皇族不敬的可能性並不太高的因素,這個稱呼背後的意義或可不言而喻。
如果說武則天積極參政是她本身個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而出現的話,則其中一個客觀條件,無疑是李氏皇室的健康。不過論者每多提及高宗,而少顧及他的兒子。前面曾記咸亨四年高宗不豫時太子曾受諸司啟事,但太子身體比父親似乎更壞,他的肺癆病早在咸亨二年已令他在京師監國時不能親問政事,四年後更一病嗚呼。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武則天得到機會發揮她的本領。
李氏皇室的健康,或許是武則天積極參政的誘因,但並不能說是決定性因素。武后能夠成為二聖,實在主要是拜李治之賜。武則天吸引李治之處,相信是感性多於理性。我們知道武氏入宮後不久即懷了高宗骨肉,卻沒有明顯地方看出這時她可以有甚麼機會表現她的治國能力。高宗發現武氏具備這方潛質,相信大概是在武氏有機會實際決定奏事以後,亦即是說,在顯慶末年又或麟德元年上官儀事件發生後。當時高宗已經當了皇帝十多年,雖然不能說他已經疲乏以至厭倦,但如果說沒有初登位時一般積極,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龍朔三年(六六三年)二月,他雖然親自重審死囚,但卻出現了「不盡者令皇太子錄之」的現象。
同年十月,他又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
這些都是給予皇太子熟習政事的機會,所以其他皇子沒有份兒。但咸亨二年六月,高宗在洛陽以旱親錄囚徒時,又出現令兒子李賢和李顯分慮諸司和洛州及兩縣囚的情形,這當然不能用以作為高宗疏於政事的證據,不過若認為類似的情形間中會出現在朝廷中,即武則天和諸皇子在慮囚事上一樣,擔起輔助甚或更重要角色,是完全可能的。就目前的記載所見,高宗直至去世前一年,差不多每年均有巡幸,可知身體並不太壞。要解釋武則天的積極參政,以高宗的健康為唯一理由,顯然說服力不足,必須同時注意到高宗的心態,始能找到較佳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