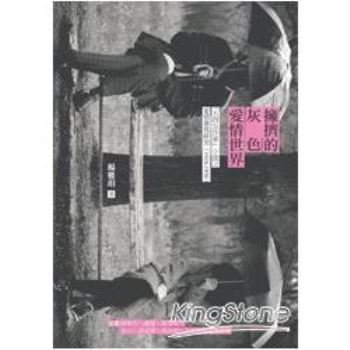一九八九年,孟悅、戴錦華在其「將社會學批評、符號學、結構主義?事學、讀者反應批評及解構批評結合在女性主義批評的大旗下」 的名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裡進行「中國現代女作家由『女性被講述』到『女性自述』的系譜」 的建構時,便曾肯定過五四女作家以「愛」作為時代旋律的文學價值。 無獨有偶,王德威也曾於〈被遺忘的繆思——五四及三、四○年代女作家鉤沈錄〉一文,特意指出五四女作家愛情書寫的特殊之處。
然而,儘管如此,海峽兩岸專題研究五四女作家小說愛情書寫者,其實並不多見。在相關出版著作方面,據筆者目前所見,只有兩本。一是陳碧月《大陸女性婚戀小說——五四時期與新時期的女性意識書寫》;其以小說中的愛情類型與女性人物形象為線索,比較五四女作家與新時期女作家的女性意識,然後指出:早期女作家「主要取材於親身見聞,從她們最容易投入的主題切入愛情、婚姻與家庭」,新時期女作家則眼界擴大,「已走向要求兩性平等對話的時代」。 此書雖有整理爬梳之功,但筆者認為其未能如范銘如所言善用愛情文學挖掘女性對兩性關係之審思與渴望 ,實為可惜。
陳碧月之外,另還有徐仲佳《性愛問題——一九二○年代中國小說的現代性闡釋》;該書以文化語境觀察二○年代小說,除闢有專節探究馮沅君等五四女作家小說中的「女性想像」外,並另以近三千字的篇幅深入討論廬隱(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一八九八至一九三四)小說「欲望與理性」之間的悖論,足見其對五四女作家愛情書寫的重視。 不過,其將「靈肉一致的現代性愛」視為一九二○年代性愛問題核心的作法,似乎可再加商榷。由書中所述來看,徐仲佳應是由現代性「包括對有限的身體時間自足性的認同」,進而由「現代性愛思潮第一次發現了人的身體和慾望,為它們尋找到合法的存在性」,導出「現代性愛追求靈肉一致」這樣的結論。 可是,事實上,根據現代性社會理論來看,現代性發現人的身體和慾望,並不等於必然開始追求靈肉一致,因為當身體成為「享用性的在世者」,最後也可能轉為「身體崇拜」,服膺起身體本然的原則,追求「單純的衝動和快樂或合意的自虐」。 社會學大師安東尼‧紀登思(Anthony Giddens,1938-)亦曾指出:生殖科技的精進,使得現代愛情雖然擁抱了「性」,卻也同時開始和「性」產生斷裂,因而產生「可塑的性」(plastic sexuality)。 如此看來,「現代性」恐怕未必一定會如徐仲佳書中所推論將驅使人們渴望「靈肉一致的性愛觀」。
然而,儘管如此,海峽兩岸專題研究五四女作家小說愛情書寫者,其實並不多見。在相關出版著作方面,據筆者目前所見,只有兩本。一是陳碧月《大陸女性婚戀小說——五四時期與新時期的女性意識書寫》;其以小說中的愛情類型與女性人物形象為線索,比較五四女作家與新時期女作家的女性意識,然後指出:早期女作家「主要取材於親身見聞,從她們最容易投入的主題切入愛情、婚姻與家庭」,新時期女作家則眼界擴大,「已走向要求兩性平等對話的時代」。 此書雖有整理爬梳之功,但筆者認為其未能如范銘如所言善用愛情文學挖掘女性對兩性關係之審思與渴望 ,實為可惜。
陳碧月之外,另還有徐仲佳《性愛問題——一九二○年代中國小說的現代性闡釋》;該書以文化語境觀察二○年代小說,除闢有專節探究馮沅君等五四女作家小說中的「女性想像」外,並另以近三千字的篇幅深入討論廬隱(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一八九八至一九三四)小說「欲望與理性」之間的悖論,足見其對五四女作家愛情書寫的重視。 不過,其將「靈肉一致的現代性愛」視為一九二○年代性愛問題核心的作法,似乎可再加商榷。由書中所述來看,徐仲佳應是由現代性「包括對有限的身體時間自足性的認同」,進而由「現代性愛思潮第一次發現了人的身體和慾望,為它們尋找到合法的存在性」,導出「現代性愛追求靈肉一致」這樣的結論。 可是,事實上,根據現代性社會理論來看,現代性發現人的身體和慾望,並不等於必然開始追求靈肉一致,因為當身體成為「享用性的在世者」,最後也可能轉為「身體崇拜」,服膺起身體本然的原則,追求「單純的衝動和快樂或合意的自虐」。 社會學大師安東尼‧紀登思(Anthony Giddens,1938-)亦曾指出:生殖科技的精進,使得現代愛情雖然擁抱了「性」,卻也同時開始和「性」產生斷裂,因而產生「可塑的性」(plastic sexuality)。 如此看來,「現代性」恐怕未必一定會如徐仲佳書中所推論將驅使人們渴望「靈肉一致的性愛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