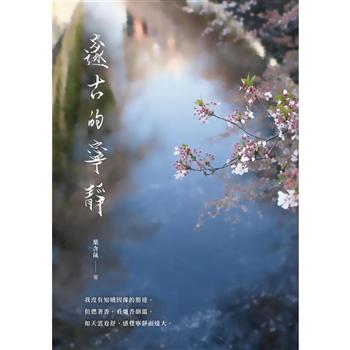【聽風】
有時走進寺廟,只是想聽一回風聲。
曾經為了某個景色,專程到某處,常常會有來早了,或來晚了之憾。慢慢的,了解到大自然瞬息萬變,總有太多意外,人不能強求,只能順受。
但聆聽風聲,四季皆宜,無時不佳。
一直很喜歡京都大原寶泉院,此院建於日本平安時期,是座小巧的傳統寺院建築。來這裡數回,有時晴日,有時雨雪。走進斑駁的院門,會先經過一段小徑。徑旁的花草雖不嚴整,但蔓生中有規矩,紛沓中有法度,頗有千利休所說的「如花在野」的意趣。「野」,有自然之意,它是萬物的本來面目。人愈接近自然,也會與大地調和得愈圓融。
寶泉院客殿處無門板相隔,木柱如畫框般圍繞著庭園。視線寬闊,又居處山間,於是遠方山巔林木也成了庭院一景,風可以帶著野氣恣意湧入。在沒有什麼遊客的早晨,坐在面向群山的紅色地毯上,可以閉上雙眼感覺空氣的流動。就算坐一整個上午,人去人來,也互不干擾。來者彷彿都有一個默契,就是安靜。
這裡宜聽風,宜賞雪,宜觀天,唯獨不宜與人語。安坐於室,內心毫無牽掛與懸念,一如庭前老松如如不動。
如果「靈氣」是有客觀型態可以辨識,那麼我覺得此地是大原最有靈氣的地方。單單是坐著,也能感覺內心清淨盈滿。
東方美學有一種審美意識,稱為「素」,是保持素樸,沒有雜質的本真。它的核心是信任,信任自然,也深諳「變」的道理。知道世間所有的物質都會改變,於是不擋不競也不拒。這樣順應自然的「素」,讓寶泉院的椽木門扉即便遭受風化雨蝕,也是美麗萬分。那是因為經過時間的催化,所產生的閑靜寂寞。
是的,在寶泉院我所感覺到的就是「閑靜寂寞」。這裡的「寂寞」不是孤單冷清的意思,而是一種更深層的靜謐與出離。像一大片的留白,那留白處是天地,是風雲,人在此中,如墨跡暈染,心神會向四周逐漸虛化而延伸,然後,物我相融。那洪荒以來的古老光芒,也會一寸寸地收攝到身體裡。
風,就是這個過程的媒介。它是自然界最原始的樣貌,人類文明無法為它設色刻畫,但它又是一個豐饒的存在。不知它在何處生成,在何地消滅。聽風的時候,其實是對天地的一種敬仰,一種歸順。它帶來時間的流動,帶來萬物的生死,帶來草木的變化。秋去冬來,日升月落,於是大地有流動,有沉積。聽這山間野風,也許帶著溽暑的水氣,也許含藏著朝陽升起時的混沌,也許是大雪來前的呼嘯,也許是款步徐徐的謙遜。身體感覺著風的姿態與氣味,心神同時也正走向通往太古的捷徑。
我無法與人訴說這種很幽微的經驗,如同玻璃杯盛著清涼的水,不劇烈,也不炫耀,安詳與愉悅在心底流盪。
每次走出院門,都會再望一眼院裡巍峨的五葉松,心下總捨不得離開這樣的閑寂。很羨慕那棵老松,靜靜地在這裡聽風,聽了七百年。
【靈隱印象】
在杭州時,有天從市區搭公車到岳王廟。那時車上人多,沒座位,我面朝車窗站著,手扶在前方椅子上的握把。大概十分鐘後,公車轉往西湖北山路,突然有人拍拍我的手臂,我以為我站的地方影響到別人了,連忙轉頭看,看到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先生,坐在我左前方的椅子上,他客氣且驚喜地問:「姑娘,這就是西湖啊?」
我看著窗外,遠處是優美的斷橋白堤。那時我到杭州已數天,連看了幾日湖景,很確定地對他說:「是啊!」。
那老先生接著問:「我要到靈隱寺,還要幾站?」
我:「還要好一會兒呢!最後一站才是靈隱。」
他:「還很久喔。我要到靈隱寺還願......我年輕時來過杭州的,現在都不一樣了。」
他將那「還願」二字說得清楚而篤定。說完又轉頭新奇地望向窗外湖景。
他一路忐忑,唯恐坐過站似的,沒多久就站起來看貼在座位上方的路線圖。而我是到杭州的第二天就去過靈隱寺了。
我去靈隱寺那天,下著大雨。靈隱寺在西湖北面的山間,在中國佛教寺廟中,可說是香火鼎盛的前幾名。進入靈隱寺前,會經過飛來峰,這是一段綿延數百公尺的佛像石刻群,雕刻的年代大約是五代至元朝。雖然很多佛像的面目神態都已漫漶不清,但不難看出這片石雕同時呈現漢藏兩地的佛教信仰。
因為連日雨,山間溪水洪波滾滾,飛來峰的階梯也溼滑,遊人走到石窟區的並不多。這樣的天氣,顯然不是出遊的好時機,但來之安之,人在旅途,很多事掌握不了,只能順從。也唯有順從,才能心平氣和。卻也因為這場雨,才讓我看見褪盡塵染的新綠青山,還有清澈潤澤的花樹碧草。而走過這段石刻佛像的小徑,就到了靈隱寺。
我買了門票入寺,在門口有工作人員給了三柱供佛的線香。其實撐著傘,又拿著香,既忙亂又侷促,恨不得能向觀音借幾隻手,還好進門不遠處就有個大香爐,我穿越人群將這三支香對著大殿,對著蒼天囫圇一拜,然後擲入爐中。用「擲」雖有失禮之虞,但實在是因為香客太多,爐中滿滿的線香,若要伸手妥善地放入,一定會被燙出幾個香疤。
這樣的天氣,遊人還這樣多,大概也只有靈隱寺了。杭州的寺廟大多建於東晉時期,靈隱寺也不例外,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歷史,算得上是這片山林中最古老的佛寺。這座寺廟之所以聞名遐邇,大概是南宋時高僧濟公曾在此地剃度修行,再加上稗官野史與電視劇的推波助瀾,造成此地聲名深植於市井百姓間,以致長年香客絡繹。
其實不只是濟公,北宋時的蘇東坡也常到這裡,他與寺中僧眾皆友好。如今寺廟門前有個「壑雷亭」,其典故就是源自東坡詩句「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這壑雷亭屹立在寺門前的溪邊,那幾日梅雨淅瀝,坐在亭中見那浩浩湯湯的溪水從巖壑中流逝,果真聲如雷吼,狀如電奔。
靈隱寺占地深廣,建築閎麗,有江南的雅緻,也有北地的磅礴。這裡是我走過的中國寺廟中佛像最多的一座,其中有間殿堂矗立著五百尊身形高大的羅漢,人走在其間,會有一種被神佛環伺的緊迫感,成了名副其實的舉頭三尺有神明,當然,在如此莊嚴懾人的環境中,心念也自覺地端正肅然,思無邪。
我在廣闊的寺廟裡悠悠轉轉,走到大雄寶殿、藥師殿,看人們合掌祝禱。又走過一面刻著觀音像的高牆,看見一位年輕的婦人跪在地上喃喃禱告。我仔細聽那婦人的禱詞,字字從心,句句懇切,都是為了求子。
忽覺得這裡彷彿積聚了千百年來無數人的希望,有的攸關家運順遂,有的希冀化險為夷,有的也許只是祈求個人安康。人們一邊向神佛交托了心願,一邊也生出面對困蹇的勇氣。在這塵世浮生,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摸索著萬般滋味扶繩而走。
而那日在公車上遇到的那位老先生,想必已走過當年許願時的惶惑不安。他說要去還願的心念,單一而明確。迢迢而來只是去道聲謝,圓一場天人之間的約定,這樣的情懷,多麼謙遜可貴。
【小喜】
小喜,見到我時總是喊我姐,說我長得像她的親姐姐。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她特別信任我。十年前認識她,她剛從北京嫁到台灣,跟著丈夫經營一家咖啡店。她來台灣三年,生了一個女娃,後來離婚,獨自回到北京。當中的原由我不便多問,只知道她離開台灣時,狀態並不好,像一朵枯萎的花。
前幾年我去北京,行程很緊湊,只有短暫的空檔。我其實不抱見面的希望與她聯繫,我說:「不要有壓力,沒有空也沒關係,只是想知道妳好不好。」
才剛說完,她馬上在電話裡回:「姐,妳都老遠來了,我一定能騰出空。妳說這話不是見外嗎?只是才三小時啊!去過景山了嗎?要不我帶妳去那兒逛逛。」小喜聲調高昂,像火箭似地迅速說完全部的話。
那天不是假日,見了面才知道,她是跟公司請了假出來的。
景山在故宮北邊,與神武門隔街對望。它在歷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大概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皇城,崇禎皇帝倉皇地從神武門逃出,在景山的一棵槐樹下自縊。如今那棵老槐樹已魂歸西天,取而代之的是一株年輕的樹,樹旁有一個紀念碑,寫著:「明思宗殉國處」。
在明朝為數不多的明君裡,崇禎是其中的一個。他像是一顆白子落到被黑子圍困的棋局裡,終究敵不過亡國的命運。我在碑前站了一會兒,看著「殉國」兩個字,彷彿看見四百年前,那個才三十三歲,卻已萬念俱灰的朱由檢。
我們沿著階梯上山,小喜說,剛回到北京,以為自己撐不下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窩在家裡,哪裡也不想去。如此過了半年,想想人生還長,為那樣一個人糟蹋自己多不值得?碰巧那時家人介紹了一個環境與待遇都不錯的工作,也與自己的本科相關,決定再試試。
我們一路走到半山腰,對向正好有一群遊客浩浩蕩蕩地下山,我跟小喜往邊沿靠,讓出路。我們靠邊時,小喜拉緊著我的手臂,擔心我沒站穩,同時低聲的在我耳邊說:「姐,我覺得我已經死過一次,但我現在挺好的,這是真的。如果沒有那時的辛苦,我不會體會到現在的尋常多麼不容易。」
小喜神態自若,語氣堅定,比起之前開朗許多。我不知跟她說什麼,心想,人對於一件事的釋懷,有時不是依賴時間的流逝,而是明白自己曾經發生了什麼。感情的事,外人總難置喙,但我知道那時她是有委屈的。
景山嚴格說來並不是「山」,它是近六百年由護城河的淤泥堆積起來的小丘。景山也不高,但高度正好可以俯瞰北京市。我們走到山頂涼亭,找到涼亭旁的中軸標記。這條無形的中軸線,將北京城分成東西兩邊。我在書裡看過梁思成先生說:「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產生的。」
其實,何止北京城有中軸,很多古老的城市都有一個中軸線。中軸是美的基點,是黃金分割,是形成一個城市流動的主要脈絡。它統攝對立與均衡,蘊含平等與尊重。若再往深處想去,這些意涵,不單是指城市規劃,也像一個人在面對世間人情時,秉持的那一道不偏不倚的脊梁。
從景山往下望,如曠野裡刮過一陣風,將氣勢磅礴的紫禁城如長卷般鋪展開來。紅牆明麗,黃瓦灼煥。這座宮殿,呼風喚雨六百年。而六百年歲月就這樣,說過去就過去了,不過就是一轉眼的工夫。
小喜帶著我沿著山上涼亭走了一圈,指著遠方說:鼓樓在哪兒、天壇在哪兒、北海在哪兒......。我望向遠方邊聽邊想,究竟是怎樣的領悟,讓她將昨日的深谷,換作今日的淡然;讓那些灼傷人心的,終成檣櫓灰飛煙滅?人的命運不也像歷史的規律,起伏有時,榮悴有時。甚至以為自己已走到山之窮水之盡,倏忽間又能峰迴路轉柳暗花明。
我沒有想到,能跟小喜在景山再見一面。當年她離開台灣時,傳短訊給我,我回她那句「後會有期」說得很心虛,因為知道再見的機會微乎其微。如今我想,人與人之間,如果分別之後又能重逢,那一定要珍重。
那天,我們沒有說將來,將來太虛渺,現在這樣就很好。
有時走進寺廟,只是想聽一回風聲。
曾經為了某個景色,專程到某處,常常會有來早了,或來晚了之憾。慢慢的,了解到大自然瞬息萬變,總有太多意外,人不能強求,只能順受。
但聆聽風聲,四季皆宜,無時不佳。
一直很喜歡京都大原寶泉院,此院建於日本平安時期,是座小巧的傳統寺院建築。來這裡數回,有時晴日,有時雨雪。走進斑駁的院門,會先經過一段小徑。徑旁的花草雖不嚴整,但蔓生中有規矩,紛沓中有法度,頗有千利休所說的「如花在野」的意趣。「野」,有自然之意,它是萬物的本來面目。人愈接近自然,也會與大地調和得愈圓融。
寶泉院客殿處無門板相隔,木柱如畫框般圍繞著庭園。視線寬闊,又居處山間,於是遠方山巔林木也成了庭院一景,風可以帶著野氣恣意湧入。在沒有什麼遊客的早晨,坐在面向群山的紅色地毯上,可以閉上雙眼感覺空氣的流動。就算坐一整個上午,人去人來,也互不干擾。來者彷彿都有一個默契,就是安靜。
這裡宜聽風,宜賞雪,宜觀天,唯獨不宜與人語。安坐於室,內心毫無牽掛與懸念,一如庭前老松如如不動。
如果「靈氣」是有客觀型態可以辨識,那麼我覺得此地是大原最有靈氣的地方。單單是坐著,也能感覺內心清淨盈滿。
東方美學有一種審美意識,稱為「素」,是保持素樸,沒有雜質的本真。它的核心是信任,信任自然,也深諳「變」的道理。知道世間所有的物質都會改變,於是不擋不競也不拒。這樣順應自然的「素」,讓寶泉院的椽木門扉即便遭受風化雨蝕,也是美麗萬分。那是因為經過時間的催化,所產生的閑靜寂寞。
是的,在寶泉院我所感覺到的就是「閑靜寂寞」。這裡的「寂寞」不是孤單冷清的意思,而是一種更深層的靜謐與出離。像一大片的留白,那留白處是天地,是風雲,人在此中,如墨跡暈染,心神會向四周逐漸虛化而延伸,然後,物我相融。那洪荒以來的古老光芒,也會一寸寸地收攝到身體裡。
風,就是這個過程的媒介。它是自然界最原始的樣貌,人類文明無法為它設色刻畫,但它又是一個豐饒的存在。不知它在何處生成,在何地消滅。聽風的時候,其實是對天地的一種敬仰,一種歸順。它帶來時間的流動,帶來萬物的生死,帶來草木的變化。秋去冬來,日升月落,於是大地有流動,有沉積。聽這山間野風,也許帶著溽暑的水氣,也許含藏著朝陽升起時的混沌,也許是大雪來前的呼嘯,也許是款步徐徐的謙遜。身體感覺著風的姿態與氣味,心神同時也正走向通往太古的捷徑。
我無法與人訴說這種很幽微的經驗,如同玻璃杯盛著清涼的水,不劇烈,也不炫耀,安詳與愉悅在心底流盪。
每次走出院門,都會再望一眼院裡巍峨的五葉松,心下總捨不得離開這樣的閑寂。很羨慕那棵老松,靜靜地在這裡聽風,聽了七百年。
【靈隱印象】
在杭州時,有天從市區搭公車到岳王廟。那時車上人多,沒座位,我面朝車窗站著,手扶在前方椅子上的握把。大概十分鐘後,公車轉往西湖北山路,突然有人拍拍我的手臂,我以為我站的地方影響到別人了,連忙轉頭看,看到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先生,坐在我左前方的椅子上,他客氣且驚喜地問:「姑娘,這就是西湖啊?」
我看著窗外,遠處是優美的斷橋白堤。那時我到杭州已數天,連看了幾日湖景,很確定地對他說:「是啊!」。
那老先生接著問:「我要到靈隱寺,還要幾站?」
我:「還要好一會兒呢!最後一站才是靈隱。」
他:「還很久喔。我要到靈隱寺還願......我年輕時來過杭州的,現在都不一樣了。」
他將那「還願」二字說得清楚而篤定。說完又轉頭新奇地望向窗外湖景。
他一路忐忑,唯恐坐過站似的,沒多久就站起來看貼在座位上方的路線圖。而我是到杭州的第二天就去過靈隱寺了。
我去靈隱寺那天,下著大雨。靈隱寺在西湖北面的山間,在中國佛教寺廟中,可說是香火鼎盛的前幾名。進入靈隱寺前,會經過飛來峰,這是一段綿延數百公尺的佛像石刻群,雕刻的年代大約是五代至元朝。雖然很多佛像的面目神態都已漫漶不清,但不難看出這片石雕同時呈現漢藏兩地的佛教信仰。
因為連日雨,山間溪水洪波滾滾,飛來峰的階梯也溼滑,遊人走到石窟區的並不多。這樣的天氣,顯然不是出遊的好時機,但來之安之,人在旅途,很多事掌握不了,只能順從。也唯有順從,才能心平氣和。卻也因為這場雨,才讓我看見褪盡塵染的新綠青山,還有清澈潤澤的花樹碧草。而走過這段石刻佛像的小徑,就到了靈隱寺。
我買了門票入寺,在門口有工作人員給了三柱供佛的線香。其實撐著傘,又拿著香,既忙亂又侷促,恨不得能向觀音借幾隻手,還好進門不遠處就有個大香爐,我穿越人群將這三支香對著大殿,對著蒼天囫圇一拜,然後擲入爐中。用「擲」雖有失禮之虞,但實在是因為香客太多,爐中滿滿的線香,若要伸手妥善地放入,一定會被燙出幾個香疤。
這樣的天氣,遊人還這樣多,大概也只有靈隱寺了。杭州的寺廟大多建於東晉時期,靈隱寺也不例外,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歷史,算得上是這片山林中最古老的佛寺。這座寺廟之所以聞名遐邇,大概是南宋時高僧濟公曾在此地剃度修行,再加上稗官野史與電視劇的推波助瀾,造成此地聲名深植於市井百姓間,以致長年香客絡繹。
其實不只是濟公,北宋時的蘇東坡也常到這裡,他與寺中僧眾皆友好。如今寺廟門前有個「壑雷亭」,其典故就是源自東坡詩句「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這壑雷亭屹立在寺門前的溪邊,那幾日梅雨淅瀝,坐在亭中見那浩浩湯湯的溪水從巖壑中流逝,果真聲如雷吼,狀如電奔。
靈隱寺占地深廣,建築閎麗,有江南的雅緻,也有北地的磅礴。這裡是我走過的中國寺廟中佛像最多的一座,其中有間殿堂矗立著五百尊身形高大的羅漢,人走在其間,會有一種被神佛環伺的緊迫感,成了名副其實的舉頭三尺有神明,當然,在如此莊嚴懾人的環境中,心念也自覺地端正肅然,思無邪。
我在廣闊的寺廟裡悠悠轉轉,走到大雄寶殿、藥師殿,看人們合掌祝禱。又走過一面刻著觀音像的高牆,看見一位年輕的婦人跪在地上喃喃禱告。我仔細聽那婦人的禱詞,字字從心,句句懇切,都是為了求子。
忽覺得這裡彷彿積聚了千百年來無數人的希望,有的攸關家運順遂,有的希冀化險為夷,有的也許只是祈求個人安康。人們一邊向神佛交托了心願,一邊也生出面對困蹇的勇氣。在這塵世浮生,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摸索著萬般滋味扶繩而走。
而那日在公車上遇到的那位老先生,想必已走過當年許願時的惶惑不安。他說要去還願的心念,單一而明確。迢迢而來只是去道聲謝,圓一場天人之間的約定,這樣的情懷,多麼謙遜可貴。
【小喜】
小喜,見到我時總是喊我姐,說我長得像她的親姐姐。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她特別信任我。十年前認識她,她剛從北京嫁到台灣,跟著丈夫經營一家咖啡店。她來台灣三年,生了一個女娃,後來離婚,獨自回到北京。當中的原由我不便多問,只知道她離開台灣時,狀態並不好,像一朵枯萎的花。
前幾年我去北京,行程很緊湊,只有短暫的空檔。我其實不抱見面的希望與她聯繫,我說:「不要有壓力,沒有空也沒關係,只是想知道妳好不好。」
才剛說完,她馬上在電話裡回:「姐,妳都老遠來了,我一定能騰出空。妳說這話不是見外嗎?只是才三小時啊!去過景山了嗎?要不我帶妳去那兒逛逛。」小喜聲調高昂,像火箭似地迅速說完全部的話。
那天不是假日,見了面才知道,她是跟公司請了假出來的。
景山在故宮北邊,與神武門隔街對望。它在歷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大概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皇城,崇禎皇帝倉皇地從神武門逃出,在景山的一棵槐樹下自縊。如今那棵老槐樹已魂歸西天,取而代之的是一株年輕的樹,樹旁有一個紀念碑,寫著:「明思宗殉國處」。
在明朝為數不多的明君裡,崇禎是其中的一個。他像是一顆白子落到被黑子圍困的棋局裡,終究敵不過亡國的命運。我在碑前站了一會兒,看著「殉國」兩個字,彷彿看見四百年前,那個才三十三歲,卻已萬念俱灰的朱由檢。
我們沿著階梯上山,小喜說,剛回到北京,以為自己撐不下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窩在家裡,哪裡也不想去。如此過了半年,想想人生還長,為那樣一個人糟蹋自己多不值得?碰巧那時家人介紹了一個環境與待遇都不錯的工作,也與自己的本科相關,決定再試試。
我們一路走到半山腰,對向正好有一群遊客浩浩蕩蕩地下山,我跟小喜往邊沿靠,讓出路。我們靠邊時,小喜拉緊著我的手臂,擔心我沒站穩,同時低聲的在我耳邊說:「姐,我覺得我已經死過一次,但我現在挺好的,這是真的。如果沒有那時的辛苦,我不會體會到現在的尋常多麼不容易。」
小喜神態自若,語氣堅定,比起之前開朗許多。我不知跟她說什麼,心想,人對於一件事的釋懷,有時不是依賴時間的流逝,而是明白自己曾經發生了什麼。感情的事,外人總難置喙,但我知道那時她是有委屈的。
景山嚴格說來並不是「山」,它是近六百年由護城河的淤泥堆積起來的小丘。景山也不高,但高度正好可以俯瞰北京市。我們走到山頂涼亭,找到涼亭旁的中軸標記。這條無形的中軸線,將北京城分成東西兩邊。我在書裡看過梁思成先生說:「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產生的。」
其實,何止北京城有中軸,很多古老的城市都有一個中軸線。中軸是美的基點,是黃金分割,是形成一個城市流動的主要脈絡。它統攝對立與均衡,蘊含平等與尊重。若再往深處想去,這些意涵,不單是指城市規劃,也像一個人在面對世間人情時,秉持的那一道不偏不倚的脊梁。
從景山往下望,如曠野裡刮過一陣風,將氣勢磅礴的紫禁城如長卷般鋪展開來。紅牆明麗,黃瓦灼煥。這座宮殿,呼風喚雨六百年。而六百年歲月就這樣,說過去就過去了,不過就是一轉眼的工夫。
小喜帶著我沿著山上涼亭走了一圈,指著遠方說:鼓樓在哪兒、天壇在哪兒、北海在哪兒......。我望向遠方邊聽邊想,究竟是怎樣的領悟,讓她將昨日的深谷,換作今日的淡然;讓那些灼傷人心的,終成檣櫓灰飛煙滅?人的命運不也像歷史的規律,起伏有時,榮悴有時。甚至以為自己已走到山之窮水之盡,倏忽間又能峰迴路轉柳暗花明。
我沒有想到,能跟小喜在景山再見一面。當年她離開台灣時,傳短訊給我,我回她那句「後會有期」說得很心虛,因為知道再見的機會微乎其微。如今我想,人與人之間,如果分別之後又能重逢,那一定要珍重。
那天,我們沒有說將來,將來太虛渺,現在這樣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