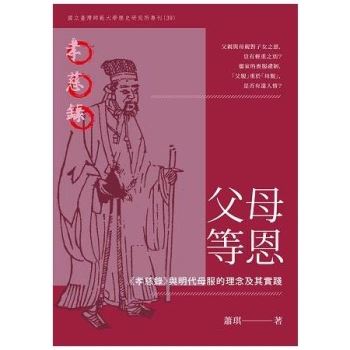「洪武七年,《御製孝慈錄》刊行天下,云:『子為父母,庶子為其生母,皆斬衰三年。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此煌煌天語也。」--清‧李海觀,《歧路燈》,第九回
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貴妃孫氏薨逝,因孫氏生前並未產下皇子,明太祖遂命曾受孫貴妃撫養的周王橚主喪事,為孫貴妃行慈母(庶子無母,父令無子之他妾撫育之)服禮斬衰三年,而東宮、諸王則為庶母(父妾有子者)孫貴妃服齊衰杖期(一年)之服。但是這樣的上諭,卻違反了洪武元年(1368)《大明令》中為母服的規定,也與先秦以來喪服經典《儀禮.喪服》的記載不符,在朝中引起不少爭議,遂使明太祖只好命令禮部討論孫貴妃的喪服問題,並將結果上奏。
等待三日後,禮部官員以《儀禮》為定式,不贊同上述太祖對孫貴妃喪服的提議。根據古禮,如果父親尚在世而逢慈母去世,人子只能為其服齊衰杖期之服,若是庶母去世,長子、眾子對庶母則無服。這樣的答案讓太祖非常不滿,而嚴加訓斥道:「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為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
明太祖顯然反對人子為母親服喪還必須考慮父親在世與否的喪服原則,於是,再命翰林學士宋濂(1310-1381)等人詳加考察古人母服的實例。最後,根據官員回報的結果,發現歷代願為母服三年喪者倍於願為母服一年喪者,太祖於是順勢將母服規定改為「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並「使內外有所遵守」,如願以償的實踐了他「父母之恩,一也」的看法,也就等於提高了母親在家內倫理秩序中的地位。
因為此次明太祖與官員對喪服禮中母服部分的爭議,使太祖進而製作了《孝慈錄》以作為明代喪服制度的定本,從其書名「孝慈」二字即可知曉其動機是為了發揚「孝順母親」這樣一個意念而來。透過此書,明太祖重新規劃了他心中理想的親屬服喪關係,並由禮入律,將之納入《大明律》之首,成為有明一代的定制,並為清代所承襲。
從上述明太祖與群臣議禮,到幾乎可說是「斷自聖衷」的制禮過程,即可以想像《孝慈錄》本身所具有的突破性與爭議性,而由此觸發的一連串問題,亦深深地引起筆者的興趣。首先,在制度上,《孝慈錄》的母服規定明顯與《儀禮‧喪服》以及前代喪服禮制有所不同。唐代的武則天曾針對古禮中的母服部分進行改革,其內容被納入唐代《開元禮》,並為宋、元、明初所承襲,由武則天所提議的母服改革與明太祖所御製的《孝慈錄》之間存在著多少差異,而《孝慈錄》的母服制度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是筆者亟欲處理的第一個問題;其次,在理念上,《孝慈錄》的制訂,來自於明太祖「父母之恩,一也」的觀念,這個觀念的內涵為何,明太祖的其他政策是否亦蘊含此一想法,而此想法與前代統治者所宣揚的孝道觀念有何不同,是本書擬探究的第二個論題。最後,研究一個制度,除了探討其來由與意義之外,制度的實踐亦是研究者無法迴避的問題。太祖之後的明代皇帝與士人如何看待作為洪武開國定制之一的《孝慈錄》,而這份大大提升母親禮制地位的喪服制度的落實情況又是如何,正反意見與實踐與否爭議的背後,隱藏了什麼樣的因素與知識、觀念上的衝突,無疑亦是本書重要的探討面向。綜言之,關於《孝慈錄》理念與實踐的探索,實涉及了孝道觀念、性別、喪服禮制三者的交相關涉,不論是從制度史、社會文化史抑或性別史的角度而言,皆是一個亟待深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