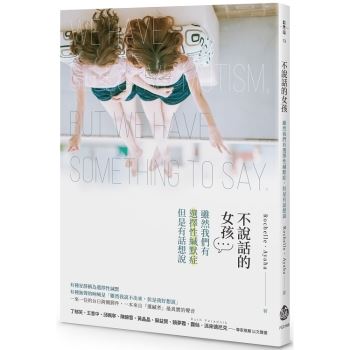〈寫在開始之前〉
雖然我可以說話,但是不知不覺間,我養成了隱藏真心、不把自己真實想法說出來的習慣,內心就變得空洞,覺得無話可說;雖然你平時不說話,但是內心卻有著很多想要傳達給別人的話語。看著你,我就覺得自己也許還有很多想要表達、想要告訴別人的話,和你相遇,我非常高興。
這是日本動畫片《好想大聲說出心底的話》中,男孩對緘默女孩所說的一段經典台詞,這段話語深深觸動我心。女孩年幼時,活潑開朗、伶牙俐齒,卻稚子無心道出父親出軌之事,導致家庭支離破碎,遭到父母親怨懟,「蛋魔」為其封印言語,換取一生平安順遂,此後,女孩一旦嘗試張嘴說話,便腹痛不止,於是長期緘默,直到高中,同班同學甚至誤認為她是語言障礙者/瘖啞人士而口出惡語揶揄。男孩與女孩同為老師指定的社區活動主負責人,在準備活動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交集與羈絆,男孩學會坦承以待,女孩學習敞開心扉,而活動之中的音樂劇是女孩的創作,也是她內心最真實的聲音,最終得以擔任戲劇主角,本色演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話語是能夠傷人的
「話語是能夠傷人的,就算後悔也是絕對無法挽回的。」童年的創傷牢牢刻劃於女孩心中。
「我已經能夠接受無趣的自己了。說出自己所想的,被唸了、被批評了還要反擊實在太累了,和周圍的人發生衝突也很麻煩,所以感覺都無所謂了。」男孩對於自己、世界的解讀與詮釋。
「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別出門,實在太丟臉了!」這是女孩頭一次鼓足勇氣應門把電費交給社區負責人時,母親的回應。
「為什麼啊?我就那麼可恨嗎?你一直都不說話,鄰居都在說我閒話,你到底想做什麼?故意惹我生氣嗎?你倒是說話啊!想反抗就說啊!我已經累了!」母親在急診對腹痛就醫的女孩這麼說道。儘管影片中的女孩並非典型選擇性緘默症(更像是創傷反應),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有想說卻說不出來的時候,不論是什麼樣的原因─選擇性緘默症、失語症、溝通障礙也好,礙於社會規範、不願讓自己或他人由於言詞受到傷害也罷,多多少少有些「情非得已」,因而「有口難開」。我們有自己不說話的緣由、也可能被誤解,甚至無意間刺傷了別人,語言的本質是為了溝通,卻由於各種因素,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變質,可能曖昧不明;可能虛與委蛇;可能用冷漠寡言或嘮叨多語的面具保護自己。「囝仔人,有耳無嘴」大概是大家共同的童年記憶吧!在傳統文化中,是前人教育孩子學會傾聽、學會尊重、學會察言觀色並因時制宜地表達的智慧諺語,儘管隨著時代演進、社會背景的不同以及普遍的濫用,反倒可能成了苛責孩子的說辭、不允許孩子表達的理由(也許是對於孩子的滔滔不絕感到不耐煩;也許是工作家事繁忙而分身乏術;也許擔憂孩子的純真無邪、不諳世事在外頭失了體面)。另外,生活裡還存在著一些中華文化的禁忌,還記得小時候,舉凡說到「死」、「鬼」等字眼,像是:「高興死了!」、「搞什麼鬼?」之類的,長輩便會提醒我們注意言詞,由於忌諱而使用借代、婉曲修辭,似乎是人們的默契,也是每個人「社會化」的過程。所有人都被「規矩」所囿陷、束縛,而選擇性緘默症的孩子,則是被焦慮綁架與囚禁。
不說話也能被聽懂
「唱歌反而是最能傳達心情的。唱出來就不疼了。」男孩鼓勵女孩。
「她是一個很開朗的人,雖然不太愛說話,她的內心活動很豐富。她一直都很努力的。」男孩是如此形容女孩的。
「縱然你不說話,還是能知道你想說什麼呢!」女孩生動的肢體語言逗樂了男孩,帶給他這樣的感受。
「蛋魔什麼的其實根本不存在,是我給自己施加詛咒,蛋魔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封閉在蛋裡的自己。蛋裡究竟有什麼?封閉著各種心情、到後來再也裝不下、然後爆發而誕生的這個世界,比想像還要美。」豁然開朗的女孩娓娓道來。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其中之一,但非唯一。猶記系上諮商、臨床相關課程雖然基礎,老師們卻不約而同教導我們不要遺漏非語言的訊息,不論是當事人呈現出來的,或是我們傳達給當事人的,往往這些非語言訊息更為真實,和語言訊息一樣擁有無可取代的地位,這也是實務上,有些人對於「網路諮商」、「人工智慧諮商」的疑慮之處,我們的表情、眼神、肢體動作、身體姿勢都在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雖說語言是人類獨有的優勢,然而其他物種沒有語言仍然得以生存不是嗎?再說,我們也經歷過不能說話的嬰兒時期,依然能夠以哭泣告知照顧者我們的需要、以舞拳踢腿表露自己的喜怒哀樂,在學會語言之前,我們已經能夠使用非語言,那麼,又怎麼反倒遺忘、失去了這項技能呢?國中時期大概是紙條最蓬勃發展的年紀吧!各種形式的偷渡紙條不足為奇,塞在筆管裡的、藏在立可帶中的、夾在課本內頁的、直接打在電子辭典的,可是,紙條一波三折、跋山涉水也不是辦法,當時同學之間唇語讀得久了也就能心領神會了。樂團裡的指揮家手持細棒帶領著樂手們、球員在球場上以手勢互打暗號、警員使用吹哨和警示棒疏導交通,不也是非語言訊息的體現嗎?
或許某些時刻,不便使用語言,但是,只要我們願意,任何一種方式都能溝通。我想,這是選擇性緘默症帶給我們的領悟。雖然我們有時候不能說話,仍然如同世上的每一個人一樣,透過各式各樣的途徑好好地活著、努力地與人溝通、交流。雖然我們有選擇性緘默症,但是我們還是有許多話想說。
我覺得《好想大聲說出心底的話》裡男孩的情況彷彿是某一部分的我,能夠言語,卻將最真誠的情感、思緒深深沉落心湖埋藏;女孩的情況好比另一部分的我,縱然無法言語,卻特別希望傳遞溫暖與能量。不論你是那個能說話,卻總是隱忍、默默承擔的男孩;抑或那位說不出話,卻以自己的方式與世界互動的女孩,希望我們的故事,能夠讓你感覺不那麼孤單。讓我們一起長出大聲呼喊的勇氣吧!
〈每個人生命裡都有一位不說話的女孩〉
診斷
「不知道你有沒有學到選擇性緘默症了?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像?」醫師不疾不徐地對我說道,帶著一絲幽然,又不失謹慎鄭重。我點點頭。
我猜想,就給予診斷時的用字遣詞而言,醫師對我應該是另眼相待吧!這是我的第二個診斷,有別於第一次的懵懂無知,我清楚醫師是間接地訴說她的判斷,而非單純與身為心理系學生的我討論精神疾患的相關知識而已。我不知道多數人得到診斷時是什麼樣的反應,是無法接受的討價還價、哭天搶地?抑或終於鬆一口氣、得到一個說法的救贖感?我只是一如既往的一號表情,兩次都是,沒有泛起天大的波瀾,只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去消化,去接納自己複雜的心情。
或許是名稱的關係,許多人都誤以為選擇性緘默症是「自願選擇不說話」,然而,就連我們自己也不那麼清楚能夠說話的對象與情境,儘管可以試圖歸納潛規則,現實狀況更傾向本能。事實上,在感到放鬆的情境(通常是家裡),我們與一般人無異,能說會道、能歌會唱,耳朵聽得見,大腦也能理解語意,只是當焦慮侵襲時(通常是在學校中),我們的聲音彷彿被竊取,不但說不出話來,還成了肢體僵硬、動彈不得的小木偶。大家習以為常的語言表達,對我們而言是來之不易的,其實,選緘和害羞不一樣(有些選緘者甚至是外向活潑的),並不是長大後便能自然改善,也不一定在與人熟悉後就能消失無蹤。不免俗地列出DSM-5診斷標準,可是,我總覺得診斷標準是不易理解、感受的2D,在後面的故事裡,希望讓選擇性緘默症在3D世界活了起來。
根據DSM-5(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選擇性緘默症之診斷標準如下:
一、持續地無法在需要說話的特定社交情境中說話(例如:學校),儘管在其他情境可以說話。
二、上述困難妨礙教育、職業成就,或社交溝通。
三、此困難持續至少一個月(不包括入學的第一個月)。
四、無法說話並非因為對於社交情境所須使用的語言,缺乏了解或感到不適。
五、此困難無法以溝通障礙做更適切解釋(例如:兒童期初發型語暢障礙),且並不僅只發生於自閉譜系疾患、思覺失調或其他精神病症的病程中。
許多人在第一次聽聞「選擇性緘默症」時,都向我反應:「我小時候也是這樣耶!」、「國小的時候,一直到畢業我都沒有聽過那位同學的聲音呢!」在教室中,安靜沉默的孩子時常是師長相對放心的一群,「文靜」、「乖巧」是師長對這些孩子的第一印象,如此一來,是不是幾乎沒有人會將他們和「特殊需求」連結在一起呢?
不說話也值得擁有愛
儘管沒有聽過選擇性緘默症,儘管不曾遇見選擇性緘默者,在你的腦海裡,是否浮現了一位幾乎不說話的人呢?或許是男孩/女孩;或許是小孩/青少年/成人;或許是同學/子女/同事/學生/親戚;或許你不曾留意他/曾經疑惑的念頭轉眼即逝/與他親密無間,總有那麼一個身影,駐足於你的記憶。也許,他,就是那一百四十人之一,其中一個被選擇性緘默症偷走聲音的靈魂。
又或者,你是否憶起年少青澀的自己?現在的你是否依然處於靜默的狀態?這些歲月裡,你總是默默地存在,悄悄地來來去去,就像一陣微風掠過,卻沒有激起一道漣漪。看似沉靜的你,也渴望平凡如常的一段親情、友情與愛情,卻將聲音輕輕埋藏在心底的沙灘裡,圈禁在囹圄之中。然而,你也有自己的萬千世界,你也想對人們訴說無數精彩故事。是的,不論如何,你都值得擁有愛和理解。
我們都希望被當作人來對待,而這點人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行為。對某人說話和傾聽某人,就是將他像人一樣對待,或者至少是『人性』對待的開始。然而,這只是第一步,語言只是我們『人類化』的一個出發,不僅僅是語言,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我們做為人類的互相承認,比如一個人用理解的眼神和尊重的神情看待另一個人。--《對與錯的人生邏輯課》
這段話語是在倫理學課程中讀到的一段文字。作者提及:如果我們舉目所見之人皆是行走的「器物」或「野獸」,我們自己也不會是更好的東西,因此我們需要視他人為「人」。傾聽很難,不帶評價的聆聽更難,我們都渴望被聽懂、被接納、被同理,但是,更習慣「說」而非「聽」,實際上,就算我們當下不能說話,但還是可以用真摯的神情去聽、去傳達自己的感同身受。曾經有一位在活動中認識的學妹告訴我:「謝謝你聽我說,謝謝你總是以笑容回應我。雖然我覺得自己講得很無趣,可是你還是始終面帶微笑,我覺得很開心。」或許下次聽朋友訴苦時,你不需要像我一樣沉默,倒是可以試試看,少說一些、多聽一些,沒有「我覺得」、「你應該」,一個會心的表情、一個真誠的擁抱往往能表達得更多。從另一個角度看,選緘不只是障礙,還是老天爺賜予的禮物,固然被剝奪某些言語的能力,卻擁有更多練習聽、練習寫的機會,其實,我們都一樣,不論可不可以說話,不論有什麼樣的生命課題,都可以愛人與被愛,這是生而為人的天賦。
以病會友
仍然炙熱、毫無秋意的二零一七年九月,台灣女孩向日本女孩遞出臉書的交友邀請,日本女孩回應:「你也是選擇性緘默症社團的成員嗎?」就這樣,兩位女孩便因為選擇性緘默症這個共通點,結下橫越海洋的異國友誼。
「我是Ayaha,二十一歲,日本的大學生。」螢幕上出現她的訊息。
「我的名字是Rochelle,十九歲,來自台灣。」我也簡單自我介紹。
那是我第一次在社群網站上結交異國友人,當時的我們都不會想到,彼此能藉由訊息及電子郵件的往返,與素未謀面的對方發展出深厚的友誼,帶給彼此溫暖堅強的支持、陪伴,更沒有想過,身為大學生的我們,能夠一起為選擇性緘默症發聲。縱使年幼孩童的患者比率較高(根據《選擇性緘默症資源手冊》,一百四十人中有一人),但是延續至青少年、成人的案例亦非罕見(五百五十人中有一人),Ayaha和我都是其中之一。特定情境的無法言語,阻隔了我們與世界交流的機會,深深影響著我們的學習、人際、自我概念及自理能力等,也可能出現拒學、焦慮、憂鬱的情況。在成長過程中,我和Ayaha為選緘所困,卻不自知,直到成年之後,因緣際會求診,才讓我們的生命得到一個解釋。因為走過這段漫漫長路,更希望選緘能夠被看見。有一種安靜稱為選擇性緘默,有一種無聲的吶喊叫做「雖然我說不出來,但是我好想說」,請聽聽我們的心聲,請幫幫我們,讓含苞的聲音能夠綻放,讓束縛的靈魂得以破繭而出、展翅翱翔。
雖然我們有選擇性緘默症,但是我們有話想說。
〈選擇性緘默不是你想的那樣〉
緘默
之前有段時間,網上瘋傳「一句話惹怒各科系學生」、「一句話惹怒各縣市人」,對於某一類型的人,我們似乎都會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往往伴隨不太正確的觀念,當聽見他人脫口而出與我們自身相關的NG語句,難免忍不住在心裡直翻白眼。即便選擇性緘默症鮮為人知,多數人第一次接觸這個名詞,依舊習慣「望文生義」:
「所以是你選擇不說話嗎?」、「你是針對某些人不說話喔?」、「你聽得見嗎?聽得懂我說的嗎?」、「你是完全不能說話嗎?可是你現在可以說話欸!」、「那我拿麥克風給你說。」、「是不是相處比較久、比較熟就可以說啦?要認識多長時間你才會說啊?」、「小時候害羞沒關係呀!長大就會好了!」、「我以前也很害羞,強迫自己多說幾次就敢說了啊!」、「之前我也都很安靜,我也是選擇性緘默症啊!」
類似的聲音層出不窮,縱然可以理解他人並無惡意,不免有些受傷,就像胸口被利刃劃過一樣。那些說法當中,最讓人敏感的是:「我也是選擇性緘默症啊!」我想了想,這和日常生活充斥的「髒話」、「罵人的話」、「揶揄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與朋友打鬧之間,我們時常不經意地回嘴:神經病、弱智、腦殘、眼瞎、耳幹、肢障、手殘等等都是以社會上某一群人的困難作為玩笑話,再說精神(心理)疾患好了,心情偶感鬱悶便自稱憂鬱症、脾氣暴躁就說人家是躁鬱症、孩子活潑好動便責備其為過動……。撇除誤用疾病名稱及症狀不談,對多數人而言不過是茶餘飯後的嬉笑怒罵,但是,假如身心障礙人士聽到這些詞語被如此使用,該情何以堪?同等地,我希望在選擇性緘默症更為人知的過程中,「選擇性緘默」這個名詞不輕易被濫用,小自親友談天,大至媒體傳播,不僅僅是患者與家屬的觀感問題,而是普遍的誤用可能讓選擇性緘默者被看見卻視而不見,反倒與宣導、普及的初衷背道而馳,這是我們所不樂見的。
談起選緘,「緘默」是核心症狀,也最容易理解,因此,會從這方面開始,也傾向先簡略帶過,因為在後面的故事裡,不論是什麼樣的主題,亦都緊扣「說話」這件事情。
雖然我可以說話,但是不知不覺間,我養成了隱藏真心、不把自己真實想法說出來的習慣,內心就變得空洞,覺得無話可說;雖然你平時不說話,但是內心卻有著很多想要傳達給別人的話語。看著你,我就覺得自己也許還有很多想要表達、想要告訴別人的話,和你相遇,我非常高興。
這是日本動畫片《好想大聲說出心底的話》中,男孩對緘默女孩所說的一段經典台詞,這段話語深深觸動我心。女孩年幼時,活潑開朗、伶牙俐齒,卻稚子無心道出父親出軌之事,導致家庭支離破碎,遭到父母親怨懟,「蛋魔」為其封印言語,換取一生平安順遂,此後,女孩一旦嘗試張嘴說話,便腹痛不止,於是長期緘默,直到高中,同班同學甚至誤認為她是語言障礙者/瘖啞人士而口出惡語揶揄。男孩與女孩同為老師指定的社區活動主負責人,在準備活動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交集與羈絆,男孩學會坦承以待,女孩學習敞開心扉,而活動之中的音樂劇是女孩的創作,也是她內心最真實的聲音,最終得以擔任戲劇主角,本色演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話語是能夠傷人的
「話語是能夠傷人的,就算後悔也是絕對無法挽回的。」童年的創傷牢牢刻劃於女孩心中。
「我已經能夠接受無趣的自己了。說出自己所想的,被唸了、被批評了還要反擊實在太累了,和周圍的人發生衝突也很麻煩,所以感覺都無所謂了。」男孩對於自己、世界的解讀與詮釋。
「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別出門,實在太丟臉了!」這是女孩頭一次鼓足勇氣應門把電費交給社區負責人時,母親的回應。
「為什麼啊?我就那麼可恨嗎?你一直都不說話,鄰居都在說我閒話,你到底想做什麼?故意惹我生氣嗎?你倒是說話啊!想反抗就說啊!我已經累了!」母親在急診對腹痛就醫的女孩這麼說道。儘管影片中的女孩並非典型選擇性緘默症(更像是創傷反應),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有想說卻說不出來的時候,不論是什麼樣的原因─選擇性緘默症、失語症、溝通障礙也好,礙於社會規範、不願讓自己或他人由於言詞受到傷害也罷,多多少少有些「情非得已」,因而「有口難開」。我們有自己不說話的緣由、也可能被誤解,甚至無意間刺傷了別人,語言的本質是為了溝通,卻由於各種因素,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變質,可能曖昧不明;可能虛與委蛇;可能用冷漠寡言或嘮叨多語的面具保護自己。「囝仔人,有耳無嘴」大概是大家共同的童年記憶吧!在傳統文化中,是前人教育孩子學會傾聽、學會尊重、學會察言觀色並因時制宜地表達的智慧諺語,儘管隨著時代演進、社會背景的不同以及普遍的濫用,反倒可能成了苛責孩子的說辭、不允許孩子表達的理由(也許是對於孩子的滔滔不絕感到不耐煩;也許是工作家事繁忙而分身乏術;也許擔憂孩子的純真無邪、不諳世事在外頭失了體面)。另外,生活裡還存在著一些中華文化的禁忌,還記得小時候,舉凡說到「死」、「鬼」等字眼,像是:「高興死了!」、「搞什麼鬼?」之類的,長輩便會提醒我們注意言詞,由於忌諱而使用借代、婉曲修辭,似乎是人們的默契,也是每個人「社會化」的過程。所有人都被「規矩」所囿陷、束縛,而選擇性緘默症的孩子,則是被焦慮綁架與囚禁。
不說話也能被聽懂
「唱歌反而是最能傳達心情的。唱出來就不疼了。」男孩鼓勵女孩。
「她是一個很開朗的人,雖然不太愛說話,她的內心活動很豐富。她一直都很努力的。」男孩是如此形容女孩的。
「縱然你不說話,還是能知道你想說什麼呢!」女孩生動的肢體語言逗樂了男孩,帶給他這樣的感受。
「蛋魔什麼的其實根本不存在,是我給自己施加詛咒,蛋魔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封閉在蛋裡的自己。蛋裡究竟有什麼?封閉著各種心情、到後來再也裝不下、然後爆發而誕生的這個世界,比想像還要美。」豁然開朗的女孩娓娓道來。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其中之一,但非唯一。猶記系上諮商、臨床相關課程雖然基礎,老師們卻不約而同教導我們不要遺漏非語言的訊息,不論是當事人呈現出來的,或是我們傳達給當事人的,往往這些非語言訊息更為真實,和語言訊息一樣擁有無可取代的地位,這也是實務上,有些人對於「網路諮商」、「人工智慧諮商」的疑慮之處,我們的表情、眼神、肢體動作、身體姿勢都在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雖說語言是人類獨有的優勢,然而其他物種沒有語言仍然得以生存不是嗎?再說,我們也經歷過不能說話的嬰兒時期,依然能夠以哭泣告知照顧者我們的需要、以舞拳踢腿表露自己的喜怒哀樂,在學會語言之前,我們已經能夠使用非語言,那麼,又怎麼反倒遺忘、失去了這項技能呢?國中時期大概是紙條最蓬勃發展的年紀吧!各種形式的偷渡紙條不足為奇,塞在筆管裡的、藏在立可帶中的、夾在課本內頁的、直接打在電子辭典的,可是,紙條一波三折、跋山涉水也不是辦法,當時同學之間唇語讀得久了也就能心領神會了。樂團裡的指揮家手持細棒帶領著樂手們、球員在球場上以手勢互打暗號、警員使用吹哨和警示棒疏導交通,不也是非語言訊息的體現嗎?
或許某些時刻,不便使用語言,但是,只要我們願意,任何一種方式都能溝通。我想,這是選擇性緘默症帶給我們的領悟。雖然我們有時候不能說話,仍然如同世上的每一個人一樣,透過各式各樣的途徑好好地活著、努力地與人溝通、交流。雖然我們有選擇性緘默症,但是我們還是有許多話想說。
我覺得《好想大聲說出心底的話》裡男孩的情況彷彿是某一部分的我,能夠言語,卻將最真誠的情感、思緒深深沉落心湖埋藏;女孩的情況好比另一部分的我,縱然無法言語,卻特別希望傳遞溫暖與能量。不論你是那個能說話,卻總是隱忍、默默承擔的男孩;抑或那位說不出話,卻以自己的方式與世界互動的女孩,希望我們的故事,能夠讓你感覺不那麼孤單。讓我們一起長出大聲呼喊的勇氣吧!
〈每個人生命裡都有一位不說話的女孩〉
診斷
「不知道你有沒有學到選擇性緘默症了?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像?」醫師不疾不徐地對我說道,帶著一絲幽然,又不失謹慎鄭重。我點點頭。
我猜想,就給予診斷時的用字遣詞而言,醫師對我應該是另眼相待吧!這是我的第二個診斷,有別於第一次的懵懂無知,我清楚醫師是間接地訴說她的判斷,而非單純與身為心理系學生的我討論精神疾患的相關知識而已。我不知道多數人得到診斷時是什麼樣的反應,是無法接受的討價還價、哭天搶地?抑或終於鬆一口氣、得到一個說法的救贖感?我只是一如既往的一號表情,兩次都是,沒有泛起天大的波瀾,只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去消化,去接納自己複雜的心情。
或許是名稱的關係,許多人都誤以為選擇性緘默症是「自願選擇不說話」,然而,就連我們自己也不那麼清楚能夠說話的對象與情境,儘管可以試圖歸納潛規則,現實狀況更傾向本能。事實上,在感到放鬆的情境(通常是家裡),我們與一般人無異,能說會道、能歌會唱,耳朵聽得見,大腦也能理解語意,只是當焦慮侵襲時(通常是在學校中),我們的聲音彷彿被竊取,不但說不出話來,還成了肢體僵硬、動彈不得的小木偶。大家習以為常的語言表達,對我們而言是來之不易的,其實,選緘和害羞不一樣(有些選緘者甚至是外向活潑的),並不是長大後便能自然改善,也不一定在與人熟悉後就能消失無蹤。不免俗地列出DSM-5診斷標準,可是,我總覺得診斷標準是不易理解、感受的2D,在後面的故事裡,希望讓選擇性緘默症在3D世界活了起來。
根據DSM-5(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選擇性緘默症之診斷標準如下:
一、持續地無法在需要說話的特定社交情境中說話(例如:學校),儘管在其他情境可以說話。
二、上述困難妨礙教育、職業成就,或社交溝通。
三、此困難持續至少一個月(不包括入學的第一個月)。
四、無法說話並非因為對於社交情境所須使用的語言,缺乏了解或感到不適。
五、此困難無法以溝通障礙做更適切解釋(例如:兒童期初發型語暢障礙),且並不僅只發生於自閉譜系疾患、思覺失調或其他精神病症的病程中。
許多人在第一次聽聞「選擇性緘默症」時,都向我反應:「我小時候也是這樣耶!」、「國小的時候,一直到畢業我都沒有聽過那位同學的聲音呢!」在教室中,安靜沉默的孩子時常是師長相對放心的一群,「文靜」、「乖巧」是師長對這些孩子的第一印象,如此一來,是不是幾乎沒有人會將他們和「特殊需求」連結在一起呢?
不說話也值得擁有愛
儘管沒有聽過選擇性緘默症,儘管不曾遇見選擇性緘默者,在你的腦海裡,是否浮現了一位幾乎不說話的人呢?或許是男孩/女孩;或許是小孩/青少年/成人;或許是同學/子女/同事/學生/親戚;或許你不曾留意他/曾經疑惑的念頭轉眼即逝/與他親密無間,總有那麼一個身影,駐足於你的記憶。也許,他,就是那一百四十人之一,其中一個被選擇性緘默症偷走聲音的靈魂。
又或者,你是否憶起年少青澀的自己?現在的你是否依然處於靜默的狀態?這些歲月裡,你總是默默地存在,悄悄地來來去去,就像一陣微風掠過,卻沒有激起一道漣漪。看似沉靜的你,也渴望平凡如常的一段親情、友情與愛情,卻將聲音輕輕埋藏在心底的沙灘裡,圈禁在囹圄之中。然而,你也有自己的萬千世界,你也想對人們訴說無數精彩故事。是的,不論如何,你都值得擁有愛和理解。
我們都希望被當作人來對待,而這點人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行為。對某人說話和傾聽某人,就是將他像人一樣對待,或者至少是『人性』對待的開始。然而,這只是第一步,語言只是我們『人類化』的一個出發,不僅僅是語言,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我們做為人類的互相承認,比如一個人用理解的眼神和尊重的神情看待另一個人。--《對與錯的人生邏輯課》
這段話語是在倫理學課程中讀到的一段文字。作者提及:如果我們舉目所見之人皆是行走的「器物」或「野獸」,我們自己也不會是更好的東西,因此我們需要視他人為「人」。傾聽很難,不帶評價的聆聽更難,我們都渴望被聽懂、被接納、被同理,但是,更習慣「說」而非「聽」,實際上,就算我們當下不能說話,但還是可以用真摯的神情去聽、去傳達自己的感同身受。曾經有一位在活動中認識的學妹告訴我:「謝謝你聽我說,謝謝你總是以笑容回應我。雖然我覺得自己講得很無趣,可是你還是始終面帶微笑,我覺得很開心。」或許下次聽朋友訴苦時,你不需要像我一樣沉默,倒是可以試試看,少說一些、多聽一些,沒有「我覺得」、「你應該」,一個會心的表情、一個真誠的擁抱往往能表達得更多。從另一個角度看,選緘不只是障礙,還是老天爺賜予的禮物,固然被剝奪某些言語的能力,卻擁有更多練習聽、練習寫的機會,其實,我們都一樣,不論可不可以說話,不論有什麼樣的生命課題,都可以愛人與被愛,這是生而為人的天賦。
以病會友
仍然炙熱、毫無秋意的二零一七年九月,台灣女孩向日本女孩遞出臉書的交友邀請,日本女孩回應:「你也是選擇性緘默症社團的成員嗎?」就這樣,兩位女孩便因為選擇性緘默症這個共通點,結下橫越海洋的異國友誼。
「我是Ayaha,二十一歲,日本的大學生。」螢幕上出現她的訊息。
「我的名字是Rochelle,十九歲,來自台灣。」我也簡單自我介紹。
那是我第一次在社群網站上結交異國友人,當時的我們都不會想到,彼此能藉由訊息及電子郵件的往返,與素未謀面的對方發展出深厚的友誼,帶給彼此溫暖堅強的支持、陪伴,更沒有想過,身為大學生的我們,能夠一起為選擇性緘默症發聲。縱使年幼孩童的患者比率較高(根據《選擇性緘默症資源手冊》,一百四十人中有一人),但是延續至青少年、成人的案例亦非罕見(五百五十人中有一人),Ayaha和我都是其中之一。特定情境的無法言語,阻隔了我們與世界交流的機會,深深影響著我們的學習、人際、自我概念及自理能力等,也可能出現拒學、焦慮、憂鬱的情況。在成長過程中,我和Ayaha為選緘所困,卻不自知,直到成年之後,因緣際會求診,才讓我們的生命得到一個解釋。因為走過這段漫漫長路,更希望選緘能夠被看見。有一種安靜稱為選擇性緘默,有一種無聲的吶喊叫做「雖然我說不出來,但是我好想說」,請聽聽我們的心聲,請幫幫我們,讓含苞的聲音能夠綻放,讓束縛的靈魂得以破繭而出、展翅翱翔。
雖然我們有選擇性緘默症,但是我們有話想說。
〈選擇性緘默不是你想的那樣〉
緘默
之前有段時間,網上瘋傳「一句話惹怒各科系學生」、「一句話惹怒各縣市人」,對於某一類型的人,我們似乎都會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往往伴隨不太正確的觀念,當聽見他人脫口而出與我們自身相關的NG語句,難免忍不住在心裡直翻白眼。即便選擇性緘默症鮮為人知,多數人第一次接觸這個名詞,依舊習慣「望文生義」:
「所以是你選擇不說話嗎?」、「你是針對某些人不說話喔?」、「你聽得見嗎?聽得懂我說的嗎?」、「你是完全不能說話嗎?可是你現在可以說話欸!」、「那我拿麥克風給你說。」、「是不是相處比較久、比較熟就可以說啦?要認識多長時間你才會說啊?」、「小時候害羞沒關係呀!長大就會好了!」、「我以前也很害羞,強迫自己多說幾次就敢說了啊!」、「之前我也都很安靜,我也是選擇性緘默症啊!」
類似的聲音層出不窮,縱然可以理解他人並無惡意,不免有些受傷,就像胸口被利刃劃過一樣。那些說法當中,最讓人敏感的是:「我也是選擇性緘默症啊!」我想了想,這和日常生活充斥的「髒話」、「罵人的話」、「揶揄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與朋友打鬧之間,我們時常不經意地回嘴:神經病、弱智、腦殘、眼瞎、耳幹、肢障、手殘等等都是以社會上某一群人的困難作為玩笑話,再說精神(心理)疾患好了,心情偶感鬱悶便自稱憂鬱症、脾氣暴躁就說人家是躁鬱症、孩子活潑好動便責備其為過動……。撇除誤用疾病名稱及症狀不談,對多數人而言不過是茶餘飯後的嬉笑怒罵,但是,假如身心障礙人士聽到這些詞語被如此使用,該情何以堪?同等地,我希望在選擇性緘默症更為人知的過程中,「選擇性緘默」這個名詞不輕易被濫用,小自親友談天,大至媒體傳播,不僅僅是患者與家屬的觀感問題,而是普遍的誤用可能讓選擇性緘默者被看見卻視而不見,反倒與宣導、普及的初衷背道而馳,這是我們所不樂見的。
談起選緘,「緘默」是核心症狀,也最容易理解,因此,會從這方面開始,也傾向先簡略帶過,因為在後面的故事裡,不論是什麼樣的主題,亦都緊扣「說話」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