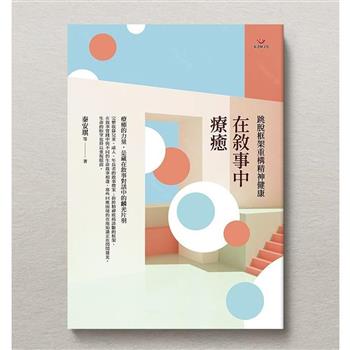96 PART 2 兒少的經驗
當亞斯伯格遇上霸凌
謝杰雄
前言
生活在現今社會,不同的主流社會群體也講求個人的社交能力。自年幼時,不同的師長與父母也紛紛叮囑我要「學做人」,意思要學習待人處世之道。所謂待人處世之道有著不同的說法,但自古以來,諸子百家也有不同的教導,例如孔子的為人之道:「人之初,性本善」、「為人需本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老子的處事之道:「謙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詳是處世第一法,寬容是處事第一法,寡慾是養心第一法。」;孟子的君臣之道:「君講禮,臣講忠,故君臣之道在於禮。」長大後出來社會做事,在不同的社交環境中,也曾被人教訓需要懂得「圓滑世故」,個人的成功與否,似乎也與這些社交上的規範相關。偶一不慎,便容易落入人際關係的難題當中,被人冠以「不成熟、不懂做人」等稱呼。事實上,在推祟「合群」與「面面俱圓」的主流社會中,有多少人會願意理解在堅持己見、選擇坦率背後的價值信念與原則。
在主流下被孤立的一班年青人
在重視社交禮儀的主流文化下,往往排擠了一群與主流不同的人。阿希今年15歲,他是其中一位參加敘事社群實踐小組的組員。認識他是因為阿希媽媽到中心尋求協助,因他一直受著社交問題的困擾。據阿希媽媽表示,他在初小時已被精神科醫師診斷為亞斯伯格症(Asperger Syndrome,另譯亞氏保加症)。此症由一位奧地利的兒科醫生漢斯.亞斯伯格(Hans Asperger)於1944年間提出,那時他留意到有部分兒童有著相似的社交困難問題,例如缺乏非語言的溝通技巧、難以明白他人的想法與感受、缺乏同理心等等(Autism Speaks, n.d.)。到1994年,此症亦納入到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4)中。但在2013年出版的第五版(DSM-5)便作出了修訂,將亞斯伯格症歸納為「自閉症譜系障礙」。在重視病理學論述的社會下,這些青年被建構了不同於殘疾相關的身分,而這身分更隨著病理學的知識更新而轉變,這正是傅柯(Foucault)提出語言與權力如何在社會中運作,並建構了身分的過程(Jenkins, 2014)。White(2011)曾提及現代權力往往會為人的生活建立一套規範並驅使人隨著此規範生活。若人們未能遵從這些規範,往往會被界定為「不正常」並設法改變行為以合乎正常的標準。這個病理學的論述往往令當事人建構了一個薄弱的身分結論,讓人的智慧、能力、技能以致他的身分也被問題故事所遮蔽(Morgan, 2000)。在初接觸這些年青人的組群時,不論與家長、師長還是社工的對話中,也充滿著有關「能力不足」等語言,受著病理學論述的影響,也會以「殘疾」與「不正常」的問題與身分訴說他們的故事。坊間自然也充斥著不同種類的治療性或訓練性小組,以改變他們的行為來符合正常規範為目標。
從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角度再思亞斯伯格
Norman Kunc及Emma van der Klift曾分享有關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的概念,並以不同的角度看殘疾問題(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 2015)。神經多樣性的角度與病理學論述不同,它理解自閉症譜系障礙為社會所建構,沒有所謂正常與不正常的腦袋,每人的神經發展也有不同的程度與步伐。這概念使人從「缺憾不足」的假設解放至尊重每人不同的差異,亦鼓勵我離開亞斯伯格的問題身分,繼而探索其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