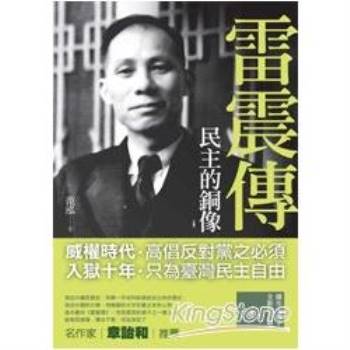〈第二十二章 在獄中〉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許,宋英及兩位女兒在二三親友的陪同下,前往台北青島東路警備總部看守所探望「複判後」的雷震。未料,雷震在一小時之前已被移至新店鎮安坑鄉國防部軍人監獄,宋英等人只好再匆忙乘車趕往新店。
第二天,雷震好友齊世英、夏濤聲、蔣勻田、胡秋原、夏道平、周棄子等七人,前往軍人監獄看望開始服刑的雷震,遭到獄方的拒絕,理由是「每週二、五的例行接見日,求見者以服刑人的親屬為限,朋友沒有必要時,監方可拒絕接見」。實際上,當局已下達有關指令,非親屬探望雷震,「一概得要先經申請,獲得國防部批准,否則免談」。
根據當時的規定,「軍人無論是受審判或服刑,都是按階級而有所不同的。非軍人而受軍法審判的,也依其身份職位比照軍人之待遇」。雷震仍是「國大代表」,相當於軍人「將軍」之銜,可住單人囚室。新店安坑軍人監獄條件比看守所好不了多少,許多設施尚不盡如人意。雷震因高大身材,軍人監獄中的床似乎太小,雷震讓家人送去自己平時睡的那張大床,還有一張桌子,一把籐椅,一張靠椅,以及一個洗澡盆。以雷震的身份,在這裡無需穿囚服,雷震最初兩次會見家屬時,穿的都是西服。後來天氣漸冷,雷震讓家人又送去棉袍。安坑在鄉下,早晚特別涼。在看守所時,家人經常會送一點小菜來。到了這裡,雷震覺得不甚方便,就關照家人不必再天天送了。宋英是每週五探監,如夫人向筠是每週二探監,孩子則分別隨宋英和向筠一起去。朋友們來探望雷震,往往由於見不到人,會留一點水果給他。
有一次,立法委員胡秋原 、成舍我偕雷夫人宋英一起來探監,胡、成二人硬是被擋在了門外。胡秋原只好留下自己的名片,在反面寫道,「儆寰兄:今日兄坐牢,不是壞事;唯坐牢之道,首須安心。安心之法,不外讀書與思想。一當讀輕鬆者,二當讀費腦筋者。蓋唯有用心深思,始能安心也。不得見,所欲告兄者如此……」
雷震在獄中發出的第一封家書,是入獄兩天之後。他讓宋英透過「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負責協商政治解決」,其辦法是「我不參加反對黨,自由中國社改組……希望我今後脫離現實,過一點寫作生活」。十天之後,再次致函宋英,「政治解決,除『總統』外,恐要與經國談談……這裡雖然特別優待,如果再住一二年,也是無法下去的」,信末特別交代「絕對秘密看完燒去不可留」。雷震一直認為此次當局之制裁「決心如鐵」,其關鍵癥結在於參與組黨,因此,想透過「政治協商解決」的方式,來改變目前的困境。應當說,這並非雷震此時萌發出來的「悔意」,而是不想「新黨」因此而胎死腹中,他在信中說「新黨我不能參加,希望他們成功」。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雷震在獄中致函胡適,為他的七十大壽提前祝賀,並向胡適索書,「本月十七日為先生七十大慶,我在獄中不能前來祝壽,謹寫此信代賀……賀壽不能無紀念品,我現在把『讀《胡適文存》校誤表』作為紀念品,向您敬呈……先生還有什麼書,請賜幾本,外國人的傳記(譯本)如有,請賜下幾本。我讀了一本中譯本《阿德諾傳》,給我啟發的地方甚多。」獲悉雷震在獄中開始寫一些回憶性質的文字,胡適感到十分高興。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宋英前往探監,胡適特意托她帶了一封信給雷震,其中說,「我很高興你能夠安心寫回憶的文字了,也很贊成你儘量寫得『白』。但不要學我,趙元任兄常說適之的白話是不夠『白』的」。
自雷震入獄,至一九六二年二月胡適以心臟病猝發逝世的一年多裡,雷震先後給胡適寫過二十餘封信。一九六一年陰曆五月二十六日,雷震六十五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桂源鋪)以相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其寓意,不言自明。第二年,胡適就去世了。聶華苓始終認為「胡適的速死與雷案有關」,唐德剛說「雷震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歲。雷震自己也說,「胡適為我的事,是遭受了冤屈,但胡適本身也有錯誤,他不應該回台的,回來了即等於『甕中之?』,蔣中正就不會買他的賬,胡適也沒有辦法來對抗」。
雷震在獄中受到嚴密監視,有一個「雷震監視班」,共四人,輪流值班。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時與潮》雜誌刊發〈訪監委宋英女士問雷震獄中生活〉一文惹怒了當局,雷震旋被停止會見家屬達半年之久,《時與潮》雜誌也因此被迫停刊一年。這篇文章係《時與潮》記者對宋英的一次專訪實錄,同時附有「雷震獄中自勵詩」一首。宋英在專訪題記中特別感謝「所有海內外關心儆寰之好友的殷殷至情」,並借用《聖經》上的話,稱自己的丈夫「為義而受難」,他的冤屈將得到歷史最公正的評價。關於這首「雷震獄中自勵詩」及自己的心情,宋英這樣說:
這首詩,是儆寰……自新店安坑軍人監獄寄給我的。我讀了他的這首詩後,覺得他在監獄中的心情,已逐漸平和下來,這點對我來說,自是一件最可欣慰的事。儆寰以垂老之年,坐牢已快三年了。自他被捕入獄至今,一直受到海內外甚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的同情和關懷,我個人亦常受到許多友好的熱誠安慰和幫助……一般說來,一個坐牢的人,心情總是不好受的;儆寰坐牢,難免亦是如此;所以儆寰常說自己是個「受難」人。儆寰以所謂「文字叛國罪」被捕的情景,對我來說,真是歷歷在目,有如昨日之事一樣,但它畢竟已是兩年以前的事了,再來舊事重提,似乎無此必要。至於儆寰坐牢,究竟是「罪有應得」,還是如聖經上所說「為義而受難」,這自然只有訴諸世人的公道與良心,和留待後來歷史的判斷……最近,又承《時與潮》雜誌記者先生來訪,承其關心儆寰,探詢他的獄中生活至詳。臨時乃將儆寰寄我已快半年的這首詩,順便交請《時與潮》雜誌發表。
從對宋英的這篇專訪中,可瞭解到雷震前三年的獄中生活主要以寫作為主,多是回憶類的文字。宋英對記者說,「據我觀察,談不到寫作興趣的高低,只能說他精神來得及時就寫……這是一個獄中人寂寞時惟一使用(或發洩)精力靈感的方法和方式。他曾告訴我,寫起來幾千字,還是沒有困難;哪一天精神不濟了,就休息不寫。」當記者問及雷震獄中健康問題,宋英說,「還算好。你想,他到底是六十七歲的人了,再好也沒法與青年人相比。何況他有風濕病,氣候一變化,他就免不了痛苦……」記者又問,先生與入獄前相比有什麼顯著不同,宋英以兩年多來會見雷震時觀察所得,告訴記者「他現在安靜得多了」,「人生經驗比以前更豐富了,容忍的修養更高深了,觀察事理更深入了」。
雷震患有多年失眠症,一直困擾他的健康。宋英對記者說,雷震在入獄後一段時間裡每天確實需要安眠藥才能入睡,「後來因為購買不方便,以及他有意要藉此機會擺脫安眠藥的糾纏,就像一般人戒煙一樣地把『藥』戒掉了。現在他已完全可以不需藥片而能安眠了」。記者詢問當時那場「中西文化論戰」雙方主角 由論爭而訴諸法庭一事,雷震在獄中對此案十分關注,宋英解釋說,「那是雷先生看報知道打筆戰打進法庭,他向來的性情愛關心朋友,便在給我的一封信上順便提了一句,說他認為那件官司打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囑我見到胡秋原先生時,就說儆寰誠意勸胡先生千萬不要繼續打官司,如果不是他在獄中,他一定要給雙方調解息爭」。
記者提出想看一看這封信,宋英表示這是一封夫妻私函「不便公開」。不過,她又說:「我可以把雷先生附有識言的一首詩交給你發表。因為那首詩是〈自勵詩〉,足以說明他的心境和修養的進度。詩後的跋語,等於是一篇日記,可以讓關心他的朋友們知道他的生活情形而放心。那是他親筆寫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時與潮》雜誌第一百六十六期刊表了雷震的這首〈自勵詩〉(附跋),全文如下:
九月九日夜夢到胡適之先生所示容忍與自由因成自勵詩一首。
無分敵友,和氣致祥,多聽意見,少出主張。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見,民主是張。批評責難,攻錯之則,虛心接納,改勉是從,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不飾非;不說大話,不自誇張,少說多做,功成不居。毋揭他人短,毋揚自己長,毋追懷既往,毋幻想將來。忠於信守,悉力以赴,只顧耕耘,莫問收穫。虛心無愧,毀譽由人,當仁不讓,視死如歸。做人和處世,皆賴之以進;治國平天下,更非此莫成。
九月五日夜,颱風肆虐,居室浸水,物件凌亂,黴氣四溢。七日亞英(即宋英,作者注)探視,送來書架一只。九日天晴,乃抖擻精神,將書籍文稿,衣履被服,碗櫥炊具,藥瓶壺盂,以及??罐罐,全部搬到室外曝曬,洗刷拭淨,然後一一搬回室內,上午十二時完畢。其間雖有一人相助,而大部分工作是我一人任之,跑進跑出,不下百次之多。午間小睡後,又趕寫今日應寫的回憶文字,成二千五百字,復利用休息時間,將書籍放到書架上,並略事整理。其他物件,亦均一一放到適當地方,其間曾準備午晚兩餐。晚飯後又洗衣三件。因之精疲力竭,頭昏眼花,晚間運動因而停止。九點鐘即上床休息。不意橫身酸痛,皮膚發燒(太陽曬的),疲勞過甚,竟不能成眠。十一時半又起床出外散步,腹餓吃餅乾兩塊,然後上床再睡。在迷迷糊糊中,忽然夢到適之先生告訴我們「容忍與自由」的意思,因成詩一首,藉以明志自勉。
《時與潮》這篇溫和、平實的專訪遭到台灣當局的責難。《時與潮》是雷震老友齊世英以「立法委員」身份辦的一個黨外刊物,此時齊世英已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多年。雷震說,「蔣氏父子認為這是諷刺語,即下令《時與潮》停刊一年,我則停止接見,不准帶冰箱和電扇。我的停止接見未付期限,一下子停止接見半年,這又是大大違法的」 。雷震在四月二十八日日記中有「《時與潮》載有陶元珍教授〈讀雷儆寰代表(震)獄中詩〉」之記載,第二天,收到老友徐復觀〈讀儆寰獄中詩感賦〉的抄件,足見這首〈自勵詩〉感人至深。
雷震在獄中為爭得自由閱讀報刊合法權利,與獄方做過一番堅決抗爭。軍人監獄規定訂閱的報紙是黨報和軍報。雷震不願看官方刊物,要求訂閱《聯合報》以及一份英文的《中國郵報》。經過兩個月的審核,方才獲准。獄方對於書刊的閱讀管制特別嚴格,雷震所訂《聯合報》,除負責檢查報紙的保防室外,其他受刑人,甚至獄吏、獄卒一律不許看。在那段時間,獄方只要提及《聯合報》,常稱之為「同路報」,意即「自由派的同路者,思想有問題」的報紙。獄官告訴雷震,獄吏和獄卒為了也能瞭解社會大事,常跑到新店公路局車站內看張貼在公告欄上的「同路報」。
雷震在《雷案回憶》和《獄中十年》等書中,經常提及在獄中閱報時的遭遇和不堪心情。獄方雖然特別核准他在獄中訂閱《聯合報》,對每天的報紙仍加以嚴格檢查,並不時查扣,雷震想盡一切辦法爭取自己的閱報權,其中有若干記載:
《聯合報》常常要到下午才送來,上午要經過保防室檢查,其實他們也要看這些同路報,而不要看那些成天歌功頌德的黨報和官報。
可是保防室的檢查,常常扣去一天,我就抗議:不見得報上所載全部我都不能看吧?
於是保防室改變辦法,抽出不給我看的那一張。
我又抗議:難道全張都是不能給我看的嗎?
保防室又改變辦法,把不准我看的那一部分剪去了。
我再又抗議:保防室不准我看的,只有一則新聞,這一剪去一塊,我連背面可以看的也就看不到了。於是保防室又改變辦法,把不要給我看的那一部分用油墨塗去,如何用水洗刷也洗不掉。
雷震被捕之初,確實受到過軍方在某些方面的「優待」。宋英承認「雷先生自入獄後,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獄中生活那樣苦(例如挨打、受辱和做苦工),但也沒有得到家屬親友特別的照顧(例如「監犯有接見任何家屬親友的便利」)……我每禮拜按軍獄的規定,給他送兩次菜去。」 當局無疑知道此次逮捕雷震在海內外引起的震動和反應,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作採用一些辦法來緩解雷震的情緒,對他在獄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儘量給予滿足。
還在看守所時,所長張福慶對雷震透露過,「雷先生過去對於國家有很大的貢獻,這次事情,理由並不充分,自『雷案』發生後,外國的報刊,包括香港在內,對於政府和國民黨,甚至蔣總統都抨擊甚烈,說是『蔣總統鑄下了一項最大的錯誤』。逮捕雷先生是蔣總統下的手令……為補救起見,關照我們對雷先生特別優待,我們自然要照辦的。」 雷震大發感慨,「我聽到這一段話,馬上聯想到許多人所說『外國的月亮圓些!』這話卻不無道理,這些諷刺的話,當是由經驗而來,我的優待就是受了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之賜!」
自發生〈自勵詩〉事件,獄方對雷震的態度立即有所改變,監控得更加嚴密。李敖曾托宋英女士將其新作《胡適評傳》送給獄中的雷震,此書一審查就是十九天。這本《胡適評傳》讓雷震看了許多天,他還將書中「錯誤的地方均一一記出,將來可交給李敖」。
雷震在獄中十年,軍人監獄更換過四位監獄長。他回憶道:
第一位是李玉漢,據說是特務出身,我未見到過;第二位叫做馬光漢,他任軍監監獄長三年,每年倒是來囚室給我拜年,他是對我特別客氣,他知道我是被蔣氏父子誣陷,下令而坐牢,我本身是清白無辜的,所以每年來給我拜年,對其他受刑人當然無此禮貌,和其他監獄長對受刑人是一樣的態度,依然是「牢頭禁子」的作風。第三位姓趙,做了好多年,我根本沒有見過。第四任監獄長叫做「洪濤」(即洪破浪,作者注),係憲兵出身……洪濤任監獄長後作風大變,對待受刑人的態度則大為和善,受刑人都覺得這位監獄長有人性,是一個人,不是牢頭禁子,對我也特別客氣……洪濤到任之後,對於受刑人也舉行「生日會」,使受刑人也得到一點溫暖……受刑人的生日會是在監獄的禮堂中舉行,洪濤和許多監獄官親自參加……我是受蔣氏父子下令不准和大眾見面,所以給我添了幾樣菜,由我一人在監房中吃。這雖是美中不足的事,但不能責怪洪濤,那是他不敢違背獨裁者的命令,除非他不想做官,不要這條命。
以雷震坐牢的親身體會,發現在軍監中態度最為惡劣、最不講道理、又無法律觀念的機構當屬「保防室」。「保防室」名義上屬於軍人監獄政治處代管,實際上是一個特務機構,隸屬蔣經國管轄之下的一個安全室,在軍監中誰也管不了它。「保防室」對雷震特別苛刻,「我所接見的人,要它核可,我除掉家屬和親屬外,任何人也不許接見,連家中燒飯伙夫送菜來時,也不許我接見」。每次會見家屬時,只有三十分鐘,兩部答錄機同時錄音,更有人在一旁監視。立法委員、原「軍統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來軍監探人,提出順便見一見雷震,同樣遭到拒絕。王新衡只好留下名片一張,以示來過了。就是這張小小的名片,「保防室」從未交給雷震。雷震出獄後,一次與王新衡閒聊,才得知當年還有過這樣一件事。
「保防室」檢查受刑人書信更是苛刻,近乎不可理喻,「凡有一語他們認為不妥者,就不給你看,或不給你發出。實際上在檢查書信工作的人,都是那些半瓢子水的外役,自己的肚子裡是半通不通的,他們只知道從嚴,只會挑剔。我的來信,看了一遍,馬上就收回去了 ,存放在保防室那裡……我刑滿出獄前幾天,我要索回存在保防室的來信,可是來信不多。在這十年坐牢中,何止一兩百封信呢,只還了二十幾封……殷海光有一封長信,有十頁之多,這封信我記得很清楚,而殷海光在我出獄前的前一年已去世,我要留這封信作為紀念,故一再向保防室提出要求退還此信,他們一概置之不理,仗著他們是蔣經國培植出來的特務,可以無法無天而不顧一切。」
牢中十年,讓雷震沒有想到的是,軍人監獄內腐敗之事,筆不勝書,貪污之奇,「也和政府一樣,最不貪污的監獄長,只要蓋上三、五幢房子,所得就極為可觀……其他如軍監的各工廠購買原料和出售成品,官兵及囚人的伙食費……有的彼此利益均沾,有的則主持者獨吞其款」。雷震說,若不是蔣氏父子將他不折不扣的關了十年,否則,還不會知道軍人監獄中的腐敗情形 。當局對軍監的意識形態控制得相當嚴密,那些低階獄卒,表面上唯唯諾諾,實際上,對國民黨早已心懷不滿,每次軍人監獄大禮堂舉行「國民黨黨員大會」,「黨歌」響成一片,背後卻有人大罵,切齒痛恨。「有一次正遇上一個護士(軍中護士均是男的,同為士兵)給我打針時,我問他何以不去參加?打針遲一點沒有關係。不料那個護士卻氣沖沖地對我說:『哪個人要去參加這些流氓集團?』」。
若論坐牢,雷震早有預感,畢竟是國民黨高官而淪為「階下囚」的,幾十年來,他在國民黨內部,經歷過太多的風風雨雨,對當局打壓異己之手段無所不知,此次坐牢完全因其理念與體制相悖所致,而且純屬「政治構陷」,因此,他的心態較之一般犯人相對平靜和從容。不過,作為當局重要的政治犯,漫長的鐵窗生涯,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與普通犯人毫無二致,雷震在信中對如夫人向筠說,「第一次看眼睛(指眼疾,作者注),如此困難,失去自由的人,多可憐啊!」他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正如馬之驌所說「雷震坐牢十年,之所以能保存了性命,他惟一的『哲學』是他能『欣賞坐牢』」。雷震出獄後,歷史學家唐德剛與他見過一面,兩人談了很多,從中大致可瞭解到雷震當年在獄中的真實心態,唐德剛這樣記述:
這次我與雷先生談了兩個多鐘頭,甚為投契。他告訴我一個人做人要有骨頭,也要有修養。坐牢就要有修養;他說他坐牢十載,左右隔壁的難友都死了,只有他一人活了下來。「有什麼秘訣呢?」我問。「要欣賞坐牢嘛!」雷說時微笑。他說他左右鄰難友都煩躁不堪,一個不斷傻笑,另一個終日唧唧咕咕,大小便都不能控制,結果一個一個死掉。「我想我如不拿出點修養來『欣賞坐牢』,我一定跟他們一樣死掉……」雷說他用修養克制自己,終於神經還能維持不錯亂,而終於「活著出來」。
雷震「欣賞坐牢」的心態,並非一開始時就有。初到看守所時,因憤懣於蔣氏父子對他的「政治構陷」,整整三天未吃任何東西,連一口水也未喝過,打算絕食而死,以示抗爭。後來想到「事情尚未搞明白就絕食而死,蔣氏父子可能誣我『畏罪自殺』,那就太不值得了」。女兒雷美琳回憶,「我父親自己在牢裡頭,他也很注意自己,每天該吃什麼吃什麼,他也不是很消沉的,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寫這個回憶錄,就是說他有一個事情做,有一個目標的話,他就沒有那麼煩躁。」
儘管如此,以雷震的個性,在獄中心情漸漸平靜下來,但骨子裡仍對蔣介石將他送入大牢感到憤激。他時常想到自己從事推動民主政治運動,完全是為了台灣和政府的進步,最後遭如此「政治構陷」,不免內心痛楚。他在獄中寫道:有人告訴我說,「雷公,你是逃不了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這一關的,你總是要坐這個牢的,政府對於輿論的控制,出版法和懲治叛亂條例乃是並行的兩道鉗子,如果覺得出版法的控制不夠勁,就使用最後法寶的懲治叛亂條例,這樣就可以萬無一失。懲治叛亂條例在平時則是備而不用。」
在獄中,雷震多次夢見胡適,可見對先生情感至深,也可見胡適對他的影響最大,以下這篇獄中日記寫於胡適去世一月之後:
昨夜睡得迷迷糊糊,做夢遇到胡先生,好像在上海八仙橋上海銀行樓上,又好像在南港,又好像在自由中國社,做了一晚上的夢。他勸我放棄搞政治,他說我是搞民主政治的健將,今日時候不到,在台灣不適合,這裡根本無民主政治,所以英雄無用〔武〕之地。勸我今後連政治也不要談。他又說過去不來看我,是怕觸怒了蔣先生,其目的是為我。又說他沒有幫到忙,很抱歉,勸我忍耐,勸我逆來順受,勸我放棄搞政治和談政治,勸我從事著述,說我是研究憲法的,中國憲法書很少,勸我寫一部巨著,臨走時勸我保重身體,坐牢人以身〔體〕為重,這樣迷迷糊糊了一晚。醒了一身汗,我想今後還是脫離政治吧!左舜生就退出政治,我也應該這樣。
雷震入獄的後五年,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毛病,軍監醫生查出他已患有前列腺炎,「解小便時即感很不暢通,有時很吃力」,申請出獄做手術的手續十分煩瑣,再加上家中沒有治療費,此事就拖了下來,一直未能得以及時治療,出獄不久,即惡化為前列腺癌。此時雷家經濟狀況十分糟糕,雷震的「國大代表」津貼被取消,其子雷德成患有重病,前後大小手術二十餘次,「最後兩腿全被鋸掉,僅剩軀體」。雷震被關在新店,雷德成住在榮總,一南一北,宋英兩地奔波,孩子們看在眼裡,說母親最可憐,真是筋疲力盡了。雷震在獄中日記中也說,「我想到她過去常說,她總有一天要送牢飯的,有許多事情她比我看得清楚,我還是太天真啊……」
雷德成的病是二十歲那年馬祖服兵役時落下的。馬祖地區只是幾個荒涼的小島,駐軍沒有什麼設施,軍營十分簡陋,海邊搭一個棚子,前後通風,沒有門障,地上鋪著榻榻米,只有一條軍毯。
雷德成與父親一樣,個子高大,軍毯太短,蓋了上身,就遮不住下身,軍醫說是得了風濕性麻痹症。雷震夫婦向當局五次提出請假讓其回台醫治,都未予核准。雷震此時與當局的關係已然緊張,雷德成遂成這場政治衝突中第一個遭遇肉體打擊的人。三年後退伍回到台北,已是完全不能行動。雷震當時找到前衛生署長施純仁大夫進行手術,未獲成功。
在美國的姐姐雷德全,十分心疼這個弟弟,建議母親將其送來美國治療,並說已在羅斯福醫院為他找好了醫生。「母親將全部有關羅斯福醫院所提出的文件,送交當局,準備去辦出臺手續,幾個月下來,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從側面打聽,也不得要領。後來才證實德成弟弟領不到護照,因為當局認定他已是殘廢,政府不能允許殘廢的人出國,當我聽到這一個消息,真是心內咯血,眼冒火花……當局會怕我們在德成弟弟到了美國之後,暴露給新聞界他的一切不幸遭遇,而影響政府的顏面」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雷震出獄前一年,雷德成不幸早逝,「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他的一生還沒有開始,卻在極權專制的政治鬥爭中被犧牲了」,雷震獄中得知,老淚縱橫。
雷震身陷牢獄十年,失去人身自由,在高牆之內,除獄中兩次嫁女無法參加外 ,還有幾件令他痛苦不堪的事:
第一件:下獄數年後,老友高玉樹以無黨派身份高票再次當選第五屆台北市市長 。在獄中,每當雷震聽到很多人在痛罵國民黨為「狗民黨」時,心中不免戚戚焉,確實「難過之至」。雷震二十歲時即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直至被開除黨籍,前後有三十七年黨齡。當看到自己曾經投效多年的政黨被無數人批評或憎恨,不免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應當說,這很真實。「這一晚上,聽到離我囚室不遠的斜坡上,人聲鼎沸,我遂出來看看,見到許許多多充當『外役』的囚人,一堆一堆的群集在那裡,拍手狂歡,狀若得到了『愛國獎券』頭彩似的,其欣喜若狂的樣子,好像發了瘋一樣。我為好奇心所驅使,就跑過去問問他們今晚為什麼這樣高興?是不是有人得了『愛國獎券』的頭彩?他們爭先恐後地對我說道:高玉樹當選了台北市長,『狗民黨』的周百煉落選了!我們高興之至,因為『狗民黨』已失去了台灣的民心。』」 獄友們的肺腑之言,雷震慨然萬千,「不料成天自吹自擂的國民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竟是一個畜類東西……今日這個局面,真是古人所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
第二件:一部近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在出獄前兩月被強行沒收。對雷震來說,撰寫這部回憶錄是獄中十年最重要的一件事,無論是抗日初期國民參政會的成立;或抗戰勝利後,從「國共和談」到「政治協商會議」,及至「制憲國大」,雷震均為重要的親歷者和參與者。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對那一段潮起潮落的歷史真貌,應當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當時獄方奉命將雷震的囚室搜索一空,連一張紙片也未留下。幾十年後,台灣政治大學研究員洪茂雄針對「前東德國安部機密文件展覽」一事,在《自由時報》上撰文,「反觀台灣,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時代,有不少懸案迄今仍不明不白,如一團迷霧。諸如: 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當雷震準備離開黑牢前夕,他憑其堅定不屈的意志在獄中夜以繼日所完成的回憶錄卻不翼而飛,無故沒收,甚至予以銷毀。雷氏出獄後,還相當長一段時間遭監視,形同軟禁。試問,雷震的冤獄始末,誰該負起責任,還其清白?」
第三件:雷震刑滿行將出獄,當局卻提出要有雙重保人,並須簽署一份「誓書」,保證出獄後「絕不發生任何不利於政府之言論與行動,並不與不利於政府之人員往來」。雷震遭此節外生枝,對於坐滿十年冤獄的他來說,內心痛楚可想而知,表示不願出獄。「要我在出獄前立下『誓書』,始能於十年刑期終了時開釋,否則不得出獄。我因為『於法無據』,一再拒絕。我說『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執行期滿者應於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之』,並未附有任何條件。因而,我不肯做『違法』的『法外』之事……於是軍監又通知我妻,要她來監勸我接受這件『法外』的規定。迨我的妻女來監勸我時,我還是拒絕,她們不僅落淚,甚至下跪懇求,我總是無動於衷……我妻不得已,乃請於民國三十八年春,在上海保衛戰中,出生入死,共過患難的谷正綱先生來軍監勸我接受,並勸我要可憐我妻這十年間所受的煎熬和痛苦……過了兩三天,王雲五、陳啟天、谷正綱三位先生來到軍人監獄要我出具誓書時……我看到八十以上的老人王雲五先生這麼遠跑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有含淚而寫」。
所謂「雙重保人」,是指具有兩種不同身份的人出面作保。第一種,乃直系親屬,雷震的選擇是:女婿陳襄夫,時任台灣「中央信託局」高級主管;侄女婿毛富貴,時任台灣鐵路局運務處主管;內姨侄程積寬,原《自由中國》社職員。第二種,乃政治的社會人士,雷震的選擇是:老友王雲五,時任國民大會代表,曾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青年黨領袖陳啟天,前經濟部長,時任青年黨中央主席團成員;國民黨高幹谷正綱,時任大陸救濟總會理事長。
臨將出獄前,對於軍監強取他的稿件、日記等,雷震怒不可遏,五次給監獄長洪破浪寫抗議信,對軍監違法亂紀行為表示嚴重不滿,其中一封抗議信這樣說:
七月二十三日軍監強取了我的稿件、日記,經保防室剪塗過的報刊及自來水筆和台幣等等之後,再加以次日停止接見的不當處分,我的精神上已因此而遭到重大的打擊,故連日服安眠藥和鎮靜劑了,此事可詢問彭醫生……我已坐牢了,生死一切均掌握在軍監的手掌之中,我之受到軍監的折磨和打擊,自在意想之中……我這一次所爭者為法律,為人權,並非坐牢而不安分守己。蔣總統一再訓示部屬要「守法」,而軍監又是一個執法機關,一切自應依法辦事,我們擁護領袖,就必須依照他所訓示的「守法」等等切實去做,僅僅喊喊口號、貼貼標語是算不得擁護的。「知恥」也是蔣總統的訓示,那麼,一切依法辦事才是「知恥」,而違法亂紀就是「無恥」。台灣環境誠然特殊,但是蔣總統叫人「守法」,是在台灣說的,不是在大陸說的,就是要在特殊環境之下實行法治。
我向軍監索取我的稿件,能說這是「不合作」嗎?是不是軍監要我做耶穌,人家打了你的右臉,你還要把左臉再送給人家打啊?現在長話短說:一、軍監如不把不依法而強取的稿件、日記等等還給我,我是不會出獄的;二、《監獄行刑法》上有規定的,我一定照做不誤,其他沒有規定的,我一樣也不做。即使不讓我出去,也是如此。
儘管如此,高牆之內,鐵窗之下,同情雷震的不乏其人。某個深夜,雷震收到過一張偷偷送來的紙條,特別注明閱後立即毀掉,「千萬不可保存,萬一查出筆跡來了,他們要受到嚴厲的處分」。紙條這樣寫道:
德不孤,必有憐,願先生勿因此而氣餒,太公舉於渭水,夷吾囚於士,國父蒙難於英,皆先賢雖殊途而同歸也,凡此三賢,未嘗不先難後獲,危然後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巧立名目,圖窮匕見而已,凡有血性而志在救中國之人,思念先生至此,未嘗不泣血椎心,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後生之心,願先生因此保重玉體健康,繼而異日負救苦難國家而不辭使命而已矣 。
雷震將此內容抄在老友端木愷送給他的那本《聖經》包皮紙裡面,將原件銷毀。端木愷時任東海大學校長,他是著名律師和法學家,雷震被判刑時,他委託梁肅戎作為辯護。雷震入獄後,端木愷特意送來一本《聖經》,「這是他多年來,每天必讀的,送給儆寰兄在苦難中閱讀」,端木愷還把舊約羅馬書第五章二至五節寫在這本《聖經》的封底上,「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明理,明理不至於羞恥……」端木對雷震精神上的支持,使其受到很大的安慰。十年之後,雷震把這本《聖經》帶出了監獄。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許,宋英及兩位女兒在二三親友的陪同下,前往台北青島東路警備總部看守所探望「複判後」的雷震。未料,雷震在一小時之前已被移至新店鎮安坑鄉國防部軍人監獄,宋英等人只好再匆忙乘車趕往新店。
第二天,雷震好友齊世英、夏濤聲、蔣勻田、胡秋原、夏道平、周棄子等七人,前往軍人監獄看望開始服刑的雷震,遭到獄方的拒絕,理由是「每週二、五的例行接見日,求見者以服刑人的親屬為限,朋友沒有必要時,監方可拒絕接見」。實際上,當局已下達有關指令,非親屬探望雷震,「一概得要先經申請,獲得國防部批准,否則免談」。
根據當時的規定,「軍人無論是受審判或服刑,都是按階級而有所不同的。非軍人而受軍法審判的,也依其身份職位比照軍人之待遇」。雷震仍是「國大代表」,相當於軍人「將軍」之銜,可住單人囚室。新店安坑軍人監獄條件比看守所好不了多少,許多設施尚不盡如人意。雷震因高大身材,軍人監獄中的床似乎太小,雷震讓家人送去自己平時睡的那張大床,還有一張桌子,一把籐椅,一張靠椅,以及一個洗澡盆。以雷震的身份,在這裡無需穿囚服,雷震最初兩次會見家屬時,穿的都是西服。後來天氣漸冷,雷震讓家人又送去棉袍。安坑在鄉下,早晚特別涼。在看守所時,家人經常會送一點小菜來。到了這裡,雷震覺得不甚方便,就關照家人不必再天天送了。宋英是每週五探監,如夫人向筠是每週二探監,孩子則分別隨宋英和向筠一起去。朋友們來探望雷震,往往由於見不到人,會留一點水果給他。
有一次,立法委員胡秋原 、成舍我偕雷夫人宋英一起來探監,胡、成二人硬是被擋在了門外。胡秋原只好留下自己的名片,在反面寫道,「儆寰兄:今日兄坐牢,不是壞事;唯坐牢之道,首須安心。安心之法,不外讀書與思想。一當讀輕鬆者,二當讀費腦筋者。蓋唯有用心深思,始能安心也。不得見,所欲告兄者如此……」
雷震在獄中發出的第一封家書,是入獄兩天之後。他讓宋英透過「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負責協商政治解決」,其辦法是「我不參加反對黨,自由中國社改組……希望我今後脫離現實,過一點寫作生活」。十天之後,再次致函宋英,「政治解決,除『總統』外,恐要與經國談談……這裡雖然特別優待,如果再住一二年,也是無法下去的」,信末特別交代「絕對秘密看完燒去不可留」。雷震一直認為此次當局之制裁「決心如鐵」,其關鍵癥結在於參與組黨,因此,想透過「政治協商解決」的方式,來改變目前的困境。應當說,這並非雷震此時萌發出來的「悔意」,而是不想「新黨」因此而胎死腹中,他在信中說「新黨我不能參加,希望他們成功」。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雷震在獄中致函胡適,為他的七十大壽提前祝賀,並向胡適索書,「本月十七日為先生七十大慶,我在獄中不能前來祝壽,謹寫此信代賀……賀壽不能無紀念品,我現在把『讀《胡適文存》校誤表』作為紀念品,向您敬呈……先生還有什麼書,請賜幾本,外國人的傳記(譯本)如有,請賜下幾本。我讀了一本中譯本《阿德諾傳》,給我啟發的地方甚多。」獲悉雷震在獄中開始寫一些回憶性質的文字,胡適感到十分高興。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宋英前往探監,胡適特意托她帶了一封信給雷震,其中說,「我很高興你能夠安心寫回憶的文字了,也很贊成你儘量寫得『白』。但不要學我,趙元任兄常說適之的白話是不夠『白』的」。
自雷震入獄,至一九六二年二月胡適以心臟病猝發逝世的一年多裡,雷震先後給胡適寫過二十餘封信。一九六一年陰曆五月二十六日,雷震六十五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桂源鋪)以相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其寓意,不言自明。第二年,胡適就去世了。聶華苓始終認為「胡適的速死與雷案有關」,唐德剛說「雷震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歲。雷震自己也說,「胡適為我的事,是遭受了冤屈,但胡適本身也有錯誤,他不應該回台的,回來了即等於『甕中之?』,蔣中正就不會買他的賬,胡適也沒有辦法來對抗」。
雷震在獄中受到嚴密監視,有一個「雷震監視班」,共四人,輪流值班。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時與潮》雜誌刊發〈訪監委宋英女士問雷震獄中生活〉一文惹怒了當局,雷震旋被停止會見家屬達半年之久,《時與潮》雜誌也因此被迫停刊一年。這篇文章係《時與潮》記者對宋英的一次專訪實錄,同時附有「雷震獄中自勵詩」一首。宋英在專訪題記中特別感謝「所有海內外關心儆寰之好友的殷殷至情」,並借用《聖經》上的話,稱自己的丈夫「為義而受難」,他的冤屈將得到歷史最公正的評價。關於這首「雷震獄中自勵詩」及自己的心情,宋英這樣說:
這首詩,是儆寰……自新店安坑軍人監獄寄給我的。我讀了他的這首詩後,覺得他在監獄中的心情,已逐漸平和下來,這點對我來說,自是一件最可欣慰的事。儆寰以垂老之年,坐牢已快三年了。自他被捕入獄至今,一直受到海內外甚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的同情和關懷,我個人亦常受到許多友好的熱誠安慰和幫助……一般說來,一個坐牢的人,心情總是不好受的;儆寰坐牢,難免亦是如此;所以儆寰常說自己是個「受難」人。儆寰以所謂「文字叛國罪」被捕的情景,對我來說,真是歷歷在目,有如昨日之事一樣,但它畢竟已是兩年以前的事了,再來舊事重提,似乎無此必要。至於儆寰坐牢,究竟是「罪有應得」,還是如聖經上所說「為義而受難」,這自然只有訴諸世人的公道與良心,和留待後來歷史的判斷……最近,又承《時與潮》雜誌記者先生來訪,承其關心儆寰,探詢他的獄中生活至詳。臨時乃將儆寰寄我已快半年的這首詩,順便交請《時與潮》雜誌發表。
從對宋英的這篇專訪中,可瞭解到雷震前三年的獄中生活主要以寫作為主,多是回憶類的文字。宋英對記者說,「據我觀察,談不到寫作興趣的高低,只能說他精神來得及時就寫……這是一個獄中人寂寞時惟一使用(或發洩)精力靈感的方法和方式。他曾告訴我,寫起來幾千字,還是沒有困難;哪一天精神不濟了,就休息不寫。」當記者問及雷震獄中健康問題,宋英說,「還算好。你想,他到底是六十七歲的人了,再好也沒法與青年人相比。何況他有風濕病,氣候一變化,他就免不了痛苦……」記者又問,先生與入獄前相比有什麼顯著不同,宋英以兩年多來會見雷震時觀察所得,告訴記者「他現在安靜得多了」,「人生經驗比以前更豐富了,容忍的修養更高深了,觀察事理更深入了」。
雷震患有多年失眠症,一直困擾他的健康。宋英對記者說,雷震在入獄後一段時間裡每天確實需要安眠藥才能入睡,「後來因為購買不方便,以及他有意要藉此機會擺脫安眠藥的糾纏,就像一般人戒煙一樣地把『藥』戒掉了。現在他已完全可以不需藥片而能安眠了」。記者詢問當時那場「中西文化論戰」雙方主角 由論爭而訴諸法庭一事,雷震在獄中對此案十分關注,宋英解釋說,「那是雷先生看報知道打筆戰打進法庭,他向來的性情愛關心朋友,便在給我的一封信上順便提了一句,說他認為那件官司打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囑我見到胡秋原先生時,就說儆寰誠意勸胡先生千萬不要繼續打官司,如果不是他在獄中,他一定要給雙方調解息爭」。
記者提出想看一看這封信,宋英表示這是一封夫妻私函「不便公開」。不過,她又說:「我可以把雷先生附有識言的一首詩交給你發表。因為那首詩是〈自勵詩〉,足以說明他的心境和修養的進度。詩後的跋語,等於是一篇日記,可以讓關心他的朋友們知道他的生活情形而放心。那是他親筆寫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時與潮》雜誌第一百六十六期刊表了雷震的這首〈自勵詩〉(附跋),全文如下:
九月九日夜夢到胡適之先生所示容忍與自由因成自勵詩一首。
無分敵友,和氣致祥,多聽意見,少出主張。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見,民主是張。批評責難,攻錯之則,虛心接納,改勉是從,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不飾非;不說大話,不自誇張,少說多做,功成不居。毋揭他人短,毋揚自己長,毋追懷既往,毋幻想將來。忠於信守,悉力以赴,只顧耕耘,莫問收穫。虛心無愧,毀譽由人,當仁不讓,視死如歸。做人和處世,皆賴之以進;治國平天下,更非此莫成。
九月五日夜,颱風肆虐,居室浸水,物件凌亂,黴氣四溢。七日亞英(即宋英,作者注)探視,送來書架一只。九日天晴,乃抖擻精神,將書籍文稿,衣履被服,碗櫥炊具,藥瓶壺盂,以及??罐罐,全部搬到室外曝曬,洗刷拭淨,然後一一搬回室內,上午十二時完畢。其間雖有一人相助,而大部分工作是我一人任之,跑進跑出,不下百次之多。午間小睡後,又趕寫今日應寫的回憶文字,成二千五百字,復利用休息時間,將書籍放到書架上,並略事整理。其他物件,亦均一一放到適當地方,其間曾準備午晚兩餐。晚飯後又洗衣三件。因之精疲力竭,頭昏眼花,晚間運動因而停止。九點鐘即上床休息。不意橫身酸痛,皮膚發燒(太陽曬的),疲勞過甚,竟不能成眠。十一時半又起床出外散步,腹餓吃餅乾兩塊,然後上床再睡。在迷迷糊糊中,忽然夢到適之先生告訴我們「容忍與自由」的意思,因成詩一首,藉以明志自勉。
《時與潮》這篇溫和、平實的專訪遭到台灣當局的責難。《時與潮》是雷震老友齊世英以「立法委員」身份辦的一個黨外刊物,此時齊世英已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多年。雷震說,「蔣氏父子認為這是諷刺語,即下令《時與潮》停刊一年,我則停止接見,不准帶冰箱和電扇。我的停止接見未付期限,一下子停止接見半年,這又是大大違法的」 。雷震在四月二十八日日記中有「《時與潮》載有陶元珍教授〈讀雷儆寰代表(震)獄中詩〉」之記載,第二天,收到老友徐復觀〈讀儆寰獄中詩感賦〉的抄件,足見這首〈自勵詩〉感人至深。
雷震在獄中為爭得自由閱讀報刊合法權利,與獄方做過一番堅決抗爭。軍人監獄規定訂閱的報紙是黨報和軍報。雷震不願看官方刊物,要求訂閱《聯合報》以及一份英文的《中國郵報》。經過兩個月的審核,方才獲准。獄方對於書刊的閱讀管制特別嚴格,雷震所訂《聯合報》,除負責檢查報紙的保防室外,其他受刑人,甚至獄吏、獄卒一律不許看。在那段時間,獄方只要提及《聯合報》,常稱之為「同路報」,意即「自由派的同路者,思想有問題」的報紙。獄官告訴雷震,獄吏和獄卒為了也能瞭解社會大事,常跑到新店公路局車站內看張貼在公告欄上的「同路報」。
雷震在《雷案回憶》和《獄中十年》等書中,經常提及在獄中閱報時的遭遇和不堪心情。獄方雖然特別核准他在獄中訂閱《聯合報》,對每天的報紙仍加以嚴格檢查,並不時查扣,雷震想盡一切辦法爭取自己的閱報權,其中有若干記載:
《聯合報》常常要到下午才送來,上午要經過保防室檢查,其實他們也要看這些同路報,而不要看那些成天歌功頌德的黨報和官報。
可是保防室的檢查,常常扣去一天,我就抗議:不見得報上所載全部我都不能看吧?
於是保防室改變辦法,抽出不給我看的那一張。
我又抗議:難道全張都是不能給我看的嗎?
保防室又改變辦法,把不准我看的那一部分剪去了。
我再又抗議:保防室不准我看的,只有一則新聞,這一剪去一塊,我連背面可以看的也就看不到了。於是保防室又改變辦法,把不要給我看的那一部分用油墨塗去,如何用水洗刷也洗不掉。
雷震被捕之初,確實受到過軍方在某些方面的「優待」。宋英承認「雷先生自入獄後,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獄中生活那樣苦(例如挨打、受辱和做苦工),但也沒有得到家屬親友特別的照顧(例如「監犯有接見任何家屬親友的便利」)……我每禮拜按軍獄的規定,給他送兩次菜去。」 當局無疑知道此次逮捕雷震在海內外引起的震動和反應,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作採用一些辦法來緩解雷震的情緒,對他在獄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儘量給予滿足。
還在看守所時,所長張福慶對雷震透露過,「雷先生過去對於國家有很大的貢獻,這次事情,理由並不充分,自『雷案』發生後,外國的報刊,包括香港在內,對於政府和國民黨,甚至蔣總統都抨擊甚烈,說是『蔣總統鑄下了一項最大的錯誤』。逮捕雷先生是蔣總統下的手令……為補救起見,關照我們對雷先生特別優待,我們自然要照辦的。」 雷震大發感慨,「我聽到這一段話,馬上聯想到許多人所說『外國的月亮圓些!』這話卻不無道理,這些諷刺的話,當是由經驗而來,我的優待就是受了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之賜!」
自發生〈自勵詩〉事件,獄方對雷震的態度立即有所改變,監控得更加嚴密。李敖曾托宋英女士將其新作《胡適評傳》送給獄中的雷震,此書一審查就是十九天。這本《胡適評傳》讓雷震看了許多天,他還將書中「錯誤的地方均一一記出,將來可交給李敖」。
雷震在獄中十年,軍人監獄更換過四位監獄長。他回憶道:
第一位是李玉漢,據說是特務出身,我未見到過;第二位叫做馬光漢,他任軍監監獄長三年,每年倒是來囚室給我拜年,他是對我特別客氣,他知道我是被蔣氏父子誣陷,下令而坐牢,我本身是清白無辜的,所以每年來給我拜年,對其他受刑人當然無此禮貌,和其他監獄長對受刑人是一樣的態度,依然是「牢頭禁子」的作風。第三位姓趙,做了好多年,我根本沒有見過。第四任監獄長叫做「洪濤」(即洪破浪,作者注),係憲兵出身……洪濤任監獄長後作風大變,對待受刑人的態度則大為和善,受刑人都覺得這位監獄長有人性,是一個人,不是牢頭禁子,對我也特別客氣……洪濤到任之後,對於受刑人也舉行「生日會」,使受刑人也得到一點溫暖……受刑人的生日會是在監獄的禮堂中舉行,洪濤和許多監獄官親自參加……我是受蔣氏父子下令不准和大眾見面,所以給我添了幾樣菜,由我一人在監房中吃。這雖是美中不足的事,但不能責怪洪濤,那是他不敢違背獨裁者的命令,除非他不想做官,不要這條命。
以雷震坐牢的親身體會,發現在軍監中態度最為惡劣、最不講道理、又無法律觀念的機構當屬「保防室」。「保防室」名義上屬於軍人監獄政治處代管,實際上是一個特務機構,隸屬蔣經國管轄之下的一個安全室,在軍監中誰也管不了它。「保防室」對雷震特別苛刻,「我所接見的人,要它核可,我除掉家屬和親屬外,任何人也不許接見,連家中燒飯伙夫送菜來時,也不許我接見」。每次會見家屬時,只有三十分鐘,兩部答錄機同時錄音,更有人在一旁監視。立法委員、原「軍統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來軍監探人,提出順便見一見雷震,同樣遭到拒絕。王新衡只好留下名片一張,以示來過了。就是這張小小的名片,「保防室」從未交給雷震。雷震出獄後,一次與王新衡閒聊,才得知當年還有過這樣一件事。
「保防室」檢查受刑人書信更是苛刻,近乎不可理喻,「凡有一語他們認為不妥者,就不給你看,或不給你發出。實際上在檢查書信工作的人,都是那些半瓢子水的外役,自己的肚子裡是半通不通的,他們只知道從嚴,只會挑剔。我的來信,看了一遍,馬上就收回去了 ,存放在保防室那裡……我刑滿出獄前幾天,我要索回存在保防室的來信,可是來信不多。在這十年坐牢中,何止一兩百封信呢,只還了二十幾封……殷海光有一封長信,有十頁之多,這封信我記得很清楚,而殷海光在我出獄前的前一年已去世,我要留這封信作為紀念,故一再向保防室提出要求退還此信,他們一概置之不理,仗著他們是蔣經國培植出來的特務,可以無法無天而不顧一切。」
牢中十年,讓雷震沒有想到的是,軍人監獄內腐敗之事,筆不勝書,貪污之奇,「也和政府一樣,最不貪污的監獄長,只要蓋上三、五幢房子,所得就極為可觀……其他如軍監的各工廠購買原料和出售成品,官兵及囚人的伙食費……有的彼此利益均沾,有的則主持者獨吞其款」。雷震說,若不是蔣氏父子將他不折不扣的關了十年,否則,還不會知道軍人監獄中的腐敗情形 。當局對軍監的意識形態控制得相當嚴密,那些低階獄卒,表面上唯唯諾諾,實際上,對國民黨早已心懷不滿,每次軍人監獄大禮堂舉行「國民黨黨員大會」,「黨歌」響成一片,背後卻有人大罵,切齒痛恨。「有一次正遇上一個護士(軍中護士均是男的,同為士兵)給我打針時,我問他何以不去參加?打針遲一點沒有關係。不料那個護士卻氣沖沖地對我說:『哪個人要去參加這些流氓集團?』」。
若論坐牢,雷震早有預感,畢竟是國民黨高官而淪為「階下囚」的,幾十年來,他在國民黨內部,經歷過太多的風風雨雨,對當局打壓異己之手段無所不知,此次坐牢完全因其理念與體制相悖所致,而且純屬「政治構陷」,因此,他的心態較之一般犯人相對平靜和從容。不過,作為當局重要的政治犯,漫長的鐵窗生涯,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與普通犯人毫無二致,雷震在信中對如夫人向筠說,「第一次看眼睛(指眼疾,作者注),如此困難,失去自由的人,多可憐啊!」他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正如馬之驌所說「雷震坐牢十年,之所以能保存了性命,他惟一的『哲學』是他能『欣賞坐牢』」。雷震出獄後,歷史學家唐德剛與他見過一面,兩人談了很多,從中大致可瞭解到雷震當年在獄中的真實心態,唐德剛這樣記述:
這次我與雷先生談了兩個多鐘頭,甚為投契。他告訴我一個人做人要有骨頭,也要有修養。坐牢就要有修養;他說他坐牢十載,左右隔壁的難友都死了,只有他一人活了下來。「有什麼秘訣呢?」我問。「要欣賞坐牢嘛!」雷說時微笑。他說他左右鄰難友都煩躁不堪,一個不斷傻笑,另一個終日唧唧咕咕,大小便都不能控制,結果一個一個死掉。「我想我如不拿出點修養來『欣賞坐牢』,我一定跟他們一樣死掉……」雷說他用修養克制自己,終於神經還能維持不錯亂,而終於「活著出來」。
雷震「欣賞坐牢」的心態,並非一開始時就有。初到看守所時,因憤懣於蔣氏父子對他的「政治構陷」,整整三天未吃任何東西,連一口水也未喝過,打算絕食而死,以示抗爭。後來想到「事情尚未搞明白就絕食而死,蔣氏父子可能誣我『畏罪自殺』,那就太不值得了」。女兒雷美琳回憶,「我父親自己在牢裡頭,他也很注意自己,每天該吃什麼吃什麼,他也不是很消沉的,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寫這個回憶錄,就是說他有一個事情做,有一個目標的話,他就沒有那麼煩躁。」
儘管如此,以雷震的個性,在獄中心情漸漸平靜下來,但骨子裡仍對蔣介石將他送入大牢感到憤激。他時常想到自己從事推動民主政治運動,完全是為了台灣和政府的進步,最後遭如此「政治構陷」,不免內心痛楚。他在獄中寫道:有人告訴我說,「雷公,你是逃不了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這一關的,你總是要坐這個牢的,政府對於輿論的控制,出版法和懲治叛亂條例乃是並行的兩道鉗子,如果覺得出版法的控制不夠勁,就使用最後法寶的懲治叛亂條例,這樣就可以萬無一失。懲治叛亂條例在平時則是備而不用。」
在獄中,雷震多次夢見胡適,可見對先生情感至深,也可見胡適對他的影響最大,以下這篇獄中日記寫於胡適去世一月之後:
昨夜睡得迷迷糊糊,做夢遇到胡先生,好像在上海八仙橋上海銀行樓上,又好像在南港,又好像在自由中國社,做了一晚上的夢。他勸我放棄搞政治,他說我是搞民主政治的健將,今日時候不到,在台灣不適合,這裡根本無民主政治,所以英雄無用〔武〕之地。勸我今後連政治也不要談。他又說過去不來看我,是怕觸怒了蔣先生,其目的是為我。又說他沒有幫到忙,很抱歉,勸我忍耐,勸我逆來順受,勸我放棄搞政治和談政治,勸我從事著述,說我是研究憲法的,中國憲法書很少,勸我寫一部巨著,臨走時勸我保重身體,坐牢人以身〔體〕為重,這樣迷迷糊糊了一晚。醒了一身汗,我想今後還是脫離政治吧!左舜生就退出政治,我也應該這樣。
雷震入獄的後五年,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毛病,軍監醫生查出他已患有前列腺炎,「解小便時即感很不暢通,有時很吃力」,申請出獄做手術的手續十分煩瑣,再加上家中沒有治療費,此事就拖了下來,一直未能得以及時治療,出獄不久,即惡化為前列腺癌。此時雷家經濟狀況十分糟糕,雷震的「國大代表」津貼被取消,其子雷德成患有重病,前後大小手術二十餘次,「最後兩腿全被鋸掉,僅剩軀體」。雷震被關在新店,雷德成住在榮總,一南一北,宋英兩地奔波,孩子們看在眼裡,說母親最可憐,真是筋疲力盡了。雷震在獄中日記中也說,「我想到她過去常說,她總有一天要送牢飯的,有許多事情她比我看得清楚,我還是太天真啊……」
雷德成的病是二十歲那年馬祖服兵役時落下的。馬祖地區只是幾個荒涼的小島,駐軍沒有什麼設施,軍營十分簡陋,海邊搭一個棚子,前後通風,沒有門障,地上鋪著榻榻米,只有一條軍毯。
雷德成與父親一樣,個子高大,軍毯太短,蓋了上身,就遮不住下身,軍醫說是得了風濕性麻痹症。雷震夫婦向當局五次提出請假讓其回台醫治,都未予核准。雷震此時與當局的關係已然緊張,雷德成遂成這場政治衝突中第一個遭遇肉體打擊的人。三年後退伍回到台北,已是完全不能行動。雷震當時找到前衛生署長施純仁大夫進行手術,未獲成功。
在美國的姐姐雷德全,十分心疼這個弟弟,建議母親將其送來美國治療,並說已在羅斯福醫院為他找好了醫生。「母親將全部有關羅斯福醫院所提出的文件,送交當局,準備去辦出臺手續,幾個月下來,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從側面打聽,也不得要領。後來才證實德成弟弟領不到護照,因為當局認定他已是殘廢,政府不能允許殘廢的人出國,當我聽到這一個消息,真是心內咯血,眼冒火花……當局會怕我們在德成弟弟到了美國之後,暴露給新聞界他的一切不幸遭遇,而影響政府的顏面」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雷震出獄前一年,雷德成不幸早逝,「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他的一生還沒有開始,卻在極權專制的政治鬥爭中被犧牲了」,雷震獄中得知,老淚縱橫。
雷震身陷牢獄十年,失去人身自由,在高牆之內,除獄中兩次嫁女無法參加外 ,還有幾件令他痛苦不堪的事:
第一件:下獄數年後,老友高玉樹以無黨派身份高票再次當選第五屆台北市市長 。在獄中,每當雷震聽到很多人在痛罵國民黨為「狗民黨」時,心中不免戚戚焉,確實「難過之至」。雷震二十歲時即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直至被開除黨籍,前後有三十七年黨齡。當看到自己曾經投效多年的政黨被無數人批評或憎恨,不免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應當說,這很真實。「這一晚上,聽到離我囚室不遠的斜坡上,人聲鼎沸,我遂出來看看,見到許許多多充當『外役』的囚人,一堆一堆的群集在那裡,拍手狂歡,狀若得到了『愛國獎券』頭彩似的,其欣喜若狂的樣子,好像發了瘋一樣。我為好奇心所驅使,就跑過去問問他們今晚為什麼這樣高興?是不是有人得了『愛國獎券』的頭彩?他們爭先恐後地對我說道:高玉樹當選了台北市長,『狗民黨』的周百煉落選了!我們高興之至,因為『狗民黨』已失去了台灣的民心。』」 獄友們的肺腑之言,雷震慨然萬千,「不料成天自吹自擂的國民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竟是一個畜類東西……今日這個局面,真是古人所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
第二件:一部近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在出獄前兩月被強行沒收。對雷震來說,撰寫這部回憶錄是獄中十年最重要的一件事,無論是抗日初期國民參政會的成立;或抗戰勝利後,從「國共和談」到「政治協商會議」,及至「制憲國大」,雷震均為重要的親歷者和參與者。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對那一段潮起潮落的歷史真貌,應當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當時獄方奉命將雷震的囚室搜索一空,連一張紙片也未留下。幾十年後,台灣政治大學研究員洪茂雄針對「前東德國安部機密文件展覽」一事,在《自由時報》上撰文,「反觀台灣,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時代,有不少懸案迄今仍不明不白,如一團迷霧。諸如: 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當雷震準備離開黑牢前夕,他憑其堅定不屈的意志在獄中夜以繼日所完成的回憶錄卻不翼而飛,無故沒收,甚至予以銷毀。雷氏出獄後,還相當長一段時間遭監視,形同軟禁。試問,雷震的冤獄始末,誰該負起責任,還其清白?」
第三件:雷震刑滿行將出獄,當局卻提出要有雙重保人,並須簽署一份「誓書」,保證出獄後「絕不發生任何不利於政府之言論與行動,並不與不利於政府之人員往來」。雷震遭此節外生枝,對於坐滿十年冤獄的他來說,內心痛楚可想而知,表示不願出獄。「要我在出獄前立下『誓書』,始能於十年刑期終了時開釋,否則不得出獄。我因為『於法無據』,一再拒絕。我說『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執行期滿者應於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之』,並未附有任何條件。因而,我不肯做『違法』的『法外』之事……於是軍監又通知我妻,要她來監勸我接受這件『法外』的規定。迨我的妻女來監勸我時,我還是拒絕,她們不僅落淚,甚至下跪懇求,我總是無動於衷……我妻不得已,乃請於民國三十八年春,在上海保衛戰中,出生入死,共過患難的谷正綱先生來軍監勸我接受,並勸我要可憐我妻這十年間所受的煎熬和痛苦……過了兩三天,王雲五、陳啟天、谷正綱三位先生來到軍人監獄要我出具誓書時……我看到八十以上的老人王雲五先生這麼遠跑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有含淚而寫」。
所謂「雙重保人」,是指具有兩種不同身份的人出面作保。第一種,乃直系親屬,雷震的選擇是:女婿陳襄夫,時任台灣「中央信託局」高級主管;侄女婿毛富貴,時任台灣鐵路局運務處主管;內姨侄程積寬,原《自由中國》社職員。第二種,乃政治的社會人士,雷震的選擇是:老友王雲五,時任國民大會代表,曾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青年黨領袖陳啟天,前經濟部長,時任青年黨中央主席團成員;國民黨高幹谷正綱,時任大陸救濟總會理事長。
臨將出獄前,對於軍監強取他的稿件、日記等,雷震怒不可遏,五次給監獄長洪破浪寫抗議信,對軍監違法亂紀行為表示嚴重不滿,其中一封抗議信這樣說:
七月二十三日軍監強取了我的稿件、日記,經保防室剪塗過的報刊及自來水筆和台幣等等之後,再加以次日停止接見的不當處分,我的精神上已因此而遭到重大的打擊,故連日服安眠藥和鎮靜劑了,此事可詢問彭醫生……我已坐牢了,生死一切均掌握在軍監的手掌之中,我之受到軍監的折磨和打擊,自在意想之中……我這一次所爭者為法律,為人權,並非坐牢而不安分守己。蔣總統一再訓示部屬要「守法」,而軍監又是一個執法機關,一切自應依法辦事,我們擁護領袖,就必須依照他所訓示的「守法」等等切實去做,僅僅喊喊口號、貼貼標語是算不得擁護的。「知恥」也是蔣總統的訓示,那麼,一切依法辦事才是「知恥」,而違法亂紀就是「無恥」。台灣環境誠然特殊,但是蔣總統叫人「守法」,是在台灣說的,不是在大陸說的,就是要在特殊環境之下實行法治。
我向軍監索取我的稿件,能說這是「不合作」嗎?是不是軍監要我做耶穌,人家打了你的右臉,你還要把左臉再送給人家打啊?現在長話短說:一、軍監如不把不依法而強取的稿件、日記等等還給我,我是不會出獄的;二、《監獄行刑法》上有規定的,我一定照做不誤,其他沒有規定的,我一樣也不做。即使不讓我出去,也是如此。
儘管如此,高牆之內,鐵窗之下,同情雷震的不乏其人。某個深夜,雷震收到過一張偷偷送來的紙條,特別注明閱後立即毀掉,「千萬不可保存,萬一查出筆跡來了,他們要受到嚴厲的處分」。紙條這樣寫道:
德不孤,必有憐,願先生勿因此而氣餒,太公舉於渭水,夷吾囚於士,國父蒙難於英,皆先賢雖殊途而同歸也,凡此三賢,未嘗不先難後獲,危然後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巧立名目,圖窮匕見而已,凡有血性而志在救中國之人,思念先生至此,未嘗不泣血椎心,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後生之心,願先生因此保重玉體健康,繼而異日負救苦難國家而不辭使命而已矣 。
雷震將此內容抄在老友端木愷送給他的那本《聖經》包皮紙裡面,將原件銷毀。端木愷時任東海大學校長,他是著名律師和法學家,雷震被判刑時,他委託梁肅戎作為辯護。雷震入獄後,端木愷特意送來一本《聖經》,「這是他多年來,每天必讀的,送給儆寰兄在苦難中閱讀」,端木愷還把舊約羅馬書第五章二至五節寫在這本《聖經》的封底上,「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明理,明理不至於羞恥……」端木對雷震精神上的支持,使其受到很大的安慰。十年之後,雷震把這本《聖經》帶出了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