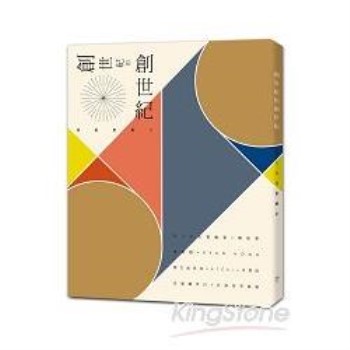中國現代詩的「超現實主義風潮」:一個影響研究的倣作
張漢良
出處:林燿德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文學現象卷》,二七九至二八四頁,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三年。
超現實主義於一九五○年代中期介紹到台灣詩壇來,起初並非有計畫的輸入。詩人在五四運動以來,持續的「影響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之下,對傳統詩與直接前行代(如喜作韻腳工整之浪漫呻吟的徐志摩)反動,很自然地向外借取模式,以與父親形象的傳統抗衡。這種家庭式的父子辯證關係與涉及外國楷模的負影響(negative influence),結合成奧妙的文學演化機械,造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特色,也是比較文學研究者應關心的課題。超現實主義風潮祇不過是這段歷史中的一個插曲。正因為如此,筆者以一九五六年為編年的開始,並非武斷的,而是由於它正好適時出現在紀弦的〈「現代派」宣言〉中。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現代詩》十三期出版,紀弦在革命性的宣言中指出:「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羣。」這些紀弦總稱為「現代主義」的詩派,包括「達達派」與「超現實派」。紀弦並在同期刊物上發表了高克多(Jean Cocteau)譯詩六首。
從此以後, 阿拉貢(Louis Aragon)、許拜維艾爾(Jules Supervielle、米修(Henri Michaux)、德斯諾斯(Robert Desnos)、羅特阿孟(Lautréamont)、素波(Philippe Soupault)、聖約翰濮斯(Saint-John Perse)、杭乃沙(René Char)等人先後被譯介到台灣來。這些詩人,除羅特阿孟外,屬於同一時代,也多少被視為具有超現實主義傾向。但嚴格說來,祇有阿拉貢、素波、德斯諾斯、杭乃沙參加了當年布魯東(André Breton)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其實,布魯東認為「聖約翰濮斯遠望為超現實主義者」(“St.-J. Perse est suréaliste á distance”),至於高克多,布魯東執意把他排除在外,一九二六年甚至指名貶責他。我們指出這些事實,有一個啓迪作用,即:並非所有與布魯東同時代的法國詩人都是超現實主義者;同樣的,譯介他們到台灣詩壇來的媒人,也未必有意宣揚某一詩派,雖然這些法國詩人傳到台灣來之後,會非常意外地被誤判陣營,造成了讀者的誤解、詩壇的混亂,以及比較文學上作家聲譽研究(doxologie)的有趣問題。
與聲譽學相關的另一問題,是媒介學(mésologie),包括翻譯者與發表的刊物等媒介的研究。上述法國詩人分別透過原文(胡品清)、英譯(李英豪、秀陶、柏谷)、日譯(紀弦、葉泥、葉笛)介紹到我國詩壇來。比較傳真的是胡品清。由於覃子豪的魚雁私誼,當年旅居巴黎的女詩人,在覃子豪主編的《藍星季刊》上,譯介了一系列的法國詩人,包括布魯東推崇為超現實主義先驅的藍波(Arthur Rimbaurd)與正牌超現實主義詩人德斯諾斯。胡品清同時(後來)也為《現代詩》、《創世紀》等刊物撰稿,她對台灣超現實主義風潮應有部分推動的作用。除了胡品清的翻譯外,輸入的超現實主義泰半透過英、日叛逆過來,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文獻,布魯東的〈超現實主義宣言〉。
前面曾指出,這些所謂文學世界主義媒人(Agents du cosmopolitisme littéraire),也許無意推動超現實主義運動。以覃子豪為例,除了翻譯外,它至少在兩篇論文中提及超現實主義,但他批評紀弦的「揚棄」與「發揚」論調時,指出:「達達派的原始觀念和超現實派的囈語,何嘗不是流弊?標榜達達派與超現實派,無形的就否定了所謂健康的,向上部分的發揚。」刊載布魯東宣言的《笠》,竟然在譯文前加案語:「本刊並不做此種主張」云云。
另外,有少數詩人研讀超現實主義理論與(或)作品,並且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實踐其創作方法,進而權充媒人,有意地引介。這就是《創世紀》詩社的少數成員。據瘂弦某次表示,最先研究超現實主義的是商禽。一九五八年二月,《南北笛》十八期發表了瘂弦的詩〈給超現實主義者——紀念與商禽在一起的日子〉。這首詩有特殊的歧義,它可能同時透露兩人對超現實主義的了解,或者其中一人的了解。無論真相如何,這種了解是相當深入的:
你渴望能在另一個世界聞到蕎麥香
把一切搗碎
又把一切拼湊
(十九~二十一行)
⋯⋯
你不屬於邏輯
邏輯的鋼釘
甚至,你也不屬於詩
(三十三~三十五行)
遺憾的是,商禽有關超現實主義的理論文字很少。惟一接近布魯東觀念的是〈詩的演出〉中的一句話:「不論詩人或讀者,請把所有的官能:視的、聽的、觸的、想的(便是思考的)全部動員,在各自的心中建立『舞台』,『詩』在那裡『演出』!」但這個觀念並非超現實主義自動語言論專利,它可以擺在許多不同派別的理論格式裡,如象徵主義。我們很難追溯它的血緣。商禽之為超現實主義詩人,已成公論,尤其〈躍場〉、〈遙遠的的催眠〉、〈透支的足印〉等詩最為代表,雖然就此論點徹底研究其詩作的論文尚未出現。至於商禽透過何種媒介、讀過何人作品、如何接受影響,這些問題祇有留待日後考據(或無法考據)。
一九六○年初,瘂弦在《創世紀》十四期(改版趨向前衛後第二期)上發表了論文〈詩人手札〉。作者以小部分篇幅介紹超現實主義的思想淵源、理論及重要詩人,同時指出中國「靆靆和超現實主義影響下的作品至今尚不多見。」瘂弦對超現實主義顯然是認可的,他說:「一種較之任何前輩詩人所發現或表現過的更原始的真實,存在於靆靆主義與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者底詩中,一種無意識的心理世界(The World of unconscious mind)的獨創表現,使他們底藝術成為令人驚悚(有時也令人愉悅)的靈魂探險的速記。」可惜這篇論文是以詩話與札記方式寫出,未註明出處,實證主義學者無法判斷它的資料來源,以及瘂弦是否透過媒人(包括翻譯與其他二手資料提供者)接受了布魯東的觀念。
高舉超現實主義大纛的《創世紀》詩人是洛夫。他坦承「在寫《石室之死亡》一詩之前,尚未正式研究過超現實主義。」《石室之死亡》一九五九年開始在《創世紀》連載。到底何時開始正式與非正式地研究,我們無法得知。從商禽、瘂弦、洛夫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實證主義的影響研究學者蒐集資料時,必須大量求助於未發表的或不宜發表的信札、日記,以及不能發表的或無法確定的訪問、面談。
張漢良
出處:林燿德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文學現象卷》,二七九至二八四頁,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三年。
超現實主義於一九五○年代中期介紹到台灣詩壇來,起初並非有計畫的輸入。詩人在五四運動以來,持續的「影響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之下,對傳統詩與直接前行代(如喜作韻腳工整之浪漫呻吟的徐志摩)反動,很自然地向外借取模式,以與父親形象的傳統抗衡。這種家庭式的父子辯證關係與涉及外國楷模的負影響(negative influence),結合成奧妙的文學演化機械,造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特色,也是比較文學研究者應關心的課題。超現實主義風潮祇不過是這段歷史中的一個插曲。正因為如此,筆者以一九五六年為編年的開始,並非武斷的,而是由於它正好適時出現在紀弦的〈「現代派」宣言〉中。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現代詩》十三期出版,紀弦在革命性的宣言中指出:「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羣。」這些紀弦總稱為「現代主義」的詩派,包括「達達派」與「超現實派」。紀弦並在同期刊物上發表了高克多(Jean Cocteau)譯詩六首。
從此以後, 阿拉貢(Louis Aragon)、許拜維艾爾(Jules Supervielle、米修(Henri Michaux)、德斯諾斯(Robert Desnos)、羅特阿孟(Lautréamont)、素波(Philippe Soupault)、聖約翰濮斯(Saint-John Perse)、杭乃沙(René Char)等人先後被譯介到台灣來。這些詩人,除羅特阿孟外,屬於同一時代,也多少被視為具有超現實主義傾向。但嚴格說來,祇有阿拉貢、素波、德斯諾斯、杭乃沙參加了當年布魯東(André Breton)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其實,布魯東認為「聖約翰濮斯遠望為超現實主義者」(“St.-J. Perse est suréaliste á distance”),至於高克多,布魯東執意把他排除在外,一九二六年甚至指名貶責他。我們指出這些事實,有一個啓迪作用,即:並非所有與布魯東同時代的法國詩人都是超現實主義者;同樣的,譯介他們到台灣詩壇來的媒人,也未必有意宣揚某一詩派,雖然這些法國詩人傳到台灣來之後,會非常意外地被誤判陣營,造成了讀者的誤解、詩壇的混亂,以及比較文學上作家聲譽研究(doxologie)的有趣問題。
與聲譽學相關的另一問題,是媒介學(mésologie),包括翻譯者與發表的刊物等媒介的研究。上述法國詩人分別透過原文(胡品清)、英譯(李英豪、秀陶、柏谷)、日譯(紀弦、葉泥、葉笛)介紹到我國詩壇來。比較傳真的是胡品清。由於覃子豪的魚雁私誼,當年旅居巴黎的女詩人,在覃子豪主編的《藍星季刊》上,譯介了一系列的法國詩人,包括布魯東推崇為超現實主義先驅的藍波(Arthur Rimbaurd)與正牌超現實主義詩人德斯諾斯。胡品清同時(後來)也為《現代詩》、《創世紀》等刊物撰稿,她對台灣超現實主義風潮應有部分推動的作用。除了胡品清的翻譯外,輸入的超現實主義泰半透過英、日叛逆過來,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文獻,布魯東的〈超現實主義宣言〉。
前面曾指出,這些所謂文學世界主義媒人(Agents du cosmopolitisme littéraire),也許無意推動超現實主義運動。以覃子豪為例,除了翻譯外,它至少在兩篇論文中提及超現實主義,但他批評紀弦的「揚棄」與「發揚」論調時,指出:「達達派的原始觀念和超現實派的囈語,何嘗不是流弊?標榜達達派與超現實派,無形的就否定了所謂健康的,向上部分的發揚。」刊載布魯東宣言的《笠》,竟然在譯文前加案語:「本刊並不做此種主張」云云。
另外,有少數詩人研讀超現實主義理論與(或)作品,並且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實踐其創作方法,進而權充媒人,有意地引介。這就是《創世紀》詩社的少數成員。據瘂弦某次表示,最先研究超現實主義的是商禽。一九五八年二月,《南北笛》十八期發表了瘂弦的詩〈給超現實主義者——紀念與商禽在一起的日子〉。這首詩有特殊的歧義,它可能同時透露兩人對超現實主義的了解,或者其中一人的了解。無論真相如何,這種了解是相當深入的:
你渴望能在另一個世界聞到蕎麥香
把一切搗碎
又把一切拼湊
(十九~二十一行)
⋯⋯
你不屬於邏輯
邏輯的鋼釘
甚至,你也不屬於詩
(三十三~三十五行)
遺憾的是,商禽有關超現實主義的理論文字很少。惟一接近布魯東觀念的是〈詩的演出〉中的一句話:「不論詩人或讀者,請把所有的官能:視的、聽的、觸的、想的(便是思考的)全部動員,在各自的心中建立『舞台』,『詩』在那裡『演出』!」但這個觀念並非超現實主義自動語言論專利,它可以擺在許多不同派別的理論格式裡,如象徵主義。我們很難追溯它的血緣。商禽之為超現實主義詩人,已成公論,尤其〈躍場〉、〈遙遠的的催眠〉、〈透支的足印〉等詩最為代表,雖然就此論點徹底研究其詩作的論文尚未出現。至於商禽透過何種媒介、讀過何人作品、如何接受影響,這些問題祇有留待日後考據(或無法考據)。
一九六○年初,瘂弦在《創世紀》十四期(改版趨向前衛後第二期)上發表了論文〈詩人手札〉。作者以小部分篇幅介紹超現實主義的思想淵源、理論及重要詩人,同時指出中國「靆靆和超現實主義影響下的作品至今尚不多見。」瘂弦對超現實主義顯然是認可的,他說:「一種較之任何前輩詩人所發現或表現過的更原始的真實,存在於靆靆主義與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者底詩中,一種無意識的心理世界(The World of unconscious mind)的獨創表現,使他們底藝術成為令人驚悚(有時也令人愉悅)的靈魂探險的速記。」可惜這篇論文是以詩話與札記方式寫出,未註明出處,實證主義學者無法判斷它的資料來源,以及瘂弦是否透過媒人(包括翻譯與其他二手資料提供者)接受了布魯東的觀念。
高舉超現實主義大纛的《創世紀》詩人是洛夫。他坦承「在寫《石室之死亡》一詩之前,尚未正式研究過超現實主義。」《石室之死亡》一九五九年開始在《創世紀》連載。到底何時開始正式與非正式地研究,我們無法得知。從商禽、瘂弦、洛夫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實證主義的影響研究學者蒐集資料時,必須大量求助於未發表的或不宜發表的信札、日記,以及不能發表的或無法確定的訪問、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