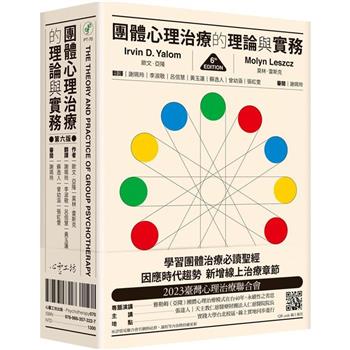第六版前言
從這本教科書第五版出版至今,已過了15個年頭,我們在第六版的任務是闡述這些年團體治療出現的新興且重要的創新。我們很高興也很感謝我們長期的合作能持續,這樣的合作緣起於40年前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我們以經驗豐富的協同治療師之姿共同工作;在撰寫本版時,我們也力求彼此的支持和挑戰。我們大多以「我們」一詞來表達雙方融合的看法,在某些段落,為了準確傳達這是我們其中一位的經驗,我們會切換為第一人稱,並以括號及其中的縮寫表示這是我們其中哪一位的述說(亞隆或雷斯克)。
我們的目的是將團體治療實務之新知識和智慧結晶的整合內容提供給讀者,我們大量採用臨床案例將這些概念和原則帶到眼前,使這本書既實用又具有指導性。和過去的版本一樣,這本書的對象是學生、受訓者、一線專業人員,以及督導者和教師們。
團體治療自1940年代首次問世後,治療方式便一直不斷調整以反映臨床實務的變化。隨著新的臨床症候群、場域和理論取徑的出現,團體治療也有相對應的變異,其形式的繁多在今日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提到團體治療時,以複數稱之(group therapies)比以單數稱之更為合宜。在所有的年齡層和臨床需求上,都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團體治療的有效性,其效果通常與個別治療相當,而且所需成本低得多,在心理健康和物質使用障礙症以及生理疾病的處遇上都是如此。
網路使今日團體治療的觸及比前數位時代便利許多,地理環境不再像以前那樣是治療的阻礙,新的技術平台為團體治療師創造了新的機會和挑戰,當團體治療從團體治療室搬到團體螢幕上時,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我們在此版以新的一章〈線上心理治療團體〉討論這些問題(見第十四章)。
現在,進入團體治療的案主常來自多樣種族文化背景,可能來自於北美或是其他地方,隨著此現象,很重要的是,治療師們必須發展出多元文化取向,以及適配於文化的敏感性和專業知識。治療性團體一直是進行「困難談話」與揭露的場域,在具有反應性的治療團體環境中,種族和性別認同議題可以獲得有效的處理(見第十六章)。團體治療是一個對遭受創傷和流離失所的人們工作的有力工具。
然而,矛盾的是,團體治療師的專業訓練並未跟上團體治療在臨床應用上已遍布開花的步調。愈來愈少訓練方案提供的訓練和督導能達到未來工作者需要的深度,無論是在心理學、社會工作、諮商或精神醫學領域。治療師在僅接受少許團體治療訓練或督導下,即被逼上戰場要求帶領團體,而團體中的案主有複雜的過去史與形形色色的需求,此狀況屢見不鮮。經濟壓力、專業領域的爭鬥,以及現今心理衛生領域中生物性解釋與藥物治療占主導地位,都促成了這種狀況。每一個世代都天真地相信自己已經發現真正的解決方法。心理健康是一個特別容易因擺盪於極度高估和極度貶抑之間而受影響的領域,甚至也會受自家領域內的實務工作者影響。因此我們非常樂見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最近認可團體心理治療是一門特定的專業領域,此一決定將激發在教育與訓練上挹注更多的投資,我們希望這能將團體治療提升到符應其在實務上不斷擴展的地位,我們知道培訓是可以徹底造成改變的。
今日的團體治療師因實務上對於當責程度要求增加而受到影響,實證導向的實務是我們必須完全遵守的標準。許多年來,實務工作者抵制這種強調使用研究、測量和數據做為實務之有效指引的方式,認為這是對他們工作的侵犯,侵犯了他們的自主權且壓縮了創造力,但是將實證導向的實務視為綁手綁腳地牽制是不合時宜的,我們認為更有效的方法是將實證導向的實務視為一套提高臨床有效性的指引與原則(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我們在本書闡述了實證導向團體治療師的特徵:建立有凝聚力的團體和緊密的關係、有效地傳遞真誠和準確的同理心、處理反移情,以及保持文化的覺察力和敏感度。能反思我們的工作方式,並將持續的專業發展視為悉心關注的焦點,是實證導向團體治療師的樣貌。我們從進行中的團體蒐集資料,讓我們能對實際發生在各次聚會和在每位案主身上的情況,獲得即時和重要的回饋(見第十三章)。
我們注意到團體治療師現在在他們的工作中使用一系列令人眼花撩亂的方法,認知—行為、心理教育、人際取向、完形、支持性—表達性、現代分析取向、精神分析、動力—人際取向、心理劇,以及還有其他更多樣的方式,都被運用在現今的團體治療中。團體治療師還將我們對人類依戀的理解和人際關係的神經生物學知識帶入團體治療,致力將心智、身體和大腦融入他們的工作中(見第二章與第三章)。
儘管單單以一本書處理所有的團體治療法有很多挑戰,但是我們相信本書第一版所依循的策略仍是明智的,此策略即是在討論每個團體治療方法時將「表面」(front)與「核心」(core)分開來看。表面是指樣貌、形式、技術、專門語言和各家理論學派周邊的光環核心是指治療歷程內在帶有的種種經驗,也就是改變的基本機轉。
假如你不考慮「表面」,只考慮案主自身產生改變的實際機轉,你會發現改變機轉的數量有限,而且在不同團體之間非常相似。有相似目標的治療團體如果僅依其外在形式來看,會顯得截然不同,但卻可能仰賴著相同的改變機轉,這些機轉繼續構成本書的核心梗概。我們首先詳細討論11個療效因素,然後描述建立在這些療效因素之上的團體心理治療方法(見第一、二、三、四章)。 決定要討論哪一類型的團體是另一個難題,團體治療方法現在如此繁多,要分別討論各種團體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把討論聚焦在一個原型的情況,即門診心理治療團體,並提供一套原則使治療師能夠修改這個基本的團體模式,以適合各種特定的臨床情況(見第十五章)。
我們的原型門診心理治療團體至少要進行幾個月,此團體以緩解症狀和改變人格為宏旨,我們詳細闡述此團體從醞釀到結束的歷程,首先是有效篩選、團體組成和行前準備的原則(見第八、九章),再來是團體的發展,從團體第一次聚會到團體的進階期,以及常見的臨床挑戰(見第十、十一、十二章)。
因經濟因素所迫,當代治療領域被其他較短期、目標更為局限的團體所主導,而在此狀況下為什麼要關注這種特殊形式的團體治療?答案是,長期團體治療已經存在數十年,實務工作者已經從實徵研究和深思熟慮的臨床觀察中累積大量知識。我們認為我們在本書中描述的原型團體是一種密集的、企圖宏大的治療形式,對案主和治療師的要求都很高,這個團體也為治療師提供一個特別的視角,可藉由它來學習團體歷程、團體動力和團體帶領,而這些將會在他們全面的臨床工作發揮作用。帶領這樣一個團體所需的治療策略與技術是精細且複雜的(見第五、六、七章),然而,一旦學習者有所掌握,了解如何修改這些以運用於特定的治療情境,他們便能發展出在各式場域對各種臨床族群皆有效的團體治療方式。
受訓者應該自許成為富有創造性和悲憫之心的治療師,了解如何將理論應用於實務;同樣地,有悲憫之心的督導者也要有如此的理解(見第十六章)。臨床照護的需求不斷增加,加上團體治療的有效性和效率,使團體治療能成為符合未來所需的治療形式,團體治療師需盡可能地準備好迎向這些機會。團體治療師也要能夠好好地照顧自己,這樣才能持續有效地為他人處遇,並在工作中找尋到意義。
因為本書的大多數讀者都是臨床工作者,本書的目的乃是要與臨床有密切的相關性,然而,我們也認為臨床工作者必須與研究領域保持接軌,即使治療師不親自參與研究,也必須知道如何評估他人的研究。
本書最重要的基本假設之一是,此時此地的人際互動在有效的團體治療中至關重要。真正有力的治療團體能提供一個舞台,案主們能在這個舞台上自由地與他人互動,然後幫助成員辨識和理解他們互動中的問題,最終讓我們的案主能夠改變那些適應不良的型態。我們相信僅建立在其他假設的團體無法獲得完整的治療成果,例如心理教育或認知—行為取向。任何一種團體治療形式都可以藉由加入對人際關係歷程的覺察而變得更為有效,我們在本書深入探討互動性聚焦(interactional focus)的範疇和性質,以及它為性格和人際關係帶來明顯變化的能力。互動性聚焦是團體治療的引擎,有能力利用它的治療師更有能力進行各式團體治療,即使其團體模式未強調或未認可互動的中心地位亦然(見第十五章)。
我(亞隆)的小說《叔本華的眼淚》(The Schopenhauer Cure)可以做為本書的共同讀本,它以一個治療團體為背景,描述了本書所述的多項團體歷程和治療師技巧的原則,因此,在本版的幾個地方,我們請讀者閱讀《叔本華的眼淚》中對治療師技術作虛構描繪的段落。
過於厚重的書往往最終會被放在「參考書」的書架上,為了避免這種命運,我們不願意大幅增加本書的篇幅,因此,我們在增添許多新材料時不得不刪去舊的段落和引文。這是一個痛苦的任務,刪除許多被劃去的段落傷了我們的心也傷了我們的手,但我們希望這個成果是一部符合現今的、跟上時代的作品,能夠為學生和專業人員在未來15年及更長的時間裡提供良好的幫助。
第一章 療效因素
團體治療能幫助案主嗎?是的,確實可以。大量療效研究已一致且清楚地證實團體治療是極為有效的心理治療方式,它在提供助益上的力量不但至少等同於個別治療,它還能更為有效率地運用心理健康醫療資源。1然而吊詭的是,心理健康的專業培育課程卻縮減了團體治療的訓練。這是個極需關注的現象:如果我們想帶來我們所期待,同時也是案主所需要的影響力,便需要確保團體治療具有高品質。2有助於治療效果的團體因素和帶領者的特徵,便是本書全書的重點。
團體治療如何幫助案主?也許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但如果我們能以精準且明確的測量工具來回答這個問題,那麼對於處理心理治療中最惱人且最受爭議的問題,心中就能有判斷的準則了。一旦這個準則確定後,便可依改變過程的重要面向制訂出一套理論依據,而治療師也可根據這些來釐訂策略,據此形塑團體經驗,以使它在各種案主、各式情境上能發揮最大的火力。雖然團體治療是有效的,治療師們在有效性上仍有極大的不同。3知曉如何最能推動這些具有療效的歷程,便是團體治療有效工作的核心,還好我們可以由研究證據得到許多方向,光有經驗並不等於有較佳的效果,那麼如何才會有較佳效果呢?答案是深思地工作、自省、獲得對工作的回饋,以及靈敏地運用具備同理與同調之治療關係。4
我們認為治療中的改變是十分複雜的過程,它經由人類各種錯綜複雜的經驗交互作用而產生,我把這種交互作用稱為「療效因素」(therapeutic factors)。由簡單面來探討複雜面,從基本細部歷程來了解整體現象,有相當大的好處,因此,我們將以描述及討論這些細部因素來開頭。
依我們的觀點,具治療性的經驗可自然分為下列11個主要因素:
1.灌輸希望(Instillation of hope)
2.普同感(Universality)
3.傳遞訊息(Imparting information)
4.利他主義(Altruism)
5.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現(The corrective recapitulation of the primary family group)
6.發展社交技巧(Development of socializing techniques)
7.行為模仿(Imitative behavior)
8.人際學習(Interpersonal learning)
9.團體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
10.情緒宣洩(Catharsis)
11.存在性因素(Existential factors)
我們在本章會討論前7個因素。因為「人際學習」和「團體凝聚力」非常重要與複雜,我們將它們安排在後續兩章中單獨討論。「存在性因素」將在第四章討論,因為與那一章的其他內容擺在一起,它們會最容易被了解。「情緒宣洩」與其他因素是息息相關的,因此也會在第四章一併討論。
這些因素之間的區分是人為的,雖然我們一一討論,但這些因素彼此間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並不是獨立發生作用的。此外,這些因素代表的是改變歷程的不同環節,有些因素發生在認知層次(例如,人際學習),有些因素發生在行為改變層次(例如發展社會技巧),有些發生在情緒層次(例如情緒宣洩),有些本身既是療效力量又是改變的前提(例如凝聚力)。雖然相同的療效因素發生在各種團體治療中,但它們的交互作用和相對重要性在各團體中有著極大的不同,而且,由於個別差異,同一個團體的成員感到獲益的療效因素也不同。5
請謹記療效因素乃是人為的建構,我們甚至可以將之視為對在學讀者提供的認知地圖。6這組療效因素並非不可替換,其他臨床工作者與研究者有提出不同的因素組合,雖然那些組合同樣也是人為的。某研究團隊認為一項核心的療效因素是:案主對其情緒表露與關係覺察可化為社會學習懷抱著希望。7沒有任何解釋系統可以涵蓋所有的治療,治療歷程的核心極為複雜,由經驗走向此核心的途徑幾不勝數(我們會在第四章更完整地討論這些相關議題)。
我們在此提出的這組療效因素乃得自於我們的臨床經驗、其他治療師的經驗、在團體治療獲得成功處遇之案主的觀點,及相關的系統性研究。然而,這些訊息來源並非無可質疑,不論團體成員或團體帶領者都不是全然客觀的,而且我們的研究方法常常也有限制。
我們從團體治療師們得到一些療效因素清單,其中真是五花八門且相互矛盾,這反映出探查了範圍廣泛的案主與團體。治療師們絕不是公正無私或不偏不倚的觀察者,他們為了鑽研某種治療方法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們的回答大多由他們所信服的學派所決定,這乃是效忠效應(the allegiance effect)。8即使在抱持相同理念、說著相同語言的治療師群,對於案主進步的原因也不盡有共識。但對此我們並不訝異,在心理治療史上,處處可見帶來效果的治療師,但療癒之道卻非其所以為的理由。誰不曾碰過不知所以大幅進步的案主呢?
訊息的重要來源是由團體成員判斷他們認為最有幫助和最沒幫助的療效因素,研究者會繼續提出有關探討療效因素上的重要問題,像是療效因素對所有團體成員有著同樣的影響力嗎?影響案主反應的因素是什麼?是與治療師的關係或與團體的關係嗎?治療品質或深度有何影響力?9再者,研究還顯示團體成員所重視的療效因素,可能與其治療師或團體觀察員所認為的大不相同。10成員的反應也可能受其他許多因素影響:團體類型(即門診、住院、日間留院或短期治療);11案主的年齡與診斷;12案主的動機階段與依戀風格;13團體帶領者的理念;14以及案主們對同一事件有著不同的經驗,也會影響著彼此的經驗。15
從這本教科書第五版出版至今,已過了15個年頭,我們在第六版的任務是闡述這些年團體治療出現的新興且重要的創新。我們很高興也很感謝我們長期的合作能持續,這樣的合作緣起於40年前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我們以經驗豐富的協同治療師之姿共同工作;在撰寫本版時,我們也力求彼此的支持和挑戰。我們大多以「我們」一詞來表達雙方融合的看法,在某些段落,為了準確傳達這是我們其中一位的經驗,我們會切換為第一人稱,並以括號及其中的縮寫表示這是我們其中哪一位的述說(亞隆或雷斯克)。
我們的目的是將團體治療實務之新知識和智慧結晶的整合內容提供給讀者,我們大量採用臨床案例將這些概念和原則帶到眼前,使這本書既實用又具有指導性。和過去的版本一樣,這本書的對象是學生、受訓者、一線專業人員,以及督導者和教師們。
團體治療自1940年代首次問世後,治療方式便一直不斷調整以反映臨床實務的變化。隨著新的臨床症候群、場域和理論取徑的出現,團體治療也有相對應的變異,其形式的繁多在今日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提到團體治療時,以複數稱之(group therapies)比以單數稱之更為合宜。在所有的年齡層和臨床需求上,都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團體治療的有效性,其效果通常與個別治療相當,而且所需成本低得多,在心理健康和物質使用障礙症以及生理疾病的處遇上都是如此。
網路使今日團體治療的觸及比前數位時代便利許多,地理環境不再像以前那樣是治療的阻礙,新的技術平台為團體治療師創造了新的機會和挑戰,當團體治療從團體治療室搬到團體螢幕上時,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我們在此版以新的一章〈線上心理治療團體〉討論這些問題(見第十四章)。
現在,進入團體治療的案主常來自多樣種族文化背景,可能來自於北美或是其他地方,隨著此現象,很重要的是,治療師們必須發展出多元文化取向,以及適配於文化的敏感性和專業知識。治療性團體一直是進行「困難談話」與揭露的場域,在具有反應性的治療團體環境中,種族和性別認同議題可以獲得有效的處理(見第十六章)。團體治療是一個對遭受創傷和流離失所的人們工作的有力工具。
然而,矛盾的是,團體治療師的專業訓練並未跟上團體治療在臨床應用上已遍布開花的步調。愈來愈少訓練方案提供的訓練和督導能達到未來工作者需要的深度,無論是在心理學、社會工作、諮商或精神醫學領域。治療師在僅接受少許團體治療訓練或督導下,即被逼上戰場要求帶領團體,而團體中的案主有複雜的過去史與形形色色的需求,此狀況屢見不鮮。經濟壓力、專業領域的爭鬥,以及現今心理衛生領域中生物性解釋與藥物治療占主導地位,都促成了這種狀況。每一個世代都天真地相信自己已經發現真正的解決方法。心理健康是一個特別容易因擺盪於極度高估和極度貶抑之間而受影響的領域,甚至也會受自家領域內的實務工作者影響。因此我們非常樂見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最近認可團體心理治療是一門特定的專業領域,此一決定將激發在教育與訓練上挹注更多的投資,我們希望這能將團體治療提升到符應其在實務上不斷擴展的地位,我們知道培訓是可以徹底造成改變的。
今日的團體治療師因實務上對於當責程度要求增加而受到影響,實證導向的實務是我們必須完全遵守的標準。許多年來,實務工作者抵制這種強調使用研究、測量和數據做為實務之有效指引的方式,認為這是對他們工作的侵犯,侵犯了他們的自主權且壓縮了創造力,但是將實證導向的實務視為綁手綁腳地牽制是不合時宜的,我們認為更有效的方法是將實證導向的實務視為一套提高臨床有效性的指引與原則(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我們在本書闡述了實證導向團體治療師的特徵:建立有凝聚力的團體和緊密的關係、有效地傳遞真誠和準確的同理心、處理反移情,以及保持文化的覺察力和敏感度。能反思我們的工作方式,並將持續的專業發展視為悉心關注的焦點,是實證導向團體治療師的樣貌。我們從進行中的團體蒐集資料,讓我們能對實際發生在各次聚會和在每位案主身上的情況,獲得即時和重要的回饋(見第十三章)。
我們注意到團體治療師現在在他們的工作中使用一系列令人眼花撩亂的方法,認知—行為、心理教育、人際取向、完形、支持性—表達性、現代分析取向、精神分析、動力—人際取向、心理劇,以及還有其他更多樣的方式,都被運用在現今的團體治療中。團體治療師還將我們對人類依戀的理解和人際關係的神經生物學知識帶入團體治療,致力將心智、身體和大腦融入他們的工作中(見第二章與第三章)。
儘管單單以一本書處理所有的團體治療法有很多挑戰,但是我們相信本書第一版所依循的策略仍是明智的,此策略即是在討論每個團體治療方法時將「表面」(front)與「核心」(core)分開來看。表面是指樣貌、形式、技術、專門語言和各家理論學派周邊的光環核心是指治療歷程內在帶有的種種經驗,也就是改變的基本機轉。
假如你不考慮「表面」,只考慮案主自身產生改變的實際機轉,你會發現改變機轉的數量有限,而且在不同團體之間非常相似。有相似目標的治療團體如果僅依其外在形式來看,會顯得截然不同,但卻可能仰賴著相同的改變機轉,這些機轉繼續構成本書的核心梗概。我們首先詳細討論11個療效因素,然後描述建立在這些療效因素之上的團體心理治療方法(見第一、二、三、四章)。 決定要討論哪一類型的團體是另一個難題,團體治療方法現在如此繁多,要分別討論各種團體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把討論聚焦在一個原型的情況,即門診心理治療團體,並提供一套原則使治療師能夠修改這個基本的團體模式,以適合各種特定的臨床情況(見第十五章)。
我們的原型門診心理治療團體至少要進行幾個月,此團體以緩解症狀和改變人格為宏旨,我們詳細闡述此團體從醞釀到結束的歷程,首先是有效篩選、團體組成和行前準備的原則(見第八、九章),再來是團體的發展,從團體第一次聚會到團體的進階期,以及常見的臨床挑戰(見第十、十一、十二章)。
因經濟因素所迫,當代治療領域被其他較短期、目標更為局限的團體所主導,而在此狀況下為什麼要關注這種特殊形式的團體治療?答案是,長期團體治療已經存在數十年,實務工作者已經從實徵研究和深思熟慮的臨床觀察中累積大量知識。我們認為我們在本書中描述的原型團體是一種密集的、企圖宏大的治療形式,對案主和治療師的要求都很高,這個團體也為治療師提供一個特別的視角,可藉由它來學習團體歷程、團體動力和團體帶領,而這些將會在他們全面的臨床工作發揮作用。帶領這樣一個團體所需的治療策略與技術是精細且複雜的(見第五、六、七章),然而,一旦學習者有所掌握,了解如何修改這些以運用於特定的治療情境,他們便能發展出在各式場域對各種臨床族群皆有效的團體治療方式。
受訓者應該自許成為富有創造性和悲憫之心的治療師,了解如何將理論應用於實務;同樣地,有悲憫之心的督導者也要有如此的理解(見第十六章)。臨床照護的需求不斷增加,加上團體治療的有效性和效率,使團體治療能成為符合未來所需的治療形式,團體治療師需盡可能地準備好迎向這些機會。團體治療師也要能夠好好地照顧自己,這樣才能持續有效地為他人處遇,並在工作中找尋到意義。
因為本書的大多數讀者都是臨床工作者,本書的目的乃是要與臨床有密切的相關性,然而,我們也認為臨床工作者必須與研究領域保持接軌,即使治療師不親自參與研究,也必須知道如何評估他人的研究。
本書最重要的基本假設之一是,此時此地的人際互動在有效的團體治療中至關重要。真正有力的治療團體能提供一個舞台,案主們能在這個舞台上自由地與他人互動,然後幫助成員辨識和理解他們互動中的問題,最終讓我們的案主能夠改變那些適應不良的型態。我們相信僅建立在其他假設的團體無法獲得完整的治療成果,例如心理教育或認知—行為取向。任何一種團體治療形式都可以藉由加入對人際關係歷程的覺察而變得更為有效,我們在本書深入探討互動性聚焦(interactional focus)的範疇和性質,以及它為性格和人際關係帶來明顯變化的能力。互動性聚焦是團體治療的引擎,有能力利用它的治療師更有能力進行各式團體治療,即使其團體模式未強調或未認可互動的中心地位亦然(見第十五章)。
我(亞隆)的小說《叔本華的眼淚》(The Schopenhauer Cure)可以做為本書的共同讀本,它以一個治療團體為背景,描述了本書所述的多項團體歷程和治療師技巧的原則,因此,在本版的幾個地方,我們請讀者閱讀《叔本華的眼淚》中對治療師技術作虛構描繪的段落。
過於厚重的書往往最終會被放在「參考書」的書架上,為了避免這種命運,我們不願意大幅增加本書的篇幅,因此,我們在增添許多新材料時不得不刪去舊的段落和引文。這是一個痛苦的任務,刪除許多被劃去的段落傷了我們的心也傷了我們的手,但我們希望這個成果是一部符合現今的、跟上時代的作品,能夠為學生和專業人員在未來15年及更長的時間裡提供良好的幫助。
第一章 療效因素
團體治療能幫助案主嗎?是的,確實可以。大量療效研究已一致且清楚地證實團體治療是極為有效的心理治療方式,它在提供助益上的力量不但至少等同於個別治療,它還能更為有效率地運用心理健康醫療資源。1然而吊詭的是,心理健康的專業培育課程卻縮減了團體治療的訓練。這是個極需關注的現象:如果我們想帶來我們所期待,同時也是案主所需要的影響力,便需要確保團體治療具有高品質。2有助於治療效果的團體因素和帶領者的特徵,便是本書全書的重點。
團體治療如何幫助案主?也許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但如果我們能以精準且明確的測量工具來回答這個問題,那麼對於處理心理治療中最惱人且最受爭議的問題,心中就能有判斷的準則了。一旦這個準則確定後,便可依改變過程的重要面向制訂出一套理論依據,而治療師也可根據這些來釐訂策略,據此形塑團體經驗,以使它在各種案主、各式情境上能發揮最大的火力。雖然團體治療是有效的,治療師們在有效性上仍有極大的不同。3知曉如何最能推動這些具有療效的歷程,便是團體治療有效工作的核心,還好我們可以由研究證據得到許多方向,光有經驗並不等於有較佳的效果,那麼如何才會有較佳效果呢?答案是深思地工作、自省、獲得對工作的回饋,以及靈敏地運用具備同理與同調之治療關係。4
我們認為治療中的改變是十分複雜的過程,它經由人類各種錯綜複雜的經驗交互作用而產生,我把這種交互作用稱為「療效因素」(therapeutic factors)。由簡單面來探討複雜面,從基本細部歷程來了解整體現象,有相當大的好處,因此,我們將以描述及討論這些細部因素來開頭。
依我們的觀點,具治療性的經驗可自然分為下列11個主要因素:
1.灌輸希望(Instillation of hope)
2.普同感(Universality)
3.傳遞訊息(Imparting information)
4.利他主義(Altruism)
5.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現(The corrective recapitulation of the primary family group)
6.發展社交技巧(Development of socializing techniques)
7.行為模仿(Imitative behavior)
8.人際學習(Interpersonal learning)
9.團體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
10.情緒宣洩(Catharsis)
11.存在性因素(Existential factors)
我們在本章會討論前7個因素。因為「人際學習」和「團體凝聚力」非常重要與複雜,我們將它們安排在後續兩章中單獨討論。「存在性因素」將在第四章討論,因為與那一章的其他內容擺在一起,它們會最容易被了解。「情緒宣洩」與其他因素是息息相關的,因此也會在第四章一併討論。
這些因素之間的區分是人為的,雖然我們一一討論,但這些因素彼此間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並不是獨立發生作用的。此外,這些因素代表的是改變歷程的不同環節,有些因素發生在認知層次(例如,人際學習),有些因素發生在行為改變層次(例如發展社會技巧),有些發生在情緒層次(例如情緒宣洩),有些本身既是療效力量又是改變的前提(例如凝聚力)。雖然相同的療效因素發生在各種團體治療中,但它們的交互作用和相對重要性在各團體中有著極大的不同,而且,由於個別差異,同一個團體的成員感到獲益的療效因素也不同。5
請謹記療效因素乃是人為的建構,我們甚至可以將之視為對在學讀者提供的認知地圖。6這組療效因素並非不可替換,其他臨床工作者與研究者有提出不同的因素組合,雖然那些組合同樣也是人為的。某研究團隊認為一項核心的療效因素是:案主對其情緒表露與關係覺察可化為社會學習懷抱著希望。7沒有任何解釋系統可以涵蓋所有的治療,治療歷程的核心極為複雜,由經驗走向此核心的途徑幾不勝數(我們會在第四章更完整地討論這些相關議題)。
我們在此提出的這組療效因素乃得自於我們的臨床經驗、其他治療師的經驗、在團體治療獲得成功處遇之案主的觀點,及相關的系統性研究。然而,這些訊息來源並非無可質疑,不論團體成員或團體帶領者都不是全然客觀的,而且我們的研究方法常常也有限制。
我們從團體治療師們得到一些療效因素清單,其中真是五花八門且相互矛盾,這反映出探查了範圍廣泛的案主與團體。治療師們絕不是公正無私或不偏不倚的觀察者,他們為了鑽研某種治療方法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們的回答大多由他們所信服的學派所決定,這乃是效忠效應(the allegiance effect)。8即使在抱持相同理念、說著相同語言的治療師群,對於案主進步的原因也不盡有共識。但對此我們並不訝異,在心理治療史上,處處可見帶來效果的治療師,但療癒之道卻非其所以為的理由。誰不曾碰過不知所以大幅進步的案主呢?
訊息的重要來源是由團體成員判斷他們認為最有幫助和最沒幫助的療效因素,研究者會繼續提出有關探討療效因素上的重要問題,像是療效因素對所有團體成員有著同樣的影響力嗎?影響案主反應的因素是什麼?是與治療師的關係或與團體的關係嗎?治療品質或深度有何影響力?9再者,研究還顯示團體成員所重視的療效因素,可能與其治療師或團體觀察員所認為的大不相同。10成員的反應也可能受其他許多因素影響:團體類型(即門診、住院、日間留院或短期治療);11案主的年齡與診斷;12案主的動機階段與依戀風格;13團體帶領者的理念;14以及案主們對同一事件有著不同的經驗,也會影響著彼此的經驗。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