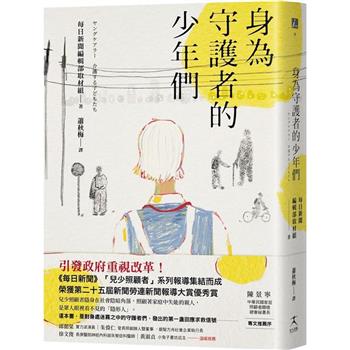【摘文】
他佇立在剪票口附近的麵包店前等著。
二○二○年二月,晴朗無雲、冬陽和煦的東京,中午過後即颳起強風。一身深藍色夾克、牛仔褲裝扮的他,看起來就像個隨處可見的平凡大學生。沒人會察覺他從小學就開始照護祖母。往來的行人對他絲毫不感興趣,他兀自縮著脖子,穿梭在車站外面的瑟瑟寒風中。
當天早報清一色是停靠在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遊輪相關報導。這是日本首度發生的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即便如此,路上戴口罩的人還是寥寥無幾。要過一段時間後,全球才會知道這未知病毒的凶猛威力。
歷經約一個月的電子郵件往來後,他指定碰面接受採訪的地點是,位於東京市中心的市之谷。除了在郵件中詳述會合地點的所在,他還附上地標店家的照片,在在令人感受到他細膩嚴謹的個性。
隸屬《每日新聞》特別報導部的向畑泰司,先到附近查看有無適合用來訪談的咖啡廳後,再依約於下午兩點來到車站與他會合。兩人互相自我介紹後,他開口第一句話就說:「風又大又冷,不知道有沒有讓您久等?」
接著又關心地問道:「這個地點會不會很難找?」果如郵件字裡行間透露的,是個體貼認真的年輕人。
前往咖啡廳的路上,為了舒緩他緊張的情緒,向畑泰司隨口問了他近況。他表示,大學畢業在即,除了寫畢業論文,還要打工、探望三年前住進療養設施的祖母,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
「已經接到錄取通知,確定到超市就職,畢業論文也終於寫完了」。他一邊邁著步伐,一邊臉上浮起鬆了口氣的表情。向畑也應和著說:「那真是太好了,恭喜。」
其實向畑此刻比平常來得緊張許多。據他所知,受訪對象從幼年時期就一肩挑起照護的重擔和責任。「很多孩子還無法理清自己心中照護家人的經驗。所以,請務必體諒、關照他們的感受」,專家和支援團體這樣建議向畑。
向畑雖然採訪經驗豐富,但是這次的訪談卻需要異於平常的細膩和顧慮。寒風呼嘯的街頭喧囂紛擾,打亂向畑的平常心,也令他感到些許鬱悶。
說起來,向畑其實是有點半信半疑的。從小學就擔任自己奶奶的「主要照護者」,並且一做就做了近十年。真的有這樣的小孩嗎?如果只是輔助性的幫忙,還可以理解……
雖然如此,可以直接採訪所謂「兒少照顧者」(young carer)的當事人,對他來說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是記者,所以也許會問到一些你不願再想起的事,或是不想被觸及的問題。碰到這種情況時,不必勉強回答喔。」
到了咖啡廳,兩人才隔著桌子面對面就座,他就笑著回答:「您儘管問。只要能說的,我會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
採訪時間長達兩個小時。訪談內容大致如下:
他從小學六年級就開始照顧祖母,每天準備早餐和晚餐。
全權負責與照護支援專員、居家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居服員」)等成人的溝通聯繫事宜。
他躲在學校廁所講電話,安撫對他奪命連環call的祖母。
放學後立刻回家,陪祖母一起唱歌、聊天。
隨著祖母失智症惡化,變得常要承受她的惡言相向。
他心力交瘁,情緒潰堤,對著房間牆壁丟東西。
但是,唯獨絕不對祖母丟東西。
被他幫忙清理下半身時,祖母哭了。
他的照護歷程從小六一直持續到大一,而這樣的處境幾乎不曾受到周圍關懷重視。但是,他既沒有悲觀,反倒像是理所當然似地,時而穿插些玩笑話,坦然訴說那種孤獨。那態度實在太過超然,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成熟許多。不計其數的插曲,既具體、詳細又真實。在在說明這無庸置疑地,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兒少照顧者的故事。
向畑問他,是否會對自己一直以來的境遇感到怨懟。
「雖然在進行照護的當時不免怨天尤人,但是現在已能覺得,因為做過照護所以也獲得很多。」
他說自己是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
「為什麼願意接受採訪?」
「大概是想讓人們知道我們這種小孩的存在吧。雖然我不清楚需要什麼支援,但還是希望更多人瞭解我們的處境。如果因為我說出來而可讓目前身處困境、孤單無援的其他兒少照顧者獲得些許幫助,我願意出面接受採訪。」
兩人步出咖啡廳時,強風已經停歇。向畑站在車站的剪票口,目送鄭重道別的他離去。
向畑確信今天的採訪可以寫成一篇報導。只要是記者,不管是誰都會在採訪成功時感到雀躍萬分。但是,此刻他心裡卻充滿了不安和沉重的壓力。
他以不著痕跡的勇氣和決心,娓娓道出那段也許其實並不想說予外人知曉的辛酸歲月。面對這樣的他,自己能否寫出一篇足以回報的報導?自己是否有這個資格?報導會不會反而擾亂他們的心思或家庭,讓他們陷入不幸?
這既非社會喧騰一時的事件,也不是什麼獨家報導。說穿了,「兒少照顧者」這個令人似懂非懂的名詞,幾乎可說完全不為大眾所知曉。
雖然如此,也不能斷定沒有其他小孩處在類似的家庭環境。像他這樣的兒少照顧者,日本應該為數不少吧。這個日趨少子高齡化和小家庭化的國家,即將迎來與兒少照顧者密不可分、切也切不斷的時代。不!說不定早就已經邁入這樣的階段了。在有限的時間內,還有多如牛毛的事項必須調查。
冬天太陽比較早下山。他剛離去的薄暮街道已再次恢復沉靜。
基於某些緣由,在此不能寫出他的真實姓名。
姑且以谷村純一的化名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