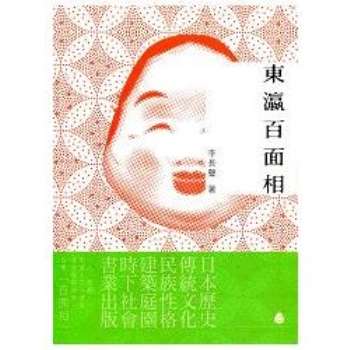優雅的牛車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十五世紀歐洲諸小國競相發展,猶如中國春秋無義戰,鏗鏗鏘鏘,一片片海洋都被他們佔了去。假設……假設中國少一點皇恩浩蕩的念頭,不到處買好,汲汲於利,鄭和之後繼續下西洋,稱霸海上,或許不至於如今才有了一艘航母,卻招人説三道四。
歷史沒有假設,人死不能復活。但分析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或教訓,其實就是在假設,雖然常難免事後諸葛亮之嫌。保阪正康著《假設的昭和史》,「考察在某個史實的某個斷面、某個局面若另有選擇,史實會變成什麼樣呢」。上下兩卷,截取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的日本歷史提出了四十九個假設,其中只要有幾個當年不是假設的話,興許就會有一個別樣的日本。如:假設日本不退出國際聯盟,假設共產黨幹部不在獄中變節,假設二‧二六造反部隊佔領了皇宫,假設德國駐華大使為日中斡旋成功,假設日本研製出原子彈,假設日本被美蘇分割佔領,假設日語改用羅馬字……
一九二六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一九二八年張作霖從北京乘火車退回奉天(瀋陽),車將抵達,發生爆炸,這位東北王傷重不治,而跟隨他乘車的日本人顧問,叫町野武馬,卻已在天津下車而去。町野説,他在天津下車,是前一天張作霖命令他協助張宗昌抵抗北伐軍。一九六一年町野曾經對作家山本有三口述歷史,但三十年過後開封,並沒有多大的史料價值。炸死張作霖,這一事件始作俑昭和年代的軍事主導體制,「在哪裡提出假設才能看出史實的背面呢」?保阪正康認為,町野在爆炸之前下車,對於歷史具有頗大意義。假設他知情,車到天津就逃之夭夭,説明炸死張作霖是陸軍當局的意思;假設他不知情,冥冥之中躲過一劫,那就是關東軍的瘋狂,為掃除有礙於製造滿洲國的張作霖,賠上老前輩(町野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與事件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恆同期)也在所不惜。
對往事如煙的歷史作出假設,需要有學識、史觀、良知。假設往往就是編故事,或許更屬於歷史小說家的擅場。例如台灣小說家高陽在歷史小說《玉壘浮雲》中替張學良假設;與張作霖同歲的町野武馬,雖有軍籍,但跟日本陸軍的關係不深,自從三任共九年任期滿後,改充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每年從五夫人手中領取交際費三萬元,到日本活動的對象,大致是財界、滿鐵及「玄洋社」──「黑龍會」的重要人物;在軍界,常接觸的只有一個影響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帥。町野武馬由於跟關東軍的關係不深,不可能參與密謀,但卻可能從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又有個俄國小説家,叫德米特里‧普羅霍洛夫,二○○○年與人合著《GRU帝國》,假設皇姑屯事件乃蘇聯情報機關的所為。二○○五年英國作家張戎和丈夫聯手出版了一本《毛》,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炸死張作霖事件一般認為是日軍幹的,但是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最近清楚了,實際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NaumEtingon(此人後來參與暗殺托洛茨基)策劃的,偽裝成日軍的勾當。(據日譯本轉譯,但不知日譯準確與否)所謂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恐怕不過是取自普羅霍洛夫的假設。二○○六年《毛》日文版上市,這段話引起日本媒體注意。不過,普羅霍洛夫始終未拿出史料證據,而且日本沒有一個史學家對此説感興趣,鬧閧的都是些論客。説來有些歷史就是當時的假設造成的。日本投降後,蘇聯、英聯邦等都要把天皇列為頭號戰犯,但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假設:處刑天皇可能會引發遊擊戰,因而不可傷及他一根毫毛。經麥克阿瑟同意,一九四六年昭和天皇巡行各地,到處都受到狂熱的歡迎,麥克阿瑟不由地擔心出現反佔領軍傾向,又命令天皇好好呆在皇宮裡。天皇有退位之意,麥克阿瑟耳聞,悄悄傳話:那是不可能的。保阪正康假設昭和天皇真的退了位,就可以明示天皇對那場戰爭心懷多麼強烈的自省之念,日本戰敗後社會就不只是單純表面上比戰前有所改變,而且包括太平洋戰爭在內的昭和這一時代的歷史意義也大有變化。
一個史實的形成有前因,還有當時的環境,回頭再來一次,假設未必能變成現實,未必就做得更好。保阪正康的假設大都不是從時代所具備的現實條件提出來的,一廂情願,希望那麼一來就避免了戰爭,歷史的進程會一路和平。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向中國出兵七十餘萬,其中也有人退伍回鄕,講述侵華故事,使陸軍部擔憂會暴露「皇軍」所作所為的真相,於是草擬了一紙關於指導、取締還鄕軍人言行的通令,其中列舉不當的誇誇其談,如戰鬥的時候最高興的是掠奪,參加戰爭的軍人挨個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戰場上長官下令卻沒人冒着彈雨往前衝。保阪正康寫道:士兵們誇張、虚偽、隱瞞事實的證言也延續到戰後社會。被虛偽證言洗腦的國民當中,至今還有人不相信日軍的野蠻行徑,公然説那場戰爭敗給了美國但戰勝了中國什麼的。假設陸軍部、媒體當時公佈了這樣的內部文件,有勇氣糾正軍紀……讓老百姓知道戰爭另一面,打下去的能量就會一下子變小。這樣的假設,完全忽略了軍國主義的本質,甚至要覺得作者過於天真,甚而有點膚淺了。
保阪正康是紀實作家,專攻日本近現代史,著述頗豐。自二○○六年在週刊雜誌上連載《昭和史溯往》,歷史五年餘,結集第十二、十三卷即《假設的昭和史》。優雅的牛車
近幾年每當晚秋去一趟深圳,參加讀書月活動,以致對於我來説,深圳就是讀書。今年除了讀書,還參觀了十月剛剛開館的望野博物館,不消説,精彩輝煌。聽説是個人收藏,更不禁想像值多少錢。最吸引我的,是一輛陶牛車,北齊年間的。那頭牛塑造得碩壯敦實,四條腿短得只是個意思,很有點當代藝術的趣味。悠悠牛車,惟穩惟緩,坐上去一定很安逸,不思再變革什麼。
四十多年前下鄉在延邊,常看見牛車,木輪鐵箍,車架子簡陋,老黃牛不畏鞭策,那樣子好像永遠也走不到目的地。離開延邊後再沒遇見過牛車,來在日本居然又得見。譬如京都三大祭之一的葵祭,年年五月裡舉行,招搖的首先是牛車。黑牛披紅掛綵,車篷垂掛紫藤花,兩個穿一身紅的女孩兒左右牽長韁,牛車兩側有幾個渾身縞素的男人挾持。總計五百多人遊行,説是像一幅王朝畫卷,如實再現了王朝貴族的優雅。王朝指平安時代(794-1185,京城在平安京,即京都),葵祭是潔齋三日的國家祭典。《源氏物語》描寫光源氏參與這種修禊行列,皇太子遺孀六條御息所是他的戀人,偷偷去觀看,而光源氏結髮之妻葵上懷孕在身,也出來散心,車填牛隘,已無停車位。家僕們仗勢,硬是把六條妃子的兩輛車擠了出去,並且折損了上下車的木凳。現今有的地方搞什麼祭,也有車遊行,卻是人推拉,其實本應是牛車,但近年來日本只有肉牛奶牛了,找一頭能駕車的牛已經是難事。
日本飛鳥時代(592-710)以前受六朝影響,奈良時代(710-784,京城在奈良,即平城京)以後受唐影響。即為受影響,就不會是同步,日本乘用工具的發展進程跟中國差不多,但時間上錯位,好像往昔男女走在街上,不是並肩而行,女人要落後一步。八世紀後半編成的《萬葉集》裡出現車:「戀如野草積七車,車車出自我心窩」。這車是人力車,九世紀初駕上牛牽引,起先是貴族女性的專車。走起來四平八穩,男人們艷羨,也競相享用。八九四年朝廷發出告示,「男女有別,禮敬殊著」,禁止不分貴賤地乘坐牛車。《延喜式》一書記載九世紀末禮儀風俗,對女性乘坐的牛車樣式、服飾等規定甚詳。九九九年朝廷又對於六位以下的卑位凡庶者嚴加禁止,坐牛車成為五位以上的特權。器物因人而異,車形按位階與俸祿而不同,各種各樣的牛車成為車主身份的視覺指標。牛車相遇,根據身份差異,或者停車讓路,或者卸牛下車,蹲踞或平伏。平安時代的繪畫、文學描寫牛車很多見,譬如後白河天皇敕繪的《年中行事繪卷》、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前半的小説《平家物語》寫平家惡行之始:攝政藤原基房的車隊與平資盛相遇,資盛不下馬行禮,被基房的家僕拽下馬。資盛的爺爺平清盛得知,派三百騎襲擊基房,把幾個隨從拽下馬,剪掉髮髻,並撕毀牛車簾子。北齊陶牛車的車廂後面有出入口,而日本牛車從後面上,前面下。下車時牛童先把牛卸下,軛觸地,人踏木凳下來,然後將軛架在木凳上。女性乘車,把裳裾從車簾下露出來,讓路人知道是女性乘車,也藉以炫耀或誘惑。《源氏物語》中,六條御息所深坐在車裡,只略微露出袖口、裳裾、汗衫等,顏色搭配很得當,且明顯有微行之意。
天皇在位時不乘牛車,坐沒有輪子的輿,由眾人肩扛,前呼後擁。退位的太上皇乘坐有輪子的人力輦車或者牛車。美在細節,坐牛車才可以細緻入微地觀賞世界,平安貴族的雅文化乘着牛車來。但牛車在路上吱嘎作響,庶民聽來是噪音。平安時代後期創作的裝飾性圖案有車形紋、源氏車紋。車形紋是整個車,以《源氏物語》為題材的源氏繪的車紋只表現車輪。東京國立博物館珍藏一個十二世紀的泥金螺鈿盒,是國寶,上面畫了許多半浸在流水中的車輪。這叫半輪車,非常圖案化,卻源於生活,木製車輪需要浸在河水中保養。所以,旅遊日本,若看見酒館外面擺設一個車輪子,莫聯想田園風光,那車輪象徵平安時代,是一種優雅。京都市的市徽就是一個車輪子。車輪圖案在和服、日常用品上很常見,買紀念品可不要以為車輪子圖案很土氣喲。
乘坐工具發展史:奈良時代用的是輿,平安時代乘牛車,鐮倉時代(1185前後-1333,執掌國柄的幕府在鐮倉)、室町時代(1338-1573,幕府在平安京的室町;自一四六七年的後期亦稱戰國時代)騎馬,江戶時代(1603-1867)坐駕籠,明治時代(1868-1912)出現人力車等。牛車是乘坐工具發達的頂點,式微後興起的不是馬車,更不是汽車,而是駕籠,類似於中國的轎子,歷史開了倒車。
中國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就利用馬車了,但日本人好像直到一八六○年出使美國才見識馬車似的,引進來不久又讓位給自動車。為什麼從中國拿來牛車,不拿來馬車呢?許是車文化經朝鮮半島傳入,而那裡始終未發展馬車。看見延邊朝鮮族趕牛車,優哉游哉,對馬車不感興趣,聽憑大鞭子一甩嘎嘎響,我也曾驚奇。鹹蘿蔔的禪味
説到中日關係,兩國都津津樂道遣唐使。唐太宗貞觀四年,即六三○年,舒明天皇向唐朝派出使節以及留學生、留學僧,從此二百多年間,有成行的,也有未能成行的,總計遣唐二十回,恨不能把我大唐的文物制度統統搬回去。到了唐昭宗乾寧元年,菅原道真被任命為大使,本該率領船隊第二十回赴唐,卻奏請宇多天皇緩行。理由有二:一是唐朝已衰敗,名存實亡,無須再學了;二是航路阻遏,九死一生,不值得冒險。大概頭一條理由很有效,所以第十九回遣唐的副使小野篁望海生畏,稱病不行,被處以流放,而這次准奏。時當八九四年,學生學歷史,為記住這個年代,諧音為白紙,意思是取消、撤回。九○七年唐朝滅亡,遣唐也真就廢止了。
大海茫茫,出航確實極危險。留學僧圓載在唐朝鑽研四十年,八七七年攜萬卷經典歸國,不幸船破,葬身於波濤。不過,海上船帆從不曾減少,而是越來越多,商人和僧侶冒死往來。圓載滯留唐朝時,日本朝廷曾兩度給他送金子,應該是這些人捎帶的罷。商船不絕於途,國家也就用不着遣使,那是要傾其國庫的,耗資巨大。清末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鄰交志》中寫道:「有宋一代,聘使雖罕,而緇流估客往來日密。」緇流是取經或傳經的緇衣僧侶,估客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他們取代了國家行為。南宋被蒙古鐵騎征服,有更多僧侶亡命東渡,不僅帶來了清規戒律,也帶來日常生活。誠如周作人所言:「日本舊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貴族、寺院等階層崇尚從中國舶來的文物,卻叫作「唐物」,可能也讓人誤以為這唐就是唐代,不知有宋。
正是禪宗興盛之時,入宋或渡日大多是禪僧。南宋傳來水墨畫,禪寺將其立體化,在地上創作出沙盤也似的日式園林枯山水。飲茶始於中國,宋代茶及酒鹽專賣,並輸出海外。日本茶道用抹茶,這種茶就是宋代定型的。八一五年出使過唐朝的僧永忠向嵯峨天皇獻過茶,是為日本正史上關於飲茶的第一條記錄,但真正讓日本人吃起茶來的是榮西。他兩度到南宋學禪,一一九一年歸國後開山日本臨濟宗。還帶回茶種,在雲仙寺(在今佐賀縣)附近種植,寺院由此愛種茶。榮西撰寫了日本第一本茶書《吃茶養生記》。中國文化主要由僧侶引進日本,寺院堪為最先進的學問機構。禪寺有「茶禮」。武士、貴族、文化人出入,看見和尚們裝飾了華麗的中國文物,在禪房裡飲茶,一定覺得酷。照葫蘆晝瓢,在家裡擺設中國的書畫陶瓷學喝茶。也曾坐在椅子上吃茶,到底坐不來,逐漸按日本生活方式設計了茶禮。飲茶在中國是日常的,世俗的,日本把茶和禪一起拿了來,日常化、世俗化之前,先加以精神化,這或許是拿來外國文化的一個手法。茶從禪寺傳出來,被誇大解釋,演變為世間的茶道。非同尋常的事物就容易成「道」,日本人給茶附加了太多的精神性、宗教性感覺。由於戰亂,王朝的建築及收集的唐物焚燬殆盡,厭世空氣籠罩,吃茶的道具也只好採用日本製造了,茶就枯寂起來。僧珠光是枯寂茶的先驅,傳説他隨一休參禪,領悟了茶禪一味的境界。珠光的弟子宗珠曾題畫:「料知茶味與禪味同」。珠光的徒孫武野紹鷗及其弟子利休都曾在大德寺參禪,禪的思想被充作茶道的理論支柱。明治時代否定江戶時代的價值觀,吃穿住等生活環境急劇西方化,茶道衰微。為求活路,基本上變成禮儀修行,並普及大眾。戰敗後,茶道更搞成表演藝術,還有點神秘兮兮。尤為女性所好,會做點茶道、花道,顯得有女人味,看着就賢惠。
和尚吃什麼,人們自古就好奇,而禪宗尤其講究吃。平常人家喝的「建長汁」,是用蘿蔔、豆腐、魔芋之類做的湯。傳説七百五十年前,南宋禪僧蘭溪道隆在鐮倉開山建長寺,某日,小和尚把豆腐掉在了地上,不知所措,蘭溪禪師就用這碎豆腐,再加上蘿蔔絲什麼的做成湯。
日本菜餚幾乎離不開蘿蔔,魚生用蘿蔔絲墊底,烤魚用蘿蔔泥調味。醃鹹菜基本是蘿蔔,各種各樣的鹹蘿蔔在市場裡擺了一架。這種鹹蘿蔔叫「澤庵漬」,可用來下酒,但有人討厭它的味道。澤庵者,江戶時代臨濟宗和尚澤庵宗彭也,創建東海寺。第二代將軍德川家光來訪,拿出鹹蘿蔔招待,將軍為之命名。十八世紀從江戶傳到京都、九州,遍及日本,自不免「鹹吃蘿蔔禪操心」。
江戶時代初葉的一六五四年,禪僧隱元隆琦從福建來到日本,建萬福寺,開山黃檗宗,他帶來扁豆、孟宗竹、西瓜、蓮藕等。黃檗宗寺院的素菜也傳到市井人家。素菜卻要做出肉味來,只怕心思仍然是葷的。中國烹飪好用澱粉和油,而日本人學會炒與炸,「料理」至今少油水。好些東西如豆腐、納豆都是由禪僧帶入日本,先普及寺院,再傳入民間,不免染上了禪味,或附加了禪味傳説,所以我們常覺得日本有禪味兒。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十五世紀歐洲諸小國競相發展,猶如中國春秋無義戰,鏗鏗鏘鏘,一片片海洋都被他們佔了去。假設……假設中國少一點皇恩浩蕩的念頭,不到處買好,汲汲於利,鄭和之後繼續下西洋,稱霸海上,或許不至於如今才有了一艘航母,卻招人説三道四。
歷史沒有假設,人死不能復活。但分析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或教訓,其實就是在假設,雖然常難免事後諸葛亮之嫌。保阪正康著《假設的昭和史》,「考察在某個史實的某個斷面、某個局面若另有選擇,史實會變成什麼樣呢」。上下兩卷,截取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的日本歷史提出了四十九個假設,其中只要有幾個當年不是假設的話,興許就會有一個別樣的日本。如:假設日本不退出國際聯盟,假設共產黨幹部不在獄中變節,假設二‧二六造反部隊佔領了皇宫,假設德國駐華大使為日中斡旋成功,假設日本研製出原子彈,假設日本被美蘇分割佔領,假設日語改用羅馬字……
一九二六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一九二八年張作霖從北京乘火車退回奉天(瀋陽),車將抵達,發生爆炸,這位東北王傷重不治,而跟隨他乘車的日本人顧問,叫町野武馬,卻已在天津下車而去。町野説,他在天津下車,是前一天張作霖命令他協助張宗昌抵抗北伐軍。一九六一年町野曾經對作家山本有三口述歷史,但三十年過後開封,並沒有多大的史料價值。炸死張作霖,這一事件始作俑昭和年代的軍事主導體制,「在哪裡提出假設才能看出史實的背面呢」?保阪正康認為,町野在爆炸之前下車,對於歷史具有頗大意義。假設他知情,車到天津就逃之夭夭,説明炸死張作霖是陸軍當局的意思;假設他不知情,冥冥之中躲過一劫,那就是關東軍的瘋狂,為掃除有礙於製造滿洲國的張作霖,賠上老前輩(町野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與事件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恆同期)也在所不惜。
對往事如煙的歷史作出假設,需要有學識、史觀、良知。假設往往就是編故事,或許更屬於歷史小說家的擅場。例如台灣小說家高陽在歷史小說《玉壘浮雲》中替張學良假設;與張作霖同歲的町野武馬,雖有軍籍,但跟日本陸軍的關係不深,自從三任共九年任期滿後,改充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每年從五夫人手中領取交際費三萬元,到日本活動的對象,大致是財界、滿鐵及「玄洋社」──「黑龍會」的重要人物;在軍界,常接觸的只有一個影響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帥。町野武馬由於跟關東軍的關係不深,不可能參與密謀,但卻可能從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又有個俄國小説家,叫德米特里‧普羅霍洛夫,二○○○年與人合著《GRU帝國》,假設皇姑屯事件乃蘇聯情報機關的所為。二○○五年英國作家張戎和丈夫聯手出版了一本《毛》,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炸死張作霖事件一般認為是日軍幹的,但是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最近清楚了,實際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NaumEtingon(此人後來參與暗殺托洛茨基)策劃的,偽裝成日軍的勾當。(據日譯本轉譯,但不知日譯準確與否)所謂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恐怕不過是取自普羅霍洛夫的假設。二○○六年《毛》日文版上市,這段話引起日本媒體注意。不過,普羅霍洛夫始終未拿出史料證據,而且日本沒有一個史學家對此説感興趣,鬧閧的都是些論客。説來有些歷史就是當時的假設造成的。日本投降後,蘇聯、英聯邦等都要把天皇列為頭號戰犯,但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假設:處刑天皇可能會引發遊擊戰,因而不可傷及他一根毫毛。經麥克阿瑟同意,一九四六年昭和天皇巡行各地,到處都受到狂熱的歡迎,麥克阿瑟不由地擔心出現反佔領軍傾向,又命令天皇好好呆在皇宮裡。天皇有退位之意,麥克阿瑟耳聞,悄悄傳話:那是不可能的。保阪正康假設昭和天皇真的退了位,就可以明示天皇對那場戰爭心懷多麼強烈的自省之念,日本戰敗後社會就不只是單純表面上比戰前有所改變,而且包括太平洋戰爭在內的昭和這一時代的歷史意義也大有變化。
一個史實的形成有前因,還有當時的環境,回頭再來一次,假設未必能變成現實,未必就做得更好。保阪正康的假設大都不是從時代所具備的現實條件提出來的,一廂情願,希望那麼一來就避免了戰爭,歷史的進程會一路和平。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向中國出兵七十餘萬,其中也有人退伍回鄕,講述侵華故事,使陸軍部擔憂會暴露「皇軍」所作所為的真相,於是草擬了一紙關於指導、取締還鄕軍人言行的通令,其中列舉不當的誇誇其談,如戰鬥的時候最高興的是掠奪,參加戰爭的軍人挨個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戰場上長官下令卻沒人冒着彈雨往前衝。保阪正康寫道:士兵們誇張、虚偽、隱瞞事實的證言也延續到戰後社會。被虛偽證言洗腦的國民當中,至今還有人不相信日軍的野蠻行徑,公然説那場戰爭敗給了美國但戰勝了中國什麼的。假設陸軍部、媒體當時公佈了這樣的內部文件,有勇氣糾正軍紀……讓老百姓知道戰爭另一面,打下去的能量就會一下子變小。這樣的假設,完全忽略了軍國主義的本質,甚至要覺得作者過於天真,甚而有點膚淺了。
保阪正康是紀實作家,專攻日本近現代史,著述頗豐。自二○○六年在週刊雜誌上連載《昭和史溯往》,歷史五年餘,結集第十二、十三卷即《假設的昭和史》。優雅的牛車
近幾年每當晚秋去一趟深圳,參加讀書月活動,以致對於我來説,深圳就是讀書。今年除了讀書,還參觀了十月剛剛開館的望野博物館,不消説,精彩輝煌。聽説是個人收藏,更不禁想像值多少錢。最吸引我的,是一輛陶牛車,北齊年間的。那頭牛塑造得碩壯敦實,四條腿短得只是個意思,很有點當代藝術的趣味。悠悠牛車,惟穩惟緩,坐上去一定很安逸,不思再變革什麼。
四十多年前下鄉在延邊,常看見牛車,木輪鐵箍,車架子簡陋,老黃牛不畏鞭策,那樣子好像永遠也走不到目的地。離開延邊後再沒遇見過牛車,來在日本居然又得見。譬如京都三大祭之一的葵祭,年年五月裡舉行,招搖的首先是牛車。黑牛披紅掛綵,車篷垂掛紫藤花,兩個穿一身紅的女孩兒左右牽長韁,牛車兩側有幾個渾身縞素的男人挾持。總計五百多人遊行,説是像一幅王朝畫卷,如實再現了王朝貴族的優雅。王朝指平安時代(794-1185,京城在平安京,即京都),葵祭是潔齋三日的國家祭典。《源氏物語》描寫光源氏參與這種修禊行列,皇太子遺孀六條御息所是他的戀人,偷偷去觀看,而光源氏結髮之妻葵上懷孕在身,也出來散心,車填牛隘,已無停車位。家僕們仗勢,硬是把六條妃子的兩輛車擠了出去,並且折損了上下車的木凳。現今有的地方搞什麼祭,也有車遊行,卻是人推拉,其實本應是牛車,但近年來日本只有肉牛奶牛了,找一頭能駕車的牛已經是難事。
日本飛鳥時代(592-710)以前受六朝影響,奈良時代(710-784,京城在奈良,即平城京)以後受唐影響。即為受影響,就不會是同步,日本乘用工具的發展進程跟中國差不多,但時間上錯位,好像往昔男女走在街上,不是並肩而行,女人要落後一步。八世紀後半編成的《萬葉集》裡出現車:「戀如野草積七車,車車出自我心窩」。這車是人力車,九世紀初駕上牛牽引,起先是貴族女性的專車。走起來四平八穩,男人們艷羨,也競相享用。八九四年朝廷發出告示,「男女有別,禮敬殊著」,禁止不分貴賤地乘坐牛車。《延喜式》一書記載九世紀末禮儀風俗,對女性乘坐的牛車樣式、服飾等規定甚詳。九九九年朝廷又對於六位以下的卑位凡庶者嚴加禁止,坐牛車成為五位以上的特權。器物因人而異,車形按位階與俸祿而不同,各種各樣的牛車成為車主身份的視覺指標。牛車相遇,根據身份差異,或者停車讓路,或者卸牛下車,蹲踞或平伏。平安時代的繪畫、文學描寫牛車很多見,譬如後白河天皇敕繪的《年中行事繪卷》、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前半的小説《平家物語》寫平家惡行之始:攝政藤原基房的車隊與平資盛相遇,資盛不下馬行禮,被基房的家僕拽下馬。資盛的爺爺平清盛得知,派三百騎襲擊基房,把幾個隨從拽下馬,剪掉髮髻,並撕毀牛車簾子。北齊陶牛車的車廂後面有出入口,而日本牛車從後面上,前面下。下車時牛童先把牛卸下,軛觸地,人踏木凳下來,然後將軛架在木凳上。女性乘車,把裳裾從車簾下露出來,讓路人知道是女性乘車,也藉以炫耀或誘惑。《源氏物語》中,六條御息所深坐在車裡,只略微露出袖口、裳裾、汗衫等,顏色搭配很得當,且明顯有微行之意。
天皇在位時不乘牛車,坐沒有輪子的輿,由眾人肩扛,前呼後擁。退位的太上皇乘坐有輪子的人力輦車或者牛車。美在細節,坐牛車才可以細緻入微地觀賞世界,平安貴族的雅文化乘着牛車來。但牛車在路上吱嘎作響,庶民聽來是噪音。平安時代後期創作的裝飾性圖案有車形紋、源氏車紋。車形紋是整個車,以《源氏物語》為題材的源氏繪的車紋只表現車輪。東京國立博物館珍藏一個十二世紀的泥金螺鈿盒,是國寶,上面畫了許多半浸在流水中的車輪。這叫半輪車,非常圖案化,卻源於生活,木製車輪需要浸在河水中保養。所以,旅遊日本,若看見酒館外面擺設一個車輪子,莫聯想田園風光,那車輪象徵平安時代,是一種優雅。京都市的市徽就是一個車輪子。車輪圖案在和服、日常用品上很常見,買紀念品可不要以為車輪子圖案很土氣喲。
乘坐工具發展史:奈良時代用的是輿,平安時代乘牛車,鐮倉時代(1185前後-1333,執掌國柄的幕府在鐮倉)、室町時代(1338-1573,幕府在平安京的室町;自一四六七年的後期亦稱戰國時代)騎馬,江戶時代(1603-1867)坐駕籠,明治時代(1868-1912)出現人力車等。牛車是乘坐工具發達的頂點,式微後興起的不是馬車,更不是汽車,而是駕籠,類似於中國的轎子,歷史開了倒車。
中國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就利用馬車了,但日本人好像直到一八六○年出使美國才見識馬車似的,引進來不久又讓位給自動車。為什麼從中國拿來牛車,不拿來馬車呢?許是車文化經朝鮮半島傳入,而那裡始終未發展馬車。看見延邊朝鮮族趕牛車,優哉游哉,對馬車不感興趣,聽憑大鞭子一甩嘎嘎響,我也曾驚奇。鹹蘿蔔的禪味
説到中日關係,兩國都津津樂道遣唐使。唐太宗貞觀四年,即六三○年,舒明天皇向唐朝派出使節以及留學生、留學僧,從此二百多年間,有成行的,也有未能成行的,總計遣唐二十回,恨不能把我大唐的文物制度統統搬回去。到了唐昭宗乾寧元年,菅原道真被任命為大使,本該率領船隊第二十回赴唐,卻奏請宇多天皇緩行。理由有二:一是唐朝已衰敗,名存實亡,無須再學了;二是航路阻遏,九死一生,不值得冒險。大概頭一條理由很有效,所以第十九回遣唐的副使小野篁望海生畏,稱病不行,被處以流放,而這次准奏。時當八九四年,學生學歷史,為記住這個年代,諧音為白紙,意思是取消、撤回。九○七年唐朝滅亡,遣唐也真就廢止了。
大海茫茫,出航確實極危險。留學僧圓載在唐朝鑽研四十年,八七七年攜萬卷經典歸國,不幸船破,葬身於波濤。不過,海上船帆從不曾減少,而是越來越多,商人和僧侶冒死往來。圓載滯留唐朝時,日本朝廷曾兩度給他送金子,應該是這些人捎帶的罷。商船不絕於途,國家也就用不着遣使,那是要傾其國庫的,耗資巨大。清末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鄰交志》中寫道:「有宋一代,聘使雖罕,而緇流估客往來日密。」緇流是取經或傳經的緇衣僧侶,估客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他們取代了國家行為。南宋被蒙古鐵騎征服,有更多僧侶亡命東渡,不僅帶來了清規戒律,也帶來日常生活。誠如周作人所言:「日本舊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貴族、寺院等階層崇尚從中國舶來的文物,卻叫作「唐物」,可能也讓人誤以為這唐就是唐代,不知有宋。
正是禪宗興盛之時,入宋或渡日大多是禪僧。南宋傳來水墨畫,禪寺將其立體化,在地上創作出沙盤也似的日式園林枯山水。飲茶始於中國,宋代茶及酒鹽專賣,並輸出海外。日本茶道用抹茶,這種茶就是宋代定型的。八一五年出使過唐朝的僧永忠向嵯峨天皇獻過茶,是為日本正史上關於飲茶的第一條記錄,但真正讓日本人吃起茶來的是榮西。他兩度到南宋學禪,一一九一年歸國後開山日本臨濟宗。還帶回茶種,在雲仙寺(在今佐賀縣)附近種植,寺院由此愛種茶。榮西撰寫了日本第一本茶書《吃茶養生記》。中國文化主要由僧侶引進日本,寺院堪為最先進的學問機構。禪寺有「茶禮」。武士、貴族、文化人出入,看見和尚們裝飾了華麗的中國文物,在禪房裡飲茶,一定覺得酷。照葫蘆晝瓢,在家裡擺設中國的書畫陶瓷學喝茶。也曾坐在椅子上吃茶,到底坐不來,逐漸按日本生活方式設計了茶禮。飲茶在中國是日常的,世俗的,日本把茶和禪一起拿了來,日常化、世俗化之前,先加以精神化,這或許是拿來外國文化的一個手法。茶從禪寺傳出來,被誇大解釋,演變為世間的茶道。非同尋常的事物就容易成「道」,日本人給茶附加了太多的精神性、宗教性感覺。由於戰亂,王朝的建築及收集的唐物焚燬殆盡,厭世空氣籠罩,吃茶的道具也只好採用日本製造了,茶就枯寂起來。僧珠光是枯寂茶的先驅,傳説他隨一休參禪,領悟了茶禪一味的境界。珠光的弟子宗珠曾題畫:「料知茶味與禪味同」。珠光的徒孫武野紹鷗及其弟子利休都曾在大德寺參禪,禪的思想被充作茶道的理論支柱。明治時代否定江戶時代的價值觀,吃穿住等生活環境急劇西方化,茶道衰微。為求活路,基本上變成禮儀修行,並普及大眾。戰敗後,茶道更搞成表演藝術,還有點神秘兮兮。尤為女性所好,會做點茶道、花道,顯得有女人味,看着就賢惠。
和尚吃什麼,人們自古就好奇,而禪宗尤其講究吃。平常人家喝的「建長汁」,是用蘿蔔、豆腐、魔芋之類做的湯。傳説七百五十年前,南宋禪僧蘭溪道隆在鐮倉開山建長寺,某日,小和尚把豆腐掉在了地上,不知所措,蘭溪禪師就用這碎豆腐,再加上蘿蔔絲什麼的做成湯。
日本菜餚幾乎離不開蘿蔔,魚生用蘿蔔絲墊底,烤魚用蘿蔔泥調味。醃鹹菜基本是蘿蔔,各種各樣的鹹蘿蔔在市場裡擺了一架。這種鹹蘿蔔叫「澤庵漬」,可用來下酒,但有人討厭它的味道。澤庵者,江戶時代臨濟宗和尚澤庵宗彭也,創建東海寺。第二代將軍德川家光來訪,拿出鹹蘿蔔招待,將軍為之命名。十八世紀從江戶傳到京都、九州,遍及日本,自不免「鹹吃蘿蔔禪操心」。
江戶時代初葉的一六五四年,禪僧隱元隆琦從福建來到日本,建萬福寺,開山黃檗宗,他帶來扁豆、孟宗竹、西瓜、蓮藕等。黃檗宗寺院的素菜也傳到市井人家。素菜卻要做出肉味來,只怕心思仍然是葷的。中國烹飪好用澱粉和油,而日本人學會炒與炸,「料理」至今少油水。好些東西如豆腐、納豆都是由禪僧帶入日本,先普及寺院,再傳入民間,不免染上了禪味,或附加了禪味傳説,所以我們常覺得日本有禪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