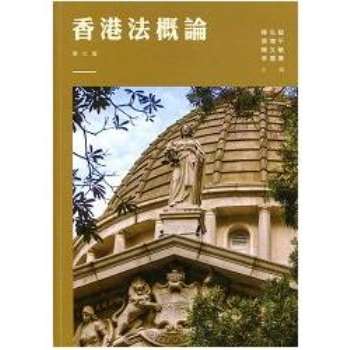第一章 法律制度
陳文敏*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安定繁榮的國際大都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擁有一個相當健全的法律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7月1日成立後,香港原有的法律基本不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8條亦明確指出,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與《基本法》相抵觸者外,均予保留。《基本法》並同時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的不同範疇作出具體的規定,總的原則是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香港在1997年7月之前的法律制度,在特區成立以後予以保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性法律和法律原則,除《基本法》另有規定外,將不會在特區實施。所謂“法律制度”,除了包括法律的淵源和組成部份外,亦同時包括制度內不同架構和人士的角色與任命、運作和程序,司法推理方法與基本價值體系等。本章將就這各方面作簡單的介紹。
* 就張達明先生對本章初稿所提出的寶貴意見,作者謹此致謝。
一 不同法系與普通法法系
不同國家因應不同的歷史發展、社會需要,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法律制度,而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可根據一些共通的特徵和架構而歸納為不同的“法系”(families of legal systems)。在同一法系內的法律制度有共通的特徵,有類似的架構,還有一些共通的價值觀念。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法系包括普通法法系、歐陸法系(大陸法系)、社會主義法系,以及一些以回教或印度教為基礎的宗教式法系。香港特別行政區屬於普通法法系,而中國內地則屬於社會主義法系,但當中又吸收了不少歐陸法系的元素1。
1 就不同法系的進一步介紹,請參閱René David and John Brierley,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Stevens & Sons, 3rd ed. 1985)。
(一)普通法系
普通法(Common Law)源自英國。在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即英皇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後,鑑於當時的英格蘭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風俗和習慣法,但卻沒有一套統一和適用於全國的法律,於是他和他以後的幾位皇位繼承者便着手建立一套以皇權為中心的全國性法律制度。他們建立了一些皇室法院,這些皇室法院最初主要處理一些和皇室利益有關的事項,例如涉及土地、税項,以及破壞公共安寧(Breach of the peace)的刑事罪行等方面的案件。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這些皇室法院逐漸取代了各地自己設立的地方法院的職權,並通過判例逐漸形成了一套統一的法律制度。從這裏可明白到“普通法”這個用語的其中一個涵義,即普通法是指適用於全國的普遍性的法律,有別於不同地方因應不同風俗而形成的地方性法律。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亦產生了普通法的另一個特點,即普通法是由法院的判例累積而成的,時至今日,不少部門的法律,例如合同法、侵權法、信託法等,仍然是以普通法判例為骨幹的。故此,普通法的另一涵義是指由判例衍生出來的法律。早期,普通法又發展出一套複雜的令狀制度(writ system),根據這套令狀制度,不同的訴訟需要採用不同的令狀,而不同的令狀又會相應有不同的司法程序,甚至不同的司法補救方式(即法院判決勝訴一方可得的賠償或其他補救)。在15世紀,這個令狀制度變得相當僵化和臃腫,甚至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不少人往往因為程序方面的失誤而被拒諸於法院門外,於是這些人紛紛向英皇提出申訴,英皇遂將這些申訴轉交首席大臣(即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處理,隨着這些申訴日漸增加,大法官便設立了一個衡平法法院(Court of Chancery),專門處理這些申訴。在處理這些申訴時,大法官避免過分重視令狀和程序方面的技術性問題,而集中考慮案情的理據得失,漸漸地,這個法院便發展出另外一套的法律規範,亦即所謂“衡平法”(Equity)。於是,“普通法”的一個較狹義的解釋,是指由皇室法院的判例所衍生出來的法律,而不包括由衡平法法院所衍生出來的另一套法律原則。一般而言,衡平法是較為有彈性及注重案情的合理性,程序方面或技術性的失誤相對上是較次要的考慮。然而,隨着時間流逝和判例制度的發展,衡平法亦逐漸失去其原有的靈活性,加上衡平法和普通法兩套法律規範並存,也引來不少的衝突和不便。於是,在1873年至1875年間,英國國會通過立法對司法制度進行大幅改革,將涉及衡平法和普通法的案件的管轄權共冶一爐。時至今曰,衡平法和普通法的分別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了,但由於衡平法規範和普通法規範在具體應用時仍有若干不同的考慮,而衡平法衍生了多套重要的法律原則,例如信託法、強制履行令、禁制令(強制令)等,故此,我們仍須瞭解衡平法與普通法的區別。
在17世紀以後,英國國力日漸強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時,英國人同時引進了這套普通法制度〈這裏的“普通法”是指其廣義的涵義,即包括衡平法)。在今天,美國和幾乎所有英聯邦國家,一些前英國殖民地,包括澳洲、新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加拿大,以及不少非洲國家及太平洋島國等,都是採用這套普通法制度的。這套制度有四個特點:(a)它是以判例為骨幹,有些重要法律部門(如合同法、侵權法、財產法、行政法等)的基本概念和原則都來自判例而非成文法(即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例),普通法的一個特點,就是法院每一宗判案的理據所蘊涵的原則都可成為法律,而這些原則便構成所謂“判例”。一般而言,上級法院的判例對下級法院是有約束力的;普通法信奉三權分立的原則,司法機關獨立於行政和立法機關,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着監察與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b)承襲西方民主自由思潮的傳統,普通法亦極為重視個人自由與財產的權利,例如在未判罪之前假定無罪(“無罪推定”的其中一方面),或任何人的財產都不得在沒有合理補償的情況下予以剝奪等原則,都是由普通法衍生而來的。此外,普通法亦極為注重公平審判的原則,從而發展出很多在程序方面對人身自由的保障,這些保障,在刑事訴訟制度中尤為重要;普通法的審訊程序比較傾向於辯論式或對抗式(adversarial)。普通法認為,若果控辯雙方能竭盡所能,各自提出對己方最有利的證供和論據,然後由一個公正的第三者進行裁決,這將是一個最公平的制度。於是在對抗式或辯論式的審訊程序中,法官的角色主要是一個公正的仲裁人,而決定審訊中所採用的策略的主動權,以至提出甚麼法律論據或傳召哪些證人的決定權,均屬於訴訟雙方或他們的律師代表;故此,在普通法的審訊制度中,律師扮演着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二)歐陸法系
歐陸法系又稱“民法法系”(civil law family),源於歐洲大陸,其內容及發展都受到古羅馬法的深遠影響。羅馬帝國在全盛時期已經發展出一套相當完整的法律體系,但隨着西羅馬帝國在公元5世紀滅亡以後,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亦隨之在西歐湮滅。中世紀的西歐起初是無法無天的黑暗年代,直至11世紀商旅興盛和及後的文藝復興時代,重燃對古羅馬法研究,才將這個局面轉變過來。文藝復興是指在文學、藝術、哲學、建築等各方面重新發現古代希臘和羅馬文明的成就並加以推展的一個時期,法學亦沒有例外。在這段時期,不少學者都在思索如何建立一個更公義的法律制度,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商業城市,如佛羅倫斯、威尼斯等,城市裏新興的商人階級意識到如果商業貿易要繼續發展的話,便必須依賴一個公平和理性的法律制度,而古羅馬法正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去發展這樣一種理性的法律制度。故此,如果説英倫普通法乃建基於一個統一的王朝的法律制度,歐陸法系則建基於一個共通的歷史遺產和文化源流。英倫普通法的發展是由法院作主導,而歐陸法系的發展則是以大學裏的學者為骨幹。
歐陸法系的一個最大特色,便是以法典(code)為基礎。法典不同於普通法系中的一般成文法,普通法法制中的成文法通常只會就個別的問題訂出規範,而歐陸法系的法典則將某一個法律部門中所有的有關原則和概念,很有系統和很有條理地寫出來,這和它的歷史發展在於尋找一個合理、公平和理性的社會有密切的關係;其次,歐陸法系國家雖然亦接受三權分立的原則,但它們的司法機關(主要是指法院)所享有的權力和地位,卻遠遜於普通法制度下的司法機關,這也和它們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因為在一些歐陸國家(如法國),法院曾經一度淪為統治者壓迫異己的工具。故此,三權分立的意思便變成法院只能扮演忠實演繹法律的角色,而不能有類似普通法法院那種透過判例而建立法律規範的權力,這也是在歐陸法系中沒有一套嚴謹的約束性判例制度的原因,法院的判案一般都不會對其他法院具有約束力;最後,歐陸法系的審訊程序是傾向於調查式(inquisitorial system)的。在調查式的審訊制度裏,法官不再是普通法制度中的被動的公正人,而是積極和主動的調查者,法官會在審訊中主動地調査事件的真相,盤問有關的證人,甚至傳召一些雙方律師可能都不願傳召的證人。審訊再不是像普通法制度中的一場由控辯雙方作主導的辯論,而是由法院主導的對事件真相進行調查的過程。歐陸法系可分作兩個支派,一個是法國法系,另外一個是德國法系。法國法系最基本的法律文獻是法國在1804年頒佈的法國民法典(French Civil Code),亦稱為“拿破崙法典”(Napoleonic Code),這個法典對所有屬於法國法系的國家都有深遠的影響。德國法系則主要是受到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所影響,中國台灣地區和日本,甚至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們的法律制度都比較接近德國法系;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主要是模仿德國的法律制度,中華民國南京國民黨政府時代亦是主要參考德國、瑞士和日本的民法來制定自己的民法典。(三)社會主義法系
雖然,普通法系和歐陸法系在制度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它們都有一些共通的價值觀念,例如尊崇個人自由和重視對私有財產的保障等。故此,在這些問題上,它們往往會有相類似的法律條文或判例。社會主義法系則建基於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價值體系之上,它源於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認為法律乃上層建築;在資本主義社會,法律是資本家統治人民的工具,為了消除剝削及解放工人,便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打破對資產階級生產工具的壟斷及階級的剝削,從而建立一個無分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法律的作用是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換言之,法律只是一種手段去達致一個政治目的。因此,社會主義法系的法律都會有一些政策性的條文,法律的解釋往往會從廣義的政策作出發點,而沒有普通法那種細緻甚至咬文嚼字的推理。傳統上,社會主義法系都是以公法為主,私法難以有足夠的發展空間。這一點在中國內地開始實行經濟改革的時候便曾帶來不少理論上的阻力,例如如果在社會主義法系中不保護私有產權,那麼如何發展國營企業以外的私營或合資企業,或當破產法只適用於私有產權時,如何處理不斷虧蝕的國營企業?
社會主義法系的另一個特點是將國家權力集中於人民代表大會,並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原則。因此,它並不接受三權分立;相反地,它認為不論立法、執法,甚至解釋法律的權力均應該在人民手上,而人民的意願就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一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行。故此,在今日中國內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行使立法權,並可透過其常務委員會行使法律解釋權,法院雖然可以對個別的案件擁有最終的裁判權,但對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法律,卻沒有最終的解釋權。
二 法律的分類
法律可以有不同的分類。首先,有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和國內法(Municipal Law)之分,國際法主要涉及國家與國家(包括國家與國際機構)之間的關係,它們的主要來源是條約、國家慣例,以及一些普遍受國際公認的習慣法。國際法又可分為國際公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及國際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國際公法管轄的範圍包括主權、領土、領海、人權、國籍、難民等等,而國際私法則涉及不同種類的國際經貿活動和不同法域之間的法律衝突。有人認為,國際間只有政治角力而沒有法律可言,這是一個比較偏激的觀點。試想想,為甚麼飛機需要按照固定的航道飛行?為甚麼信件只要貼上一個郵票便可以穿州過省地送到遠方朋友的手上?又或為甚麼你安坐家中便可收看透過人造衛星直接轉播千里以外進行中的體育賽事?這些都是由國際法管轄的行為。誠然,在國際司法制度中,沒有國際警察或享有強制執行的權力的司法機構來執行國際法,但國際關係千絲萬縷,互相牽引,以致國際法在執行方面也遠比一般人想像中更為複雜和有效。事實上,就正如國內法一樣,各國遵從國際法的行為是遠比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為多。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社會成立了兩個刑事審訊法庭,審訊在前南斯拉夫及非洲的盧旺達進行的“種族清洗”罪行,這又再一次燃起國際社會對成立國際刑法制度的希望,聯合國後來更在1998年召開會議,正式通過成立國際刑事法院的條約,該羅馬條約在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至2008年已獲一百零六個國家簽署,並在海牙成立國際刑事法院,審訊像戰爭罪行、種族滅絕、干犯人道罪等違反國際法的嚴重罪行。國內法亦和國際法一樣,可以分為公法(Public Law)和私法(Private Law),公法是關於政府的運作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的法律,而私法則主要涉及人民之間,即私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財產和經濟方面的法律。公法的範圍包括憲法、行政法、國籍法、刑法、税務法等;私法則包括合同法、侵權法、財產法、信託法、家事法、繼承法、公司法、商法等。
另外一種分類方法,是把法律分為民法和刑法。民法牽涉的是民事訴訟(civil proceedings),刑法牽涉的是刑事訴訟(criminal proceedings)。刑法訂立了一些社會公認為最起碼的行為標準,並對違反這些行為標準的人作出懲罰。因此,刑法一般是由政府提出檢控,目的在懲罰犯法者。由於懲罰可能涉及剝奪人身自由,故此,刑法要求一個較高的舉證標準:控方必須提出足夠的證據,舉證標準須達到沒有合理疑點(beyond reasonable doubt),法院才能將被吿入罪。民法則規範私人與私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及處理因違反這些權利或義務而導致的索償要求。由於民法並不涉及個人自由,加上普通市民沒有政府那樣龐大的資源和權力去進行調査、拘捕或搜集證據,故此,民法的舉證標準是較刑法為低的:舉證一方所提出的證據,只要證明他所主張的事實存在的可能性高於其不可能性(balance of probabilities),便達到民事的舉證標準了。另一方面,由於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索取賠償而非懲罰被吿,故此,通常原告必須提出證據證明其損失。例如在一宗交通意外中,司機醉酒駕駛,警方可對司機提出刑事檢控,因為醉酒駕駛是觸犯了刑法所訂出的社會認可的最低行為標準。刑事檢控的後果是司機可能被判罰款,或被吊銷駕駛執照,甚至被判入獄。在刑事檢控的過程中,因交通意外而受傷的路人將會作為控方證人,但刑事程序的目的,不在於對傷者作出賠償,如果傷者需要索取賠償,便要進行民事訴訟了。在民事訴訟中,傷者要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受傷的原因是因為司機的疏忽,以及足夠的證據證明他的損失,例如醫藥費、工資的損失和工作能力的喪失等。由於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是兩套不同的程序,也有不同的舉證標準,故此,即使在一宗工業意外或交通意外中,政府沒有對僱主或司機提出刑事檢控,仍不會影響傷者(或死者的家屬)向僱主或司機提出民事索償的權利。
最後一種較為普遍的分類方法,是把法律分為程序法(Procedural Law)和實體法(Substantive Law)。實體法是指各個法律部門中的具體原則和規範,例如怎樣才構成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合約,或在甚麼情況下才構成民事疏忽;程序法則規範了向法院提出訴訟的程序。普通法相當重視程序的要求,目的在保證司法程序能夠公正地進行;在今天,程序法是一個相當複雜和技術性的法律部門。事實上,在高等法院處理的一般民事和刑事訴訟中,程序方面的爭論往往佔了訴訟一半以上的時間。
陳文敏*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安定繁榮的國際大都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擁有一個相當健全的法律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7月1日成立後,香港原有的法律基本不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8條亦明確指出,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與《基本法》相抵觸者外,均予保留。《基本法》並同時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的不同範疇作出具體的規定,總的原則是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香港在1997年7月之前的法律制度,在特區成立以後予以保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性法律和法律原則,除《基本法》另有規定外,將不會在特區實施。所謂“法律制度”,除了包括法律的淵源和組成部份外,亦同時包括制度內不同架構和人士的角色與任命、運作和程序,司法推理方法與基本價值體系等。本章將就這各方面作簡單的介紹。
* 就張達明先生對本章初稿所提出的寶貴意見,作者謹此致謝。
一 不同法系與普通法法系
不同國家因應不同的歷史發展、社會需要,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法律制度,而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可根據一些共通的特徵和架構而歸納為不同的“法系”(families of legal systems)。在同一法系內的法律制度有共通的特徵,有類似的架構,還有一些共通的價值觀念。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法系包括普通法法系、歐陸法系(大陸法系)、社會主義法系,以及一些以回教或印度教為基礎的宗教式法系。香港特別行政區屬於普通法法系,而中國內地則屬於社會主義法系,但當中又吸收了不少歐陸法系的元素1。
1 就不同法系的進一步介紹,請參閱René David and John Brierley,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Stevens & Sons, 3rd ed. 1985)。
(一)普通法系
普通法(Common Law)源自英國。在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即英皇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後,鑑於當時的英格蘭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風俗和習慣法,但卻沒有一套統一和適用於全國的法律,於是他和他以後的幾位皇位繼承者便着手建立一套以皇權為中心的全國性法律制度。他們建立了一些皇室法院,這些皇室法院最初主要處理一些和皇室利益有關的事項,例如涉及土地、税項,以及破壞公共安寧(Breach of the peace)的刑事罪行等方面的案件。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這些皇室法院逐漸取代了各地自己設立的地方法院的職權,並通過判例逐漸形成了一套統一的法律制度。從這裏可明白到“普通法”這個用語的其中一個涵義,即普通法是指適用於全國的普遍性的法律,有別於不同地方因應不同風俗而形成的地方性法律。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亦產生了普通法的另一個特點,即普通法是由法院的判例累積而成的,時至今日,不少部門的法律,例如合同法、侵權法、信託法等,仍然是以普通法判例為骨幹的。故此,普通法的另一涵義是指由判例衍生出來的法律。早期,普通法又發展出一套複雜的令狀制度(writ system),根據這套令狀制度,不同的訴訟需要採用不同的令狀,而不同的令狀又會相應有不同的司法程序,甚至不同的司法補救方式(即法院判決勝訴一方可得的賠償或其他補救)。在15世紀,這個令狀制度變得相當僵化和臃腫,甚至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不少人往往因為程序方面的失誤而被拒諸於法院門外,於是這些人紛紛向英皇提出申訴,英皇遂將這些申訴轉交首席大臣(即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處理,隨着這些申訴日漸增加,大法官便設立了一個衡平法法院(Court of Chancery),專門處理這些申訴。在處理這些申訴時,大法官避免過分重視令狀和程序方面的技術性問題,而集中考慮案情的理據得失,漸漸地,這個法院便發展出另外一套的法律規範,亦即所謂“衡平法”(Equity)。於是,“普通法”的一個較狹義的解釋,是指由皇室法院的判例所衍生出來的法律,而不包括由衡平法法院所衍生出來的另一套法律原則。一般而言,衡平法是較為有彈性及注重案情的合理性,程序方面或技術性的失誤相對上是較次要的考慮。然而,隨着時間流逝和判例制度的發展,衡平法亦逐漸失去其原有的靈活性,加上衡平法和普通法兩套法律規範並存,也引來不少的衝突和不便。於是,在1873年至1875年間,英國國會通過立法對司法制度進行大幅改革,將涉及衡平法和普通法的案件的管轄權共冶一爐。時至今曰,衡平法和普通法的分別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了,但由於衡平法規範和普通法規範在具體應用時仍有若干不同的考慮,而衡平法衍生了多套重要的法律原則,例如信託法、強制履行令、禁制令(強制令)等,故此,我們仍須瞭解衡平法與普通法的區別。
在17世紀以後,英國國力日漸強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時,英國人同時引進了這套普通法制度〈這裏的“普通法”是指其廣義的涵義,即包括衡平法)。在今天,美國和幾乎所有英聯邦國家,一些前英國殖民地,包括澳洲、新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加拿大,以及不少非洲國家及太平洋島國等,都是採用這套普通法制度的。這套制度有四個特點:(a)它是以判例為骨幹,有些重要法律部門(如合同法、侵權法、財產法、行政法等)的基本概念和原則都來自判例而非成文法(即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例),普通法的一個特點,就是法院每一宗判案的理據所蘊涵的原則都可成為法律,而這些原則便構成所謂“判例”。一般而言,上級法院的判例對下級法院是有約束力的;普通法信奉三權分立的原則,司法機關獨立於行政和立法機關,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着監察與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b)承襲西方民主自由思潮的傳統,普通法亦極為重視個人自由與財產的權利,例如在未判罪之前假定無罪(“無罪推定”的其中一方面),或任何人的財產都不得在沒有合理補償的情況下予以剝奪等原則,都是由普通法衍生而來的。此外,普通法亦極為注重公平審判的原則,從而發展出很多在程序方面對人身自由的保障,這些保障,在刑事訴訟制度中尤為重要;普通法的審訊程序比較傾向於辯論式或對抗式(adversarial)。普通法認為,若果控辯雙方能竭盡所能,各自提出對己方最有利的證供和論據,然後由一個公正的第三者進行裁決,這將是一個最公平的制度。於是在對抗式或辯論式的審訊程序中,法官的角色主要是一個公正的仲裁人,而決定審訊中所採用的策略的主動權,以至提出甚麼法律論據或傳召哪些證人的決定權,均屬於訴訟雙方或他們的律師代表;故此,在普通法的審訊制度中,律師扮演着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二)歐陸法系
歐陸法系又稱“民法法系”(civil law family),源於歐洲大陸,其內容及發展都受到古羅馬法的深遠影響。羅馬帝國在全盛時期已經發展出一套相當完整的法律體系,但隨着西羅馬帝國在公元5世紀滅亡以後,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亦隨之在西歐湮滅。中世紀的西歐起初是無法無天的黑暗年代,直至11世紀商旅興盛和及後的文藝復興時代,重燃對古羅馬法研究,才將這個局面轉變過來。文藝復興是指在文學、藝術、哲學、建築等各方面重新發現古代希臘和羅馬文明的成就並加以推展的一個時期,法學亦沒有例外。在這段時期,不少學者都在思索如何建立一個更公義的法律制度,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商業城市,如佛羅倫斯、威尼斯等,城市裏新興的商人階級意識到如果商業貿易要繼續發展的話,便必須依賴一個公平和理性的法律制度,而古羅馬法正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去發展這樣一種理性的法律制度。故此,如果説英倫普通法乃建基於一個統一的王朝的法律制度,歐陸法系則建基於一個共通的歷史遺產和文化源流。英倫普通法的發展是由法院作主導,而歐陸法系的發展則是以大學裏的學者為骨幹。
歐陸法系的一個最大特色,便是以法典(code)為基礎。法典不同於普通法系中的一般成文法,普通法法制中的成文法通常只會就個別的問題訂出規範,而歐陸法系的法典則將某一個法律部門中所有的有關原則和概念,很有系統和很有條理地寫出來,這和它的歷史發展在於尋找一個合理、公平和理性的社會有密切的關係;其次,歐陸法系國家雖然亦接受三權分立的原則,但它們的司法機關(主要是指法院)所享有的權力和地位,卻遠遜於普通法制度下的司法機關,這也和它們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因為在一些歐陸國家(如法國),法院曾經一度淪為統治者壓迫異己的工具。故此,三權分立的意思便變成法院只能扮演忠實演繹法律的角色,而不能有類似普通法法院那種透過判例而建立法律規範的權力,這也是在歐陸法系中沒有一套嚴謹的約束性判例制度的原因,法院的判案一般都不會對其他法院具有約束力;最後,歐陸法系的審訊程序是傾向於調查式(inquisitorial system)的。在調查式的審訊制度裏,法官不再是普通法制度中的被動的公正人,而是積極和主動的調查者,法官會在審訊中主動地調査事件的真相,盤問有關的證人,甚至傳召一些雙方律師可能都不願傳召的證人。審訊再不是像普通法制度中的一場由控辯雙方作主導的辯論,而是由法院主導的對事件真相進行調查的過程。歐陸法系可分作兩個支派,一個是法國法系,另外一個是德國法系。法國法系最基本的法律文獻是法國在1804年頒佈的法國民法典(French Civil Code),亦稱為“拿破崙法典”(Napoleonic Code),這個法典對所有屬於法國法系的國家都有深遠的影響。德國法系則主要是受到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所影響,中國台灣地區和日本,甚至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們的法律制度都比較接近德國法系;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主要是模仿德國的法律制度,中華民國南京國民黨政府時代亦是主要參考德國、瑞士和日本的民法來制定自己的民法典。(三)社會主義法系
雖然,普通法系和歐陸法系在制度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它們都有一些共通的價值觀念,例如尊崇個人自由和重視對私有財產的保障等。故此,在這些問題上,它們往往會有相類似的法律條文或判例。社會主義法系則建基於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價值體系之上,它源於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認為法律乃上層建築;在資本主義社會,法律是資本家統治人民的工具,為了消除剝削及解放工人,便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打破對資產階級生產工具的壟斷及階級的剝削,從而建立一個無分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法律的作用是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換言之,法律只是一種手段去達致一個政治目的。因此,社會主義法系的法律都會有一些政策性的條文,法律的解釋往往會從廣義的政策作出發點,而沒有普通法那種細緻甚至咬文嚼字的推理。傳統上,社會主義法系都是以公法為主,私法難以有足夠的發展空間。這一點在中國內地開始實行經濟改革的時候便曾帶來不少理論上的阻力,例如如果在社會主義法系中不保護私有產權,那麼如何發展國營企業以外的私營或合資企業,或當破產法只適用於私有產權時,如何處理不斷虧蝕的國營企業?
社會主義法系的另一個特點是將國家權力集中於人民代表大會,並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原則。因此,它並不接受三權分立;相反地,它認為不論立法、執法,甚至解釋法律的權力均應該在人民手上,而人民的意願就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一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行。故此,在今日中國內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行使立法權,並可透過其常務委員會行使法律解釋權,法院雖然可以對個別的案件擁有最終的裁判權,但對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法律,卻沒有最終的解釋權。
二 法律的分類
法律可以有不同的分類。首先,有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和國內法(Municipal Law)之分,國際法主要涉及國家與國家(包括國家與國際機構)之間的關係,它們的主要來源是條約、國家慣例,以及一些普遍受國際公認的習慣法。國際法又可分為國際公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及國際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國際公法管轄的範圍包括主權、領土、領海、人權、國籍、難民等等,而國際私法則涉及不同種類的國際經貿活動和不同法域之間的法律衝突。有人認為,國際間只有政治角力而沒有法律可言,這是一個比較偏激的觀點。試想想,為甚麼飛機需要按照固定的航道飛行?為甚麼信件只要貼上一個郵票便可以穿州過省地送到遠方朋友的手上?又或為甚麼你安坐家中便可收看透過人造衛星直接轉播千里以外進行中的體育賽事?這些都是由國際法管轄的行為。誠然,在國際司法制度中,沒有國際警察或享有強制執行的權力的司法機構來執行國際法,但國際關係千絲萬縷,互相牽引,以致國際法在執行方面也遠比一般人想像中更為複雜和有效。事實上,就正如國內法一樣,各國遵從國際法的行為是遠比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為多。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社會成立了兩個刑事審訊法庭,審訊在前南斯拉夫及非洲的盧旺達進行的“種族清洗”罪行,這又再一次燃起國際社會對成立國際刑法制度的希望,聯合國後來更在1998年召開會議,正式通過成立國際刑事法院的條約,該羅馬條約在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至2008年已獲一百零六個國家簽署,並在海牙成立國際刑事法院,審訊像戰爭罪行、種族滅絕、干犯人道罪等違反國際法的嚴重罪行。國內法亦和國際法一樣,可以分為公法(Public Law)和私法(Private Law),公法是關於政府的運作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的法律,而私法則主要涉及人民之間,即私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財產和經濟方面的法律。公法的範圍包括憲法、行政法、國籍法、刑法、税務法等;私法則包括合同法、侵權法、財產法、信託法、家事法、繼承法、公司法、商法等。
另外一種分類方法,是把法律分為民法和刑法。民法牽涉的是民事訴訟(civil proceedings),刑法牽涉的是刑事訴訟(criminal proceedings)。刑法訂立了一些社會公認為最起碼的行為標準,並對違反這些行為標準的人作出懲罰。因此,刑法一般是由政府提出檢控,目的在懲罰犯法者。由於懲罰可能涉及剝奪人身自由,故此,刑法要求一個較高的舉證標準:控方必須提出足夠的證據,舉證標準須達到沒有合理疑點(beyond reasonable doubt),法院才能將被吿入罪。民法則規範私人與私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及處理因違反這些權利或義務而導致的索償要求。由於民法並不涉及個人自由,加上普通市民沒有政府那樣龐大的資源和權力去進行調査、拘捕或搜集證據,故此,民法的舉證標準是較刑法為低的:舉證一方所提出的證據,只要證明他所主張的事實存在的可能性高於其不可能性(balance of probabilities),便達到民事的舉證標準了。另一方面,由於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索取賠償而非懲罰被吿,故此,通常原告必須提出證據證明其損失。例如在一宗交通意外中,司機醉酒駕駛,警方可對司機提出刑事檢控,因為醉酒駕駛是觸犯了刑法所訂出的社會認可的最低行為標準。刑事檢控的後果是司機可能被判罰款,或被吊銷駕駛執照,甚至被判入獄。在刑事檢控的過程中,因交通意外而受傷的路人將會作為控方證人,但刑事程序的目的,不在於對傷者作出賠償,如果傷者需要索取賠償,便要進行民事訴訟了。在民事訴訟中,傷者要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受傷的原因是因為司機的疏忽,以及足夠的證據證明他的損失,例如醫藥費、工資的損失和工作能力的喪失等。由於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是兩套不同的程序,也有不同的舉證標準,故此,即使在一宗工業意外或交通意外中,政府沒有對僱主或司機提出刑事檢控,仍不會影響傷者(或死者的家屬)向僱主或司機提出民事索償的權利。
最後一種較為普遍的分類方法,是把法律分為程序法(Procedural Law)和實體法(Substantive Law)。實體法是指各個法律部門中的具體原則和規範,例如怎樣才構成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合約,或在甚麼情況下才構成民事疏忽;程序法則規範了向法院提出訴訟的程序。普通法相當重視程序的要求,目的在保證司法程序能夠公正地進行;在今天,程序法是一個相當複雜和技術性的法律部門。事實上,在高等法院處理的一般民事和刑事訴訟中,程序方面的爭論往往佔了訴訟一半以上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