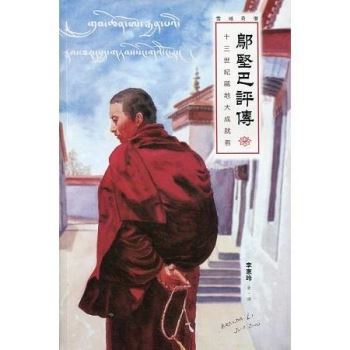第四章 堅毅不屈苦行者
無懼飢寒誓苦行遊方
(1253年,水牛年,二十三歲)
前往塔若措湖之心願未遂,鄔師再向法主請准。法主:「常言道,縱使大英雄也會碰到難關,〔但放心,〕即使你遊方他鄉,也會遇上善緣。昨夜我夢見二人以小棒擷取對岸樹上之果實,一人淹死,另一人得到很多成熟果子。孩子,你會有所成,去一趟罷!釋迦牟尼於尼連禪河畔苦修六年淨化胎氣,待三十五年其化身始得成熟,期間並未造福眾生。」
法主對鄔師說:「且看人們受慾念之箭貫穿,受苦楚磨折而不得解脫。要棄慾念如草芥,於曠野中作苦行,法性相投者互敬互重,但心智如惡狗的連吠也懶得花工夫。到處都有兇惡地祇,你可施展威力除魔障。」
其後,與辛波東巴和巴恰結伴啟程前往塔若措湖之島嶼前,向法主辭行。法主賜各種吃食,但三人只求一株青麥穗,餘者不受。法主:「光吃這點東西如何使得?日子難過啊!」之後三人去了羌卡荒原之塔若措小島,每人除了五藏升乾糧外,沒帶上其他糧食,路上「飲水吃石」(有啥吃啥)作苦行,有時煮水窪裏的浮萍來吃,有時吃野獸吃剩之魚骨。鄔師留着一點青稞,節慶時煮熟與兩同伴作「會供」。一日,三人豎起棍子,蓋上帽,作會供,然後相約好分頭採集食物後帶回來。三人到不同之山谷採食,鄔師採得滿袋蕨麻和一些魚肉,辛波東巴採得滿兩巴掌的蕨麻,巴恰則毫無收穫。之後,巴恰不再跟他們一起去羌卡,而去了查地之牧戶中。
郭倉巴終於讓步了。他焉會不知鄔堅巴之痛苦,但他疼惜他的聰慧,了解他的倔強,終於決定縱使自己損壽也讓他到外頭闖一趟,日後自有造化。臨別依依,流露出不捨之情,語重深長,一再囑咐他不要急於利眾,又叮嚀他遇到災彰如何化解,知道他不肯接受糧食時又擔心他日子難過。郭倉巴大概也知道此刻一別,師徒倆再會無期。
「羌」(chang),藏語原意是「北」,一般指藏北的「羌塘」草原,但傳記中的「羌」或「羌卡」(Chang-ka)是指羌塘草原向南伸延至日喀則地區西部的一片區域,約相當於今日仲巴縣的南部,與尼泊爾西北接壤。此地其實並非完全荒蕪,是北面的高原牧民和南面尼泊爾以至恆河流域的貿易通道之一。一夜,傳來酥油味道。翌晨同伴說:「有新鮮酥油味道,但羌卡空無一人,不可能!」其後每夜如是,氣味越來越濃。一日,遠處荒原中央出現一些帳篷,之後帳篷越來越多。二人往化緣,遇到兩名趕羊的孩子,遂問:「這是誰之帳篷?」答道:「是白利人之營帳。」問:「我倆打算去化緣,會給否?」答:「會的。」二人來到山下,一小孩說:「師父你若不歸順,他們會說你倆是探子,殺了你們。」鄔師問:「向誰歸順?」答:「齊伽綽甲以及答古班沖。」說罷離去。
見一人策馬而來,二人問:「大爺如何稱呼?往何處?」那人答:「我叫齊伽,到上方牧童那兒。」鄔師說:「我倆是山上之修禪者,到您帳中化緣去,想向您歸順。」齊伽說:「很好,若有人問話,說歸順了齊伽便可。」說罷離去。跟着又遇上答古班沖率領之白利人,問二人:「你們可不是探子罷?」答:「我們是山上的修禪者,歸順了齊伽。」那幫人雖然沒有即時為難二人,卻把二人團團圍着。此時齊伽策馬馳至,對答古班沖說:「長官,此人歸順於我,讓我們問話好了,別傷害他們。」
「白利」,藏語Be-re或Bi-ri,漢文史籍又稱「白蘭」,屬羌族一支,本來生活於青海東南部一帶,據《新唐書》,此族「勇戰鬥,善作兵,俗與党項同」。七世紀時被吐蕃君主松贊干布征服,後來向南遷徙至今日四川西部甘孜一帶,約1247年跟隨藏地降於蒙古,同年薩迦派教主勸說藏人歸順元朝的書函中說:「我帶領白利人來歸順。」白利後來疑被元朝收編為輔助部隊。筆者手上一份郭倉巴傳記文本提到他晚年居於定日中部巴爾卓(Barjo)之金剛林時(約1256至1258年),蒙古和白利聯合派兵來侵,曾作法事驅逐之,這可能就是鄔堅巴於1253年所遇之白利兵,由此可見藏地縱使歸降,仍不斷受軍事威脅。1250年,蒙古對藏西阿里的統治已建立,《元史.憲宗本紀》提到1251年蒙哥派人「統土蕃等處蒙古、漢軍」,這些白利人可能正是當時派去支援蒙古駐軍的。軍隊遂將二人分開帶走問話,由於鄔師已預先囑咐同伴:「不要說謊,實話實說」,二人口供吻合,都說「是山上之修禪者,有啥吃啥過日子,今日看到你們之帳篷,來化緣。」齊伽對手下說:「派人到山上看!」派去的人看到除了草墊、皮火筒和陶鍋煮食之痕跡外,別無他物,跟二人所說一致。那幫人於是變得很虔敬,給他們很多酥油糕和肉乾。鄔師大口地吃,很快便吃得一乾二淨,同伴把自己那份分給他,鄔師不受,說:「口中仍有食物之味道,你的一份我不吃。」
其後,來到幾戶黃色帳篷的人家化緣,有很多惡犬,鄔師解下牦牛皮護足之牦牛皮綁繩,坐在地上以繩打圈想嚇退惡犬,但無濟於事。一女子打水後到來,想打退狗兒,不果。鄔師於是停止揮舞綁繩,坐下來,把己心與狗心作「一味觀」,融合為一,狗不再吠。
次日再往化緣,那女戶主歡迎他們,頂禮並求賜福。狗隻舔及尾隨二人,好像對主人般熟絡。鄔師向聚集之所有牧民授「上師瑜伽」、「觀音禪定與誦唸」、「近住戒」、「八支律儀」等各種善法和戒律。眾人非常虔敬,不斷頂禮,求賜福,獻上很多酥油糕和肉乾。
有一次,齊伽把剛懂走路之孩兒放在牦牛背的馱子上,那牛不沿牧區的山路走,卻奔下陡坡。齊伽大喊:「幫忙抓着那牦牛!」鄔師沒捉得着牦牛,但及時從馱子上把孩子提起,放在自己肩上,牦牛跟着墮下山崖。齊伽說:「要不是大師及時相救,我兒必死。」
該地有一凶險之修行洞,洞中遺有昔日修行者之破衣,大有法力。鄔師感到一頭牦牛在踢打着,並有女子說:「這牦牛踢我,你不要留此,出去!」次日,以魚屍作會供,施金剛鐝法,把洞中之地祇驅走。
其後繼續西上,沿途「飲水吃石」充飢,但四天找不到水。下大雪,鄔師患了雪盲。同伴捧來滿掌青稞,以化緣缽煮熟來讓他吃。野牦牛也患上雪盲,鄔師須擊手鼓使其知道閃避。在羌卡荒原有啥吃啥,共浪跡九個月,虔敬心更熾,心智通明,雖有野獸威脅,仍覺滿有福力。藏地獒犬(藏獒)是牧民不可缺的守衛犬,體型巨大而極具攻擊性,對陌生人非常兇猛,對遊方者造成頗大威脅。直至二十世紀初,藏地的苦行遊方者上路時大多一手握着禪杖,或另一手持着手鼓,背着以藤架紮成之行囊。禪杖除了是法器,更是路上作倚仗和自衛之用,尤其是對付這些惡犬。鄔堅巴捨禪杖而用牦牛皮綁繩打圈自衛,看來他的揮索技術相當了得,否則相信已被獒犬咬得體無完膚了。他掌握瞬間機會從疾跑的牦牛背上攫救孩兒,身手矯健亦可想而知。
這段日子中,鄔堅巴除了頭頂的破帽,身上的破袍、腳上的芒鞋和綁腿、懷中的化緣缽、背囊中的皮火筒和陶鍋外,大概一無所有。嚴寒酷暑,大雪紛飛,穴居野處,強忍飢寒,也得如是。難得這位數年前還要兩名僕人陪伴出行的貴家公子不怕艱辛,甘之如飴,還修持得「心智通明」,感覺「滿有福力」。修行人要苦行遊方,誠然。
神山聖湖旁著書冥想
(1254年夏,木虎年,二十四歲)
其後,穿越杜爾波往四河之源——舉世聞名之底斯神山(岡仁波齊峰)。傳說底斯神山是勝樂金剛之宮殿(道場)。鄔師看到水晶塔中有無量壽宮,在該塔淨光照耀下,鄔師神智盈明。雖然文獻說底斯全是「冰柱子」,其實更像白皚皚之水晶。鄔師之同門珠仁堪布〔正好〕也在,心中正想問:「塔中究竟有啥?」鄔師已感應到,答:「看不到內部。」
盤踞於這聖地之拉隆、達隆、南波日宗等三處之止貢噶舉派修行人對鄔師說:「佛弟子,別留在此!」鄔師唯有離開。
杜爾波(Dolpo)位於今日尼泊爾西北加爾納利河(Karnali River)源頭(藏地稱「孔雀河」)的荒僻地區,是喜馬拉雅南坡海拔四五千米的馬蹄形河谷盤地,三面環山。居民信奉苯教和藏傳佛教,古時與其北面之藏地關係密切,互通有無。此地冬天漫長而嚴寒,每年十月至翌年四月完全冰封,因不易攻伐而多個世紀來較為太平。入冬前,此地居民把牛羊送交北面,由後藏與阿里之間羌地的牧民照料。往來杜爾波和羌地之間的通道,年中大部分時間可以通過。相信鄔堅巴在羌地流浪過冬後,取道杜爾波北面或穿過東面信奉苯教為主的古國洛曼塘(今日稱「木斯塘」〔Mustang〕),進入杜爾波。此地是藏地遊方修行者之苦行勝地,亦以其「伏藏秘域」聞名,鄔堅巴到此,大概是想找進入香巴拉秘境的路徑。阿里的岡仁波齊峰是藏地最神聖的雪山,峰頂終年積雪,據說從沒有人敢攀爬。傳統的「轉山」需時三天,從正南面的山麓起步,佛教徒以順時針方向登高繞山,沿途誦經並朝拜聖跡,第二天抵達與雪峰近在咫尺的山頸。鄔堅巴來到神山時是夏天,雪線約在山頸,他所說的「水晶塔」即指這雪峰。善信登上神山作巡禮看來沒受阻擾,但打算在神山居停卻是另一回事。
噶舉教派之支派止貢噶舉為擴張勢力和根據地,於1190至1215年間先後派遣三批門人至藏西阿里,其中1206年和1215年這兩次是因為前藏饑荒所致。自吐蕃王朝於九世紀覆亡,衛藏長期分裂,形成多個世紀以來地方豪強結合佛教教派割據統治的局面,各方均積極拓展據地。十一世紀以後,阿里的岡底斯神山一帶全屬噶舉派勢力範圍,十二至十三世紀中期更差不多為止貢噶舉派所壟斷。大批止貢派門人單獨或成群前往阿里,盤踞神山聖湖一帶,並受當時「阿里三圍」統治者所支持。郭倉巴曾於1210年代中期在此地居停三年,也像鄔堅巴一樣被驅逐。明顯當時止貢派門人不但敵視薩迦派,對同屬噶舉派而勢力日大的竹巴噶舉也非常不友善。1240年,窩闊台委任總督治理藏西,把管治權交給止貢教派。鄔堅巴在1254年來到此地時,全藏西已屬止貢派管治領域,對鄔堅巴之敵意是意料中事,鄔堅巴看來似乎完全接受這事實,沒有反抗,起碼在傳記中沒有埋怨。
鄔師曾經觀想其他神山,都無得着,但在底斯神山某處觀想則有得着,於是仍留在神山一帶修行。心中通明,結無限善緣,尤其悟得《時輪》所說外世界、內金剛、別壇城之神祇三者無別之道理。心中生起本來法性,於此聖地寫成《內外辨識論》一書。
其時,心中每現善念便撿一小顆白石放下,每現惡念則撿一小顆黑石放下,後來一顆黑石都不用再撿,鄔師會心微笑。
底斯神山附近之卡莫拉草原聚集了很多修行人,良莠不齊。某些懂得藏巴嘉熱大師(竹巴祖師)「勝樂十三密法儀軌」之修行人,以為鄔師不熟此法,看輕他,對他說:「你不懂這些儀軌,坐到最後去!」鄔師但笑不語,心想:「我甚至懂得講授經藏、密續等佛學寶典!以為我啥都不懂,他只懂唸那竹巴噶舉的『勝樂十三密法』而已,卻要裝作淵博。」卡莫拉草原位置不詳,相信位於神山外圍,此地的修行人大抵很多來自止貢派以外各門派。這次排擠他的人跟止貢派無關,而是同屬竹巴噶舉派的人,否則不會懂得竹巴祖師的密法儀軌。修行人良莠不齊不足為奇,當年在郭倉巴門下已遇到不少,然而這次鄔堅巴似乎沒有動怒或哀傷,只是一笑置之。經過一年的野外刻苦遊方和苦思冥想,身心果真如經過爐火鍛煉,修為終於高了,看通了,情緒不輕易受外間干擾。
眾人在佛堂就寢,上半夜看到佛堂中有極恐怖之形體,不知是何物,不斷出沒,尾巴着火,欲破壞修法,所有人均大力祈福。鄔師暗中施法,眾人均未察覺。鄔師集中意念,厲目瞪之,妖怪消失。鄔師後來說:「若非我出手,某些人恐會遭遇障難。」
其後鄔師來到瑪旁雍錯聖湖畔,飲聖水並稍作居停,然後到普蘭峒瑪去。三天沒吃東西,飢腸轆轆,大力拍打一貴夫人之門,人們以為來了瘋子,都嚇得跑掉。男僕從房子出來,說:「大師別打門,你一定瘋了,竟連這兒是何處都不曉得!」鄔師:「施我吃喝!」僕人:「別打門,我往稟告主人。」進去片刻後,拿來大份施品和大缽糌粑,鄔師唸經迴向。僕人:「夫人說很崇敬您,奉上這些禮品和糌粑,請你留下作應供喇嘛。」鄔師:「就這麼一點麵糰和糌粑便要我留下?不留!」得綽號「普蘭峒瑪的瘋子」。
其時,鄔師施隱身術上路,人、狗都看不到他。取道普蘭峒瑪,半天便抵達底斯神山之北。
其後,冬天到日土去,獲朗科兄弟三人施捨及供養,降伏一兇惡地祇。大哥知其有神通後,就家人松石被偷一事,刻意對外放話:「我有神通喇嘛,若不送還松石,喇嘛會查出並追究,偷者會受罰。」松石失而復得。找遍羌地的塔若湖以至杜爾波一帶,鄔堅巴明顯找不着《時輪》所說的秘境香巴拉,大概終於相信香巴拉與他無緣,烏仗才與他有緣。由聖湖北行前往日土是因為要由阿里西北進入北印度,相信他在攝氏零下十多度低溫的深秋或初冬所走的是傳統路線,先向西北走二百公里滿是碎石或已冰封的荒蕪地帶,至獅泉河和噶爾藏布江交匯處附近之噶爾,再向北走,穿越整個阿里高原平均海拔最高的部分,走過一千五百公里的荒野至彭公湖(Pangong Lake)以東之日土(Rutog),在這兒度過攝氏冰點以下四十多度的嚴冬。這片阿里高原上的遼闊地域人煙極稀,沿途若有缺水缺糧,料不在話下。
傳記說鄔堅巴「施隱身術」上路,只半天便抵達神山北面,這是傳記首次提到他懂隱身術。姑且假設普蘭峒瑪位於聖湖以東,以直線計距離岡仁波齊峰北面也有一百公里,何況實際路徑迂迴曲折,半天便走畢,縱使真的用上「輕功」也非易事。「隱身」而不讓惡犬看見,可以理解為避免給惡犬襲擊,但為何不讓人看到?難道為了避過止貢派門人的耳目?另一疑問,與鄔堅巴結伴而行的辛波東巴,他的修為較遜,莫非他也有能力跟鄔堅巴一同「隱身」和以「輕功」上路?
無懼飢寒誓苦行遊方
(1253年,水牛年,二十三歲)
前往塔若措湖之心願未遂,鄔師再向法主請准。法主:「常言道,縱使大英雄也會碰到難關,〔但放心,〕即使你遊方他鄉,也會遇上善緣。昨夜我夢見二人以小棒擷取對岸樹上之果實,一人淹死,另一人得到很多成熟果子。孩子,你會有所成,去一趟罷!釋迦牟尼於尼連禪河畔苦修六年淨化胎氣,待三十五年其化身始得成熟,期間並未造福眾生。」
法主對鄔師說:「且看人們受慾念之箭貫穿,受苦楚磨折而不得解脫。要棄慾念如草芥,於曠野中作苦行,法性相投者互敬互重,但心智如惡狗的連吠也懶得花工夫。到處都有兇惡地祇,你可施展威力除魔障。」
其後,與辛波東巴和巴恰結伴啟程前往塔若措湖之島嶼前,向法主辭行。法主賜各種吃食,但三人只求一株青麥穗,餘者不受。法主:「光吃這點東西如何使得?日子難過啊!」之後三人去了羌卡荒原之塔若措小島,每人除了五藏升乾糧外,沒帶上其他糧食,路上「飲水吃石」(有啥吃啥)作苦行,有時煮水窪裏的浮萍來吃,有時吃野獸吃剩之魚骨。鄔師留着一點青稞,節慶時煮熟與兩同伴作「會供」。一日,三人豎起棍子,蓋上帽,作會供,然後相約好分頭採集食物後帶回來。三人到不同之山谷採食,鄔師採得滿袋蕨麻和一些魚肉,辛波東巴採得滿兩巴掌的蕨麻,巴恰則毫無收穫。之後,巴恰不再跟他們一起去羌卡,而去了查地之牧戶中。
郭倉巴終於讓步了。他焉會不知鄔堅巴之痛苦,但他疼惜他的聰慧,了解他的倔強,終於決定縱使自己損壽也讓他到外頭闖一趟,日後自有造化。臨別依依,流露出不捨之情,語重深長,一再囑咐他不要急於利眾,又叮嚀他遇到災彰如何化解,知道他不肯接受糧食時又擔心他日子難過。郭倉巴大概也知道此刻一別,師徒倆再會無期。
「羌」(chang),藏語原意是「北」,一般指藏北的「羌塘」草原,但傳記中的「羌」或「羌卡」(Chang-ka)是指羌塘草原向南伸延至日喀則地區西部的一片區域,約相當於今日仲巴縣的南部,與尼泊爾西北接壤。此地其實並非完全荒蕪,是北面的高原牧民和南面尼泊爾以至恆河流域的貿易通道之一。一夜,傳來酥油味道。翌晨同伴說:「有新鮮酥油味道,但羌卡空無一人,不可能!」其後每夜如是,氣味越來越濃。一日,遠處荒原中央出現一些帳篷,之後帳篷越來越多。二人往化緣,遇到兩名趕羊的孩子,遂問:「這是誰之帳篷?」答道:「是白利人之營帳。」問:「我倆打算去化緣,會給否?」答:「會的。」二人來到山下,一小孩說:「師父你若不歸順,他們會說你倆是探子,殺了你們。」鄔師問:「向誰歸順?」答:「齊伽綽甲以及答古班沖。」說罷離去。
見一人策馬而來,二人問:「大爺如何稱呼?往何處?」那人答:「我叫齊伽,到上方牧童那兒。」鄔師說:「我倆是山上之修禪者,到您帳中化緣去,想向您歸順。」齊伽說:「很好,若有人問話,說歸順了齊伽便可。」說罷離去。跟着又遇上答古班沖率領之白利人,問二人:「你們可不是探子罷?」答:「我們是山上的修禪者,歸順了齊伽。」那幫人雖然沒有即時為難二人,卻把二人團團圍着。此時齊伽策馬馳至,對答古班沖說:「長官,此人歸順於我,讓我們問話好了,別傷害他們。」
「白利」,藏語Be-re或Bi-ri,漢文史籍又稱「白蘭」,屬羌族一支,本來生活於青海東南部一帶,據《新唐書》,此族「勇戰鬥,善作兵,俗與党項同」。七世紀時被吐蕃君主松贊干布征服,後來向南遷徙至今日四川西部甘孜一帶,約1247年跟隨藏地降於蒙古,同年薩迦派教主勸說藏人歸順元朝的書函中說:「我帶領白利人來歸順。」白利後來疑被元朝收編為輔助部隊。筆者手上一份郭倉巴傳記文本提到他晚年居於定日中部巴爾卓(Barjo)之金剛林時(約1256至1258年),蒙古和白利聯合派兵來侵,曾作法事驅逐之,這可能就是鄔堅巴於1253年所遇之白利兵,由此可見藏地縱使歸降,仍不斷受軍事威脅。1250年,蒙古對藏西阿里的統治已建立,《元史.憲宗本紀》提到1251年蒙哥派人「統土蕃等處蒙古、漢軍」,這些白利人可能正是當時派去支援蒙古駐軍的。軍隊遂將二人分開帶走問話,由於鄔師已預先囑咐同伴:「不要說謊,實話實說」,二人口供吻合,都說「是山上之修禪者,有啥吃啥過日子,今日看到你們之帳篷,來化緣。」齊伽對手下說:「派人到山上看!」派去的人看到除了草墊、皮火筒和陶鍋煮食之痕跡外,別無他物,跟二人所說一致。那幫人於是變得很虔敬,給他們很多酥油糕和肉乾。鄔師大口地吃,很快便吃得一乾二淨,同伴把自己那份分給他,鄔師不受,說:「口中仍有食物之味道,你的一份我不吃。」
其後,來到幾戶黃色帳篷的人家化緣,有很多惡犬,鄔師解下牦牛皮護足之牦牛皮綁繩,坐在地上以繩打圈想嚇退惡犬,但無濟於事。一女子打水後到來,想打退狗兒,不果。鄔師於是停止揮舞綁繩,坐下來,把己心與狗心作「一味觀」,融合為一,狗不再吠。
次日再往化緣,那女戶主歡迎他們,頂禮並求賜福。狗隻舔及尾隨二人,好像對主人般熟絡。鄔師向聚集之所有牧民授「上師瑜伽」、「觀音禪定與誦唸」、「近住戒」、「八支律儀」等各種善法和戒律。眾人非常虔敬,不斷頂禮,求賜福,獻上很多酥油糕和肉乾。
有一次,齊伽把剛懂走路之孩兒放在牦牛背的馱子上,那牛不沿牧區的山路走,卻奔下陡坡。齊伽大喊:「幫忙抓着那牦牛!」鄔師沒捉得着牦牛,但及時從馱子上把孩子提起,放在自己肩上,牦牛跟着墮下山崖。齊伽說:「要不是大師及時相救,我兒必死。」
該地有一凶險之修行洞,洞中遺有昔日修行者之破衣,大有法力。鄔師感到一頭牦牛在踢打着,並有女子說:「這牦牛踢我,你不要留此,出去!」次日,以魚屍作會供,施金剛鐝法,把洞中之地祇驅走。
其後繼續西上,沿途「飲水吃石」充飢,但四天找不到水。下大雪,鄔師患了雪盲。同伴捧來滿掌青稞,以化緣缽煮熟來讓他吃。野牦牛也患上雪盲,鄔師須擊手鼓使其知道閃避。在羌卡荒原有啥吃啥,共浪跡九個月,虔敬心更熾,心智通明,雖有野獸威脅,仍覺滿有福力。藏地獒犬(藏獒)是牧民不可缺的守衛犬,體型巨大而極具攻擊性,對陌生人非常兇猛,對遊方者造成頗大威脅。直至二十世紀初,藏地的苦行遊方者上路時大多一手握着禪杖,或另一手持着手鼓,背着以藤架紮成之行囊。禪杖除了是法器,更是路上作倚仗和自衛之用,尤其是對付這些惡犬。鄔堅巴捨禪杖而用牦牛皮綁繩打圈自衛,看來他的揮索技術相當了得,否則相信已被獒犬咬得體無完膚了。他掌握瞬間機會從疾跑的牦牛背上攫救孩兒,身手矯健亦可想而知。
這段日子中,鄔堅巴除了頭頂的破帽,身上的破袍、腳上的芒鞋和綁腿、懷中的化緣缽、背囊中的皮火筒和陶鍋外,大概一無所有。嚴寒酷暑,大雪紛飛,穴居野處,強忍飢寒,也得如是。難得這位數年前還要兩名僕人陪伴出行的貴家公子不怕艱辛,甘之如飴,還修持得「心智通明」,感覺「滿有福力」。修行人要苦行遊方,誠然。
神山聖湖旁著書冥想
(1254年夏,木虎年,二十四歲)
其後,穿越杜爾波往四河之源——舉世聞名之底斯神山(岡仁波齊峰)。傳說底斯神山是勝樂金剛之宮殿(道場)。鄔師看到水晶塔中有無量壽宮,在該塔淨光照耀下,鄔師神智盈明。雖然文獻說底斯全是「冰柱子」,其實更像白皚皚之水晶。鄔師之同門珠仁堪布〔正好〕也在,心中正想問:「塔中究竟有啥?」鄔師已感應到,答:「看不到內部。」
盤踞於這聖地之拉隆、達隆、南波日宗等三處之止貢噶舉派修行人對鄔師說:「佛弟子,別留在此!」鄔師唯有離開。
杜爾波(Dolpo)位於今日尼泊爾西北加爾納利河(Karnali River)源頭(藏地稱「孔雀河」)的荒僻地區,是喜馬拉雅南坡海拔四五千米的馬蹄形河谷盤地,三面環山。居民信奉苯教和藏傳佛教,古時與其北面之藏地關係密切,互通有無。此地冬天漫長而嚴寒,每年十月至翌年四月完全冰封,因不易攻伐而多個世紀來較為太平。入冬前,此地居民把牛羊送交北面,由後藏與阿里之間羌地的牧民照料。往來杜爾波和羌地之間的通道,年中大部分時間可以通過。相信鄔堅巴在羌地流浪過冬後,取道杜爾波北面或穿過東面信奉苯教為主的古國洛曼塘(今日稱「木斯塘」〔Mustang〕),進入杜爾波。此地是藏地遊方修行者之苦行勝地,亦以其「伏藏秘域」聞名,鄔堅巴到此,大概是想找進入香巴拉秘境的路徑。阿里的岡仁波齊峰是藏地最神聖的雪山,峰頂終年積雪,據說從沒有人敢攀爬。傳統的「轉山」需時三天,從正南面的山麓起步,佛教徒以順時針方向登高繞山,沿途誦經並朝拜聖跡,第二天抵達與雪峰近在咫尺的山頸。鄔堅巴來到神山時是夏天,雪線約在山頸,他所說的「水晶塔」即指這雪峰。善信登上神山作巡禮看來沒受阻擾,但打算在神山居停卻是另一回事。
噶舉教派之支派止貢噶舉為擴張勢力和根據地,於1190至1215年間先後派遣三批門人至藏西阿里,其中1206年和1215年這兩次是因為前藏饑荒所致。自吐蕃王朝於九世紀覆亡,衛藏長期分裂,形成多個世紀以來地方豪強結合佛教教派割據統治的局面,各方均積極拓展據地。十一世紀以後,阿里的岡底斯神山一帶全屬噶舉派勢力範圍,十二至十三世紀中期更差不多為止貢噶舉派所壟斷。大批止貢派門人單獨或成群前往阿里,盤踞神山聖湖一帶,並受當時「阿里三圍」統治者所支持。郭倉巴曾於1210年代中期在此地居停三年,也像鄔堅巴一樣被驅逐。明顯當時止貢派門人不但敵視薩迦派,對同屬噶舉派而勢力日大的竹巴噶舉也非常不友善。1240年,窩闊台委任總督治理藏西,把管治權交給止貢教派。鄔堅巴在1254年來到此地時,全藏西已屬止貢派管治領域,對鄔堅巴之敵意是意料中事,鄔堅巴看來似乎完全接受這事實,沒有反抗,起碼在傳記中沒有埋怨。
鄔師曾經觀想其他神山,都無得着,但在底斯神山某處觀想則有得着,於是仍留在神山一帶修行。心中通明,結無限善緣,尤其悟得《時輪》所說外世界、內金剛、別壇城之神祇三者無別之道理。心中生起本來法性,於此聖地寫成《內外辨識論》一書。
其時,心中每現善念便撿一小顆白石放下,每現惡念則撿一小顆黑石放下,後來一顆黑石都不用再撿,鄔師會心微笑。
底斯神山附近之卡莫拉草原聚集了很多修行人,良莠不齊。某些懂得藏巴嘉熱大師(竹巴祖師)「勝樂十三密法儀軌」之修行人,以為鄔師不熟此法,看輕他,對他說:「你不懂這些儀軌,坐到最後去!」鄔師但笑不語,心想:「我甚至懂得講授經藏、密續等佛學寶典!以為我啥都不懂,他只懂唸那竹巴噶舉的『勝樂十三密法』而已,卻要裝作淵博。」卡莫拉草原位置不詳,相信位於神山外圍,此地的修行人大抵很多來自止貢派以外各門派。這次排擠他的人跟止貢派無關,而是同屬竹巴噶舉派的人,否則不會懂得竹巴祖師的密法儀軌。修行人良莠不齊不足為奇,當年在郭倉巴門下已遇到不少,然而這次鄔堅巴似乎沒有動怒或哀傷,只是一笑置之。經過一年的野外刻苦遊方和苦思冥想,身心果真如經過爐火鍛煉,修為終於高了,看通了,情緒不輕易受外間干擾。
眾人在佛堂就寢,上半夜看到佛堂中有極恐怖之形體,不知是何物,不斷出沒,尾巴着火,欲破壞修法,所有人均大力祈福。鄔師暗中施法,眾人均未察覺。鄔師集中意念,厲目瞪之,妖怪消失。鄔師後來說:「若非我出手,某些人恐會遭遇障難。」
其後鄔師來到瑪旁雍錯聖湖畔,飲聖水並稍作居停,然後到普蘭峒瑪去。三天沒吃東西,飢腸轆轆,大力拍打一貴夫人之門,人們以為來了瘋子,都嚇得跑掉。男僕從房子出來,說:「大師別打門,你一定瘋了,竟連這兒是何處都不曉得!」鄔師:「施我吃喝!」僕人:「別打門,我往稟告主人。」進去片刻後,拿來大份施品和大缽糌粑,鄔師唸經迴向。僕人:「夫人說很崇敬您,奉上這些禮品和糌粑,請你留下作應供喇嘛。」鄔師:「就這麼一點麵糰和糌粑便要我留下?不留!」得綽號「普蘭峒瑪的瘋子」。
其時,鄔師施隱身術上路,人、狗都看不到他。取道普蘭峒瑪,半天便抵達底斯神山之北。
其後,冬天到日土去,獲朗科兄弟三人施捨及供養,降伏一兇惡地祇。大哥知其有神通後,就家人松石被偷一事,刻意對外放話:「我有神通喇嘛,若不送還松石,喇嘛會查出並追究,偷者會受罰。」松石失而復得。找遍羌地的塔若湖以至杜爾波一帶,鄔堅巴明顯找不着《時輪》所說的秘境香巴拉,大概終於相信香巴拉與他無緣,烏仗才與他有緣。由聖湖北行前往日土是因為要由阿里西北進入北印度,相信他在攝氏零下十多度低溫的深秋或初冬所走的是傳統路線,先向西北走二百公里滿是碎石或已冰封的荒蕪地帶,至獅泉河和噶爾藏布江交匯處附近之噶爾,再向北走,穿越整個阿里高原平均海拔最高的部分,走過一千五百公里的荒野至彭公湖(Pangong Lake)以東之日土(Rutog),在這兒度過攝氏冰點以下四十多度的嚴冬。這片阿里高原上的遼闊地域人煙極稀,沿途若有缺水缺糧,料不在話下。
傳記說鄔堅巴「施隱身術」上路,只半天便抵達神山北面,這是傳記首次提到他懂隱身術。姑且假設普蘭峒瑪位於聖湖以東,以直線計距離岡仁波齊峰北面也有一百公里,何況實際路徑迂迴曲折,半天便走畢,縱使真的用上「輕功」也非易事。「隱身」而不讓惡犬看見,可以理解為避免給惡犬襲擊,但為何不讓人看到?難道為了避過止貢派門人的耳目?另一疑問,與鄔堅巴結伴而行的辛波東巴,他的修為較遜,莫非他也有能力跟鄔堅巴一同「隱身」和以「輕功」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