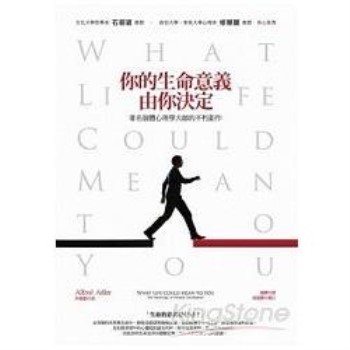生命的三項工作
人活在「意義」的領域裡。對於事物,我們的經驗不是抽象的;我們始終以人的立場去經驗它們。即使對於它的根源,我們的經驗仍以人的認知做標準。「木頭」指「木頭跟人的關係」,「石頭」指「人類生命要素之一的石頭」。任何試圖去考慮狀況而排拒意義的人,都會非常不幸:他隔絕起自己,他的行為對他自己,或對別人,都會毫無用處;總而言之,他們的行為會毫無意義。不過,沒人能跳脫意義的範疇。唯有透過我們認為的意義,我們才經驗到現實;但那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某種詮釋過的東西。於是,自然而然,這個意義總是或多或少地不圓滿,或不完整,甚至永遠都不是正確的。因此,意義的領域就是錯誤的領域。
如果我們問某個人:「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或許他根本就答不出來。通常人不會拿這個問題自找麻煩,或嘗試去架構出任何答案。但這個問題就跟人類一樣古老,在我們的一生裡,年輕人還有年齡較長的人,有時會追問:「生命為的是什麼?生命是什麼?」然而,可以這麼公平地說,他們只有在為某些挫折所苦的時候,才會提問這些問題。只要他們凡事平順,沒有磨難,這個問題就絕不會被提及。反而是在行為上,每個人都不能避免地提出這些問題,並予以回答。如果我們不去聆聽,而專心觀察行為本身,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每個人都已架構出他個人的「生命意義」,而他所有的意見、態度、舉動、表達、格調、野心、習慣和個性特色,都根據這個意義。每個人的行為就好像他能依靠一個確實的生命詮釋一樣。他所有的行為,隱含著一個他對世界和他個人的結論;就像判決一樣:我就是這樣,宇宙就是那樣;一個他給自己,以及他所認為的生命意義。
人有多少,生命的意義就有多少,或許就如我們先前提過的,每個意義都有某些程度上的錯誤。沒人知道什麼才是生命絕對正確的意義,所以我們也不能說任何有用的詮釋絕對是錯的。所有的意義在這兩個限制間都有差異。不過,在這些差異裡,我們能夠辨識出來,有的極為有效,有的成效較低;有些錯誤小,有些錯誤大。我們能找出較佳的詮釋有哪些共同點,還有較不令人滿意的詮釋缺少了什麼。從中我們能找出一個真理的共同標準,一個共同的意義,促使我們把人類關切至今的現實解讀出來。再來,我們必須牢記在心,這「真理」是為了人類的目的和目標的真理。除此之外,再沒其他真理。即使真有其他真理,也不會影響我們。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那是毫無意義的。
每個人都在三大限制下生活,他必須顧及這些限制。他所面對的每個問題或疑問都由它們而起,所以它們為他構成現實,由於他不斷面對它們,他總被迫要回答和處理這些問題,而我們可由他的答案裡,找出他個人對生命意義的詮釋。
第一個限制是我們都生活在地球,這個小星球的表面上,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我們必須盡力在地球有限的資源和限制下生活。我們必須發展身心兩面,以讓我們能夠繼續個人在地球上的生命,並協助確保人類生命的延續。這個問題挑戰每個人,沒人規避得了。不論我們做什麼,每個行為都是我們個人對人類生命的一個答案:它們顯示出我們認為必要、適合、可能和期待的東西。每一個答案都必須顧及我們是人類的一分子,並聚居在這個地球上的事實。
現在,如果考量到人體的脆弱,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潛藏著的危險,為維護我們的生命,以及人類的福祉,重新評估我們的答案,讓其具有遠瞻性和清楚的意義,對我們就變得十分緊要。這就像做一道數學題目一樣;我們必須努力找出解答。不能隨便或瞎猜,我們必須持續努力,用盡方法,把答案找出來。雖然我們未必能找到一個能夠澈底解釋真理、絕對完美的答案,但必須竭盡所能,找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此外,我們必須持續努力,找更好的解答,而所有答案都必須把我們局限在地球上,以及把我們所處地位的全部優勢、劣勢等事實,都考慮在內。
到這裡我們談到第二個限制,就是我們之中沒人是人類的唯一成員。我們週遭有別人,我們的存在跟他們脫離不了關係。由於個體的弱點和限制,如果一個人孤立,他絕對達成不了個人的目標。如果一個人獨自生活,試圖單獨解決問題,他一定會滅亡。他繼續不了自己的生命,也無法延續人類的生命。由於個人的弱點、短處和限制,他總是跟別人連結在一起。對他個人的利益,以及對人類的福祉而言,夥伴關係的貢獻最大。因此,對生命問題的每一個答案,都必須把這個限制考慮在內;必須考慮我們的生活與別人息息相關,我們孤獨必亡的事實。如果要生存,即便是我們的情緒都必須順應這個最偉大的課題、目的和目標;在這個我們與人類夥伴共棲的星球上,延續我們個人的生命,以及人類的生命。
我們還受到人由男女兩性構成這第三個限制的支配。個體和全體生命的存續也必須把這個事實考慮在內。愛情和婚姻難題源自這第三個限制,沒有一個男性或女性能夠倖免一生。每個人對這個難題的反應,構成他個人的答案。人類有許多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行為總顯露出他們相信的唯一答案。
因此,這三個限制引出三個問題:首先,在我們所居住的星球自然環境的限制下,如何找到一個職業,讓我們能夠生存下去;其次,在芸芸眾人裡,我們如何自我定位,以讓我們能相互合作,並分享合作的利益;第三,我們怎樣去調適兩性,而且依靠這兩性關係延續人類生命的事實。
個體心理學發現,人所有的問題可以歸納成三大類:職業性、社會性,以及性方面的問題。每個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應裡,都不免透露出個人對生命意義的詮釋。打個比方,假設有一個人愛情生活不如意,或缺乏愛情滋潤,職業表現不彰,朋友寥寥無幾,而且與別人接觸時感覺痛苦不堪。那麼,由於他的自我設限,我們可以總結說,他把活著視為一件既艱難又危險的事情,機會稀少,失敗連連。他行為上的狹隘為他表達出意見:「生命只指保護自己,避免受傷,封閉起自己,不受傷害。」
另一方面,假設有一個人愛情關係既親密又契合,工作成就卓著,朋友很多,人際接觸廣泛又豐碩。那麼,我們可以做出結論說,這個人把生命看成一件創造性十足的差事,充滿機會,沒有克服不了的挫折。他面對所有生命問題的勇氣,就像是在解釋說:「生命只指對人有興趣,成為全體的一分子,並為人類福祉貢獻一己之力。」
社會感
在這裡我們會找出所有錯誤的「生命意義」和所有真實的「生命意義」的共同點。神經症者、精神病人、罪犯、酗酒者、問題兒童、自殺、變態和賣淫的人,所有這些人的失敗,都是因為他們欠缺同伴感和社群興趣引起的。碰到工作、友誼和性方面的問題時,他們對透過合作來解決問題的方式沒有信心。這表示生命對他們的意義是私己的,沒人能由他們個人的成就裡獲益。他們成功的目標其實是一個純粹假想的優越目標,他們的成功只對他們自己有意義。
以殺人犯為例,他們坦承殺人是由於手裡拿著武器時的一股權力感作祟,但這明顯表示,他們的重要性只止於對他們自己。對於其他人的我們,我們想也想不透,怎麼有一件武器在手就可以產生優越價值來。一個私己的意義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唯有交流,意義才可能真實。只對一個人有意義的話,實際上是絲毫無意義的。我們的目標和行為也一樣:它們唯一真實的意義,就是對他人有意義。每個人都努力想讓自己變得重要,但如果不能認清自己的重要性,讓自己對他人生命做出的貢獻,則人始終有錯。
有一個小教派教主的故事。有一天,她召集所有信徒,跟他們說世界末日將在下個星期三來臨。她的信徒深信不疑,馬上變賣財產,不顧世事,一心企盼著這場大災難。到了星期三這天,一天如常過去。星期四他們找教主要求解釋:「看看妳是怎麼把我們搞得一團糟。我們拋棄一切,告訴所有遇到的人說,世界末日將在星期三來臨,當他們譏笑的時候,我們不但一點也沒灰心,還再三強調它的真實性。如今星期三來了又去,一切卻相安無事,世界依然存在。」
這位女先知辯護說:「但是我的星期三,不是你們的星期三。」在此方式下,她以一個私己的意義來自我抗辯。一個私己的意義永遠無法測試和獲得證實。
所有真實的「生命意義」都有一個特徵,就是它們皆是普通的意義,他人能夠分享與接納的意義。一個有效解決生命問題的方法,往往也為他人樹立典範,因為我們會由其中看見常見的問題。即使天才也不過被定義為「至高無上的有用性」:當某個人的生命對多數人具有重大意義且獲得認同時,我們即稱他為天才。所以,天才賦予生命的意義往往即是:「生命表示貢獻全體人類。」在這裡我們不是在表白動機,我們暫且放下這類主張不談,反而把重心放在具體成就上。遭遇生命問題的人成功克服問題,彷彿他澈底和自然地認清生命的基本意義,就是為他人的利益著想,並與他人合作。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似乎都是為了人類同伴的利益,他以不影響他人的利益為前提,試圖克服個人遭遇的難題。
或許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觀點,而且可能懷疑我們說生命的意義實際上是貢獻,為他人的利益著想,並與他人合作的這個說法正確與否。他們可能問說:「但個人呢?」如果總是為他人著想,為他人的利益奉獻,那麼他個人不是會受傷害嗎?有些個人為了獲得適當發展,他們不是至少得先為自己著想嗎?有些個人不是應該先學習保護自己的利益,或者強化他們的個性嗎?
我相信這種觀點是個極大的錯誤,而且它所提出的問題是虛假的。如果一個人希望他的生命意義是提供貢獻,而且他致力往此目標前進的話,那麼他自然會朝著能夠讓他做出貢獻的最佳方向去發展。他會讓自己符合他的目標:他將發展出社會感,並且透過實際參與取得更多技巧。一旦目標設定完成後,訓練即接踵而來。之後他會開始自我充實來解決人生問題,以及發展他的能力。讓我們拿愛和婚姻為例。如果我們對伴侶有興趣,盡力舒緩和豐富伴侶的生命,我們自然會展現我們所能夠做到的最好一面。假如我們認為必須像吸塵機般發展個性,不願為他人的生命做任何貢獻,我們只會變得專制和不快樂。
生命的真實意義取決於貢獻和合作的推論,裡面含有另一個暗意。如果我們環顧今日由前人處繼承而來的週遭,我們看見什麼?現在我們擁有的一切都是前人為人類生命貢獻的遺跡。我們看見耕種的土地;我們看見道路和建築物。透過傳統、哲學、科學和藝術,以及處理人類狀況的技術,我們看見他們人生經驗的果實。所有這些事物,都是為人類福祉貢獻的先人遺留給我們的。
那麼,其他人呢?那些從未跟人合作,有其他生命意義,只問:「我能由生命裡獲得什麼?」的人呢?他們死後未曾留下痕跡。他們不僅死了;他們的生命亦毫無價值。彷彿我們的地球跟他們說了:「我們不需要你。你不適合生命。你的目的和努力,你自認的價值,你的心靈沒有未來。走開吧!我們不要你。離開這個人世消失吧!」不把合作當作生命意義的人,他們獲得的最後判決總是:「你毫無用處。沒人要你。走吧!」當然在現今的文化裡,我們能夠找到許多的不完美。我們發現有不怎麼令人滿意的地方,我們必須改變;但是這個改變必須以人類福祉做進一步貢獻為宗旨。
一直以來都不乏有人明白這個事實,了解生命的意義是為維護全體人類的福祉,並且試圖發展社會興趣和愛,我們發現所有宗教信仰皆關切人類的解救。世界所有重大的演變皆以增進社會福祉為目標,而宗教即朝此方向進行最大努力。然而,宗教經常被誤解,除了既有的努力外,它們很難再做更多,除非這個人類共同的目標更進一步發揚光大。個體心理學以科學方式達成相同結論,並且建議以科學方法來達成這個目標。我相信這是往前的一步。也許科學增進人類對其他人類夥伴和全體人類福祉的利益,能夠比其他如政治或宗教等所主導的變革達成更多。我們以不同角度看待一個問題的同時,立意依然相同──增進他人的利益。
由於我們所賦予生命的意義,就跟以往一樣,變成生命的守護天使或欲望的惡魔,所以了解這些意義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修正以避免鑄成大錯,顯然對我們極為重要。所以心理學的角色明顯不同於生理學或生物學:讓我們對意義,以及它們對人類行為和人類命運的影響有一個了解。
人活在「意義」的領域裡。對於事物,我們的經驗不是抽象的;我們始終以人的立場去經驗它們。即使對於它的根源,我們的經驗仍以人的認知做標準。「木頭」指「木頭跟人的關係」,「石頭」指「人類生命要素之一的石頭」。任何試圖去考慮狀況而排拒意義的人,都會非常不幸:他隔絕起自己,他的行為對他自己,或對別人,都會毫無用處;總而言之,他們的行為會毫無意義。不過,沒人能跳脫意義的範疇。唯有透過我們認為的意義,我們才經驗到現實;但那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某種詮釋過的東西。於是,自然而然,這個意義總是或多或少地不圓滿,或不完整,甚至永遠都不是正確的。因此,意義的領域就是錯誤的領域。
如果我們問某個人:「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或許他根本就答不出來。通常人不會拿這個問題自找麻煩,或嘗試去架構出任何答案。但這個問題就跟人類一樣古老,在我們的一生裡,年輕人還有年齡較長的人,有時會追問:「生命為的是什麼?生命是什麼?」然而,可以這麼公平地說,他們只有在為某些挫折所苦的時候,才會提問這些問題。只要他們凡事平順,沒有磨難,這個問題就絕不會被提及。反而是在行為上,每個人都不能避免地提出這些問題,並予以回答。如果我們不去聆聽,而專心觀察行為本身,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每個人都已架構出他個人的「生命意義」,而他所有的意見、態度、舉動、表達、格調、野心、習慣和個性特色,都根據這個意義。每個人的行為就好像他能依靠一個確實的生命詮釋一樣。他所有的行為,隱含著一個他對世界和他個人的結論;就像判決一樣:我就是這樣,宇宙就是那樣;一個他給自己,以及他所認為的生命意義。
人有多少,生命的意義就有多少,或許就如我們先前提過的,每個意義都有某些程度上的錯誤。沒人知道什麼才是生命絕對正確的意義,所以我們也不能說任何有用的詮釋絕對是錯的。所有的意義在這兩個限制間都有差異。不過,在這些差異裡,我們能夠辨識出來,有的極為有效,有的成效較低;有些錯誤小,有些錯誤大。我們能找出較佳的詮釋有哪些共同點,還有較不令人滿意的詮釋缺少了什麼。從中我們能找出一個真理的共同標準,一個共同的意義,促使我們把人類關切至今的現實解讀出來。再來,我們必須牢記在心,這「真理」是為了人類的目的和目標的真理。除此之外,再沒其他真理。即使真有其他真理,也不會影響我們。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那是毫無意義的。
每個人都在三大限制下生活,他必須顧及這些限制。他所面對的每個問題或疑問都由它們而起,所以它們為他構成現實,由於他不斷面對它們,他總被迫要回答和處理這些問題,而我們可由他的答案裡,找出他個人對生命意義的詮釋。
第一個限制是我們都生活在地球,這個小星球的表面上,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我們必須盡力在地球有限的資源和限制下生活。我們必須發展身心兩面,以讓我們能夠繼續個人在地球上的生命,並協助確保人類生命的延續。這個問題挑戰每個人,沒人規避得了。不論我們做什麼,每個行為都是我們個人對人類生命的一個答案:它們顯示出我們認為必要、適合、可能和期待的東西。每一個答案都必須顧及我們是人類的一分子,並聚居在這個地球上的事實。
現在,如果考量到人體的脆弱,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潛藏著的危險,為維護我們的生命,以及人類的福祉,重新評估我們的答案,讓其具有遠瞻性和清楚的意義,對我們就變得十分緊要。這就像做一道數學題目一樣;我們必須努力找出解答。不能隨便或瞎猜,我們必須持續努力,用盡方法,把答案找出來。雖然我們未必能找到一個能夠澈底解釋真理、絕對完美的答案,但必須竭盡所能,找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此外,我們必須持續努力,找更好的解答,而所有答案都必須把我們局限在地球上,以及把我們所處地位的全部優勢、劣勢等事實,都考慮在內。
到這裡我們談到第二個限制,就是我們之中沒人是人類的唯一成員。我們週遭有別人,我們的存在跟他們脫離不了關係。由於個體的弱點和限制,如果一個人孤立,他絕對達成不了個人的目標。如果一個人獨自生活,試圖單獨解決問題,他一定會滅亡。他繼續不了自己的生命,也無法延續人類的生命。由於個人的弱點、短處和限制,他總是跟別人連結在一起。對他個人的利益,以及對人類的福祉而言,夥伴關係的貢獻最大。因此,對生命問題的每一個答案,都必須把這個限制考慮在內;必須考慮我們的生活與別人息息相關,我們孤獨必亡的事實。如果要生存,即便是我們的情緒都必須順應這個最偉大的課題、目的和目標;在這個我們與人類夥伴共棲的星球上,延續我們個人的生命,以及人類的生命。
我們還受到人由男女兩性構成這第三個限制的支配。個體和全體生命的存續也必須把這個事實考慮在內。愛情和婚姻難題源自這第三個限制,沒有一個男性或女性能夠倖免一生。每個人對這個難題的反應,構成他個人的答案。人類有許多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行為總顯露出他們相信的唯一答案。
因此,這三個限制引出三個問題:首先,在我們所居住的星球自然環境的限制下,如何找到一個職業,讓我們能夠生存下去;其次,在芸芸眾人裡,我們如何自我定位,以讓我們能相互合作,並分享合作的利益;第三,我們怎樣去調適兩性,而且依靠這兩性關係延續人類生命的事實。
個體心理學發現,人所有的問題可以歸納成三大類:職業性、社會性,以及性方面的問題。每個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應裡,都不免透露出個人對生命意義的詮釋。打個比方,假設有一個人愛情生活不如意,或缺乏愛情滋潤,職業表現不彰,朋友寥寥無幾,而且與別人接觸時感覺痛苦不堪。那麼,由於他的自我設限,我們可以總結說,他把活著視為一件既艱難又危險的事情,機會稀少,失敗連連。他行為上的狹隘為他表達出意見:「生命只指保護自己,避免受傷,封閉起自己,不受傷害。」
另一方面,假設有一個人愛情關係既親密又契合,工作成就卓著,朋友很多,人際接觸廣泛又豐碩。那麼,我們可以做出結論說,這個人把生命看成一件創造性十足的差事,充滿機會,沒有克服不了的挫折。他面對所有生命問題的勇氣,就像是在解釋說:「生命只指對人有興趣,成為全體的一分子,並為人類福祉貢獻一己之力。」
社會感
在這裡我們會找出所有錯誤的「生命意義」和所有真實的「生命意義」的共同點。神經症者、精神病人、罪犯、酗酒者、問題兒童、自殺、變態和賣淫的人,所有這些人的失敗,都是因為他們欠缺同伴感和社群興趣引起的。碰到工作、友誼和性方面的問題時,他們對透過合作來解決問題的方式沒有信心。這表示生命對他們的意義是私己的,沒人能由他們個人的成就裡獲益。他們成功的目標其實是一個純粹假想的優越目標,他們的成功只對他們自己有意義。
以殺人犯為例,他們坦承殺人是由於手裡拿著武器時的一股權力感作祟,但這明顯表示,他們的重要性只止於對他們自己。對於其他人的我們,我們想也想不透,怎麼有一件武器在手就可以產生優越價值來。一個私己的意義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唯有交流,意義才可能真實。只對一個人有意義的話,實際上是絲毫無意義的。我們的目標和行為也一樣:它們唯一真實的意義,就是對他人有意義。每個人都努力想讓自己變得重要,但如果不能認清自己的重要性,讓自己對他人生命做出的貢獻,則人始終有錯。
有一個小教派教主的故事。有一天,她召集所有信徒,跟他們說世界末日將在下個星期三來臨。她的信徒深信不疑,馬上變賣財產,不顧世事,一心企盼著這場大災難。到了星期三這天,一天如常過去。星期四他們找教主要求解釋:「看看妳是怎麼把我們搞得一團糟。我們拋棄一切,告訴所有遇到的人說,世界末日將在星期三來臨,當他們譏笑的時候,我們不但一點也沒灰心,還再三強調它的真實性。如今星期三來了又去,一切卻相安無事,世界依然存在。」
這位女先知辯護說:「但是我的星期三,不是你們的星期三。」在此方式下,她以一個私己的意義來自我抗辯。一個私己的意義永遠無法測試和獲得證實。
所有真實的「生命意義」都有一個特徵,就是它們皆是普通的意義,他人能夠分享與接納的意義。一個有效解決生命問題的方法,往往也為他人樹立典範,因為我們會由其中看見常見的問題。即使天才也不過被定義為「至高無上的有用性」:當某個人的生命對多數人具有重大意義且獲得認同時,我們即稱他為天才。所以,天才賦予生命的意義往往即是:「生命表示貢獻全體人類。」在這裡我們不是在表白動機,我們暫且放下這類主張不談,反而把重心放在具體成就上。遭遇生命問題的人成功克服問題,彷彿他澈底和自然地認清生命的基本意義,就是為他人的利益著想,並與他人合作。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似乎都是為了人類同伴的利益,他以不影響他人的利益為前提,試圖克服個人遭遇的難題。
或許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觀點,而且可能懷疑我們說生命的意義實際上是貢獻,為他人的利益著想,並與他人合作的這個說法正確與否。他們可能問說:「但個人呢?」如果總是為他人著想,為他人的利益奉獻,那麼他個人不是會受傷害嗎?有些個人為了獲得適當發展,他們不是至少得先為自己著想嗎?有些個人不是應該先學習保護自己的利益,或者強化他們的個性嗎?
我相信這種觀點是個極大的錯誤,而且它所提出的問題是虛假的。如果一個人希望他的生命意義是提供貢獻,而且他致力往此目標前進的話,那麼他自然會朝著能夠讓他做出貢獻的最佳方向去發展。他會讓自己符合他的目標:他將發展出社會感,並且透過實際參與取得更多技巧。一旦目標設定完成後,訓練即接踵而來。之後他會開始自我充實來解決人生問題,以及發展他的能力。讓我們拿愛和婚姻為例。如果我們對伴侶有興趣,盡力舒緩和豐富伴侶的生命,我們自然會展現我們所能夠做到的最好一面。假如我們認為必須像吸塵機般發展個性,不願為他人的生命做任何貢獻,我們只會變得專制和不快樂。
生命的真實意義取決於貢獻和合作的推論,裡面含有另一個暗意。如果我們環顧今日由前人處繼承而來的週遭,我們看見什麼?現在我們擁有的一切都是前人為人類生命貢獻的遺跡。我們看見耕種的土地;我們看見道路和建築物。透過傳統、哲學、科學和藝術,以及處理人類狀況的技術,我們看見他們人生經驗的果實。所有這些事物,都是為人類福祉貢獻的先人遺留給我們的。
那麼,其他人呢?那些從未跟人合作,有其他生命意義,只問:「我能由生命裡獲得什麼?」的人呢?他們死後未曾留下痕跡。他們不僅死了;他們的生命亦毫無價值。彷彿我們的地球跟他們說了:「我們不需要你。你不適合生命。你的目的和努力,你自認的價值,你的心靈沒有未來。走開吧!我們不要你。離開這個人世消失吧!」不把合作當作生命意義的人,他們獲得的最後判決總是:「你毫無用處。沒人要你。走吧!」當然在現今的文化裡,我們能夠找到許多的不完美。我們發現有不怎麼令人滿意的地方,我們必須改變;但是這個改變必須以人類福祉做進一步貢獻為宗旨。
一直以來都不乏有人明白這個事實,了解生命的意義是為維護全體人類的福祉,並且試圖發展社會興趣和愛,我們發現所有宗教信仰皆關切人類的解救。世界所有重大的演變皆以增進社會福祉為目標,而宗教即朝此方向進行最大努力。然而,宗教經常被誤解,除了既有的努力外,它們很難再做更多,除非這個人類共同的目標更進一步發揚光大。個體心理學以科學方式達成相同結論,並且建議以科學方法來達成這個目標。我相信這是往前的一步。也許科學增進人類對其他人類夥伴和全體人類福祉的利益,能夠比其他如政治或宗教等所主導的變革達成更多。我們以不同角度看待一個問題的同時,立意依然相同──增進他人的利益。
由於我們所賦予生命的意義,就跟以往一樣,變成生命的守護天使或欲望的惡魔,所以了解這些意義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修正以避免鑄成大錯,顯然對我們極為重要。所以心理學的角色明顯不同於生理學或生物學:讓我們對意義,以及它們對人類行為和人類命運的影響有一個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