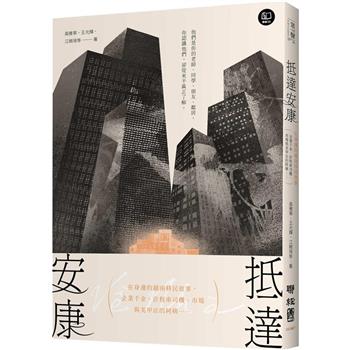從自由到安康:有兩個名字的女人
黃馨慧、蔡佳璇
從昆明出發的流離光陰
劉鳳玲奶奶,小名定芬,是木柵安康平宅中的住戶,但她出生、成長的地方不是臺灣,而是中國雲南昆明。西元一九四七年出生的鳳玲奶奶,即便已經七十好幾,梳在腦後被精心呵護的整齊短髮還是黑的,她左邊的手臂上有一個彈孔留下的疤痕,右手的大拇指少了半截,左手的食指呈現彎曲狀,這些都是戰爭與逃難的歲月刻畫在她身上的印記。
她右腳拇趾與二趾經常不自主地疊在一起,走路只能緩緩的,又因不會搭乘公車,所以在木柵的活動範圍有限,外出主要靠步行。
奶奶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偶爾會到木柵市場和越南商店買菜和調味料。假日,同住的大兒子阿強會騎摩托車帶奶奶到遠一點的超級市場,一買,就是一星期的分量。
偶爾在外頭遇到附近同樣來自越南的鄰居時,鳳玲奶奶會用越南語交談幾句,回到家中則跟大兒子用粵語交流,跟孫子用華語。燒香祭拜爸爸與媽媽時,她說昆明話。
鳳玲奶奶會講的語言,代表了她生命中走過的地、遇到的人。
鳳玲奶奶的媽媽叫做劉喬坤,外祖父名為劉玉堂,原是雲南元江一代的大戶人家。當時雲南地區有許多地方都會種植罌粟,元江位於雲南中南部,靠近東南亞地區,海拔高度從三百至兩千公尺,適合罌粟生長,而罌粟正是提煉鴉片的主要原料。他們家裡做過煙幫,所謂的煙幫是當時一種製作與運送鴉片的生意。
對於近二十一世紀出生的人來說,鴉片只是一個歷史課本上出現過的名詞,鳳玲奶奶實際活過那個年代,能侃侃而談有關鴉片的所有細節。鴉片就像奇異果的種子一樣,小小、黑黑的。她親眼見過外祖父用煙管吸入鴉片後,徐徐地吐出深灰色的煙,那是一股比塑膠燃燒還要難聞的味道,奶奶不僅看過、聞過,甚至連菸草捲成菸的製作過程也一淸二楚。她指著自己鼻子左側一個淺淺的淡褐色疤痕,不仔細看的話,根本注意不到,但那是她外祖父邊抽煙邊抱著她時,長長的煙槍不小心燙傷她所留下的缺口。
過去的痕跡就像鳳玲奶奶鼻子旁那道傷疤,現在看來很淺,卻深深地刻在血肉裡。
奶奶的外祖父當過官員,與寮國永珍地區的政治圈往來密切。在國共內戰期間,奶奶五歲那年,這個官宦背景成了他們一家逃亡的原因。因擔心外祖父擔任官員一事為家中帶來災難,他們決定逃離中國。
奶奶的雙親帶上了幾個丫鬟還有長工一起離開。奶奶總喜歡說在那個年代用十二隻羊就可以買斷一個人,讓他一輩子在有錢人家裡做工。
鳳玲奶奶的外祖母留在昆明,沒有隨著兒子一家人離開,說是因為她裹了小腳,走路不方便,根本無法逃難,只好留下。奶奶的媽媽劉喬坤之正逢民初解放小腳的風潮,便沒再繼續,這才能於舉家逃難時徒步跋山涉水。
鳳玲奶奶和弟弟定忠當時年紀還小,無法自己走遠路。他們被裝在簍子裡,再安放在馬背上。還有一對龍鳳胎大雙、小雙,以及一個襁褓中的小妹妹,由丫鬟背著或抱著。長工負責趕馬,一家人往外祖父曾經待過的寮國永珍而去。
這一走,就是一輩子。
由中國到中南半島
從雲南到寮國永珍的路上,奶奶一家人跟著游擊隊到處逃亡,後來又走過了寮國、緬甸、泰國、越南等區域。孩子們由馬馱著,大人則是徒步行走。
「有一種蟲叫做螞蝗,荒山野嶺才會有,牠喜歡爬在人的腳底板,而且會吸人血,你怎麼拔都拔不下來,要擤鼻涕(塗在蟲身上),滑滑的才拔得下來。」回憶起過往的一些場景,奶奶總是會搓搓自己的手臂,說一想到就不由自主地起雞皮疙瘩。
在逃難期間,龍鳳胎大雙、小雙以及小妹妹相繼早夭離世。那個因戰亂而逃難的年代離我們如此遙遠,很難想像奶奶的一生經歷了多少危險,才能擁有一個相對安穩的生活。
鳳玲奶奶的小名「定芬」是媽媽取的,為的就是防止一雙兒女在逃難的過程中走失。
弟弟在劉家中的字輩是「定」,叫做劉定忠,媽媽因此幫她取了「定芬」的小名,告訴她:「如果姊弟失散了,就要照這個字牌去尋找,姊姊就叫『定芬』,弟弟叫『定忠』。」這個小名成了奶奶重要的標誌,象徵著她逃難的歲月,同時也是另外一種看不見的「身分證」。
在寮國的日子,定芬奶奶一家在少數民族的村寨裡躱避追捕。
外祖父家在寮國當地的工人(昆明話叫老撾子)幫忙接應他們、蓋了暫時居所,煮了一大鍋玉米粥給辛苦逃難的他們吃頓飽飯。
定芬奶奶的母親從雲南逃出來時,身上帶了一些菸草,這些菸草在逃難期間有如同貨幣一樣的交易功能,他們便拿菸草及布料跟當地人換米來吃。
「逃難的時候比較精彩,四五歲嘛,沒水喝,就一直哭,毛澤東他們那些軍人(要是)聽到會來槍斃、掃殺(我們)。大象走過去後有個窩(地上有泥坑),我媽就這樣捧起那個水來給我們喝,現在想想覺得很噁心,但那時候也沒辦法。」這是定芬奶奶這是一家人從中國逃往中南半島過程中最鮮明的一幕之一,這讓她養成了四季都能喝冷水的習慣,也造就了她一天可以只吃一餐的能耐。
一邊回憶過往邊訴說那段艱難逃難的歲月,奶奶摸著左手呈現彎曲狀的食指說:「這個也是當時逃難時候受傷的。」她媽媽是大戶人家出身的小姐,不會下廚,身為家中長女的定芬就扛起了做家事的責任,和媽媽帶著的丫鬟們學做事,會下廚煮飯也會砍柴,卻意外砍斷自己的食指。那時候沒有醫生,受傷了只能自己處理,定芬奶奶的媽媽見狀,急忙地將奶奶斷掉的手指接回去,在斷口處撒下雲南白藥,再用布包裹起來。結果斷掉的手指雖然接回去了,卻有著不自然的彎曲樣態,在定芬奶奶的身體上留下了一輩子的印記。
一九五二年開始逃難,定芬一家人一路從中國出發跟隨游擊隊的步伐,也為了躱避共產黨的追捕,走了不知多遠的路。後來在寮國永珍的山上,他們遇到法國軍隊,法軍以為這些難民是中國軍人,便開槍掃射,奶奶的父親劉喬淸就這麼不幸中槍去世了。噩耗來得突然,人命如鴻毛。當時沒有什麼工具能挖洞又沒錢,定芬的媽媽只好和丫鬟們徒手挖了一個洞,把丈夫推進去、埋起來,再打起精神帶著一家人繼續逃難。
他們從中國到寮國,又從寮國逃到緬甸和泰國,再從緬甸和泰國搭船一路往北越前進,最後在北越河內乘著飛機飛往南越,成為當時南撤華僑中的一分子。
在自由新村的年少歲月
二戰後,國民黨政府曾在西貢(現胡志明市)的堤岸(Chợ Lớn)資助興建數個村落,來收容反共的南撤華僑,定芬奶奶一家人落腳的自由新村就是其一。他們暫時脫離流離顚沛的日子,在南越共和國政府的領地下找到一塊臨時的庇蔭所。
自由新村的入口處有個大立牌,上頭題了「自由新村」四個大字,一旁還寫著「本村房屋係越南共和國政府捐資興建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奶奶回憶道,當時自由新村是由在泥土地上,用木板、鐵皮臨時搭建的簡單建築物組成,房子是透天的;一戶人家不管有多少人,都只能擠在三平方米大小的空間裡。他們睡在一張木板上,木板下就是泥土地。好處是他們不用付房租,等有錢了還能自行擴建,擴大居住空間。
除了睡覺的空間,自由新村的廚房、澡堂和廁所都是採公共式的,所有人必須一起使用。
定芬奶奶的母親在領事館認識了之前做游擊隊的張國良,兩人在西貢的領事館內結婚,「當時也沒領結婚證書,在領事館認識、看對了眼就在一起,不然一個女人怎麼自己帶小孩生活。」
張國良就這麼成了定芬奶奶的繼父,他後來在領事館做廚師,住在當時的華航宿舍裡,而媽媽帶著小孩住進了自由新村的避難屋。到達西貢時,定芬奶奶已經七、八歲左右,可以上小學了。她上的是自由小學(現團結小學)。當時的自由學校免費提供華人就學,提供中文教育。上課時間是從週一到週五,禮拜六早上還要上半天課。「當時要學毛筆,還要學歷史、公民、數學、中文,每天書包都好重。」定芬奶奶在那裡認識了六位要好的朋友,七個人在畢業那年成了結拜「金蘭姊妹」。十四歲從小學畢業後,定芬就開始工作,負擔起家裡的生計。
她先去了當時位於第十一郡的于飛塑膠廠。在那個年代,當地有許多塑膠產業是由當地華人投入生產,于飛就是其中之一。裡頭的工人也大多以南撤的北越華人為主,可惜奶奶後來在工作時不愼被拉塑膠布的機器捲入,導致左手大拇指的指頭少了半截,無法在塑膠廠繼續工作,當時竟也沒有獲得任何補償。
接下來,奶奶到一家上海老闆開的旗袍店當學徒,要學挑衣服、褲子,用手針挑。
旗袍店老闆為人凶悍,如果挑錯一點,一巴掌就對著人毫不留情的賞過來了。
奶奶笑說:「所以你們現在很幸福啦。」
黃馨慧、蔡佳璇
從昆明出發的流離光陰
劉鳳玲奶奶,小名定芬,是木柵安康平宅中的住戶,但她出生、成長的地方不是臺灣,而是中國雲南昆明。西元一九四七年出生的鳳玲奶奶,即便已經七十好幾,梳在腦後被精心呵護的整齊短髮還是黑的,她左邊的手臂上有一個彈孔留下的疤痕,右手的大拇指少了半截,左手的食指呈現彎曲狀,這些都是戰爭與逃難的歲月刻畫在她身上的印記。
她右腳拇趾與二趾經常不自主地疊在一起,走路只能緩緩的,又因不會搭乘公車,所以在木柵的活動範圍有限,外出主要靠步行。
奶奶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偶爾會到木柵市場和越南商店買菜和調味料。假日,同住的大兒子阿強會騎摩托車帶奶奶到遠一點的超級市場,一買,就是一星期的分量。
偶爾在外頭遇到附近同樣來自越南的鄰居時,鳳玲奶奶會用越南語交談幾句,回到家中則跟大兒子用粵語交流,跟孫子用華語。燒香祭拜爸爸與媽媽時,她說昆明話。
鳳玲奶奶會講的語言,代表了她生命中走過的地、遇到的人。
鳳玲奶奶的媽媽叫做劉喬坤,外祖父名為劉玉堂,原是雲南元江一代的大戶人家。當時雲南地區有許多地方都會種植罌粟,元江位於雲南中南部,靠近東南亞地區,海拔高度從三百至兩千公尺,適合罌粟生長,而罌粟正是提煉鴉片的主要原料。他們家裡做過煙幫,所謂的煙幫是當時一種製作與運送鴉片的生意。
對於近二十一世紀出生的人來說,鴉片只是一個歷史課本上出現過的名詞,鳳玲奶奶實際活過那個年代,能侃侃而談有關鴉片的所有細節。鴉片就像奇異果的種子一樣,小小、黑黑的。她親眼見過外祖父用煙管吸入鴉片後,徐徐地吐出深灰色的煙,那是一股比塑膠燃燒還要難聞的味道,奶奶不僅看過、聞過,甚至連菸草捲成菸的製作過程也一淸二楚。她指著自己鼻子左側一個淺淺的淡褐色疤痕,不仔細看的話,根本注意不到,但那是她外祖父邊抽煙邊抱著她時,長長的煙槍不小心燙傷她所留下的缺口。
過去的痕跡就像鳳玲奶奶鼻子旁那道傷疤,現在看來很淺,卻深深地刻在血肉裡。
奶奶的外祖父當過官員,與寮國永珍地區的政治圈往來密切。在國共內戰期間,奶奶五歲那年,這個官宦背景成了他們一家逃亡的原因。因擔心外祖父擔任官員一事為家中帶來災難,他們決定逃離中國。
奶奶的雙親帶上了幾個丫鬟還有長工一起離開。奶奶總喜歡說在那個年代用十二隻羊就可以買斷一個人,讓他一輩子在有錢人家裡做工。
鳳玲奶奶的外祖母留在昆明,沒有隨著兒子一家人離開,說是因為她裹了小腳,走路不方便,根本無法逃難,只好留下。奶奶的媽媽劉喬坤之正逢民初解放小腳的風潮,便沒再繼續,這才能於舉家逃難時徒步跋山涉水。
鳳玲奶奶和弟弟定忠當時年紀還小,無法自己走遠路。他們被裝在簍子裡,再安放在馬背上。還有一對龍鳳胎大雙、小雙,以及一個襁褓中的小妹妹,由丫鬟背著或抱著。長工負責趕馬,一家人往外祖父曾經待過的寮國永珍而去。
這一走,就是一輩子。
由中國到中南半島
從雲南到寮國永珍的路上,奶奶一家人跟著游擊隊到處逃亡,後來又走過了寮國、緬甸、泰國、越南等區域。孩子們由馬馱著,大人則是徒步行走。
「有一種蟲叫做螞蝗,荒山野嶺才會有,牠喜歡爬在人的腳底板,而且會吸人血,你怎麼拔都拔不下來,要擤鼻涕(塗在蟲身上),滑滑的才拔得下來。」回憶起過往的一些場景,奶奶總是會搓搓自己的手臂,說一想到就不由自主地起雞皮疙瘩。
在逃難期間,龍鳳胎大雙、小雙以及小妹妹相繼早夭離世。那個因戰亂而逃難的年代離我們如此遙遠,很難想像奶奶的一生經歷了多少危險,才能擁有一個相對安穩的生活。
鳳玲奶奶的小名「定芬」是媽媽取的,為的就是防止一雙兒女在逃難的過程中走失。
弟弟在劉家中的字輩是「定」,叫做劉定忠,媽媽因此幫她取了「定芬」的小名,告訴她:「如果姊弟失散了,就要照這個字牌去尋找,姊姊就叫『定芬』,弟弟叫『定忠』。」這個小名成了奶奶重要的標誌,象徵著她逃難的歲月,同時也是另外一種看不見的「身分證」。
在寮國的日子,定芬奶奶一家在少數民族的村寨裡躱避追捕。
外祖父家在寮國當地的工人(昆明話叫老撾子)幫忙接應他們、蓋了暫時居所,煮了一大鍋玉米粥給辛苦逃難的他們吃頓飽飯。
定芬奶奶的母親從雲南逃出來時,身上帶了一些菸草,這些菸草在逃難期間有如同貨幣一樣的交易功能,他們便拿菸草及布料跟當地人換米來吃。
「逃難的時候比較精彩,四五歲嘛,沒水喝,就一直哭,毛澤東他們那些軍人(要是)聽到會來槍斃、掃殺(我們)。大象走過去後有個窩(地上有泥坑),我媽就這樣捧起那個水來給我們喝,現在想想覺得很噁心,但那時候也沒辦法。」這是定芬奶奶這是一家人從中國逃往中南半島過程中最鮮明的一幕之一,這讓她養成了四季都能喝冷水的習慣,也造就了她一天可以只吃一餐的能耐。
一邊回憶過往邊訴說那段艱難逃難的歲月,奶奶摸著左手呈現彎曲狀的食指說:「這個也是當時逃難時候受傷的。」她媽媽是大戶人家出身的小姐,不會下廚,身為家中長女的定芬就扛起了做家事的責任,和媽媽帶著的丫鬟們學做事,會下廚煮飯也會砍柴,卻意外砍斷自己的食指。那時候沒有醫生,受傷了只能自己處理,定芬奶奶的媽媽見狀,急忙地將奶奶斷掉的手指接回去,在斷口處撒下雲南白藥,再用布包裹起來。結果斷掉的手指雖然接回去了,卻有著不自然的彎曲樣態,在定芬奶奶的身體上留下了一輩子的印記。
一九五二年開始逃難,定芬一家人一路從中國出發跟隨游擊隊的步伐,也為了躱避共產黨的追捕,走了不知多遠的路。後來在寮國永珍的山上,他們遇到法國軍隊,法軍以為這些難民是中國軍人,便開槍掃射,奶奶的父親劉喬淸就這麼不幸中槍去世了。噩耗來得突然,人命如鴻毛。當時沒有什麼工具能挖洞又沒錢,定芬的媽媽只好和丫鬟們徒手挖了一個洞,把丈夫推進去、埋起來,再打起精神帶著一家人繼續逃難。
他們從中國到寮國,又從寮國逃到緬甸和泰國,再從緬甸和泰國搭船一路往北越前進,最後在北越河內乘著飛機飛往南越,成為當時南撤華僑中的一分子。
在自由新村的年少歲月
二戰後,國民黨政府曾在西貢(現胡志明市)的堤岸(Chợ Lớn)資助興建數個村落,來收容反共的南撤華僑,定芬奶奶一家人落腳的自由新村就是其一。他們暫時脫離流離顚沛的日子,在南越共和國政府的領地下找到一塊臨時的庇蔭所。
自由新村的入口處有個大立牌,上頭題了「自由新村」四個大字,一旁還寫著「本村房屋係越南共和國政府捐資興建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奶奶回憶道,當時自由新村是由在泥土地上,用木板、鐵皮臨時搭建的簡單建築物組成,房子是透天的;一戶人家不管有多少人,都只能擠在三平方米大小的空間裡。他們睡在一張木板上,木板下就是泥土地。好處是他們不用付房租,等有錢了還能自行擴建,擴大居住空間。
除了睡覺的空間,自由新村的廚房、澡堂和廁所都是採公共式的,所有人必須一起使用。
定芬奶奶的母親在領事館認識了之前做游擊隊的張國良,兩人在西貢的領事館內結婚,「當時也沒領結婚證書,在領事館認識、看對了眼就在一起,不然一個女人怎麼自己帶小孩生活。」
張國良就這麼成了定芬奶奶的繼父,他後來在領事館做廚師,住在當時的華航宿舍裡,而媽媽帶著小孩住進了自由新村的避難屋。到達西貢時,定芬奶奶已經七、八歲左右,可以上小學了。她上的是自由小學(現團結小學)。當時的自由學校免費提供華人就學,提供中文教育。上課時間是從週一到週五,禮拜六早上還要上半天課。「當時要學毛筆,還要學歷史、公民、數學、中文,每天書包都好重。」定芬奶奶在那裡認識了六位要好的朋友,七個人在畢業那年成了結拜「金蘭姊妹」。十四歲從小學畢業後,定芬就開始工作,負擔起家裡的生計。
她先去了當時位於第十一郡的于飛塑膠廠。在那個年代,當地有許多塑膠產業是由當地華人投入生產,于飛就是其中之一。裡頭的工人也大多以南撤的北越華人為主,可惜奶奶後來在工作時不愼被拉塑膠布的機器捲入,導致左手大拇指的指頭少了半截,無法在塑膠廠繼續工作,當時竟也沒有獲得任何補償。
接下來,奶奶到一家上海老闆開的旗袍店當學徒,要學挑衣服、褲子,用手針挑。
旗袍店老闆為人凶悍,如果挑錯一點,一巴掌就對著人毫不留情的賞過來了。
奶奶笑說:「所以你們現在很幸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