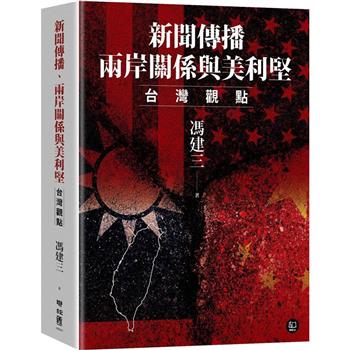公共服務媒介的錢、人與問責:多重模式,兼論中國傳媒改革
前言
「中國模式」不會只有一種論述,不會只有一種實踐。同理,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的模式也有許多種,各自烙印其歷史條件的胎記,面對當代資本壓力,各國PSM的奮進成果,亦見差別。
有些在商業影音環境中,被迫增加私人的贊助,如美國。與此相反,另有逆流而上,將原本是PSM部分財源的廣告,從其收入剔除,為此而短缺之數,另從財政撥款與商業稅捐挹注,如法國與西班牙。有些蓄勢待發,先由民間社團醞釀鼓動,要求其政府創新組織與開徵多樣財源,鞏固、支持與擴大PSM的能見度與影響力,平衡商業勢力,方向之一是結合高教等等非營利資源與機構,如美國。另外,同樣或說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經有公廣機構,如英國的BBC,力能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卻又因為其市場競爭力強大,因「成功」而遭忌,政治力在意識形態作祟,以及資本遊說的壓力與召喚下,出面阻撓PSM擴充。
「不是BBC就不可能是公共電視嗎?」答案是明顯的。何況,BBC本身也歷經變化,並不靜止,BBC以外,PSM模式林立、五花八門,本文的任務就在釐清與闡述,先說同,後述異,目的在於從中演繹理論的憑藉、實踐的取徑,作為改革中國傳媒的參考。
中國各層級的廣播與電視機構,與世界各國的PSM,至少有兩個共同點。
首先,財產權都不是私人所有,1980、9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浪潮,沒有席捲公廣領域,法國第一台之外,各國公廣機構不但維持公有地位,其頻道數量亦在擴張,包括香港特首在2009年9月宣布,香港電台未來數年內即將升級,收音機之外,另要自擁數個電視頻道,不再如同現制,只是責成私人商業台播放其節目。其次,不斷改革,隨技術條件的變化,公廣機構產制與採購的內容,不僅只是利用地表特高頻無線電波傳輸,而是業已利用衛星與超高頻電波,並進入了有線、電信系統與互聯網,這就使得傳統的PSM不得不與時俱進,成為公共服務「傳媒」(public service media, PSM),融合影音圖文於一爐,雖然各國PSM進入這個新階段的速度與表現,必有差異。
有共相,就有殊相。除了產權公有不變與服務範圍的不斷革新,各國PSM的內涵頗見差異。PSM在各國誕生的條件與性質,是很重要,惟後天演變,更稱關鍵。下文擇要簡述PSM出現的歷史背景後,隨即進入主體,分梳PSM的三個面向。一是財政收入的來源。二是人員構成,包括兩類人,一是經營團隊,再就是基層員工。PSM員工的多寡與組織形式,經常又是PSM財政大小的直接反映。三是PSM通過哪些機制(市場表現、受眾參與及資訊公開),以示對其真正主人,也就是本國公民與社會負責;反過來說,社會如何向PSM「問責」,如何要求PSM對公民負責。最後,依據對各國PSM的共相與殊相的析辨,本文主張,在公有產權的基礎下,承襲但又創新的財政與內容流通模式,可以是改革中國傳媒的優先選項。
誕生背景
反對公共廣電的眾多論述當中,相當常見的理由之一,就在反覆強調,該制度成為當年的世界主流,是因頻道稀有,如今技術發達,頻道過多而不再稀少,既然如此,公共體制就當退位。事實上,這個說法並沒有正視史實,若能正本清源,予以還原,就會發現,無論是歐洲或美國,電波資源稀有都不是最重要,更稱不上是政府高度管制這個新興傳媒的唯一理由。更不用說,不但早年已有經濟分析,指陳廣電的公共性與外部性,都是PSM問世的重要原因,迄今,更有精湛的專業解剖,指出在多頻道的年代,公共服務廣電制度不但並非明日黃花,反倒更見需要。
英國廣電協會(BBC)最早是私有,1922年由電器商聯合組成,1927年元旦改為公營,主要原因有三。先是民族與統治階級的「文化」考慮,擔心商業低俗,品味擾人。其次是市場經濟競爭的殘酷性,導致第一次歐戰,「社會」力量遂有反省,進而反制。最後是「經濟」因素,消費電子器材廠商無力供應制播節目的資源,公權力直接向納稅人抽取收視費,對硬體廠商無害,反倒有利於快速籌措生產廣播內容的經費。
美國的體制雖然不同,但仍保留二成電波作為非商業用途,商用波段不是如同土地按價出售,而是依據「公共信託」模式分配,申請人必須滿足「公共利益、便利或需要」的條件。同樣,電波稀有與否並非重點,1920年代國會就此辯論時,議員清楚指認,電波是公共財,電波承載的內容足以產生龐大的政治、文化……作用,10亦即廣播具有明顯的「社會效益」,不容任何人完全占有其利。
只是,信託與公益,只能在小範圍約束私有的商業電子傳媒。美國公共電視的誕生,還要等到1960年代。當時,民權運動風起雲湧,權利意識延伸進入傳媒,除了抨擊利潤歸私的傳媒,美國人成群結社,紛紛要求政府創設公視。1967年末,總統詹森(Linden Johnson)很快收割社運的果實,跳上推動公視的列車,要求國會快速通過法案。就在美國民眾尚且沉醉於公視降臨時,詹森迅速提名陸軍名人、曾任「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公司總裁的培士(Frank Pace)作為公視首任執行長。培士表示,他將研究如何利用公共電視,作為控制暴動之用:現在,一度熱情擁抱公共電視的支持者,不免納悶「這下子公視豈不要被詹森擁抱至死?」
創建公共電子傳媒的動力,出於政治,不是電波多寡的技術原因,同樣顯現在亞洲,只是更戲劇化。1979年南韓總統遇刺身亡、次年光州事件,隨即有大眾傳媒重新組合的政策,一舉將所有私人廣電國有化,殘酷的歷史際遇竟然意外地成為日後韓流的先河。2006年,反對泰國首相塔信(Thaksin Shinawatra)政府的示威活動長期盤據曼谷大街,軍方介入後,塔信外逃,軍方成立臨時政府,沒收塔信擁有的電視公司。幾經折衝,軍政府順應社會業已倡議一段時間的要求,亦即將該商營頻道轉變為公共電視。雖然不乏國會議員質疑,傳播學者、社會行動人士及媒改社團的意見亦告分歧,有人認為軍政府不可信賴而反對,但也有人主張順水推舟並無不可。正反勿論,2008年元月,亞洲最新的公共電視台誕生於激烈的社會與政治衝突聲中。
財政來源:政府撥款、執照費與廣告
如同誕生背景有別,各國公視的收入來源及其規模,亦見差異。節目產制經費從何處取得,對於傳媒內容的品質良窳、多樣程度與保守改良或激進的性格,固然不是一對一的決定或影響方式,卻不可能不生短期的牽制,也不會不對公視之長期性格與內部文化,發生長遠的約制及塑造之能。如果徹底依賴商業收入,並且必須自行承攬廣告、進入市場競爭的傳媒,即便產權國有或公有,其表現究竟與私有商業傳媒會有多少差異,恐有疑問。反之,縱使必須從事市場競爭、爭取合適的收視份額,但只要其產權公有,且收入不取廣告而是另由政府安排,全額撥款或取執照費,則其表現與「私有且營利導向」的傳媒,必有差異,甚至可以大相逕庭。
前言
「中國模式」不會只有一種論述,不會只有一種實踐。同理,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的模式也有許多種,各自烙印其歷史條件的胎記,面對當代資本壓力,各國PSM的奮進成果,亦見差別。
有些在商業影音環境中,被迫增加私人的贊助,如美國。與此相反,另有逆流而上,將原本是PSM部分財源的廣告,從其收入剔除,為此而短缺之數,另從財政撥款與商業稅捐挹注,如法國與西班牙。有些蓄勢待發,先由民間社團醞釀鼓動,要求其政府創新組織與開徵多樣財源,鞏固、支持與擴大PSM的能見度與影響力,平衡商業勢力,方向之一是結合高教等等非營利資源與機構,如美國。另外,同樣或說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經有公廣機構,如英國的BBC,力能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卻又因為其市場競爭力強大,因「成功」而遭忌,政治力在意識形態作祟,以及資本遊說的壓力與召喚下,出面阻撓PSM擴充。
「不是BBC就不可能是公共電視嗎?」答案是明顯的。何況,BBC本身也歷經變化,並不靜止,BBC以外,PSM模式林立、五花八門,本文的任務就在釐清與闡述,先說同,後述異,目的在於從中演繹理論的憑藉、實踐的取徑,作為改革中國傳媒的參考。
中國各層級的廣播與電視機構,與世界各國的PSM,至少有兩個共同點。
首先,財產權都不是私人所有,1980、9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浪潮,沒有席捲公廣領域,法國第一台之外,各國公廣機構不但維持公有地位,其頻道數量亦在擴張,包括香港特首在2009年9月宣布,香港電台未來數年內即將升級,收音機之外,另要自擁數個電視頻道,不再如同現制,只是責成私人商業台播放其節目。其次,不斷改革,隨技術條件的變化,公廣機構產制與採購的內容,不僅只是利用地表特高頻無線電波傳輸,而是業已利用衛星與超高頻電波,並進入了有線、電信系統與互聯網,這就使得傳統的PSM不得不與時俱進,成為公共服務「傳媒」(public service media, PSM),融合影音圖文於一爐,雖然各國PSM進入這個新階段的速度與表現,必有差異。
有共相,就有殊相。除了產權公有不變與服務範圍的不斷革新,各國PSM的內涵頗見差異。PSM在各國誕生的條件與性質,是很重要,惟後天演變,更稱關鍵。下文擇要簡述PSM出現的歷史背景後,隨即進入主體,分梳PSM的三個面向。一是財政收入的來源。二是人員構成,包括兩類人,一是經營團隊,再就是基層員工。PSM員工的多寡與組織形式,經常又是PSM財政大小的直接反映。三是PSM通過哪些機制(市場表現、受眾參與及資訊公開),以示對其真正主人,也就是本國公民與社會負責;反過來說,社會如何向PSM「問責」,如何要求PSM對公民負責。最後,依據對各國PSM的共相與殊相的析辨,本文主張,在公有產權的基礎下,承襲但又創新的財政與內容流通模式,可以是改革中國傳媒的優先選項。
誕生背景
反對公共廣電的眾多論述當中,相當常見的理由之一,就在反覆強調,該制度成為當年的世界主流,是因頻道稀有,如今技術發達,頻道過多而不再稀少,既然如此,公共體制就當退位。事實上,這個說法並沒有正視史實,若能正本清源,予以還原,就會發現,無論是歐洲或美國,電波資源稀有都不是最重要,更稱不上是政府高度管制這個新興傳媒的唯一理由。更不用說,不但早年已有經濟分析,指陳廣電的公共性與外部性,都是PSM問世的重要原因,迄今,更有精湛的專業解剖,指出在多頻道的年代,公共服務廣電制度不但並非明日黃花,反倒更見需要。
英國廣電協會(BBC)最早是私有,1922年由電器商聯合組成,1927年元旦改為公營,主要原因有三。先是民族與統治階級的「文化」考慮,擔心商業低俗,品味擾人。其次是市場經濟競爭的殘酷性,導致第一次歐戰,「社會」力量遂有反省,進而反制。最後是「經濟」因素,消費電子器材廠商無力供應制播節目的資源,公權力直接向納稅人抽取收視費,對硬體廠商無害,反倒有利於快速籌措生產廣播內容的經費。
美國的體制雖然不同,但仍保留二成電波作為非商業用途,商用波段不是如同土地按價出售,而是依據「公共信託」模式分配,申請人必須滿足「公共利益、便利或需要」的條件。同樣,電波稀有與否並非重點,1920年代國會就此辯論時,議員清楚指認,電波是公共財,電波承載的內容足以產生龐大的政治、文化……作用,10亦即廣播具有明顯的「社會效益」,不容任何人完全占有其利。
只是,信託與公益,只能在小範圍約束私有的商業電子傳媒。美國公共電視的誕生,還要等到1960年代。當時,民權運動風起雲湧,權利意識延伸進入傳媒,除了抨擊利潤歸私的傳媒,美國人成群結社,紛紛要求政府創設公視。1967年末,總統詹森(Linden Johnson)很快收割社運的果實,跳上推動公視的列車,要求國會快速通過法案。就在美國民眾尚且沉醉於公視降臨時,詹森迅速提名陸軍名人、曾任「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公司總裁的培士(Frank Pace)作為公視首任執行長。培士表示,他將研究如何利用公共電視,作為控制暴動之用:現在,一度熱情擁抱公共電視的支持者,不免納悶「這下子公視豈不要被詹森擁抱至死?」
創建公共電子傳媒的動力,出於政治,不是電波多寡的技術原因,同樣顯現在亞洲,只是更戲劇化。1979年南韓總統遇刺身亡、次年光州事件,隨即有大眾傳媒重新組合的政策,一舉將所有私人廣電國有化,殘酷的歷史際遇竟然意外地成為日後韓流的先河。2006年,反對泰國首相塔信(Thaksin Shinawatra)政府的示威活動長期盤據曼谷大街,軍方介入後,塔信外逃,軍方成立臨時政府,沒收塔信擁有的電視公司。幾經折衝,軍政府順應社會業已倡議一段時間的要求,亦即將該商營頻道轉變為公共電視。雖然不乏國會議員質疑,傳播學者、社會行動人士及媒改社團的意見亦告分歧,有人認為軍政府不可信賴而反對,但也有人主張順水推舟並無不可。正反勿論,2008年元月,亞洲最新的公共電視台誕生於激烈的社會與政治衝突聲中。
財政來源:政府撥款、執照費與廣告
如同誕生背景有別,各國公視的收入來源及其規模,亦見差異。節目產制經費從何處取得,對於傳媒內容的品質良窳、多樣程度與保守改良或激進的性格,固然不是一對一的決定或影響方式,卻不可能不生短期的牽制,也不會不對公視之長期性格與內部文化,發生長遠的約制及塑造之能。如果徹底依賴商業收入,並且必須自行承攬廣告、進入市場競爭的傳媒,即便產權國有或公有,其表現究竟與私有商業傳媒會有多少差異,恐有疑問。反之,縱使必須從事市場競爭、爭取合適的收視份額,但只要其產權公有,且收入不取廣告而是另由政府安排,全額撥款或取執照費,則其表現與「私有且營利導向」的傳媒,必有差異,甚至可以大相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