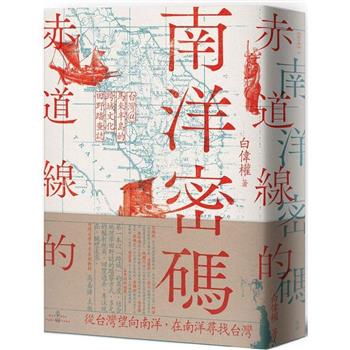華夷交融的拿督公信仰
走在馬來西亞的街道或是華人住宅區,經常能夠在街頭巷尾、住宅前、大樹下,抑或是大樓後方的角落見到類似台灣鄉間的小土地公廟。這些小土地公廟設計簡單,與其說它是小廟,倒不如說它是簡單的小神龕。它的屋頂沒有過於華麗的龍雕,較多的是像馬來西亞普通平房的那種倒「V」字型的屋頂。沒錯,它確實是為了供奉土地神而設的神龕。然而走近一看,裡面所供奉的神祇雖然看起來與我們一般所見的土地公相似,但在穿著打扮,甚至長相上,卻與我們熟知的土地公有些許出入。這尊神明便是馬來版的土地神—「拿督公」。
典型拿督公的長相與土地公幾乎相同,同樣是留著白色長鬍子的長者形象,只是膚色略黑。穿著上,祂的帽子與土地公相似,但設計較為簡單,嚴格說來應該是馬來人或伊斯蘭教徒所戴的「宋谷」(songkok)。拿督公所穿的服裝也並非中式服裝,而是馬來人的上衣(baju)和圍幔—「沙郎」(sarong)。有別於土地公手上所拿的如意,祂所持的會是馬來短劍(kriss)。而拿督公手上的中國式金元寶以及拐杖,則與土地公所持的大致相同。是的,拿督公就是這樣一尊參雜著中國與南洋在地色彩的神祇。
什麼是拿督?
字面上,拿督公源於馬來語的Datuk或Dato,・為爺爺之意,馬來人會用以稱呼祖父以及尊稱男性長者。此外,拿督也是馬來貴族及領導階層中的一種尊稱,這些拿督的位階有高有低,高者可以是在整個馬來王國當中統領一整片封地的諸侯,・低者可以是協助諸侯管理地方的基層領袖。因此若翻開馬來歷史文獻,總是會見到許多的拿督。在十九世紀馬來半島華人大開發時期,前來維生的華人,便需要和這些拿督打交道,以承租農地、礦地及繳納稅收。
在現今,拿督也成為一種勳銜,擁有拿督頭銜的人,多半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在每年馬來西亞各州蘇丹華誕時,也會冊封勳銜予州內的有功人士,而拿督便是其中一個冊封的項目。當然,在拿督之上,還有拿督斯里(Datuk / Dato Sri)、丹斯里(Tan Sri)、敦(Tun)等等。拿督之下,也還有許多不同的名目。
在馬來西亞,拿督已是普遍可見的勳銜,這個傳統馬來封號已不僅限於馬來人,也有相當多的華人被封為拿督。有些州甚至可以透過捐錢予皇室而獲得拿督的封號,報章上也經常可見恭賀某某人獲得拿督勳銜的廣告。雖然現今的拿督可能已經有些氾濫,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拿督已經深入民心,即使後來拿督的「含金量」已逐漸降低,但拿督在本地人心目中的長者或社會領袖形象,卻是未曾改變的。
本地華人用自己的語言把Datuk進行音譯詮釋,再將之文字化,並且後方加多一個華文固有詞—「公」以方便理解。在語言上,廣東話和福建話是馬來西亞最主要的兩大華人語系,在廣東語言方面,雖然廣府話和客家話有所不同,但他們在念馬來語datuk時,會將之詮釋為漢字的「拿督」(粵語:naa4-duk1;客語:nˋ)。而福建語系當中的閩南語和潮州話,則較常會將之詮釋為漢字的「藍卓」、「籃卓」(閩南語:n;潮語:n-toh)、「那卓」(閩南語:n;潮語:n)、「藍督」(閩南語:n;潮語:n)或「拿卓」(閩南語:n;潮語:n)等等。或許是因為大眾傳播或是製造廠商的關係,廣東話為詮釋的漢字—「拿督」在馬來西亞較為常見,反觀「藍卓」較少,但若是我們見到「藍卓」的寫法,這就表示我們所在的地區多半是以福建人為主流了。・像是在檳城、吉打、玻璃市以及霹靂北部的太平這些以福建人為主的地區,籃卓、那卓都是常見的拿督公寫法。
形形色色的拿督公
在形象上,拿督公的形式多樣,除了上述一開始所提及的馬來版土地公形象之外,我們也可以見到以馬來酋長與王公貴族形象的拿督公,他們戴著馬來傳統的布帽,如同馬幣上蘇丹所戴的帽子。有的兩邊甚至有持槍的護衛;有的則身穿皇室特有黃衣;有的則是馬來人的形象,但是卻如同佛教修行者一樣盤腿而坐;也有的拿督公穿著西裝大衣和西褲;有的旁邊則配有拿督婆,與中國傳統的土地公、土地婆概念一樣。
人們對於拿督公的配偶,有很多不同的稱呼,像是拿督奶奶或拿督娘娘。拿督婆在造型上通常戴著頭巾(tudung),以伊斯蘭教婦女的形象出現。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南洋的拿督婆並非像中國的土地婆一樣有著傳統女性「不出廳堂」的特徵。本地的拿督婆有的地位頗高,有些公廟也會大肆慶祝拿督婆千秋寶誕(如柔佛州峇株巴轄海口的青龍宮),有的宮廟主神甚至就是拿督娘娘(雪蘭莪巴生吉膽島的拿督娘娘宮)。這樣的現象或許也對應了南洋土著女性地位相對較高的傳統。
馬來西亞各地的拿督公也以很多種不同的形式被人們所塑造,除了塑像的之外,較常見的形式還有牌位式的。牌位一般多是以漆上紅色的木板配上金色的雕刻字體,寫上「拿督公」或「拿督公神位」等。有的也會在拿督公神位的中榜文字的兩旁刻上對聯,較常見到的是「拿管地方興旺;督理財源廣進」,充分展現了拿督公的神格職能。此外,有的牌位也會刻上拿督公的人像圖形,取代文字的使用。另一種形式是以畫像或照片的形式,將拿督公畫像放進相框中,置於神龕內膜拜。但這種形式較少見,筆者在一次造訪霹靂州南部沿海市鎮—安順時,在當地普遍見到。
另一種較常見的形式是石塊或土堆型的拿督公,人們會將一些長相特殊的石頭,或是因為白蟻窩而形成的大土堆視為可能會有神靈的存在,特別是當這些自然物在人們的夢中或是生活中被認為有靈驗的事件,人們便會開始在石塊或土堆旁插香膜拜,有的也會用紅布、金花或是其他裝飾品裝點它們,若是這位拿督公持續靈驗的話,人們甚至會在現地蓋廟供奉。
總體而言,無論是塑像、牌位、畫像抑或是石頭、土堆型的拿督公,這些形式都與華人在原鄉供奉土地公的方式如出一轍,唯一不同的是,中國和南洋文化交融後所產生的拿督公,人們對他的想像可能更加豐富,或許是人在南洋地域的緣故,本地拿督公的受重視度也高於本地的土地公。
土地公與「代天巡狩」
拿督公的出現,顯然是中國傳統信仰文化和南洋馬來文化碰撞・之後的結果。傳統上,華人便有土地崇拜的習慣,並將土地神具象化成為老者的形象。土地神掌管了農業社會的收成與自然環境的安定,是土地的管理者。華人來到馬來亞之後,無論是從事熱帶栽培業(香料、甘蜜、橡膠等的種植)還是採礦業,都與土地脫離不了關係,土地崇拜自然也隨之扎根南洋。然而在這片中華帝國之外的南洋異域,土地管理者自然不是傳統中國的身穿唐裝的土地公,估計孫悟空用金箍棒在此敲打地上所呼叫出來的也不會是祂們,而是馬來籍的土地管理者Datuk。Datuk無論是在字面意義上或是在馬來王國的角色(地方頭人)上,都與土地公一致。或許是如此,便催生了本地的拿督公信仰。
例如早年的華人礦場幾乎都會安奉拿督公,礦工們每天早晚均須膜拜拿督公,以保護工作安全,避免意外事件發生,同時期望藉由神力召喚大量錫苗。・在現今馬來西亞的新村,特別是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彭亨一帶的新村,村中幾乎每條路的路口都設有拿督公的小神龕,像是筆者到訪的雪蘭莪新古毛新村便是如此,該新村面積大約零點二八平方公里,裡面擁有十四座拿督公神龕。
在雪蘭莪沿海的吉膽島和五條港漁村,幾乎家家戶戶門外都能找到拿督公神龕。此外,對於討海的漁民而言,不同海域也有它所屬的拿督公,人們也會在海中插上長長的竹製旗杆,表示拿督公的存在,有的則會在海上建立獨立的拿督公小廟用以祭祀。總體而言,拿督公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祂甚至取代了華人土地公的信仰功能。
雖然一般認知中的拿督公是以在地化土地公的形象出現在民間,但拿督公與中國傳統土地公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拿督公有很強的個人特色,祂們許多都有名字,像是拿督哈山(Dato Hassan)、拿督阿里(Dato Ali)、拿督阿旺(Dato Awang)、拿督歐士曼(Dato Osman)等,神龕等處上有的會寫上祂們的名字。這種情形有點類似於台灣所能見到那些有名字的有應公或地基主。
事實上,馬來傳統社會當中其實早有聖人崇拜的傳統,一些地方長老、英雄或巫師,在過世之後由於持續被人們所緬懷,或是出現顯靈事件而被認為會保佑地方,被地方社群尊奉,稱之為Keramat或Dato Keramat(聖者)。・因此也有一說認為正是因為華人來到馬來亞後,吸收了馬來人的Keramat信仰,而產生出拿督公崇拜。但無論如何,這種由人而成神的過程,與其說祂是土地公,但祂更像由幽魂升格成為能夠代天巡狩的王爺,只是在馬來西亞,有很多應該成為王爺的「人」最終在地化成為了拿督公而已。若從這個思路出發,便不難理解馬來西亞除了正港的馬來人拿督公之外,其他族群也具備了成為拿督公的潛能,而馬來西亞各地確實有這些案例。
先從正港的馬來人說起,在雪蘭莪沿海瓜拉冷岳縣的蚶山(Jugra,又稱蛤山)天寶宮,便供奉了拿督尊王。除了主祀拿督王之外,還供奉了祂的皇后、弟弟、義子等其他王室成員以及侍衛。這位拿督尊王正是十九世紀的第四任雪蘭莪王國的統治者—蘇丹阿都沙末(Sultan Abdul Samad)。蘇丹在位四十一年之久,由於華人認為蘇丹勤政愛民,因此蘇丹駕崩後,便被華人所供奉。拿督尊王的塑像甚至參照蘇丹的真實樣貌打造。由於這位拿督位階高至蘇丹,因此頗有名氣,雪蘭莪沿海一帶的拿督公有許多都是分靈自此。
再來是雪蘭莪武來岸(Broga)由原住民成神的石拿督公。據說在十九世紀華人南來時因為水土不服,全賴一位名叫石滿的原住民指點草藥良方,因而受人敬重。石滿晚年修行,後來也失蹤了一段時間,有幾位村民同時夢見石滿羽化成仙,並被玉帝冊封為「石拿督」。之後,人們發現石滿骨骸,後來便將他安葬並立廟祭拜。石拿督由此成為當地的地方神,石拿督公廟也成為武來岸地區的地方公廟。
華人成為拿督的情形也頗為常見,較著名的案例有霹靂太平馬登的蘇藍卓,蘇藍卓原名蘇正祥或蘇亞祥,是十九世紀中葉當地義興礦區的領袖,然而在一八六五年第二次拿律戰爭期間,蘇正祥因戰敗而在逃亡期間遭敵對陣營所虜獲,最終被處死。・蘇氏死後顯靈成為河中巨鱷,人們在河邊為祂立廟為蘇藍卓。另一個華人拿督則是在霹靂與檳城交界處—巴里文打(Parit Puntar)的鄭籃卓,祂原名鄭亞文,是一名蔗園督工,無奈在一次火災中為救同僚而喪生。人們為感念祂而為祂立廟,尊奉祂為鄭籃卓或鄭伯公,成為現今的籃卓古廟。這間拿督公廟已成為地方居民的信仰中心,最終發展成地方大廟,連媽祖和三山國王都成為鄭籃卓的配祀神。該市鎮的一條大街也以祂為命名,為鄭伯公路(Jalan Teh Peh Kong)。
除了馬來人本身、原住民和華人之外,馬來西亞也有錫克人死後成為拿督的案例,馬來西亞著名反對黨領袖卡巴星(Karpal Singh)是十分受人愛戴的政治明星,名望甚高,無奈他於二○一四年因車禍過世。三年後,霹靂安順(Teluk Intan)天峰宮的壇主兼乩童便決定請人製作塑像,供奉拿督卡巴星。拿督卡巴星成為最「年輕」的拿督,至於祂的「神力」如何?是否會持續壯大?則有待進一步觀察。在馬來西亞北部的檳城、吉打、玻璃市地區,當地因為靠近泰國,與泰裔居民雜處,因此也有泰國裔的拿督公。
從這個由人成神的角度而言,拿督公並不只是單純的土地公信仰,它內部其實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性,一方面可以說祂類似華人原鄉的王爺信仰,另一方面又可說祂是吸收了馬來人的聖人信仰,可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祂和土地公比起來,這種類似王爺型的拿督,應該分作兩個不同的信仰體系來理解。
走在馬來西亞的街道或是華人住宅區,經常能夠在街頭巷尾、住宅前、大樹下,抑或是大樓後方的角落見到類似台灣鄉間的小土地公廟。這些小土地公廟設計簡單,與其說它是小廟,倒不如說它是簡單的小神龕。它的屋頂沒有過於華麗的龍雕,較多的是像馬來西亞普通平房的那種倒「V」字型的屋頂。沒錯,它確實是為了供奉土地神而設的神龕。然而走近一看,裡面所供奉的神祇雖然看起來與我們一般所見的土地公相似,但在穿著打扮,甚至長相上,卻與我們熟知的土地公有些許出入。這尊神明便是馬來版的土地神—「拿督公」。
典型拿督公的長相與土地公幾乎相同,同樣是留著白色長鬍子的長者形象,只是膚色略黑。穿著上,祂的帽子與土地公相似,但設計較為簡單,嚴格說來應該是馬來人或伊斯蘭教徒所戴的「宋谷」(songkok)。拿督公所穿的服裝也並非中式服裝,而是馬來人的上衣(baju)和圍幔—「沙郎」(sarong)。有別於土地公手上所拿的如意,祂所持的會是馬來短劍(kriss)。而拿督公手上的中國式金元寶以及拐杖,則與土地公所持的大致相同。是的,拿督公就是這樣一尊參雜著中國與南洋在地色彩的神祇。
什麼是拿督?
字面上,拿督公源於馬來語的Datuk或Dato,・為爺爺之意,馬來人會用以稱呼祖父以及尊稱男性長者。此外,拿督也是馬來貴族及領導階層中的一種尊稱,這些拿督的位階有高有低,高者可以是在整個馬來王國當中統領一整片封地的諸侯,・低者可以是協助諸侯管理地方的基層領袖。因此若翻開馬來歷史文獻,總是會見到許多的拿督。在十九世紀馬來半島華人大開發時期,前來維生的華人,便需要和這些拿督打交道,以承租農地、礦地及繳納稅收。
在現今,拿督也成為一種勳銜,擁有拿督頭銜的人,多半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在每年馬來西亞各州蘇丹華誕時,也會冊封勳銜予州內的有功人士,而拿督便是其中一個冊封的項目。當然,在拿督之上,還有拿督斯里(Datuk / Dato Sri)、丹斯里(Tan Sri)、敦(Tun)等等。拿督之下,也還有許多不同的名目。
在馬來西亞,拿督已是普遍可見的勳銜,這個傳統馬來封號已不僅限於馬來人,也有相當多的華人被封為拿督。有些州甚至可以透過捐錢予皇室而獲得拿督的封號,報章上也經常可見恭賀某某人獲得拿督勳銜的廣告。雖然現今的拿督可能已經有些氾濫,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拿督已經深入民心,即使後來拿督的「含金量」已逐漸降低,但拿督在本地人心目中的長者或社會領袖形象,卻是未曾改變的。
本地華人用自己的語言把Datuk進行音譯詮釋,再將之文字化,並且後方加多一個華文固有詞—「公」以方便理解。在語言上,廣東話和福建話是馬來西亞最主要的兩大華人語系,在廣東語言方面,雖然廣府話和客家話有所不同,但他們在念馬來語datuk時,會將之詮釋為漢字的「拿督」(粵語:naa4-duk1;客語:nˋ)。而福建語系當中的閩南語和潮州話,則較常會將之詮釋為漢字的「藍卓」、「籃卓」(閩南語:n;潮語:n-toh)、「那卓」(閩南語:n;潮語:n)、「藍督」(閩南語:n;潮語:n)或「拿卓」(閩南語:n;潮語:n)等等。或許是因為大眾傳播或是製造廠商的關係,廣東話為詮釋的漢字—「拿督」在馬來西亞較為常見,反觀「藍卓」較少,但若是我們見到「藍卓」的寫法,這就表示我們所在的地區多半是以福建人為主流了。・像是在檳城、吉打、玻璃市以及霹靂北部的太平這些以福建人為主的地區,籃卓、那卓都是常見的拿督公寫法。
形形色色的拿督公
在形象上,拿督公的形式多樣,除了上述一開始所提及的馬來版土地公形象之外,我們也可以見到以馬來酋長與王公貴族形象的拿督公,他們戴著馬來傳統的布帽,如同馬幣上蘇丹所戴的帽子。有的兩邊甚至有持槍的護衛;有的則身穿皇室特有黃衣;有的則是馬來人的形象,但是卻如同佛教修行者一樣盤腿而坐;也有的拿督公穿著西裝大衣和西褲;有的旁邊則配有拿督婆,與中國傳統的土地公、土地婆概念一樣。
人們對於拿督公的配偶,有很多不同的稱呼,像是拿督奶奶或拿督娘娘。拿督婆在造型上通常戴著頭巾(tudung),以伊斯蘭教婦女的形象出現。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南洋的拿督婆並非像中國的土地婆一樣有著傳統女性「不出廳堂」的特徵。本地的拿督婆有的地位頗高,有些公廟也會大肆慶祝拿督婆千秋寶誕(如柔佛州峇株巴轄海口的青龍宮),有的宮廟主神甚至就是拿督娘娘(雪蘭莪巴生吉膽島的拿督娘娘宮)。這樣的現象或許也對應了南洋土著女性地位相對較高的傳統。
馬來西亞各地的拿督公也以很多種不同的形式被人們所塑造,除了塑像的之外,較常見的形式還有牌位式的。牌位一般多是以漆上紅色的木板配上金色的雕刻字體,寫上「拿督公」或「拿督公神位」等。有的也會在拿督公神位的中榜文字的兩旁刻上對聯,較常見到的是「拿管地方興旺;督理財源廣進」,充分展現了拿督公的神格職能。此外,有的牌位也會刻上拿督公的人像圖形,取代文字的使用。另一種形式是以畫像或照片的形式,將拿督公畫像放進相框中,置於神龕內膜拜。但這種形式較少見,筆者在一次造訪霹靂州南部沿海市鎮—安順時,在當地普遍見到。
另一種較常見的形式是石塊或土堆型的拿督公,人們會將一些長相特殊的石頭,或是因為白蟻窩而形成的大土堆視為可能會有神靈的存在,特別是當這些自然物在人們的夢中或是生活中被認為有靈驗的事件,人們便會開始在石塊或土堆旁插香膜拜,有的也會用紅布、金花或是其他裝飾品裝點它們,若是這位拿督公持續靈驗的話,人們甚至會在現地蓋廟供奉。
總體而言,無論是塑像、牌位、畫像抑或是石頭、土堆型的拿督公,這些形式都與華人在原鄉供奉土地公的方式如出一轍,唯一不同的是,中國和南洋文化交融後所產生的拿督公,人們對他的想像可能更加豐富,或許是人在南洋地域的緣故,本地拿督公的受重視度也高於本地的土地公。
土地公與「代天巡狩」
拿督公的出現,顯然是中國傳統信仰文化和南洋馬來文化碰撞・之後的結果。傳統上,華人便有土地崇拜的習慣,並將土地神具象化成為老者的形象。土地神掌管了農業社會的收成與自然環境的安定,是土地的管理者。華人來到馬來亞之後,無論是從事熱帶栽培業(香料、甘蜜、橡膠等的種植)還是採礦業,都與土地脫離不了關係,土地崇拜自然也隨之扎根南洋。然而在這片中華帝國之外的南洋異域,土地管理者自然不是傳統中國的身穿唐裝的土地公,估計孫悟空用金箍棒在此敲打地上所呼叫出來的也不會是祂們,而是馬來籍的土地管理者Datuk。Datuk無論是在字面意義上或是在馬來王國的角色(地方頭人)上,都與土地公一致。或許是如此,便催生了本地的拿督公信仰。
例如早年的華人礦場幾乎都會安奉拿督公,礦工們每天早晚均須膜拜拿督公,以保護工作安全,避免意外事件發生,同時期望藉由神力召喚大量錫苗。・在現今馬來西亞的新村,特別是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彭亨一帶的新村,村中幾乎每條路的路口都設有拿督公的小神龕,像是筆者到訪的雪蘭莪新古毛新村便是如此,該新村面積大約零點二八平方公里,裡面擁有十四座拿督公神龕。
在雪蘭莪沿海的吉膽島和五條港漁村,幾乎家家戶戶門外都能找到拿督公神龕。此外,對於討海的漁民而言,不同海域也有它所屬的拿督公,人們也會在海中插上長長的竹製旗杆,表示拿督公的存在,有的則會在海上建立獨立的拿督公小廟用以祭祀。總體而言,拿督公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祂甚至取代了華人土地公的信仰功能。
雖然一般認知中的拿督公是以在地化土地公的形象出現在民間,但拿督公與中國傳統土地公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拿督公有很強的個人特色,祂們許多都有名字,像是拿督哈山(Dato Hassan)、拿督阿里(Dato Ali)、拿督阿旺(Dato Awang)、拿督歐士曼(Dato Osman)等,神龕等處上有的會寫上祂們的名字。這種情形有點類似於台灣所能見到那些有名字的有應公或地基主。
事實上,馬來傳統社會當中其實早有聖人崇拜的傳統,一些地方長老、英雄或巫師,在過世之後由於持續被人們所緬懷,或是出現顯靈事件而被認為會保佑地方,被地方社群尊奉,稱之為Keramat或Dato Keramat(聖者)。・因此也有一說認為正是因為華人來到馬來亞後,吸收了馬來人的Keramat信仰,而產生出拿督公崇拜。但無論如何,這種由人而成神的過程,與其說祂是土地公,但祂更像由幽魂升格成為能夠代天巡狩的王爺,只是在馬來西亞,有很多應該成為王爺的「人」最終在地化成為了拿督公而已。若從這個思路出發,便不難理解馬來西亞除了正港的馬來人拿督公之外,其他族群也具備了成為拿督公的潛能,而馬來西亞各地確實有這些案例。
先從正港的馬來人說起,在雪蘭莪沿海瓜拉冷岳縣的蚶山(Jugra,又稱蛤山)天寶宮,便供奉了拿督尊王。除了主祀拿督王之外,還供奉了祂的皇后、弟弟、義子等其他王室成員以及侍衛。這位拿督尊王正是十九世紀的第四任雪蘭莪王國的統治者—蘇丹阿都沙末(Sultan Abdul Samad)。蘇丹在位四十一年之久,由於華人認為蘇丹勤政愛民,因此蘇丹駕崩後,便被華人所供奉。拿督尊王的塑像甚至參照蘇丹的真實樣貌打造。由於這位拿督位階高至蘇丹,因此頗有名氣,雪蘭莪沿海一帶的拿督公有許多都是分靈自此。
再來是雪蘭莪武來岸(Broga)由原住民成神的石拿督公。據說在十九世紀華人南來時因為水土不服,全賴一位名叫石滿的原住民指點草藥良方,因而受人敬重。石滿晚年修行,後來也失蹤了一段時間,有幾位村民同時夢見石滿羽化成仙,並被玉帝冊封為「石拿督」。之後,人們發現石滿骨骸,後來便將他安葬並立廟祭拜。石拿督由此成為當地的地方神,石拿督公廟也成為武來岸地區的地方公廟。
華人成為拿督的情形也頗為常見,較著名的案例有霹靂太平馬登的蘇藍卓,蘇藍卓原名蘇正祥或蘇亞祥,是十九世紀中葉當地義興礦區的領袖,然而在一八六五年第二次拿律戰爭期間,蘇正祥因戰敗而在逃亡期間遭敵對陣營所虜獲,最終被處死。・蘇氏死後顯靈成為河中巨鱷,人們在河邊為祂立廟為蘇藍卓。另一個華人拿督則是在霹靂與檳城交界處—巴里文打(Parit Puntar)的鄭籃卓,祂原名鄭亞文,是一名蔗園督工,無奈在一次火災中為救同僚而喪生。人們為感念祂而為祂立廟,尊奉祂為鄭籃卓或鄭伯公,成為現今的籃卓古廟。這間拿督公廟已成為地方居民的信仰中心,最終發展成地方大廟,連媽祖和三山國王都成為鄭籃卓的配祀神。該市鎮的一條大街也以祂為命名,為鄭伯公路(Jalan Teh Peh Kong)。
除了馬來人本身、原住民和華人之外,馬來西亞也有錫克人死後成為拿督的案例,馬來西亞著名反對黨領袖卡巴星(Karpal Singh)是十分受人愛戴的政治明星,名望甚高,無奈他於二○一四年因車禍過世。三年後,霹靂安順(Teluk Intan)天峰宮的壇主兼乩童便決定請人製作塑像,供奉拿督卡巴星。拿督卡巴星成為最「年輕」的拿督,至於祂的「神力」如何?是否會持續壯大?則有待進一步觀察。在馬來西亞北部的檳城、吉打、玻璃市地區,當地因為靠近泰國,與泰裔居民雜處,因此也有泰國裔的拿督公。
從這個由人成神的角度而言,拿督公並不只是單純的土地公信仰,它內部其實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性,一方面可以說祂類似華人原鄉的王爺信仰,另一方面又可說祂是吸收了馬來人的聖人信仰,可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祂和土地公比起來,這種類似王爺型的拿督,應該分作兩個不同的信仰體系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