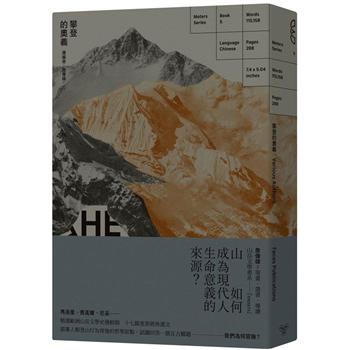▍遠征隊的誕生 Birth of an Expedition
遠征隊的誕生有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由委員會來指揮的大型國家遠征隊,另一種是由三五好友組成的登山隊伍。一九七○年我們的安娜普納南壁遠征隊,則是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一個綜合體。
一九六二年我放棄了正常的工作,擔任了八年的軍職,又在聯合利華公司(Unilever)當了九個月的儲備幹部後,對於工作內容不滿足,又期待生活能夠更貼近於登山。但我在踩出了這一步後,卻比許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更少登山。一九六八年十月以前的三年間,我浪跡天涯在世界各地採訪報導探險活動。這是一段精采的日子,曾經到厄瓜多爾攀登一座活火山,隆冬時節到巴芬島(Baffin Island)獵捕北美馴鹿,一九六八年夏天參加一支陸軍遠征隊循藍尼羅河(Blue Nile)下溯,這是第一支完成藍尼羅河全程航行的探險隊。然而這種生活方式卻讓我離登山越來越遠,總覺得我是一個旁觀者而非實踐者。
一九六八年秋季,我從藍尼羅河下溯歸來。這次探險活動十分驚險,有三回差點沒命,有一次船在激流中翻覆,陷在漩渦中奮鬥了八次終於脫困,另外兩次則是遭遇到原住民的攻擊。我在這個探險活動中非常的投入,而且實在太過刺激了,然而並不感到滿足,畢竟那不是我熟悉的環境,需要面對太多無法掌控的危險。這一次的探險活動使我對於專注在一個登山計畫的念頭益發強烈,然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卻一點頭緒都還沒有。
當時我萬分躊躇。與溫蒂在湖區(Lake District)住了五年,風景秀麗,對登山而言那又是一個極其理想的環境,大多數人也以為我很幸運可以住在這個地方。然而我卻是極度的焦躁不安,部分是對於未來要何去何從仍無所定見;想成為一個成功的報導攝影作家,同時又只想要登山。住在湖區讓我失魂落魄,與世隔絕,一來遠離登山主流,又與我所思考報導攝影的生涯也距離遙遠。我甚至考慮搬到倫敦,拖著一個不快樂的老婆在倫敦北部繆斯威爾丘(Muswell Hill)和倫敦中心區伊斯靈頓(Islington)度過了好幾個悲慘悽涼的週末,而她卻只眷戀著湖區的石頭圓屋。我們終於達成一個協議,決定搬下去到曼徹斯特,在倫敦、威爾斯、湖區與德比郡(Derbyshire)砂岩之間取得一個妥協。
啟程前往藍尼羅河探險之前,我們在曼徹斯特西南市郊波頓(Bowdon)買了一間房子,我天真的以為,當我安全歸來之時,溫蒂早已經搬進去安頓好所有的房間了。然而,實際上我回來時才剛簽約完成,建築師另外又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裝修所有的房間,才讓這房子適合居住。
這段期間我們只得住在朋友家。尼克.艾斯考特與卡蘿琳(Nick Estcourt and Carolyn Estcourt)在曼徹斯特南邊砂岩高地的奧爾德利坪頂(Alderley Edge)有一間兩房的公寓,原先只打算借住個幾天,直到我們找到一個有家具的棲身之地,結果一待就待了兩個月之久,帶著十八個月大的兒子睡在他們起居室的地板上,那麼長的時間兩家人竟然相安無事,這似乎是個奇蹟。對於遠征隊員之間的相處而言,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考驗。
這段期間也是安娜普納南壁遠征隊誕生、或者說演化的時候。初時它只是一個簡單的構想,並不像整個計畫完成時那般富有挑戰性。
尼克和我,以及另外一位朋友馬丁.波以森(Martin Boysen)這兩年不時討論有關遠征的構想,然而並沒有什麼具體的進展。一九六八年十月,我們終於下定決心預計在一九七○年進行一次遠征,合適的目標卻很有限。當時所有尼泊爾境內的山峰,以及巴基斯坦與印度境內比較有吸引力的山脈,因為政治的因素並未開放攀登,主要是因為西藏邊境的緊張情勢所致。我們可以選擇攀登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脈(Hindukush),或是巴基斯坦喀拉崑崙山脈外圍的山峰,然而我對於這些目標沒有興趣,它們只能夠蹲伏在喜馬拉雅巨峰的陰影之下。我們因此將目標轉移到阿拉斯加州,那兒仍有數以百計未被登臨的山壁,比起喜馬拉雅山脈而言,阿拉斯加尤其空寂而孤絕,但它的海拔高度卻差了一大截。
我跟馬丁認識了約八年之久,當年在倫敦東南肯特郡通布里奇泉(Turnbridge Wells)郊外露頭的哈里遜砂岩(Harrison Rocks),他還在學時已經是個爬岩天才。他現年二十八歲,已經是英國最佳的攀岩者之一,雖然初見面很難給人這個聯想。平地上,他那雙長手長腿似乎不太協調,可觀的體能也被外衣給遮住了。然而當他在岩壁上攀登時卻行走自如,像一個平順運轉的攀登機器。馬丁就像是一隻巨大聰明的樹懶,天生就生活在垂直的世界裡。
馬丁與他的妻子瑪姬(Maggie)是我們在湖區家裡的常客,過去我們曾在國內各地一起攀登,卻從未到過阿爾卑斯山脈或更遠的地方。從通布里奇學院畢業後,馬丁進入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 University)就讀,之後就擔任老師的工作,利用教職的長假保持一個快樂的業餘登山者的角色。做為一個才華洋溢的登山者,他明顯是非競爭性的,或許因為天分,而懶得去加入英國登山界永無休止的競爭。儘管如此,他在威爾斯與英格蘭等地所開創的新路線,均被視為英國至今最困難、最具挑戰性的路線。他也曾經到訪阿爾卑斯山脈嘗試一些高難度的攀登,完成了一些新路線的首登,以及一些路線的英國人首登紀錄。
尼克截然不同,他並非一個天生的登山者,精瘦而結實,十分的敏感且富競爭性,他驅使自己成為一流的登山者。某些方面而言,他具有戰前中產階級的背景,與一九五三年首登聖母峰之前大部分的英國遠征隊員相似。他曾就讀於東柏恩學院(Eastbourne College),然後就讀於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並成為劍橋大學登山社(Cambridge University Mountaineering Club)的社長。尼克的父親在他學生時代就帶他到阿爾卑斯山脈登山,這是很典型的愛德華皇室傳統,因此尼克對阿爾卑斯登山有很廣博的背景。劍橋時代他曾經參與一支北極地區格陵蘭島的遠征隊,這也是他唯一一次歐陸以外的遠征經驗。
尼克有工程學位,在奈及利亞做了一年的海外志工服務後,進入土木工程領域。雖然他從事傳統正規的工作,然而他盡力投入登山,並試圖將自己的事業往登山靠攏,最後,他捨棄了相當束縛的工程專業,進入了電腦領域。一九六七年他在費蘭蒂(Ferranti)電力工程公司謀得一職,工作地點在曼徹斯特,所以他有很多的機會登山,尼克與他老婆卡蘿琳也是我們在湖區週末的常客。
接下來我們試著找尋第四位隊員,那是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我們曾經一起參與一九六六年冬季愛格峰北壁直登路線(Eiger Direct)的開拓,當時我擔任隨隊的攝影師,攀登到愛格峰北壁四分之三的高度。前一年冬季,我們也曾經一起嘗試德洛提斯峰(Les Droites,四千公尺)北壁的冬季首登,結果卻完成了阿簡提爾針峰(Aiguille d’Argentière,三九○一公尺)北壁的攀登。馬丁與道格爾也很熟,曾一起攀登巴塔哥尼亞的托雷岩塔(Cerro Torre,三一二八公尺),這座山雖然僅高於海平面一萬英尺,卻是世界上最陡峭困難的山峰之一,過去只有一次的攀登紀錄。他們試圖攀登一條稜脊的新路線,卻被技術上的困難與惡劣的天候打敗。
道格爾.哈斯頓無疑是當今英國登山界最傑出的登山者之一,十分的內斂沉默寡言,不易探知他的內心世界;同時他又是一個好夥伴,不論是在山腳下把酒言歡的時刻,或是困頓在半山腰的風雪之際。道格爾的長相十分的精緻淳樸,以現代的語彙來說,可說是一個十分「流行」的人物,完全自我放縱,又是個十足的苦行主義者,一種相當怪異的組合。道格爾曾就讀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待了幾年卻未完成哲學士的學位,離校後在蘇格蘭高地創立了一所登山學校。他所往來的愛丁堡登山人物是一群飲酒作樂反社會分子,專門打群架搞破壞。道格爾也和羅賓.史密斯3一起開創了一些極度困難的路線;而羅賓.史密斯於一九六二年在帕米爾高原喪生以前,他可能是當時英國登山界最有希望的登山者。
道格爾一九六三年攀登了愛格北壁(Eiger,三九七○公尺),然後一九六六年愛格北壁直登,至今仍是阿爾卑斯山脈最困難的路線。約翰.哈林(John Harlin)在瑞士創立國際現代登山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odern Mountaineering),並鼓吹推動愛格北壁直登路線的開拓,卻不幸在攀登途中因繩索斷裂而喪生。道格爾繼約翰.哈林後接任國際現代登山學校的校長。與尼克及馬丁不同,道格爾全力的投入登山事業,夏季在登山學校內指導學員登山技術,其他時間則參與遠征活動,然而,至今他也未曾造訪過喜馬拉雅山脈。
我記得曾經看過一張安娜普納峰南壁的照片,是由吉米.羅伯特(J. O. M. Roberts)中校拍攝送給一位朋友的。吉米.羅伯特中校曾任英國駐加德滿都武官,也是我所參與一九六○年安娜普納二峰(Annapurna II,七九三七公尺)三軍聯合遠征隊的領隊。
我提議:「我們就來爬這座山壁吧!」然而當時我對於這個目標要付出多少代價卻不甚了然,其他人也毫無所悉,但大夥就這樣決定了。有另外一支英國遠征隊也曾經造訪那個山區,攀登的目標是瑪恰普恰峰(Machapuchare,六九九三公尺),它是一座雄偉的雪峰,又名為「魚尾峰」,座落於安娜普納峰南壁正對面。吉米.羅伯特在攀登途中首先看到了南壁。等待吉米.羅伯特回覆我詢問的期間,我先以電話請教了仍定居國內的兩位遠征隊員。第一位是大衛.考克斯(David Cox),他任教於牛津大學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教授現代史,「南壁?我不太記得了,似乎很龐大;對了,有一大堆雪崩從上面沖刷下來,我認為是從雪溝中下來的。」另外一位定居倫敦的會計師羅傑.喬利(Roger Chorley)的看法更為悲觀,「攀登安娜普納峰南壁?」他一副不可思議的語調,「南壁被雪崩毫不間斷的沖刷著。」此時,我已經開始動搖,考慮其他可能的目標。正當此刻,吉米.羅伯特的回信來了:
「安娜普納峰南壁很有挑戰性,比聖母峰更困難,然而運補比較簡單。它確實非常困難,我本人不是一個氧氣迷,但我認為兩萬四千英尺以上的高難度攀登,可能還是需要氧氣吧!」
這封信給我了一絲鼓舞。數日後,我收到了大衛.考克斯寄來南壁的彩色幻燈片。我們把幻燈片投射在房間的牆壁上,投射出六英尺高的照片,反覆的端詳、揣摩,初時頗為興奮,後來卻不寒而慄。
馬丁說:「看,這裡看似有一條路線,但它真是龐大啊!」是的,我從未看過一座山的照片那麼的龐大而陡峭,就像把四個阿爾卑斯山壁疊在一起那般高聳。但那兒確實似有一條路線,非常困難,整條路線上去,一點破綻都沒有。一道蹲伏的雪稜(snow ridge)像一座哥德式教堂的拱壁斜倚著南壁的低處,這是攀登路線的起登點。或許可以沿著這道雪稜山腳下的冰河邊緣蜿蜒繞行,但雪崩的風險有多少呢?拱壁以上是一道冰刃稜線(ice arête),從照片上的距離遠眺,也看得出來那是一道貨真價實的刀稜。我曾經在紐布茲峰(Nuptse,七八六一公尺)看過類似的地形,有些地方在稜脊下方百呎處,就可以從許多孔穴中看穿整個稜線,真是非常可怕,而這道冰刃稜線似乎更恐怖。這道冰刃稜線最後接上了一片冰崖(ice cliff)。
尼克說:「我滿懷疑它是否穩固?」我也有同感,雖然不太有把握,還是試著在畫面上揣摩著一條貫穿冰崖的路線。這片冰崖最後接上了一片大岩階帶(Rock Band)。
「這片岩階帶至少有一千英尺高吧!」
「它的起點海拔究竟有多高?至少是兩萬三千英尺吧!你可以想像嗎,在這個海拔做高難度的岩壁攀登?」
「是的,但看那一道像攤開的書本一般的大岩溝(groove)。」它將這道大岩階帶劈成兩半,一道巨大深長的切口,非常誘人,但毫無疑問,它的難度與高度在這個海拔,從未曾有人嘗試過這樣的挑戰。
這一片岩階帶接上了一個積雪的山肩(snow shoulder),最後通往了山頂。
「這張照片由下往上拍攝,必然壓縮了上部,雪肩距離山頂想必還有一大段高度。」
我試著找出一些一九六○年從安娜普納二峰拍攝的幻燈片,當時我對安娜普納南壁一無所知,一來它距離很遠,再者在那個年代,也不會斗膽考慮這個目標。從安娜普納二峰的角度看過去,岩階帶的頂端約莫在整片山壁四分之三的高度,以上還有三千英尺的高度才接上一道陡峭的雪刃稜線,它的頂端是一道岩脊。
我們敬畏的看著這一片龐然大物,它的高度與困難度,遠超過過去任何被嘗試過的路線。我們將一九六一年我曾經攀登過的紐布茲峰南壁幻燈片重疊投射上去,在龐然的安娜普納南壁面前,紐布茲峰南壁可說只是一個侏儒。
然而,我有信心,只要有恰當的組合,我們有機會可以登上安娜普納南壁。過去的登山歷程冥冥中讓我一步一步的邁向這個目標。我們必須以在愛格北壁直登路線發展出來的技術應用在喜馬拉雅的環境。我曾經攀登過一面喜馬拉雅山壁──紐布茲峰南壁,雖然它比安娜普納南壁的簡捷許多,然而,它可以做為一個比較的量尺。我們未使用氧氣登上了紐布茲峰,因此我有無氧攀登二五八五○英尺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使用氧氣攀登安娜普納二峰,我也有使用氧氣器材的經驗,因此了解使用氧氣對於攀登能力所帶來的巨大的效益。
我曾經著迷於以一支堅強的四人小隊攀登喜馬拉雅山的想法,隊伍越小,越能無拘無束的親近山巒,不需要耗費心力去處理大型遠征隊所帶來的龐雜後勤作業與繁複的人事糾葛。然而,安娜普納南壁的尺度非四人小隊所能,需要更多的人力,我們曾討論是否可以增加到六人,似乎還是力有未殆,最後增加到八名攀登隊員。
接下來的問題是該找哪些人呢?在英國登山界有許多頂尖好手,但我們需要一組人馬,必須擁有高超的冰雪岩攀登能力、堅忍卓絕的毅力,願意犧牲個人的野心以達成團隊的目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相處的默契。第一流的登山好手天性自負,通常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者;某方面而言,最佳的遠征隊員是那種肯吃苦耐勞負重的苦行者;然而,以安娜普納南壁而言,必須要有高比例的頂尖好手能夠在艱鉅的環境下奮戰,當其他人疲憊放慢腳步時,能夠挺身而出,站上第一線持續的克服最困難的挑戰。此外,每一個人在高海拔攀登的表現很難預期,高度適應的速率因人而異,有些人完全無法適應高海拔的攀登。當然最保險的方法是只選用那些過去有高海拔攀登經驗的成員,然而因為尼泊爾與巴基斯坦在六○年代晚期的封山政策,造成一流的阿爾卑斯登山者(Alpinist)普遍缺乏喜馬拉雅山脈高海拔攀登的經驗。在英國不乏曾經參與聖母峰攀登經驗的登山好手,然而,攀登安娜普納南壁是全然不同的挑戰。
遠征隊的誕生有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由委員會來指揮的大型國家遠征隊,另一種是由三五好友組成的登山隊伍。一九七○年我們的安娜普納南壁遠征隊,則是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一個綜合體。
一九六二年我放棄了正常的工作,擔任了八年的軍職,又在聯合利華公司(Unilever)當了九個月的儲備幹部後,對於工作內容不滿足,又期待生活能夠更貼近於登山。但我在踩出了這一步後,卻比許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更少登山。一九六八年十月以前的三年間,我浪跡天涯在世界各地採訪報導探險活動。這是一段精采的日子,曾經到厄瓜多爾攀登一座活火山,隆冬時節到巴芬島(Baffin Island)獵捕北美馴鹿,一九六八年夏天參加一支陸軍遠征隊循藍尼羅河(Blue Nile)下溯,這是第一支完成藍尼羅河全程航行的探險隊。然而這種生活方式卻讓我離登山越來越遠,總覺得我是一個旁觀者而非實踐者。
一九六八年秋季,我從藍尼羅河下溯歸來。這次探險活動十分驚險,有三回差點沒命,有一次船在激流中翻覆,陷在漩渦中奮鬥了八次終於脫困,另外兩次則是遭遇到原住民的攻擊。我在這個探險活動中非常的投入,而且實在太過刺激了,然而並不感到滿足,畢竟那不是我熟悉的環境,需要面對太多無法掌控的危險。這一次的探險活動使我對於專注在一個登山計畫的念頭益發強烈,然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卻一點頭緒都還沒有。
當時我萬分躊躇。與溫蒂在湖區(Lake District)住了五年,風景秀麗,對登山而言那又是一個極其理想的環境,大多數人也以為我很幸運可以住在這個地方。然而我卻是極度的焦躁不安,部分是對於未來要何去何從仍無所定見;想成為一個成功的報導攝影作家,同時又只想要登山。住在湖區讓我失魂落魄,與世隔絕,一來遠離登山主流,又與我所思考報導攝影的生涯也距離遙遠。我甚至考慮搬到倫敦,拖著一個不快樂的老婆在倫敦北部繆斯威爾丘(Muswell Hill)和倫敦中心區伊斯靈頓(Islington)度過了好幾個悲慘悽涼的週末,而她卻只眷戀著湖區的石頭圓屋。我們終於達成一個協議,決定搬下去到曼徹斯特,在倫敦、威爾斯、湖區與德比郡(Derbyshire)砂岩之間取得一個妥協。
啟程前往藍尼羅河探險之前,我們在曼徹斯特西南市郊波頓(Bowdon)買了一間房子,我天真的以為,當我安全歸來之時,溫蒂早已經搬進去安頓好所有的房間了。然而,實際上我回來時才剛簽約完成,建築師另外又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裝修所有的房間,才讓這房子適合居住。
這段期間我們只得住在朋友家。尼克.艾斯考特與卡蘿琳(Nick Estcourt and Carolyn Estcourt)在曼徹斯特南邊砂岩高地的奧爾德利坪頂(Alderley Edge)有一間兩房的公寓,原先只打算借住個幾天,直到我們找到一個有家具的棲身之地,結果一待就待了兩個月之久,帶著十八個月大的兒子睡在他們起居室的地板上,那麼長的時間兩家人竟然相安無事,這似乎是個奇蹟。對於遠征隊員之間的相處而言,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考驗。
這段期間也是安娜普納南壁遠征隊誕生、或者說演化的時候。初時它只是一個簡單的構想,並不像整個計畫完成時那般富有挑戰性。
尼克和我,以及另外一位朋友馬丁.波以森(Martin Boysen)這兩年不時討論有關遠征的構想,然而並沒有什麼具體的進展。一九六八年十月,我們終於下定決心預計在一九七○年進行一次遠征,合適的目標卻很有限。當時所有尼泊爾境內的山峰,以及巴基斯坦與印度境內比較有吸引力的山脈,因為政治的因素並未開放攀登,主要是因為西藏邊境的緊張情勢所致。我們可以選擇攀登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脈(Hindukush),或是巴基斯坦喀拉崑崙山脈外圍的山峰,然而我對於這些目標沒有興趣,它們只能夠蹲伏在喜馬拉雅巨峰的陰影之下。我們因此將目標轉移到阿拉斯加州,那兒仍有數以百計未被登臨的山壁,比起喜馬拉雅山脈而言,阿拉斯加尤其空寂而孤絕,但它的海拔高度卻差了一大截。
我跟馬丁認識了約八年之久,當年在倫敦東南肯特郡通布里奇泉(Turnbridge Wells)郊外露頭的哈里遜砂岩(Harrison Rocks),他還在學時已經是個爬岩天才。他現年二十八歲,已經是英國最佳的攀岩者之一,雖然初見面很難給人這個聯想。平地上,他那雙長手長腿似乎不太協調,可觀的體能也被外衣給遮住了。然而當他在岩壁上攀登時卻行走自如,像一個平順運轉的攀登機器。馬丁就像是一隻巨大聰明的樹懶,天生就生活在垂直的世界裡。
馬丁與他的妻子瑪姬(Maggie)是我們在湖區家裡的常客,過去我們曾在國內各地一起攀登,卻從未到過阿爾卑斯山脈或更遠的地方。從通布里奇學院畢業後,馬丁進入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 University)就讀,之後就擔任老師的工作,利用教職的長假保持一個快樂的業餘登山者的角色。做為一個才華洋溢的登山者,他明顯是非競爭性的,或許因為天分,而懶得去加入英國登山界永無休止的競爭。儘管如此,他在威爾斯與英格蘭等地所開創的新路線,均被視為英國至今最困難、最具挑戰性的路線。他也曾經到訪阿爾卑斯山脈嘗試一些高難度的攀登,完成了一些新路線的首登,以及一些路線的英國人首登紀錄。
尼克截然不同,他並非一個天生的登山者,精瘦而結實,十分的敏感且富競爭性,他驅使自己成為一流的登山者。某些方面而言,他具有戰前中產階級的背景,與一九五三年首登聖母峰之前大部分的英國遠征隊員相似。他曾就讀於東柏恩學院(Eastbourne College),然後就讀於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並成為劍橋大學登山社(Cambridge University Mountaineering Club)的社長。尼克的父親在他學生時代就帶他到阿爾卑斯山脈登山,這是很典型的愛德華皇室傳統,因此尼克對阿爾卑斯登山有很廣博的背景。劍橋時代他曾經參與一支北極地區格陵蘭島的遠征隊,這也是他唯一一次歐陸以外的遠征經驗。
尼克有工程學位,在奈及利亞做了一年的海外志工服務後,進入土木工程領域。雖然他從事傳統正規的工作,然而他盡力投入登山,並試圖將自己的事業往登山靠攏,最後,他捨棄了相當束縛的工程專業,進入了電腦領域。一九六七年他在費蘭蒂(Ferranti)電力工程公司謀得一職,工作地點在曼徹斯特,所以他有很多的機會登山,尼克與他老婆卡蘿琳也是我們在湖區週末的常客。
接下來我們試著找尋第四位隊員,那是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我們曾經一起參與一九六六年冬季愛格峰北壁直登路線(Eiger Direct)的開拓,當時我擔任隨隊的攝影師,攀登到愛格峰北壁四分之三的高度。前一年冬季,我們也曾經一起嘗試德洛提斯峰(Les Droites,四千公尺)北壁的冬季首登,結果卻完成了阿簡提爾針峰(Aiguille d’Argentière,三九○一公尺)北壁的攀登。馬丁與道格爾也很熟,曾一起攀登巴塔哥尼亞的托雷岩塔(Cerro Torre,三一二八公尺),這座山雖然僅高於海平面一萬英尺,卻是世界上最陡峭困難的山峰之一,過去只有一次的攀登紀錄。他們試圖攀登一條稜脊的新路線,卻被技術上的困難與惡劣的天候打敗。
道格爾.哈斯頓無疑是當今英國登山界最傑出的登山者之一,十分的內斂沉默寡言,不易探知他的內心世界;同時他又是一個好夥伴,不論是在山腳下把酒言歡的時刻,或是困頓在半山腰的風雪之際。道格爾的長相十分的精緻淳樸,以現代的語彙來說,可說是一個十分「流行」的人物,完全自我放縱,又是個十足的苦行主義者,一種相當怪異的組合。道格爾曾就讀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待了幾年卻未完成哲學士的學位,離校後在蘇格蘭高地創立了一所登山學校。他所往來的愛丁堡登山人物是一群飲酒作樂反社會分子,專門打群架搞破壞。道格爾也和羅賓.史密斯3一起開創了一些極度困難的路線;而羅賓.史密斯於一九六二年在帕米爾高原喪生以前,他可能是當時英國登山界最有希望的登山者。
道格爾一九六三年攀登了愛格北壁(Eiger,三九七○公尺),然後一九六六年愛格北壁直登,至今仍是阿爾卑斯山脈最困難的路線。約翰.哈林(John Harlin)在瑞士創立國際現代登山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odern Mountaineering),並鼓吹推動愛格北壁直登路線的開拓,卻不幸在攀登途中因繩索斷裂而喪生。道格爾繼約翰.哈林後接任國際現代登山學校的校長。與尼克及馬丁不同,道格爾全力的投入登山事業,夏季在登山學校內指導學員登山技術,其他時間則參與遠征活動,然而,至今他也未曾造訪過喜馬拉雅山脈。
我記得曾經看過一張安娜普納峰南壁的照片,是由吉米.羅伯特(J. O. M. Roberts)中校拍攝送給一位朋友的。吉米.羅伯特中校曾任英國駐加德滿都武官,也是我所參與一九六○年安娜普納二峰(Annapurna II,七九三七公尺)三軍聯合遠征隊的領隊。
我提議:「我們就來爬這座山壁吧!」然而當時我對於這個目標要付出多少代價卻不甚了然,其他人也毫無所悉,但大夥就這樣決定了。有另外一支英國遠征隊也曾經造訪那個山區,攀登的目標是瑪恰普恰峰(Machapuchare,六九九三公尺),它是一座雄偉的雪峰,又名為「魚尾峰」,座落於安娜普納峰南壁正對面。吉米.羅伯特在攀登途中首先看到了南壁。等待吉米.羅伯特回覆我詢問的期間,我先以電話請教了仍定居國內的兩位遠征隊員。第一位是大衛.考克斯(David Cox),他任教於牛津大學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教授現代史,「南壁?我不太記得了,似乎很龐大;對了,有一大堆雪崩從上面沖刷下來,我認為是從雪溝中下來的。」另外一位定居倫敦的會計師羅傑.喬利(Roger Chorley)的看法更為悲觀,「攀登安娜普納峰南壁?」他一副不可思議的語調,「南壁被雪崩毫不間斷的沖刷著。」此時,我已經開始動搖,考慮其他可能的目標。正當此刻,吉米.羅伯特的回信來了:
「安娜普納峰南壁很有挑戰性,比聖母峰更困難,然而運補比較簡單。它確實非常困難,我本人不是一個氧氣迷,但我認為兩萬四千英尺以上的高難度攀登,可能還是需要氧氣吧!」
這封信給我了一絲鼓舞。數日後,我收到了大衛.考克斯寄來南壁的彩色幻燈片。我們把幻燈片投射在房間的牆壁上,投射出六英尺高的照片,反覆的端詳、揣摩,初時頗為興奮,後來卻不寒而慄。
馬丁說:「看,這裡看似有一條路線,但它真是龐大啊!」是的,我從未看過一座山的照片那麼的龐大而陡峭,就像把四個阿爾卑斯山壁疊在一起那般高聳。但那兒確實似有一條路線,非常困難,整條路線上去,一點破綻都沒有。一道蹲伏的雪稜(snow ridge)像一座哥德式教堂的拱壁斜倚著南壁的低處,這是攀登路線的起登點。或許可以沿著這道雪稜山腳下的冰河邊緣蜿蜒繞行,但雪崩的風險有多少呢?拱壁以上是一道冰刃稜線(ice arête),從照片上的距離遠眺,也看得出來那是一道貨真價實的刀稜。我曾經在紐布茲峰(Nuptse,七八六一公尺)看過類似的地形,有些地方在稜脊下方百呎處,就可以從許多孔穴中看穿整個稜線,真是非常可怕,而這道冰刃稜線似乎更恐怖。這道冰刃稜線最後接上了一片冰崖(ice cliff)。
尼克說:「我滿懷疑它是否穩固?」我也有同感,雖然不太有把握,還是試著在畫面上揣摩著一條貫穿冰崖的路線。這片冰崖最後接上了一片大岩階帶(Rock Band)。
「這片岩階帶至少有一千英尺高吧!」
「它的起點海拔究竟有多高?至少是兩萬三千英尺吧!你可以想像嗎,在這個海拔做高難度的岩壁攀登?」
「是的,但看那一道像攤開的書本一般的大岩溝(groove)。」它將這道大岩階帶劈成兩半,一道巨大深長的切口,非常誘人,但毫無疑問,它的難度與高度在這個海拔,從未曾有人嘗試過這樣的挑戰。
這一片岩階帶接上了一個積雪的山肩(snow shoulder),最後通往了山頂。
「這張照片由下往上拍攝,必然壓縮了上部,雪肩距離山頂想必還有一大段高度。」
我試著找出一些一九六○年從安娜普納二峰拍攝的幻燈片,當時我對安娜普納南壁一無所知,一來它距離很遠,再者在那個年代,也不會斗膽考慮這個目標。從安娜普納二峰的角度看過去,岩階帶的頂端約莫在整片山壁四分之三的高度,以上還有三千英尺的高度才接上一道陡峭的雪刃稜線,它的頂端是一道岩脊。
我們敬畏的看著這一片龐然大物,它的高度與困難度,遠超過過去任何被嘗試過的路線。我們將一九六一年我曾經攀登過的紐布茲峰南壁幻燈片重疊投射上去,在龐然的安娜普納南壁面前,紐布茲峰南壁可說只是一個侏儒。
然而,我有信心,只要有恰當的組合,我們有機會可以登上安娜普納南壁。過去的登山歷程冥冥中讓我一步一步的邁向這個目標。我們必須以在愛格北壁直登路線發展出來的技術應用在喜馬拉雅的環境。我曾經攀登過一面喜馬拉雅山壁──紐布茲峰南壁,雖然它比安娜普納南壁的簡捷許多,然而,它可以做為一個比較的量尺。我們未使用氧氣登上了紐布茲峰,因此我有無氧攀登二五八五○英尺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使用氧氣攀登安娜普納二峰,我也有使用氧氣器材的經驗,因此了解使用氧氣對於攀登能力所帶來的巨大的效益。
我曾經著迷於以一支堅強的四人小隊攀登喜馬拉雅山的想法,隊伍越小,越能無拘無束的親近山巒,不需要耗費心力去處理大型遠征隊所帶來的龐雜後勤作業與繁複的人事糾葛。然而,安娜普納南壁的尺度非四人小隊所能,需要更多的人力,我們曾討論是否可以增加到六人,似乎還是力有未殆,最後增加到八名攀登隊員。
接下來的問題是該找哪些人呢?在英國登山界有許多頂尖好手,但我們需要一組人馬,必須擁有高超的冰雪岩攀登能力、堅忍卓絕的毅力,願意犧牲個人的野心以達成團隊的目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相處的默契。第一流的登山好手天性自負,通常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者;某方面而言,最佳的遠征隊員是那種肯吃苦耐勞負重的苦行者;然而,以安娜普納南壁而言,必須要有高比例的頂尖好手能夠在艱鉅的環境下奮戰,當其他人疲憊放慢腳步時,能夠挺身而出,站上第一線持續的克服最困難的挑戰。此外,每一個人在高海拔攀登的表現很難預期,高度適應的速率因人而異,有些人完全無法適應高海拔的攀登。當然最保險的方法是只選用那些過去有高海拔攀登經驗的成員,然而因為尼泊爾與巴基斯坦在六○年代晚期的封山政策,造成一流的阿爾卑斯登山者(Alpinist)普遍缺乏喜馬拉雅山脈高海拔攀登的經驗。在英國不乏曾經參與聖母峰攀登經驗的登山好手,然而,攀登安娜普納南壁是全然不同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