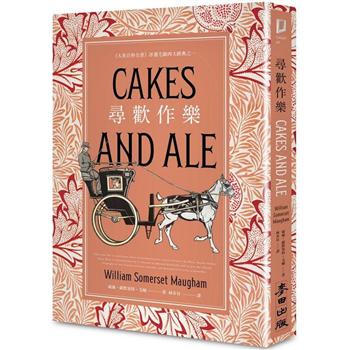1
我發覺,凡是有人打電話找你,得知你不在就留言要你盡速回電、還說有重要的事,那件事多半對你沒那麼重要。若是要送你禮物或主動幫忙,一般人多半按捺得住自己的急性子。所以我回到住處,正打算抓緊時間喝一杯、抽根菸、讀讀報,再換衣服吃晚餐。聽到房東太太費羅斯女士說,歐洛伊.基爾先生請我馬上回電,便心想可以不予理會。
「是那位作家嗎?」房東太太問。
「是啊。」
她好意地瞥了電話一眼。
「要我回撥嗎?」
「沒關係,謝謝。」
「如果他又打來,我要說什麼?」
「請他留言吧。」
「好的,先生。」
她噘著嘴,拿起空咖啡壺、往房間掃視一遍,確定乾淨後便走了出去。費羅斯女士熱愛讀小說,想必已讀遍洛伊的小說。她對我隨便的態度很不以為然,可見很欣賞他的作品。後來我再度進門時,看見廚櫃上擺了一張紙條,上頭是費羅斯女士粗大清晰的字跡:
基爾先生又打了兩通電話,問你明天能否跟他共進午餐?如果不行,你哪天方便?
我不禁挑起眉,想想有三個月沒看到洛伊了,上次也僅在某場聚會上短暫一會。他十分和善,而且向來如此。道別時,他還對我倆甚少碰面大嘆可惜。
「真受不了倫敦,」他說:「老是沒時間見想見的朋友。要不要下星期找時間吃頓午飯呢?」
「當然好。」我回道。
「我回家看看記事本再打給你。」
「好啊。」
我認識洛伊二十年來,都曉得他老在西裝背心左上方口袋裡,放著一本記錄自己行程的小冊子。因此,後來他沒消沒息,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他這麼急著展現熱絡,我實在無法相信不是出於私心。就寢前,我抽著菸斗,腦袋裡推敲著洛伊找我吃午餐的可能原因。也許有位女性仰慕者纏著他,央求他介紹給我認識;也許有位美國編輯恰巧在倫敦待幾天,希望洛伊安排他跟我見面。不過,我可不能把這位老友看扁了,以為他沒法子應付這類情況。況且,他還叫我挑自己方便的日子,不太像是要我跟別人碰面。
洛伊有件事無人能出其右:對於當紅的同行小說家,他必定真誠地熱情以待,但當小說家的名聲被懶散、失敗或他人的光環蒙上陰影,他又懂得不失禮貌地疏遠。寫作生涯難免起起落落,我很清楚自己當時並未受到大眾矚目。我當然可以找些不得罪他的藉口加以婉拒,但這傢伙的態度堅決,假如出於私心打定主意要見我,除非我直接叫他「去死」,否則他絕對會繼續死纏爛打。不過,我實在忍不住好奇,況且我還滿喜歡洛伊的。
我曾滿懷欽佩地看他在文壇崛起。他的寫作生涯堪稱典範,可供有志從事文學創作的年輕人參考。同輩作家當中,我還真想不到有誰能像他一樣,才華無比淺薄卻能取得一席之地,就好比聰明如他每天吃的胚芽粉,可能頂多就堆滿一湯匙吧。他對此相當有自知之明,憑這點本事就寫成了將近三十本書,想必偶爾連他自己都覺得簡直是奇蹟。查爾斯.狄更斯在一場晚宴後的演說中提到,天才就是具有無窮無盡的吃苦工夫,我不禁揣想,洛伊初次讀到這句話時想必靈光乍現,加以反覆咀嚼。假使如此,他一定暗自以為,自己可以當個不亞於他人的天才。而當某女性刊物的書評興高采烈地在討論他一本作品的短評中,真的用上「天才」一詞(近來書評動輒就用),他勢必心滿意足地歎了口氣,宛如耗費數小時絞盡心思,終於完成了填字遊戲。凡是多年來看過他孜孜不倦的人,都得承認再怎麼說,他都配得上天才的稱號。
洛伊的生涯剛起步就有些優勢。他是家中獨子,父親多年在香港擔任輔政司,最後官拜牙買加總督退休。若你翻開密密麻麻的名人錄查找歐洛伊.基爾,便會看到以下文字:聖米迦勒暨聖喬治司令勳章與皇家維多利亞司令勳章得主雷蒙.基爾爵士(詳見該條目)獨生子,其母愛蜜莉為已故印度陸軍少將波西.康伯頓之次女。他先後於溫徹斯特與牛津新學院就讀,擔任學生會會長,要不是因為不幸罹患麻疹,很可能就成為划船隊一員。他的學業成績雖不到出類拔萃,卻也四平八穩,而且大學畢業時沒留下任何債務。早在當時,洛伊就已節儉度日,絲毫不想有無謂的開銷。他也是貼心的兒子,很清楚自己享有所費不貲的教育,全憑父母的犧牲。他父親退休後,住在格洛斯特郡斯特勞德鎮一間樸素卻不簡陋的房子裡。他不時會到倫敦出席跟他治理過殖民地相關的官方晚宴,也習慣順便造訪自己參與的文藝俱樂部。而洛伊從牛津畢業返家時,正是有賴父親在俱樂部的老友牽線,才得以獲派為某位政治人物的私人祕書。說到這位政治人物,他在保守黨兩度執政期間擔任內閣大臣時出盡洋相,好不容易才獲封爵位,年紀輕輕的洛伊因而有機會接觸上流社會。有些作家僅憑畫報刊物研究上層社交圈,導致寫出悖禮冒失的作品,但洛伊的書絕對找不到這類錯誤。他深諳公爵之間的言談辭令,也熟悉議員、律師、貼身男僕、賽馬投注商等身分對公爵說話時各自應有的禮數。他的早期小說中,描寫總督、大使、首相、王室和貴婦名媛的筆觸活潑,讀來頗令人著迷。文字友善卻不流露輕視,親暱卻不魯莽無禮。他不會讓你忘記筆下人物的身分地位,卻也不吝展現自己的自在,認為這些人同樣有血有肉。說來可惜,由於潮流改變,貴族的日常不再適合作為嚴肅小說的主題。對於時代趨勢向來敏銳的洛伊,後期小說主題都局限於律師、特許會計師與農產盤商的內心衝突,但他對這些圈子的掌握就不若以往。
我認識洛伊時,他剛辭去祕書一職不久,打算全心投入文學創作。當時的洛伊高大挺拔,未穿鞋身長便超過一百八十公分,擁有壯碩的體格與寬闊的雙肩,舉手投足散發自信。他並不俊朗,但有著順眼的陽剛氣息,與一對大大的清澈藍眼眸、一頭淡棕色鬈髮,鼻子短而寬,下巴方方正正,看起來老實、乾淨又健康,算是半個運動員。凡是讀過他早期作品中,與獵犬外出打獵時那生動又精準的描述,都不會懷疑他是寫自親身經歷。一直到不久前,他仍喜歡偶爾拋下伏案的工作,到野外打獵一整天。他出第一本小說時,文人雅士時興喝啤酒、打板球一展男子氣概,有好些年,文學圈內的板球隊幾乎都看得到洛伊。不知何故,這群人已不像過往那般無所畏懼,筆下作品也不再受重視,雖然依舊是打板球的夥伴,卻很難找到發表文章的管道。洛伊早已多年沒碰板球了,如今改對波爾多紅酒十分講究。
對於筆下首部小說,洛伊的態度極為謙虛,其篇幅短小、文字簡潔,樹立了日後作品的高尚格調。他把小說送給所有當時引領文壇的作家,隨書附上一封文情並茂的信,表達對他們莫大的仰慕、自己何以獲益良多,以及即使難以望其項背,仍熱烈企盼踏上前輩開創的道路。他畢恭畢敬地把書擺在文學巨擘跟前,宛如年輕後輩初入文壇時,向自己崇拜的大師致意。他十分清楚,要求大師在百忙之中,撥冗閱讀新人不成氣候的作品,毋寧是愚勇之舉,但依然低聲下氣,懇求前輩予以賜教提點。這些作家因為他的盛讚受寵若驚,多半洋洋灑灑地回信,鮮少敷衍了事,不僅大力稱許洛伊的書,許多人還邀請他參加午宴。他們無不欣賞洛伊直率的個性與暖心的熱情。他求教時總是十分謙虛,無比誠懇地答應會確實改進。眾前輩都覺得,眼前的小伙子值得費點心思指導。
洛伊的小說一炮而紅,因而在文學圈結交許多好友。不久後,凡是前往布魯姆斯伯里、坎普敦丘或西敏等地區出席茶會,必定會見到他分發奶油麵包給賓客,或忙著幫年長女士的空杯斟茶添水。他年輕、直爽又開朗,聽到有人講笑話總是開懷大笑,教人想不喜歡他都難。他會到維多利亞街或霍本的飯店地下室出席餐會,跟文人墨客、年輕律師,以及身穿利柏提百貨 絲衣、戴著珠寶項鍊的女士,吃頓三先令六便士的晚宴,暢談文學與藝術。旁人不久便發覺,洛伊格外擅長餐後高談闊論,而他為人實在討喜,其他作家、對手和同輩都待他寬容,甚至不介意他屬於仕紳階級。他們的作品往往備受他讚揚,寄手稿過去讓他評論,也總是得到毫無缺失的美譽。在他們看來,洛伊不僅好相處,更有不偏頗的眼光。
他寫了第二本小說,過程嘔心瀝血,並受惠於前輩提供的創作建議。好幾位前輩在洛伊請託下,寫了書評投稿到一家報紙,自然好話說盡,洛伊也事先聯絡了該報編輯。他第二本小說成功歸成功,卻不足以喚起競爭對手的危機意識,反倒證實了眾人的猜疑:他在倫敦絕對無法興起太大波瀾。他是性格爽朗的好人,並非搞小圈圈之流。既然他再怎麼往上爬也成不了絆腳石,前輩當然頗樂於提攜這位年輕人。我認識其中一些作家,反省起自己當初犯的錯,也只能面帶苦笑。
不過,說他自命不凡倒是他們的判斷錯誤。洛伊打從年輕開始,就保有謙虛這項最討喜的特質。
「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一流的小說家,」他老是這麼說:「跟那些文壇巨擘相比,我根本什麼都不是。以往,我都認為自己總有一天會寫出一本了不起的小說,但現在早就不抱這個奢望了。我只希望在別人眼中,自己凡事都盡力而為。我寫得很認真,任何粗心的錯誤絕對逃不過我的眼眸。我自認能把故事說好、創造出有血有肉的角色。到頭來,還是要看成果來見真章。《針眼》在英國賣了三萬五千本、在美國賣了八萬本。至於我下一部小說的連載版權,簽約金也打破自己的紀錄。」
即使是現在,洛伊依然會寫信給這些書評家,感謝他們的美言,同時邀請他們共進午餐,這難道不是謙虛的展現嗎?而且不僅如此。每當有人寫了篇措詞尖銳的批評,洛伊不得不忍受惡毒攻擊,尤其在自己聲譽卓著時,他不會像多數人一樣,內心咒罵著討厭自己作品的渾球,隨之拋諸腦後,反而會寫一封長信給那位書評家,除了對其不滿表達遺憾之意,還表示書評本身饒富興味,而且容他冒昧一句:評論精湛有理、文字情感真摯,所以非得寫信致意不可。他比誰都急著想精進自己,希望仍能不斷學習,加上不想成為無趣之人,便會詢問書評家週三或週五若有空,是否願意賞光前往薩佛伊飯店 吃午餐,告訴他究竟為何他的小說寫得差?洛伊比誰都懂得點一整桌佳餚,等到書評家吃下半打生蠔、一塊羔羊排後,本來的話也就吞回肚裡了。而洛伊下一本小說問世時,該書評家看到了大幅的進步,自然屬於因緣果報的事
我發覺,凡是有人打電話找你,得知你不在就留言要你盡速回電、還說有重要的事,那件事多半對你沒那麼重要。若是要送你禮物或主動幫忙,一般人多半按捺得住自己的急性子。所以我回到住處,正打算抓緊時間喝一杯、抽根菸、讀讀報,再換衣服吃晚餐。聽到房東太太費羅斯女士說,歐洛伊.基爾先生請我馬上回電,便心想可以不予理會。
「是那位作家嗎?」房東太太問。
「是啊。」
她好意地瞥了電話一眼。
「要我回撥嗎?」
「沒關係,謝謝。」
「如果他又打來,我要說什麼?」
「請他留言吧。」
「好的,先生。」
她噘著嘴,拿起空咖啡壺、往房間掃視一遍,確定乾淨後便走了出去。費羅斯女士熱愛讀小說,想必已讀遍洛伊的小說。她對我隨便的態度很不以為然,可見很欣賞他的作品。後來我再度進門時,看見廚櫃上擺了一張紙條,上頭是費羅斯女士粗大清晰的字跡:
基爾先生又打了兩通電話,問你明天能否跟他共進午餐?如果不行,你哪天方便?
我不禁挑起眉,想想有三個月沒看到洛伊了,上次也僅在某場聚會上短暫一會。他十分和善,而且向來如此。道別時,他還對我倆甚少碰面大嘆可惜。
「真受不了倫敦,」他說:「老是沒時間見想見的朋友。要不要下星期找時間吃頓午飯呢?」
「當然好。」我回道。
「我回家看看記事本再打給你。」
「好啊。」
我認識洛伊二十年來,都曉得他老在西裝背心左上方口袋裡,放著一本記錄自己行程的小冊子。因此,後來他沒消沒息,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他這麼急著展現熱絡,我實在無法相信不是出於私心。就寢前,我抽著菸斗,腦袋裡推敲著洛伊找我吃午餐的可能原因。也許有位女性仰慕者纏著他,央求他介紹給我認識;也許有位美國編輯恰巧在倫敦待幾天,希望洛伊安排他跟我見面。不過,我可不能把這位老友看扁了,以為他沒法子應付這類情況。況且,他還叫我挑自己方便的日子,不太像是要我跟別人碰面。
洛伊有件事無人能出其右:對於當紅的同行小說家,他必定真誠地熱情以待,但當小說家的名聲被懶散、失敗或他人的光環蒙上陰影,他又懂得不失禮貌地疏遠。寫作生涯難免起起落落,我很清楚自己當時並未受到大眾矚目。我當然可以找些不得罪他的藉口加以婉拒,但這傢伙的態度堅決,假如出於私心打定主意要見我,除非我直接叫他「去死」,否則他絕對會繼續死纏爛打。不過,我實在忍不住好奇,況且我還滿喜歡洛伊的。
我曾滿懷欽佩地看他在文壇崛起。他的寫作生涯堪稱典範,可供有志從事文學創作的年輕人參考。同輩作家當中,我還真想不到有誰能像他一樣,才華無比淺薄卻能取得一席之地,就好比聰明如他每天吃的胚芽粉,可能頂多就堆滿一湯匙吧。他對此相當有自知之明,憑這點本事就寫成了將近三十本書,想必偶爾連他自己都覺得簡直是奇蹟。查爾斯.狄更斯在一場晚宴後的演說中提到,天才就是具有無窮無盡的吃苦工夫,我不禁揣想,洛伊初次讀到這句話時想必靈光乍現,加以反覆咀嚼。假使如此,他一定暗自以為,自己可以當個不亞於他人的天才。而當某女性刊物的書評興高采烈地在討論他一本作品的短評中,真的用上「天才」一詞(近來書評動輒就用),他勢必心滿意足地歎了口氣,宛如耗費數小時絞盡心思,終於完成了填字遊戲。凡是多年來看過他孜孜不倦的人,都得承認再怎麼說,他都配得上天才的稱號。
洛伊的生涯剛起步就有些優勢。他是家中獨子,父親多年在香港擔任輔政司,最後官拜牙買加總督退休。若你翻開密密麻麻的名人錄查找歐洛伊.基爾,便會看到以下文字:聖米迦勒暨聖喬治司令勳章與皇家維多利亞司令勳章得主雷蒙.基爾爵士(詳見該條目)獨生子,其母愛蜜莉為已故印度陸軍少將波西.康伯頓之次女。他先後於溫徹斯特與牛津新學院就讀,擔任學生會會長,要不是因為不幸罹患麻疹,很可能就成為划船隊一員。他的學業成績雖不到出類拔萃,卻也四平八穩,而且大學畢業時沒留下任何債務。早在當時,洛伊就已節儉度日,絲毫不想有無謂的開銷。他也是貼心的兒子,很清楚自己享有所費不貲的教育,全憑父母的犧牲。他父親退休後,住在格洛斯特郡斯特勞德鎮一間樸素卻不簡陋的房子裡。他不時會到倫敦出席跟他治理過殖民地相關的官方晚宴,也習慣順便造訪自己參與的文藝俱樂部。而洛伊從牛津畢業返家時,正是有賴父親在俱樂部的老友牽線,才得以獲派為某位政治人物的私人祕書。說到這位政治人物,他在保守黨兩度執政期間擔任內閣大臣時出盡洋相,好不容易才獲封爵位,年紀輕輕的洛伊因而有機會接觸上流社會。有些作家僅憑畫報刊物研究上層社交圈,導致寫出悖禮冒失的作品,但洛伊的書絕對找不到這類錯誤。他深諳公爵之間的言談辭令,也熟悉議員、律師、貼身男僕、賽馬投注商等身分對公爵說話時各自應有的禮數。他的早期小說中,描寫總督、大使、首相、王室和貴婦名媛的筆觸活潑,讀來頗令人著迷。文字友善卻不流露輕視,親暱卻不魯莽無禮。他不會讓你忘記筆下人物的身分地位,卻也不吝展現自己的自在,認為這些人同樣有血有肉。說來可惜,由於潮流改變,貴族的日常不再適合作為嚴肅小說的主題。對於時代趨勢向來敏銳的洛伊,後期小說主題都局限於律師、特許會計師與農產盤商的內心衝突,但他對這些圈子的掌握就不若以往。
我認識洛伊時,他剛辭去祕書一職不久,打算全心投入文學創作。當時的洛伊高大挺拔,未穿鞋身長便超過一百八十公分,擁有壯碩的體格與寬闊的雙肩,舉手投足散發自信。他並不俊朗,但有著順眼的陽剛氣息,與一對大大的清澈藍眼眸、一頭淡棕色鬈髮,鼻子短而寬,下巴方方正正,看起來老實、乾淨又健康,算是半個運動員。凡是讀過他早期作品中,與獵犬外出打獵時那生動又精準的描述,都不會懷疑他是寫自親身經歷。一直到不久前,他仍喜歡偶爾拋下伏案的工作,到野外打獵一整天。他出第一本小說時,文人雅士時興喝啤酒、打板球一展男子氣概,有好些年,文學圈內的板球隊幾乎都看得到洛伊。不知何故,這群人已不像過往那般無所畏懼,筆下作品也不再受重視,雖然依舊是打板球的夥伴,卻很難找到發表文章的管道。洛伊早已多年沒碰板球了,如今改對波爾多紅酒十分講究。
對於筆下首部小說,洛伊的態度極為謙虛,其篇幅短小、文字簡潔,樹立了日後作品的高尚格調。他把小說送給所有當時引領文壇的作家,隨書附上一封文情並茂的信,表達對他們莫大的仰慕、自己何以獲益良多,以及即使難以望其項背,仍熱烈企盼踏上前輩開創的道路。他畢恭畢敬地把書擺在文學巨擘跟前,宛如年輕後輩初入文壇時,向自己崇拜的大師致意。他十分清楚,要求大師在百忙之中,撥冗閱讀新人不成氣候的作品,毋寧是愚勇之舉,但依然低聲下氣,懇求前輩予以賜教提點。這些作家因為他的盛讚受寵若驚,多半洋洋灑灑地回信,鮮少敷衍了事,不僅大力稱許洛伊的書,許多人還邀請他參加午宴。他們無不欣賞洛伊直率的個性與暖心的熱情。他求教時總是十分謙虛,無比誠懇地答應會確實改進。眾前輩都覺得,眼前的小伙子值得費點心思指導。
洛伊的小說一炮而紅,因而在文學圈結交許多好友。不久後,凡是前往布魯姆斯伯里、坎普敦丘或西敏等地區出席茶會,必定會見到他分發奶油麵包給賓客,或忙著幫年長女士的空杯斟茶添水。他年輕、直爽又開朗,聽到有人講笑話總是開懷大笑,教人想不喜歡他都難。他會到維多利亞街或霍本的飯店地下室出席餐會,跟文人墨客、年輕律師,以及身穿利柏提百貨 絲衣、戴著珠寶項鍊的女士,吃頓三先令六便士的晚宴,暢談文學與藝術。旁人不久便發覺,洛伊格外擅長餐後高談闊論,而他為人實在討喜,其他作家、對手和同輩都待他寬容,甚至不介意他屬於仕紳階級。他們的作品往往備受他讚揚,寄手稿過去讓他評論,也總是得到毫無缺失的美譽。在他們看來,洛伊不僅好相處,更有不偏頗的眼光。
他寫了第二本小說,過程嘔心瀝血,並受惠於前輩提供的創作建議。好幾位前輩在洛伊請託下,寫了書評投稿到一家報紙,自然好話說盡,洛伊也事先聯絡了該報編輯。他第二本小說成功歸成功,卻不足以喚起競爭對手的危機意識,反倒證實了眾人的猜疑:他在倫敦絕對無法興起太大波瀾。他是性格爽朗的好人,並非搞小圈圈之流。既然他再怎麼往上爬也成不了絆腳石,前輩當然頗樂於提攜這位年輕人。我認識其中一些作家,反省起自己當初犯的錯,也只能面帶苦笑。
不過,說他自命不凡倒是他們的判斷錯誤。洛伊打從年輕開始,就保有謙虛這項最討喜的特質。
「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一流的小說家,」他老是這麼說:「跟那些文壇巨擘相比,我根本什麼都不是。以往,我都認為自己總有一天會寫出一本了不起的小說,但現在早就不抱這個奢望了。我只希望在別人眼中,自己凡事都盡力而為。我寫得很認真,任何粗心的錯誤絕對逃不過我的眼眸。我自認能把故事說好、創造出有血有肉的角色。到頭來,還是要看成果來見真章。《針眼》在英國賣了三萬五千本、在美國賣了八萬本。至於我下一部小說的連載版權,簽約金也打破自己的紀錄。」
即使是現在,洛伊依然會寫信給這些書評家,感謝他們的美言,同時邀請他們共進午餐,這難道不是謙虛的展現嗎?而且不僅如此。每當有人寫了篇措詞尖銳的批評,洛伊不得不忍受惡毒攻擊,尤其在自己聲譽卓著時,他不會像多數人一樣,內心咒罵著討厭自己作品的渾球,隨之拋諸腦後,反而會寫一封長信給那位書評家,除了對其不滿表達遺憾之意,還表示書評本身饒富興味,而且容他冒昧一句:評論精湛有理、文字情感真摯,所以非得寫信致意不可。他比誰都急著想精進自己,希望仍能不斷學習,加上不想成為無趣之人,便會詢問書評家週三或週五若有空,是否願意賞光前往薩佛伊飯店 吃午餐,告訴他究竟為何他的小說寫得差?洛伊比誰都懂得點一整桌佳餚,等到書評家吃下半打生蠔、一塊羔羊排後,本來的話也就吞回肚裡了。而洛伊下一本小說問世時,該書評家看到了大幅的進步,自然屬於因緣果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