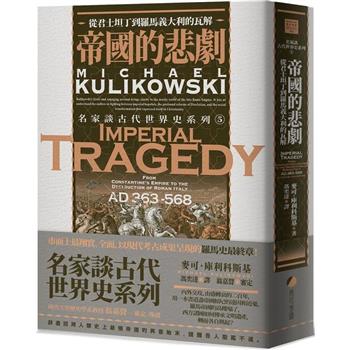第一章 締造君士坦丁帝國
西元三二四年,西奧古斯都君士坦丁徹底擊敗了他的妹婿,也是曾經的盟友、如今的死敵─東奧古斯都李錫尼(Licinius)。打了這場勝仗之後,君士坦丁就此成為羅馬帝國唯一的統治者。兩人從先前的一系列血腥內戰中倖存,我們所說的「四帝共治」便是隨著那些內戰而崩解。四帝共治制度是二九三年時,由皇帝戴克里先所創造的。西元三世紀期間,羅馬政治菁英與軍隊受到連續不斷的危機所苦。戴克里先想出四帝共治,是為了化解危機,而這個制度大體上是成功的。戴克里先深知,這麼一個西起大西洋,東至幼發拉底河,北起萊茵河、泰恩河(Tyne),南至撒哈拉沙漠的大帝國,光靠一個人是無法有效統治的。
戴克里先在先皇出征美索不達米亞、遭到暗殺時透過軍事政變奪權,接著在巴爾幹擊敗先皇的皇子,讓羅馬元老院勉為其難承認了他。當時的元老院徒餘象徵作用,幾無實權。這個紫袍加身的道路早已是三世紀的常態:對立的軍隊擁立自己的指揮官為皇帝,接著為了統治全帝國而戰。如此局面從二三○年代起反覆出現,其實有諸多原因。其一就是好幾個邊疆地帶出現了更強大的新敵人,尤其是萊茵河畔與萊茵河/多瑙河上游的新興蠻族聯盟(前者稱為「法蘭克人」[Franks],後者稱為「阿拉曼人」),以及波斯的新王朝(推翻了羅馬人知之甚詳的安息統治者)。
這個新王朝根據傳說中的始祖而稱為薩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相對於安息王朝來說,薩珊王朝的希臘化程度較低,也不為羅馬人所熟悉,而且更具攻擊性。薩珊王朝的「萬王之王」信奉二元論的瑣羅亞斯德宗教(Zoroastrianism),狂熱擁護其神職人員,而這種信仰為他們武力征服(尤其是羅馬帝國東部行省)的行動賦予一種使命感。三世紀時(尤其是今上遠在天邊的時候),外來威脅一再促成內部有人篡位─為了面對威脅,軍隊會擁立地方指揮官為皇帝。對於今上而言,篡位對於自己存續的威脅都遠勝過任何一種外敵入侵,因此安內的順序永遠先於攘外。結果,就是接連不斷的內戰。
話雖如此,羅馬統治階級的生存危機可不只是內戰肆虐。危機也跟社會與王朝轉型有關─內戰加速了轉變,但內戰本身並非轉變的起因。奧古斯都建立了羅馬帝國體系。頭一百年間,帝國的運作有賴於出身羅馬元老院的政務官。元老院本是舊共和國的統治機構,此時轉型為某種地方行政官員與軍事指揮官的孵化場,而元老院實質上也不再獨立於皇帝。隨著帝國中有愈來愈多人口得到羅馬公民權,這一批「元老階級」(ordo senatorius,羅馬人所謂的「階級」[ordine],是以其特權與責任來界定的,而非社會出身)也日漸膨脹。一旦地方社會得到政治權利,當地社會上層最富有的成員便有資格加入元老院。於是乎,我們先後看到來自高盧南部與西班牙南部、東部,來自希臘化世界的中心─希臘、愛琴海島嶼與小亞細亞,還有來自非洲和北方行省少數城鎮區的元老。
但是,無論元老院怎麼擴大,元老人數總是趕不上政務官必須進行的諸多任務:稅收、司法行政、維護公共建設、鎮壓土匪……諸如此類。皇帝自己的財富與直轄土地(並非羅馬政府公有的土地與財產)大幅擴張,意味著數十年來,內廷的奴隸與自由人早已包辦從產業管理到稅收的大小事。然而,羅馬統治階級的第二層─人稱「騎士階級」(ordo equester)─卻逐漸成為帝國行政的主幹。從二世紀到三世紀,帝國政府逐漸常態化、官僚化與職業化,絕大多數的管理職都由騎士階級出任。與此同時,軍隊的晉升制度也變得更有彈性,連出身行伍的人都有晉身騎士階級、成為軍官的機會。可以肯定,這類人到了三世紀中期已經把元老從大多數的指揮職中擠掉了。
等到戴克里先終結五十年的內戰後,舊的元老階層貴族已蕩然無存。四世紀時,甚至連備受敬重的古老家族,亦即出身羅馬城的那些家族,也只能把自家的祖譜回溯到三世紀的動盪年間(恐怕只有兩個家族例外)。從諸多方面而論,戴克里先可說是銳意改革,但這不包括他對統治階層的處理,元老與騎士階級之間仍然保有分野。改革得等到君士坦丁出現之後。君士坦丁深有體會,知道這兩個階級所發揮的功能,已經實質上毫無分野,於是將騎士階級與元老階級合併,並確保四世紀的元老階級貴族會跟帝國早期的前輩們大不相同。但除此之外,君士坦丁所繼承的多半仍是經過戴克里先從頭到腳重新形塑過的帝國,本書的劇情正是以這個背景為舞台。
二九○年代,戴克里先打破帝國早期的遼闊行省,將之化為上百個小行省,每一個行省都有一位行政長官,許多行省更設有某種軍事機構。他一以貫之的目的,在於讓任何潛在叛變者可以使用的資源大幅縮水,將部隊的指揮與補給、薪餉(annona)等職能區隔開來,從而減少有人篡位的可能性。戴克里先式行省的明證,是一份來自大約三一二年前後的政府文件,稱為〈維洛納清單〉(Laterculus Veronensis)。清單上列出帝國百餘個行省的名稱,每一個行省都有其行政長官。這些行政長官的頭銜不一─例如「資深執政官」(proconsul)、「執政官」(consularis)、「監察官」(corrector)─隨著四世紀演進,明確擁有影響力的階級體系也從各個行省之間浮現。資深執政官,統轄著阿非利加資深執政省(Africa Proconsularis,大致等於今日的突尼西亞)、亞細亞行省(Asia,今日土耳其西北角)以及亞該亞資深執政省(Achaea Proconsularis,希臘與愛琴海島嶼),因為自帝國誕生以來,這三個省份一直居於最重要的位置;其實在四世紀晚期,資深執政還會得到無須透過任何上級官員,就可直接向皇帝報告的法律特權。「執政官」與「監察官」頭銜與「資深執政官」不同,兩者的官職本身並沒有高下之分,但在人們心中,某些省份(尤其是那些隸屬帝國時間較久、都市化較深的地區)分量就是比較高。因此,擔任行政長官一職─比方說義大利南部的行政長官─也就成為未來仕途的良好指標。然而,無論頭銜為何,各種行政長官扮演的都是相同的角色:監督行省內的民政,亦即包括司法體系,以及行省對政府財政負有的各種義務。
百餘個行省的數量與邊界不時會重新安排,此外也構成更大的行政單位。這些行省群稱為「管區」(dioceses),相當穩定,從各方面來說都是構成四世紀政府的真正磚瓦。起先在戴克里先與共治皇帝的統治下,管區主要發揮的功能是財政,將特定稅官階級體系負責的幾個行省組合起來。君士坦丁進一步將管區治理制度化,由稱為「代巡官」(vicarii)、有權代表帝國裁判法律案件的官員主事。他的目標不只在讓司法管理趨於一致,更是為了確保行省與管區司法階層重重相疊,有重複彼此工作的可能性。這種重複審理,以及有意模糊誰來仲裁、誰應該做出仲裁的作法,旨在促成各種官員彼此監督─監視與告發,向來是遠在天邊的朝廷約束官員的好方法。
原本的戴克里先管區(參見地圖)基本上保持原狀,直到帝國在五世紀時開始瓦解為止,頂多只有君士坦丁在巴爾幹新成立兩個管區─將原有的單一管區一分為二,成為達契亞(Dacia)與馬其頓(Macedonia)。後來,瓦倫斯(Valens)讓埃及自己成為一個管區,從廣大的東方管區(Oriens,從亞美尼亞與托魯斯山脈[Taurus]到阿拉伯與巴勒斯坦)之中獨立出來。這兩個獨特管區的代巡官也有不同於人的頭銜─埃及代巡官稱為「奧古斯都長官」(praefectus Augustalis),而東方管區代巡官則是「東方伯」(comes Orientis)。大致上,這些管區是帝國政府最重要的層級、最大的轄區,能實際以單一財政單位的身分運作。儘管代巡官重要非常,但他們始終沒有獲得終審權,因為在他們之上還有晚期帝國政府最重要的民政官員─禁衛總長(praetorian prefects)。
晚期帝國的這些禁衛總長,是帝國奠基時一種官職的直系傳人。一開始,禁衛軍─駐守羅馬城的特別部隊─是由兩名總長指揮。但是,由於是騎士階級在政府中的最高官職,加上經常作為皇帝的代表,他們不久後便出現在政府的各個角落,行使職權。禁衛總長的職能在三世紀開始變化,而君士坦丁徹底結束了他們的軍事功能─一次內戰中,禁衛軍支持了對手,於是君士坦丁在內戰結束後鎮壓了禁衛軍。
四帝共治制度下,每個皇帝都有自己的禁衛總長,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君士坦丁讓孩子建立自己的副朝廷為止。總長的人數隨著副皇帝(「凱薩」)的人數而異,而他們始終是帝國政府中最強大的官員。他們可以代表皇帝做出終審判決,監督轄下管區歲入的出納,還能審理下級地方官的訴願。他們在財政上負有重責大任,因為他們負責「薪餉」─帝國民事官員與軍隊所有的薪水與配給。羅馬帝國的稅收有現金、有實物。無論處於哪一個階段,羅馬帝國都是一台將來自各省的稅收重新分配給軍隊與民政機構的機器(事實上,帝國晚期的拉丁語,都是用「militia」稱呼效力於軍事、民政階級體系的人)。私人物流網路乘上了公家薪餉網路的順風車─這是晚期帝國政府對於商業經濟運作至關重要的原因之一。總長除了控制龐大的財政機制,還要照顧帝國的基礎建設,維護公共郵政體系,並透過徵收現金、實物稅,或是徵用徭役(corvées,無薪水的勞動),來確保前述基礎建設之運作。
君士坦丁死於三三七年。此時,我們可以看出禁衛總長轄區(praetorian prefecture)已經成為實質行政區劃。到了君士坦丁之子統治的時代─尤其是三子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在三五○年成為合法皇帝之後,禁衛總長區劃更成為正式制度。屬於特定總長轄區的管區固然會隨時代而改變(由於內戰與外敵入侵之故,總長轄區所屬的管區在四世紀晚期與五世紀初期變化頻仍),但在西元三五○年時,已經浮現四個相對穩定的總長轄區:高盧總長轄區,通常從特雷維里管理,轄有不列顛(Britannia)、西班牙(Hispania)、「納博訥高盧」(Gallia Narbonensis,羅亞爾河以南的高盧),以及「三高盧」(Tres Galliae,羅亞爾河以北、萊茵河以西的高盧與日耳曼)等四個管區;義大利與阿非利加總長轄區,負責兩個義大利管區(羅馬以北的「糧倉義大利」[Italia Annonaria]與羅馬以南的「城郊義大利」[Italia Suburbicaria])、昔蘭尼(Cyrene)以西的阿非利加拉丁語區、阿爾卑斯山各省,有時候還包括潘諾尼亞(Pannonia,匈牙利、奧地利與部分的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伊利里亞(Illyricum),有時候跟義大利與阿非利加共同理政,轄有馬其頓、達契亞與潘諾尼亞;最後是東方總長區,掌管色雷斯(Thrace)、亞細亞納(Asiana,小亞細亞)、東方管區(托魯斯山脈、黎凡特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
由於地位優越,亞該亞、亞細亞與阿非利加資深執政省無須對各自的總長當局負責,但實際上仍需與總長在財政上合作。羅馬城由「都總長」(praefectus urbi)與薪餉總長(praefectus annonae)管轄,前者是個德高望重的元老階級職位,而後者則是跟禁衛總長有關的較低官職。君士坦丁的新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四世紀期間成為第二羅馬城,這座城市也不受色雷斯管轄─君士坦提烏斯在三五九年設立了獨立的君士坦丁堡總長。
每一名行政長官、代巡官與總長都有數十名左右手,人數有時甚至超過百人,但相較於帝國中央政府,他們仍只是一小撮人。御前的宮廷機構統稱為「御衛」(comitatus,字面意思是武裝衛隊),隨著皇帝在各個駐蹕處之間移動。內務職員稱為「侍寢」(cubicularii),以「御寢長」(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為首;幾乎所有的御寢長都是宦官,他們多半出身羅馬、波斯之間的邊境地區,因為禁止羅馬人去勢的禁令在此並不適用。他們監督宮內的大小事,照料皇帝與皇后最私密的需求,並管理統稱為「僕役」(ministeriales)或「宮人」(curae palatiorum)的教師、文書與僕人。
其他的御衛機構則處理皇帝的公共職能。在眾多機構主管中,最強大的就屬「執事長官」(magister officiorum),他轄下的各種「部門」(scrinia)必須照顧到皇帝的公開角色─他有三名次官,分別為「機要吏」(magister memoriae)、「監查吏」(magister libellorum)與「書信吏」(magister epistularum),處理皇帝的信件、收受對皇帝的請願、仲裁申訴案與地方官的「正式報告」(relationes),並起草回覆。為了外交,執事長官公署設有通譯團,而執事長官同時還控制帝國政府的密件體系,由大約千名「稽查使」(agentes in rebus)構成。這些稽查使以信差起家,但最後泰半成為高階間諜與殺手,安靜且迅速地完成所有政府都會幹的那種骯髒活。
執事長官大權在握的另一個證明,就是他身兼皇帝的親衛部隊─帕拉丁衛隊名義上的指揮官。這是羅馬晚期政府唯一握有兵權的民政官員。衛隊的每個「分隊」(schola,不同時代的數量仍有爭議)由五百名精銳騎兵組成,以皇帝親自任命的「軍政官」(tribunus)為首。皇帝從衛隊中挑選貼身侍衛,由於他們穿著白色制服,因而得名「白衣」(candidati)。另一個皇家機構─書記團(corps of notaries),其職能則與執事長官公署有所重複。「書記」(notarii)由「首席書記官」(primicerius notariorum)管理,他們記錄帝國由東到西、從南到北的官員派任,並為皇帝起草委任書。首席書記官負責維護所有帝國官職的「總清單」(laterculum maius)。理論上,書記官雖然只是文職人員,但他們和稽查使一樣,經常受到調任,執行間諜、審訊等不太光彩的祕密行動。
禁衛總長監管的金額,固然是流經政府體系中最大的一筆款項,但君士坦丁仍舊從戴克里先的政府改革中,繼承了兩個皇家財政機構,各自以一名「伯」(comes,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一為「官員」,一為「同伴」,此處為前者)為長官。「內庫」(res privata)監督五個不同的部門,處理皇帝各個方面的私產,從稅收、租金、買賣到沒入物一應俱全,而「內庫伯」(comes rei privatae)也是正皇帝的當然隨員。內庫職能如此,意味著在每一個行省都有大批內庫官員。御衛中的另一個財政機構是「廣財衛」(sacrae largitiones)。「廣財伯」(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主管帝國的鑄幣廠,最重要的鑄幣廠設於羅馬、特雷維里、亞雷拉特、斯爾米烏姆、塞爾迪卡、帖撒羅尼迦(Thessalonica)、安提阿與亞歷山卓(Alexandria)。
經過多年的財政不穩,君士坦丁以純度極高的金幣為基礎,重建了羅馬的貨幣體系。這種金幣重四點五公克,稱為「索幣」(solidus)。政府依舊鑄造銀幣與卑金屬錢幣,供小額交易使用,但它們跟索幣沒有固定的匯率,而帝國經濟體的財政面卻完全奠基在黃金上。廣財衛也經營政府的金、銀礦場,並監督那些為軍官武器與甲冑裝飾貴金屬的「兵工廠」(fabricae,製作無裝飾武備的兵工廠則由執事長官主理)。最後,各種以銀或金的形式所繳交的稅款,都會送到廣財衛─包括各種通行費與港口稅、「代役金」(aurum tironicum,以金幣來折抵兵役)、「加冕金」(aurum coronarium,皇帝登基以及每逢五週年紀念日時,各城鎮的「志願」捐獻)、「敬獻金」(aurum oblaticium,與加冕金同時間繳交,只是繳交的人為元老)、「土地稅」(collatio glebalis(元老繳交的年費),以及「清稅」(collatio lustralis,希臘語作「金銀稅」[chrysárgyron],是從商店主到妓女等各種生意人都要交的稅,每五年徵收一次。原本金、銀皆可上繳,後來只收金)。廣財伯管理的機構中有十個完整部門,而且和內庫一樣,除了中央御衛層級以外,也有各省層級的分支機構。在執事長官官署,以及執事長官領軍的帕拉丁衛隊之外,君士坦丁徹底把帝國的軍政與民政分離,將這股三世紀的勁流化為正式制度。野戰部隊(comitatenses)由數個大致千人的單位組成。許多行省(尤其是邊境)也有自己的駐軍,稱為「陸邊衛」(limitanei)或「河邊衛」(ripenses),許多駐衛軍都是從早期帝國的大型羅馬軍團演化而來的。野戰部隊由兩名將軍指揮,他們經常與皇帝御衛同行,因此稱為「御前軍長」(magistri militum praesentales)。主將稱為「御前步兵長」(magister peditum praesentalis),副將稱為「御前騎兵長」(magister equitum praesentalis),但其實兩人都會率領步兵與騎兵,平常也都統稱為「軍長」。假如同一時間有數名皇帝集體統治,則每一位皇帝的御衛中也會設有這些軍職,只不過隨著時間(以及區域性總長轄區的發展)也逐漸演變出野戰部隊的區域指揮官:除了上述御前軍長之外,四世紀中葉還發展出高盧軍長(magister per Gallias)、伊利里亞軍長(magister per Illyricum)與東方軍長(magister per Orientem)。他們或多或少是穩定的野戰部隊核心,而整個部隊的規模則視區域軍情而定。
邊境的常駐軍由「伯」(comites)或「公」(duces)指揮,他們轄有各種邊衛,只不過這些單位不時散布在整個行省,結果維護治安、收取關稅的時間和當兵的時間常常不相上下。除了上述野戰部隊與邊衛之外,還有一支禁軍,成員來自民政、軍政體系裡身分尊貴、關係良好的官員子嗣,以及邊境附庸國出身高貴的年輕人。這些士兵執行皇帝親自下達的軍事命令,而整個衛隊也成為各種背景的人所組成的儲備軍官團,構成了帝國晚期的軍官階級。禁軍由御衛的資深成員「禁軍伯」(comes domesticorum)指揮。(其他出身「一般」的衛隊由普通士兵組成,他們在職涯末期晉升,分配擔任管理職,通常位在遙遠的行省,作為多年服役的獎賞。)
後面的章節,我們將了解君士坦丁式的政府體制實際上如何運作,又如何劃定皇帝與子民「能與不能」的範圍,這裡只先稍微勾勒。不過,政府結構固然重要,卻不是君士坦丁再造帝國的唯一途徑。他還展開了讓帝國遵奉基督教的過程,不久後便無法逆轉。基督教原本是猶太教的異議教派,但到了二世紀,這些信徒認為自己信奉的是個新宗教,敬拜那一位「派自己兒子耶穌來救贖人類的好妒單一神」。基督教的發展起先局限於巴勒斯坦鄉下小社區與東部希臘語地區大城,但到了三世紀時已開枝散葉。這多少有點出人意料,畢竟以古代標準而論,基督教是個古怪的宗教。長久以來,希臘人與羅馬人都認為猶太人的排外一神教,以及拒絕接受羅馬官方神祇的態度,是一種反常的現象。他們之所以容忍猶太教,是因為這種宗教顯然是少數族群的信仰,走不出範圍有限的社群。不過,基督教的特出之處,在於信仰的效用,而非外顯的儀式。這一點不僅與猶太教不同,也異於希臘─羅馬世界的其他宗教。
西元三二四年,西奧古斯都君士坦丁徹底擊敗了他的妹婿,也是曾經的盟友、如今的死敵─東奧古斯都李錫尼(Licinius)。打了這場勝仗之後,君士坦丁就此成為羅馬帝國唯一的統治者。兩人從先前的一系列血腥內戰中倖存,我們所說的「四帝共治」便是隨著那些內戰而崩解。四帝共治制度是二九三年時,由皇帝戴克里先所創造的。西元三世紀期間,羅馬政治菁英與軍隊受到連續不斷的危機所苦。戴克里先想出四帝共治,是為了化解危機,而這個制度大體上是成功的。戴克里先深知,這麼一個西起大西洋,東至幼發拉底河,北起萊茵河、泰恩河(Tyne),南至撒哈拉沙漠的大帝國,光靠一個人是無法有效統治的。
戴克里先在先皇出征美索不達米亞、遭到暗殺時透過軍事政變奪權,接著在巴爾幹擊敗先皇的皇子,讓羅馬元老院勉為其難承認了他。當時的元老院徒餘象徵作用,幾無實權。這個紫袍加身的道路早已是三世紀的常態:對立的軍隊擁立自己的指揮官為皇帝,接著為了統治全帝國而戰。如此局面從二三○年代起反覆出現,其實有諸多原因。其一就是好幾個邊疆地帶出現了更強大的新敵人,尤其是萊茵河畔與萊茵河/多瑙河上游的新興蠻族聯盟(前者稱為「法蘭克人」[Franks],後者稱為「阿拉曼人」),以及波斯的新王朝(推翻了羅馬人知之甚詳的安息統治者)。
這個新王朝根據傳說中的始祖而稱為薩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相對於安息王朝來說,薩珊王朝的希臘化程度較低,也不為羅馬人所熟悉,而且更具攻擊性。薩珊王朝的「萬王之王」信奉二元論的瑣羅亞斯德宗教(Zoroastrianism),狂熱擁護其神職人員,而這種信仰為他們武力征服(尤其是羅馬帝國東部行省)的行動賦予一種使命感。三世紀時(尤其是今上遠在天邊的時候),外來威脅一再促成內部有人篡位─為了面對威脅,軍隊會擁立地方指揮官為皇帝。對於今上而言,篡位對於自己存續的威脅都遠勝過任何一種外敵入侵,因此安內的順序永遠先於攘外。結果,就是接連不斷的內戰。
話雖如此,羅馬統治階級的生存危機可不只是內戰肆虐。危機也跟社會與王朝轉型有關─內戰加速了轉變,但內戰本身並非轉變的起因。奧古斯都建立了羅馬帝國體系。頭一百年間,帝國的運作有賴於出身羅馬元老院的政務官。元老院本是舊共和國的統治機構,此時轉型為某種地方行政官員與軍事指揮官的孵化場,而元老院實質上也不再獨立於皇帝。隨著帝國中有愈來愈多人口得到羅馬公民權,這一批「元老階級」(ordo senatorius,羅馬人所謂的「階級」[ordine],是以其特權與責任來界定的,而非社會出身)也日漸膨脹。一旦地方社會得到政治權利,當地社會上層最富有的成員便有資格加入元老院。於是乎,我們先後看到來自高盧南部與西班牙南部、東部,來自希臘化世界的中心─希臘、愛琴海島嶼與小亞細亞,還有來自非洲和北方行省少數城鎮區的元老。
但是,無論元老院怎麼擴大,元老人數總是趕不上政務官必須進行的諸多任務:稅收、司法行政、維護公共建設、鎮壓土匪……諸如此類。皇帝自己的財富與直轄土地(並非羅馬政府公有的土地與財產)大幅擴張,意味著數十年來,內廷的奴隸與自由人早已包辦從產業管理到稅收的大小事。然而,羅馬統治階級的第二層─人稱「騎士階級」(ordo equester)─卻逐漸成為帝國行政的主幹。從二世紀到三世紀,帝國政府逐漸常態化、官僚化與職業化,絕大多數的管理職都由騎士階級出任。與此同時,軍隊的晉升制度也變得更有彈性,連出身行伍的人都有晉身騎士階級、成為軍官的機會。可以肯定,這類人到了三世紀中期已經把元老從大多數的指揮職中擠掉了。
等到戴克里先終結五十年的內戰後,舊的元老階層貴族已蕩然無存。四世紀時,甚至連備受敬重的古老家族,亦即出身羅馬城的那些家族,也只能把自家的祖譜回溯到三世紀的動盪年間(恐怕只有兩個家族例外)。從諸多方面而論,戴克里先可說是銳意改革,但這不包括他對統治階層的處理,元老與騎士階級之間仍然保有分野。改革得等到君士坦丁出現之後。君士坦丁深有體會,知道這兩個階級所發揮的功能,已經實質上毫無分野,於是將騎士階級與元老階級合併,並確保四世紀的元老階級貴族會跟帝國早期的前輩們大不相同。但除此之外,君士坦丁所繼承的多半仍是經過戴克里先從頭到腳重新形塑過的帝國,本書的劇情正是以這個背景為舞台。
二九○年代,戴克里先打破帝國早期的遼闊行省,將之化為上百個小行省,每一個行省都有一位行政長官,許多行省更設有某種軍事機構。他一以貫之的目的,在於讓任何潛在叛變者可以使用的資源大幅縮水,將部隊的指揮與補給、薪餉(annona)等職能區隔開來,從而減少有人篡位的可能性。戴克里先式行省的明證,是一份來自大約三一二年前後的政府文件,稱為〈維洛納清單〉(Laterculus Veronensis)。清單上列出帝國百餘個行省的名稱,每一個行省都有其行政長官。這些行政長官的頭銜不一─例如「資深執政官」(proconsul)、「執政官」(consularis)、「監察官」(corrector)─隨著四世紀演進,明確擁有影響力的階級體系也從各個行省之間浮現。資深執政官,統轄著阿非利加資深執政省(Africa Proconsularis,大致等於今日的突尼西亞)、亞細亞行省(Asia,今日土耳其西北角)以及亞該亞資深執政省(Achaea Proconsularis,希臘與愛琴海島嶼),因為自帝國誕生以來,這三個省份一直居於最重要的位置;其實在四世紀晚期,資深執政還會得到無須透過任何上級官員,就可直接向皇帝報告的法律特權。「執政官」與「監察官」頭銜與「資深執政官」不同,兩者的官職本身並沒有高下之分,但在人們心中,某些省份(尤其是那些隸屬帝國時間較久、都市化較深的地區)分量就是比較高。因此,擔任行政長官一職─比方說義大利南部的行政長官─也就成為未來仕途的良好指標。然而,無論頭銜為何,各種行政長官扮演的都是相同的角色:監督行省內的民政,亦即包括司法體系,以及行省對政府財政負有的各種義務。
百餘個行省的數量與邊界不時會重新安排,此外也構成更大的行政單位。這些行省群稱為「管區」(dioceses),相當穩定,從各方面來說都是構成四世紀政府的真正磚瓦。起先在戴克里先與共治皇帝的統治下,管區主要發揮的功能是財政,將特定稅官階級體系負責的幾個行省組合起來。君士坦丁進一步將管區治理制度化,由稱為「代巡官」(vicarii)、有權代表帝國裁判法律案件的官員主事。他的目標不只在讓司法管理趨於一致,更是為了確保行省與管區司法階層重重相疊,有重複彼此工作的可能性。這種重複審理,以及有意模糊誰來仲裁、誰應該做出仲裁的作法,旨在促成各種官員彼此監督─監視與告發,向來是遠在天邊的朝廷約束官員的好方法。
原本的戴克里先管區(參見地圖)基本上保持原狀,直到帝國在五世紀時開始瓦解為止,頂多只有君士坦丁在巴爾幹新成立兩個管區─將原有的單一管區一分為二,成為達契亞(Dacia)與馬其頓(Macedonia)。後來,瓦倫斯(Valens)讓埃及自己成為一個管區,從廣大的東方管區(Oriens,從亞美尼亞與托魯斯山脈[Taurus]到阿拉伯與巴勒斯坦)之中獨立出來。這兩個獨特管區的代巡官也有不同於人的頭銜─埃及代巡官稱為「奧古斯都長官」(praefectus Augustalis),而東方管區代巡官則是「東方伯」(comes Orientis)。大致上,這些管區是帝國政府最重要的層級、最大的轄區,能實際以單一財政單位的身分運作。儘管代巡官重要非常,但他們始終沒有獲得終審權,因為在他們之上還有晚期帝國政府最重要的民政官員─禁衛總長(praetorian prefects)。
晚期帝國的這些禁衛總長,是帝國奠基時一種官職的直系傳人。一開始,禁衛軍─駐守羅馬城的特別部隊─是由兩名總長指揮。但是,由於是騎士階級在政府中的最高官職,加上經常作為皇帝的代表,他們不久後便出現在政府的各個角落,行使職權。禁衛總長的職能在三世紀開始變化,而君士坦丁徹底結束了他們的軍事功能─一次內戰中,禁衛軍支持了對手,於是君士坦丁在內戰結束後鎮壓了禁衛軍。
四帝共治制度下,每個皇帝都有自己的禁衛總長,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君士坦丁讓孩子建立自己的副朝廷為止。總長的人數隨著副皇帝(「凱薩」)的人數而異,而他們始終是帝國政府中最強大的官員。他們可以代表皇帝做出終審判決,監督轄下管區歲入的出納,還能審理下級地方官的訴願。他們在財政上負有重責大任,因為他們負責「薪餉」─帝國民事官員與軍隊所有的薪水與配給。羅馬帝國的稅收有現金、有實物。無論處於哪一個階段,羅馬帝國都是一台將來自各省的稅收重新分配給軍隊與民政機構的機器(事實上,帝國晚期的拉丁語,都是用「militia」稱呼效力於軍事、民政階級體系的人)。私人物流網路乘上了公家薪餉網路的順風車─這是晚期帝國政府對於商業經濟運作至關重要的原因之一。總長除了控制龐大的財政機制,還要照顧帝國的基礎建設,維護公共郵政體系,並透過徵收現金、實物稅,或是徵用徭役(corvées,無薪水的勞動),來確保前述基礎建設之運作。
君士坦丁死於三三七年。此時,我們可以看出禁衛總長轄區(praetorian prefecture)已經成為實質行政區劃。到了君士坦丁之子統治的時代─尤其是三子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在三五○年成為合法皇帝之後,禁衛總長區劃更成為正式制度。屬於特定總長轄區的管區固然會隨時代而改變(由於內戰與外敵入侵之故,總長轄區所屬的管區在四世紀晚期與五世紀初期變化頻仍),但在西元三五○年時,已經浮現四個相對穩定的總長轄區:高盧總長轄區,通常從特雷維里管理,轄有不列顛(Britannia)、西班牙(Hispania)、「納博訥高盧」(Gallia Narbonensis,羅亞爾河以南的高盧),以及「三高盧」(Tres Galliae,羅亞爾河以北、萊茵河以西的高盧與日耳曼)等四個管區;義大利與阿非利加總長轄區,負責兩個義大利管區(羅馬以北的「糧倉義大利」[Italia Annonaria]與羅馬以南的「城郊義大利」[Italia Suburbicaria])、昔蘭尼(Cyrene)以西的阿非利加拉丁語區、阿爾卑斯山各省,有時候還包括潘諾尼亞(Pannonia,匈牙利、奧地利與部分的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伊利里亞(Illyricum),有時候跟義大利與阿非利加共同理政,轄有馬其頓、達契亞與潘諾尼亞;最後是東方總長區,掌管色雷斯(Thrace)、亞細亞納(Asiana,小亞細亞)、東方管區(托魯斯山脈、黎凡特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
由於地位優越,亞該亞、亞細亞與阿非利加資深執政省無須對各自的總長當局負責,但實際上仍需與總長在財政上合作。羅馬城由「都總長」(praefectus urbi)與薪餉總長(praefectus annonae)管轄,前者是個德高望重的元老階級職位,而後者則是跟禁衛總長有關的較低官職。君士坦丁的新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四世紀期間成為第二羅馬城,這座城市也不受色雷斯管轄─君士坦提烏斯在三五九年設立了獨立的君士坦丁堡總長。
每一名行政長官、代巡官與總長都有數十名左右手,人數有時甚至超過百人,但相較於帝國中央政府,他們仍只是一小撮人。御前的宮廷機構統稱為「御衛」(comitatus,字面意思是武裝衛隊),隨著皇帝在各個駐蹕處之間移動。內務職員稱為「侍寢」(cubicularii),以「御寢長」(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為首;幾乎所有的御寢長都是宦官,他們多半出身羅馬、波斯之間的邊境地區,因為禁止羅馬人去勢的禁令在此並不適用。他們監督宮內的大小事,照料皇帝與皇后最私密的需求,並管理統稱為「僕役」(ministeriales)或「宮人」(curae palatiorum)的教師、文書與僕人。
其他的御衛機構則處理皇帝的公共職能。在眾多機構主管中,最強大的就屬「執事長官」(magister officiorum),他轄下的各種「部門」(scrinia)必須照顧到皇帝的公開角色─他有三名次官,分別為「機要吏」(magister memoriae)、「監查吏」(magister libellorum)與「書信吏」(magister epistularum),處理皇帝的信件、收受對皇帝的請願、仲裁申訴案與地方官的「正式報告」(relationes),並起草回覆。為了外交,執事長官公署設有通譯團,而執事長官同時還控制帝國政府的密件體系,由大約千名「稽查使」(agentes in rebus)構成。這些稽查使以信差起家,但最後泰半成為高階間諜與殺手,安靜且迅速地完成所有政府都會幹的那種骯髒活。
執事長官大權在握的另一個證明,就是他身兼皇帝的親衛部隊─帕拉丁衛隊名義上的指揮官。這是羅馬晚期政府唯一握有兵權的民政官員。衛隊的每個「分隊」(schola,不同時代的數量仍有爭議)由五百名精銳騎兵組成,以皇帝親自任命的「軍政官」(tribunus)為首。皇帝從衛隊中挑選貼身侍衛,由於他們穿著白色制服,因而得名「白衣」(candidati)。另一個皇家機構─書記團(corps of notaries),其職能則與執事長官公署有所重複。「書記」(notarii)由「首席書記官」(primicerius notariorum)管理,他們記錄帝國由東到西、從南到北的官員派任,並為皇帝起草委任書。首席書記官負責維護所有帝國官職的「總清單」(laterculum maius)。理論上,書記官雖然只是文職人員,但他們和稽查使一樣,經常受到調任,執行間諜、審訊等不太光彩的祕密行動。
禁衛總長監管的金額,固然是流經政府體系中最大的一筆款項,但君士坦丁仍舊從戴克里先的政府改革中,繼承了兩個皇家財政機構,各自以一名「伯」(comes,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一為「官員」,一為「同伴」,此處為前者)為長官。「內庫」(res privata)監督五個不同的部門,處理皇帝各個方面的私產,從稅收、租金、買賣到沒入物一應俱全,而「內庫伯」(comes rei privatae)也是正皇帝的當然隨員。內庫職能如此,意味著在每一個行省都有大批內庫官員。御衛中的另一個財政機構是「廣財衛」(sacrae largitiones)。「廣財伯」(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主管帝國的鑄幣廠,最重要的鑄幣廠設於羅馬、特雷維里、亞雷拉特、斯爾米烏姆、塞爾迪卡、帖撒羅尼迦(Thessalonica)、安提阿與亞歷山卓(Alexandria)。
經過多年的財政不穩,君士坦丁以純度極高的金幣為基礎,重建了羅馬的貨幣體系。這種金幣重四點五公克,稱為「索幣」(solidus)。政府依舊鑄造銀幣與卑金屬錢幣,供小額交易使用,但它們跟索幣沒有固定的匯率,而帝國經濟體的財政面卻完全奠基在黃金上。廣財衛也經營政府的金、銀礦場,並監督那些為軍官武器與甲冑裝飾貴金屬的「兵工廠」(fabricae,製作無裝飾武備的兵工廠則由執事長官主理)。最後,各種以銀或金的形式所繳交的稅款,都會送到廣財衛─包括各種通行費與港口稅、「代役金」(aurum tironicum,以金幣來折抵兵役)、「加冕金」(aurum coronarium,皇帝登基以及每逢五週年紀念日時,各城鎮的「志願」捐獻)、「敬獻金」(aurum oblaticium,與加冕金同時間繳交,只是繳交的人為元老)、「土地稅」(collatio glebalis(元老繳交的年費),以及「清稅」(collatio lustralis,希臘語作「金銀稅」[chrysárgyron],是從商店主到妓女等各種生意人都要交的稅,每五年徵收一次。原本金、銀皆可上繳,後來只收金)。廣財伯管理的機構中有十個完整部門,而且和內庫一樣,除了中央御衛層級以外,也有各省層級的分支機構。在執事長官官署,以及執事長官領軍的帕拉丁衛隊之外,君士坦丁徹底把帝國的軍政與民政分離,將這股三世紀的勁流化為正式制度。野戰部隊(comitatenses)由數個大致千人的單位組成。許多行省(尤其是邊境)也有自己的駐軍,稱為「陸邊衛」(limitanei)或「河邊衛」(ripenses),許多駐衛軍都是從早期帝國的大型羅馬軍團演化而來的。野戰部隊由兩名將軍指揮,他們經常與皇帝御衛同行,因此稱為「御前軍長」(magistri militum praesentales)。主將稱為「御前步兵長」(magister peditum praesentalis),副將稱為「御前騎兵長」(magister equitum praesentalis),但其實兩人都會率領步兵與騎兵,平常也都統稱為「軍長」。假如同一時間有數名皇帝集體統治,則每一位皇帝的御衛中也會設有這些軍職,只不過隨著時間(以及區域性總長轄區的發展)也逐漸演變出野戰部隊的區域指揮官:除了上述御前軍長之外,四世紀中葉還發展出高盧軍長(magister per Gallias)、伊利里亞軍長(magister per Illyricum)與東方軍長(magister per Orientem)。他們或多或少是穩定的野戰部隊核心,而整個部隊的規模則視區域軍情而定。
邊境的常駐軍由「伯」(comites)或「公」(duces)指揮,他們轄有各種邊衛,只不過這些單位不時散布在整個行省,結果維護治安、收取關稅的時間和當兵的時間常常不相上下。除了上述野戰部隊與邊衛之外,還有一支禁軍,成員來自民政、軍政體系裡身分尊貴、關係良好的官員子嗣,以及邊境附庸國出身高貴的年輕人。這些士兵執行皇帝親自下達的軍事命令,而整個衛隊也成為各種背景的人所組成的儲備軍官團,構成了帝國晚期的軍官階級。禁軍由御衛的資深成員「禁軍伯」(comes domesticorum)指揮。(其他出身「一般」的衛隊由普通士兵組成,他們在職涯末期晉升,分配擔任管理職,通常位在遙遠的行省,作為多年服役的獎賞。)
後面的章節,我們將了解君士坦丁式的政府體制實際上如何運作,又如何劃定皇帝與子民「能與不能」的範圍,這裡只先稍微勾勒。不過,政府結構固然重要,卻不是君士坦丁再造帝國的唯一途徑。他還展開了讓帝國遵奉基督教的過程,不久後便無法逆轉。基督教原本是猶太教的異議教派,但到了二世紀,這些信徒認為自己信奉的是個新宗教,敬拜那一位「派自己兒子耶穌來救贖人類的好妒單一神」。基督教的發展起先局限於巴勒斯坦鄉下小社區與東部希臘語地區大城,但到了三世紀時已開枝散葉。這多少有點出人意料,畢竟以古代標準而論,基督教是個古怪的宗教。長久以來,希臘人與羅馬人都認為猶太人的排外一神教,以及拒絕接受羅馬官方神祇的態度,是一種反常的現象。他們之所以容忍猶太教,是因為這種宗教顯然是少數族群的信仰,走不出範圍有限的社群。不過,基督教的特出之處,在於信仰的效用,而非外顯的儀式。這一點不僅與猶太教不同,也異於希臘─羅馬世界的其他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