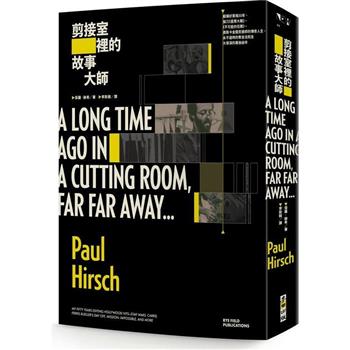自序|坐在剪接室裡的五十年
一九七五年,我負責剪接布萊恩.狄帕瑪執導的《迷情記》。那是一部獨立電影,由於劇情過於前衛,拍完後好萊塢沒有一家電影公司願意發行。經過幾番思量,我提議修改片中某個畫面,將原本廣角拍攝豪宅的建立鏡頭,改成主角的特寫。更換這個鏡頭之後,哥倫比亞影業才同意發行。這就是剪接發揮功用之處。
我在電影產業工作了五十年,參與過的作品有些極為成功,有些非常失敗。我剪過史上最賣座的電影,也剪過票房慘澹的作品,但是我不得不承認:不管怎麼說,我的人生實在很精采。這本書的宗旨,是與大家分享我在電影產業工作的經驗,以及一些個人意見,還有我從相識者及共事過的卓越人士身上所學到的點點滴滴。
想想看,全世界最大牌的電影明星、最具權力的製片人、最有才華的劇作家、導演和攝影師,齊聚在好萊塢最富歷史的電影公司,一同打造出一部電影。他們投入數億美元,將電影行銷到世界各地。有時候,光是一部電影的工作人員就超過一千人。製作團隊耗費數星期甚至數月的時間精心籌備、建造場景、設計服裝及進行場勘。接下來,再花更多時間拍攝,通常是在天寒地凍或炙熱難耐的天候下進行拍攝,也可能在陰雨綿綿、白雪紛飛,或者在深夜時分。工作人員往往不眠不休,只能窩在帳篷裡用餐,而且通常一天得工作十二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演員在拍攝前幾個小時就得到場,以便按照電影裡要求的模樣梳化。將這些投入的時間、金錢、創意和體力結合在一起,就能製造出剪接師可以運用的素材。我是一個剪接師,剪接師是電影團隊中最棒的工作。
◎「剪接」這份工作
「剪接」這種職稱其實並不正確,如同人們把可以隨身攜帶的「口袋型電腦」稱為「電話」一樣,撥打電話只是其中一項功能,剪接也不過是剪接師的職責之一。擔任剪接師的我們會花很多時間進行「初剪」。初剪就像拿到一個裝滿各種小零件的大箱子,我們必須把這些小零件組裝起來。然而大箱子裡除了等待組裝的零件之外,還有很多沒用的廢物。我們必須篩選每天拍攝的所有畫面,尋找並擷取各種可用的角度或鏡位,然後將這些片段剪接成愈來愈長的段落。有時候,這些有用的片段就像句子,有時候又像片語或個別的單字,甚至音節,組合在一起時所產生的意義可能遠大於各個片段獨自存在時。鏡頭的意義來自其前後脈絡,脈絡就是一切。雖然你可以把一部悲劇電影最讓人感動的片段剪接進一部浮誇的喜劇中,但是看起來會非常荒謬。我們必須謹慎選擇,才能架構出最好的片段。瀏覽毛片就像尋寶一樣,一旦我們挖到寶了,就必須使其發揮最大功效。畫面的銜接非常重要,剪接藝術的一環,就是讓每個鏡頭在一連串影像中充分發揮潛力。
初剪不僅僅要把「不好的東西」剪掉,更重要的是,要把一段段動作和聲音拼貼起來。每位剪接師選擇的片段及排列的方式都不相同,因此大家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等到所有場次都拍攝完畢、每個畫面都放進初剪版之後,後製階段的剪接才能真正開始。著手剪接給觀眾看的最終版,是電影剪接過程中最有趣也最關鍵的階段。這個過程必須與導演共事,所以會因為合作對象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把初剪版交給導演時總是令人緊張,尤其在雙方第一次合作時。與新導演合作有點類似跟沒見過面的陌生人初次約會,你可以先與導演見面會談,並且從其他剪接師的經驗預作功課,但等到你們正式開始合作,準備把初剪版變成電影成品時,就是關鍵時刻了。對導演而言,篩選初剪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會擔心自己的想法與大家的努力,究竟能不能變成一部好作品?我從我的第一部電影學到:無論每個段落剪接得多出色,都不代表整部電影一定會成功。儘管如此,篩選初剪仍是極其重要的時刻,正如導演赫伯特.羅斯曾說過的:「你只有一次機會第一次看一部電影。」
剪接師和導演會互相影響。剪接師是導演的第一個觀眾,拍攝過程中的任何錯誤,我們都能夠從銀幕上看見。對於身為剪接師的我們而言,導演是我們唯一的真正觀眾,只有導演明白我們所做的各種選擇,而且不會被其他人的鑑賞能力所左右。因此,導演和剪接師之間的創意聯繫可以說非常緊密。在理想的狀況下,雙方在情感上能夠相互支持。
每一部電影都是由手工打造,不是機械量產,因此剪接師的創作風格對電影有強大的影響力。然而在電影製作文化中,剪接師的作品在導演觀賞且加以修改之前,沒有任何人看得見,所以有時候剪接師會被當成導演的助理。不過,由於科技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再有這種保密傳統。要製作一部充滿複雜特效的電影,大批工作人員必須很早就看到電影的全貌,而且各種嶄新的技術也使得分享電影內容變得更容易。
常有人問我,我在工作時有多少權限。實際情況是,人們聘請我為同一場戲做出各式各樣的選擇。就像演員一樣,演員在同一個場景中可能必須重演十次,而且每次要有不同的演法,但最後只有一種演法能獲得導演的認可,被使用在電影中,另外九種都不會被選上。我每天必須做出幾十種甚至幾百種選擇—最後當然必須交給導演審核,然而這並不表示我的選擇都會被導演否決。每當我看見電影播映的畫面就是我的初剪版時,心裡會非常開心,因為這表示導演認為初剪版的畫面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不可能修改得更好。就像一九七○年代的電視劇《歡樂時光》,裡面有個角色叫馮茲,他總是拿著梳子檢視鏡中的自己,最終決定把梳子收起來,因為他看起來已經十足完美。
◎電影幻象如何誕生?
剪接是電影製作中唯一沒有扎根於早期藝術形式的工作職位。劇本創作和演員的表演都源自劇場藝術,製作設計(production design)的前身也源自於劇場,服裝和妝髮亦同。攝影則是從繪畫轉變而來,但透過連續的影像和聲音說故事,是電影製作這門藝術的本質。雖然圖畫書與電影剪接多少有點關聯,但如果拿一本靜態的書與電影剪接的動態性相比,差異就如同牛車遇上太空梭。
我們稱之為「電影」的幻象,全憑靠人類的感知與一組生理和心理現象。這組現象之一是「飛現象」(phi phenomenon),一種視覺上的假象,最早於一九一二年由格式塔心理學創始人之一的馬克斯.韋特墨提出。當一個物體出現在某個位置,接著又出現在第二個位置時,觀看者會認為該物體從第一個位置移動到第二個位置。電影是由一幅幅靜止的畫面組成,每秒鐘顯現二十四格畫面,因此圖像中的物體位移,會產生運動感。第二種現象是「視覺暫留」(persistence of vision)。當我們眼前的圖像突然發生變化時,原本的圖像會短暫停留在我們的視網膜上。閉上眼睛的那一瞬間,你會看見剛才一直注視著的物體殘影。前述兩種生理及心理現象結合之後,就能打造出營收高達數十億美元的電影產業。
除了連續播放靜止圖像而產生物體移動的假象之外,電影剪接還立足於另一種錯覺之上:透過剪接所接合的各種動作,其發生順序與時間會被認為與視覺上所看見的相同。假設我們有一段這樣的畫面—先是一個特寫鏡頭:一位帥氣的猛男深情款款地凝視著;再接一個特寫鏡頭:一位美麗的女子回望男人的目光;最後是一個雙人鏡頭:猛男與美女接吻。看了這段影像,觀眾無法知悉,其實接吻鏡頭可能是先拍好的,接著才拍攝猛男的特寫,然後劇組休息吃午飯,最後再回來拍美女的特寫。這個過程可能要花費好幾個小時,取決於導演在每個角度要拍攝幾次,以及每個鏡頭重新打光的複雜度。但是我們會暫時拋開懷疑,深信事情發展的順序就如同我們在電影銀幕上看見的那樣。這種時間軸的重建,讓電影充滿魔法,也讓我的工作令人著迷。
我偶爾會去拍片現場,看見一群群劇組人員。他們雖然在現場觀看,可是能看到的其實不多,除非是準備炸毀一棟建築物或者準備執行大型特技的工作人員。人們在拍攝現場觀看,是因為他們想要與電影魔法再靠近一點。然而真正的魔法並不在拍片現場,唯有在剪接師將兩段影片結合為一、讓它們看起來像是一個畫面牽引著另外一個畫面時,或者用蒙太奇手法剪接連續影像、因而產生出如詩詞般令人感動的效果時,魔法才會出現。
為了解釋剪接的意義,人們經常將它描述為「宛如」其他形式的藝術。就某種意義而言,剪接像黏土雕刻,因為可以添加或減少其內容。剪接也像建築,因為必須建立在一定的基石之上,才能打造出視覺方面的結構,而且必須注意美觀、比例與平衡。剪接也像編舞,只不過剪接不是在特定時間於三度空間裡編排律動,而是在二度空間的平面上作業,並且不是依靠音樂來形塑律動,而是靠對話。剪接亦好比寫作,重新排列鏡頭的順序可使之產生全新的意義。有人說:剪接是劇本的最終改寫;還有人說:一部電影可以拍三次:一次在劇本裡,一次在拍攝中,一次在剪接時。
剪接就像上述的各種藝術,可是它也獨一無二。繪畫呈現在觀眾眼前時是一個完整樣貌。當我們在美術館或畫廊中,朝著一幅畫慢慢走近時,我們會先看見整幅畫作,但隨著我們距離那幅畫愈來愈近,我們才能漸漸看到細節。我們在欣賞這些細節的同時,藝術家只能施展局部的控制力:我們可以從畫作的頂部開始看,也可以從底部開始看,或者從任何吸引我們目光的構圖著眼。在欣賞一座雕塑品時,我們可以繞著作品而走,從不同角度觀看,以便了解它的全貌。建築設計會以更為循序漸進的方式展現。我們會先看見建築物的外觀,然後從不同路徑欣賞建築物的內部結構,等到我們在腦中重建這些觀察體驗時,才能夠「看見」整棟建築。關於我們體驗建築物細節的順序,建築師只能施展有限的控制。
文學以不同的方式向讀者展現內容—讀者必須遵循作者所建立的路徑。有別於前述的視覺藝術,文學的細節展現完全依照作者選擇的順序,作者以經過深思熟慮的方式透露訊息,唯有在完成作者預先決定的旅程之後,我們才能掌握作品的全部內容。
音樂也與文學相似,可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我們在聆聽音樂的過程中,連速度也是被決定好的。一本書可以一口氣讀完,也可以花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時間閱讀。音樂以一種受到控制的速度呈現給聽眾,這點與電影最為相似。電影製作團隊不僅要考慮以什麼樣的順序提供資訊,還必須考慮在什麼時間點、用什麼速度提供資訊。
◎視覺藝術的核心
電影已經成為現代最卓越的視覺藝術,因為它同時結合許多種類型的藝術。它展現出畫家最關注的美麗生動圖像;它說出揭露角色內在和洞察人類處境的故事;它控制了將圖像傳達給觀眾的速度,依照電影的需求而減緩或加快。它運用所有的電影技術,不僅要觸及觀眾的眼睛和耳朵,還要打動他們的心。
從最早期的電影開始,電影語言就持續演變。無聲電影的創作者以精巧或詩意的視覺來克服他們所受的限制;有聲電影的出現,反而使以視覺敘事的手法倒退,然而這些年來導演們已經找到新鮮刺激的拍攝方式。現在觀眾可以接受時間碎片化(例如以倒敘法和順敘法說故事)、不同現實的交替出現(例如夢境與回憶)、時間的壓縮或拉長(例如慢動作或時間流逝,甚至在單一鏡頭中變換季節)。剪接的步調也可以變得瘋狂,讓觀眾努力跟上情節。
剪接是電影創造魔法的核心。在幽暗的剪接室裡,我們把劇組在攝影棚內精心拍攝的影像轉化為愛情故事、太空冒險、懸疑驚悚、搞笑喜劇、銀河之旅、史前時代或遙遠未來。剪接非常有趣,或者說,剪接可以非常有趣,取決於你為誰工作。
第一個剪接出來的完整版本,也被稱為「剪接師版」,但我比較喜歡將它稱為「初剪版」。對我而言,「剪接師版」意味著這個版本代表著剪接師認為這部電影應該如何呈現。但實際上,初剪版裡完整包含所有場次,而且通常是依照編劇最初安排的順序。很多時候,這其實並不是最理想的順序。更常發生的是,有些場次或者某一場戲的其中一部分,在最後完成的電影中應該予以刪除。有人問我如何判別一部電影是否剪接得宜,這並不容易。有時候我在電影中的最大貢獻就是剪掉整整一場,唯有如此,整部電影才會更為流暢,或者營造出更加神祕緊張的氛圍。正如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藝術家米開朗基羅所說的:「除去多餘就是美。」
電影剪接得如何,會真實反映在作品完成後的整體感。找出多餘的部分,並選擇如何組合處理剩下的部分,會讓一部電影產生「好」和「極佳」的差異。因為要負責將畫面剪接在一起,我們必須比別人擁有更敏銳的感覺。真正的剪接師版會反映出我們認為這部電影應該是什麼樣子,而且剪接師版可能會與初剪版有很大的差異。儘管如此,一開始先保留全部素材還是最明智的做法。只要手邊有全部的素材,導演和剪接師就能夠加以修剪和重組,直到完成最終的版本。
在實務上,初剪版很難令人滿意,無論剪接師如何努力將它剪得精采。偶爾會有劇本寫得完美、拍攝過程也十分順利的情況,這時就可以在拍攝工作結束後不久便「鎖定」整部電影的內容—不再做出改變。要完成一部電影,或者任何形式的藝術作品,其中一項關鍵就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手。
一九七五年,我負責剪接布萊恩.狄帕瑪執導的《迷情記》。那是一部獨立電影,由於劇情過於前衛,拍完後好萊塢沒有一家電影公司願意發行。經過幾番思量,我提議修改片中某個畫面,將原本廣角拍攝豪宅的建立鏡頭,改成主角的特寫。更換這個鏡頭之後,哥倫比亞影業才同意發行。這就是剪接發揮功用之處。
我在電影產業工作了五十年,參與過的作品有些極為成功,有些非常失敗。我剪過史上最賣座的電影,也剪過票房慘澹的作品,但是我不得不承認:不管怎麼說,我的人生實在很精采。這本書的宗旨,是與大家分享我在電影產業工作的經驗,以及一些個人意見,還有我從相識者及共事過的卓越人士身上所學到的點點滴滴。
想想看,全世界最大牌的電影明星、最具權力的製片人、最有才華的劇作家、導演和攝影師,齊聚在好萊塢最富歷史的電影公司,一同打造出一部電影。他們投入數億美元,將電影行銷到世界各地。有時候,光是一部電影的工作人員就超過一千人。製作團隊耗費數星期甚至數月的時間精心籌備、建造場景、設計服裝及進行場勘。接下來,再花更多時間拍攝,通常是在天寒地凍或炙熱難耐的天候下進行拍攝,也可能在陰雨綿綿、白雪紛飛,或者在深夜時分。工作人員往往不眠不休,只能窩在帳篷裡用餐,而且通常一天得工作十二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演員在拍攝前幾個小時就得到場,以便按照電影裡要求的模樣梳化。將這些投入的時間、金錢、創意和體力結合在一起,就能製造出剪接師可以運用的素材。我是一個剪接師,剪接師是電影團隊中最棒的工作。
◎「剪接」這份工作
「剪接」這種職稱其實並不正確,如同人們把可以隨身攜帶的「口袋型電腦」稱為「電話」一樣,撥打電話只是其中一項功能,剪接也不過是剪接師的職責之一。擔任剪接師的我們會花很多時間進行「初剪」。初剪就像拿到一個裝滿各種小零件的大箱子,我們必須把這些小零件組裝起來。然而大箱子裡除了等待組裝的零件之外,還有很多沒用的廢物。我們必須篩選每天拍攝的所有畫面,尋找並擷取各種可用的角度或鏡位,然後將這些片段剪接成愈來愈長的段落。有時候,這些有用的片段就像句子,有時候又像片語或個別的單字,甚至音節,組合在一起時所產生的意義可能遠大於各個片段獨自存在時。鏡頭的意義來自其前後脈絡,脈絡就是一切。雖然你可以把一部悲劇電影最讓人感動的片段剪接進一部浮誇的喜劇中,但是看起來會非常荒謬。我們必須謹慎選擇,才能架構出最好的片段。瀏覽毛片就像尋寶一樣,一旦我們挖到寶了,就必須使其發揮最大功效。畫面的銜接非常重要,剪接藝術的一環,就是讓每個鏡頭在一連串影像中充分發揮潛力。
初剪不僅僅要把「不好的東西」剪掉,更重要的是,要把一段段動作和聲音拼貼起來。每位剪接師選擇的片段及排列的方式都不相同,因此大家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等到所有場次都拍攝完畢、每個畫面都放進初剪版之後,後製階段的剪接才能真正開始。著手剪接給觀眾看的最終版,是電影剪接過程中最有趣也最關鍵的階段。這個過程必須與導演共事,所以會因為合作對象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把初剪版交給導演時總是令人緊張,尤其在雙方第一次合作時。與新導演合作有點類似跟沒見過面的陌生人初次約會,你可以先與導演見面會談,並且從其他剪接師的經驗預作功課,但等到你們正式開始合作,準備把初剪版變成電影成品時,就是關鍵時刻了。對導演而言,篩選初剪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會擔心自己的想法與大家的努力,究竟能不能變成一部好作品?我從我的第一部電影學到:無論每個段落剪接得多出色,都不代表整部電影一定會成功。儘管如此,篩選初剪仍是極其重要的時刻,正如導演赫伯特.羅斯曾說過的:「你只有一次機會第一次看一部電影。」
剪接師和導演會互相影響。剪接師是導演的第一個觀眾,拍攝過程中的任何錯誤,我們都能夠從銀幕上看見。對於身為剪接師的我們而言,導演是我們唯一的真正觀眾,只有導演明白我們所做的各種選擇,而且不會被其他人的鑑賞能力所左右。因此,導演和剪接師之間的創意聯繫可以說非常緊密。在理想的狀況下,雙方在情感上能夠相互支持。
每一部電影都是由手工打造,不是機械量產,因此剪接師的創作風格對電影有強大的影響力。然而在電影製作文化中,剪接師的作品在導演觀賞且加以修改之前,沒有任何人看得見,所以有時候剪接師會被當成導演的助理。不過,由於科技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再有這種保密傳統。要製作一部充滿複雜特效的電影,大批工作人員必須很早就看到電影的全貌,而且各種嶄新的技術也使得分享電影內容變得更容易。
常有人問我,我在工作時有多少權限。實際情況是,人們聘請我為同一場戲做出各式各樣的選擇。就像演員一樣,演員在同一個場景中可能必須重演十次,而且每次要有不同的演法,但最後只有一種演法能獲得導演的認可,被使用在電影中,另外九種都不會被選上。我每天必須做出幾十種甚至幾百種選擇—最後當然必須交給導演審核,然而這並不表示我的選擇都會被導演否決。每當我看見電影播映的畫面就是我的初剪版時,心裡會非常開心,因為這表示導演認為初剪版的畫面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不可能修改得更好。就像一九七○年代的電視劇《歡樂時光》,裡面有個角色叫馮茲,他總是拿著梳子檢視鏡中的自己,最終決定把梳子收起來,因為他看起來已經十足完美。
◎電影幻象如何誕生?
剪接是電影製作中唯一沒有扎根於早期藝術形式的工作職位。劇本創作和演員的表演都源自劇場藝術,製作設計(production design)的前身也源自於劇場,服裝和妝髮亦同。攝影則是從繪畫轉變而來,但透過連續的影像和聲音說故事,是電影製作這門藝術的本質。雖然圖畫書與電影剪接多少有點關聯,但如果拿一本靜態的書與電影剪接的動態性相比,差異就如同牛車遇上太空梭。
我們稱之為「電影」的幻象,全憑靠人類的感知與一組生理和心理現象。這組現象之一是「飛現象」(phi phenomenon),一種視覺上的假象,最早於一九一二年由格式塔心理學創始人之一的馬克斯.韋特墨提出。當一個物體出現在某個位置,接著又出現在第二個位置時,觀看者會認為該物體從第一個位置移動到第二個位置。電影是由一幅幅靜止的畫面組成,每秒鐘顯現二十四格畫面,因此圖像中的物體位移,會產生運動感。第二種現象是「視覺暫留」(persistence of vision)。當我們眼前的圖像突然發生變化時,原本的圖像會短暫停留在我們的視網膜上。閉上眼睛的那一瞬間,你會看見剛才一直注視著的物體殘影。前述兩種生理及心理現象結合之後,就能打造出營收高達數十億美元的電影產業。
除了連續播放靜止圖像而產生物體移動的假象之外,電影剪接還立足於另一種錯覺之上:透過剪接所接合的各種動作,其發生順序與時間會被認為與視覺上所看見的相同。假設我們有一段這樣的畫面—先是一個特寫鏡頭:一位帥氣的猛男深情款款地凝視著;再接一個特寫鏡頭:一位美麗的女子回望男人的目光;最後是一個雙人鏡頭:猛男與美女接吻。看了這段影像,觀眾無法知悉,其實接吻鏡頭可能是先拍好的,接著才拍攝猛男的特寫,然後劇組休息吃午飯,最後再回來拍美女的特寫。這個過程可能要花費好幾個小時,取決於導演在每個角度要拍攝幾次,以及每個鏡頭重新打光的複雜度。但是我們會暫時拋開懷疑,深信事情發展的順序就如同我們在電影銀幕上看見的那樣。這種時間軸的重建,讓電影充滿魔法,也讓我的工作令人著迷。
我偶爾會去拍片現場,看見一群群劇組人員。他們雖然在現場觀看,可是能看到的其實不多,除非是準備炸毀一棟建築物或者準備執行大型特技的工作人員。人們在拍攝現場觀看,是因為他們想要與電影魔法再靠近一點。然而真正的魔法並不在拍片現場,唯有在剪接師將兩段影片結合為一、讓它們看起來像是一個畫面牽引著另外一個畫面時,或者用蒙太奇手法剪接連續影像、因而產生出如詩詞般令人感動的效果時,魔法才會出現。
為了解釋剪接的意義,人們經常將它描述為「宛如」其他形式的藝術。就某種意義而言,剪接像黏土雕刻,因為可以添加或減少其內容。剪接也像建築,因為必須建立在一定的基石之上,才能打造出視覺方面的結構,而且必須注意美觀、比例與平衡。剪接也像編舞,只不過剪接不是在特定時間於三度空間裡編排律動,而是在二度空間的平面上作業,並且不是依靠音樂來形塑律動,而是靠對話。剪接亦好比寫作,重新排列鏡頭的順序可使之產生全新的意義。有人說:剪接是劇本的最終改寫;還有人說:一部電影可以拍三次:一次在劇本裡,一次在拍攝中,一次在剪接時。
剪接就像上述的各種藝術,可是它也獨一無二。繪畫呈現在觀眾眼前時是一個完整樣貌。當我們在美術館或畫廊中,朝著一幅畫慢慢走近時,我們會先看見整幅畫作,但隨著我們距離那幅畫愈來愈近,我們才能漸漸看到細節。我們在欣賞這些細節的同時,藝術家只能施展局部的控制力:我們可以從畫作的頂部開始看,也可以從底部開始看,或者從任何吸引我們目光的構圖著眼。在欣賞一座雕塑品時,我們可以繞著作品而走,從不同角度觀看,以便了解它的全貌。建築設計會以更為循序漸進的方式展現。我們會先看見建築物的外觀,然後從不同路徑欣賞建築物的內部結構,等到我們在腦中重建這些觀察體驗時,才能夠「看見」整棟建築。關於我們體驗建築物細節的順序,建築師只能施展有限的控制。
文學以不同的方式向讀者展現內容—讀者必須遵循作者所建立的路徑。有別於前述的視覺藝術,文學的細節展現完全依照作者選擇的順序,作者以經過深思熟慮的方式透露訊息,唯有在完成作者預先決定的旅程之後,我們才能掌握作品的全部內容。
音樂也與文學相似,可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我們在聆聽音樂的過程中,連速度也是被決定好的。一本書可以一口氣讀完,也可以花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時間閱讀。音樂以一種受到控制的速度呈現給聽眾,這點與電影最為相似。電影製作團隊不僅要考慮以什麼樣的順序提供資訊,還必須考慮在什麼時間點、用什麼速度提供資訊。
◎視覺藝術的核心
電影已經成為現代最卓越的視覺藝術,因為它同時結合許多種類型的藝術。它展現出畫家最關注的美麗生動圖像;它說出揭露角色內在和洞察人類處境的故事;它控制了將圖像傳達給觀眾的速度,依照電影的需求而減緩或加快。它運用所有的電影技術,不僅要觸及觀眾的眼睛和耳朵,還要打動他們的心。
從最早期的電影開始,電影語言就持續演變。無聲電影的創作者以精巧或詩意的視覺來克服他們所受的限制;有聲電影的出現,反而使以視覺敘事的手法倒退,然而這些年來導演們已經找到新鮮刺激的拍攝方式。現在觀眾可以接受時間碎片化(例如以倒敘法和順敘法說故事)、不同現實的交替出現(例如夢境與回憶)、時間的壓縮或拉長(例如慢動作或時間流逝,甚至在單一鏡頭中變換季節)。剪接的步調也可以變得瘋狂,讓觀眾努力跟上情節。
剪接是電影創造魔法的核心。在幽暗的剪接室裡,我們把劇組在攝影棚內精心拍攝的影像轉化為愛情故事、太空冒險、懸疑驚悚、搞笑喜劇、銀河之旅、史前時代或遙遠未來。剪接非常有趣,或者說,剪接可以非常有趣,取決於你為誰工作。
第一個剪接出來的完整版本,也被稱為「剪接師版」,但我比較喜歡將它稱為「初剪版」。對我而言,「剪接師版」意味著這個版本代表著剪接師認為這部電影應該如何呈現。但實際上,初剪版裡完整包含所有場次,而且通常是依照編劇最初安排的順序。很多時候,這其實並不是最理想的順序。更常發生的是,有些場次或者某一場戲的其中一部分,在最後完成的電影中應該予以刪除。有人問我如何判別一部電影是否剪接得宜,這並不容易。有時候我在電影中的最大貢獻就是剪掉整整一場,唯有如此,整部電影才會更為流暢,或者營造出更加神祕緊張的氛圍。正如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藝術家米開朗基羅所說的:「除去多餘就是美。」
電影剪接得如何,會真實反映在作品完成後的整體感。找出多餘的部分,並選擇如何組合處理剩下的部分,會讓一部電影產生「好」和「極佳」的差異。因為要負責將畫面剪接在一起,我們必須比別人擁有更敏銳的感覺。真正的剪接師版會反映出我們認為這部電影應該是什麼樣子,而且剪接師版可能會與初剪版有很大的差異。儘管如此,一開始先保留全部素材還是最明智的做法。只要手邊有全部的素材,導演和剪接師就能夠加以修剪和重組,直到完成最終的版本。
在實務上,初剪版很難令人滿意,無論剪接師如何努力將它剪得精采。偶爾會有劇本寫得完美、拍攝過程也十分順利的情況,這時就可以在拍攝工作結束後不久便「鎖定」整部電影的內容—不再做出改變。要完成一部電影,或者任何形式的藝術作品,其中一項關鍵就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手。